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间主题
编者按
时间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主题。单纯歌颂美貌以及友谊和爱情并非这部作品的本意,在十四行诗集中,无论是美还是友谊和爱情,都受到时间的制约。莎士比亚力图通过对艺术、爱情等超越时间之物的探寻,来超越人的生命隶属于时间的被动地位。因此,面对时间的惶恐,与时间妥协和抗衡但又无法摆脱时间的无情吞噬,是导致莎士比亚在创作中思想和情绪从乐观自信向悲观乃至失望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
吴笛,1954年12月生,发表此文时为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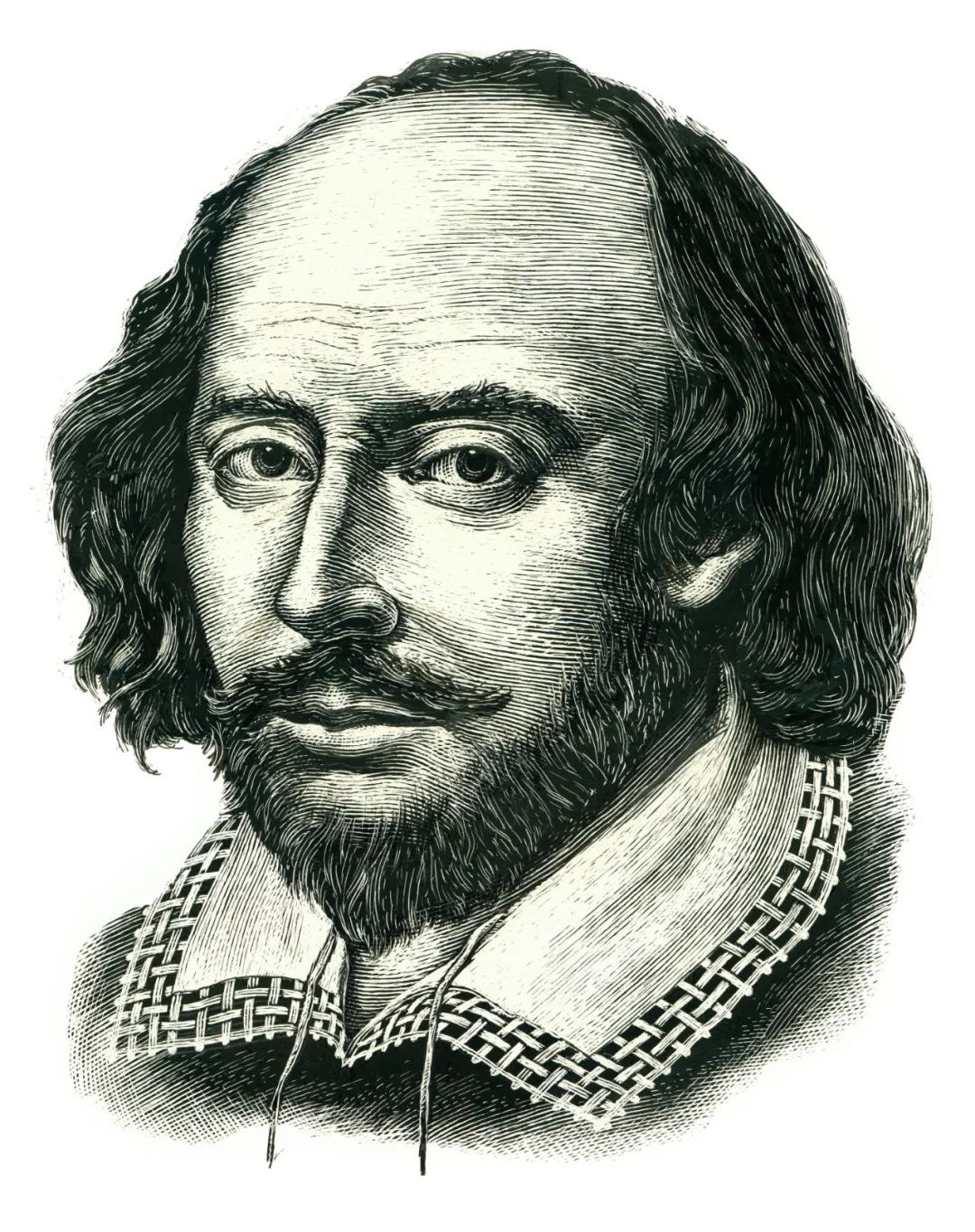
莎士比亚像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作者思想和艺术高度凝练的结晶,历来受人重视,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研究十四行诗的论著,其数量仅次于《哈姆莱特》。关于这部诗集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歌颂真善美以及友谊和爱情,从而表现人文主义思想。也有专家认为“《十四行诗集》按内容可以分为三类:歌颂美的诗,以友谊为题的诗,以爱情为题的诗”。[1] 国外的学者大多也持这种观点,一些教材甚至把这部诗集当成“爱情十四行诗”来看待。
但这种观点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如果我们能够结合莎士比亚整个的创作生涯来研究,也许会得出比较客观的评价。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创作于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正是他的戏剧创作从喜剧向悲剧过渡的时期。而十四行诗集所反映的情绪恰恰是从乐观向悲观乃至失望的转变。导致这种情绪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这一概念。
笔者认为,在莎士比亚这部十四行诗集中,无论是美,还是友谊和爱情,都因受到时间的无情吞噬而弥漫着强烈的悲观情调。在这部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与时间抗衡和妥协的思想以及面对时间而表现出的茫然和困惑。这种困惑正是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人文主义者对时代感到困惑的一个反映。
美和艺术与时间的妥协和抗衡
时间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一个很受关注的对象。“Time”这个词语在诗集中出现过79次,而且大多是以大写字母出现的。另有hour,week,day,month,season,winter,spring等多种表示时间概念的词语频繁出现在诗集中,如出现“day”出现46处,“hour”出现16处,“winter”出现10处。可见,时间是我们探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我们先从歌颂真善美这一传统观点入手。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主题是歌颂真善美,其主要依据是莎士比亚第105首诗中的陈述:

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
真,善,美,变化成不同的辞章;
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里,
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2]

但仅从以上流行的译文中难以看出问题。我们不妨核查一下英文原文:

‘Fair,kind and true’ is all my argument,
‘Fair,kind,and true’ varying to other words;
And in this change is my invention spent,
Three themes in one,which wondrous scope affords.

可见,这里的“主题”是译自英语的“Argument”一词。然而,“Argument”就文学作品而言,是泛指的情节和内容,这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基本原则是相一致的,即主张“形式之美”以及“人物和事件的真实”。[3] 因此,这里说的是艺术主张,并非主题。而且,“Argument”在严格意义上是争论、讨论之意,也就是说,即使是指主题,那也并非歌颂它们,而是讨论这些话题。这样,不妨理解为讨论这些话题在时间长河中的变幻以及与时间的冲撞。诗集开头部分写给年青友人的诗,也主要是想规劝年青友人通过成婚把自己的美在后代身上保存下来,从而与时间抗衡,避免时间对美的扼杀。
诗人在开头的十多首诗中,主要想通过劝婚与时间妥协,以及通过艺术与时间抗衡。

波提切利《春》中的美惠三女神
在第1首中,诗人歌颂了友人难以比拟的美:

你现在是大地的清新的点缀,
又是锦绣阳春的惟一的前锋……[4]

诗人接着在第2首诗中认为只有通过结婚,繁衍后代,才能战胜时光,重焕青春:

这将使你在衰老的暮年更生,
并使你垂冷的血液感到重温。

在第5首中,莎士比亚以极其具有表现力的形象化语句直接表达了时间的恐怖和对美的残忍的摧残。诗人写道:

那些时辰曾经用轻盈的细工
织就这众目共注的可爱明眸,
终有天对它摆出魔王的面孔,
把绝代佳丽剁成龙钟的老丑:
因为不舍昼夜的时光把盛夏
带到狰狞的冬天去把它结果;
生机被严霜窒息,绿叶又全下,
白雪掩埋了美,满目是赤裸裸:
那时候如果夏天尚未经提炼,
让它凝成香露锁在玻璃瓶里,
美和美的流泽将一起被截断,
美,和美的记忆都无人再提起:
但提炼过的花,纵和冬天抗衡,
只失掉颜色,却永远吐着清芬。

在这首“4442”结构的十四行诗中,诗人以前面的“起、承、转”三个部分的十二个诗行来描述时间这一“魔王”的恐怖以及对人生和自然的盲目作用。而最后两行的“合”,尽管是以“提炼”的形式与时间进行了抗衡,但这种抗衡的思想相对显得苍白无力。他必须寻找新的抗争方式。
所以,在第15首诗中,诗人不再指望靠友人以结婚的方式来与时间抗衡了,而是决心要用自己的诗篇来记录男性青年的美,与时间抗衡。诗的最后两句写道:

为了对你的爱我与时间交战,
它把你夺走,我把你重新嫁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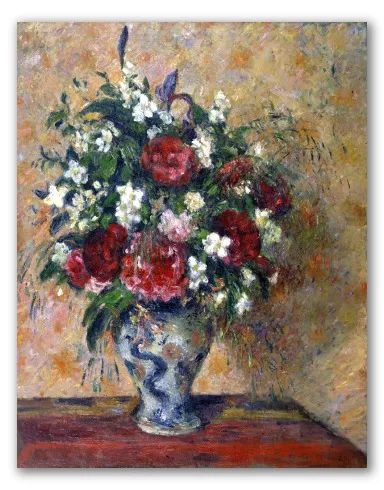
《芍药和山梅花》卡米耶·毕沙罗
可是,第16首笔锋一转,说无论是诗还是画都不能使美永存,抵抗时间最好的办法还是生儿育女,这比枯燥的诗要好得多。经过一番犹豫,诗人终于认识到,对待时间这样的顽敌,仅靠诗歌也是不够的,得联合起来进行抗争。所以在第17首诗中,诗人提出既靠繁衍后代,又靠诗歌创作来使美丽得以永存,从而获得双重的生命:

但那时你若有个儿子来到了人世,
你就活两次:在他身上,在我诗里。

第18首是表达艺术与时间抗衡这一思想的代表性的诗篇。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说,该诗的主题是表达“唯有文学可以同时间抗衡;文学既是人所创造的业绩,因此这里又是宣告了人的伟大与不朽”。[5] 这样,该诗就具有了明显的人文主义思想。

被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没有芳艳不终于雕残或销毁。
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雕落,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诗中可以感受到对爱的信念,正是相信这种爱,使得他的诗能够永恒,而诗歌又使情人的美得以永恒。不过,这种永恒到了诗集的后部分,仍然反复受到怀疑。如在第65首中,诗人在歌颂美的时候,也哀叹美的短暂、美的脆弱,认为“她的活力比一朵花还柔脆”。在第104首诗中,诗人觉得所谓美的常驻,不过是自己的眼睛被迷惑而已。所以美也像时针一样,它蹑着脚步移过钟面,悄然而逝。因此,他在该诗的结尾写道:“颤栗吧,未来的时代,听我呼吁:/你还没有生,美的夏天已死去。”
友谊与爱情的“时间”审视
诚然,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中确有一些歌颂友谊和爱情的作品,但是,由于“莎士比亚(十四行中)所讲述的故事轮廓是清晰的,细节却是朦胧的”[6], 所以,我们同时也应在清晰的爱情叙事中看到潜在的悲剧情绪。实际上,随着作品的展开,爱情和友谊便受到了“时光”的无情吞噬,抒情的主人公只是在消极地及时行乐,尽管有的论者认为莎士比亚不会写及时行乐这类主题。[7]
其实,莎士比亚不同于同时代的诗人,不像他们那样歌颂“爱的永恒”,或像约翰·多恩那样认为爱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8] 他的这部十四行诗集中的友谊和爱情的线索是处于发展和变换之中的,并且在时间的支配下,在思想感情和气氛上造成一种一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无论是对男性青年的友谊还是对“黑肤女郎”的爱情,都主要是为了突出时间的残酷和无情。所以,到了诗集的最后部分,即第146-152首,随着时间的流逝,诗人遇到的是友谊和爱情的双重背叛。他似乎完全陷入绝望,在失恋的痛苦中挣扎,同时万般悔恨自己有眼无珠,错爱一场。可见,莎士比亚描写爱情,主要是悲叹爱情短促易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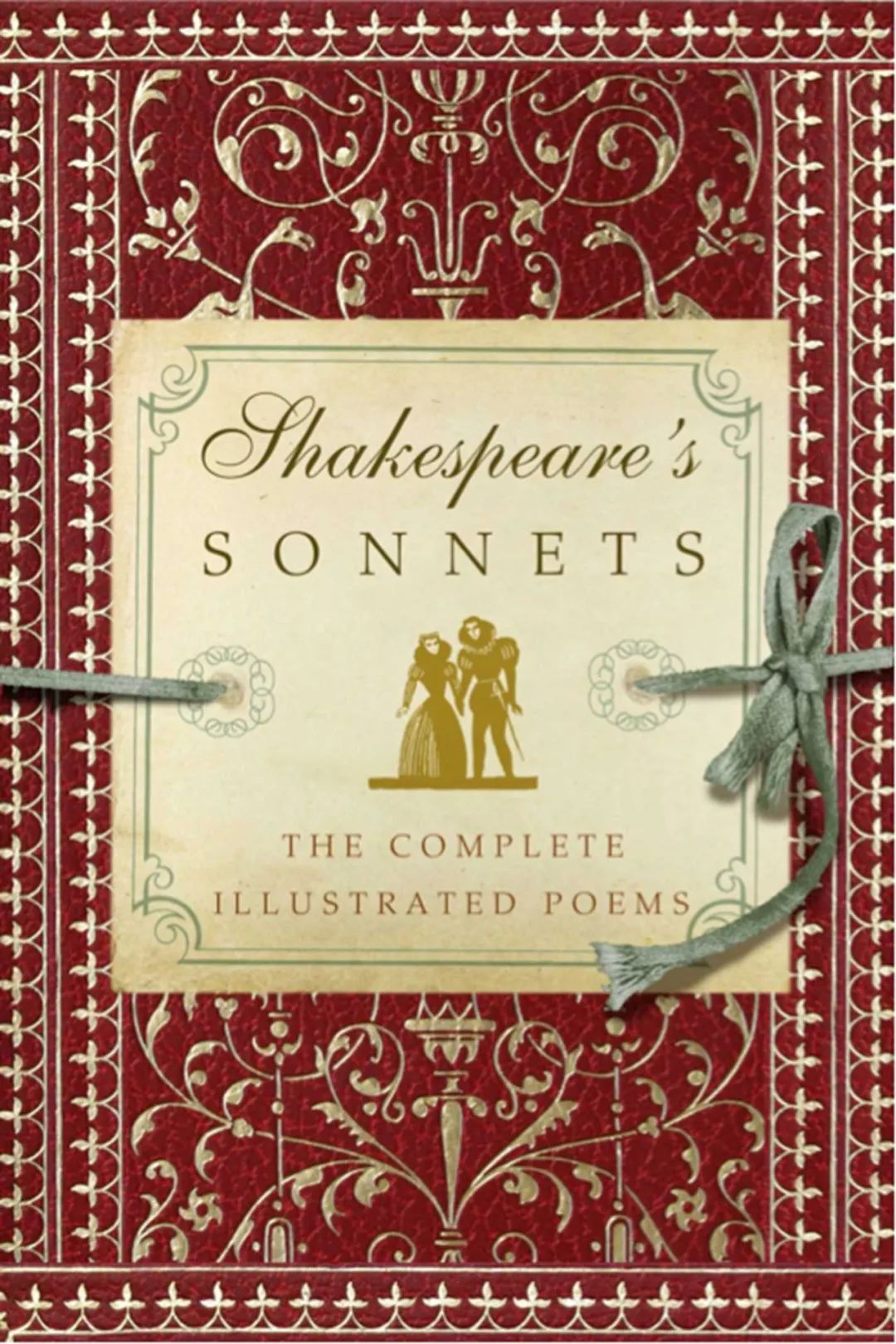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封面
但是,主张爱情主题论的学者总是以著名的第116首为依据,坚持认为莎士比亚在这一首诗中提出了爱是“两颗真心的结合”,把爱情“提高到了崇高的境界”。然而,应该看到,莎士比亚在此即使是歌颂爱情,他也是以时间为参照物的,他甚至勇敢自信地以爱情来向时间挑战,而且一反常态,以爱情的永恒来对照具体时间的短暂和无常。

我绝不承认两颗真心的结合
会有任何障碍;爱算不得真爱,
若是一看见人家改变便转舵,
或者一看见人家转弯便离开。
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塔灯,
它定睛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
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恒星,
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
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
和皓齿难免遭受时光的毒手;
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
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
我这话若说错,并被证明不确,
就算我没写诗,也没人真爱过。

如果结合其它诗篇,就可以看出,在爱情与时间关系上,莎士比亚“爱不受时光的播弄”的思想与其他的诗句有着明显的矛盾。从上下文中我们看到,该诗与前三首和后四首共同构成一组,讨论爱情。前三首是讨论爱情怎样既欺骗了眼睛又欺骗了心灵,后四首则是力图为爱的不忠和背叛寻找理由。
此外,我们还应考察此处“时光”的确切含义。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时间是具有双重含义的,时间是间断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既是有始有终的直线时间,又是无始无终的连续系列。[9] 爱所战胜的显然只是指能以日月星体的运转所测量的直线时间,而最终仍然难逃厄运。
尽管他在这首诗中宣称“爱不受时光的播弄”,但这也仅仅是作为一种理想,该诗所处的上下文已经对此作出了解释。而且就该诗的基调而言,也有一种潜在的感伤成分,诗人在强调不要见异思迁时,却在句首用“Let me not…admit…”(让我不要承认……)这样的话语,这实际上包含着对这种现象的哀叹,说明了理想的爱情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整部诗集的结构更是对这一理想予以了否定,因为如上所述,面对时间的“播弄”,诗人最后所遭受的是男性青年的友谊和“黑肤女郎”的爱情对他的双重背叛。
时间主题的悲剧意识
一般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分为喜剧、悲剧、传奇剧三个创作阶段,这一观点较为客观,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可。既然如此,那么创作于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十四行诗集,就应该是莎士比亚从喜剧向悲剧过渡时期的创作。抒情诗创作不同于戏剧,常常是作者个人经历和心灵历程的记录,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作品都更能展现作者本人的思想情绪。
从莎士比亚这部诗集所表现的时间主题来看,可以深刻地探究出诗人的悲观情绪。莎士比亚诗中所表现的时间经常是直线的向前无情运动的时间,而不是神话意义上的周而复始、循环运动的时间,这体现了作者对时间悲观的看法。我们仅从措辞方面便可感受莎士比亚的这种悲观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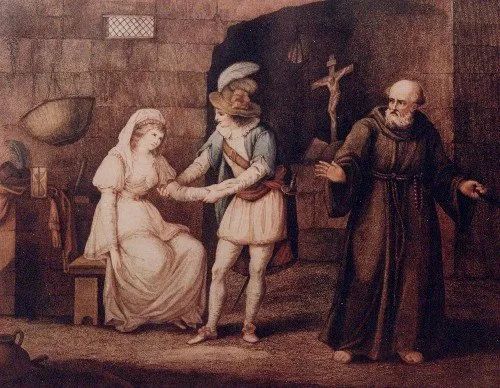
《罗密欧、朱丽叶和劳伦斯神父》班伯里
如上所述,莎士比亚在诗集中频繁使用了“time”这一词语,而且常常用多种拟人化的形容词来修饰它,使之形象生动逼真。
用来修饰“time”的形容词有“never-resting”(从不停止的)(第5首)、“devouring”(吞食的)(第19首)、“swift-footed”(脚步迅疾的)(第19首)、“sluttish”(淫荡的)(第55首)、“injurious”(不公正的)(第63首)、“balmy”(芳香的)(第107首)、“reckoning”(精打细算的)(第115首)、“inviting”(引人动心的)(第124首)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以时间作所有格而与之连用的名词:如“Time's pencil”(时间之笔)、“Time's furrows”(时间皱纹)、“Time's tyranny”(时间暴君)、“Time's chest”(时间之胸)、“Time's fickle glass”(时间的无常的沙漏)、“Time's injurious hand”(时间的毒手)、“Time's fell hand”(时间的无情的手掌)、“Time's scythe”(时间的镰刀)等等。这类名词的使用使“时间魔王”这一可怖的形象显得更为具体、栩栩如生。尤其是“scythe”或“sickle”这一意象,在第12、60、100、116、123、126首诗中多次出现。那么,为什么镰刀这一意象反复出现呢?这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有关。“镰刀一直作为克洛诺斯的象征物,他被看成了古希腊之前的丰产之神。后来人们混淆了他和时间的化身克洛诺斯的名字,于是克洛诺斯手执着镰刀(或长柄大镰刀),以提醒人们时间的无情流逝。”[10] 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诗人一样,把时间与克洛诺斯的可怕形象融合在一起是为了“强调时间的破坏作用”[11]。

《克洛诺斯与厄洛斯》阿基莫夫
这一挥镰割草的“时间魔王”的形象在第60首诗中最具典型性。在该首诗中,诗人写道:

像波浪滔滔不息地滚向沙滩:
我们的光阴息息奔赴着终点;
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换,
前推后拥,一个个在奋勇争先。
生辰,一度涌现于光明的金海,
爬行到壮年,然后,既登上极顶,
凶冥的日蚀便遮没它的光彩,
时光又撕毁了它从前的赠品。
时光戳破了青春颊上的光艳,
在美的前额挖下深陷的战壕,
自然的至珍都被它肆意狂喊,
一切挺立的都难逃它的镰刀……

在这一首诗中,割草的镰刀典型地说明了时间的残忍和恐怖。镰刀是恐怖的时间的象征,那么,被割的草在此处则是人的肉体的象征。诗人在此强调,一切挺立的东西都难逃时间镰刀的割除,这充分说明了时间的强大以及人的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渺小和不堪一击,也充分表现了莎士比亚时间观方面的强烈的悲剧意识。
莎士比亚的时间主题的悲剧意识在第73首诗中表现得最为强烈: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秋天,
当黄叶,或尽脱,或只三三两两
挂在瑟缩的枯枝上索索抖颤——
荒废的歌坛,那里百鸟曾合唱。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暮霭,
它在日落后向西方徐徐消退:
黑夜,死的化身,渐渐把它赶开,
严静的安息笼住纷纭的万类。
在我身上你或许全看见余烬,
它在青春的寒灰里奄奄一息,
在惨淡灵床上早晚总要断魂,
给那滋养过它的烈焰所销毁。
看见了这些,你的爱就会加强,
因为他转瞬要辞你溘然长往。

作者在该诗中尽情流露自己的悲观情绪,诗人甚至感到生命已进入黄昏(尽管诗人创作这首诗时才不过三十来岁),犹如在寒风中瑟瑟颤抖的几片黄叶,又如日落西山时的黄昏,或一团奄奄一息的、只剩下灰烬的火焰。因此,他恳求他的爱友能看出这一切,并企求对方加强对诗人的爱。这一恳求,使全诗的基调显得更为凄凉。

《莎士比亚和他的家人》皮里尼
综上所述,时间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主题。单纯歌颂友谊和爱情或歌颂真善美并非莎士比亚这部作品的本意。在这部十四行诗集中,无论是美还是友谊和爱情,都受到时间的制约。莎士比亚力图通过对艺术、爱情等可以超越时间之物的探寻,来超越人的生命隶属于时间的被动地位,尽管他的这种探求只能加深他的困惑。我们考察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时间主题,既能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他戏剧创作从喜剧向悲剧转换的理解,同时也更能加深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世界观的理解,尤其能加深我们对人文主义者强调现时生活意义的理解。莎士比亚与时间妥协和抗衡,但又无法摆脱时间的无情吞噬,其中表现出来的大胆揭露的精神和悲观的情绪,使他的诗作超越了时空,有了普遍的意义,成了“时代的灵魂”,从而“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12]
全文完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本公号发表的文章,版权归《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内外一体
文史一家
扫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