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或马克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重建
本文原刊于《文化与诗学》2021年第2期,感谢程巍研究员授权。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注释和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程巍
文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长期从事英美文学-文化史及当代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研究,兼及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史。
康德或马克思: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重建
摘要:
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学重建体现为一种“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本体论”,而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为此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资源和理论支撑。本文的目标是从《文学理论》一书自身在美国的“发生史”来勾勒美国中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右派保守主义与东海岸地区的左派激进主义之间的一种对抗关系,以史料来揭示以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为其理论集大成的美国新批评与美国右派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政治同盟,从而证明美国新批评的文学理论自身就是一种高度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一种“党派评论”。
关键词:
20世纪80年代 文艺学 内部研究
在中国文艺学领域,80年代像一个幽灵,不仅一直徘徊在我们的经过美学净化的回忆中,也一直在干预着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实践,有时,我们自己可能就是80年代的借尸还魂。8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思想解放”的时刻,这尤其体现于文艺学领域:为扭转此前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80年代的文学理论家们开始提倡一种“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本体论”。这些文学理论家大都具有康德美学的某种训练,尽管当初他们是把康德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靶子而进行训练的。康德在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中把“审美”定义为一种“无功利静观”的行为,说“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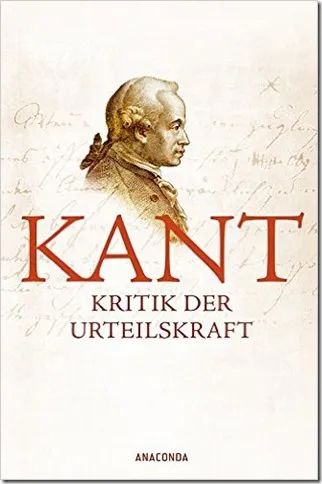
- 康德和《判断力批判》 -
但即便在80年代复活了康德的幽灵,还不足以支撑“文学的本体论”的合法性,因为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如果仅仅从18世纪吸取它的关键灵感,毕竟缺乏号召力,也难以打败那种仍然坚持认为文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文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因此,必须从西方当代文学批评中去寻找合法性依据。80年代提出“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响亮口号,其中这个“世界”,肯定不是指亚非拉世界,而是委婉指称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它此时被建构为一切先进的现代的文学理论的来源。
1981年,杨周翰先生应邀去美国进行学术考察,次年写出类似“考察报告”的论文《镜子与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一个主要差别》(以英文撰写,题为The Mirror and the Jigsaw: A Mayor Difference between Current Chinese and Western Critical Attitudes,载于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刊物《再现》1983年秋季号),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描述道:“中国当代一切文学批评都基于以下这些基本假设:文学反映或者应当反映社会生活,它不能与社会生活脱离,它有政治倾向性和教育目的;作家们被不断呼吁去深人生活,尤其是劳动大众的生活,而批评家们也因此主要关注作家是否深入了社会生活,是否成功反映了社会生活”,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在西方当代文学批评中发现了一套与之迥然不同的批评术语,各种批评流派都有着一种相互渗透的趋向,因此自然就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中最主要者就是专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中国批评家专注的是作品中反映的生活,而西方批评家观照作品本身,不屑于费心探究作品的‘外部因素’。前者与韦勒克教授归类的外部研究近似,后者则与韦勒克教授归类的内部研究近似”。

- 韦勒克 -
但“韦勒克教授”并非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区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而是针对西方自身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进行的归类——这意味着“外部研究”也同样广泛存在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其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以及其他一切基于历史和社会的文学批评中。正如艾利克斯·沃洛赫所说,美国在1980年进入右派保守主义的“平庸的年代”,但学院派的文学理论却反倒唱响了“政治化的高音”,“其标志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该书的副题为‘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在1981年的出版及其在整个1980年代的影响”。似乎刻意针对以美国新批评的“内部研究”为代表的那种非历史化倾向,杰姆逊不仅在《政治无意识》的扉页以维特根斯的“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社会方式”作为题词,而且该书序言第一句便是一个充满战斗意味的口号——“Always historicize!”要须臾不离历史化。
杨周翰先生1981年在美国进行学术考察,正是杰姆逊出版《政治无意识》并且学院派的文学理论家们正在唱响“政治化的高音”的时刻,而杨周翰先生却只“发现”了美国文学批评的一种所谓的“共同的特征”,即“专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这个考察结论完全忽视了美国(西方)的文学批评的党派冲突,而将其中一方建构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共同特征,然后又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将韦勒克和沃伦本用来区分美国(西方)自身并存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建构为一种中西对立,即“西方批评家们”在从事“内部研究”,而“中国批评家们”却在从事“外部研究”。
不过,比杨周翰晚两年(1983)去美国访学的乐黛云先生一到美国,就接触到了美国或者西方文学批评的另一大潮,而她与杰姆逊在加州大学的会面,直接促成了杰姆逊1985年秋冬来北京大学授课三个月。乐黛云在为1986年出版的杰姆逊讲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所写的序言中回顾说:“在加州时,我们曾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及其无限潜能,也许正是这一切在吸引他罢。”序言谈到开课情形甚详:“1985年9月至12月,美国杜克大学弗·杰姆逊教授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国际政治系国际文化专业之请,在北京大学开设有关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听讲的学生来自中文系、英语系、西语系和国际政治系,还有一些来自美国和苏联的留学生。他的课非常严格地按每周6个小时进行,用英文讲授,同时由英语系唐小兵用每周3小时另向英语较差的同学进行辅助性翻译复述。”
从译者唐小兵为这部译著所写的译后记,可知杨周翰先生也参与了此事:“1985年秋冬,F.杰姆逊教授在北大讲课期间,我受杨周翰先生、乐黛云教授之托,为中文系部分比较文学及文艺学研究生翻译杰姆逊教授授课内容。那是繁忙紧张而又充满愉悦的4个月。”由此可见,杨周翰先生对杰姆逊也颇为重视,但为何1981年他在美国进行学术考察时,却只“发现”了作为西方各种文学批评的“共同的特征”的“内部研究”或者说“专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或许美方邀请者只想让他“发现”他们想要他“发现”的一面?或许是当时国内以“文学本体论”为基础重建中国文艺学的迫切需要,使杨周翰先生刻意忽略西方文学批评的另一大潮,因为它对“文学本体论”有对抗乃至拆台之虞?这真是一个令人不解的谜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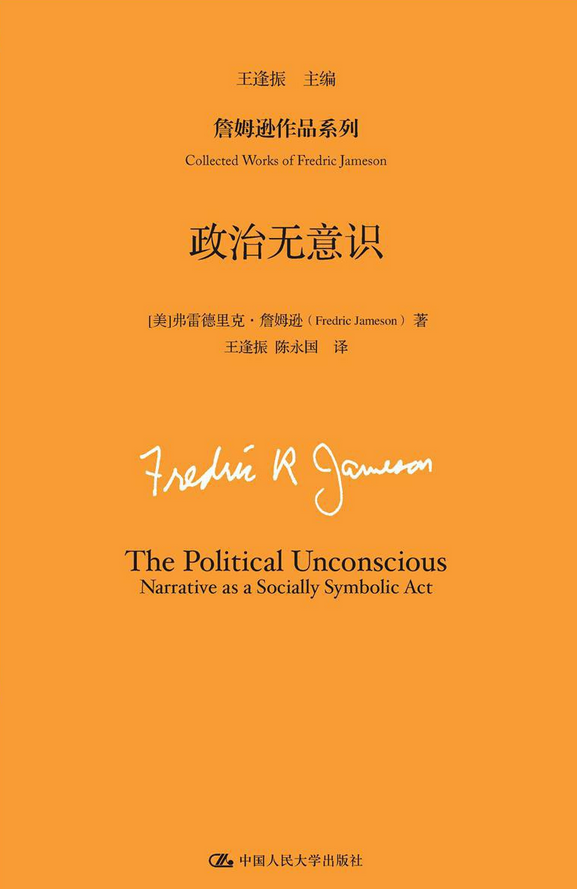
- 杰姆逊和《政治无意识》 -
不管怎样,1988年7月16日,杨周翰在《文艺报》发表了由王宁从英文翻译的《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此文立即产生了影响,《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随即发表无署名短评,题目有些惊悚——《中国文艺批评面临十字路口》,在撮要转述杨周翰文章的内容后,添加评论云:“中国文学批评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要想在此前进一步,就得承认创作工作的复杂性。现已有迹象表明,中国批评家已开始意识到了文学的内部研究的重要性。”
直到1990年,也就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已成为中国新文艺学的圭臬之后,当《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一文收入杨周翰的论文集《镜子和七巧板》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杨周翰在文章末尾添了一个“附记”,承认当初《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一文对西方文学批评的整体场景有所遮蔽:“此文写于1982年,未能涉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两种新理论虽仍是形式主义的理论,但值得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此外,本文也未涉及所谓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这一批评流派可以说是对形式主义批评的一种反作用,也值得作比较研究。”
不过,在以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来重建中国文艺学的基础的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1985年秋冬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三个月的系列讲座,还是杨周翰先生在1988年为当初的《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添加的“附记”,都被边缘化了。意味深长的是,作为美国和英国的头号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杰姆逊和伊格尔顿,他们各自第一部中译本著作(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和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在1986年和1987年均出版于地处“边缘地带”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而形式主义新批评派的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的中译本则在1984年由“中心地带的中心”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既然80年代最有号召力的囗号是“走向世界”和“与世界接轨”,那么,中国当代批评家们理当抛弃自己的“外部研究”,转向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的共同的特征”的“内部研究”。一度在8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获得其明晰内涵的“文学本体论”,终于在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简单而明晰的美国式表述方式。
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之于80年代中国文艺学重建的深远影响,姜涛在2009年的一篇笔谈中或许描述得最为全面和准确:“所谓‘内外’有别观念在中国的确立,得益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的广泛阅读,‘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元区分,也成为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批评的基本框架。为了反抗粗暴的外部干预,必须要在文学的内部建立起自己的尺度,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的转移也奠基于此。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归结到一点,也就是要用内部的标准替代外部的政治标准,重述一种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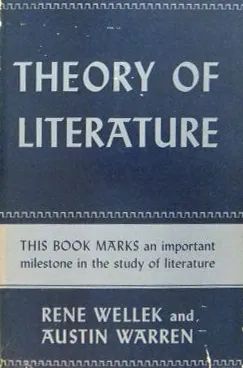
- 《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著) -
但姜涛此话描述不是在为“内部研究”辩护,恰恰相反,他认为这种“向内转”的“内部研究”后来造成了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普遍地疏离甚至逃避现实的趋势’”,正如参与那次笔谈的另一个学者洪子诚所说:“出现这种状况的很大部分原因,是80年代以来对‘纯文学’和‘文学自主性’的提倡。这些在80年代具有‘革命能量’的思潮,在历史情景发生变化的时候,未能及时加以调整,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其负面的影响。确实,在80年代,出于对‘十七年’,特别是‘文革’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反思,文学界的许多人怀有‘纯文学’的想象,并推动着文学尽可能对政治的‘离弃’。这与90年代以来的文学在批判精神上存在的缺失,应该说有一定的关联。”
这个看法在“内部研究”的反思派那里颇具代表性,即强调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本身具有“革命能量”——错不在《文学理论》——而是中国社会自身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历史情景发生了变化,将这种“革命能量”冷却了。
但反思派没有费心去探寻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自身的“发生史”,如果他们知道,《文学理论》本身就是美国中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右派政治保守主义的一种文学理论,它反对的恰恰是美国东海岸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的以及其他一切文学的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那么,他们肯定对这部著作在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有另一番见解。形式主义的“内部研究”通过把文学从其须臾不可割裂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中想象性地割裂出来,变成一个形式主义的孤岛,本身就不荷载任何“革命能量”。顺便说一句,正如美国新批评派其他人,韦勒克和沃伦也是康德学者,而他们要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中以康德的幽灵驱逐马克思的幽灵。
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是美国新批评和俄罗斯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的理论集大成者,不过它与俄罗斯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一线的直接联系,仅仅因为韦勒克在1939年移民到美国的中西部地区的爱荷华州。美国新批评有时被定义为“英美新批评”,其实主要是一种美国现象,它的产生与内战之后美国南部农业地区的庄园经济结构及其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对北部地区的具有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入侵的抗拒息息相关——现实中的抗拒的无能最终导致一种想象性的复归或者说“怀旧”以及T.S.艾略特式的“出走”(被后溯为“英美新批评的开创者”之一的T.S.艾略特出生并成长于美国中西部,一战爆发后滞留于英国,不久转为英籍)。
美国新批评不仅大盛于1945到1955年的麦卡锡主义运动的高峰时期,而且与麦卡锡主义一样发端于美国南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这并非一个时间和地理的巧合。新批评和麦卡锡主义,都主要以美国内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作为其地区基础和群众基础,那里盛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主义的、种族主义的、重农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反智主义的传统,而这些地区对知识分子云集的美国东海岸地区充满怀疑和敌意,这些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东欧和中欧,大多是犹太新移民,具有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的理论思辨的传统,并且从欧洲带来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左派学说在内的一切现代激进主义思潮。
美国1919到1933年的禁酒运动和1945到1955年的麦卡锡主义运动,可以被视为美国南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社会向美国东海岸地区的大都市社会发起的两次十字军东征,正是在这两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刻,美国新批评先是兴起于南部地区,以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德大学为其精神中心,以重农主义和对南方奴隶制时代的“美好旧时光”的怀旧来对抗东海岸地区北部的工业和现代性,继而,随着捷克形式主义者韦勒克和深受南部新批评影响的沃伦先后来到爱荷华州,爱荷华大学就成了与南部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德大学相互呼应的新批评的另一个精神中心。
新批评的这两个精神中心地处“边缘地带”的美国南部和中西部,而它发展壮大以及最终走向“中心地带”(东海岸地区),并非完全由其自身理论的吸引力所赢得,而是受到了美国政府暗中支持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保守主义者常常指控主流基金会在资助上偏向左派,不过,约翰·威尔逊在检视这些被指控的基金会的档案后却发现:“这些基金会无一资助过任何一项具有左翼意识形态色彩的项目,不像奥林基金会的资助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动机。即便是麦克唐纳提到的‘最激进’的现代语言协会,也从来没有资助过什么人。那些大的基金会一般资助一些主流项目,例如课程改革,而不是资助对社会或学术机构进行激烈批评。”川休斯·维尔福德谈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先锋派的体制化”中所起的作用时,在一个脚注中提到洛克菲勒的政治偏向:“对新批评派的杂志的资助,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新批评派显示其偏向的唯一方式。195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拒绝了ACCF提出的给那些小杂志编辑们的一次会议提供资助的申请。ACCF受纽约知识分子群的控制。两年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新批评派在纳什维尔这个所谓的‘修辞运动的摇篮’的一次重聚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
对麦卡锡主义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部的秘密档案了如指掌的埃里克·本内特在《帝国的工作室》一书中谈到人文部,说“它巡视着高等教育,以确认哪些系和哪些学者与基金会的观点一致;它资助那些尚处在边缘的人物和发展,直到这些人物走向中心,这些发展变得关键;它紧盯学科的活动和兴趣的新的中心——任何看起来有希望对过度专业化和墨守成规形成一种对抗力量的中心。它资助的人有一长串,包括直到2015年的今天听起来依然不陌生的一些名字,他们是英文学科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199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约翰·兰瑟姆七千五百美元,用于《肯庸评论》的编辑活动,另资助这份杂志的编辑埃里克· R.本特利1千美元(保罗·恩格尔也受了资助)。1946年,他们同意承担之前提到的罗伯特· P.沃伦的编辑费。1945年,该基金会通过爱荷华大学资助韦勒克和沃伦8千美元,用于完成他们的《文学理论》。1947年,该基金会开出4万美元,资助肯庸学院英文研究学校由莱昂内尔·屈瑞林、F.O.马希森和约翰·兰色姆担纲、致力于塑造美国的文学批评的三个学期的课程。1949年,F. R.利维斯通过剑桥大学获得该基金会的资助,得以连续三年雇用助手,让更多学生受惠。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3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推进文学批评新方法的探索。1951 年,爱荷华写作中心的首任主任威尔布·希冉通过爱荷华大学获得该基金会‘九千一百零五十美元的资助,用于研究在人文学科写作方面培训人员的可能性’。(他那时已是一个传播学的一个创始人,后来作为宣传顾问为中央情报局工作)1952年,普林斯顿大学从该基金会获得一笔高达10万美元的多年资助,用于支持高斯文学批评研讨班”。
格里姆·库珀谈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新批评派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大盛之间的关系时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背后资助了新批评派的反叛,这已不是什么新闻。但爱荷华的崛起,与这场反叛之间在政治、哲学和金钱上的密切联系,却鲜为人知,同样鲜为人知的是这场反叛的规模远不止新批评,新批评只是其中一个侧面,而不是整体。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秘密档案显示它曾资助四份评论杂志,资助把爱荷华变成改变美国的文学文化的一个战场。”
但这个战场比爱荷华更大,因为受到它支持的爱荷华和田纳西的“新批评派”开始纷纷向此前主要为左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盘踞的东海岸地区常春藤联校进军:“在我们这个时代,绅士—批评家和诗人—批评家以及文人们被职业的大学批评家所取代:除艾略特外,新批评派诸人都在学院和大学找到了长期的教职。他们的诸多作品被大学资助的季刊和出版社出版……布鲁克斯、韦勒克和维姆萨特成了耶鲁大学教授,布莱克穆尔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肯尼斯·伯克去了本宁顿的罗格斯大学,艾略特获得了诺贝尔奖,克里格和兰色姆去了肯庸大学,在那里,兰色姆领导着名声远播的肯庸英文学院(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瑞恰慈去了哈佛大学,泰特去了明尼苏达大学,而温特斯刚成为斯坦福的全职教授。身处这些负有盛名的高校,新批评派获得了权威,使他们得以通过出版物和日常授课将他们的思想广泛传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新批评的全套理论原则被韦勒克和沃伦编入了后来证明影响深远的《文学理论》(1949),此书不像《理解诗歌》瞄准本科生,而是瞄准研究生和教授。‘批评股份有限公司’在1940年代后期成了现实。”
美国新批评与美国右派保守主义政治之间的关联,证明美国新批评是一种高度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即便它像康德美学一样声称自己是一种“无功利的静观”的文学本体论、一种形式主义的“内部研究”。不过,随着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到来,美国新批评一度失去了其学术的影响力,而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其他一切社会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文学批评——诸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族裔文学批评等等——如雨后春笋,繁盛一时,它们关注千千万万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在历史中和现实中的境遇,将文学批评重新与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事业紧紧相连。
不久之后,随着右派保守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卷土重来,尤其是1980年极右保守主义者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入主白宫和唐宁街10号,右派保守主义再一次开始清算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其他一切新老左派的文学理论,此时,在1949年麦卡锡主义高峰时期出版的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作为清洗这些激进主义的一味政治保守主义的泻药,被再一次抬举出来。但奇特的是,这种政治保守主义的文学理论却随即被挪用到中国,作为中国80年代文艺学重建的基础——与其说它重建的是一种“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不如说它以“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本体论”或“文学自主性”为名号,将左派的意识形态悉数括入“外部",而将一种右派保守主义的文学理论建构为一种“形式主义”。
中国的80年代被认为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不过,这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其文艺学重建中却将一种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右派保守主义的、重农主义的、怀旧的文学意识形态,供奉为一种“真正的文学理论”,以排斥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内的一切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文学批评——其无远弗届的深远影响,几乎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并不是说,80年代之后,一切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文学批评在中国文艺学中消失了,恰恰相反,它们形成了一种批评大潮,但在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虚构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专断尺度下,它们不被认为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正道,不是文艺学的学科合法性的基础。
这里不是在指责80年代的理论前辈,因为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继承下来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提出自己的问题,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解决。现在应该是走向正—反—合的时候了。或许“内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磨砺批评家对形式的敏感性,但代价却是丢掉了整个世界及其社会关系,因此也完全不能说明形式自身的历史变化和阶层差异,因为形式的历史变化和阶层差异只有在历史进程的全部复杂关系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说明。实际上,那些与生活世界息息相关并且最具政治洞见和历史深度的文学批评,恰恰体现出对于文学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敏感,而形式主义的“内部研究”反倒因为缺乏政治敏感性而不能在形式研究方面达到这种敏感——或许正因为它具有政治敏感,它才出于一种右派保守主义的政治需要,将文学研究囚禁于“内部”。
-END-
新媒体责任编辑:郭一岫
审校:张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