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威 | 《布拉姆比拉公主》中的演员成长之路 ——兼论E. T. A. 霍夫曼对歌德戏剧表演理论的批判
本文原载于《德语人文研究》2025年第1期。感谢作者罗威老师和《德语人文研究》的支持。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注释。


内容提要:在艺术童话《布拉姆比拉公主》中,德国浪漫派作家E. T. A.霍夫曼完整地呈现了主人公吉里奥从自恋的悲剧演员到“幽默的”喜剧演员的成长历程。通过对文本进行分析能够看到,程式化的表演方式是吉里奥演艺事业失败与生活窘迫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吉里奥走出困境、逐步认清自我的过程中,霍夫曼不仅融入了自己对于演员职业要求、戏剧创作与舞台实践等戏剧问题的思考,而且还对歌德的戏剧表演理论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在此基础之上,霍夫曼通过吉里奥与其恋人贾钦塔的圆满结局,在童话中进一步展示了自己的“幽默”戏剧理念,以及对歌德古典戏剧理念的否定与超越。
关键词:《布拉姆比拉公主》、演员、戏剧表演理论、戏剧理念


《布拉姆比拉公主》(Prinzessin Brambilla,以下简称《公主》)成文于1820年,是德国浪漫派晚期代表作家E. T. A. 霍夫曼(E. T. A. Hoffmann, 1776-1822)创作的一篇艺术童话。不同于霍夫曼的其它六篇艺术童话,这部被评论界称作“长篇童话小说”的作品拥有极其复杂的叙事结构。根据德国学者凯泽尔(Gerhard R. Kaiser)的总结,《公主》中至少存在五个层面的故事情节:日常生活、戏剧世界、狂欢活动、童话故事与神话传说。这些情节虚实交错,彼此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相应地,在这些情节层面之间来回穿梭的童话人物也被赋予了多重亦真亦幻的身份,让人难以捉摸。因此,早在这部作品问世之初,评论界就出现了“无数谴责这种混乱无序与杂乱无章的批评声音”,即使有赞之者如海涅,认为“布拉姆比拉公主就是个高贵的美人”,但也不得不承认会“被她的娇艳弄晕脑袋”。这种令读者深感不知所措的阅读体验贯穿了《公主》的接受史,使其一度被贴上拙劣的标签。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这部作品的关注程度也远不及对霍夫曼的《金罐》(Der goldene Topf)等名篇。

E. T. A. 霍夫曼
的确,《公主》错综复杂的叙事结构给读者设置了不小的阅读障碍,但是正如德国著名的霍夫曼研究学者施泰因艾克(Hartmut Steinecke)在评述这部作品时所言,“认真的读者还是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逻辑上可以理解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构。”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这部作品虽然缺少一条清晰的叙事主线,各个章节之间的衔接也不甚紧密,但它的故事架构是比较完整的:《公主》一共由八章组成,除了第三章和第五章里出现的神话传说以外,整篇童话的故事情节基本围绕着主人公吉里奥·法瓦在罗马城里的活动轨迹展开。在狂欢节期间,吉里奥不仅弥合了自己的梦境与现实世界的割裂,而且身为戏剧演员的他也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蜕变,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演员。纵观吉里奥的整段经历不难发现,戏剧表演从始至终都处在最重要的位置。它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围绕其展开的讨论也占据了童话大量的篇幅。在这个意义上,把《公主》视作一部“戏剧童话小说”是十分贴切的。在吉里奥作为一名演员的成长过程中,霍夫曼融入了自己对于演员职业要求、戏剧创作与舞台实践等一系列戏剧问题的思考,如果以德国当时的戏剧话语作为参照,那么《公主》中其实隐含着对以歌德为首的魏玛戏剧学派表演理论的批判与反思。霍夫曼在表达自己戏剧观点的同时,也展现了自己与歌德在戏剧艺术理念上存在的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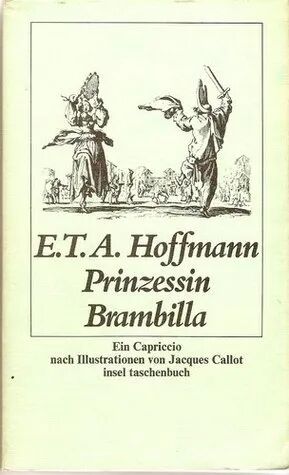
《布拉姆比拉公主》封面
在童话主人公吉里奥首次登场时,叙事者对他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有兴致的读者,你也许察觉到了这位衣着突兀的年轻人不是别人,而是一个有些自恋的演员。他的收入没有多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引文中“收入”的德语原文是“Verdienste”,这个单词在德语中还有成就的意思。因此,叙事者此处的介绍也暗示了现在的吉里奥在戏剧表演领域尚未取得多少成就,还不是一位优秀的演员。Verdienste一词的双重含义对应了吉里奥初登场时的两种处境,即童话人物碧阿特丽斯口中的“穷光蛋先生”与“废物演员先生”,而叙事者强调的自恋二字,正是他生活窘迫与事业失败的根源所在。
在童话的第一章里,吉里奥在与恋人贾钦塔的谈话中自夸道:“我的外貌相当俊朗,生来就在各种令人愉悦的才能方面拥有天赋。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我是演员。”从这几句引文不难看出,吉里奥自视甚高,并且尤以自己的悲剧演员身份为傲。他眼中的自己是“世上最知名的演员”,他自认能在舞台上“绝妙地扮演恋爱中的王子”,所以在现实世界里也理应得到一位公主的青睐。可见,吉里奥将自己的舞台感受代入现实生活,形成了脱离实际的自我认知,这直接导致他后来沉浸在对布拉姆比拉公主的“爱情虚荣”中难以自拔。除此以外,自恋的吉里奥也不能接受旁人对他的演技提出半点质疑,所以当街头商贩塞里奥纳提指出他“现在的悲剧演得相当糟糕”时,“吉里奥怒不可遏地叫道:‘什么?塞里奥纳提先生,您胆敢认为我是一个糟糕的演员?’”然而,在事实上,吉里奥的虚荣与自恋早已让他的表演变得乏善可陈。在童话的第二章里,有两个戴面具的人在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吉里奥在表演方面的缺陷:“如果您批评他[吉里奥]自恋、矫揉造作,如果您认为他扮演的从来都不是他的角色而只是他自己,他在以不值得称道的方式去追求掌声,那么您当然是正确的”。面具人的评价不仅解释了自恋的吉里奥为什么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演员”,而且还间接地表达了霍夫曼对于演员职业要求的基本看法。
在1817年发表的《艺术亲人》一文中,霍夫曼以两位演员临时拒演的自私行为作为引子,对演员的“极度自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评。在霍夫曼看来,戏剧表演是一门非常依赖“艺术家个性”的艺术,“它的实践是以对个人的展现作为前提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个人并非演员本人,而是指诗人创作的戏剧人物。因此,演员不能把舞台当成一个展现个人风采的秀场,将自己凌驾于人物之上,而是应该尽己所能地融入角色,想其所想,感其所感。只有当演员在台上展现的一切皆属于所饰角色时,他才能呈现良好的舞台效果,“所以完全否定,或者更确切地说,忘记自我正是表演艺术的第一要求。”以此作为参照,那么自恋的吉里奥显然犯了表演的大忌,尚不具备成为一名优秀演员的前提条件。
霍夫曼非常喜爱的法国作家狄德罗在其著名的《演员奇谈》中曾写道:“凭感情去表演的演员总是好坏无常。你不能指望从他们的表演里看到什么一致性”。由于吉里奥总是以展现自我的方式去从事表演工作,在台上从不节制自己的感情冲动,所以他也如狄德罗所言,难以保证舞台效果的稳定性。而当吉里奥陷入对布拉姆比拉公主的爱情幻想中以后,完全受制于个人情感的他更是“掉进了混乱与夸张台词的迷宫之中”,再也无法像往常一样登台表演了。随后,演技拙劣的吉里奥被剧院经理当成疯子赶下了舞台。在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以后,这位自命不凡的“罗马偶像”也过上了穷困潦倒的生活。
将放下自我视作演员职业的第一要求,这一观点在当时欧洲的戏剧舞台上并不罕见。狄德罗在《演员奇谈》中就已言明:“演员之所以能表演各种性格正是因为他们本来没有性格。”因此,他认为演员“需要用冷静的头脑来节制热情的冲动”,将自己完全隐匿在所饰角色之后。在德国,魏玛古典时期的歌德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1802年发表的《魏玛宫廷剧院》中,歌德明确地指出:“人们在这座剧院里一直看到的最重要的准则中,有一条是演员必须否定并改造他的性格,从而让他能够在某些角色中隐藏自己的个性。”多年以后,在与艾克曼谈论自己挑选演员的标准时,歌德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他[演员]的职业要求他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在旁人的面具下研究问题和生活!”由此可见,在对演员表演的出发点问题上,霍夫曼与歌德的看法别无二致,他们都要求演员放弃自我以适应角色的需要。然而,出发点的相同并不意味着霍夫曼就完全认可歌德的戏剧活动。恰恰相反,霍夫曼在《公主》中以悲剧表演对吉里奥造成的不利影响作为切入点,对歌德的表演理论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
由艾克曼汇编整理的《演员守则》(Regeln für Schauspieler)是歌德在魏玛戏剧活动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他的表演理论的集中体现。根据《歌德谈话录》中的记载,《演员守则》是以“歌德和演员沃尔夫以及格律纳尔一起讨论的有关戏剧研究的材料”作为基础的,歌德支持艾克曼的整理工作,并与他“对某些个别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因此,虽然这本“戏剧问答手册”的整理者是艾克曼,但它的直接作者仍然是歌德。
在歌德看来,“演员的艺术存在于语言和身体动作之中”,所以他在《演员守则》中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共列出91条规则,对演员的台词规范、身体姿态、彩排以及演出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规定与说明,例如“一句方言都不能出现在舞台上!在那里只能讲由趣味、艺术和科学培养与雕琢后的纯正德语”,“如果把手交叉或者放在腹部,或是把一只手插在背心里,甚至将两只手都插进去,这些都是极其错误的”,“即使是在排练中也不得做剧本里没有出现的事情”等等。在掌管魏玛宫廷剧院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些规则始终贯穿在歌德的戏剧活动之中。他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演员,并在魏玛的戏剧舞台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演风格。
毫无疑问,《演员守则》为彩排和表演提供了理论指导,演员只需遵照歌德制订的这些“清规戒律”就能对不同的角色与剧本应对裕如。从这个角度而言,歌德要求演员放弃自我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全身心地研习表演规则,“按照所有这些技术与文法规则的意义来掌握它们,并不断地加以练习,使其成为习惯”。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演方式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舞台效果的稳定性,但是歌德对台词与身体动作的过分强调,使得情节这一至关重要的戏剧要素遭到了忽视。除此以外,由于演员在台上的言行举止,甚至是情感表达都必须按照固定的模式来展现,所以这也使得表演呈现出明显的程式化倾向。对于歌德倡导的这种“以程式化的思维、‘节制的’动作、‘庄重的’出场以及注重抑扬顿挫与‘修辞的’话白为特征”的魏玛表演风格,霍夫曼持否定的态度。
在《公主》中有一位名叫阿巴特·基亚里的悲剧诗人,他认为“真正的悲剧要素”是“通过表达产生的”,所以与生动的情节相比,这位诗人更加看重剧本的语言表述。在创作时,“他[阿巴特]把所有可怕行为引起的战栗包裹进满是优美词句的粘稠纸浆里,让观众能够平静地吃下这块甜蜜的纸板,但却品尝不出其中苦涩的内核。”对“修辞术”的过分倚重使得阿巴特的剧本里充斥着“感恩的角色”,这种角色“满口浮夸的话,这些话观众不懂,演员和诗人自己也不懂”。通过阿巴特与吉里奥在童话第四章里的谈话可以得知,如果想要演好这种语言优美但剧情空洞的剧本,演员们只需要声情并茂地朗诵韵文台词、摆出恰到好处的姿势并适时地表现出相应的情绪变化即可。可见,阿巴特认可的悲剧表演其实是按照固定的模式来呈现的,其核心是一套以台词和身体动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表演体系,带有明显的程式化特征。
出于对阿巴特的崇拜与认可,吉里奥在扮演悲剧主角时也非常注重台词与身体姿态,例如他会“用考究的舞步从剧院下方登上舞台”,在台上摆出“少见的矫揉造作的姿势”以及“用低沉的声音朗诵韵文台词”等等。然而,吉里奥的这种表演方式并没有得到方家的认可,在童话第二章里出现的两个面具人在评价他的表演时就轻蔑地说道:“我们想要一瞬间给我们带来强烈震撼的夸张事物,但一旦意识到我们视为真人的不过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木偶时,我们就会对此嗤之以鼻。这个木偶受到来自外界的艺术丝线牵制,用它奇怪的动作糊弄我们。”可见,在霍夫曼看来,程式化的表演是缺乏生命力的,受此影响,台上的演员也仿佛成为了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提线木偶,一举一动都受制于外在的表演规则体系。而对于台下的观众而言,当他们意识到眼前的所见所闻不过是固定模式下的产物时,无论表演显得多么精彩,他们都会对台上的演员投去鄙夷的目光。因此,扮演悲剧主角时的吉里奥被其中一位面具人戏谑地比作“一只在太阳底下骄傲啄食的滑稽彩毛小公鸡”,他试图激起的悲剧效果也荡然无存。

《布拉姆比拉公主》初版插画
虽然霍夫曼在《公主》中对阿巴特的悲剧创作方式与吉里奥的悲剧表演方式进行了讽刺与幽默化处理,但是通过二人对情节的忽视,以及对台词与身体动作的过分重视,读者仍然能够看到霍夫曼对歌德以及魏玛表演风格的影射。除了以戏仿的方式指出魏玛表演风格的舞台缺陷以外,霍夫曼在《公主》中还把矛头对准了歌德对演员日常生活提出的要求,并借此对吉里奥自恋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剖析。
为了让演员能够更好地掌握表演规则,歌德主张他们把表演融入日常生活,并以此作为标准来纠正自己平日里一些不符合舞台预期的行为习惯。因此,歌德在《演员守则》的第75条中写道:“演员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该想到,他要公开地进行艺术表演。”在第78条里他又指出,“对于演员来说,一条重要的规则就是,他要努力调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体态、举止以及其它行为,从而让自己仿佛一直处于练习之中。”在第80条里,歌德更是着重强调,“他[演员]应该总是设想自己面前是坐着观众的场所。”从吉里奥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来看,他显然已经将表演彻底融入了日常生活,并将其内化为了歌德要求的演员的“第二本性”。
在童话的第四章里,吉里奥在阿巴特的提点下暂时回归现实。在得知自己现实中的恋人贾钦塔已经移情别恋以后,他立刻“陷入了阿巴特·基亚里某部悲剧中令人厌烦的绝望独白之中”,用悲剧角色夸张的台词来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情到浓时,吉里奥更是抽出表演用的道具木剑佯装自尽。对于吉里奥这种高度戏剧化的表达方式,贾钦塔早就习以为常,她不仅能在吉里奥说话卡壳时提醒他要说的台词,而且在他恢复平静以后,她还以观众的视角对他刚才的表现进行点评:“好吉里奥,你的悲剧表演十分出色”。除了这个典型的例子以外,吉里奥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言行举止也带有明显的悲剧角色的烙印,例如在童话的第二章里,吉里奥来到贾钦塔的门前深情告白,但由于他的表达方式与表演非常接近,所以他被贾钦塔的房东当成了“某部愚蠢的悲剧中说着‘哦’和‘啊’的角色”;在第五章里,吉里奥在动身前往罗马城里的匹斯托亚宫之前,他更是“试着在镜子前摆出最优雅迷人的姿势”,并且“回想起患相思病的英雄们口中那些奇妙的套话”,以此让自己确信“他[吉里奥]是彻底令人倾倒的”。
由此可见,表演的内化已经切实地影响到了吉里奥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与自我认知。如果说自恋是这位演员事业失败与生活窘迫的缘由,那么他以悲剧主角为蓝本构建出的理想自我,则是让他变得自恋的根源所在。歌德提倡的这种将表演融入现实的做法不仅让吉里奥将自己与所饰角色视为一体,而且还让他把真实与幻象混为一谈。正如批评吉里奥的其中一位面具人所言,“表演的劳累或许正是他疯癫的原因”。当吉里奥以“戏剧王子”的身份恋上虚幻的布拉姆比拉公主以后,他也彻底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沦为了旁人眼中的疯子。借此,霍夫曼也让读者看到了歌德对于演员职业要求的矛盾与危险之处:如果演员将表演彻底融入日常生活,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规范自己平日里的言行举止以后,那么他们既不能在台上忘记自我,也难以在台下脱离角色,因为他们的自我与所饰角色已经合二为一,难分彼此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吉里奥想要摆脱自恋,走出事业与生活的双重困境,那么他首先要做的,便是消除悲剧表演对自己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童话的第六章里,霍夫曼以充满想象色彩的笔法勾勒了吉里奥打破悲剧表演桎梏的关键一幕。
在与塞里奥纳提离开匹斯托亚宫以后,吉里奥化身为阿巴特新剧中的主角来到了科尔索大街上,此刻以“英雄和骑士”自居的他与意大利假面喜剧中的丑角潘塔隆狭路相逢,两人随即展开决斗。在经过一番交谈与打斗之后,喜剧丑角获胜,悲剧英雄殒命于此。在第七章里,一位年轻人在回顾这场决斗时冷静地陈述道:
我不清楚这位悲剧演员吉里奥·法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有血有肉的,又或许他仅仅只是由纸板组合而成。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解剖时发现他的内部已经被某个名叫阿巴特·基亚里的人创作的悲剧角色给塞满了,而医生也只能把吉里奥·法瓦受对手这一击的致死原因归结为撑得太厉害,以及享用无效且乏味的营养品导致的所有消化原则的彻底紊乱。
从后续的故事情节可以得知,潘塔隆与这位年轻人其实都是吉里奥本人,所以这场决斗真正的事发地点不可能是现实世界里的科尔索大街,而是按照叙事者在童话第四章开头的提示,被转移到了“场上人物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吉里奥的两个戏剧自我之间的分歧,其实是他在内心深处对悲剧和假面喜剧进行的一次抉择。潘塔隆的胜利象征着吉里奥认可并接受了假面喜剧“这种没有脚本、不经排练即进行演出的戏剧形式”,而他随后以旁观者的身份对被自己亲手杀死的悲剧自我进行剖析,并对曾经视作模仿对象的悲剧主角进行批判的行为,则代表着他已经认清了自己在表演方面存在的问题,彻底摆脱了程式化的悲剧表演方式。在这之后,如获新生的吉里奥告别了曾经引以为傲的悲剧演员身份,变得不再自恋与虚荣。得益于此,他也具备了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演员的可能性。
霍夫曼在《公主》中针对歌德表演理论表现出来的批判态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魏玛表演风格已经开始在柏林盛行。在伊夫兰德(August Wilhelm Iffland)离世以后,曾在魏玛当过演员的布吕尔(Carl von Brühl)成为了柏林皇家剧院新的负责人,在他的促成下,歌德的得意门生沃尔夫(Pius Alexander Wolff)于1816年与同为演员的妻子前往柏林工作,并将魏玛表演风格搬上了柏林的戏剧舞台。“虽然沃尔夫夫妇在柏林推行魏玛表演风格遇到了诸多困难,但他们仍然在布吕尔担任经理的前几年里逐步扩大了影响力。”因此,对于1814年9月迁居柏林,并且在那之后与柏林戏剧界多有接触的霍夫曼而言,歌德的表演理论并不陌生。此外,霍夫曼的好友德弗雷恩特(Ludwig Devrient)当时也在柏林皇家剧院工作,并且凭借着出众的表演才能而颇负盛名。然而,在沃尔夫夫妇担任剧院要职以后,演技高超的他遭到了排挤,只能扮演一些不入流的角色。受好友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影响,同时也基于自己对魏玛表演风格的理解,霍夫曼在1818年出版的《一位剧院经理的奇特烦恼》中不仅刻画了一个与德弗雷恩特遭遇非常相似的天才演员小嘉里克,而且意有所指地写道:“我们的诗人背离真正的戏剧艺术转向了修辞艺术,并且还把我们的演员一起拽了进去,使得他们如今也过分看重他们艺术里的修辞部分了。”

卡尔·冯·布吕尔
由此可见,霍夫曼在创作《公主》之前就已经表达过对魏玛表演风格的否定态度。从文本间性的角度而言,他在《公主》中以一位悲剧演员的演艺经历与个人生活作为线索,对歌德表演理论展开的全方位批判,则可以看作是对《一位剧院经理的奇特烦恼》这部“戏剧著作”的进一步延伸,其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他在柏林的这些戏剧经历。但是除了个人经历以外,霍夫曼拒绝歌德表演理论的深层逻辑,其实源于他与歌德在戏剧艺术理念上存在的审美观点分歧。
艺术与自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歌德古典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的戏剧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歌德认为艺术应当以模仿自然为己任,所以“对艺术家提出的最高的要求就是:他应依靠自然、研究自然、模仿自然,并创造出与自然现象毕肖的作品来。”值得注意的是,歌德虽然强调自然是艺术的基础,但是他认为“有一条巨大的鸿沟把自然同艺术分开来”,所以他并不主张艺术家去机械地复刻自然,追求高度还原现实的“自然真实”,而是要求他们对自然现象进行总结与提炼,发掘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在基于自然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一种能够表现理想自然的“艺术真实”。因此,歌德眼中的“艺术家不求自然作品,只求艺术杰作。”
受这种古典美学思想的影响,歌德在《演员守则》的第35条中明确地写道:“演员首先要想到,他不仅应该模仿自然,而且还应该想象出它的理想状态,所以他要在自己的表演中把真与美结合起来。”在第80条里,歌德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们在舞台上不仅要把一切表演得真,而且要表演得美”,所以表演艺术应该向观众呈现的是“优美的编排和姿态”。可见,歌德在舞台实践中一再强调台词与身体动作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制订《演员守则》的初衷,其实是希望演员能够作为“有教养的人”登上舞台,并按照这些规则还原古典悲剧中那些“尊贵的、高尚的人物”。这类戏剧人物的言行举止符合歌德眼中的艺术真实,因而能够为观众带来良好的审美体验。至于喜剧中那些以插科打诨为主的角色,例如在《公主》中作为悲剧英雄的对立面出现的众多假面喜剧角色,则属于“粗鲁的、愚蠢的人物”之列。这类滑稽的喜剧人物没有对自然进行正确的模仿,所以他们被歌德排除在了《演员守则》的适用范围之外。
总体而言,歌德的戏剧理念是以他对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作为基础的,无论是《演员守则》还是以此作为理论依据形成的魏玛表演风格,都是他追求真与美的古典艺术观在舞台实践中的具体体现。除此以外,从歌德在《演员守则》中的表述也能看出,他的戏剧理念里其实包含了对悲剧与喜剧的审美等级区分:相较于模仿自然的悲剧所呈现出的崇高与优美,表现滑稽与丑怪的喜剧显然更为低级。因此,在追求艺术真实的舞台上,不仅喜剧不能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而且喜剧的元素也不能混入到悲剧之中,让戏剧演出沦为一种不伦不类的“汞合金”。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歌德才会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文中指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忠实于原来的传说,然而由于加进了两个滑稽角色迈立西奥和保姆,原来传说中的悲剧内容几乎全部被破坏了。”
对于歌德以模仿自然作为依据,在悲剧与喜剧之间划定等级与界限的做法,霍夫曼并不认同,究其原因,这主要与他对“人性”(die menschliche Natur)的看法有关。霍夫曼认为,“谁也不能否认存在于人性深处的反讽,正是这种反讽决定了人性最内在的本质,并且从这种反讽中,玩笑、机智和恶作剧与最深刻的严肃一起散发出光芒。[......]痛苦的痉挛与绝望尖锐的悲叹声会汇入由奇妙乐趣引发的笑声之中,而这种乐趣正是通过痛苦和绝望才会产生。”从这几句引文可以得知,作为一种“矛盾心理的语言形式”,反讽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清楚地展现了出来。借助反讽能够看到,严肃与诙谐这两种对立的状态其实统一于人性深处,在此基础之上,痛苦与愉悦、悲叹与欢笑这些矛盾的情感体验与情绪表达也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体多面的人。因此,如果像悲剧一样只看重严肃,抑或是像喜剧一样只关注诙谐,都是仅从一个方面出发对人性进行考察,并不能让观众看到拥有完整人性的鲜活戏剧人物形象。
在霍夫曼看来,“对人性这种奇特构造的完全认识,正是我们称为幽默的事物,幽默的深刻本质就是这样规定自身的,我认为它与真正的喜剧要素是同一种事物。”由此可见,幽默同时兼顾了人性的不同方面,是一种能够直达人性本质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延伸到戏剧领域,不仅消除了悲剧与喜剧之间的界限,而且还将二者融为一体,形成了真正的喜剧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喜剧要素其实是一种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戏剧艺术理念,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喜剧并不等同于滑稽剧,而是一种超越了传统戏剧体裁分类的悲喜剧。如果说歌德为了追求艺术真实而贬斥喜剧的做法是对人性的一种片面认识,那么霍夫曼提出的这种以幽默作为本质特征的戏剧理念则全面且深刻地诠释了人性,所以它能够更好地指导戏剧创作与舞台实践,帮助诗人与演员塑造更加具有舞台张力与生命力的戏剧人物。
因此,霍夫曼认为诗人不必把模仿自然作为戏剧创作的准则,而是应当效仿莎士比亚这位“真正幽默的大声宣告者”,将悲剧元素与喜剧元素结合起来,赋予戏剧人物乃至整部剧作以幽默的底色。而作为幽默戏剧人物的舞台呈现者,演员也不能受限于歌德为了呈现艺术真实而制订的那套表演规则。他们在表演时除了要放下自我、深入理解诗人给定的人物以外,还应该积极践行幽默戏剧理念,将喜剧的诙谐融入到悲剧的严肃之中,让自己成为对人性有着深刻理解的幽默的演员。在霍夫曼看来,“如果演员被真正的、内在的幽默占据内心,并且上天赋予他通过声音、言辞和手势将这种幽默生动地表现出来的天赋,那么他将对观众的心灵拥有多么不可抗拒的威慑力与统治力啊!”
综上所述,在霍夫曼的幽默戏剧理念里,喜剧与悲剧都是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对人性进行刻画,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歌德眼中的审美等级关系。真正完善的戏剧艺术不仅应该承认喜剧具备与悲剧同等的审美价值,而且还要将二者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拓展戏剧表达的边界,向观众呈现贴合完整人性的剧作与表演。从这个角度而言,将喜剧这一不以模仿自然为基础的戏剧形式纳入到戏剧艺术的审美体系之中,是霍夫曼与歌德的根本分歧所在,同时也体现了霍夫曼对歌德古典戏剧理念的超越意识。
回到《公主》来看,在吉里奥的两个戏剧自我走向最终的决斗之前,霍夫曼就已经通过悲剧诗人阿巴特与其宿敌迪·匹斯托亚侯爵表达的戏剧观点,在童话中暗示过两种不同的戏剧理念的分歧。对于阿巴特而言,喜剧是一种低级的戏剧形式,不应该成为舞台表现的对象。因此,当他得知吉里奥曾经表演悲剧的舞台被“意大利喜剧和哑剧中所有戴面具的角色”占据以后,他怒不可遏地说道:“这个蠢货[剧院经理]完全放弃了悲剧,除了令我至死都会厌恶的、愚蠢可笑的面具和哑剧表演以外,他什么都不让出现在他的舞台上。”从表面上看,阿巴特愤怒的原因在于他的剧作无法被搬上舞台,但是作为《公主》中魏玛表演风格的倡导者与代言人,他对假面喜剧的贬低与敌视,其实指向了歌德强调艺术真实的古典戏剧理念。
与阿巴特不同,迪·匹斯托亚侯爵“维护戴面具的戏剧人物”,并且提出了一种在这位诗人看来“只有被烧焦的脑袋才能想出来的悲剧体裁”。童话中的叙事者并未对这种悲剧体裁进行直接描述,文本中的留白使得读者无法获悉其具体特征。尽管如此,从侯爵认为“最高级的悲剧效果一定要通过一种特殊形式的玩笑产生”,以及他尝试在阿巴特的悲剧中加入喜剧元素的做法仍然可以看出,侯爵认可的戏剧形式其实具有悲喜剧的特点,其依据是霍夫曼的幽默戏剧理念。以此作为出发点,便不难理解吉里奥在侯爵的指点下化身为潘塔隆时,为什么身上仍然保留着悲剧英雄的诸多特质了。由此可见,在《公主》中作为悲剧对立面出现的假面喜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滑稽剧,而是一种亦庄亦谐的幽默戏剧形式。
在童话的最后,彻底褪去“英雄外衣”后的吉里奥从布拉姆比拉公主的幻梦中清醒了过来,他与贾钦塔结为夫妻,并成为了“被真正的幽默占据着内心”的假面喜剧演员。得益于演艺事业的成功,吉里奥也摆脱了曾经的穷困潦倒,如愿地过上了富足安定的生活。吉里奥的这一圆满结局与他从事悲剧表演工作时的艰难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凸显出了霍夫曼对歌德表演理论的批判态度。除此以外,迪·匹斯托亚侯爵还指出,此时的吉里奥与贾钦塔是在“反讽与真正的幽默发挥作用的剧院”里工作,这暗示着在二人成为幽默的演员以后,不仅假面喜剧取代古典悲剧成为了舞台表现的主要对象,而且幽默戏剧理念也成功地取代古典戏剧理念,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至此,吉里奥在自己的演员成长之路上已行至终点。纵观这位演员在童话中的整段经历不难发现,他的成长不只是从悲剧演员到喜剧演员的身份转变,更是一个逐步认清自我、摆脱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与革新戏剧理念的过程。
在1827年发表的《〈克伦威尔〉序》中,法国作家雨果从历史三段论的视角出发,对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进行了说明,并指出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待“滑稽丑怪这一被近代诗神所采纳的喜剧的萌芽”的态度上。由于古典主义者遵循的艺术准则是模仿自然,所以他们在贬低喜剧的同时,还“禁止滑稽丑怪和崇高优美的结合,禁止喜剧融于悲剧”。但是在雨果看来,“我们时代的诗,就是戏剧。戏剧的特点就是真实。真实产生于两种典型,即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的非常自然的结合,这两种典型交织在戏剧中就如同交织在生活中和造物中一样。因为真正的诗,完整的诗,都是处于对立面的和谐统一之中。”因此,浪漫主义文学不仅承认喜剧的审美价值,而且认为只有将喜剧和悲剧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诗。在这篇被后世视作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宣言的序言里,雨果系统地阐释了浪漫主义文学的诗学纲领与审美原则。以此作为参照,那么霍夫曼的幽默戏剧理念显然应该被归入到浪漫主义文学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霍夫曼在《公主》中以主人公吉里奥作为一名演员的成长历程作为线索,对歌德戏剧表演理论展开的批判,不只体现了二人在戏剧艺术理念上存在的审美观点分歧,更折射出了1800年前后欧洲文学界的古典与浪漫之争。

罗威,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1800年前后的德语文学。在《文学之路》与《德语人文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