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嫣 | 托马斯·曼作品中的自然复归与生存反思
本文原载于《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感谢作者韩嫣老师和《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的支持。


摘要:德国现代派作家托马斯·曼在记叙作品《主人与狗》中构建了一只充满原始生机活力的猎犬形象,将其作为现代人的对照,探讨了人向自然状态回归的可能。猎犬宝珊以斯芬克斯的姿态出现,指引主人进行“复归”式的自我探知:它破除了主人理性的持存状态,引导其接受自然事物的感召,不断深入寻找人原始的、本性的自由。这种复归最终在两者狩猎时达到高潮,宝珊的激情表现使得主人的身体冲动与精神狂热也达到顶点,一种已然移位的、动物般的生存状态似乎成为人对抗现实虚无的可能。但当这种自我释放演变成残忍的杀戮,主人最终还是出于怜悯而遏止了暴力。小说由此为自由意志的伸张划定了道德底线。
关键词:托马斯·曼,生存移位,自然本性,自由与道德


在《善恶的彼岸》中,尼采提出“自然人”(Homo Natura)概念,认为人类生命具有动植物的渊源,自然是人类永恒的基本底稿。然而,这种“把人还原为自然状态”并不是让人重新成为自然的客体,而是呼吁人回到自然史中去探查人类本性、走向深层的自我认知。1919年,德国现代派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短篇叙事作品《主人与狗——一部田园诗》(Hund und Herr – Eine Idylle)中同样触及了这一议题。曼的作品更多地以现代生活与自然的远离为背景,将人与自然及自然事物的联结视为现代人对抗现实虚无的出口。小说中,宝珊以一种引导者的形象出现,它将主人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范式中抽离,并引领其深入原始的自然境域,踏上了回归自然状态、寻找人自然本性的旅程。从本质上说,小说借助动物的形象实现了人的生存移位,在打破现代人高度文明化的持存状态的基础上,探索人的本性特征与对自由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追求符合于尼采哲学中所谓“健康的”、充满“生机活力的”(vital)自由意志的伸张,而小说同时也对这种自由划定了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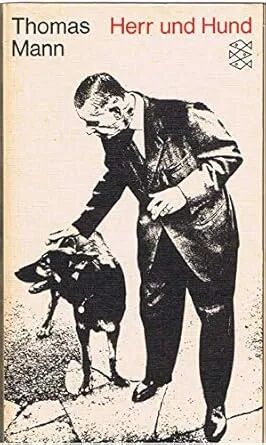
《主人与狗》封面
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曾这样描述人与动物的交互:“动物看人时,眼神既专注又警惕……动物并非在看人时才有这种眼神。但是唯有人类才能在动物的眼神中体会到这种熟悉感。其他的动物会被这样的眼神所震慑,人类则在回应这眼神时体认到了自身的存在。”人能够回应动物的眼神,这是人对于自我与他者的认定,而在目光交汇时,两者的差异将使自我不可避免与他者进行比较,其结果则是人的自我反思。由此,动物可以成为人审视自我的一种重要媒介。
在文学作品中,狗是最为常见的伴侣动物形象,它们不仅与人最为亲近,也深度参与了人类生活。许多作家都借助狗的形象来展现“忠诚”的品质,包括对主人或理想的忠诚,甚至是对于自我与本我的坚持。然而日耳曼学者罗姆希尔德指出,这里所涉及的隐喻是双面的,既指向友好的关系,也指向对原始本能与欲望的回归。他强调,仅在例如施笃姆的许多作品中,狗的形象特征就有至少两种极端的变体:一种是能够诱发恐惧的野兽、恶魔形象,即代表着冲动、本能与欲望,另一种则是人类友好而忠实的伙伴。由此罗姆希尔德认为,狗是介于尘世与天堂之间的“临界形象”(Schwellenfigur),它们既是爱神(Eros)也是死神(Thanatos)。从这个意义上说,狗的文学形象为人们编织了一张介于美德与冲动欲望之间的张力网,借助这种极端性,它们不断勾勒出人的复杂内心,隐喻出不同的生存形态。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些形象如同自由的艺术精神,能够引导人们通向自我本真。
托马斯·曼笔下的狗也兼具上文所论述的两极性与映照性。例如在其长篇小说《殿下》(Königliche Hoheit)中,贵族小姐斯波尔曼的伴侣犬佩尔西(Percy)就是一只颇具贵族气质、血统纯正、而常常表现出“歇斯底里”状态的狗:
“……这只动物非常兴奋,它具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热情本质。在酒店内,它没有抱怨,而是以优雅的姿势卧在斯波尔曼公寓前的一小块地毯上。然而每当有人出门,它都会由于不注意而遭到‘袭击’,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与震惊……结果它飞了起来,鼻子里溅满了泡沫,和它们(当地的野狗)一起在街道上狂吠,在有轨电车前激烈地表演着愤怒的回旋舞蹈。”
不难看出,佩尔西身上透露出由于过度培育,即由于过分讲究、矫饰而产生的精神病态。正常情况下它看起来端庄优雅,然而一旦遭遇刺激,这种“精致状态”便无法维持,随即变得疯狂而暴躁,或者说,回到了原始的兽性状态。相关研究认为,佩尔西身上所反映出的正是贵族阶层人群的矫饰特征。
在《主人与狗》中,主人家的前任宠物是一条同样名为 “佩尔西”的名贵猎犬,也同样具备这种精神病特征。例如它总是十分焦虑,甚至由于自己得了皮肤病、因为变丑而饱受折磨,最终主人选择将它打死。这种处理方式代表了主人对于精神病态的否认与摒弃。在尼采的学说中,过度敏感是一种精神的病态,而健康意味着昂扬向上、积极与强大的精神活力。在曼的作品中,取代佩尔西出现的宝珊即对照前者的敏感状态提供了一副极富活力的健康范式,其存在展现出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不仅如此,小说并非简单的日记,而是记录了“我”与宝珊的整体交互过程,其中分析了主人在宝珊引导下所经历的种种认识改变。由此,该作品可被视为曼对于当下生命存在方式的一段观察与思考。
在与宝珊的相处中,主人找到了新的认识可能,而这条新的认识通道正是由宝珊所打开并且引领的。这种“先知”式的特征首先在其形象建构中已有所暗指。
小说第二章首先对宝珊的外形特征进行了详细描绘:
“它的头的神态是一种懂事的正直神态,表明了品德方面的阳刚气概,也在身体方面显示出了它的身体结构:隆起的胸腔,在胸腔平滑而柔软地贴在身上的皮肤下面,肋骨有力地凸现出来。收拢的臀部,纹理似筋腱的腿,强健和美观的脚——这一切都显示出了勇敢与阳刚的美德,显示出了粗犷猎手的气质。”
粗狂、勇敢、阳刚……在主人眼中,这些气质十分宝贵,因为它代表着古老、质朴而健康的自由状态,并且这些似乎都是现代人所缺乏的。由此,宝珊的形象内涵首先指向了与现代文明化状态相对立的种种主体特征,代表着自然而古朴的活力追求。
此外,宝珊不仅仅是一只伴侣动物,而是极具个体性,其拥有明确的形象隐喻。小说首先通过强调宝珊的个体特征而尝试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亦即,相比于人们印象中的“标准德国大猎犬”形象来说,宝珊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腿要短一些,颈部有一些褶皱的“垂皮”,褐色与黑色的皮毛间还有许多混杂的白毛,形成了“虎皮状的斑纹”。此类“非常规”的身体特征也代表着宝珊这一形象的“非常规性”。而当它趴在主人脚边时,宝珊的四条腿会贴着身体,爪子向前伸出,头与胸脯抬起。小说由此揭示出宝珊的形象隐喻,或正如小说所描述的:它摆出的是“斯芬克斯那古老、刻板和偶像式的姿态”。斯芬克斯之谜是对于隐藏在复杂、神秘的表象之下的现实的指涉,而宝珊也似乎在蓦然间提醒主人去进一步地认识自己、寻找自我本真。
可以说,宝珊的形象建构出托马斯·曼小说中狗的形象的另一个维度:一种质朴的、劳动者般的存在方式,其懵懂而勇敢、健康且充满活力。其存在暗指了人的另一种生存方式:自然的本性。其隐藏在人类现代生活的表象之下,是被文明覆盖住的原始生存。宝珊的存在则意味着去揭示与探索。
在宝珊的引导下,主人开启了复归自然与探索本性之旅。这一体验得以实现的基础在于,宝珊颠覆了主人的权威,造成了其生存移位。亦即,它将主人引导到自己的生存轨迹之中,让其远离文明世界,转而从“动物般的”视角感受世界,由此逐步走向纯粹的自然状态。
这种主权关系的颠覆是在两者相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最开始,作为外来者的宝珊经过很长时间、反复几次才适应新的家庭,并归顺主人。然而实际上,也可以说从始至终,宝珊的内心都保存有对自由生活与奔跑的向往,这也是对小说强调其极具个体性、而非普通猎犬的一种印证。随着两者之间的相处愈发亲密,宝珊向主人表达自己的意志。它开始介入、或者说“打搅”主人的生活。例如每当主人回家,宝珊就立刻尝试引起其注意:它杂乱无章地扭动全身,仿佛跳着一曲“欢迎舞”,随后“充满专注与热情”地盯着主人的眼睛。它甚至通过声音、肢体与神态来表达“爱意”:“它直立起来张望,倾听我的嗓音的声调,让一种坚决赞同的强调渗入我,给我的话加上声调。突然,它把头向前伸,嘴唇迅速张开又合上……这是一种飞吻,半温柔半戏谑。”这让主人总是忍不住停下手头的事务而与其逗乐一番。在书房中,宝珊经常地用“爪子”弄脏主人书写的文字,或弄脏、扯烂房间的地毯等,由此使得书本、文字等理智生活的标志失去效力。这一点也暗示着主人理性身份的消解。
经过宝珊不懈的自我表达,主人开始对其需求予以更多的回应、甚至迁就。当一次,主人无意间观察到宝珊在梦中,亦即在无意识状态下做出捕猎与奔跑的姿势时,他的内心猛然触动:“一旦它睡着了,就开始做梦,用四只伸开的脚来完成奔跑的动作,同时还发出一种既高亢又低沉、如同腹语又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吠声……这使我感到激动和分心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首先是非常吓人的,此外,还撩拨和烦扰我的良心。”主人意识到,宝珊追求自由的天性在从属于“我”的家庭生活中很难得到满足。出于同情与愧疚,主人最终决定带它回归自然世界,而回归的形式则是每日在固定时间,前往家外未知的林区散步。外出的方向由宝珊主导,因此两者的散步活动更多的成为一种对未知境域的探索。主人借此探入了其日常很少注意到的原始林区,并由此开启了对自然与自我的重新审视。
《主人与狗》的故事有一定的现实基础。1916年,曼的家庭也曾收养过一只狗,起因及过程与作品中所记述的相似。文中所描绘的自然区域则是曼当时居住的一处未经建设的慕尼黑公爵花园,与其一同散步的还有其一位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邻居。曼则将现实中对自然的体验与认识借助故事呈现出来。小说创作于临近一战结束时,此时德国正经历政治与社会的巨大变革,而小说本身以“田园诗”为题,从表面看,似乎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背离或逃避。对此曼指出,他书写家中爱犬的故事并非想要探讨“品德的问题”或者“去追寻社会问题的答案”,而是想要通过“归园田居”的方式侧面勾勒当时的生活状态。曼在日记中也强调,回归自然是为“表达由于痛苦与战栗而引起的一种柔软情绪,以及从中产生的对于爱、温柔、善意,以及对于安宁与 感性的渴求。”

托马斯·曼和爱犬“宝珊”雕塑,位于泰根湖畔格蒙德
从本质上说,这部作品并不符合古典时期的田园题材特征,而是一种“田园诗式的”(das Idyllische)文学表现。根据学者普莱森丹兹的观点,现代田园诗拥有巨大的“文明批判潜力”,因为其创造了一种“与其他现实空间相对立的‘语义空间’”,其使得语义上的田园性在对立关系中得以呈现。曼的这部记叙同样借助自然事物表达了对于乌托邦的想象。田园式的自然图景映照出生活中感性、脆弱、隐秘的情感状态,它们隐藏在人们现实生活的表层之下,而自然的安宁、柔软与自由正是人们尝试逃避当下虚无体验的出口。对此,美国研究者哈特费尔德也将宝珊视为“曼的新(研究)方向的少有见证者”。
小说中,作者对于现实环境结构的塑造有着明确的对照与象征意义:工作、家庭与漫游的场所分别对应着现代文明、过渡点与原始自然,主人则在中心向两边摇摆,进行不同的生存体验。
具体来说,主人自家的房屋处于“一带城郊与半乡村的偏僻之中,就融合了陷入沉思的大自然与人类繁忙活动的声响。”不难看出,房屋是城区与自然区域的交界。从家中花园踏出,左边是“朝城里去的方向”,那里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有着人类社会的各式活动,也充斥着许多噪音与“世俗的混乱”。宝珊十分抗拒这些文明的混乱:“城市的喧闹也使得这只山区的狗崽不知所措。它陷入人们匆匆迈动的脚步之间,陌生的野狗攻击它的侧翼,种种古怪的气味是它从未经历过的,刺激和搅扰着它的直觉。”与主人不同,宝珊无法“理智地”在种种人造建筑与事物中找到出路,它甚至无法分辨列车的轨道,因此总是迷失在城市的地图中,有时迷路了便需要几天才能找回到家中。因此,宝珊不再跟随主人迈入城市的领地,因为那里意味着陌生、混乱与恐惧。它选择在家等待主人一同进入林区,这也是它每日最大的期盼。
从家中踏出后,朝右边则可以进入原始林区——沿着门口的林荫道走过河边延伸的砾石滩、细石路,来到被斜坡圈住的小片林地,就是宝珊散步的主要场所。主人每天都要进入城区工作,虽然没有直接表达对城市生活的厌恶,但他显然更加向往前去自然的探险。他强调,每日与宝珊的漫游是“一种稳定、简朴、专注和安逸的生活的幻想,一种完全属于你的幻想,使你感到幸福。”可以说,那条从家向右拐的自然之路激发了主人对于自身“此在”的关注,在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之中,生活的本来意义又浮现出来。

托马斯·曼位于慕尼黑的住所
在观看河流区交错的水域时,主人公与水流产生联结,得到了直观的自然感召:“水对人的吸引力是自然的,有感应的……我这个人乐于承认,水在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与形态中的直观形象,对于我是享受大自然的最直接最恳切的方式。”同时,水流的迷醉气息甚至使其进入了某种脱离时间的梦幻状态,是他自己也成为了自然的“一般之物”:“是的,真正的沉思,真正的忘却自我,自身的有限存在真正融入一般之中……使我失去了时间感,无聊成了毫无价值的概念。”在此刻,主人彻底进入了忘我的自然状态,他脱离了自身的有限性,与自然世界完全融合。世俗生活的困扰此时已然消解,主人从地理上的荒野之地进入了心灵的荒僻状态。这里的荒僻并非意指荒凉、冷清,而是返璞归真的纯净、安宁,是一种对抗现实虚无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在此处提到了“无聊”的概念,指代其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精神困扰。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说,无聊源于个体原本朴素的世界认知被某些新的价值观所冲击,传统的信念遭到挑战,由此萌生出种种“荒谬感”与虚无的存在感。卢卡奇指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大量普通的个体(劳动者)经历了客体化,亦即人的物化,而于此同时,自然本身便成为了一种价值观。他提到:
“自然——在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完全相反意义的情况下——变成为一个容器。所有一切反对不断增长的机械化、丧失灵魂、物化的内在清晰都汇聚在这个容器中。这时它就获得了和人的文明的、人为的结构相对立而有机地成长起来的东西的意义,就获得了不是人创造的东西的意义。它同时被看作是人的内心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依旧是自然的,或至少具有重新成为自然的倾向和渴望。”
由此,自然代表着一种与现代文明发展相对的概念。现代人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然人,人们在建立现代社会的同时,导致了一种不断远离自然的结果,因此也不得不面对这种形式的错误。在不断被物化的过程中,自然也许才是人真正的避难之所,是人类对抗虚无、找到自身本质存在的场域。
在一次两者共同参与的狩猎活动中,主人对生命本性状态的探知、感受与理解达到了高潮。此前,主人主要感知的是静态或单一发展的自然事物。然而,狩猎活动让主人直观地认识到残酷的自然竞争与原始的生存法则,他并由此产生了伦理层面上的感悟。
作为天生的猎犬,宝珊在狩猎时表现出本能的“狂喜”:它时而上蹿下跳、时而全身绷直警惕、时而专注寻找,时而撒腿狂奔等,十分投入。它甚至忘记了主人的存在:
“捕猎的激情已经控制了它,除了周围动物诱惑性的隐蔽活动之外,它什么也听不见和看不见。它紧张地摇尾巴,谨慎地抬高腿,悄悄地穿过草丛,在走动中又停下,让前腿和后腿各有一只抬到空中,歪起头查看,撅起嘴往地里拱,同时让竖起的耳朵的耳垂在眼睛两边朝前垂下,用两只前爪搜索,忽然向前一跃,再向前一跃,面带起疑的表情,瞅着刚才有什么而现在却什么也没有的地方。”
可见在过程中,宝珊几乎摆脱了主人的指令,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意志之中。它成为了完全自由的个体,跟随自己本能的直觉而不断行动。对此,主人一开始保持观察者的姿态,在一旁紧张、密切、并好奇地注视着。他原本不打算出手相助,想任由宝珊发挥其特长。然而随着追猎的白热化,主人深受感染,便放弃了对宝珊的“监视”,并加入了这场“战斗”:
“它的勤奋工作实在太吸引人了,它的热情感染了我……我对老鼠并不感到同情,从内心站在宝珊这一边,这使我往往不甘心充当旁观者的角色。我用手杖助阵,如果一块牢牢地嵌在地里的砾石或者一段坚韧的树根妨碍了它,我就帮他它又钻又挖,清除障碍。然后,它就在工作中朝我表示赞许和激动地快速撇一眼。”
此时,宝珊对主人投以回应的目光,确认两者完成猎人与猎犬的身份转换——充当“助手”的主人成为了宝珊狩猎的工具,宝珊则成为了完全的主导者。实际上在诸如追查气味、捕捉、跳跃等行为层面,动物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因此主人能够给予的帮助并不多。然而更重要的在于,在这种完全移位的狩猎体验中,主人开始与宝珊产生共振:他在脑海中想象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行为,仿佛他像宝珊那样,凭借出色的身体素质完成了激烈的追捕。由此,两者共同步入了身体与精神狂热的高潮。
一直到宝珊开始啃食猎物之前,主人都认为宝珊的表现是 “完全健康的……它的内心激动完全是保持在健康的热诚范围内,从没有触及歇斯底里的界限。”在他看来,宝珊身上不同的情感,不论是快乐或痛苦,甚至无聊、郁闷,都极为饱满且不加掩饰,这正是内心健康且生命力强大的表现。日耳曼学者戈贝尔指出,狩猎的狂喜与性欲是两种并行的绝对狂热状态,小说创作于战争年代,后者则在这一时期显著缺乏,因此狩猎成为宣泄生命力特征的重要场景。在这种背景下,宝珊的极致活力与真诚的欲望表达正是主人一直追寻的、用以逃脱现实生活困境的自然本性的力量。
然而,正如“欲望”“本能”“冲动”等词汇中所蕴含的贬义指向,这种本性的表达不出意外地导向了一种极端结果。在一次成功猎捕后,宝珊忍不住将猎物“活活吃掉”,而这种嗜血(Blutdurst)的本能激发了主人的恐惧。他描述到:“宝珊咬住小老鼠的尾巴,在地上来回摔打两三次,可以听到微弱的吱吱声,这是遭上帝摒弃的小老鼠发出的最后的声音。然后,宝珊就吧嗒一口咬住小老鼠,叼在白牙之间。”面对残酷的生存竞争,主人似乎与老鼠一同战栗起来,并感到自己“浑身有些发冷”,却只能对宝珊“怀着感到恐惧的赞赏”说:“你真是个角色!”与此同时,主人作为宝珊“助手”的听从性立场开始动摇。
在两者最后的猎兔经历中,主人终于对向自己求助的野兔施以援手。在追逐中,宝珊与兔子最初不相伯仲:兔子“卑微或胆小”,总是缩着脑袋飞奔而逃,而兔子善逃跑,它“在耐久的敏捷方面还是胜过了宝珊”;宝珊则在其身后狂吠紧追,它的步伐巨大,却无法像兔子那样灵活地跑窜。对此,主人的心情在这场拉锯中也不断改变。最初他站在宝珊一边,焦急地为其鼓气,希望它得胜,甚至“在嗜杀成性中跟在后面徒劳地叫喊”。然而,兔子的突然“转向”使得他情感骤然改变:
“是它害怕的昏了头吗?够了,反正它在我身边蹿起来,就像一只小狗那样,用前爪攀住我的外套,脑袋直直地钻进我的怀里,钻进猎狗主人的怀里!我抬起胳膊,上身后仰,站在那儿,俯视着兔子,它也抬头望着我。只有大约一秒钟,或者只是一刹那,但确实是这样。我看见它清楚得令人惊奇,看见它长长的耳朵,……我感觉到或者自以为感觉到,它那颗被追逐的小小心脏在悸动。”
在这次由于意外相撞而造成的目光交汇中,兔子细微的神态与表情使主人感受到其生命的悸动与震颤。这将主人从原本的狂热(嗜杀)状态中陡然抽出。他突然意识到兔子作为一种他者与弱者的生命存在,并萌发了深深的怜悯之心,由此跟随着兔子进入了新的情感世界。他甚至立马为自己建构了新的身份——兔子的主人。出于保护这位“投靠者”的心态,“兔子的主人用手杖有目标和深思熟虑地敲了一下,于是它(宝珊)尖叫着用意志暂时麻木的后腿往右边的斜坡下面踉跄了一段路……结果晚了很久才重新开始追踪那只此刻已不见踪影的兔子。”主人用暴力的方式中止了宝珊的猎杀,原本用以帮助宝珊的“手杖”,此时转而成为了它的封禁,两者的身份又再度恢复原有秩序。
一段时间后,宝珊得了一种流血不止的怪病,这击垮了宝珊的身体,使其“丧失了所有自尊与高尚,跌入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低谷”。这场怪病一方面暗示出其过度使用血腥与暴力所产生的后果,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宝珊作为死神的隐喻。面对这种状态,主人出于健康的考虑开始限制宝珊的外出,而这使得两者的关系一度转为冷淡,宝珊也意志消沉。从这里可以看出,主人并不能完全驯服宝珊的动物天性,宝珊带领主人所进行的复归于自然的旅程在这里也戛然而止。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正在于人与动物的不同:动物完全跟随自己的欲望追求而活,它们是自由而自为的,但仍然生活在原始的自然法则之下,物竞天择;人则具有同理心,会进行道德的评判,在面对全然的暴力时,人还有进行选择的可能。如果小说原本旨在说明,人向原始动物状态的回归是一种逃避现代生活困境的出口,那么兔子的出现则为这种转化划定了界限。小说借此强调,人们应该将对生命热情、活力、欲望与冲动的发掘止步于暴戾的杀戮,应坚守住道德的底线。
在故事的最终,主人与宝珊看似走向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但实际上,主人对于伦理的思考是建立在与宝珊共同“复归自然”的过程之上的。作为复归的引导者,宝珊对主人的生存认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文将对此整体过程进行复盘与分析。
从整体上说,宝珊的出现本身即意味着“打断”。它首先打破了主人仅仅需要一只“看门狗”的意图,并与其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随之,通过不断搅扰主人原本的生活秩序,尤其是其工作或从事理性活动的秩序,宝珊在引起主人的注意的同时,消解了主人身上的理性符号,使其与自身产生认同。这为主人回归自然状态打下了基础。
回归林区则是宝珊作为动物(猎犬)真正的本性追求,也是其作为家庭宠物与自然生物存在的分野。主人则借此契机,跟随“原始状态的”宝珊,在不断深入自然的体验中获得了“健康化”的感受。更准确地说,他得到了逃避世俗烦扰的幸福与满足感,收获了舒适与安心。戈贝尔指出,作品通过这种“生存移位”的方式将人的形象带入了一种有关于“生灵”(Kreatur)概念的现代性话语范畴中。或者说,作品将人的形象进行了重塑,剥去了人的文明外壳,使其回归生命的本来状态,在远离世俗的环境中,人重新找到与自然的联结。这里的回归并非指人退化至非文明化状态,而是重现人不得不承认的自然根源。在这一层面上,人与动物是平等的,也只有在这种感知体验中,人能够超越世俗,走向对自我本质的认知。
宝珊在狩猎活动中的表现则代表着一种强烈的生命范式:不论是其寻觅时的专注、捕猎时的爆发、以及捕猎失败后的失望与无聊、甚至抱怨,无一不展现出强大的生命渴求。宝珊就像是尼采哲学中所描绘的具有坚忍、勇猛意志与能力的代表,它通过克服与超越自我而成为具有价值的、自然生命中的强者。这种状态似乎也是作品试图展现的、对真正的生命活力状态的追求。宝珊在狩猎时的专注与狂热使得主人不断被吸引、感染、最终加入,使其从城市生活的颓废状态走向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高潮:他用手或者手杖协同宝珊的爪子,共同“投入疯狂的工作”,并加入了“嗜杀成性”般的激情呐喊。在此处,不仅主人“手”与宝珊的“爪”获得了同一化的定义,两者的生命状态也进入了共振,变得原始、疯狂而激情。主人幻想为宝珊冲撞厮杀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其所试图进行的理性合作,而更多的是全然的自我释放,其内在的原始冲动达到了顶点。
随后,当宝珊突然生病,两者同时感受到意志的垮塌。宝珊似乎回到了其被困在山区厨房中、与主人初次相见时的样貌:畏缩而疲惫。与此同时,主人似乎也陷入了健康危机:“自从宝珊被隔离后,我确实享受到了某种本已不再体验到的精神独立……我的健康情况不佳,我的状况同宝珊被关在笼子里的状况简直异乎寻常的相似。我作了道德上的思考,同情的束缚对我的健康来说比我所渴望的自私的自由更有益。”在这里,主人其实已经认识到击垮两者意志的根源,亦即,像宝珊那样向自我本真的回归虽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由状态,但同时也是一种自私的暴力状态。为了自身与他者的健康,主人最终选择通过强制性的“束缚”来中止这种无止境的意志伸张与对本性欲望的纵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人的自我释放几乎到达极端的时刻,道德成为了最后的包裹界限,使他没有触及到残暴的顶点。小说对人与动物行为所塑造的分野体现出托马斯·曼思想与尼采哲学的不同。尼采将道德行为视为对现实的顺从或自我伪装。他指出:“动物与道德……隐藏个人的才能和强烈愿望;与环境同化、顺从等级秩序,自我贬抑,所有这些为上流社会所要求的做法,作为原始形式的社会道德普遍存在,甚至见于低等的动物世界。”亦即,道德的本质是一种利己性的表现。根据这一观点,宝珊出于生存的需要而顺从于主人与家庭,这即是一种道德行为;它在家中常常小心翼翼地表现,则是出于对生存的“谨慎”与自我控制。然而在曼的作品中,道德行为更多是出于“保护”,是一种理性的衡量,是利他性的。宝珊的生命力最终停留在“嗜血”与“出血”的临界点,这似乎也是作品将嗜血与杀戮最终描绘为一种“病态”的讽刺。
尽管如此,在接近于嗜血的状态中,主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自我,感受到一种回归自然本源的状态。也可以说,人、动物都具有相同的本质,不同的情绪、感受随着自然情状的改变而变化,生命之流如水流一般发展变化,人们也应当顺应如此。在《歌德与托尔斯泰》中,托马斯·曼这样描述有关“人性”的问题,他提出,动物性才是本质性的存在:“动物性总是在不断超越。所有卓越的都是动物性的。亲近自然的、感性的烦躁会跨越本来的感性界限,并流入先验的、自然神秘主义的世界。”这一论断也可视为小说通过人与狗之间的交互而试图展现的一种对于自我、以及对生存本身的反思。
在这部记叙作品中,曼通过细致的动物观察与自然体验,提出了对于现实生存的理解与反思。以西方现代社会中城市发展、人的物化,亦即以无聊、空虚的存在困境为背景,作者尝试在“田园式的”自然境域中找到对抗世俗烦扰与现实虚无的可能。宝珊作为斯芬克斯式的隐喻形象,引导主人逐步回归自然状态。以宠物的身份为出发点,宝珊通过不断地自我表达,最终成为了自由意志的主导者。在其带领下,主人不仅在与自然事物的联结、感应中得以专注于自身,找到了此在的生存意义;同时,还在宝珊狩猎的激情中进入了精神的狂热状态,感受到生命原始的欲望冲动与生机活力。一种接近于动物化的激情状态成为其战胜世俗状态、消除现实烦恼的良药。但作品同时也探及了这种无限释放本性意志的危害与底线。主人公没有放纵这种本性的“自由”不断发展,而是使其止步于一种以敬畏与保护生命为核心的道德底线。

韩嫣,德语文学博士,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化学理论、现代德语文学、动物诗学等。近年在《外国文学》、《德语人文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独立译著3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