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炜 | “奥地利的本质不是中心,而是边疆”——约瑟夫·罗特笔下哈布斯堡神话中的加利西亚

约瑟夫·罗特1925年在巴黎
【摘要】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是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犹太人,对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有着深深的眷恋。直至今日,他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都还是奥地利文学中哈布斯堡神话的代表性作品。小说主人公卡尔·特罗塔的故事结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边疆区,这个地区经常作为故事背景出现在罗特的作品中,与当时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和极端排他的意识形态相对立,构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这为梳理作家的文学创作之路提供了线索。加利西亚作为中心和边疆所表现出的对立关系,体现了时代的特殊性。同时,根据阿莱达·阿斯曼的回忆空间理论,罗特笔下的加利西亚作为一种文化记忆也成为构建哈布斯堡神话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约瑟夫·罗特;加利西亚;哈布斯堡神话
//
一、引 言
//
加利西亚作为地理概念,在历史上曾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争夺的目标。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解体后,其东部的加利西亚地区被划入波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的1916年,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作为少尉军官曾在东线服役,所以他对加利西亚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当《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在1926年派人远赴苏联进行采访时,首先想到的人选就是了解当地情况且擅长游记报道的罗特。
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边疆区早在约瑟夫·罗特1924年的旅行报道中就已出现过,但读者读到的多是描写和介绍当地风土人情的内容。在1926年苏联之旅后,加利西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所以有研究者指出:“他把对皇权时代的‘回忆’与对东欧边境的记忆,变成了丰富的小说素材。”除了作为故事背景外,加利西亚也越来越多地承载了作家对过去时代和逝去家园的怀念。他通过“突出地流露出一种讴歌自然的乡土情感”,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家园的寄托,即阿莱达·阿斯曼所说的“带有特殊记忆力的代际之地”。在约瑟夫·罗特的文学作品中,加利西亚边疆区以及那里的居民显得冥顽不化,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中更是落后、混乱的代名词,被视为“贫穷的东欧正统犹太人的家乡”和“维也纳已同化的西欧犹太人的令人羞惭的亲戚”。但恰恰是在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身上,作家寄托了一种朴实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种对生命的向往和尊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动荡与纳粹上台后的恐怖暴力中,这种人文精神显得弥足珍贵。所以《先王冢》(Die Kapuzinergruft)里的主人公约瑟夫·费迪南·特罗塔才会说:“奥地利的本质不是中心,而是边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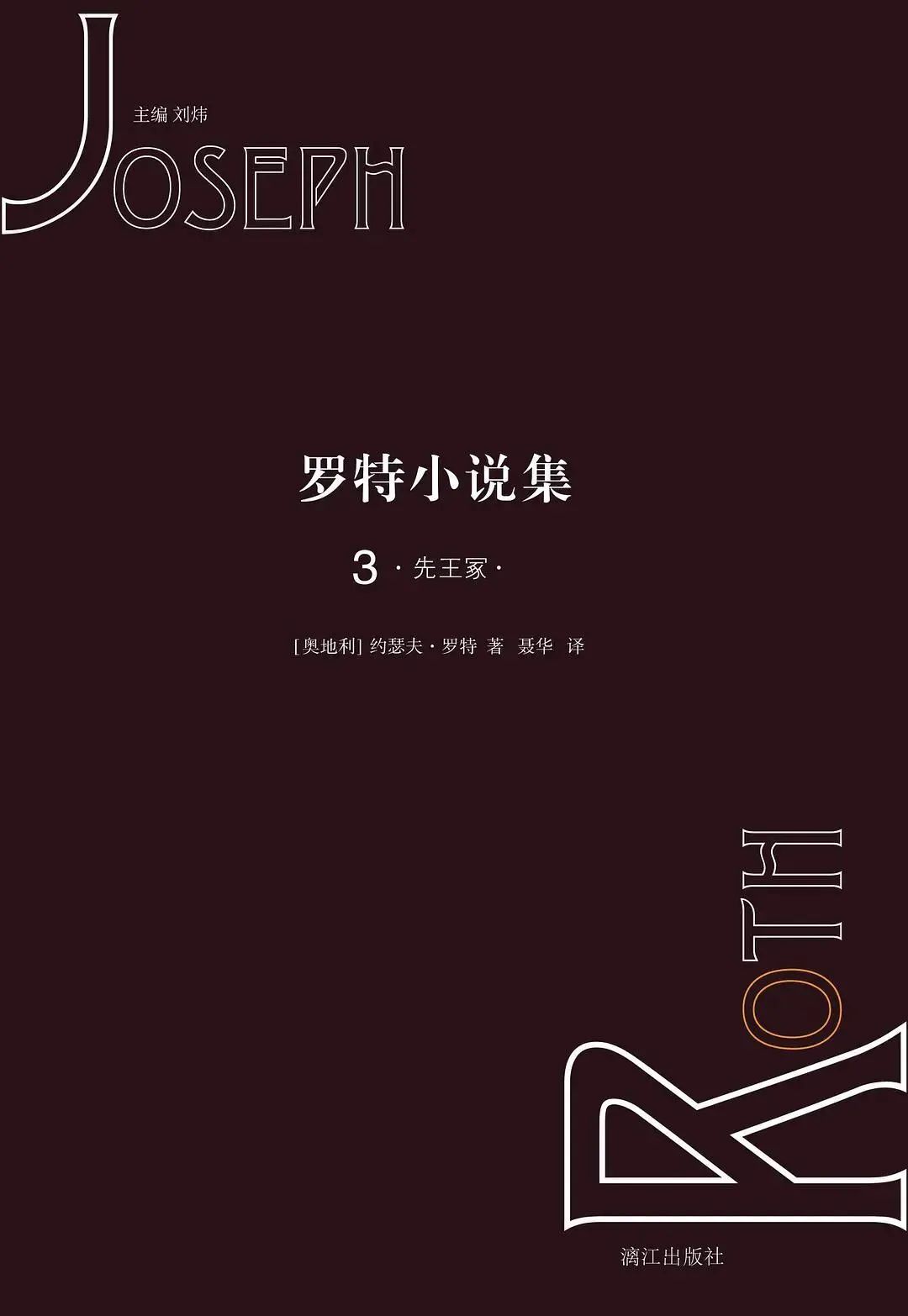
//
二、约瑟夫·罗特的回归之路——从边疆到中心再回到边疆
//
1894年,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出生在利沃夫州布罗德区(Brody)的一个犹太家庭。当时这里还是哈布斯堡王朝东部加利西亚边疆地区的一座小城镇,距离沙皇俄国的边界不远。当地居民信仰不同宗教,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家本人都刻意隐瞒自己的出身。因为当时出生于加利西亚的东欧犹太人在西欧大城市谋生不易,经常被人冷眼相待,甚至恶意取笑,所以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官方注册文件中,都将自己的出生地填写为德国人在东欧地区的一处飞地——施瓦本村(Schwabendorf)。不过,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到处都能看到加利西亚边疆区的影子。1913年,约瑟夫·罗特离开故乡前往当时加利西亚地区的首府伦贝格(Lemberg)上大学,即今天乌克兰的利沃夫国立大学,随后又转入维也纳大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是一座拥有无限活力和可能的城市,对来自帝国东部边疆区的年轻人有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吸引力。年轻的约瑟夫·罗特梦想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在这个老帝国的中心构建自己的未来。此时还带着世纪末维也纳现代派余晖的这座城市,给当时和后世的人们都留下了无限遐想和阐释的空间。甚至在2006年出版的《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一书中,作者克莱夫·詹姆斯也以书写老帝国辉煌时刻的维也纳作为自己鸿篇巨制的序章,因为“这个理想城市是真实存在的,拥有现实世界的一切纷繁复杂”。对此,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在他的学术经典《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中,以文学、音乐、建筑、政治为例,绘制了一幅令人神往的全景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约瑟夫·罗特这样的犹太人而言,这座城市当时有约10万犹太居民,是中欧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同样地,犹太文化精英也反哺了这座城市。没有这些人的参与,文学和文化史中的维也纳现代派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使这个从边疆区来帝都闯世界的年轻人的梦想彻底化为泡影。战争爆发两年后的1916年,约瑟夫·罗特报名参军,在靠近前线的军事通讯社服役。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奥匈帝国开战伊始就经历了一系列屈辱的惨败,战争初期的狂热很快就被现实的残酷所熄灭。1918年,奥匈帝国战败解体,约瑟夫·罗特在自己的家乡突然成了“外国人”。而在昔日的帝都维也纳,他又沦落为来自前边疆区的穷困潦倒的异乡人。在这种身处边疆与中心的交替变化中,年轻的约瑟夫·罗特必须要面对和承受身份认同危机带来的种种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位重返维也纳的年轻人试图继续自己的梦想,他靠给报社撰稿糊口,并很快成为颇受多家杂志文学副刊欢迎的撰稿人。除此之外,他同时期的几部文学作品如1923年的《蛛网》(Das Spinnennetz)、1924年的《萨沃伊饭店》(Hotel Savoy)和《造反》(Die Rebellion)很快得到了文坛的认可。在这些作品中,年轻的罗特针砭时弊,展现了自己的社会批判视角。他甚至在一些报纸文章上用自己的名字玩起了文字游戏,署名“红色约瑟夫”(Der rote Joseph)。在这些作品中,他都以自己熟悉的大城市底层民众为对象,刻画他们战后生活的艰辛以及社会对底层人民的压榨。
1926年,已是著名记者的约瑟夫·罗特受《法兰克福报》委托考察了苏联,并撰写了一系列旅行报道。这些报道中的很多细节,都作为故事背景出现在他此后出版的一系列以苏俄内战为背景的小说中,如1927年的《无尽的逃亡》(Die Flucht ohne Ende)、1928年的《齐珀和他的父亲》(Zipper und sein Vater)、1929年的《右与左》(Rechts und Links)和《沉默的先知》(Der stumme Prophet)以及1930年的《约伯记》(Hiob)等。同时,这趟旅行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对此,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记录了在莫斯科与约瑟夫·罗特的一次会面,后者曾向前者坦诚:“我几乎是作为一名有信仰的布尔什维克来到了俄国,但却是作为保皇党离开了这里。”这种变化自然体现在了罗特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笔下的故事背景已经不再局限于城市底层社会,老帝国边疆区的加利西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其小说创作中。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对约瑟夫·罗特这样的犹太人而言,突然在自己世代居住的家乡变成了“外国人”,这种无家可归的伤感使他在作品中塑造出一个理想化的故乡,让他对作为现代文明中心象征的维也纳也有了一种疏离感。不过这种疏离感并不强烈,因为书中的人物还是用一种城里人看乡下的眼光去俯视老帝国曾经的边陲,而作家刻意营造出一种异域风光以体现其与文明世界的脱节。
在紧随而来的20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中,作家本人在城市生活中亲身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如极端思潮的泛滥、社会阶层的割裂和冲突以及政局的混乱。在此背景下,这位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犹太作家对逝去的时代产生了眷恋之情。其1932年出版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Radetzkymarsch)正是这一时代背景的写照。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半年之内再版五次,直到今天都还是现代奥地利德语文学中“哈布斯堡神话”的代表性作品,有“文学教皇”之称的德国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将其列为德国人必读的二十部小说之一。不过,昔日的帝都已经不再是令人仰视和追求的目标。在这部小说中,帝都维也纳的精致细腻虽然与边疆加利西亚的不修边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主人公——作为特罗塔家族第三代的卡尔眼里,加利西亚已经不是城里人眼中荒蛮的异域边陲,而是昔日家园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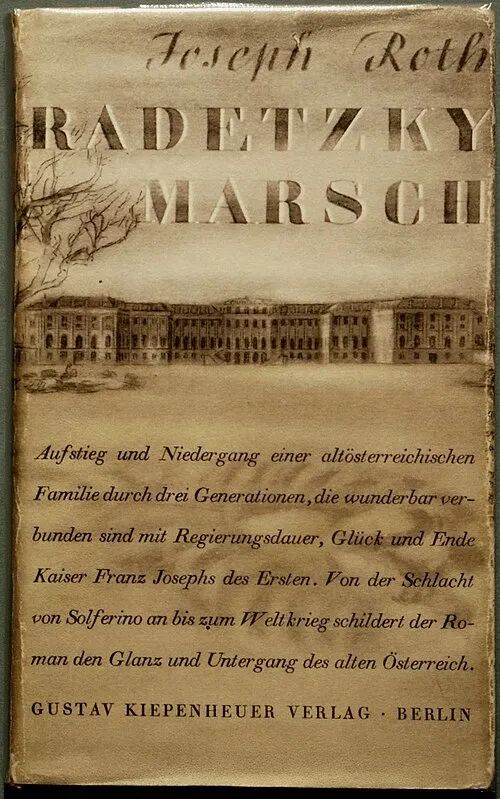
1933年1月,在希特勒被任命为魏玛共和国总理的第二天,罗特便乘早班火车逃离了德国,踏上了流亡之路。之后,他对昔日哈布斯堡王朝挽歌式的追忆更加清晰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表现就是对过去时代美化、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创作思路。在当时反法西斯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思路往往为左翼作家所诟病,被贬斥为逃避现实或缺乏斗志。例如,左翼文学理论家卢卡奇(Georg Lukács)虽然高度评价了《拉德茨基进行曲》这部小说,但又指出作家存在“理念上的弱点”。左翼作家们认为,正直的作家除了与法西斯展开针锋相对的正面斗争外,绝无任何其他可能。
此时德国的纳粹主义已成气候,极端排犹、仇他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使罗特看到现实政治中的危险与绝望。纳粹德国先是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收回了萨尔区,接着又单方面取消了《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宣布重新武装德国,还与法国、波兰等邻国签订了一系列和平条约。希特勒不但巩固了政权,还骗取了德国民众的好感。可以想象,像约瑟夫·罗特这样的犹太裔流亡作家,在面对纳粹的所谓“文治武功”时,该是怎样的绝望与愤怒。在与纳粹的斗争中,约瑟夫·罗特的思路与众不同。他认为奥匈帝国的传统和基础是多民族共生,具有宽容性和包容性,这与纳粹政权叫嚣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天然互斥。在他眼中,民族并非一定会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今天的学者如阿莱达·阿斯曼在其新著《民族的重塑——为什么我们惧怕和需要民族》一书中也同样指出:“把民族与民族主义相提并论是危险的。”既然如此,恢复已经崩溃的多民族共同体——哈布斯堡王朝,就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击垮纳粹德国这种狭隘排他的单一民族主义政权。但在罗特流亡的20世纪30年代,这一思路实在难以令其他流亡者接受,不过罗特依旧坚信其中的底层逻辑。于是,在他流亡时期的作品如《塔拉巴斯——一位大地上的过客》(Tarabas. Ein Gast auf dieser Erde)、《假秤》(Das falsche Gewicht)、《皇帝的胸像》(Die Büste des Kaisers)、《先王冢》中,就可以看到一个与纳粹统治下充满血腥暴力的第三帝国截然相反的加利西亚。对罗特而言,这个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虽然显得落后甚至荒蛮,却构成了奥地利文学中哈布斯堡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拥有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善的守护。因为承载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传统的不是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维也纳,而是地处边缘的加利西亚。这种从边疆到中心、再回到边疆的历程,展现出来的是约瑟夫·罗特内心世界和身份认同的回归之路。他在描写加利西亚的自然与人以及在构建笔下文学世界里的哈布斯堡神话时,寄托的还是奥地利文人自启蒙运动以来所秉持的人文理念与学统。
//
三、加利西亚的自然——严苛中的生机与豁达
//
这个地区的人一辈子走不出沼泽地,因为整个土地的表面都布满了大量的沼泽,大路两边尽是青蛙、热带菌和险恶的草丛,这种草丛对于毫无戒备或是不熟悉地形的行路人来说乃是引向可怕死亡的一种可怕的诱惑,许多人在此丧命,连他们绝望的呼救声都没人听见。
这片土地倾诉的一切很可怕:大雪、阴暗、寒冷、冰柱,尽管日历宣告了春天的来临,尽管波斯尼亚的驻地斯普里耶的森林里,紫罗兰早已怒放。但是这里,在茨洛托格罗特地区,乌鸦却还在空落落的牧场和栗子树上发出嘶哑的哀鸣。它们成堆地挤在光秃秃的枝丫上,看上去一点不像鸟类,倒像是长了翅膀的果实。小河的名字是施特鲁明卡,还沉睡在厚厚的冰面下。
这一年,流浪汉都急不可待地盼着春天的到来。还要再等好久,这个难熬的冬天才打算离开这个国家。冬天在各处扎下了成千上万细小、化解不开还分着叉的冷冰冰的根。它既深深地侵入地下,也高高地悬在地上。在地底下把种子冻死,在地上把灌木和草冻死。甚至连林子和路边树木里的汁液看起来都永远冻僵了。农田和草地上的雪融化得很慢,只有在中午很短的几小时才会化。但在阴暗的深谷,在路边的坟墓里,冬天还是明确而且顽固地蛰居在冰晶上。现在已经是三月中旬,房檐下仍挂着冰凌,即使在中午阳光的照耀下,也只有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在融化。当阴影在下午重新降临时,冰凌又再次冻得硬邦邦、亮晶晶。林间大地还在沉睡,树冠间也还听不见一声鸟叫。天空依然故我地呈现出凛冽的湛蓝色,可春天的鸟儿却都躲着这种可怕的晴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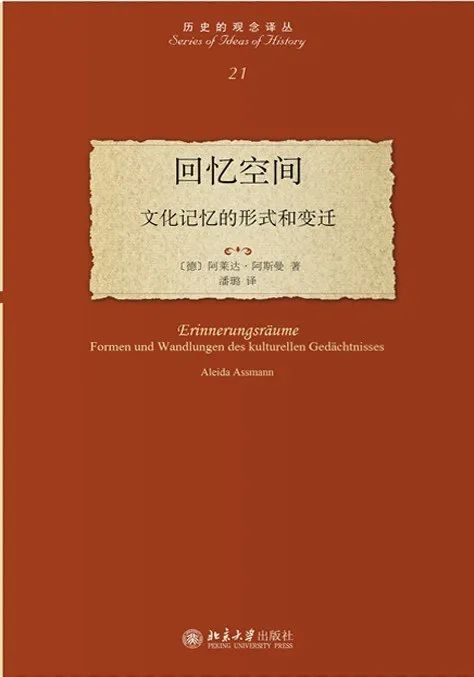
//
四、加利西亚的人——冥顽不化中的是非善恶
//
约瑟夫·罗特笔下加利西亚的居民受自然环境的限制,被隔绝于现代西方文明之外,自然秉持着与所谓文明人大相径庭的生活理念,其身上原生态的顽劣也为现代文明所不齿。这展现给读者的正是阿莱达·阿斯曼所强调的“人与地点之间的紧密联系:地点决定了人的生活以及经验的形式”。例如,在罗特1924年的报道《人与地方》(Leute und Gegend)中,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在西欧,这片土地恶名在外。”当地人显得卑微甚至猥琐,榆木疙瘩般的脑袋冥顽不化,却又与周围环境默契合拍。又如《草莓》中的主人公纳夫塔利·克鲁依,出生在一个破败不堪且没有亲情的家庭。为了生存,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四处流浪。可当他讲述自己在常人眼中的悲惨人生时,他似乎轻松地承载了生活中的一切苦涩,给人一种回首往事不过如此的洒脱。在叙述者的家乡好像没什么“好人”,他甚至以“骗子”自称,用自豪的口气讲述家里的种种不堪。书中逐一登场的是爱贪小便宜的裁缝、寄食在别人家的玻璃工、破产的美国律师、卖假表的商人、传播谣言的市侩等人物。在这些看似片面的众生相中,没有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画面。罗特在这些人物身上颇费笔墨地营造诙谐甚至引人发笑的效果,然而,恰是在对这些细节的刻意描绘上,表现出的是阿莱达·阿斯曼在关于文化回忆空间的论述中所说的个人或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在作品文本中,这些画面构成了作家和人物之间的一种“自己人”的身份认同。
一件件荒诞奇闻拼凑出了加利西亚居民的画像。作家将这些看似愚昧落后的人物形象植入作为精神家园的哈布斯堡神话中的加利西亚边疆区,形成了其与以城市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对立。恶劣和艰苦的环境不会熄灭人们心灵上的希望之光,也不会淡化他们彼此之间的人情味,这与西方文明世界中的人情冷漠、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绝情、狭隘民族主义的恶意排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看似自曝其短的描述中,读者看到的却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道貌岸然和人文精神缺失的批判。所以,罗特的女友科伊恩在1936年陪他最后一次返回家乡时,发现罗特对当地虔诚的犹太人“尊崇如同圣贤,那些人性本质是西欧人无法度量的”。

罗特幽默和伤感的叙述展现给读者的是“自己人”所特有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与弥漫于现实中的绝望与颓废相对立,体现了讲述者在面对不幸的现实时所表现出的坚韧和豁达。作者用“草莓”作为一部书写故乡的小说的标题,其寓意十分明显:它是严冬中人们的希望和期盼,其顽强的生命力是严峻条件下得以生存的保证。自然界的草莓每年春天如约而至,唤醒了人们对于生的希望和憧憬。而叙述者以某种玩世不恭的洒脱态度回首曾经经历过的坎坷,正如弗洛伊德分析幽默时曾指出的那样,展示了他自信的态度和带有些许自恋情结的自我欣赏。与此同时,艰辛困苦的环境往往会造成人性的扭曲,或给人的恶行提供口实,甚至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攻讦的借口。而文中的边境百姓,在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以满足后,不曾因恶劣的条件步入歧途,在艰难困苦中依然能够保持人性不恶,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褒扬的生存智慧和人文主义精神。
罗特笔下的加利西亚边境百姓表面冥顽不化,但其依然拥有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对比那些以“文明人”自居的城里人起到了反讽的效果。潘达莱沫这样的小偷,本来可以利用伯爵出门的机会大发一笔横财,但他却在给伯爵看门时忠于职守。丑陋的表象背后,是知足的善良心态。而那些现代人的所作所为却是另一番景象:新贵沃尔夫一到,就占用了本地唯一宾馆的所有房间;在英国发了财的勃兰德斯强占了当地百姓的休闲空场,用来盖一座仓库。在这些外来的所谓文明人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损人利己、贪得无厌的秉性。他们已经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判断好坏的标准,与本地居民纯朴的内心本质相比,更显得丑陋不堪。
在加利西亚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当地小人物身上却很有人情味。《草莓》中的裁缝和玻璃匠虽然是死对头,但彼此间的龃龉也仅限于小打小闹,最终还是以互相妥协容忍而收场。小人物之间的恩怨,在这里不会演变为族群间的冲突,更不会出现为了私利而人为恶意制造族群之间冲突的情况。在成书的1929年前后,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中,罗特的精神家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便有了现实的意义。
与罗特笔下加利西亚严苛的环境和当地人的关系一样,故事中的当地人与所处的社会也彼此包容:“我们这一带混住着不同的民族,彼此间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交流。”简单的一句话,就赋予了家园具体的含义:不用担心族裔、语言或信仰背景,包容给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生存勇气。可以设想,对于当时无家可归的犹太人来说,这样理想化的精神家园显然令人怀念和憧憬。
这种包容作为罗特笔下加利西亚的标志,还表现在百姓与统治者之间近乎理想化的和谐关系上。在短篇小说《皇帝的胸像》中,在强大却没人情味的国家机器与普通百姓之间,充当缓冲器的是当地以统治者身份出现的老伯爵。他所具有的“乐善好施”的性格,决定了他在行使职权时所做的往往是“体面的善事”,例如豁免税务、兵役和各种法外施恩的宽宥与庇护。老伯爵的权力与威信并非建立在强权和暴力的基础上,而是一种和谐秩序的延续。换言之,老帝国严峻面孔的背后,也有“睁只眼,闭只眼”的宽容。
罗特笔下的加利西亚以奥匈帝国的没落为界限,描述了对比鲜明的两个时代。在对社会现实的书写中,作家以揭示“丑陋”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在对往昔的回忆当中,作家流露更多的是温情。他塑造出的乌托邦化的理想家园同时也是一首故乡的挽歌。他虽然着力描述环境的严苛与小人物的卑微,但带给读者的却是会意的微笑。
//
五、约瑟夫·罗特哈布斯堡神话中的加利西亚
//
约瑟夫·罗特笔下的加利西亚,就像未完稿《草莓》所蕴含的象征意义那样,严苛之中总有网开一面。于是读者看到了故事里当地老百姓走私、行贿、赊账、耍赖,法律条文似乎也变成一纸空文。在规章制度的执行者与做出违规违法行为的当地百姓的较量中,最终都是以草民“得逞”而收场。在《草莓》中,气急败坏而又徒唤奈何的是严守纪律的护林员,而获得实惠的却是违禁偷采的当地百姓。这种看似违反传统价值体系的构思,在罗特笔下反而是用来描绘昔日太平盛世的夸张手法。在哈布斯堡王朝解体后,他作为犹太人不但要承受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还要额外面对针对犹太人的敌意和迫害。这使罗特在对加利西亚有选择的记忆书写中,更加突出了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怀旧情结。
同样,以《拉德茨基进行曲》为代表的哈布斯堡神话也是对过去时代有选择的演绎,是一种对老帝国时期具有标志性现象的集体记忆,在过来人的会心一笑或扼腕叹息中被唤醒。所以,罗特笔下的加利西亚如阿莱达·阿斯曼所指:“地点本身可以成为回忆的主体,成为回忆的载体。”罗特的描写尤其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善于营造伤感怀旧的气氛。如此一来,遥远的边疆区在文学世界中被抽象为一种情怀,并被植入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理想化信念,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家园。这种对远离现代文明的边远地区的理想化与乌托邦化的情结,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安全感的渴望和对价值体系崩溃的无奈。
一种现代文学叙事既然被贴上“神话”的标签,便说明其文本内容与历史史实之间存在较大出入。在奥地利文学的哈布斯堡神话中,这种文史之间的差异表现的是作者在现实困境中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如同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中所说,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奢侈享受,明日的真理完全是今日的谎言的颠倒”。在纳粹政权蛇鼠横行的20世纪30年代,到处充斥着极端暴戾和排他的种族主义的叫嚣。在这种背景下,加利西亚的多民族、多种族、多信仰共存共荣的画面便承载了象征意义和现实价值。如同在《第1002夜的故事》里主人公的家乡,“市长是个德国人,属于萨克森移民中少数溃散后留在当地的一个。管账的账房来自摩拉维亚,农民是喀尔巴仟地区的俄国人,已经聋掉了的男仆是个匈牙利人,……护林员是个来自加利西亚的鲁提尼人,乡村警队的警官是个普莱斯堡人”。不幸的是,这种文学演绎与真实历史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为在历史上,奥匈帝国从未将超越民族的思想和秩序当成自己的执政理念和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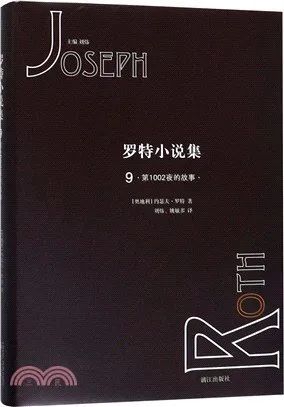
不过,罗特笔下的加利西亚并非简单的历史演绎,也非粉饰太平之作。这些画面一方面是作家对昔日帝国社会与文化的洞察,另一方面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警示,所以其中包含着很多充满黑色幽默的反讽和鞭辟入里的解析。换言之,罗特笔下的加利西亚是作家由于对现实的失望而展开的对过去时代夸张、片面或管窥式的强调。作家利用回首往事和对现实世界的置若罔闻,塑造了一个“向回看的乌托邦”。
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虚拟叙事,理想化乃至神化的写作方式也是文学中常见的手段。但哈布斯堡神话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神话中郑重其事的宣教不同,其中的内容都是作家自身的感知和情绪的宣泄。在罗特笔下,这种过去的祥和时光会具象为人所熟识的景象和色彩,如加利西亚秋天游商小贩烘烤栗子的香味,又如人迹罕至的边疆区的落日余晖。可以想象,在战后的混乱中,作家向往的是一种与现实不同的世界和价值取向,就像罗兰·巴特所说:“神话修辞术必定与世界保持一致,这一世界却并不是它本来的面貌,而是它想要自身成为的那种面貌,既是对现实的理解,又是与现实达成的默契。”这更说明当时的文人作家对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治下老帝国的重塑和演绎与现实密切相关。
翻开以约瑟夫·罗特为代表的一众犹太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这些曾生活在奥匈帝国时代的犹太知识分子对没落的帝国满怀深情,这与犹太人当时的处境密切相关。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在一战后甚嚣尘上,这种缺乏理性和人文情怀的意识形态令犹太人深受其害。而历史上的奥匈帝国虽然谈不上民主仁爱,但其广袤的疆域却为四海为家的犹太人提供了避风港。就此而言,作家笔下哈布斯堡神话中的加利西亚,无疑就是流离失所者和无家可归者的理想家园。他们在那里还保留着最后一点尊严,有序、正直、体面、内敛,这种尊严体现在生活的点滴之中,虽然带有些许无伤大雅的自鸣得意和冥顽不化,但一切都还是那么恰到好处。这些看似带些自嘲的画面汇聚一处,便成就了对逝去家园的一种挽歌式的追忆。因此,奥地利学者认为这种叙事手法含有类似寓言的结构,在叙事的过程中用虚构取代了现实,进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反映或反衬现实的写作方式。
在这个被理想化的精神家园中,奥地利文人,尤其是奥地利犹太作家呼吁一种超越狭隘民族界限的文化精神。他们在作品中流露出一种思乡之情,一种对时光不可逆转的无奈和惆怅。过去辉煌时代中有代表性的画面,都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并为他们所接受。而这样的画面带给读者的也总是一种悲今慕古的伤感。这种对历史的演绎能够为人所接受,得益于罗特笔下营造的伤感气氛。在纳粹德国1938年吞并奥地利后,被迫流亡国外的德语犹太作家在怀念过去时光的同时,也反思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如同韦尔弗在1938年3月11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前夜所说:“谁该为毁灭负责?只能说,对此负责的应该是人类理智的昏厥。”在灾难即将降临之际,加利西亚作为精神家园的意义自然无可替代。
//
六、余 论
//
在约瑟夫·罗特的文学创作中,现代大城市如作为帝都的维也纳、巴黎、柏林,几乎是没落、颓废和没有人情味的代名词,象征着已完成异化的人类社会。甚至在1930年出版的《约伯记》和1934年出版的《塔拉巴斯——一位大地上的过客》中,连罗特从未踏足过的纽约也是以一副漠然、冰冷的面孔出现在来自加利西亚的移民眼前。反观罗特笔下老帝国东部的边疆区,这里拥有标志性的广袤原野,读起来会给人留下无拘无束的自由印象。无独有偶,类似画面也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其他犹太作家笔下,如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写于1924年的《波兰之旅》(Reise in Polen)。由此可见,这种情感的流露与寄托在当时并非个例。后者作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作者,同样也颇费笔墨地描述了约瑟夫·罗特故乡伦贝格附近广袤无垠的大平原,将其形容为“原始幻象”,认为其象征着自由和宽容,与一战后形成的诸多新国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此,罗特在1926年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名为《德布林在东部》(Döblin im Osten)的文章,以此向德布林致敬。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诗人是记忆和想象力这个组合的专家”。罗特笔下的加利西亚显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个人倾向。那里有广袤的草原、茂密的森林、严寒的冬天和异域的风情,那里的人也更有人情味儿。这个被理想化的精神家园经罗特之笔成为一种文化记忆,即哈布斯堡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要寄托的,不仅是作家对故国家园的思念,还有他对当时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的人文主义的缅怀。

刘炜,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副教授,上海市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奥地利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及德语流亡文学。主编翻译出版约瑟夫·罗特小说集12卷本,主编出版德文论文集Österreichische Literatur in China(《奥地利文学在中国》)1-6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