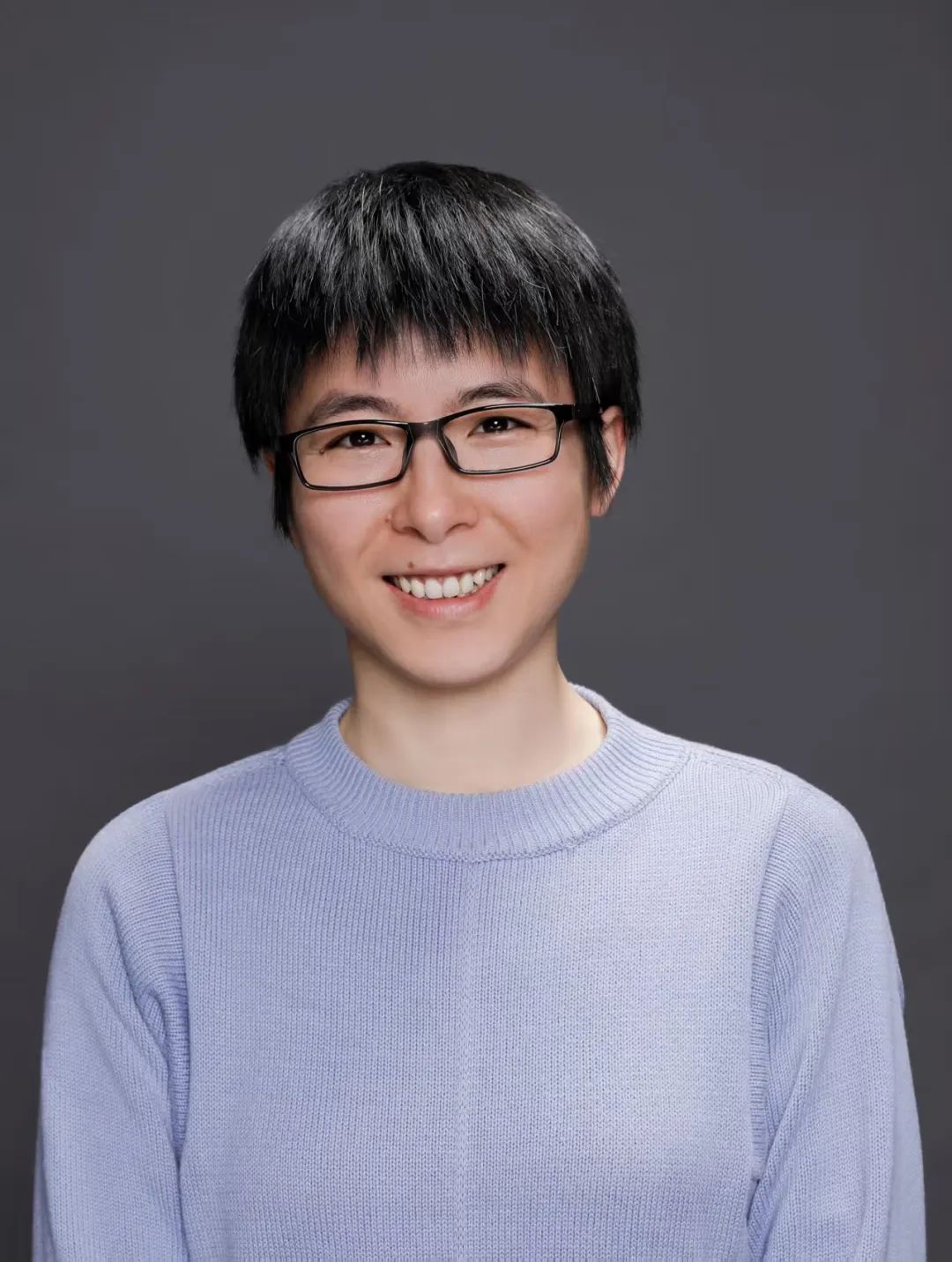德语文学研究
陈敏 | 布洛克斯自然诗歌中风景的感知、“描绘”和意义
本文原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感谢作者陈敏老师和《同济大学学报》的支持。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注释。





布洛克斯诗歌蕴含的认知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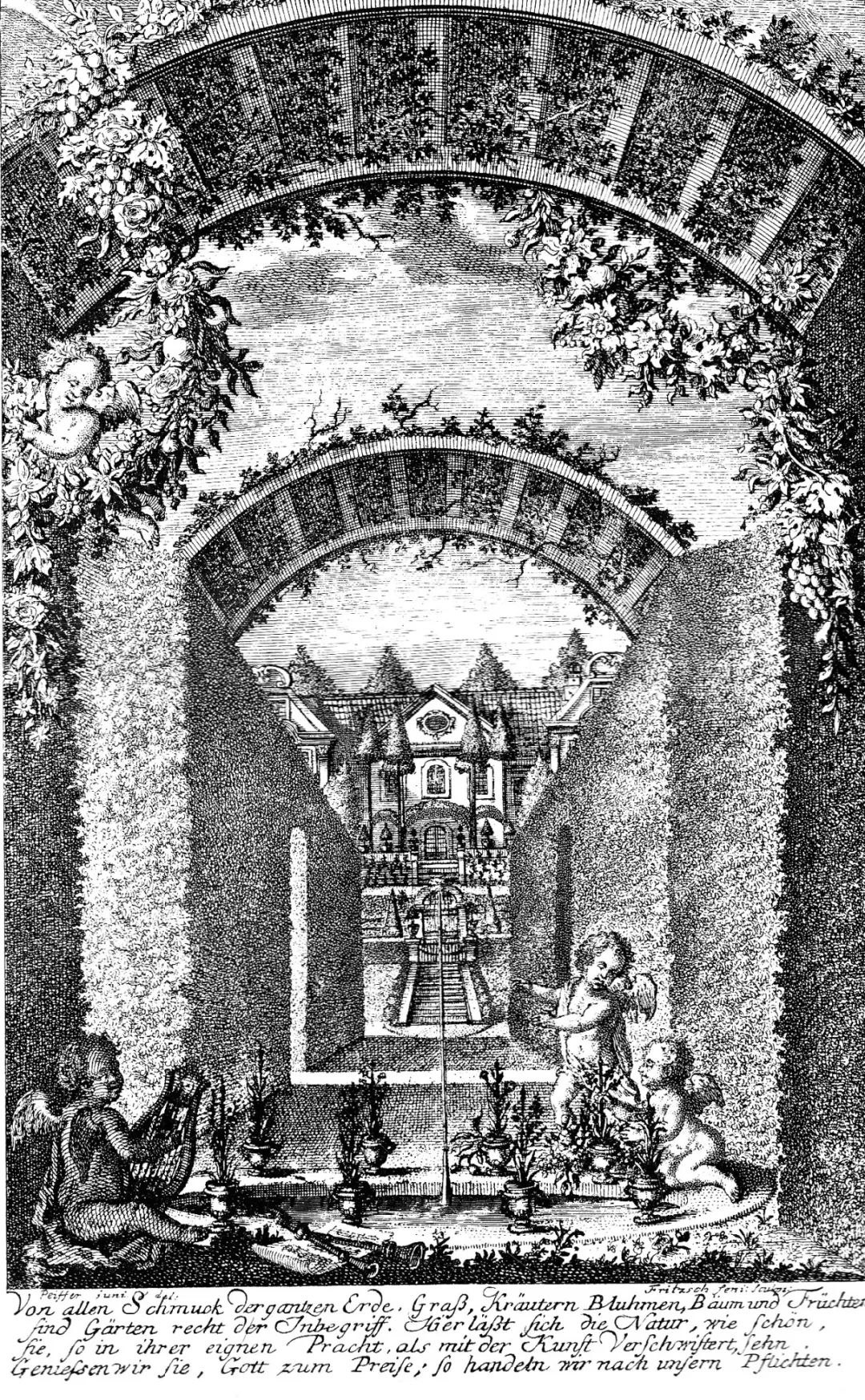
布洛克斯自然诗歌中风景的感知、“描绘”和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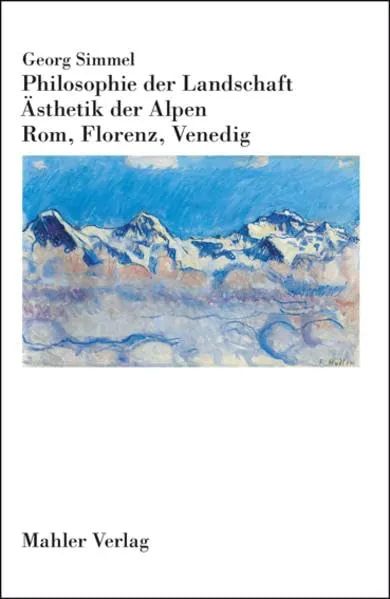
小结:布洛克斯自然诗歌的文化和文学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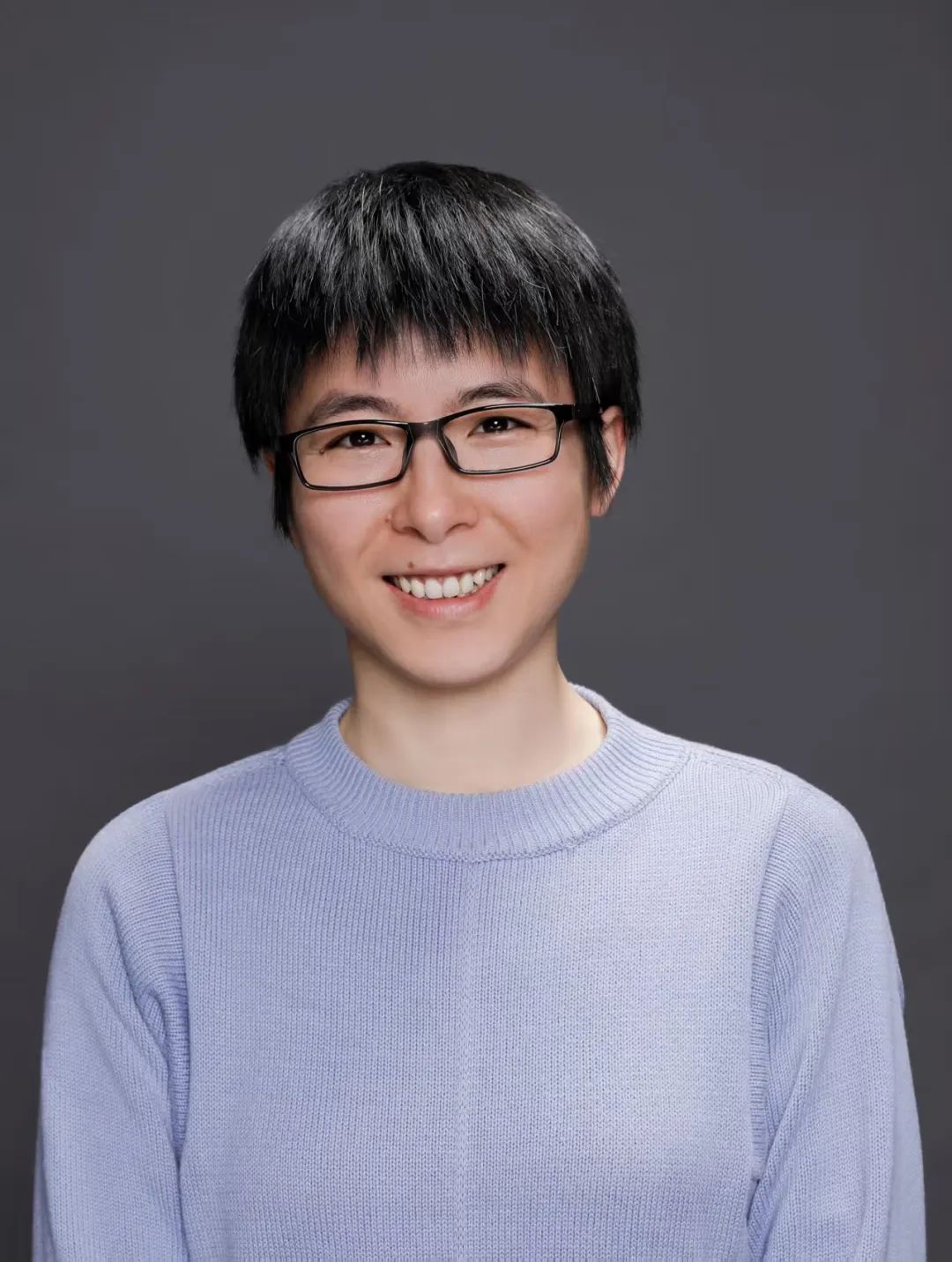

本文原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感谢作者陈敏老师和《同济大学学报》的支持。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注释。





布洛克斯诗歌蕴含的认知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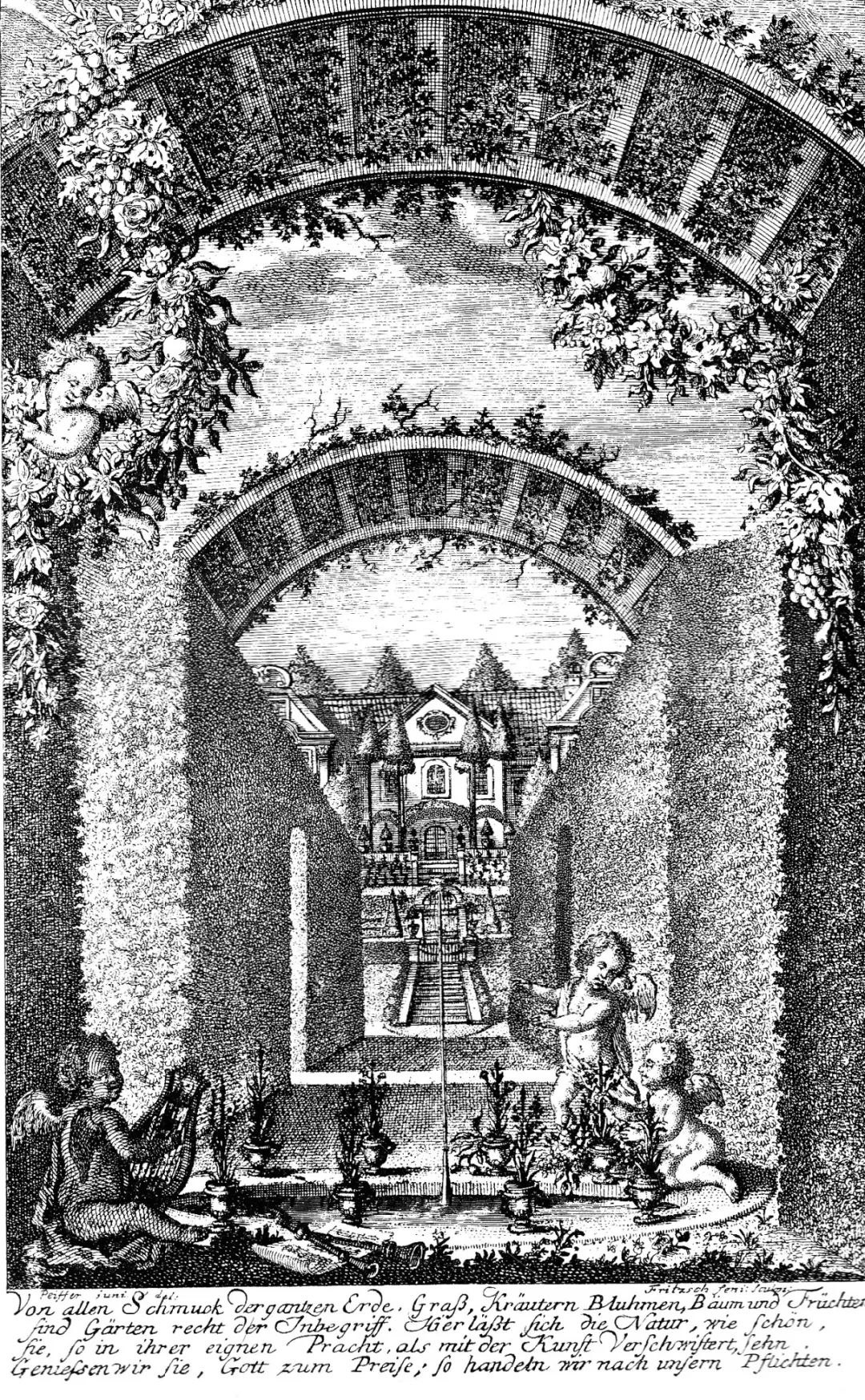
布洛克斯自然诗歌中风景的感知、“描绘”和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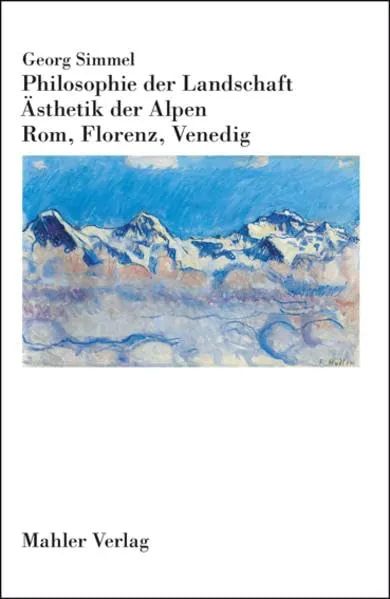
小结:布洛克斯自然诗歌的文化和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