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涵斐 | 划向日常的闪电 ——论里尔克诗中的艺人呈现
本文原载于《德语人文研究》2020年第2期。感谢作者贾涵斐老师和《德语人文研究》的支持。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注释。


内容提要:街头艺人是日常生活中的特殊存在,他们既是拥有高超技艺的、为大众所观看的对象,又是与日常的规则和秩序形成对照的边缘角色。里尔克的晚期代表诗作《杜伊诺哀歌》中的第五首着重刻画了街头艺人,将其视为无定、易逝的存在。在里尔克的中期诗作中,也已出现这类艺人的形象。本文尝试探讨这些诗歌中艺人的呈现方式,分析里尔克如何藉此制造诗作与日常生活的张力,进而撼动日常秩序和认知。
关键词:日常、街头艺人、里尔克、《杜伊诺哀歌》


在德语文学作品中,对艺术与生活之间冲突的呈现比比皆是。不过,艺术并非只是注重实用性的市民日常或者充满危机的城市生活的对立面,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并不仅是艺术与生活的二元对立,而是更复杂多元的模式。艺术或是日常的对照,或是它的补充,亦可以构建另一种日常。艺术家的生存方式与日常的节律相互映照,往往成为日常中的“异者”,成为平滑的日常锦缎上凸凹的纹理。其中,剧团艺人和街头艺人(或称流浪艺人、杂耍艺人)的生存境况则更为特殊,他们是低于艺术家的存在,其技艺与生计密不可分,这种纯粹实用的目的及其无创造性的表演致使他们的技艺处于艺术链条的底端。然而,在文学作品中,对这些艺人的呈现往往能划破日常的表层,正如卡夫卡(Franz Kafka)的《在马戏场顶层楼座》(Auf der Galerie)一文中的女骑手唤醒了一名年轻观众对表象的质疑之心那样。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自创作中期便很关注艺人这个既装点、娱乐日常又游离于日常之外的边缘群体。在与巴黎经验密不可分的中期阶段,里尔克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其中不乏对都市街头艺人的观察,在这些咏物诗中,里尔克是将街头艺人作为一种类型来描摹的,而非作为个体,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为咏物诗中被观察的客体。此时,诗人的观察与其长篇小说《马尔特手记》(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中“学习观看”的理念相符,以客观描摹为主,正如收录在《新诗集》(Neue Gedichte)中的《西班牙舞女》(Spanische Tänzerin),以及《新诗别集》(Der Neuen Gedichte anderer Teil)中的《卖艺班子》(Die Gruppe)和《弄蛇》(Schlangen-Beschwörung)等作品所展现的那样。《西班牙舞女》中,舞女的舞蹈似一团火焰,她以高超的技艺将自己点燃,娴熟掌控自己起舞的姿态,彰显了出色的身体技术;《卖艺班子》以连续的隐喻性画面来呈现杂耍艺人之间的娴熟配合,一些意象经过加工,也进入了后期的艺人诗歌;《弄蛇》则展现了一名吹奏葫芦丝的弄蛇者蕴含矛盾、徘徊于两极的魔力之音对蛇的召唤和控制,并描述了乐声带给听众的神秘、不安的感受。这些诗作中的艺人作为日常的对照,引起了诗人的关注,从诗行间,我们可以读出或隐或显的惊叹之情。

里尔克
观看这些艺人的表演触发了里尔克的思考,而随着他创作理念的发展,这些散见于中期诗作中的画面最终驶入了《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中引人瞩目的第五首哀歌,它恰是十首哀歌的中心。里尔克在192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这首由“光芒四射的后续风暴”催生的、与毕加索的《街头艺人一家》(Les Saltimbanques,1905)这幅画交相辉映的作品使哀歌之圆最终合拢,不过,他并未将这首问世最晚的哀歌置于组诗的末尾,而是将它插到了中间。
初读第五哀歌,我们便可看出其语言风格与日常表达的迥然不同,这种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界限也反映了诗歌意欲构建的文本秩序与日常秩序之间的鸿沟。德国社会学家图厄恩(Hans Peter Thurn)在《20世纪的文学与日常》一文中指出,有两类基本的文学创作意图和表达方式:一类是局限于日常生活、无意超出日常所设边界的文学实践,其语言也乐于在框架内进行重述,固化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比如通俗小说、部分爱情小说和犯罪小说;另一类文学创作则力求探索新的认识和经验,往往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日常,其语言力求跨越日常的边界,即打破单一的、模式化的表达,突破人们习以为常的束缚,创造出一种具有生成特征的、反类型化的语言。第五哀歌的语言显然属于后者,而且,它与其他九首哀歌一样,试图将这种破界推向顶点,唯有这样的语言,才能承载那样厚重地游荡在幽谷上空的思想内容。正如里尔克生平传记的作者霍尔特胡森所言:“里尔克以他语言的革命性暴力,以他思想势不可挡的独特性设计了一个赋予生活以全新意义的全新天地”。
在艺人这一主题上,里尔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前人的影响,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旅居巴黎期间,他曾大量阅读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魏尔伦(Paul Verlaine)等法国诗人的作品。波德莱尔有一首名为《卖艺老人》(Le vieus saltimbanque)的散文诗,收录在《巴黎的忧郁》中,这首诗刻画了一名衰老、潦倒的卖艺人。在巴黎一个盛大的节日,即与日常生活的节律不同的“隆重的日子”,“卖艺的、变戏法的、耍猴的和流动商贩”涌入人群,期盼获得可观的收入,而在喧嚷、欢乐之中,在一排板棚的尽头,观察者看到了“一个可怜的卖艺人,他好像自觉羞愧,自己逃离了一切华丽的东西,驼背,衰弱,老朽,简直是个废人,靠在自己的破棚子的一根柱子上”,与周围的狂欢形成了突兀的对比。在诗中的观察者看来,这个贫困而孤独的老人是“一个老文人”或“一个老诗人的形象”,他曾为世人带来累累果实,却终遭遗忘。如文学研究者威尔德(Ariane Wild)所指出的那样,现代诗常会将诗人比作居无定所、受人轻视的街头卖艺人,因为二者都要依赖受众而存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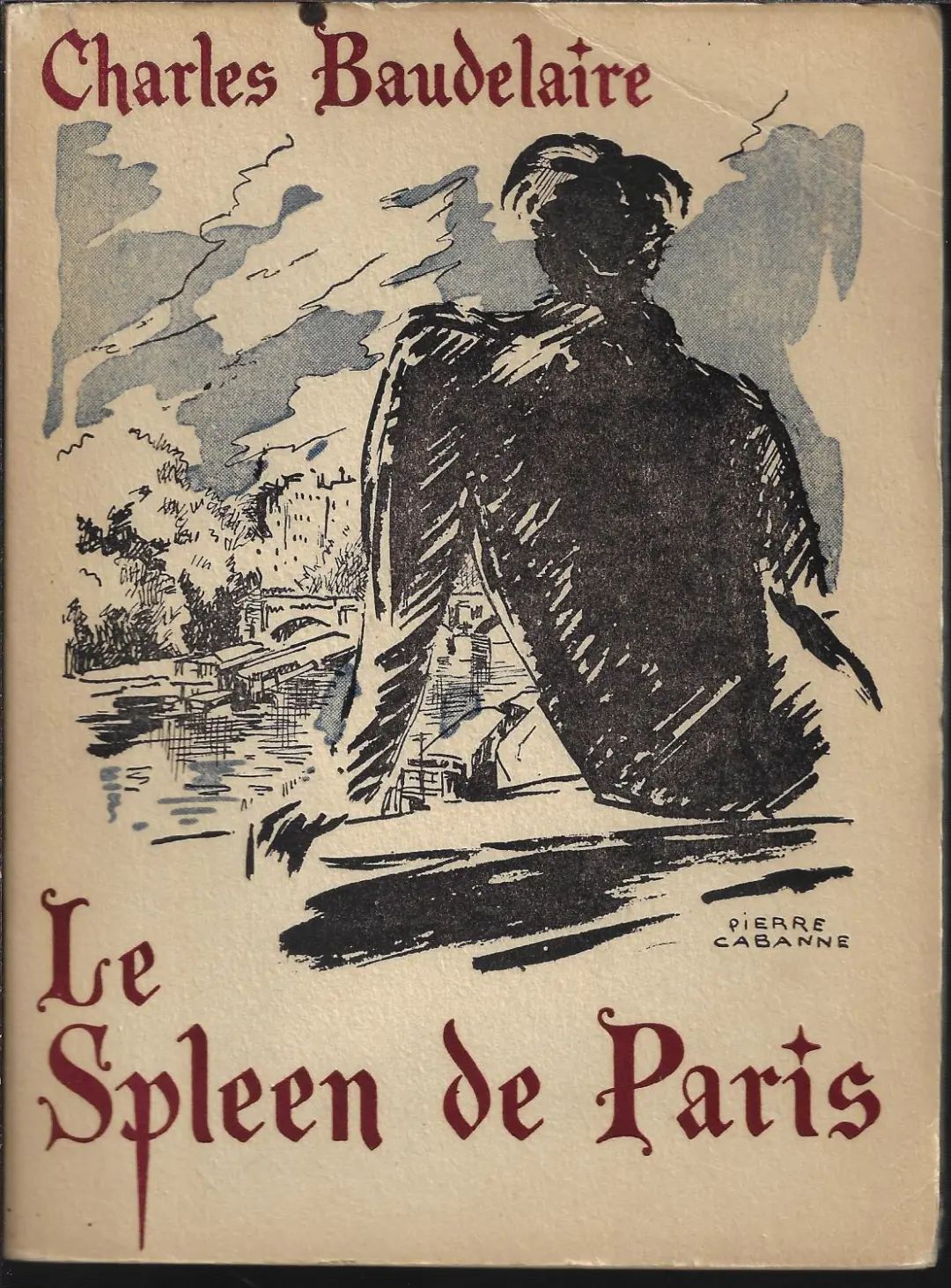
《巴黎的忧郁》
波德莱尔是从卖艺者的生存境况出发,以衰弱的卖艺老人为切入点,试图揭示节庆浮华外衣包裹着的苦难,直指大城市的繁荣所遮盖的卖艺人乃至艺术的苦难,其中虽蕴含着对衰老和消逝的感怀,但更多是着眼于社会批判:“可是他向人群和光明投去了多么深邃、令人难忘的目光啊,其涌动的浪潮就停在距他令人反感的苦难几步远的地方!”人们想在这场节庆中暂时逃离日常和现实,而这名与环境形成强烈反差的卖艺老人却迫使人们撕开迷醉的面纱,直视现实。与之不同,里尔克的第五首艺人哀歌则将这种表象与暗疮之间的对照所连接的隐痛扩展为存在本身的沉痛,在他笔下,卖艺人不只代表着为大众所遗忘的诗人、文人,而是代表着存在者本身。
第五哀歌虽着眼于探讨涉及存在的宏大问题,却仍带有时代的印迹。较为直接的影响来自毕加索的《街头艺人一家》。第五哀歌的副标题是“致赫塔·柯尼希女士”,柯尼希是一名作家和艺术收藏家,里尔克曾于1914年6月至1915年10月借住在她慕尼黑的居所。柯尼希家里挂有三幅毕加索的画,其中一幅就是《街头艺人一家》。里尔克曾多次在信中提及这幅画,比如,他在1915年1月致友人玛丽亚娜·米特弗特(Marianne Mitford)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在柯尼希女士家里,站在伟大的毕加索前,您一定得亲眼看看,这画不适合挂在您的房间,因为这幅画不欢迎来客,它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容不下周围的一切。”如果说这幅画传达出一种茫然、无解、锁闭的忧郁,那么,里尔克的诗则加深了这种忧郁,并将其融入存在的广阔洪流中。

毕加索《街头艺人一家》
除此之外,里尔克也受到了普遍的时代风尚的影响,当时涉及艺人主题的文艺作品不在少数,因为,1900年前后,随着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杂技、马戏、舞蹈、魔法等小艺术形式风靡一时。或许20世纪前期也是街头表演最后的高峰,此后,这种古老的娱乐方式不仅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而且也逐渐被新媒介所提供的广播、影视等娱乐方式所取代。
从中世纪开始,与街头艺人形象相连的,往往是一些负面词汇,如轻浮、狡猾、邪恶、道德败坏等。如研究者布里姆林格(Eva Blimlinger)所言,中世纪的艺人被视为“异者”,他们是居无定所、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亦是不诚实、不道德的一类人,因此,他们几乎不享有任何权利;在当时的等级社会中,他们游离在既定秩序之外,不属于任何阶层,因而无法真正融入社会。在中世纪重精神、轻肉体的信仰背景下,人们认为,身体的极端姿态和高空跳跃等特殊技艺是可耻的、伤风败俗的。街头艺人这种不光彩的名声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在19世纪的维也纳,艺人的地位仍然很低,政府于19世纪初颁布的管理条例规定,杂技演员、马戏演员、木偶戏演员、流浪音乐家都属于乞丐群体,而他们在街头或他人家中的乞讨行为是不合法的。然而,到了19世纪末,这些艺术门类却分外受到追捧,当然,卖艺人并未跻身有修养、有地位的人之列,而是游离在人们的认可、赞赏与排斥、驱逐之间,这种矛盾的态度也是人们对待异者的态度。媒介和电影研究者库申布赫(Thomas Kuchenbuch)指出,1900年前后,马戏、杂技等领域的艺人代表着一种与市民的日常秩序相对立的、为人们所向往的异质世界;当时的巴黎正是杂技、马戏、舞蹈爱好者的必到之地,这些精湛技艺的流行以巴黎为中心,也辐射到了德国等地。在此背景下,街头艺人这个群体很容易引起旅居巴黎、学习观看的诗人的注意,并成为他视野中不断开合的玫瑰花瓣。第五哀歌显然去除了街头艺人曾负载的道德维度,而在纯粹诗学的层面加工这一传统素材,其中仅保留了其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传统。
第五哀歌的诞生离不开诗人长期的观察、思考和经验累积,在1922年写给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的信中,里尔克谈到,街头艺人“其实从最初的巴黎时期以来就与我如此息息相关,而且自此一直是交托给我的一项任务”。在巴黎时期,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几首诗之外,里尔克还有一首写于1907年的散文诗也是以街头艺人为刻画对象的:
“在卢森堡公园门前,朝着先贤祠的方向,罗兰老爹一家人又站开了。地上铺着同一块地毯,一旁放着的还是同样的大衣,厚厚的冬大衣,堆放在椅子上,椅子上面还剩一小块地方,正好够小儿子,也就是老人的外孙,时不时地坐个一刻钟。他还需要这样的休息,据说他是个新手,当他翻完跟头,从高空回到地面时,那突然的一跃会使他的双脚疼痛。他的脸盘大大的,可以容纳许多泪水,但这些泪水有时会停留在他用力张大的眼睛边缘,之后他就得小心翼翼地支着头,就像支着一个过满的茶杯。但此时他并不悲伤,一点也不,即使他感到悲伤,他自己也丝毫不会意识到;仅仅是疼痛在哭泣,人们得容许它哭泣。渐渐地,这一切会变得容易,最终它会消失。父亲早已不记得这些了,而外祖父,不,他在六十年前就忘了这些,否则他不会如此赫赫有名。可是,看呐,名扬所有年集的罗兰老爹已经不再“工作”了。他不再挥动惊人的重量,他(所有人当中最健谈的人)不发一言。他现在专事敲鼓。他充满令人感动的耐心站在那里,那张大力士的脸庞已变得太宽[……]他一身市民衣着,粗壮的脖颈上围着天蓝色的针织领带;他在自己诚实(ehrlich)名声的高峰时期隐退了,退进了这个外套,退到了如今可以说再也没有光芒洒落的平庸地位。[……]他的力气用来敲鼓也还是绰绰有余。他开始敲鼓,但敲得太频繁,他女婿就在对面朝他吹口哨,示意他停下;他正滔滔不绝地做讲演。老人受惊停了下来,沉重的肩膀做出道歉的姿态,费劲地把重心换到另一条腿上。但很快就又得对他吹哨喊停。见鬼,老爹!罗兰老爹!他又在敲鼓了。他几乎不自知。他能一直敲下去,他们可别以为他敲久了就会累。但现在换成了他女儿讲话;敏捷有力,毫无漏洞,妙语连珠。[……]她说完了:音乐,她喊道。老人就像一下子敲响了十四面大鼓。围观的人群里有刚挤入的观众认出了这名老人,朝他喊道:罗兰老爹,嘿,罗兰老爹!但老人只是顺便点点头;敲鼓一事关乎名誉,他要严肃对待。”
这首散文诗的主角是罗兰老爹,另外几名出场的人物分别是他的外孙、女婿和女儿,在此,里尔克并未详细描写卖艺行为,而是将视线集中于小男孩的痛感、眼泪,以及老爹曾经的荣光和如今的落寞。男孩将在时间的流逝中习惯并遗忘身体的疼痛,逐渐告别真实的身体和情感经验,被机械化的技艺所改造,这种人性的失落会造成他的异化,加速他的消逝,而老爹曾以高超技艺和惊人力量赢得的显赫声名很快便黯淡下来,他在家庭团体中失去了核心地位,他无法体认自己的存在,敲鼓便成为他最后的尊严和价值。此外,诗中的艺人并未受到传统的声名所累,诗人甚至特意在道德层面为老爹正名。老爹曾拥有“诚实”的名声,却在声名大噪之时,由于身体的限制而走下人生巅峰,衰老的身体很快就会像一件旧物一样被取代和丢弃。街头艺人曾被视为招摇撞骗的人,但在里尔克笔下,技艺似乎成为一种诚实的谋生手段,成为物有所值的消遣方式。退居幕后的老人过于看重敲鼓这些事,是因为他仍重视名誉,虽然街头艺人的身体技艺往往在道德方面具有低劣性,甚至被斥为是伤风败俗的,但被随意支使的罗兰老爹将敲鼓这件小事都视为关乎名誉之事(Ehrensache),可见,一方面,他想证明自己虽老迈却仍“有用”;另一方面,“一身市民衣着”的他似乎接受了市民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这或许是一种悖论:市民在观看街头表演时,将艺人视为日常边缘的、代表异质世界的观看对象,艺人游离在观众惊叹与鄙夷的矛盾态度之间,而罗兰老爹这位声名远播的街头艺人则有意无意地接纳了市民社会的价值,给自己的技艺添上了诸如实用、道德等价值维度。而这一切又被诗人以独特的方式加工和呈现,悄然掀开了日常厚重的帘幕,诗人拒绝对街头艺人进行传统的道德批判,而是以别样的视角刻画了他们所代表的生存状态,并将其引申为存在的流离失所与普遍隐痛。
无论是毕加索的绘画所展现的六个人物,还是这首散文诗记录的四名巴黎卖艺者,都可视为第五哀歌的直接素材。当然,我们并不能将第五哀歌简单视为对画的描绘,也不能将哀歌中的艺人等同于罗兰老爹一家,单是三者涉及的人物数目就并不一致。
这首完成于1922年的“街头艺人哀歌”的开篇写道:“然而,告诉我,他们是谁,这些流浪者,这些略比/我们自身更易逝的人”(1-2),如果说“流浪”长久以来都是街头艺人的属性,那么,接下来的说法则打破了读者的期待:略比我们更易逝。“我们”已然是易逝的,而艺人的易逝性更甚于普通人,所以诗的开篇便用了转折的语气,且以斜体强调了“是”这个动词,以强烈的语气追问他们的存在特质。流浪艺人为何具有显著的易逝性?因为他们赖以为生的杂技并不能提供存在的支撑或苦难的救赎,他们“比流水更迅疾”(43)的娴熟动作实则是被降格的人机械、重复的运动——他们仅由技艺所限定,除了技艺一无所有。他们被一个“从不满足的意志”(4)“卷拧”、“弯折”、“缠绕”和“挥舞”(5-6),就像人曾是“痛苦”手中的“玩具”(38),这一切反映出人被支配的处境和与存在相依相伴的痛苦之必然。他们熟练地搭建起来的“树”(43)——指叠罗汉的技艺——“比流水更迅捷,在短短几/分钟内历经春、夏、秋”(43-44),走向坟墓,即前文未道明的冬季,超乎常人的身体技艺非但无法使他们更有价值,反而加剧了他们的消逝。诗中第一节所提及的“定立(Dastehen)的大写首字母”(13-14),即D,便是毕加索的画上除母亲之外的人物构图所呈现的形状。定立与消逝构成对比,正如街头艺人不间断的技艺展示与末尾想象中的一对恋人在地毯上的静立形成对比那样。画面上,人物之间的目光没有交集,女孩看向地面,两个男孩的目光凝聚在母亲身上,而单独坐在一旁的母亲将头偏向另一边。这种交流的缺乏在诗中也有体现,在训练中短暂喘歇时想要对母亲流露“爱的神情”(46-47)、却总被父亲击掌的信号生硬打断的男孩——脚掌的灼痛先于心脏周围的疼痛触发他的泪水——受到的粗暴对待折射出机械、重复的技艺对人情感和内心的压制,以及父子关系的异化;呈现出完美无缺外表的女孩实则不过是晃动的天平上“平静的市集果实”(71),这暗示了艺人的生存依赖于市场和观众,也折射出这种生存状态对人的物化和降格。
哀歌中的人物与散文诗中的人物亦有相似之处:敲鼓的老人都曾是大力士,如今却枯萎衰弱,满身褶皱;年轻的男人强壮结实,作为成年男性的代表,他已经遗忘了真实的痛感,似乎作为纯粹的机械身体而存在;作为新手的男孩尚未成人,尚未在技艺的支配下完全异化,他在做高难度动作时脚还会疼痛,他身上仍保留了些许人性的东西,如眼泪和微笑,它们是人本能反应下的产物。无论是哀歌中的父亲对待儿子,还是散文诗中的女婿对待罗兰老爹,都毫无情感和尊重可言,而是像对待动物一般。人早已不再是任何活动的目的,而是沦为工具和表象,这种人本身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也是艺人存在的鲜明写照。
在迅疾而空洞的流逝中,唯有男孩无意间流露出的真切微笑可供采撷,诗人呼请天使将它封存在瓶瓮中,贴上“艺人的微笑”(61)标签,它仿佛古老的、具有疗愈功能的药剂,代表着一种克服流逝、异化和虚假表象的可能性。在“城郊的天空”(11-12)下“永恒腾跃”(8-9)的技艺只是“虚假的果实”(22),哀歌中无名的、边缘的艺人一家所拥有的,只有“微露虚假微笑的厌倦”(25)。同样,众人的观看犹如玫瑰,盛开又凋谢,亦处在永恒的流逝和变动之中。诗人不禁发问,哪里是艺人还未被身体技术异化之处,在此他们还“不能够”(74),在此还有原初的重量和笨拙的跌落,虚假尚未完全取代真实,人所面对的痛苦尚且微小而具体。但他知道,这样的地点已不存在于外部,而只能在内心重塑。
里尔克研究者史蒂芬斯(Anthony Stephens)认为,这首哀歌是“人存在的易逝性以及广义上人的‘杂技’的毫无意义的一个极端例证”。在1925年以法文写的散文诗《江湖艺人》(Saltimbanques)中,里尔克重拾了这个主题,并将艺人的杂技与存在者的境况更紧密地结合。
无论是在第五哀歌中,还是这首明显受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作品影响的散文诗中,艺人的杂技都与真正的艺术和精神的持存无关,而是与危险、坠落、流逝、死亡交织在一起。杂耍艺人所面临的危险与我们的存在所面临的痛苦与危机一样,都发生在纯粹的外部,暴露在日常的重重目光之下。而克服它的唯一方式,就是将完美的技艺移植到灵魂中,在内部、在“无地”(81),实现从笨拙到能够、从虚假到真实的转化过程。在空洞的机械技艺与无异化的真实能够之间,“尚不能够”或许是一个中转站,就像人处在纯粹身体性的木偶与绝对精神性的天使之间那样。最终,在想象的广场上,在无法言说的地毯上,展露真实微笑的恋人或许会得到最特别、最光荣的认可:
“天使!若是有个广场,我们并不知晓,在那里
在不可言说的地毯上,若爱者展示着他们在此
从未做成的一切:他们果敢而
高昂的、心灵震颤的形象,
他们的兴趣建成的塔楼,在从未
有地面的地方,他们长久以来仅倚靠着
彼此的梯子;颤抖着,——并且能够做到了,
在四周环绕的观众,无数静默的死者面前:
这些观众是否就会把最后的、一直积攒的、
一直收藏的,我们不认识的,永远
有效的幸福之钱币,投向这对站在
满足的地毯上,终于真实微笑的
恋人?”(95-107)
第五哀歌的最后一节是以虚拟式表达的可能愿景,犹如短暂地划破日常表象的闪电所照亮的一个瞬间。爱者(Liebende)在里尔克笔下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能够部分地克服存在本身的危机。爱者的心灵震颤、兴趣和相互倚靠所伴随的技艺,是一种情感和心灵的外化,而非街头艺人空洞而机械的重复行为。街头艺人所面临的物化和异化实际上也是现代都市的人们对自己存在的物化和异化,因为城市居民的日常早已排除了令他们所恐惧的死亡,而孜孜不倦致力于生的人们实则只是在重复着与心灵无关的种种杂技,只是在不断编织“命运的廉价冬帽”(92-93),虚假的色彩和多样的款式并不能抵御人生之冬的严寒和凋零。当存在除了“能够”便一无所是,那么它必然是被填充得太满,却又空无一物的。
最后一节还出现了作为观众的死者,再次引入了死亡的维度。爱者所在的虚拟广场与倒数第二诗节的人间广场形成对照,“广场,哦巴黎的广场,无尽的舞台”(87)再现了里尔克早年所关注的巴黎街头的卖艺行为,但在此,它不再是卢森堡公园前的广场或者某个特定的广场,而是因恐惧、排斥死亡而陷入不安的尘世的缩影。同样,哀歌所书写的艺人最终也挣脱了任何具体的指涉,而成为展示现代人存在境况的极端例证。无声的观众所持有的钱币是不为我们所知的,因为我们不识得死,我们太过明显地区分了生与死。在爱者所处的这个涌动着幽暗诗意的、不为人知的广场上,生与死的界限被打破,身体与心灵、技术与情感之间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得以消解,死亡不再是一种阴影,而是成为存在之环的一部分。被日常所排除的死亡通过非日常的写作进入人们的视野,连通了对立的两极。开头“磨损的、因他们的永恒/腾跃而变薄的地毯”(8-9)变成了末尾满足的地毯,人不再被永不满足的意志玩弄于股掌,在外力的强制下不知疲倦地展示身体的极端技艺,而是得以满足地静立,感知自己的身体、情感与存在。迥异于日常表达的诗歌尝试言说无法言说的东西,以广阔的诗歌之地容纳本不可用此在的语言描述的地毯、广场等地点,将外部的万物和整个时空纳入无尽的内部。
在同样完成于1922年、成稿时间略早于第五哀歌的第十哀歌中,年轻的死者穿过日常生活繁荣的表象,进入广阔的悲痛之乡、死亡之境。悲痛旷野与人们在“苦难之城”中建立的“安慰集市”形成对照,在张贴着“不死”广告的木板之后,诗人渐渐开启了一片迥异于日常的领域。唯有像诗中年轻的死者那样,跟随年轻的悲痛和年长的悲痛向更深处行去,最终认识并容纳坠落和死亡,才意味着一个人真正体会到了存在。这一点,街头艺人们是无法做到的,然而,以他们为中心的第五哀歌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认知可能,本处于日常边缘的街头艺人成为诗中的主角,成为存在的极端例证,为我们反思存在的种种问题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综观里尔克的艺人诗歌,我们不难看到,街头艺人这一主题的特殊性,加上诗人长期的观察、体验、阅读与创作经验的累积,以及其所处时代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一首杰出而独特的艺人哀歌。从藩篱之中的语言到突破障碍的语言,从黯淡的现实到艺术的真实,从重重遮蔽的人的存在到克服危机、贯通内外的存在可能:相较于日常及其秩序而言,里尔克的诗提供了深层反思的诗学空间,也从多个层面给予人们新的美学认知。加缪(Albert Camus)曾说过:“真相犹如强光,令人目眩。谎言像美丽的落日余晖,粉饰一切。”或许我们可以对此稍加改动,来说明里尔克艺人诗作的影响:真相犹如闪电,穿透笼罩着虚假柔光的日常生活,令人在短暂的目眩之后获得美学的真知。

里尔克墓

贾涵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联合培养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学视野下的近现代德语文学、文学与知识的关系、德语诗歌。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一部、译著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