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刘远鹏:彼特拉克的旅人书写与现代自我的“双重面孔”
编 者 按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书写自我的作家”,彼特拉克留下了大量有关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的记录。他不止一次在书信中写道:

我这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奔波,至今依然如此……几乎没有机会在任何地方逗留或喘息。(《通信》1.1)

彼特拉克诞生于双亲流放途中,中年漂泊大半个欧洲,晚年埋骨他乡。与同时代人相比,彼特拉克以罕见的“旅人”(viator)面貌为后世所知,至于他攀登风涛山的那场壮游,更是被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视作“人对现代世界的首次发现”。
不过,学界对彼特拉克旅人身份的讨论并未局限于其生平经历,而是希图进一步透视他作为一个现代人的精神世界——“长久以来,评论家们正是以彼特拉克对‘自我中心性’(centrality of the self)的发现为切入点,探讨他身上的人文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一生漂泊无依、饱受命运折磨的彼特拉克,一直试图在战争的废墟与信仰的崩析中安顿无所适从的自我。对他而言,通过写作来面对支离破碎的世界,从而确证自我对生命的真切体验,正是他应对流亡生活和时间流逝的最佳手段。旅人作为彼特拉克内心状态的投射,构成了他在日常通信和文学作品中借以自况的重要主题。
然而,以旅人类比自我并非彼特拉克的独特发明,而是一个贯穿古典与基督教文化的悠久传统——从奥德修斯、埃涅阿斯再到奥古斯丁,这些不同时代的人物都曾以旅人的面貌出现,托马斯·格林更是在彼特拉克的作品中挖掘出大量直接承自古典与基督教文化的旅人意象。那么,彼特拉克的旅人书写和自我认识究竟有何创见,以至于能使他在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学术讨论中被如此广泛地看作“第一个现代人”?

罗纳德·威特认为,彼特拉克之所以区别于前代的人文主义者,是因为他融合了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与对基督教的信仰,这一模式构成了后世人文主义运动的重要内涵。一方面,彼特拉克作为中世纪的欧洲人,其知识背景必然以基督教的神学命题为支配要素;另一方面,由于彼特拉克对西塞罗等古典作家的充分接受,其思想又展现出与修道院哲学极其不同的一面。因此,如何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其精神世界面临的最大考验。
保罗·克里斯泰勒、普莱斯·齐默尔曼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这种“双重性”的困境促使彼特拉克选取“奥古斯丁的忏悔”作为自我书写的范例,后者不仅在中世纪影响巨大,还构成了彼特拉克沟通古典与基督教思想的桥梁。在《登风涛山》(Ascesa al monte Ventoso,Ventoso意为“多风的”)和《秘密》(Secretum)这两部最为重要的自述作品中,奥古斯丁的言行总是与彼特拉克的肉体或心灵之旅如影随形。
然而,正如奥古斯丁思想众流交汇般的复杂性,彼特拉克身上也体现出古典传统和基督教精神之间的巨大张力。尽管彼特拉克无时无刻不在宣称自己把奥古斯丁当作皈依之旅的“导师”(maestro)和“典范”(exemplum),但在修辞、文体风格乃至具体观点上,他对廊下派哲人对话的模仿却极为显著,以至于历代注家在寻找他文中“奥古斯丁言谈”的材源时,依据的往往不是奥古斯丁本人的著作,而是西塞罗的《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等古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偏离了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不少学者因此认为,廊下派哲学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得到发现”正肇始于彼特拉克对奥古斯丁的“改造”。

▲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
事实上,诗人在世时就已面临人们对他笔下“奥古斯丁”的质疑。好友隆贝(Lombez)主教贾科莫·科隆纳(Giacomo Colonna,1300—1341)曾寄给他一封带有嘲弄意味的信函,声称他虚构出一个头脑里充斥着异教思想的基督教圣人。彼特拉克则针锋相对地辩护道:

您说,我不仅用虚构的故事愚弄愚蠢的群众,还愚弄了天堂本身。您坚持认为,我假装对奥古斯丁及其著作怀有好感,但实际上并未摆脱诗人和哲人的影响。然而,我为什么要毁坏我所知道的奥古斯丁本人所坚持的东西呢?如果不是这样,他绝不会把他的《上帝之城》,更不用说他的其他作品,建立在如此庞大的哲人和诗人的基础之上,也不会用这么多演说家和史家的华彩来装饰它们。(《通信》2.9)

由此可见,彼特拉克并不试图否认他过分强调了奥古斯丁与廊下派哲学的关联,这恰恰展现出自己融合古典思想与基督教精神的努力。然而,历史上的奥古斯丁在作品中常常刻意流露对古典作家的蔑视和厌弃,比如他将西塞罗这位人人皆知的罗马先贤称作“某个叫西塞罗的人”(cuiusdam Ciceronis),甚至贬斥其为“假哲人”(philosophaster);对其著作熟稔于心、运用自如的彼特拉克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那么,彼特拉克究竟为什么还要将廊下派这个“隐匿的汇流”重新嫁接到奥古斯丁主义的基督教思想当中?
鲍斯玛在克里斯泰勒等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人文主义的双重面孔”解释。人文主义者面对的真正困境在于,他们同时继承了廊下派哲人和基督教奥古斯丁传统的写作典范,这种二元对立构成了欧洲早期现代一系列关键的思想冲突的载体,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彼特拉克。而在亚历山大·李看来,与其说彼特拉克在二者之间产生了分歧,倒不如说奥古斯丁的《论真宗教》(De vera religione)和《独语录》(Soliloquies)等早期作品,为他提供了连结廊下派哲学与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的桥梁,使他得以将对人类理性的肯定与对上帝恩典的信仰结合起来,从而对人和世界、上帝与自我等问题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
具体地说,彼特拉克虽然在表面上探讨基督教神学中的自我命题,并延续了奥古斯丁将旅人作为自我写照的传统,但他追随的这位向导实则具有来自古典时代的另一重面相。因此,彼特拉克呈现出的自我样貌不再是纯粹的羁旅者或朝圣者,而是一个融合了廊下派式的古典精神、折射出他动荡生平的忧郁的漂泊者。对自我的探索和拷问,始终困扰着这位身处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交界线上的迷茫诗人,并促使他有意识地从古代圣贤——无论他们是否为基督教徒——那里寻求答案。可以说,正是廊下派哲学与基督教精神、德性与皈依的裂隙,孕育出了彼特拉克身上的现代自我。“双重面孔”既是阐释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重要路径,也为理解现代自我的起源提供了一种可能。
尽管自我的面相在彼特拉克的作品中极其复杂,但其中最显著的影响无疑来自奥古斯丁。彼特拉克对奥古斯丁自述的模仿,意味着他必须同时接受另一个在中世纪源远流长、影响重大的母题——皈依。约翰·弗里切罗注意到,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为这种自叙程式树立了基督教式的典范,以至于在他之后的中世纪宗教传统中,所有对自我的书写都必须同时体验为一种神学意义上的皈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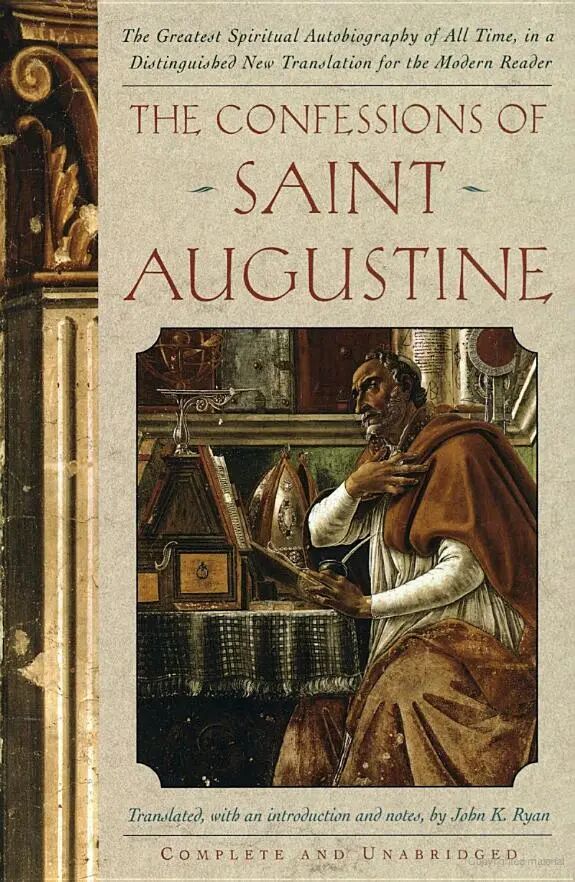
▲ 《忏悔录》,奥古斯丁 著,John K. Ryan 译
兰登书屋出版社,1960年
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在远离上帝之城的尘世里,人始终背负着被逐出伊甸园的原罪,不得不处于现世的漂泊之中;只有始终面向彼岸的信仰,才有可能在大地之外找到人之存在的终极意义。最重要的是,对皈依者而言,通往上帝恩典的朝圣之旅(peregrinatio)必然伴随着对尘世的疏离(alienatio)。在奥古斯丁看来,如果连受造物中最能分有神圣理智的自我都是可朽之物,那么这个地上之城的万事万物又有何可爱?作为此生此世的旅人(viator in hac vita),人唯有通过战胜欲望的诱惑和原罪的沉沦,将自己的自由意志正确地朝向上帝,才有可能真正摆脱永死、走向救赎。通过这种解读,古典时代的漂泊者形象被逐渐改写成基督教文化中通往永恒恩典的朝圣者:

我被迫学习某个叫埃涅阿斯的人漂泊(errores)的经历,而我却忘记了自己的失足(errores)。我为狄多女王的殉情自尽而落泪,但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的生命却因背弃主而死去。这种悲惨的境地居然没有让我流下一滴泪水。(《忏悔录》1.13)

奥古斯丁用自己的青年经历说明,尘世中的一时漂泊并不可怕,真正致命的是因灵魂失足而错失恩典、背弃上帝。在奥古斯丁式的皈依中,旧我与新我的巨大冲突无处不在,它们构成了如下叙述模式:经由对上帝恩典的顿悟,一度迷途的旧我从世俗的偏移中回到正轨,摆脱肉身对心灵的束缚,从此彻底走上通往新我的拯救之路,“成为行走在正义中的旅人(viatores)”。这种转向在基督教传统中被描述为“通向上帝的心灵之旅”(itinerarium mentis in Deum),而它得以实现的前提,正是腐朽旧我的彻底死去,以及经由上帝见证乃至参与的新我的复生。“由死往生”(postumo)叙事模式的宗教意义在于,这种对自我的言说充分彰显了作为“被言说者之我”的死去与作为“言说者之我”的复活。换言之,在人生道路的进程中,权威叙述者的典范和教诲本身即构成了皈依的证言。

基督教的皈依主题将一种彻底的断裂引入了生命的连续过程,从而满足了自传与此相反的迫切需要,而正是由于这种彻底的断裂,一个人才可以将自己的人生故事讲述得好像真实、明确和完整。生命中的死亡是故事的终结,但恰恰是由于精神上的重生,才得以讲述故事。

作为一个中世纪人,彼特拉克在形式上并未背离这种传统。在《登风涛山》中,他就叙述了一段颇为典型的由迷途转向正道、由肉体转向心灵、由有形事物转向内在自我的历程。文中最具奥古斯丁色彩的一个段落是,彼特拉克的兄弟试图从陡峭的山脊这一“更好的道路”攀登,彼特拉克却由于“身体的虚弱”和“灵魂的怠惰”,选择从山谷向下而行:

我试图用这样的借口掩饰我的怠惰,可是当其他人已经走到更高处的时候,我仍在山谷间穿行,并没有发现任何好走的路,只是路越来越漫长,人也无谓地越来越疲劳。最后我感到厌烦至极,开始懊悔误入歧途,并决定全力攀越高峰。……就这样,我的确推迟了登山的辛苦和不快。但是自然不为人类的设计所征服;有形的事物不可能通过下降而达到高峰。(《通信》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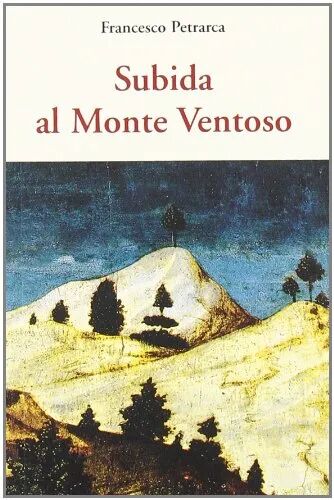
▲ 《登风涛山》西班牙语译本,2011年
在艰难攀爬后,彼特拉克终于登上风涛山顶。此时他32岁,正与皈依时的奥古斯丁同龄。根据书信记载,彼特拉克先提到同样在困惑之际登上高山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Philippos Ⅴ,公元前221—前179),又在兄弟的庄严见证下翻开了随身携带的《忏悔录》——这绝非一个旅人的无心之举,而是在人生中途进行的一场意义重大的“圣书卜”(bibliomanteia)。当彼特拉克把目光落在这本小书上时,他看到这样一段话:

人们赞赏高山大海、浩淼的波涛、日月星辰的运行,却遗弃了他们自己。(《忏悔录》10.8)

彼特拉克由此意识到,自己太过于耽爱此世的生活,以至于忘记了对自我的照看,“我感到窘迫……生气自己依然沉溺于这些世俗的事物”(《通信》4.1)。如果仅凭这段叙述,似乎可以认为,彼特拉克正是在奥古斯丁的启发下作了一场对自我的深刻思索。然而,无可调和的分歧恰恰出现在这里。对奥古斯丁来说,执着于自我并非真正的救赎之道,反而会导向苦痛甚至罪愆;期盼得到拯救的凡人必须学会舍弃对此世的爱(amor mundi),将心灵转向至高的上帝,“此生的德性,除了爱那该爱者(diligere quod diligendum est)别无其他”。换言之,在奥古斯丁眼中,要得到真正的爱之德性,就必须实现“无己的自我”。他对自我的暂时强调,只是为了使其得到更为深刻和彻底的否定。皈依的最终目的也并非仅是“登上主的山”,而是经由这场旅途获得自我的重生。
进一步说,之所以旧我必须死去,是因为皈依把人身处的此世变成了“异地”(regio disimilitudinis)。借助奥古斯丁的说法,人不可能同时把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当作最终归宿:

两种爱造就了两个城。爱自己而轻视上帝,造就了地上之城,爱上帝而轻视自己,造就了天上之城。(《上帝之城》14.28)

因此,尘世中的漂泊者一旦意识到恩典的存在,就必须立即意志坚定、方向明确地成为朝向天国的旅人,绝不能留恋有朽的尘世。托马斯·阿奎那简洁明了地指出,皈依的终点绝非自我的心灵,而是永恒的上帝:

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旅人(viator),是由于他正朝向至福前行(tendit in beatitudinem)。


▲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插图,15世纪
相较之下,彼特拉克显然没有发现,自己的攀登事实上是一段失败的旅程。比起奥古斯丁死中复生般的旧我与新我的断裂宣言,他的领悟显得过分傲慢,甚至完全不像一个中世纪的基督徒——他不但没有展现任何“告别旧我”的姿态,反而引用塞涅卡《道德书简》中的观点,首先强调心灵而非上帝的无所不能:

我早该学到——甚至是从异教哲人那里学到——这一点:“除却心灵,无一物值得赞赏;与心灵的伟大相比,无一物堪称伟大。”(《通信》4.1)

这段话可谓极其鲜明地体现出彼特拉克思想中的矛盾之处——他将奥古斯丁的忏悔作为效仿对象,最终却得出廊下派式的结论。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基督教信仰中的爱(caritas)必须始终朝向上帝,廊下派主张的却是属己之爱(oikeiōsis),后者把世界视作一个由心灵荡漾开来的同心圆,并将自我而非上帝作为世界延展和收拢的中心。因此,如果彼特拉克将“认识心灵”作为皈依之旅的启示,那么这场旅程就完全不是奥古斯丁式的。彼特拉克恰恰抛弃了基督教皈依概念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心灵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分有上帝的权能,有赖于此,人才能将自由意志转向对上帝的信仰;否则,一个从未意识到恩典的心灵根本一无是处。

▲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奥古斯丁 著,吴飞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
但是,走下风涛山的彼特拉克并未注意到这一点。在这场充满拟圣意味且意义重大的攀登后,彼特拉克仍然长期遭受精神危机的折磨。对他来说,去往何方始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就这样,我四处漂泊,仿佛成了一个永远的朝圣者。厌倦了一个地方的艰苦,我就换一个地方,虽然新的地方并不更加舒适,但至少新鲜感能对此有所缓解;就这样,我辗转反侧,因为我深知此世没有我的安息之地,我必须历经千辛万苦来寻得安宁:在这里,我注定要永远辛苦劳作,哀叹呻吟,而且——也许最糟糕的是——在生活的重重磨难与煎熬中,我仍然对不息的纷争和无尽的苦难充满恐惧。(《通信》15.4)

彼特拉克在一封“孤独中写下的书信”里向兄弟杰拉尔多(Gherardo Petrarca)坦白,自己面临着奥古斯丁描述的所谓“同时同地的自相矛盾”——既“希望生命的旅程继续”,又“永远不希望到达死亡的终点”,最终陷入“既希望前进又希望静止”的巨大悖论(《通信》10.5)。说到底,他不愿为了可能的天堂放弃现世的爱欲、荣耀和幸福,他真正爱的对象不是上帝,而是自我。因此,彼特拉克的皈依在根本上是未完成的。他既然始终在徘徊、惧怕和等待,不愿彻底告别旧我、走向新生,就无法像奥古斯丁那样为自己创造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对他来说,此世与彼岸、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断裂根本无从谈起,更别说决绝地择一而从,他能做的只有退守到自己心灵的方寸之内。就像他在《秘密》中所说,对那些“永恒事物”的追求,他虽然不愿放弃,但也只能“推迟”,直到最终的死亡降临。
因此,中世纪基督教语境下的奥古斯丁主义显然已无法为彼特拉克提供精神上的慰藉与依靠,他必须塑造出一个更加温和且面向此世的“奥古斯丁”。于是,在彼特拉克中年以后的书信和作品中,这位神父的形象愈发远离基督教传统,乃至晚期著作《秘密》中的“奥古斯丁”几乎已经成为一个“面目全非”的廊下派哲人。
正如《秘密》在中世纪广为流传的抄本标题De secreto conflictu curarum mearum[关于我内心冲突的秘密]所暗示,彼特拉克将奥古斯丁召唤到自己梦中的目的颇具私人性和隐秘性:他试图通过与“奥古斯丁”的假想对话来治愈生活带来的创痛,从而得到心灵的安慰。需要注意,这种对话形式并非仅仅来自基督教的告解传统。在廊下派哲人的劝慰体作品(consolatio)中,他们同样试图通过书信和演讲来治疗“灵魂受损”的人,并将这种劝慰视作哲学对灵魂力量的加持,从而帮助灵魂更加主动、有效地学会使用自身的能力。对此,西塞罗在《图斯库路姆论辩集》3.3中给出了解释:

哲学当然是灵魂的解药。哲学的援助并不应当如同在身体的疾病中那样从外部得到寻求,而[我们]应当以所有的资源和力量作出努力,从而使我们自己能够医治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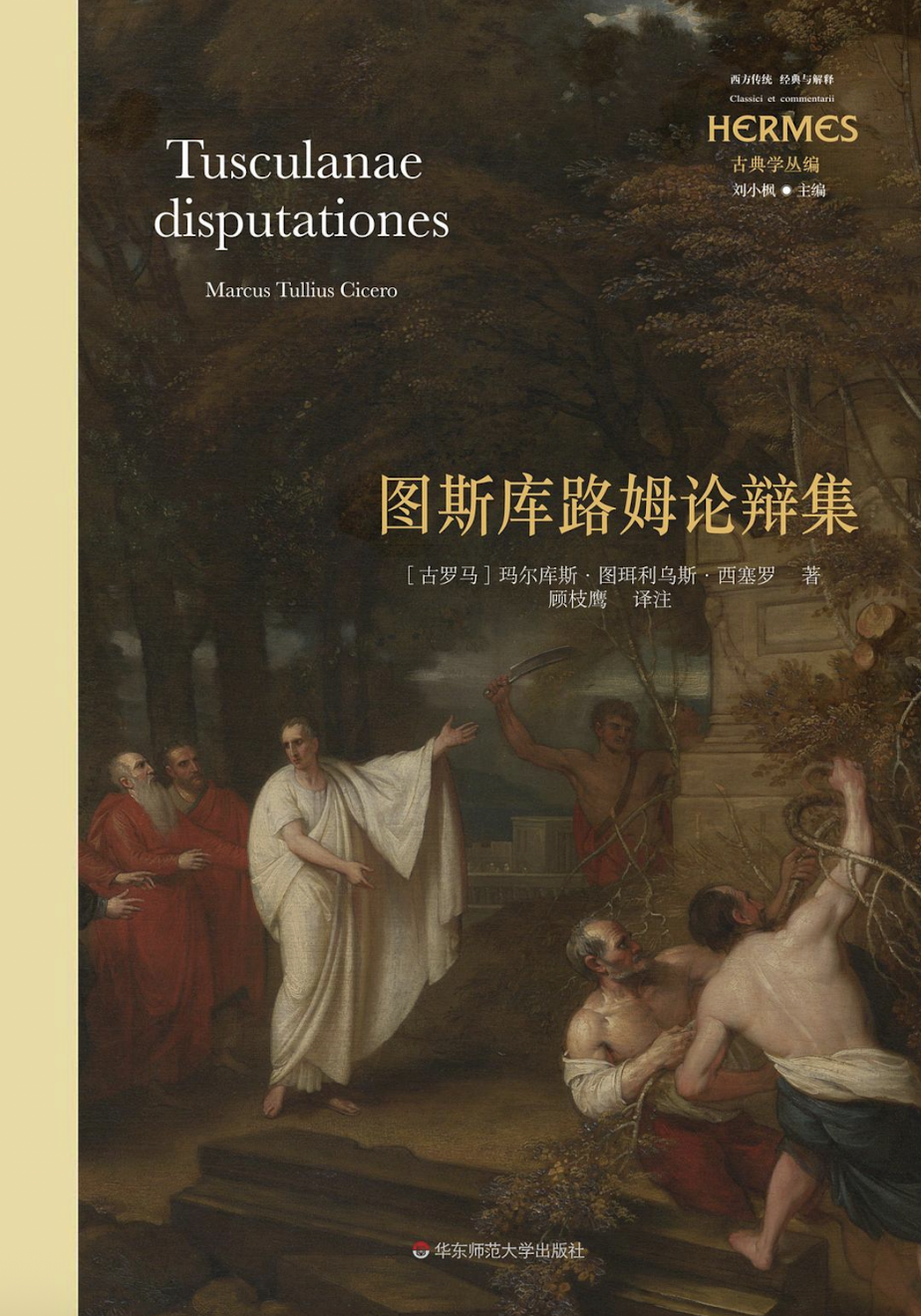
▲ 《图斯库路姆论辩集》,西塞罗 著,顾枝鹰 译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彼特拉克对廊下派哲人的这套观点颇为信服,《秘密》中引导“弗朗西斯科”与“奥古斯丁”在梦中相遇的真理女神开门见山地指出,这场对话的目的是治愈前者“严重的抑郁之症”。随后,“奥古斯丁”进一步解释这种病症:它在中世纪叫“怠惰”(accidie),在古代则称“忧郁”(aegritudo)。总而言之,这是一种“灵魂的疾病”(animi tristitia),也是彼特拉克“心中最深的伤口”(maxima tue mentis vulnera):

我承认,在其他所有折磨我的痛苦中,都掺杂着某种虚假却令人愉悦的滋味;但这种忧郁之苦(tristia),却只有彻头彻尾的痛楚、悲惨和可怖;通往绝望的道路永远敞开,驱使不幸的灵魂走向毁灭。此外,其他情感的冲击虽然频繁,却短暂而瞬息;而这种瘟疫般的痛苦却如此顽固地抓住我,以至于整日整夜将我捆绑与折磨。(《秘密》2.49)

在现实生活中,彼特拉克确实面临类似的精神问题。在一封写于同时期的书信中,他对友人的倾诉如出一辙:

我不否认我得了一种相当严重的心灵疾病,但我希望它不会致命(mortalia);我也不能为了给出借口,就把我的疾病全部归咎于床榻。即使保持沉默,我也要重复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我病了,让我好起来吧。(《通信》15.4)

这封信的收件人是安德里亚·丹多洛(Andrea Dandolo),彼特拉克提到他时任威尼斯总督,则通信应发生在1342—1354年,学界大多认为,《秘密》写于1342—1353年或1347—1353年。彼特拉克在信的开头引用了塞涅卡的名言:“心灵拥有秩序的首要标志,就是能够静处并与自我对话。”这或许可以视作对《秘密》对话形式的暗示。

▲ 《秘密》手抄本,1470年
彼特拉克承认,正是由于“忧郁的疾病”扰乱了他的内心,他才始终漂泊无依。命运在他的人生中掀起了巨大风浪,种种不幸与苦难在他身上一再发生,就像派出无数敌人将他重重包围;他既没有逃脱的可能,也没有获得怜悯的希望,更无法得到任何尘世的慰藉。彼特拉克意识到,自己一生要面对命运的无数次挑战,最终不可避免地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彻底击倒。当必死的结局降临时,世上的荣耀与德性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而这正是彼特拉克最不能舍弃的(《秘密》2.50–51)。就像齐格弗里德·温泽尔的总结:

他的悲痛不是来自命运的任何一次单独的打击,而是一连串的不幸。它源于累积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是对人类悲惨境遇的思考,是对过往艰难困苦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它们一同使得彼特拉克意志消沉。

对于这种痛苦,诗人的解决方案是退守到与自我的对话中,因为这种漂泊感归根结底是人对生命不确定性的主观感受,而他需要做的就是强化自己的灵魂力量,使其在命运的风浪中仍能保持宁静。这种观点与廊下派哲人可谓不谋而合:人尽管无法预知或改变由神圣命运掌控的外部世界,却可以在自我“心灵的堡垒”(arx interior)中坚守,从而避免“情感的扰动”(animi perturbationes),最终实现“不动心”(apatheia)的“完满德性”(perfecta virutus)。在廊下派哲人看来,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在彼特拉克笔下,“奥古斯丁”亦借用西塞罗的箴言告诫“弗朗西斯科”,“唯有德性能使心灵臻于幸福”(《秘密》1.6)。
不能否认,历史上的奥古斯丁早年确实受到廊下派德性观的影响。根据贺腾的研究,奥古斯丁在《驳学园派》(Contra Academicos)的序言中便指出,拥有德性的人能够远离不幸的纠缠,从而避免沦为命运的傀儡。这一时期的奥古斯丁与廊下派哲人一样,认为德性作为正确和整全的理性是“内在自足的”,因而不受外界触动。然而,关键的转变源于奥古斯丁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接受和对摩尼教二元论的克服。在一些后续著作中,他修正了自己早年的德性观,并从两个方面批评廊下派:首先,德性并非居于人的内在,而是必须指向作为超越性目标的上帝;其次,基于人的原罪与必死性,仅仅依赖自然理性构建的德性也全无实现幸福生活的可能。
在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对廊下派的批判最为成熟和激烈。他彻底否定将德性等同于幸福的观点,认为人的心灵并不像廊下派哲人所说的那样,有着超越一切的权能。在尘世之中,由于命运的无常和与生俱来的原罪,人往往面临着许多无能为力的困局,乃至被厄运逼迫到濒临绝境的地步。德性与其说是幸福生活的保障,不如说恰恰证明了人类身处地上之城的不幸。因此,那些对世俗事物而非永恒事物的爱、对当下纵乐而非自我德性完满的爱,都是应遭谴责的贪爱(cupiditas);只有皈依才能使人克服负罪的永死,通往上帝恩典所给予的真正幸福,舍此别无他路。
彼特拉克并未接受奥古斯丁的上述修正,他更倾向于引述奥古斯丁的早年著作,对晚期作品中有关恩典、原罪和皈依等主题的讨论,则采取相对回避的态度。一个显著例子是,《秘密》中的“奥古斯丁”曾提及“弗朗西斯科”心灵疾病的别名——“怠惰”。在基督教语境中,这被看作“致命之罪”(peccata mortalia)中最危险的一种,其后果是使人失去对恩典的希望,从而背弃上帝,最终招致灵魂的永死。虽然彼特拉克的心境与这种描述相符,但他并未因此忏悔,这无疑颇为反常。即便不了解约翰内斯·卡斯西阿努斯(Johannes Cassianus,360—435)等早期沙漠隐修士对“修道院疾病”的阐释,他也不应忘记奥古斯丁对原罪与必死性的再三申述:

迎接我的是一顿疾病的鞭子,我正走向地狱,带着我一生对你、对我、对别人所犯的罪业,这罪业既多且重,加重了使“我们在亚当身上死亡”的原罪的铁链……我的灵魂已附于真正的死亡,而我当然还以为基督肉体的死亡是虚假的;基督的肉体真正死亡过,我这个不信基督肉体死亡的灵魂也只有虚假的生命。(《忏悔录》5.9)

与此相比,彼特拉克对自身罪业的告解体现出与中世纪传统的脱节。首先,他将其完全视作一种私人的心灵困扰,而非对人类的普遍罪责加以忏悔。而在十四至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教会在指导信徒忏悔时通常会列出关于各种罪过的具体问题,比如,圣贝纳迪诺(St. Bernardino,1380—1444)编纂的忏悔指南就细分为十二条规章,并针对七宗罪、十诫等七个方面进行自我质询。这些规则确立的忏悔方式是一套极为系统的固定程式,其用意也并非关注告解者的生平经历或情感体验。在与彼特拉克同时代的基督徒眼中,忏悔的目的是发现人格中的共相而非殊性,换言之,中世纪人的自我认识本质上是借助对基督的信仰来审视每一个人有罪的心灵。

▲ 《忧郁Ⅰ》
阿尔布雷特·丢勒 绘,1514年
更重要的是,彼特拉克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对上帝的离弃,而是将他的一切不幸归咎于尘世命运的无常,并试图在地上之城中寻找德性完满与幸福生活的可能。在一首题为《给自己》的诗中,彼特拉克写道:

我常常恐惧地紧抱自己无力的灵魂,思忖能否穿越苦海茫茫,以泪水浇灭肉身的火焰;但有朽的俗世牵绊我,狂烈的欲望拖拽我,惯习用致命的绳索捆缚我——看啊,我就身处这种境况!刺骨的恐惧用浓烈的黑暗将我笼罩;因为谁若以为他能铭记死亡,并无畏地凝视生命的终点,那么,他不是自欺、自负便是癫狂……哦,盲目的我们!竟然在坟墓之下筹备伟大事业?你既知生命迅疾,岂敢怀抱长远希望,确信未来尚有时光?

彼特拉克在这首诗中毫不掩饰自己对死后世界的怀疑乃至恐惧,甚至大胆嘲弄对救赎怀有坚定信念的同时代人;但在基督教语境里,尘世的死亡恰恰是通往最终审判的门槛。约翰·惠特菲尔德注意到,彼特拉克甚至忘记了一个基督徒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灵魂被罚入地狱。
对中世纪的基督徒而言,义人的永生与罪人的永死是上帝最终审判的完成,这是人在尘世中“第二次死去”的考验,也是在“新天新地”中实现至福的必由之路。但彼特拉克从未表示,其忏悔是为了将自己从通往永死的歧途上解救出来,甚至鲜少使用“洗炼罪孽”这类风靡一时的文学题材,反而极为坚定地认为,“对于已经不幸或变得不幸这个问题,人没有任何选择”(《秘密》1.5)。彼特拉克若不是有意忽略“用心灵选择上帝的道路”这一中世纪神学的普遍观点,至少也不认为自己背负着必须在此生此世洗涤的原罪。尽管他确实引用了奥古斯丁的许多言论,但他对奥古斯丁的阅读更接近一种廊下派式的哲学练习,即希望能借此摆脱激情和欲望的困扰,而非试图成为一个虔敬的信徒。
可以说,彼特拉克就这样将羁旅者的罪愆这一概念从神学传统中抽离出来,这些缺陷不再从属于基督教的道德神学体系,而是转变为一种对世俗生活的属人体验。路德维希·盖格认为,彼特拉克的怠惰“不再是一种企图将信徒拒于天国福祉之外的宗教罪孽……而是转变为一种真正属人的苦难——并且尤其令出类拔萃之人深受其扰:这苦难表现为外在与现实之间的斗争,表现为试图以哲学思考来填补日常空虚的努力,表现为由往日苦难的回响与对未来痛楚的预感所引发的悲惨心境,表现为因对比古人的笃定安宁与自身内心的煎熬不安而产生的绝望”。概言之,彼特拉克的自述高度世俗化,以至会让读者忘记其背后的神学语境。

▲ 《徒步旅行者》
耶罗尼米斯·博斯 绘,1490年
因此,彼特拉克的真正悖谬之处在于,他虽然遭受着基督教原罪和永死观念的困扰,却不愿接受奥古斯丁式的皈依,而是试图以廊下派的方式解决奥古斯丁面临的摩尼教二元论困境,即用内在于自我的德性来克服地上之城中的种种苦难,在尘世中得到真正的幸福。然而,这种“双重面孔”的后果是,一方面,彼特拉克让笔下的“弗朗西斯科”承载了自己对世俗的所有贪爱,他纵情地宣告,“我不想变成上帝,去拥有永恒的生命或者拥抱天堂和大地,人类的荣耀对我来说已然足够”;但另一方面,在奥古斯丁的引导下,彼特拉克对属人世界的体验仍然是一个将他囚禁其中的巨大监狱,“贫穷、苦难、屈辱、疾病、死亡,及世间一切同样可怕之事”,总是违背他的意志而降临。“认清并憎恶自身的悲惨境遇极易做到,但要摆脱它却远非如此——前两者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意志(nostri arbitrii),而后者却掌握在命运(fortune)手中”(《秘密》1.5):

生命飞逝,一刻不停,死亡紧随其后,大步紧逼;当下(presenti)与过往(passate)的事物纷至沓来,在我心中交战(guerra),令我痛苦不堪,而未来更是如此;回忆与期待交替着压在我的心头;说实话,若非我对自己尚存怜悯,我早已选择从这些思绪中解脱。

在真正的奥古斯丁看来,这种不幸原本可以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得到充分化解,或者说,作为世俗时间的“心灵意向的分裂”(distentio animi)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对上帝的背弃”。在有朽的尘世里,时间永在流逝,无法把握,使人错误地将爱欲停留在个体必然消亡的生命体验当中。因此,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样彼此冲突的时间经验,在事实上造就了自我的苦难乃至罪愆。奥古斯丁认为,只有将心灵朝向“上帝永恒的现在”,抛下尘世的诱惑与沉沦,从而令“上帝的恩典(gratiam dei)将神圣的爱注入我们心中”,自我才能“从罪和死的律法中解脱出来”(liberat a lege peccati et mortis),得到真正的收束与完满:

看起来,心灵命令身体,理性命令罪过都是值得赞美的;但是,如果心灵和理性都不能像上帝命令的那样侍奉上帝,那么,心灵就无法正确地命令身体,理性也不能命令罪过……有人认为,哪怕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指向别的目的,这德性也是真实和尊荣的。但他们如此膨胀和骄傲,已经没有了德性,而算是罪过了。正如不是肉身,而是高于肉身的,才能使肉身活;同样,不是人,而是高于人的,才能使人活得幸福。(《上帝之城》19.25)

但正如彼特拉克走下风涛山时的宣告,他将自我而非上帝视为这个世界的至高者,从而“推迟”乃至拒斥了这种皈依,故而无法借助另一个具备超越自我权能的他者来提供奥古斯丁式新我重生的可能,而是必须依靠自己的心灵去治愈世俗的痛苦。在彼特拉克眼中,德性和幸福生活的真正实现应当有赖于“本人自我统治”(《图斯库路姆论辩集》2.20),而非听命于上帝恩典的召唤。可以说,对彼特拉克而言,“自我而非上帝,才是人面对世界、他者的支点”。
随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发展,晚期中世纪哲学逐渐走向了一场“主体性的革命”。雷思温指出,这场革命带来的结果是,人们对自我的认识不再局限于朝圣者的神学语境,不再始终向远离尘世的上帝之城寻求终极救赎的可能,而是开始在内在的心灵秩序中寻找存在的根基。作为经历堕落、沾染原罪并羁留此岸的受造物,人类开始更加积极地接受并肯定这种由死亡和有朽性规定的束缚状态,并试图通过自我解放与自我救赎来实现内在的超越。代表自我的旅人形象也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主体性色彩的现代概念,失去了古典和中世纪加诸其上的城邦政治、宇宙秩序和宗教神学的种种意涵。

▲ 《意大利风景中的旅行者》
扬·博特 绘,约1649年
在探索和塑造现代自我的思想进程中,彼特拉克无疑是一个重要坐标。他试图在奥古斯丁笔下挖掘出廊下派哲学的隐匿面貌,从而获得来自尘世的慰藉。但他没有料到,在弥合古典德性观与基督教皈依论的过程中,上帝作为至高权能的超越性与作为心灵本源的内在性之间发生了巨大的矛盾。因此,他不得不将上帝的权能收拢到自己的心灵之中,迫使心灵成为那个与世界相对的、至大无外的真正他者。吉莱斯皮认为,这种现代自我的诞生最终导致的是,“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实际发生的并不是神的简单清除或消失,而是将其属性、本质和能力转移到人的心灵之中。因此,所谓的去魅过程也是一个返魅过程”:只有把人在某种意义上变成神,实现所谓“内在性的下沉”,才能为现代世界的全新图景提供一种融贯相通的解释。
然而,作为基督徒的彼特拉克或许已经发现,在他笔下的世界里,个人的命运与上帝宏大的恩典无关,心灵中的秩序也无法再反映世界的救赎历史。虽然他试图在廊下派和奥古斯丁的裂隙之间重新安顿人与世界、上帝与自我的关系,但恰恰是这种尝试使他同时远离了基督教世纪和古典时代,在对当下的忧郁与对未来的恐惧中推开了现代世界的闸门。就这样,彼特拉克将自己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与世隔绝的主体,只能在自己的个体心灵中找到纯粹自我,并与所有偶然的、外部的联系割裂开来。对生活在彼特拉克身后世界的现代人来说,所有心灵之外的境地都如同奥古斯丁笔下的异乡,他们已无法在此生此世找到能够安顿自我的家园,每一个人,都成了世上忧郁的漂泊者。
作者简介



彭小瑜|“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作为主教的奥古斯丁和古代北非教会
欢迎关注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