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程茜雯:金嘴狄翁的流亡与和谐政制
编 者 按

金嘴狄翁(40—120)出生于罗马帝国比缇尼阿(Bithynia)地区(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西北部,毗邻普罗庞提斯海、黑海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名城璞茹撒(Prousa),因演说技巧绝佳得名“金嘴”,有八十余篇演说辞和一些书信传世。他的祖上皆为璞茹撒乡贤,受人景仰,而他自己则从小接受当时以希腊修辞术为核心的博雅教育。狄翁原本会成为智术师,从事公共演说和修辞术教育,继承祖上衣钵,偶尔过问璞茹撒的政治。图密善皇帝(Domitian, 51—96)统治时期,一桩偶发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狄翁有一篇演说辞谈及自己的人生变故,题为《在雅典:论流放》(Ἐν Ἀθήναις περὶ φυγῆς),其中说到,由于他与罗马权贵提图斯·撒比努斯(Titus Flavius Sabinus)的友谊,这位友人在公元82年被图密善皇帝处决之时,他也获流放之刑,不得再踏上罗马或比缇尼阿的土地。为了探知流放是福是祸,狄翁行前去德尔菲求取神谕,得到的却是阿波罗的一个“奇怪的且不易理解的回答”:
不少研究者认为,这则神谕可能是狄翁的杜撰。他在演说辞中还提到奥德修斯第二次远航前下冥府求教于先知忒瑞西阿斯,并得到如下指示:
奥德修斯归家后须再度漂流,在大地上寻找未见过大海的部族,宣扬海神波塞冬的威名。狄翁提到奥德修斯第二次远航前的求教经历,意在暗示自己前往德尔菲求取神谕得到的是奥德修斯式的使命:继续眼下的修辞术事业,经世致用,将希腊教化传扬至帝国的大地之极。教化内容包括人的德性品质到君主的善政,乃至统一的普世秩序的建立。为了证成神谕,狄翁在流亡的路途中凭借极具表演性的修辞,将流亡经历变成自我教育的契机,完成了向哲人身份的转变。自此,狄翁以哲人身份担负起在帝国构建希腊式神圣秩序的责任,从比缇尼阿开始他的“ὁμονοία[和谐]政制”实践,最终成为皇帝图拉真(Traianus, 53—117)的修辞术教师,指导他施行善治。和谐政制最终是否成功了,难以断言,而他教诲的王政计划则肯定是以失败告终。这些政治实践凸显了狄翁获得的流亡神谕的暗示能量,却也暴露了神圣言辞的内在局限。因此,流亡神谕的证成,最终并不在于狄翁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他心目中理想的神圣秩序,而在于他始终恪守并践行在帝国疆域内“到达大地之极”的政治使命。

▲ 《奥德修斯求教于先知忒瑞西阿斯》,壁画,1580年
一 流亡神谕与寻找哲人身份
史称狄翁是第二代智术师中的一员,这些靠表演性修辞术为生的文人学士得名于菲洛斯特剌托斯的《智术师列传》。菲洛斯特剌托斯(Philostratus, 约170—240)与狄翁相隔大约一个世纪,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初期的希腊文人学士喜欢用智术师式的言辞来展示思想,以至于世人以为他们是智术师,其实,“他们不是智术师,但由于看起来像智术师,因此也拥有智术师的头衔”——狄翁就名列其中。公元四世纪出生于昔兰尼(今利比亚东部)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叙内西欧斯(373—414)离狄翁生活的时代也不算太远,他区分了作为智术师与作为哲人的狄翁,但他承认,狄翁“皈依”哲学后,虽然专注于传授道德哲学教诲,但仍像智术师时期一样雄辩。
无论如何,狄翁起初的确是位智术师,后来才变成哲人。倘若如此,他如何由智术师转变为哲人,以及这种转变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有趣的问题。演说辞《在雅典,或论流放》(简称《论流放》)为我们考察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手文献。从中不难看到,彼时的狄翁已经意识到,智术师和智术师式的修辞术教育存在局限。不过,他并未放弃表演性的修辞功夫,而是策略性地将其用于更为宏大严肃的政治目的。在这篇演说辞中,狄翁借描述自己获得的神谕暗示,他将在流亡途中经历一番自我教育并实现精神转向,以此证明自己未来的政治使命乃神谕所示。狄翁在演说辞中甚至诱导读者追随自己,与他一起远离故土和罗马,前往说希腊语的诸城邦漫游,以见证他的转向,认可他的使命和承担使命的资格。我们不知道狄翁何时写下这篇演说辞,如果写于晚年,那它就相当于狄翁的回忆;如果写于流亡之初,那它表达的就是自我期许。
演说辞开篇,狄翁对自己为何会遭受流放稍作介绍后便转入正题。他首先承认,流放的最大痛苦是远离故土,奥德修斯的经历就是证明。奥德修斯曾经辉煌的功绩和卡吕璞索永生的承诺都不能打消他对伊塔卡的热爱,若能看到那片土地上燃起的青烟,他即便马上死去,也死而无憾(《论流放》4)。乍看起来,狄翁是在渲染对故土的思念让他痛苦不堪,但他紧接着就说,流放让他感到畏惧的其实并非远离故土,而是可能会让他这辈子一事无成。由此看来,狄翁提到奥德修斯的经历的真实用意在于,他与英雄奥德修斯共享同一事业。换言之,狄翁将自己遭受流放视为奥德修斯式的第二次远航,其使命是传播古希腊的诸神宗教,教化无信仰的蛮族。接下来,狄翁就说到自己曾前往德尔菲神庙求得过阿波罗的神谕——他自我激励地说:
随后,狄翁让著名的犬儒哲人西诺佩的第欧根尼出场,但只字未提他的名字,而是用修辞性的比喻称之为自己流亡时特意换上的“谦卑服饰”,还说第欧根尼被称为“流浪汉”(《论流放》10–11)。狄翁为什么要隐去第欧根尼的本名?“谦卑服饰”这个名称已经表明,犬儒哲人是一副外套,狄翁将身着这副外套踏上流放之途。倘若如此,这副外套与狄翁的身体本身是什么关系?狄翁为什么要身着这副“谦卑服饰”流亡?流亡结束时,他会脱下这副外套,抑或让外套变成自己的身体?无论如何,吸引我们的问题在于,狄翁的真身与这副“谦卑服饰”的关系是什么。

▲ 《第欧根尼》
约翰·威廉·沃特豪斯 绘,1882年
狄翁随之开始自述流亡经历。他遇到一个路人问他对善恶的看法,他发现自己很难回答,因为他自认并非哲人,而且知道那些αὑτοὺς ἀνακηρύττουσιν[自封]的哲人不是真正的哲人,因为“成为”哲人是κατ᾿ ὀλίγον[日渐月染]、οὐ βουλευσάμενον[没有计划],真正的哲人οὐδὲ ἐφ᾿ ἑαυτῷ μέγα φρονήσαντα[绝不会自以为是](《论流放》11)。ἀνακηρύσσω一词的原义是祭司宣读圣言,这会让我们想到狄翁求得的神谕——言下之意,如果狄翁成为哲人,那么,他不会是自封的哲人,而是来自神圣的受命。
狄翁接下来讲,他受人之邀“对人的义务和在他看来有益的事情发表演说”(《论流放》13)。这时,狄翁让苏格拉底出场,这是演说辞中出现的第三位人物。他讲了苏格拉底对路人的劝诫,并借苏格拉底之口发问:“你们漂泊到哪里去了?你们难道竟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没有做任何应做之事吗?”(《论流放》16)这里的人称虽然是复数,听起来却像专门针对狄翁。同样值得注意,这句发问化用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对雅典人的发问:
看来,狄翁这时已经把苏格拉底视为自己的老师,因为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回答说,世人很难从邪恶的困顿中脱身,摆脱极度的无知和混乱(《论流放》13)。自以为掌握技艺的人在谋划善的共同体时常常束手无策,若要做有益于城邦的事情,就得接受苏格拉底的告诫,先追求智慧——这意味着成为爱智者/哲人。
此时我们必须考虑狄翁在前面提到的西诺佩的第欧根尼,他与苏格拉底是什么关系?是否可以设想,狄翁在选择哲学老师时曾经历过选择,并最终选择了后者?如果确有这样的选择,那么,这种选择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西诺佩的第欧根尼作为哲人并不关切城邦的善,苏格拉底则相反。
由此看来,狄翁一直在致力于理解阿波罗的那个“奇怪的且不易理解”的神谕,而西诺佩的第欧根尼和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为他的理解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最终,他选择了苏格拉底,这让他理解了神谕:他应该在整个帝国传扬爱智的教诲,整饬帝国秩序。狄翁早年曾跟随廊下派大师穆索尼乌斯·茹福斯(Musonius Rufus)学习,此人在罗马教授哲学,狄翁25岁那年(65年)被加尔巴皇帝(Galba,公元前15—69)流放。那时,狄翁受智术师的修辞奇观支配,不懂得什么是热爱智慧。直到自己踏上流亡的道路,遭遇肉体磋磨,与形形色色的人相遇和交流,他才开始对比不同的哲人,并理解了苏格拉底的教诲。

▲ 苏格拉底的教诲
尼古拉斯·吉巴尔 绘,1780年
演说辞《论流放》提到的第一位历史人物是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后来又提到苏格拉底,这意味着狄翁心中已经有一个传统——从荷马到柏拉图的古希腊教化传统,其中蕴含着一种理想的政制。我们将会看到,狄翁后来致力于在罗马帝国实现这种政制。不过行文至此,他只是隐晦地定义了眼下所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狄翁才有底气声称与自封的哲人有别:他不是自封的哲人,而是受希腊教化和政制理想委托的哲人。由于这时的希腊地区已经是罗马的行省,而狄翁的抱负是恢复希腊的教化传统,他那充满魅力的演说辞难免让自己置身“高度紧张、充满竞争张力的表演空间”。由此可以理解,狄翁在演说辞中不以自己的名义说话,而是带上各种历史人物的面具说话,而他的面具即是灵魂本身。
现在我们可以来理解演说辞的标题“在雅典,或论流放”,直观地看,雅典是希腊政教传统的符号——由于罗马帝国的征服,希腊政教传统遭到流放。狄翁未必真的是在雅典发表了演说,我们宁可把这视为一种写作修辞:他模仿苏格拉底面对“最伟大、最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城邦的”雅典人发话,不同的是,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强调,他的教诲适用于“过去和现在几乎全人类”(《论流放》26)——这无异于说,他的教诲适用于罗马帝国。因此,在演说辞的结尾,狄翁自夸他这番老套的话让流亡途中的询问者“甚至在到达罗马时都拒绝让我安静下来”——“当罗马人召见我并邀请我发言时,我也努力与他们交谈”(《论流放》31):
显而易见,狄翁的抱负是,以希腊的教化和德政理想重建罗马秩序。因此,他的政治实践从自己最熟的家乡比缇尼阿开始,那里离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城并不遥远。

▲ 比缇尼阿的君士坦丁门遗址
二 和谐政制与哲人“统治”
公元96年9月18日那天,时年44岁的图密善皇帝遭罗马元老院中的政敌刺杀身亡,尽管他颇受罗马人民和军队的爱戴和敬重。得知这一消息时,狄翁正流亡到北方的珀恩托斯(Πόντος)或克里米亚。他还得知,老友内尔瓦(Nerva,30—98)受任于危难之际,宣布召回图密善皇帝执政时期的所有流亡者,他立即赶回罗马。然而,史称五贤帝第一位贤帝的内尔瓦执政不到两年,就突然中风离世(98年1月)。幸好他在离世前指定了44岁的图拉真为继承人,后者乃是第一位在亚平宁半岛之外出生的罗马皇帝。狄翁只好“竭尽全力与内尔瓦的继任者建立或重建联系”,“带着‘皇帝’的一封信胜利地回到璞茹撒”。狄翁在罗马建立的人脉为他以后成为图拉真的帝王师奠定了基础,他眼下的首要任务是在家乡比缇尼阿恢复希腊教化,结束几个重要城邦之间此消彼长的内耗状态——用狄翁自己的话说,他要实现希腊人的ὁμονοία[和谐]政制理想。当然,这一理想并非来自古希腊人,而是受亚历山大帝国的激发。
狄翁在罗马逗留期间,成功为璞茹撒争取到一些利益,如选举外来者的权利和增加城邦收入,把璞茹撒设为巡回审判区(assize)的首府(《罗马世界》,页52),这使得璞茹撒的“语法学家、智术师、哲人和医生从公职中获得豁免的数量”仅次于行省首府。狄翁“带着新的权威光环,在议事会上发表演讲”,他还拿出自己“与内尔瓦皇帝的通信”,让自己显得拥有尚方宝剑。当然,“与皇帝的友谊(只)是狄翁在当地进行政治实践的工具”(《希腊主义》,页195)。真正让狄翁有底气执政的是他的哲人意识。狄翁有一篇演说辞题为《在议事会发表的拒任书》(Παραίτησις ἀρχῆς ἐν βουλῇ),他在那里直接呼吁璞茹撒的精英们应该以哲人使命施政:
这种使命感承自苏格拉底当年在雅典法庭上的演说。因此,狄翁在比缇尼阿发表了多次演说,试图平息希腊诸城邦之间和城邦内部的争斗和倾轧——当时,士麦那(Σμύρνα)与以弗所(Ἔφεσος)的冲突影响很大。狄翁认为,这类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出身异族的罗马行省总督不懂得如何治理希腊诸行省的人民。针对这一情形,狄翁提出和谐政制的主张。他尝试调节尼科美得雅(Νικομήδεια)与尼凯阿(Νίκαια)两座城之间的冲突,就是显著的例子。这两个城邦分别比邻比缇尼阿和珀恩托斯行省。尼科美得雅临海,早在比缇尼阿行省和珀恩托斯行省合并为同一行省(公元前65年)之前,它便是比缇尼阿地区的首府。尼凯阿地处商路,经济条件更加优越,当时已被罗马总督设立为πρώτη[首府]。尼凯阿因此有可能得以与尼科美得雅共享以下权力:作为巡回审判区的中心城邦,可审理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案件,向其他城邦派遣军事总督,并收受比缇尼阿地区的十一税。尼科美得雅人对此深表不满,二者之间的矛盾甚至紧张到走向战争的边缘。
狄翁对尼科美得雅人发表了劝解演说——《致尼科美得雅人:论与尼凯阿人的和谐》(Πρὸς Νικομηδεῖς περὶ ὁμονοίας τῆς πρὸς Νικαεῖς)。他首先以巧妙的言辞让尼科美得雅人觉得,自己站在他们一边,他发表演说是对他们施以援手,而尼科美得雅那些“本地的或异乡的……演说家或哲人……无人敢提这种建议”(《致尼科》4–5)。言下之意,此地的哲人未能履行职责。
狄翁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例,二者为争夺希腊世界的“第一”地位而彼此倾轧,“最终却双双失去了它”(《致尼科》25)。希腊城邦喜欢追求虚假荣誉,这本应是“有教养、有品德的普通人都不屑为之的事”(《致尼科》29),却在罗马帝国的治下更加明显,以至被罗马总督称为“希腊人的陋习”(《致尼科》38)。狄翁告诫希腊人,正是这些纷争“给了统治者施行专制(τῆς τυραννίδος)的可乘之机”(《致尼科》36)。若尼科美得雅凭借临海的地理位置,与商业发达的尼凯阿联合,应城邦人民所需行事,将会获得远比“首府”这样的虚名更伟大、更美好、更丰厚的福祉。那样的话,作为地区首府赢得的“才不仅仅是领导权(τὸ πρωτεῖον),而是受城邦爱戴的引领”(《致尼科》35)。

▲ 陶罐上的希腊重装步兵
公元前5世纪,雅典博物馆 藏
随后狄翁又在尼凯阿发表了类似的演说,劝告当地人与尼科美得雅协作。秉持同样的原则,他尝试调和母邦璞茹撒与毗邻城邦阿帕美亚(Apamea)的类似矛盾,发表了《在母邦,论与阿帕美亚人的和谐》(Ἐν τῇ πατρίδι περὶ τῆς πρὸς Ἀπαμεῖς ὁμονοίας)和《致阿帕美亚人,论和谐》(Πρὸς Ἀπαμεῖς περὶ ὁμονοίας)两篇演说,还代表母邦直接与阿帕美亚人和谈。狄翁的政治实践取得了成效,比缇尼阿的诸多城邦如尼科美得雅、阿帕美亚等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甚至“竞相邀请他担任顾问”。狄翁见时机已经成熟,便进一步向璞茹撒的同胞们提出建立城邦联盟的建议:
这段讲辞表达了狄翁的和谐政制构想的基本含义,即以比缇尼阿地区为中心,建立希腊行省的自治城邦联盟,不让罗马统治者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削弱城邦的权利和管辖权”,干预希腊城邦的生活。从狄翁发表的这些演说来看,他对罗马人的统治“极端蔑视”(《希腊主义》,页221)。不过,没有证据表明,狄翁乐于见到罗马帝国的崩溃,那样的话,希腊教化恐怕会彻底沦丧。狄翁看重的是政制的德性,而雅典人若丧失教化,就不比野蛮的罗马人好到哪里去。因此,狄翁并不满足于希腊人的地方自治,而是关切整个罗马帝国的德性品质——“当罗马摆脱了罪恶,它将能够更好地统治世界”(《罗马世界》,页129)。他相信,既然罗马人“很快就学会”了“马术、射箭和重甲作战”,要让他们接受希腊的教化传统也并非难事(《论流放》37)。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得由哲人出任君王或让君王成为哲人:
由此可以理解,狄翁后来为何成了图拉真的修辞术教师,尽管我们不清楚他如何实现这一目的。
三 对罗马君主的德政教诲
狄翁把在整个罗马帝国实现希腊王政理想视为自己的流亡之途要达到的“大地之极”。用今天的说法,狄翁试图“调解希腊和罗马之间的关系”,让罗马君王来实现希腊的政制理想。对狄翁来说,希腊的政制理想是,地上的明君以天上的神王宙斯为典范。既然罗马人已经建立帝国,要实现这一理想,“狄翁别无选择,只能将罗马元首制作为君主统治的基础”(《希腊主义》,页192)。好在据说图拉真相当器重狄翁,虚心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为此,狄翁写下四篇以“王政”为题的演说辞,献给图拉真皇帝。这四篇《论王政》打造了“从荷马笔下的英雄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希腊王政传统”。从我们今天掌握的文史材料来看,这样的“传统”明显是狄翁的塑造,它并不是“历史”,而是一种理想。
《论王政》系列演说的第一篇发表于公元99/100年,其时图拉真皇帝刚继位一年有余,狄翁尚不知这位皇帝的品性,为了让他信服自己的教诲,狄翁在演说结尾提及自己的流亡,再次借助神谕来证明自己的使命。狄翁写道,在伯罗奔半岛游荡之时,由于“神圣机运的偶然”,他遇到一位像迪欧提玛(Διοτίμα)的老妇人。她预言狄翁“某一天会遇到一个强大的人,他统治了许多地方和民族”。老妇人叮嘱狄翁,要毫不犹豫地把她接下来讲的故事传达给君王。熟悉柏拉图《会饮》的读者都能看出,这是在化用迪欧提玛启迪苏格拉底的故事,不同的是,狄翁用罗马君王替换了苏格拉底或者说让哲人成了君王,如此笔法显然是在向图拉真皇帝传递某种神圣的信息。

▲ 苏格拉底与迪欧提玛交谈
弗兰兹·考吉格 绘,1810年
狄翁笔下的迪欧提玛接下来讲的故事,是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阿里斯提珀斯转述的赫拉克勒斯在十字路口面临的选择(《回忆苏格拉底》2.1)。转述完这个故事后,狄翁对图拉真皇帝直接挑明话题:
狄翁的这段演说辞的写作手法可以说是传统修辞术的“用典”,但在这里却成了政治教化的手段:正是这一自塑的“神使”身份让狄翁“有资格‘找到’并向图拉真转述和概括古代神圣智慧的神话/言辞”。
但是,仅狄翁具有教授德政的资质还不够。狄翁巧妙地以图拉真仰慕的亚历山大大帝锻造德性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 吹笛人提摩忒欧斯(Τιμόθεος)为亚历山大演奏,曲调颇有雅典娜的气质,使他着迷似地跑去拿武器。狄翁意味深长地说,笛声的激励固然重要,但他不够克制,这表明他欠缺理性,而音乐知识和技巧“并不能彻底治愈”或“完全补足(他)ἦθος[性情]上的缺陷”(《王政一》,页14)。作为修辞术教师,狄翁的职责固然是致力于找到恰切的言辞”来教育君王,它必须“既激昂,又轻缓,既勇武善战,又宁静和平,既遵循法律,又真正有王者气”(《王政一》,页13)。但这类言辞要取得实效,还得取决于听者是否先天具有王者气。狄翁的讲辞把亚历山大说成秉性有缺的君主,显得是带有风险的政治测试,即试探图拉真是否具有王者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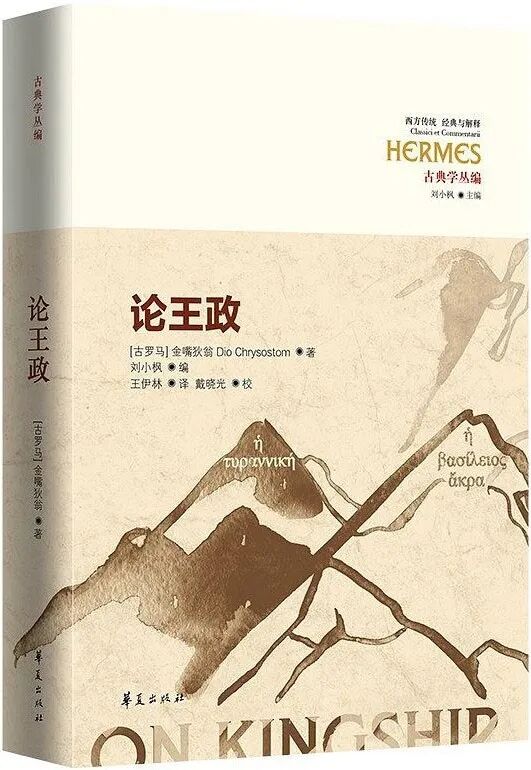
▲ 金嘴狄翁《论王政》,王伊林 译
华夏出版社,2019年
试探过后,狄翁才开始为图拉真描摹理想君主的形象。理想君主的品质体现在神王宙斯拥有的一系列不同别称,如“父亲”“君主”“城邦卫士”“朋友和伙伴的庇护者”“人类的守护者”和“乞援人的保护者”等(《王政一》,页20)。理想君主应当像牧羊人般慈爱温厚地对待臣民,他的好战必须以造福于臣民的和平为前提。这样的君主如同神王宙斯的人世化身,能够实现与天界秩序相应的人世间的和谐统治,其统治范围没有地域和民族之分,它遍及大地之极。不难看到,狄翁的理想君主与和谐政制论是荷马的宙斯神话、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神话和廊下派思想的融合。
图拉真是否通过了狄翁的政治测试?狄翁在第二篇《论王政》讲辞中为图拉真打造了量身定制的学习计划,似乎图拉真暂时得到了狄翁的认可。在这篇演说中,狄翁和图拉真显得建立起真正的师生关系。狄翁仍以亚历山大大帝作为代言人,他与其父腓力讨论荷马笔下具有王者气概的英雄、君主应热爱的诗歌、音乐,实际上是在对图拉真施行德性教化,如亚历山大大帝所言,何不“把这看作给谨慎的君主上的一堂关于王政的训练和教导课呢”?通过这种叙述方式,狄翁为图拉真皇帝拟定了阅读书目,还特别提到应当阅读“高尚、伟大且充满王者气”的荷马,而非赫西俄德的诗作。在此基础上,君王应当跟从最好的修辞术教师和哲学教师修习修辞术和哲学,以磨砺德性。
图拉真似乎听从了狄翁的教诲,开始按这位哲人拟定的计划学习。第三篇《论王政》讲辞中的语气让人明显感觉到,此时“演说家和这位君主的关系亲密”。据德裔奥地利古典学家汉斯·冯·阿尼姆(Hans von Arnim, 1859—1931)考订,这篇演说辞是在公元104年9月18日宣读的,那天是图拉真的生日。狄翁显得有意通过赞颂式的训诫激励这位罗马皇帝。他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大谈德政,企望君主懂得凭借统治的美德获得最大幸福的道理,并用波斯君主作为反面典型来对比图拉真,以至有学者认为,狄翁的这篇演说辞带有过于浓厚的谄媚色彩。但莫勒斯认为,狄翁对图拉真的“赞美”是表面修辞,“主要作用是缓和批评”,巧妙的恭维其实包裹着严厉的劝诫,修辞术派上了用场。

▲ 《图拉真的正义》
欧仁·德拉克洛瓦 绘,1840年
第四篇演说辞似乎能够证明莫勒斯的理解,因为狄翁谈论的主题之一是:帝王是否可教。这看起来与之前的演说辞主题不协调,实际上与第一篇演说辞形成呼应。换言之,狄翁一直拿不准图拉真是不是他值得期待的君王。无论如何,在第四篇《论王政》中,狄翁的言辞明显带有消极色彩。他还提到,君主的正义使他无需用武力去争取王位或打击敌人。这话很可能是针对具体现实而言,因为当时图拉真正要发起第二次征服达契亚王国(位于蒂萨河、多瑙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今大部在罗马尼亚境内)的战争(105—106)。换言之,在狄翁看来,图拉真此举是急躁冒进,他想模仿亚历山大大帝,实则并不明智。
据菲洛斯特剌托斯记载,图拉真在凯旋仪式上让狄翁与他同乘一辆金色战车,并对他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我爱你就像我爱自己。”有古典学者据此以为,这足以证明“修辞术的表演”让希腊文士在罗马的地位得到提高,或者说曾有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希腊的“第二代智术师”的教化打造了“希腊历史的[又一]新纪元”。图拉真与狄翁同乘凯旋战车,便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最好的证明。其实,菲洛斯特剌托斯记叙的这段轶事恰恰表明,图拉真皇帝表面上赐予了狄翁作为智术师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实质上拒绝了他作为哲人和王政教师的身份。换言之,这段轶事与其说证明了狄翁的政治抱负的成功,不如说证明了他的彻底失败。莫勒斯认为失败的不是狄翁,而是图拉真,因为后者的天性中欠缺某种德性,这使得他更热衷于通过征战实现对荣誉的追求。这种看法并不能为狄翁的失败提供辩护,因为,辨识受教育者的德性恰恰是苏格拉底式教育的前提。
结 论
今天的我们不应该仅仅以成败论英雄,狄翁企望以希腊教化打造罗马帝国的宏愿,毕竟让古希腊文学留下了最后一笔亮眼的遗产。他与写下《平行列传》的普鲁塔克(46—120)是同时代人,他们和其他“第二代智术师”文人一起,致力于传承古希腊文明的精粹。在《波律斯特涅斯,或在故国的演说》中,狄翁充满希冀又无助地说:

▲ 《阿波罗与缪斯在赫利孔山》
克劳德・洛兰 绘,1680 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藏
莫勒斯说得对,狄翁“于道德和哲学方面提出的主张宏伟得无以复加”。不仅如此,基于希腊的古典教化理想,狄翁对自己所处的希腊世界和罗马帝国的统治及其统治者都要求甚高,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在罗马的君主教育失败后,他仍在罗马帝国的希腊地区四处奔波,不断发表演说,至死对古希腊的教化理想忠贞不渝。通过撰写演说辞,他企望未来的读书人能像他那样“书写更好的道德故事,而不是他们各自的过去和现在的悲惨故事”。这样的道德教诲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了不讨人喜欢的陈词滥调,但正如莫勒斯所言,“也许即使在今天,一些人也会发现,‘古人’狄翁‘简单’的道德要求并没有完全失去它们的力量”。
作者简介

程茜雯,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罗马帝国的第二代智术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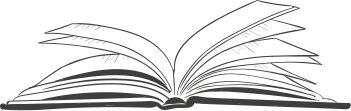

欢迎关注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