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赵宇飞:苏格拉底教育青年的中间道路
编 者 按

从古典时期到近代,色诺芬在文人圈中一直享有很高声望。但自十八世纪以来,他的声望一落千丈,被认为资质愚钝,无法把握苏格拉底哲学的真义。据说,他将苏格拉底描绘成遵守城邦传统道德的老好人,就是显著的例证。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列奥·施特劳斯为恢复色诺芬的名誉不遗余力,这一情形才得以扭转。他的学生如克里斯托弗·布吕尔和托马斯·潘戈承接施特劳斯的眼力,进一步推进了对色诺芬的认识。本文基于这些学者的研究,尝试理解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描绘的苏格拉底教育青年时采取的中间道路,并在此基础上以阿尔喀比亚德为例,比较色诺芬与柏拉图记叙的苏格拉底施教的异同。
为了反驳对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指控,色诺芬和柏拉图必须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阿尔喀比亚德等被雅典寄予厚望的年轻贵族,在与苏格拉底交好后,反而给雅典带来毁灭性打击?雅典人在审判苏格拉底时,一想到阿尔喀比亚德这样的败类,就会怀疑热爱智慧对城邦政治有何意义。显然,为苏格拉底辩护,很容易陷入两难困境:如果承认苏格拉底对阿尔喀比亚德等人的影响,那苏格拉底就得间接为西西里远征失败和“三十僭主”复辟负责;如果否认苏格拉底的影响,则又坐实卡利克勒斯的警告——热爱智慧既不能拯救苏格拉底的生命,也不能让城邦避免最大的危险(《高尔吉亚》486b)。

▲ 《苏格拉底教导年轻人》
[法]让·西蒙·贝泰勒米 绘,1784年
从这一背景出发,我们有了理解色诺芬在《回忆》中描绘苏格拉底教育青年的中间道路的基础。μέση ὁδός[ 中间道路 ] 的说法,最早见于《回忆》第二卷第1章记叙的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提珀斯(Aristippus)的对话。为了逃避城邦民义务,让自己过无拘无束的生活,阿里斯提珀斯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他既不愿做统治者也不愿做被统治者,两者的生活都不自由;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才“可以通向幸福”——他称之为自由之路(《回忆》 2.1.11)。苏格拉底轻易就驳倒了这种说法:做寄居他乡的外邦人,虽可免于城邦民的义务,但也失去了城邦对城邦民的保护,一旦遭遇暴力,外邦人远比城邦民更易受到侵害。他还指出,尽管阿里斯提珀斯不愿依附于任何城邦,但其中间道路仍依赖于所在城邦的法律。因此,他想象的自由生活不过是自欺欺人。
虽然阿里斯提珀斯的中间道路无法成立,但施特劳斯提醒我们,苏格拉底在批评阿里斯提珀斯的同时,自己也在践行一条中间道路,即践行“既非完全政治的生活,又不完全脱离政治”。基于这一洞识,有学者做了进一步阐发。肯尼思·布兰查德指出,苏格拉底完美地履行了雅典城邦民的职责,为政治家提供建议,因此间接参与了政治;同时,他也在自己的生活中享受热爱智慧的乐趣:间接参政和热爱智慧构成了苏格拉底生活方式的两个侧面。有论者认为,苏格拉底的中间道路“实现了公民与哲人两种身份的奇异结合”。
这种理解难免给人带来可疑的印象:苏格拉底似乎分裂成了两个不同形象,即作为政治人和哲人的苏格拉底。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两者何以可能结合。如果能够结合,那么苏格拉底就会是公民 - 哲人(citizen-philosopher),然而何谓公民 - 哲人恰恰是个问题。苏格拉底如何教育青年,似乎对理解这一问题具有决定意义。我们可以问:苏格拉底对青年的教育究竟是哲学教育还是政治教育?如果两者都是,那么,政治教育与哲学教育的关系是怎样的?尤其困难的问题是:为什么苏格拉底成功地教育了某些青年(如色诺芬),帮助他们在政治行为中取得了成功,而教育某些青年却没有成效?哲学教育在政治教育方面所能达到的限度在何处?本文尝试探讨这些布兰查德等人的解读没有充分回答的问题。

▲ 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年—约前355年或前354年)
01
《回忆》的前三卷,除了开篇直接为苏格拉底遭遇的指控辩护,都在记述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对话的对象主要有两类:有政治抱负的青年和智术师。与前者对话时,苏格拉底往往通过一连串反诘来暂时挫败青年的政治抱负,劝导他们在掌握相关知识后再投身城邦政治。例如,在与格劳孔交谈时,苏格拉底让他看到自己对城邦的财政和军事一无所知,并不知道如何让城邦获益(《回忆》3.6)。这些对话直接与政治事务有关,但都很简短。前三卷中篇幅较长的对话,主要发生在苏格拉底与智术师之间,如与阿里斯提珀斯(《回忆》2.1 和 3.8)和安提丰的交谈(《回忆》1.6)。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反驳智术师意在争取在场的青年。希庇阿斯曾忿忿不平地指责苏格拉底总是“通过询问和反驳所有人来嘲笑他人”,却从不给出自己对任何事情的正面判断(《回忆》4.4.9)。这足以表明,有青年在场的时候,苏格拉底不会与智术师直接讨论哲学问题,而是力图让青年远离智术师。我们可以说,这类对话体现了苏格拉底的政治行为。
在第四卷中,色诺芬记叙的苏格拉底与欧蒂德谟的对话长达数章,从而让我们得以看到在前三卷中无法看到的情形:苏格拉底如何教育有政治抱负的青年。我们看到,欧蒂德谟头脑简单,但颇有政治抱负。他搜集了“许多被认为最具名望的诗人和智术师的作品”,希望在“言说和行动”等方面 “超过所有人”(《回忆》4.2.1)。为了引起欧蒂德谟注意,苏格拉底有意在他面前谈论政治,甚至当着众人的面谈自己对他的看法(《回忆》4.2.2–7)。引起欧蒂德谟的注意后,他便开启了一对一的交谈。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不断追问欧蒂德谟对一些基本的政治观念的理解,例如“何为民人”和“何为民主”,欧蒂德谟回答民人就是“城邦民里的穷人”;苏格拉底继续追问“何为穷人”,并指出贫穷与富有具有相对性,除非用“是否足够而且有余”来衡量(《回忆》4.2.36–38)。这时欧蒂德谟才惊讶地发现,僭主由于欲壑难填,也应归入穷人和民人之列,他原本对民主的理解也随之瓦解(《回忆》 4.2.39)。通过类似的方式,苏格拉底向这位颇具政治抱负的青年表明,他对“什么是正义”和如何辨别好坏一无所知(《回忆》4.2.11–21、4.4.23–36)。欧蒂德谟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的政治抱负荡然无存,“非常沮丧地离开了”,他甚至“蔑视自己,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奴隶”(《回忆》4.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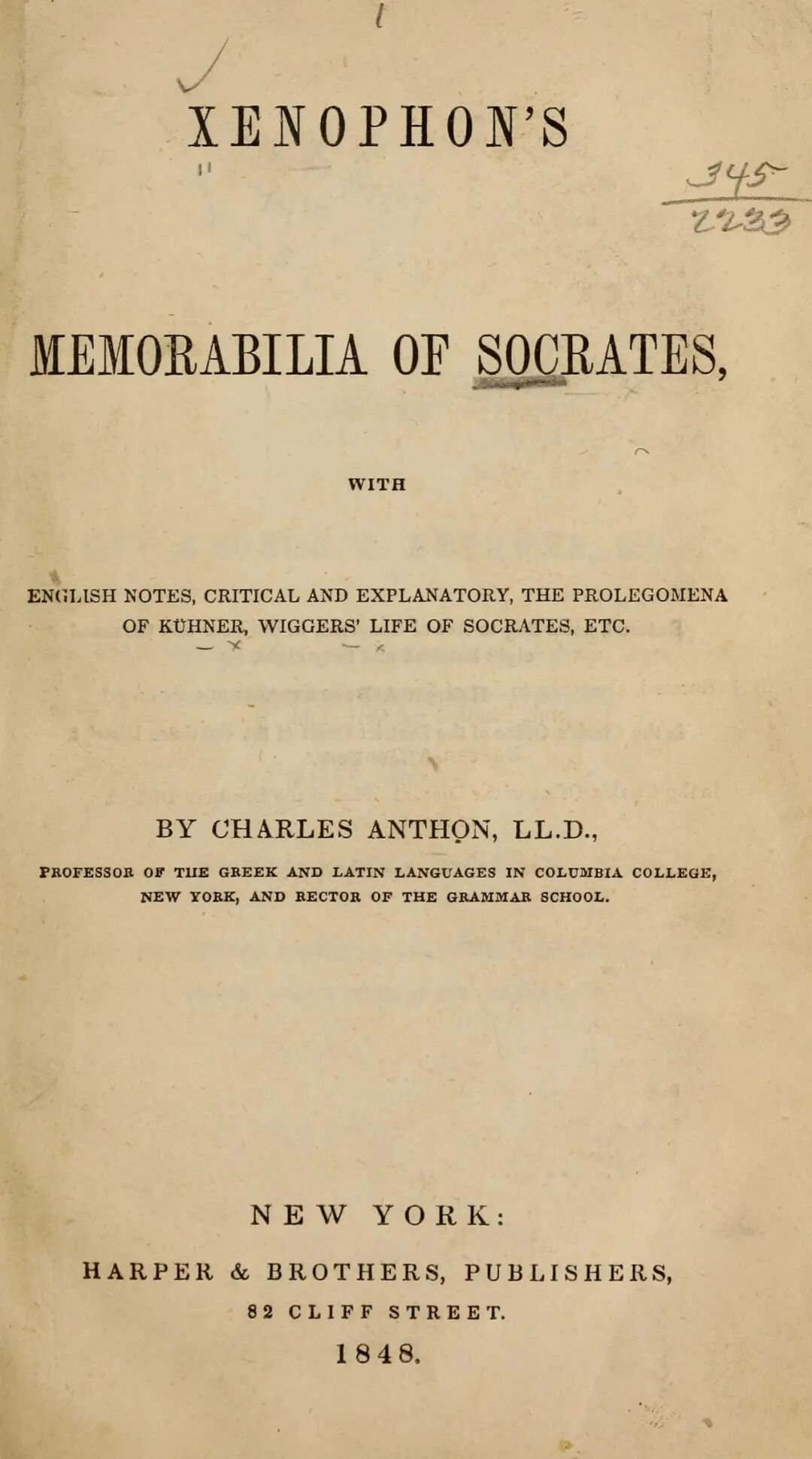
▲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查尔斯·安顿英译本,1848年
在多数情况下,色诺芬没有交代有政治抱负的青年在与苏格拉底单独交谈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格劳孔、克里提阿斯、小伯里克勒斯等人在与苏格拉底对话后,是否仍有兴趣与他交流,或是否会根据他的教诲进一步反思自己,接受他的建议。但苏格拉底与欧蒂德谟的对话不同,色诺芬不仅告诉读者,此后欧蒂德谟与苏格拉底更亲近了,还强调苏格拉底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发现欧蒂德谟已成为温顺的追随者后,苏格拉底不再像原来那样诘难他,而是“用最简单清晰的方式”解释他认为欧蒂德谟“应该知道”以及“最应去追求的东西”(《回忆》4.2.40)。
苏格拉底没有急于向欧蒂德谟展示自己教育中最核心的部分,而是先培养他的节制(σωφροσύνη)意识,尤其在神明问题上的节制(《回忆》4.3.1–2),并由此转向自制(ἐγκράτεια)。在苏格拉底看来,自制是“德性的基础”(《回忆》1.5.4),且对“更老练地行动”至关重要(《回忆》4.5.1),比如对培养交谈能力就不无裨益。显然,节制和自制是苏格拉底赖以施教的基础,而非最终目标。在此基础上,苏格拉底把欧蒂德谟引向了推理(διαλέγεσθαι)或辩证法,即“人们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并根据类别把事物区分开(διαλέγειν)”(《回忆》4.5.12)。这种“根据类别把事物区分开”的能力,就是回答“什么是”这类问题的能力,如“什么是正义”(《回忆》4.6)。第四卷第 6 章是《回忆》中最具哲学色彩的一章,也是苏格拉底与欧蒂德谟的系列对话中的最后一组。由此可以看到,色诺芬展示的苏格拉底式教育有怎样的进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苏格拉底发现自己的学生做不到节制和自制,那么,他断乎不会引领这样的学生进入辩证法教育。
欧蒂德谟显然不具有推理天赋,由此可以理解,苏格拉底与他在这方面的交谈也未见得有多复杂深刻,除非我们设想色诺芬自己对这方面的交谈没有多大兴趣,如我们在色诺芬的其他作品中看到的那样。如果他是为了替苏格拉底辩护才故意不记叙复杂深刻的对话,那么,他就与柏拉图有很大的心性差异,因为后者从不避讳这类抽象推理的对话。从色诺芬记叙的苏格拉底与欧蒂德谟的对话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哲学教育无论深浅都必须以政治教育为前提:对神明的节制态度和具有自制的美德是基础,此外还有对僭政的态度(《回忆》4.6.12)。

▲ 《雅典学园》(局部)
[意]拉斐尔 绘,1510—1511年
02
按色诺芬的记叙,苏格拉底的教育注重培养年轻人的对话能力而非行动能力。从《回忆》的前三卷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施教仅仅涉及如何擅长推理和言谈,而这恰恰是阿尔喀比亚德等人在与苏格拉底交好时希望获得的能力(《回忆》1.2.15)。我们不难理解,在民主的雅典城邦,这是成功的政治家必需的技能。但是,培养对话能力与哲学辩证法训练是一回事吗?前者无疑是一种政治教育,但后者也是吗?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哲学在苏格拉底的政治教育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与苏格拉底自己的中间道路式的生活方式有关。
前文的梳理已经表明,苏格拉底教育青年的第一步是吸引潜在对话者的注意力,让对方愿意进入对话。例如,与欧蒂德谟一对一交谈前,苏格拉底曾开他的玩笑,甚至当众羞辱他,以此引起他的注意(《回忆》4.2.1–7)。事实上,苏格拉底对色诺芬也做过类似的事(《回忆》1.3)。第二步是苏格拉底用辩证法盘诘对话者未经反思的看法,让对方因感受到挫败而极度沮丧(《回忆》4.2.8–39)。许多人在经历这番挫败后“都不再到他跟前来了”,苏格拉底把这些人视为不可雕的朽木(《回忆》4.2.40)。若对方在既有观念被摧毁后仍愿意成为苏格拉底的同伴,他才会开启下一阶段的教育。在此意义上,让青年人沮丧、遭受挫败是苏格拉底施教的关键环节,它既起到筛选作用,也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品德有所欠缺。苏格拉底施教的第三步是引导学生具有对神明的节制态度,并学会自制。第四步才是用哲学辩证法让青年开始学会探究“什么是”的问题。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施教最终落脚在辩证式的交谈,而非教青年如何开展具体的政治行动。这意味着,他的施教并非是为了让青年参与城邦政治,而是为了让青年成为有德性的人,不过这样的教育对有志从政的青年也会大有裨益。
看来,我们不能说苏格拉底将有志于城邦政治的青年引向哲学,毋宁说他的哲学教育以政治德性教育为基础,以至于哲学教学的前提是政治教育。色诺芬展示的苏格拉底式教育就像一个圆圈:从政治走向哲学,再从哲学回到政治——即便有谁不回到政治,也不至于像阿里斯提珀斯那样以为自己可以过一种“既不……也不”的中间道路式的生活。按色诺芬在《会饮》中的记叙,苏格拉底自夸最擅长的技艺是“拉客术”,这引起了在场者的哄笑(3.10)。当时没有谁能理解苏格拉底看似戏谑的说法背后所隐含的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最为严肃的表达。记叙这个细节的色诺芬当然能够理解,但他没有挑明其中的严肃含义——直到两千多年后,施特劳斯和他的学生才言明:优秀的“皮条客”的含义是,苏格拉底自信能够在取悦对方的同时传授有益之事,而这里所谓的对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个人,乃至整个城邦(3.59)。色诺芬的《回忆》让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在与青年对话时实践了这门他引以为豪的技艺。一方面,他这位“皮条客”将年轻同伴引向了节制、自制和辩证法;另一方面,他也充当了为政治与哲学牵线搭桥的中间人。当苏格拉底实践这门技艺时,他既有益于对话者,也有益于整个城邦。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苏格拉底需要践行政治与哲学之间的中间道路,以及为何这条中间道路对他的施教至关重要。有志成为政治家的青年必须首先培养自制,并通过辩证法思考“什么是”之类的问题,学会辨识好坏、对错和高尚与低俗。有抱负的青年意识到自己必须与苏格拉底交往才能成为好的政治人,这就让苏格拉底有机会成为沟通哲学与政治的桥梁。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自己不会直接投身城邦政治。不难设想,如果直接投身政治,他就不会有时间与青年交流,也就无法帮助其中一些人成为优秀的政治家,甚至还必须与之竞争,像别的政治家一样在党争中互相倾轧(《回忆》2.6.17–20)。
在《回忆》第一卷中我们看到,安提丰曾问苏格拉底:既然他不参与政治,他何以觉得自己可以让别人更好地参与政治(《回忆》1.6.15)?而直到第四卷我们才看到对这一问题的真正回答:苏格拉底对有政治抱负的青年的施教,就是他参与城邦政治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本身又是一种哲学活动;或者说,他的施教作为一种哲学活动就是最好的参与城邦政治的方式——哲学和政治在苏格拉底身上结合在了一起。

▲ 《阿尔喀比亚德接受苏格拉底的教导》
[法]弗朗索瓦·安德雷·文森特 绘,1776年
03
那么,苏格拉底是否应为阿尔喀比亚德和克里提阿斯这样的青年负责?在有些青年身上,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为何会失败?在亚历山大·内哈马斯看来,这种失败内在于苏格拉底式教育的结构之中。为了把青年引向热爱智慧和辩证法,苏格拉底就得向他们展示辩证法的魔力,但由于苏格拉底采用进阶式的教育,在学生们还没有意识到节制和自制的重要性之前,苏格拉底只能初步预演辩证法。然而,这些过于年轻的对话者反而利用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中“所教授的形式技巧去顶撞长辈,破坏固有的价值观”。因此,苏格拉底让年轻人“过早接触了一种他们尚未准备好的论辩方式”,他的教育也要为年轻人的失败负部分责任。
阿尔喀比亚德和克里提阿斯在接受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时,都没能抵达节制和自制意识。从克里提阿斯后来对苏格拉底提出的指控来看,他甚至连苏格拉底吸引青年注意的那些反驳、嘲笑和羞辱言辞都不能恰当地理解(《回忆》1.2.33–38)。换言之,在与苏格拉底的交往中,克里提阿斯的进阶停留在第一步。至于阿尔喀比亚德,从他成功驳倒伯里克勒斯这位雅典大政治家来看,他似乎在模仿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回忆》1.2.40–46)。但这不过是对苏格拉底的初阶辩证法的模仿,他并没有掌握真正的辩证法——如苏格拉底向斐德若详细解说过的灵魂辩证法。苏格拉底辩证法的目的之一是,引导对话者重新审视自己此前未经反思的观念,而阿尔喀比亚德精巧的辩论术显然没能说服伯里克勒斯重新反思自己的法律观念。阿尔喀比亚德在施展辩论术时,并不在意引导对方自我反思,只关心驳倒对方。驳倒伯里克勒斯后,他便急不可耐地投身城邦政治,远离了苏格拉底(《回忆》1.2.47)。显而易见,阿尔喀比亚德缺乏节制和自制。事实上,阿尔喀比亚德更像智术师的学生,他的论证策略与苏格拉底对希庇阿斯的反驳颇为相似,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阿尔喀比亚德更强调暴力在法律中的作用,而这对雅典民主政治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比较《回忆》1.2.44–45 和 4.4.12–13)。
色诺芬记叙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的对话时特别强调,当时有许多同伴在场(《回忆》4.4.5)。有理由猜想,一度与苏格拉底形影不离的阿尔喀比亚德亲眼目睹了这场辩论。在《普罗塔戈拉》中,柏拉图描述了一场苏格拉底、希庇阿斯、阿尔喀比亚德都在场的对话,可见当希庇阿斯来到雅典时,三人身处同一人际圈子中。阿尔喀比亚德是这两场对话的听众,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听完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的辩论后,阿尔喀比亚德对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感到惊奇,而他的机灵才智让他很快就模仿苏格拉底,并用来驳倒对手。他迫不及待地来到伯里克勒斯面前,炫耀最新学到的辩论手段。他惊讶地发现,当问到“什么是法律”时,大政治家伯里克勒斯也不堪一击。这次成功经验让他相信自己已充分掌握辩证法,而自己曾深受苏格拉底的节制和自制伤害(参见柏拉图《会饮》),却没有让他有丝毫受益。
从柏拉图《会饮》中的记叙来看,苏格拉底从未想过要把阿尔喀比亚德引向哲学,苏格拉底对他的教育停在了第二步进阶。但苏格拉底无法阻止阿尔喀比亚德在别的场合看到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并加以模仿——色诺芬的记叙表明了这一点。既然如此,阿尔喀比亚德的败坏就不能归咎于他与苏格拉底的交往,甚至不能归结于他没能完成苏格拉底式教育,而是“美德不可教”的典型案例罢了。雅典人头脑简单地认为,如果阿尔喀比亚德没有受苏格拉底蛊惑去渎神的话,他会成为救星,让雅典取得战争胜利。柏拉图在《会饮》中让阿尔喀比亚德出面作证,苏格拉底没有教他渎神。而色诺芬的记叙则指出,哪怕阿尔喀比亚德没有与苏格拉底交往,他仍会在雅典民主政治的侵染下灵魂败坏(《回忆》1.4.1、1.2.24–28)。真正败坏阿尔喀比亚德的不是苏格拉底,而是纵容和奉承他的雅典人。由此看来,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或哲学没能挽救阿尔喀比亚德,根本就是莫须有的问题。

▲ 《苏格拉底在阿斯帕西娅家中寻找阿尔喀比亚德》
[法]让-莱昂·热罗姆 绘,1861年
04
在柏拉图的作品中,阿尔喀比亚德最早出现在《普罗塔戈拉》中并扮演重要角色,接下来他又在《会饮》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柏拉图还记叙了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的单独对话——《阿尔喀比亚德前篇》。如果把这三篇对话的戏剧时间连起来看,可能会有意外发现。
《会饮》的戏剧时间在西西里远征前不久(公元前 416 年),而《普罗塔戈拉》和《阿尔喀比亚德前篇》的戏剧时间则较早,都发生在伯罗奔半岛战争爆发前后。《普罗塔戈拉》的戏剧时间较明确,即普罗塔戈拉第二次来到雅典时的公元前 433 年左右,当时阿尔喀比亚德大约 17 岁。《阿尔喀比亚德前篇》的对话发生时,阿尔喀比亚德有多大年龄并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他还没到参政年龄,大约在 17 至 20 岁之间(参考 105a–b、110a、123d),因此应在《普罗塔戈拉》之后。《阿尔喀比亚德前篇》开篇提到,虽然苏格拉底此前也常出现在阿尔喀比亚德身边,但这是两人第一次单独谈话(103a)。《普罗塔戈拉》开篇,友伴打趣说,苏格拉底“明摆着刚追过阿尔喀比亚德的青春”(309a),而苏格拉底则说,这一次他说了不少话声援自己(309b)。尽管如此,两人在对话中没有直接对话,阿尔喀比亚德对苏格拉底也没有表现出后来的亲昵态度。此时阿尔喀比亚德似乎只是常与苏格拉底在一起,听他反驳旁人,对他有兴趣。只有在《会饮》中,通过阿尔喀比亚德的自述,我们才得知他与苏格拉底一度关系颇为亲密,而且经过了进阶过程。
在这三篇对话中,戏剧场景、阿尔喀比亚德的形象及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均有变化。《普罗塔戈拉》中的对话发生在半公开场合,对话内容也会在雅典社交圈中流传,苏格拉底本人就对市场上的熟人乃至陌生人复述了对话。《阿尔喀比亚德前篇》自始至终是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的单独对话。《会饮》中的情景接近《普罗塔戈拉》,但阿尔喀比亚德讲述的与苏格拉底的交往则相当私密。
《普罗塔戈拉》和《会饮》的场景都模拟了雅典民主政治,如施特劳斯所看到的那样:前者是关起门来启蒙,后者则是启蒙之后的公然渎神。但在《普罗塔戈拉》中,阿尔喀比亚德小小年纪却已经有僭主做派,他强势打断对话,取代了主人的角色,俨然是民主议事会中的主席。他促请“每个人都必须表明自己的看法”,显得是在主持民主政治辩论(336d)。接下来我们在《阿尔喀比亚德前篇》中看到,苏格拉底敦促阿尔喀比亚德不要急于从政,应该先“认识自己”:只有认识自己,才能认识“属于自己的事物”和“属于其他人的事物”,进而知道“属于各城邦的事物”,并成为成功的政治家(133c–e)。苏格拉底对阿尔喀比亚德的告诫明显具有“反”民主政治的性质,他显然担心雅典民主会败坏阿尔喀比亚德这位青年(131e、135e)。由于这场对话具有“反”民主政治的性质,它发生在完全私人的场合并不意外。《会饮》中的阿尔喀比亚德已是雅典民主政治中的人物,而他的入场明显有僭主做派,这与《普罗塔戈拉》中的情形一脉相承。这足以表明,苏格拉底与他的单独交谈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 柏拉图之《会饮篇》
[德]安塞尔姆·费尔巴哈 绘,1869年
在《普罗塔戈拉》中,苏格拉底主要在与普罗塔戈拉辩论,除了要反驳智术师外,也希望能吸引青年。《阿尔喀比亚德前篇》中的私人对话表明,苏格拉底已成功吸引阿尔喀比亚德的关注,因此后者愿意跟他单独交谈。苏格拉底用辩证法小试牛刀,试图尽力挫败后者炽热的政治野心,让他意识到自己对政治和战争事务所知不多。在《会饮》中,阿尔喀比亚德的自述补充了他与苏格拉底交往的重要细节:苏格拉底提醒他要关注自己的灵魂,不要总是“为雅典人的事情忙碌”,但他听不进去,仍然“拜倒在众人的迎奉脚下”(216a–216b)。尤其重要的是,阿尔喀比亚德特别多次提到苏格拉底的节制和作为德性基础的自制,却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应该学习的品质。在《会饮》中,柏拉图借阿尔喀比亚德之口让我们清楚看到,苏格拉底对他早已不抱希望。
对应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式教育的各阶段,《普罗塔戈拉》属于苏格拉底吸引青年注意力的第一阶段,这并非苏格拉底好为人师,而是为了让年轻人免受智术师的败坏,从而是苏格拉底的政治行动。《阿尔喀比亚德前篇》则对应于《回忆》第四卷第 2 章第 8 节所记叙的第二阶段。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对欧蒂德谟的施教上升到第三阶段,而在柏拉图那里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并没有引导阿尔喀比亚德上升,这足以证明苏格拉底因人施教。

▲ 阿尔喀比亚德(约前450或前451年—前404年)
结 语
可以得出结论,柏拉图和色诺芬都认为是雅典民主政治(而非苏格拉底)败坏了阿尔喀比亚德(参见柏拉图:《阿尔喀比亚德前篇》131e、135e,《会饮》216a–b;色诺芬:《回忆》1.2.24–28)。不同的是,柏拉图《会饮》中的阿尔喀比亚德虽不愿遵从苏格拉底的教诲,但仍然承认苏格拉底的言辞对他的魔力。他意识到苏格拉底的智慧,希望用他的身体美来换取智慧,却不知道苏格拉底智慧的真正奥秘——柏拉图借第俄提玛之口才透露了这一奥秘。《回忆》中的阿尔喀比亚德很快就离开苏格拉底,这表明他的天性拒斥苏格拉底的教育(《回忆》1.2.47)。因此,我们不能说阿尔喀比亚德错失了进阶教诲——《阿尔喀比亚德前篇》足以证明这一点。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并非对所有青年都缄口不言最高的辩证法——《斐德若》中的灵魂神话和关于修辞术的对话就是证明,更不用说《斐多》中的灵魂不死论辩。与此不同,色诺芬从未记叙述苏格拉底向年轻人展示极为思辨的辩证法奥义。在《回忆》的第四卷第 7 章,苏格拉底与欧蒂德谟的对话内容不再是青年需要学习什么,而是学习的限度:学习测量时,只需懂得正确丈量计算即可;学习天文时,只需能分辨时令即可(《回忆》4.7.2–5)。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劝说青年不要像自然哲人那样过分探究神明之事,否则有丧失神智的危险(《回忆》4.7.6)。因此可以说,苏格拉底也没有引导欧蒂德谟上升到真正的辩证法和对天体秩序的认识。但色诺芬自己知道,苏格拉底熟悉这些主题(《回忆》4.7.3、4.7.5)。为了更好地教育青年,苏格拉底必须更深入地掌握自然世界的存在秩序——柏拉图的《斐德若》足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始终拒绝谈论这些主题,这表明他在神明问题上比柏拉图更为节制(《回忆》4.3.1–2)。 色诺芬在这方面的缄口不言,无异于对柏拉图提出了隐晦的批评: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更热衷于讨论这些主题,这既无益于教育青年,也可能构成对城邦政治的挑战。
作者简介



欢迎关注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