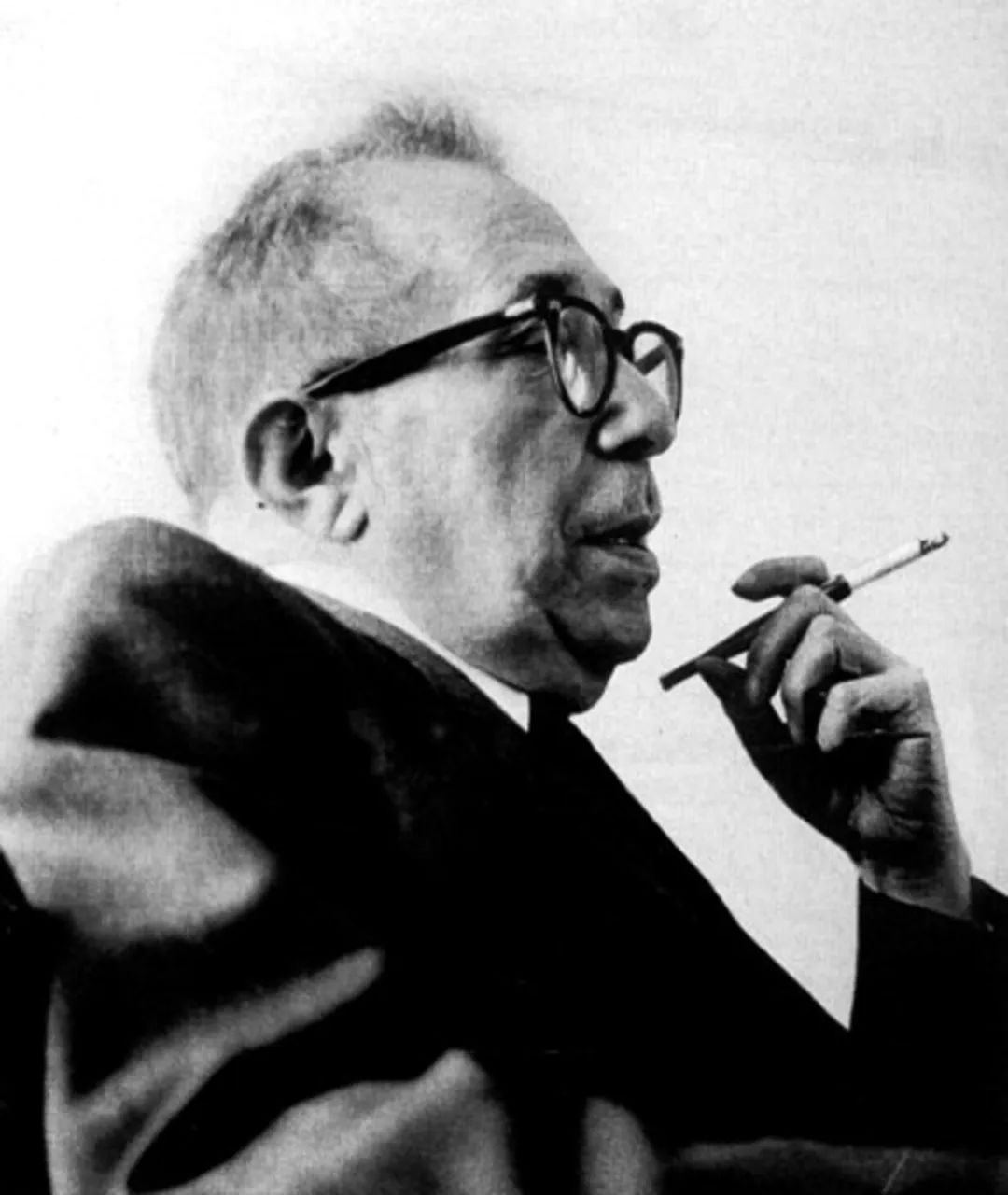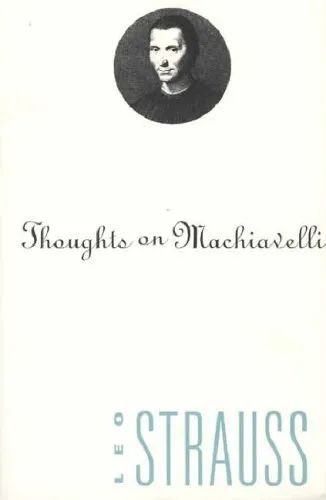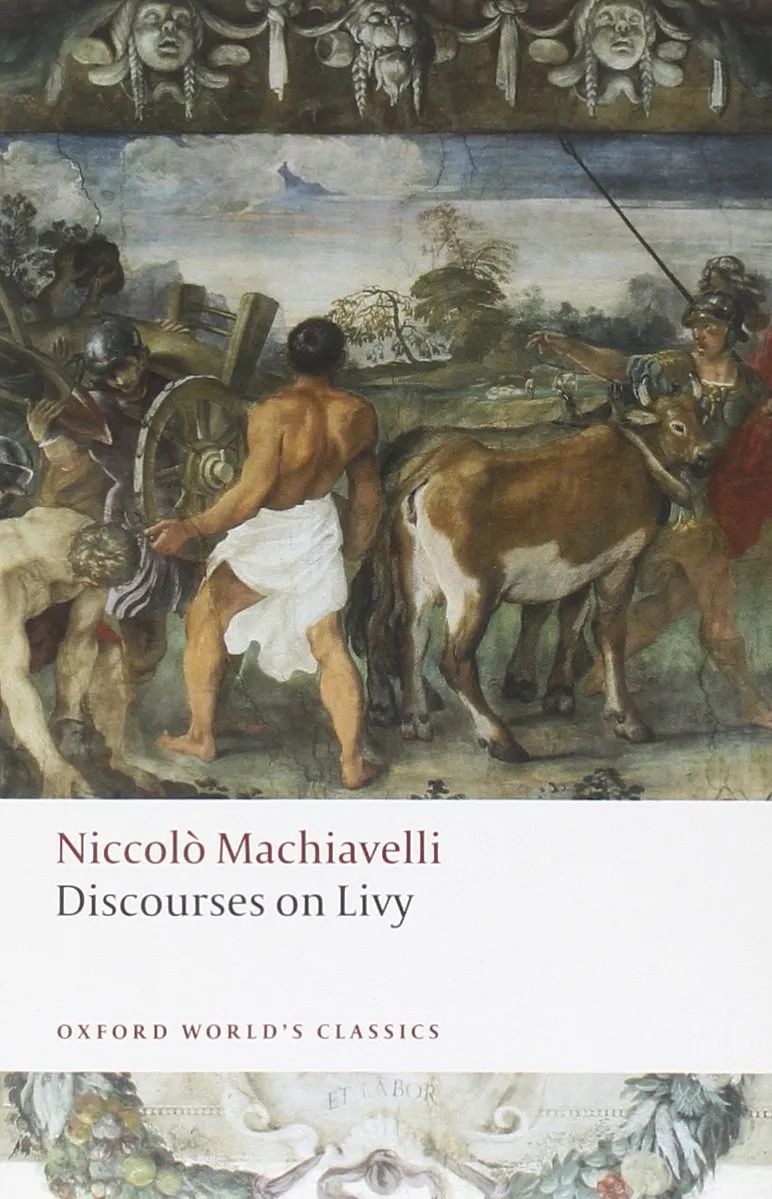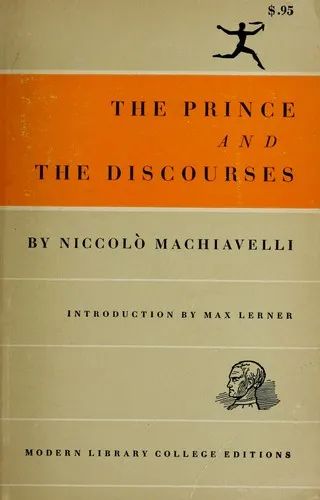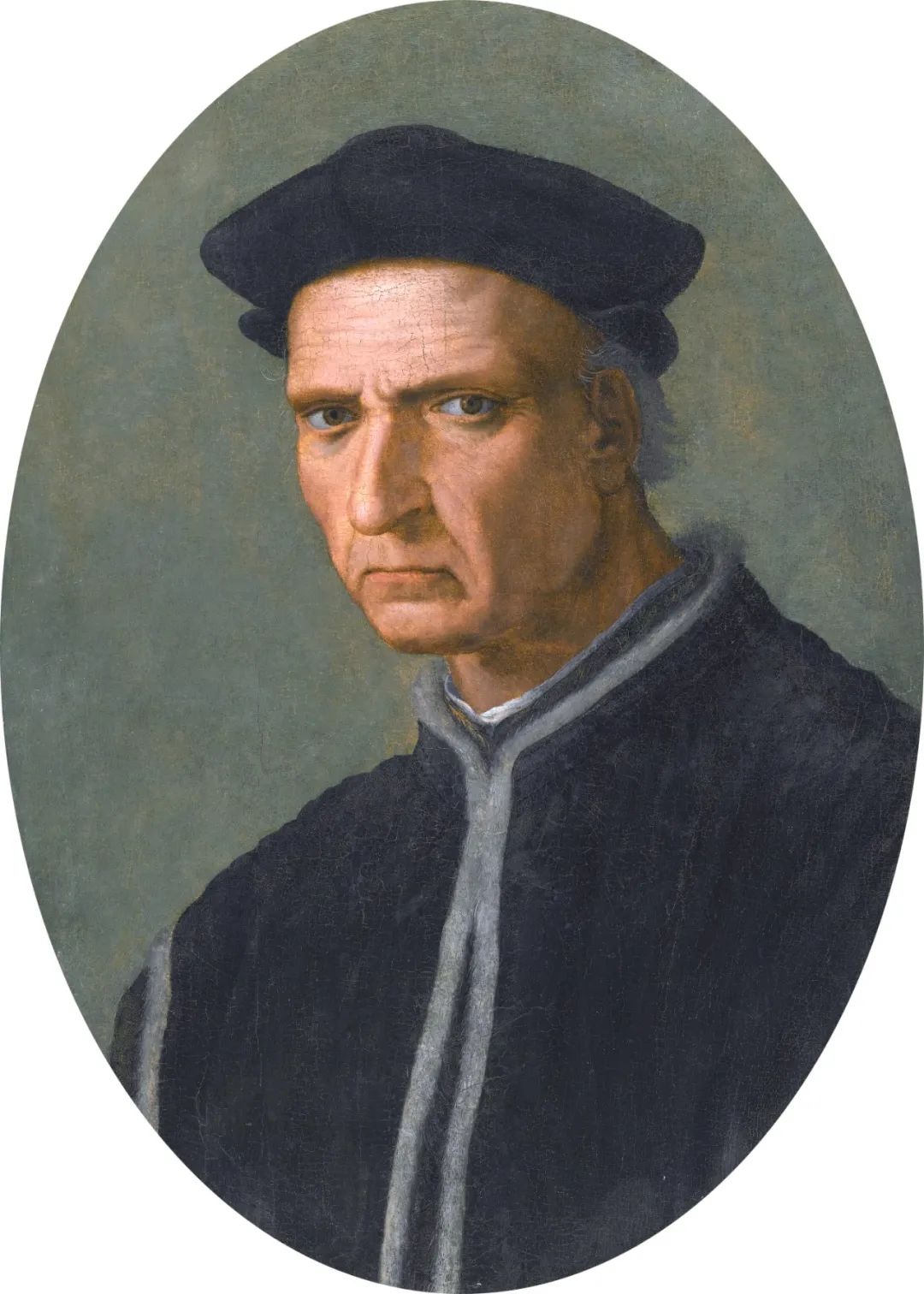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晚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里,称马基雅维利是“或许永远解不开的谜”。过去四个多世纪,无论学者们还是马基雅维利学说的传播者们都在揣摩和推测他的学说,这件事情本身似乎就可以印证克罗齐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特点的这一判断,甚至可以让人们去掉里面的“或许”。这位佛罗伦萨的国务秘书有着不同的形象,或让人们斥责为十恶不赦的魔鬼,或让人们颂扬为一心为国的圣贤,或让人们说成是一个超脱的、用“科学”手段观察政治和历史的学者。这些反映的还只是三种主要的观点,见于大量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文献。这些文献数量之浩瀚,我们无法想象。1936年,诺撒(Achille Norsa)在编其著作的参考书目时注明有2113条资料出处。今天再做参考书目,恐怕还要增加几百条。要知道,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人对这位意大利著名人物的思想作了重新论述。
尤其近几年,研究文献急剧增加。巴龙(Baron)、巴特非尔德(Butterfield)、费利克(Felix)、吉尔伯特(Gilbert)、魏特非尔德(Whitfield)及其他很多学者的研究堪称上乘。1954年,瑞多尔斐(Roberto Ridolfi)的马基雅维利传记面世,受到评论界广泛好评。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过去二十年是马基雅维利思想研究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尽管如此,克罗齐的“谜”似乎一点没有解开。虽然在落实一些存疑史料方面取得了进展,学者们的收获不能掩盖如下事实: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实质、其著述的意图以及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占据的地位之类更大的问题,今天和昨天一样困扰着人们。
近年来,在所有发表的著述里有一部十分突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认真关注,因为它提出并用很好的研究方法支持了如下断言:它解开了克罗齐的“谜”。这部著作就是施特劳斯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或是因为作者做出这个断言太过大胆,或是因为作者故意不太理会历史背景,亦或是因为作者忽略了近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施特劳斯的这部著作没有引起马基雅维利学说研究者们的注意,尽管它十分值得注意。不妨可以说,任何其它学者都不曾对研究马基雅维利思想倾注同样多的心血,展现同样高超的技巧和同样丰富的想象,以期揭示所研究的问题更深一层的含义。施特劳斯用自己习惯的方法研究,尽可能不让外部因素介入自己和研究的文本之间。结果是,他能够用一种新的目光观察佛罗伦萨的这位大人物。对政治学研究者说来,施特劳斯的这部著作不可或缺。《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集中地研究了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核心部分,也就是针对政治学里一直困扰着人们的问题而作的论述。作者研究马基雅维利整体的政治思想时力求研究方法详实、透彻,在这一方面,《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非其他同类著作可以比拟。无疑,施特劳斯让所有认为马基雅维利没有一套理论,只是凭“直观的、经验的观点”写作的说法再也没有了根据。▲ 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尽管施特劳斯这部著作的论据极为复杂──作者要随马基雅维利在其学说的迷宫里前行,论据不能不十分复杂,但主要观点非常简单:马基雅维利故意传授邪恶。该书导言(有些评论者似乎仅仅读了导言,实为可惜) 告诉我们,马基雅维利学说“没有道德、亵渎宗教”;他的思想含有“邪恶的”性质,“当代的专制统治就源于他的思想和他为了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理论”。这样,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看法就与自根提里特(Gentillet)和马洛(Marlowe,1564-1593)以来形成的阐释传统趋于一致。施特劳斯认为,大众心目中形成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马基雅维利式”这个概念实质上相当准确。不过,施特劳斯又谨慎地补充道,传统的阐释不无瑕疵,未能欣赏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坚毅和高贵,尽管这种高贵服务于邪恶的目的。的确,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十分尊崇,结果读者要再三返回导言,让自己确信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的最终评价是严酷无情的。
如果施特劳斯的观点正确,则克罗齐的“谜”当然不复存在。本文是对施特劳斯观点主要部分的初步评价(或者对他的“思考”的再思考) 。作者认为,施特劳斯的观点要得到人们的赞同,还有很大障碍。这些障碍可以很容易地从下面三个标题来论述。
▲ 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劝告忏悔”是马基雅维利写作的一篇劝告辞,显然是为了向佛罗伦萨的一个世俗宗教协会宣讲而准备的。尽管不能确定写作时间,但瑞多尔斐和其它学者确信,是在马基雅维利辞世之前写的。马基雅维利可能是这个协会的成员。不久前,吉尔伯特完成了马基雅维利大部分著述的英译工作,了却人们长久的期待,以前还没有“劝告忏悔”的英译本。尽管意大利统一后,马基雅维利著述的各种意大利文本通常都收录了这篇劝告辞,并以“道德论”(Discorso morale)为题,总的来说没有引起注意,即便那些注意到有这么一篇劝告辞的评论者也认为,它不过是一篇“讥讽”文章。多亏施特劳斯在自己的著作里好几处提到这篇劝告辞。不过,美中不足,他只是略略提到里面的内容,没有明确交代为何不予看重。至少就表面来看,这篇劝告辞完全不能印证施特劳斯的如下观点:马基雅维利这个作者反《圣经》、反基督,执意用一种革命方式立言达意,全然不顾西方世界一直恪守的文雅表意传统。由于“劝告忏悔”一文鲜为人知,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尤其如此,作者先要岔开一下,交代里面的内容。
马基雅维利的劝告辞用拉丁文《圣经》第129首(英译《圣经》第51首)圣歌 Deprofundis clamavi ad te,Domine(主啊,我从深渊向你呼告)作为宣讲内容。对“父老兄弟”听众,作者用接受了启示的先知者戴维的话开始,“为的是让那些像他一样有过罪孽的人们可以指望从至高、仁慈的主那里得到宽恕”。戴维诚恳之至地忏悔,主便欣然之至地宽恕。我们应引以为宽慰而不应感到灰心。主的怜悯和仁慈之心如天地广大。至高的主知道,人不能获救,除非在先犯罪,就是人的意志薄弱(la umana fragilita)让主震怒,而难以得到宽恕的不是犯下罪行,而是执意不断犯罪。仁慈的主为人类开启了一条“忏悔之路”,让在邪道迷途上的人们通过忏悔之路“升入天堂”。在上帝面前忏悔,是赦免我们所犯罪行的“唯一出路”。▲ 《贝里公爵的豪华时祷书》,林堡兄弟 等绘,法国尚蒂伊孔蒂博物馆 藏
虽然我们的罪行和错误不在少数且“多种多样”,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对主犯下的罪行和对邻人犯下的罪行。忘恩负义是所有罪恶的源头。在向主忏悔时,我们必须认真想一想,我们从主那里得到过多少恩赐:那“广袤无垠的地球”、那供我们享用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还有那给予了我们光和热的太阳。“世间万物创造出来为了人;人创造出来为了主和主的荣耀”。主给予人“一张面庞。与牲畜的不同,这张面庞不是朝向尘土而是朝向天堂”。主给予人双手建造庙宇;给予人语言颂扬主的荣耀;“给予人思维和理性沉思认识主的伟大”。
“反叛的人”忘恩负义,“误用主的恩赐且趋附邪恶”。
[反叛的]人用语言的天赋亵渎而非颂扬主的荣耀;用思维的天赋思考现实的世界而非主的存在;用欲望和情感专肆腐化堕落而不实现崇高的目的,故而由这些丑陋的行为人“让自己由理性的动物转化成残忍的动物”。人对主如此忘恩负义,就不再是天使而是恶魔;不再是高贵的生灵、而是卑贱的动物;不再是人而成了畜生。
接下来,“那些对主忘恩负义的人必然成为同类的敌人”。他们没有慈悲之心,因此也就没有了获救必需的一切,圣徒保罗和多少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教义已经证明这一点。“基督教立于之上的”正是慈悲之心。“人不相信主则心中不会充满慈悲……啊! 这是主赐予的美德呀! 那些心存慈悲的人有福了!”马基雅维利写道:“没有穿上一袭神圣的慈悲衣装”,人不仅不能得到邀请去天堂参加“我主基督举办的婚宴”,还要被“抛入永恒的地狱之火中”。马基雅维利提到的显然是《马太福音》第22章。
在“道德论”的结尾处,马基雅维利指出,我们站在主和邻人面前等待审判,必须将我们全副身心交由主来主宰。无论主给予什么惩罚,我们都该领受。不过仍然有让我们欣慰的事情:主告诉三次背叛耶酥基督的彼得,他会无数次地宽恕人、甚至宽恕过戴维通奸和杀人。“我的兄弟们,如果我们能够真心忏悔,有什么罪行主不能宽恕呢?”
哭泣甚至号啕大哭不足于忏悔。如果我们不是执意不停地犯罪,那么就必须“学习圣徒佛兰西斯和耶柔米”。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荆棘和石块”让自己的身体受苦。我们应该用上自己的荆棘和石块,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遏制“自己谋取私利、多行不义、欺骗和背叛邻居的愿望”。对我们的邻人,不仅不能粗暴对待,反而应该尊重和施恩。但是我们不能逃脱“恶魔之手”,不能逃脱我们用错误和罪行设好的陷阱,除非我们能够忏悔,能够与戴维一道真诚地呼喊“主啊!宽恕我们吧”;能够与彼得一道对我们所犯的过失感到万分的羞愧而痛哭流涕真诚地忏悔,看清楚,世人的享乐不过于一场春梦。
应该如何理解“劝告忏悔”?难道它只是那个时期人们司空见惯的装模作样表示对主虔诚的东西?倘若如此,我们在施特劳斯笔下看到的一个狂热、以摧毁基督教为己任的无神论者何以又愿意呈现一副信徒──狂热而虔诚的信徒──面目?难道我们真的可以认为,马基雅维利十恶不赦,写下这篇劝告辞来劝诱自己同代以及后代的轻信信徒接受《君主论》和《论李维》里面暗含的无神思想,又刻意假装一个正统基督徒写成这篇劝告辞,而且无害于他们的信仰?难道马基雅维利写作这篇劝告辞真的没有可能是从心里、从一个道德上十分敏感的人的心里发出的劝告?难道马基雅维利真的没有可能在内心厌恶政治的邪恶,从来不曾看不清楚邪恶就是邪恶,尽管他认为有必要将这类邪恶描绘出来?瑞多尔斐在评论“劝告忏悔”时肯定了最后的一种可能性:……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制造出无以数计的偏见,这些偏见深深掩盖了佛罗伦萨这位国务秘书对主的虔诚和信仰。时间让偏见成了定式,难以改变,偏见又强迫人们,为害最烈。“劝告忏悔”字里行间展现出哀婉之情和虔诚之心,足可视为达到作者基督教思想的顶端,那些评判他的道德水平和宗教质量的人们却斥责是编造了一个笑话。若不受偏见误导,他们都堪称是最具眼光的学者哩!
不必像瑞多尔斐、魏特非尔德和其它学者一样,要对马基雅维利宗教信仰的本质得出一个十分确定的看法。这些学者是要借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始终是一个自觉自愿、处心积虑、欺世盗名和厚颜无耻的无神论者,这在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这类戏剧中得到表现,也在目前施特劳斯的学术研究中获得支持,但传统的观点有悖于大量的事实。“劝告忏悔”并非马基雅维利唯一公开宣示基督教信仰的作品﹔在早些时候,他还写下一首宗教诗歌“蒙福魂颂”,而且在他的著述里,宗教词语和虔诚信徒应有的情感比比皆是。另外,作者在后面还要指出,即便在《君主论》和《论李维》里面,也见不到一个自觉自愿、处心积虑和摈弃传统的无神论者马基雅维利露面。
这里,作者无意维护如下观点:马基雅维利事实上是、或即便不是也认为自己是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或者至少关心基督教。但是作者认为,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需要有所平衡,施特劳斯则把佛罗伦萨的这位国务秘书描绘成处心积虑亵渎和反对基督教,看来未免走向了极端。
十分可惜,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这本书里,施特劳斯认为,所有那些在马基雅维利著述中找到证据,证明马基雅维利真心信仰基督的人,要么十分轻信,要么也和马基雅维利一样把宗教当作“统治工具”(instrumentum regni),信奉功利的观点。同样十分可惜的是,施特劳斯只评价过一次“劝告忏悔”,且凭这次评价就提出如下观点:在“劝告忏悔”里,马基雅维利不是严肃地劝告忏悔,而是劝告“或许就是在……死前忏悔”,也不失为逃避“地狱审判的办法”。这样俗不可耐的劝告绝难出自马基雅维利这个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是性格刚毅、思想高尚的人之口。
需要说明,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劝告忏悔”到底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还是一个问题,以后会受到人们、尤其那些认定马基雅维利为无神论者的人们更大的关注。这些人必须解释明白,他们心目中原来那个马基雅维利为何写出这么一篇不怎么“马基雅维利式”的东西。
马基雅维利在其主要著述里没有像在“劝告忏悔”里表明自己的如下信念:与人们在天堂婚宴上能够指望得到的东西相比,尘世间的欢娱不过于一场春梦。但就是在这些著述里,马基雅维利也会认为自己在矫正基督教中的一些“过于泛滥”的学说,而不是反对基督教的道德教义。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基雅维利非常清楚地表明,得到“尘世的荣耀”(worldly glory)是人们热切指望得到的最大的荣耀。马基雅维利明确反对把基督教视作只为升入另一个世界而设的宗教。他似乎找到了一点办法来协调基督教倡导的美德与罗马人信奉的美德。马基雅维利认为,在这个人“易于作恶而不是行善”的世界里,如果把《福音书》提出的最高要求按字面实行,必定造成破坏和苦难。
马基雅维利著述的很多篇章都显示,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基督教道德是对人的最高要求,用来评判有罪的人们的日常活动、他们那些低于最高境界的兴趣爱好以及那些只是相对说来美好的追求目标。一些重要的篇章,比如《论李维》第2章第2页,让人们愈加认为,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在干着推翻基督教勾当的无耻之徒;他心里经历着痛苦的折磨,行为处世既要符合道德的最高要求、又要符合我们现在所称的“权力政治”的要求。在上面提到的篇章里,马基雅维利最后提出,“我们的宗教”(la nostra religione)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及古代的人们坚定热爱自由和维护圣父(patria)的主要原因。不过,马基雅维利没有表示(当然他不会公开地表示),必须摧毁基督教或者应当让它逐步消失,然后让有美德的人民前来殖民。相反,马基雅维利明确告诉人们,“我们的宗教”给我们指出了“真道”,让人们摈弃“尘世的荣耀”,而不把它当作“至高的善”。在他看来,问题不是基督教或属虚妄飘渺,或属谬误百出,不能满足世人要求,而是“不足为道的人们”阐释基督教的方法错误,“只看它的消极一面而不看它的积极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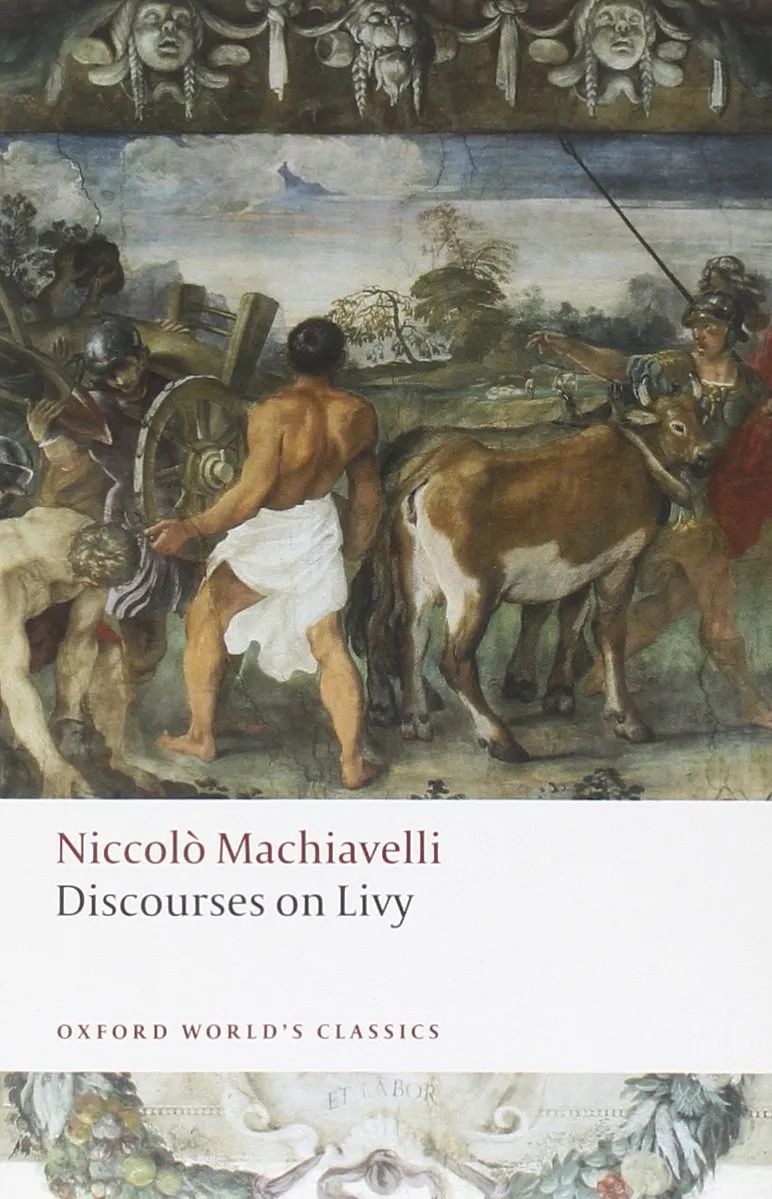
马基雅维利认为,基督教“允许”甚至“希望”我们热爱、尊敬、颂扬和保卫圣父。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政治层面上,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认为基督教完美无缺、是着眼于另一世界的宗教的阐释是错误的,基督徒既有超越俗世的责任,也有俗世要负担的责任。或许马基雅维利认为,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里,担当政治家的基督徒对现实世界里担负的责任,要么不予重视,要么胡乱应付,要么无动于衷。
马基雅维利可以说是一个反对教会卷入世俗事物的作者,对高教会派内部的腐化持尖锐批评态度。和以前的一些人士一样,马基雅维利认为教会国家的存在威胁意大利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他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当作政治教育的东西,尤其是伊拉斯莫(Erasmus)写作的小册子《基督教原原理》流于空想且文不对题。马基雅维利与贵查第尼(Guicciardini)二人都是“同人”(cognoscenti)的成员,在谈到当时的宗教活动时,两人偶尔难免有刻薄挖苦和不恭不敬的言语。无论施特劳斯提出的关于马基雅维利意图的如此理解会给我们多么深刻的印象,要说马基雅维利的言辞暗藏祸心,并用前人不曾有过的阴险狡诈曲意掩藏,目的在于摧毁基督教,未免过分,实难让人相信。
没有事实表明,马基雅维利认为可以让另一种宗教取代基督教,尽管马基雅维利清楚看到,基督教发展史呈现出周期性衰微和兴盛的格局。因此,笔者认为,施特劳斯后来表示马基雅维利“认定基督教不会永世不灭”有失妥当。
笔者认为,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第1章、第21页中说的一番话作的解释差强人意。马基雅维利大意是说,“在有人生活的地方若找不到真正的军人”,错在为人君主者,这个道理胜过所有其他道理。施特劳斯认为,这句话表明,在马基雅维利那里还有超过基督教的道理。笔者倒更有理由认为,马基雅维利只是想通过这种表述强调,为保卫国家必须建立一支民众武装。
在施特劳斯以上的解释和其它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施特劳斯重视的,常常是让自己的研究方法得以成立,而非研究问题本身,这未免可笑。我们可以在很多行为主义政治学者的著述里找到这样的错误。施特劳斯开始时提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根本上说是前后连贯的,而且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经过仔细推敲,与总体的计划相关联。然后,施特劳斯又别具匠心地将马基雅维利言语拼到自己的连贯图画里。尽管笔者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比起人们惯常的评价来要更加谨慎和连贯,但在他的著述里,完全见不到在霍布斯著述里可以见到的前后一致的学说。研究方法必须与研究问题相称,何况马基雅维利完全不是一个出言谨慎、思想连贯的作者。
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试图“在人们的是非观上搅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要达到这一目的,马基雅维利就要诱导人们接受他那“可恶的、为了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学说”。在此,笔者要强调,不能同意施特劳斯教授的见解,而且还须表明,治学如此严谨的学者竟然相信人们所言,认为马基雅维利曾经传授“为了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学说”,实属不该。在美国,《君主论》与《论李维》发行最广的一个版本由勒讷(Max Lerner)编辑。在这部《君主论》译著的第18章里,我们可以见到这句口号算在了马基雅维利的账上。这位佛罗伦萨的国务秘书其实这样写道:“世人、尤其无人与之对簿公堂的君王,做事看重结果。”就笔者的理解看来,马基雅维利从来不曾在任何地方使用“可以不择手段”这个概念和术语作为其政治词汇。传言马基雅维利建立了为了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句话似乎由耶酥会一些成员后来所创)这种学说,追根索源在于马基雅维利在几段话语里举例为一些残酷、暴烈的行为“开脱”,认为产生这些行为是有益的结果。但是,做出这样的“开脱”,必然是站在人的层次上,站在这种不尽完善的存在层次上而为之的;在主和自己的良心面前,却很难说这些是道德上正义的行为。马基雅维利不曾传授强权即公理,不曾传授历史的功绩可以洗刷所有罪恶,亦不曾传授 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世界历史就是世界审判)。就算马利坦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评论鞭挞入里、毫不留情,实难让施特劳斯斥责是“善心”多过“思想”,这位宗教作家恰恰在这么一个他所称的从宗教和道德方面为罪恶行经“辩护”的问题上,也已经认识到(而讲求治学严谨,则大家不能不认识到),马基雅维利与“马基雅维利式的思想”区别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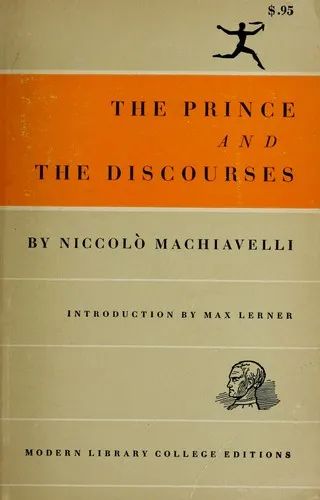
勒讷 编,(美国纽约)现代图书馆出版社,1940年
现在想来,只有一个篇章可能支持马基雅维利“不择一切不道德的手段”这种见解。这就是《君主论》最后一章。在这里,马基雅维利引用了李维的一段名言:“必要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除了诉诸武力没有其它出路时,战争亦成为神圣的。”在这一章里,马基雅维利还断言,主赐福给争取意大利摆脱外国占领的事业。施特劳斯利用这一章大做文章。在他看来,这一章的确让人们找到了理解《君主论》整体意义的线索。对于为何第26章的含义是学者们争议很大的问题,学者们常常指出,这一章最少体现出马基雅维利的写作风格,既不慎重也不现实,只是一篇饱含激情的言辞。即便如此,笔者并非意在表明,第26章导致的分歧已经得到解决。
笔者似乎有理由认为,马基雅维利倡导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以政治作为志业的人们应当恪守的“责任伦理”;这种伦理对应于“信念伦理”。十分清楚,若有可能,马基雅维利不会不同意韦伯的如下观点:在现实世界,从政者行事依从所谓良心而不权衡由此产生的后果,实属不明事理之至。支持“责任伦理”或者说“承担后果”伦理最为明显的,要算《君主论》第十七章和《罗马史论》第三章,第3页。在他那严峻的目光里,政治常常不是在善、恶之间作个选择的事情,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事情。用维吉尔(Virgil)的狄多(Dido,维吉尔作品中出现的北非迦太基女王)的话来说,政治是棘手的事物(res dura)。《君主论》第十七章里引用过这句话。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与邪恶不可能不纠缠在一起。邪恶分为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残暴可以用在“好的用途”(假如我们可以把“好”这个词与残酷联系在一起),也可以用在“坏的用途”。
但在马基雅维利眼里,邪恶就是邪恶,残暴就是残暴,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不是用教会的“辩护”辞令遮蔽得了的。我们不禁会认为,马基雅维利果敢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参与神秘莫测和充满矛盾的政治,身上有着永久不衰的魅力,个中秘密就在于此吧。参与政治似乎就会要求好人在承担政治责任时弄脏双手,即使像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那样避免使用残酷的手段的人,也难保清白。好人避免采用因政治需要使然而必须使用的残酷手段,却不能阻止不怎么好的人给民众造成惨烈灾难。现在看来,人是一类可怜的、面临很多岔道的动物。人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一方面是尽自己所能,达到既有卓越的道德意识又有人的尊严的境界,另一方面是避免滥用暴力和兽行。这些马基雅维利似乎在很多地方都有提及。
▲ 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1498—1522)
《论李维》里的那一个篇章与索德里尼有关。他在梅迪奇家族密谋反叛面前好心地不采取行动应付,最后自己连同马基雅维利让梅迪奇家族推翻。这个事件的“后果”是索德里尼倾注全力维护的共和国政体招致毁灭。由于担心招致心狠手毒的暴君恶名,索德里尼没有采取行动阻止阴谋分子的行动。索德里尼“开明而善良”,但他判断政治行动不看它们产生的“后果”。
综上所述,笔者可以表明,那些斥责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道德“分开”而且宣称“政治有独立的道德标准”的人们,未免言之过分。在马基雅维利眼里,政治与道德并非两条永不相交的并行线。政治家们为善乃因为有可能为善,即便他们不得不弃善从恶,他们的恶行最终也会在绝对的道德标准基础上受到审判。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
就割裂与主流政治思想传统的联系而言,马基雅维利所负的责任大过所有其它人……。
这位佛罗伦萨人的思想引致了现代政治思想的革命性转变,尤其那些最终导致“当代专制统治”(施特劳斯显然指我们当代的极权统治)的思想转变。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对施特劳斯提到的这些新的动态应“负有部分责任”,倒有一定道理,因为有他著作里的一些章节和概念为证;但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像施特劳斯所说的那样有意且全面背离基督教政治思想传统,则不太令人信服。
首先,我们得面对如下的事实:马基雅维利留下的学说里有很多传统的思想内容。从他的著述里,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传统政治思想学说一般都会关注的论题,以及对探讨基督教政治理论至关重要的一些概念。可以列举出的这些论题和概念应该会包括:人性的恒定性,起伏式的历史发展观(丝毫不含启蒙思想运动的发展观),混合政体乃最可行的政体形式(没有“君权”至上的极权思想),献身共同的善事业高于谋取私利(不是利益原则),法制可取,以立法的形式实行专政更能有效维护共和政体,信奉一种社会性宗教对维护国家秩序至关重要,由国家创建者担当立法者对建立法律制度并让它保持活力十分关键,应当尝试用习常词语阐明适用于所有政体、为维护国家生存和稳定所必需的条件。凡此种种,写有传统政治思想各种概念、论题的这份清单还可以继续延伸。马基雅维利至少已经部分地表明,自己在政治思想上面属于传统派而不是革命派,而且继承的是柏拉图(尤其写作《法义》时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乌斯(参见《论李维》,第2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圣托马斯·阿奎纳的思想。
笔者并非想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里没有否定传统思想的成分。显然,这些东西是有的,如今人们不解(当然是合理的意见分歧)的是,这些东西与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传统部分相比有多大的分量。马基雅维利在自己的著述里不止一次表示,需要制定出一条“新的道路”,而且在《君主论》和《论李维》里,马基雅维利深信,以前的作者们忽略或者未能充分考虑la verita effettuale delle cose[事物的实效真理]。马基雅维利在他使用一些传统概念时已经赋予了新的含义。例如,施特劳斯让人们不能不相信,“公共利益”(common good)这个词与这位佛罗伦萨国务秘书的前辈们的用法相比,含义已大为不同,马基雅维利作了很大改动。马基雅维利在自己的著述里对有些广为人知的情况,尤其涉及自然法的问题闭口不提。最后,马基雅维利的著述里还出现了一些新论题和论点,其中马基雅维利思想里的“命运”(fortuna)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对民众显著的偏爱倾向,特别值得一提。施特劳斯十分正确地特别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关于民众的一些观点里包含着激进本质。这位佛罗伦萨的国务秘书表明,他支持古罗马共和国的平民反对贵族的事业,而且蔑视他那个时代的上流阶级,斥责他们占有地产而于共同的善无所贡献,是寄生者(参见《论李维》,第1章,页55的刻薄议论)。在《论李维》第一章、第58页(这一章的标题是“民众的人之恒情与智略优于君王”),马基雅维利坦率宣称,他提出的见解“受到所有作家的责难”。对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学说的新奇特点,一位同时代的大人物奎恰迪尼(Guicciardini)有着透彻的理解。他在《对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的思考》(Considerazioni intorno ai Discorsi del Machiavelli)里,大肆抨击马基雅维利赞扬民众的议论。
毫无疑问,阅读马基雅维利的著述我们可以发现,马基雅维利认为民众身上有着巨大的政治力量,通过巧妙的心理操控可以唤醒并有可能利用这种力量。在马基雅维利的一封颇为有名的书信里,马基雅维利公开表示,他看待政治事务更爱利用“民众……这面镜子,它的好处是让我得以在事件完成之时评判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在事件发生之时评判采用的手段”。虽然马基雅维利与民主思想有联系,但施特劳斯表示“更愿意相信”马基雅维利是首开民主思想先河的哲学家,就言之过分了。我们似乎不能肯定地断言,马基雅维利认为民众意见是评判事物的最终标准的源泉,或者说除此之外我们“不能求诸其它的东西”,结果让道德既失去客观的基础又失去上天的劝诫。
马基雅维利指出,时代的精神风貌必然决定主政者的施政方向,而站在批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基雅维利却又毫不迟疑地给一些民族、时代──包括自己生活的时代贴上腐败的标签。马基雅维利由衷赞叹的只是那些受宗教启示、由有德行的少数精英引领的民众。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不曾断言,民众是正义和邪恶的可靠评判者。尽管马基雅维利曾多次说过,“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他接受边沁的如下观点:最为一般的民众意见决定社会生活的标准及其文化的质量。如同古时的学人那样,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思想中含有人类学的成分,也就是说他的学说含有为身份类型不同的人划分等级的成分。或者读者不妨可以认为,他的学说是涉及少数精英人物的学说。
不同身份类型的人组成了一个阶梯,顶端是宗教创建人,往下依次是共和国或者王国缔造者、军队首领以及“各类”文人,各个等级的人享有“与其等级相称”的荣誉。相反,在阶梯的更低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声名不好和可恶、讨厌的人。他们破坏宗教、扰乱国家、敌视美德、学问及人类一切高尚的艺术。这些人“亵渎神灵、凶残暴戾、愚昧无知、百无一用、懒惰成性、阴险狡诈”(《论李维》第1章,页10)。看来,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保留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精英”人类学,尽管让人们很伤脑筋,马基雅维利没有提到哲学家应该在阶梯上占据什么位置。他们可能被归入“文人”一类,这样他们就从最高身份的人占据的地方降了下来。马基雅维利经常表示,他喜欢积极的生活胜过沉思的生活(至少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他“有文艺复兴的思想”),哲学家地位下降就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要证明马基雅维利对哲学和哲学家“怀有敌意”,也不容易。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有待解决,才能够确定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思想的联系,从而才能评价他在政治思想史上作为一个据认为是主要的革命者所发挥的作用。简单地说,这个问题涉及到,在现代的支配思想发展史上、在基于破坏性的形而上支配欲(libido dominandi)的各种思想体系的发展史上,马基雅维利究竟是个关键人物抑或头号关键人物。在最后几页里,施特劳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如下结论:
马基雅维利的著述里清楚出现了对哲学新的[或者说现代的] 认识(将哲学视作征服自己生存环境的工具的认识)。施特劳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值得引述:
这种新的意义上的好社会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因为,头脑足够聪明的人可以靠在法律上使用必要的强制,转化最腐败的人民和最为腐败的事物。既然人并非天生要实现固定不变的目标,他们似乎变化无常……既然人并非天生向善,或者人能变得善良和保持善良仅仅因为人们受到强制和文明的教化,或者说,既然人变得善良有违人的天性,那么,这暗含的意思是,人身上的人性寓居在自然之外的阿基米德点上。自由的“唯心主义”哲学补充并衬托“唯物主义”哲学,尽管其前提正是对后者的否定。人的头脑可以转变政治的事情,进而很快想到可以转变所有事情,或者可以征服自然。陶醉于自己能力,首先让几个大人物、然后让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心荡神怡。然而,在大反叛或解放可以开始之前,必须打破支配几乎所有人头脑的旧思想模式和秩序……新的哲学一开始就是由如下希望培育出来的:近乎确信或者确信未来的征服或征服未来……发现那个任何给定事物之外的阿基米德点,或者说发现一种彻底的自由,无异于向人们许诺可以征服所有给定的东西……。
施特劳斯认为,这种反哲学的征服哲学事实上已经征服了“几乎整个人类”。这种悲哀的结论是否正确,笔者在此不作详细讨论,只想表明,这种在政治思想史上可以很方便地标明为“救世政治学”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力明显地在消退,西方尤其如此,这是笔者愿意看到的。现在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更为充分地反映人的生存处境种种局限的观念取代政治思想体系中那些过分重视不切实际的美好理想的观念,要么恢复柏拉图定义的哲学生活。这两种可能性我们都不应当忽视。但是,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是,施特劳斯把马基雅维利与现代的征服思想观念联系起来,还把他说成是应对这种思想观念“负主要责任的人”或者肇兴者,这是否正确?在这方面,笔者至多只能部分同意施特劳斯的观点。马基雅维利身上确有形而上的自命不凡,但更多见的是谦卑,至少是对人不能探究清楚、也无力改变的现存秩序的顺从和无能为力。
马基雅维利的自命不凡最生动地表现在他对命运的思考中。本文不能充分展开马基雅维利思想里的这个特点。只是需要说明,尽管在马基雅维利的许多著述中都可见到对命运的议论,终归到底并没有阐述得足够清楚,遑论形成概念。马基雅维利身上的一丝丝“征服欲望”见于他在多处地方表示的这样的希望:一个有相当“头脑”的人的确能够控制不可控制的事物,或者说(尽管这有点说不通)可以设法创立一门命运科学。马基雅维利有预测不可预测事物的欲望,这在他于1513年1月写给刚刚遭到放逐的佛罗伦萨邦主索德里尼的一封信里看得很清楚,里面有一值得注意的段落(施特劳斯没有提到这个段落,尽管与他的反驳论据有关):
可以肯定,能够通晓世事百态进而顺应的人,总会有好运道,或者总能保护自己不致招徕祸患。智者总能驾御日月星辰,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这样的智者无处可觅,其一、人都有短视的毛病;其二、人都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本能,因此人的命运便不同了,人让她掌握和控制了。
需要对这段话和马基雅维利提到“征服”或者“掌握”命运的言论(最突出的是《君主论》第25章)谈三点看法。首先,马基雅维利著述里显然有改变人的生存环境的愿望、诱惑和冲动;这样的冲动以最激进的形式表现在这样的话语里:“智者能驾御星辰,主宰自己的命运。”其次,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便在最早大为赞颂征服命运时,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马基雅维利身上一直都有的悲观意识,他认为人力不能改变命运。从《君主论》第25章,我们至多能够知道,用智谋掌握命运,我们成功的机会只有一半。

在写给索德里尼的信中,马基雅维利直率说,人(可能是所有人)不能支配自己的本能,因此就不能总从大胆转向谨慎,不能按时代的要求由崇尚战争艺术转向崇尚和平艺术。“自然”让人形成不同的“性格”和“想象力”,就像它让人有不同的面孔。马基雅维利对征服命运的前景表示悲观,这在萨索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作的颇有学识的揭示里得到明证。在马基雅维利的后期著述、尤其在他为卡斯图奇奥(Castruccio Castricani)写的传记(有些人怀疑好像是马基雅维利写给自己的)中,这种悲观意识更加明显。卡斯图奇奥胸怀大志,一心要建功立业,但“命运施展了力量”,告诫世人,因为有她而非人们的谋划,才会有人的伟大,进而让卡斯图奇奥英年早逝。马基雅维利把卡斯图奇奥当作命运主宰人的“极好例子”。临终之前,卡斯图奇奥坦言:那位睠顾所有人的命运之神没有让我有个好的头脑去理解她,也没有给我足够时间去战胜她。
不过,就是在给卡斯图奇奥写的传记中,马基雅维利也没有劝告人们不抱希望或者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尽管这位雇佣军人最终没能成功,而且上天好像不愿听他无用的哀号。马基雅维利发现,卡斯图奇奥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尽管命运最终战胜了美德,但政治活动即便在主对万事万物的最终计划中不足挂齿,仍然只有杰出人物可以为之。

▲ 卡斯图奇奥(Castruccio Castricani,1281—1328)
最后,我们不妨认为,就算那些有关征服命运的最为“乐观的”篇章表达的就是马基雅维利真实的、中心的意思,在评价马基雅维利与现代征服思想的关系时,我们仍得考虑这样一个事实,马基雅维利已经意识到人的活动有其客观限度。
智者明白如何控制对财富和荣誉的胃口,蠢人不清楚如何钳制欲望的翅膀。(《论李维》,第2章、页27结尾处)
而且,总有人──即便最擅长战胜逆境的人──在活动时受到限制的情况,这是必然所为。马基雅维利认为,必然正是人的生存环境中不可改变的东西。施特劳斯自己也指出,马基雅维利从来不曾想象人可以逃脱必然的束缚﹕这样的束缚是人超越于其它生物之上而必须要有的一个条件。在马基雅维利的世界里,不会有“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从马基雅维利不愿意承认有这样的飞跃,我们可以看到他与马克思(或恩格斯)有多大的距离。马基雅维利认为,人这样的生灵一直受一套由万事万物组成、不能改变也不可征服的秩序束缚:这套秩序不是人创造的,而且要人服从。总的来说,我们宁愿赞同阿克顿的意见。在为伯尔德编辑的《君主论》写的著名导言中他说道:
在研究了更晚近的政治思想之后,人们一定会减轻加在马基雅维利身上的骂名包袱。
不过,借用瑞多尔斐的一句话,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像有的骑手那样兴冲冲跳起,想跨上马鞍,不料掉到马的另一边”(瑞多尔斐,《马基雅维利生平》,前揭,第254页)。笔者无意向马基雅维利致歉。尽管笔者坦率表示不能同意施特劳斯的一些结论,而且尤其反对有些结论,但马基雅维利思想有引起争议的一面,一直是不争的事实,施特劳斯做出很多十分有益的工作,对于研究者认识这个问题启发很大。总的说来,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靠得住的引路人。无论他有意还是无意,在他的著述中有很多极端的事例和奇谈怪论,他的同时代人奎恰迪尼在其所写的《对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的思考》里面也提到这一点。人们还会说,在马基雅维利的著述中,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防止他人、防止后世预测天下会大乱的救世思想家们曲解。索·贝娄(Saul Bellow)笔下的主人公赫佐格(Herzog)给尼采提的建议对马基雅维利肯定也合适:哲人若要保持与人类的联系,就应该预先把自己的体系颠倒过来,看看人们接受这个体系之后几十年里的情形又如何。
笔者认为,马基雅维利实际上不像施特劳斯说的那样,建立起了一个“体系”,但施特劳斯强调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哲学”部分是正确的,因为研究者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部分。他们把马基雅维利看作一个本质上说来头脑实际的宣传家,想到自己已经失业就转而思考政治问题,一心想的是靠自己的著述可以为自己找回工作。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多少有其系统性,但笔者根本没有找到。马基雅维利在政治理论方面的大的建树,既不在于概念运用准确,也不在于他提出来的涉及该学科的主要问题丰富而又全面。的确,我们有时还很难准确回答,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建树究竟在哪里。不错,马基雅维利的写作风格享有声誉,但仅此一点还是不够。或许马基雅维利的建树蕴涵在我们以为十分精辟的分析中──对权力带来的责任和道德提出的要求之间的冲突所做的分析。如果说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有一个主线的话,那么,分析权力责任和道德要求的冲突就是主线。这样的分析可能更能全面地揭示马基雅维利不搞伪善、不搞自我欺骗的决心。这种学者的诚实是真正的政治理论家不同于思想家的标志。
依笔者之见,尽管施特劳斯所研究颇有见地,克罗齐的“谜”仍然没有解开。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意图这个“谜”,何以在好几百个头脑敏锐的学者和其它人士做了很多辛苦研究后还没有解开,很难说得清楚,原因也可能只是,马基雅维利自己没有把意思说明白。或者说,还需要更辛勤的分析才能解开这个“谜”;或者说,马基雅维利喜欢把意思弄得含混不清。后一种看法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没有道理,可以考虑一下他在1521年5月17日写给贵查第尼的信里说的话:很久以来,我说的不是心里想的,心里想的不是说出口的。有时要是确实碰巧说了真话,我也要把真话藏在大堆假话中,让别人难得找出来。
我们不妨可以认定,这便是马基雅维利著述的“恶魔般的”或者说淘气似的特质,但在这里,我们又有一个反证的事实:我们并没有无懈可击的理由相信,在这一段话里马基雅维利说了心里所想的。
实际上,笔者倒十分愿意不相信马基雅维利在这里说的就是真心话,宁愿支持莫斯卡的观点:马基雅维利“作为一个作家是所有时代可以见到的最诚实的人”。也许,正是因为做人老实倔强、做学问诚实可靠,马基雅维利才得以认清人类生活异常复杂并昭示于他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里天生就有刻薄挖苦的特点,故而他对世上屡见不鲜的欺诈、幻灭、谎言以及人们彼此交往过程中的以假作真、半真半假等等十分敏感。马基雅维利不愿意表示,在一个问题完全没有解决办法的时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思想里的主要“矛盾”可能(尽管不能确定)是内心冲突的结果,而诚实又让他不得掩饰这些矛盾,或者用模棱两可的方法“解决”问题。
例如,马基雅维利在著述里没有能很好地把政治“现实”与基督信仰协调一致,这兴许是因为,他看出双方的冲突客观上不能克服。我们可以不赞同这个结论,但我们不能不对这位引来了这种冲突的思想家的老实和诚实表示羡慕。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略如下可能性: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前后矛盾,与其怪他有意掩盖自己真实的革命意图,或者不能清楚地表达思想,或者他喜爱玩弄模糊,不如说他真的没有能力就一些重大的道德和政治理论问题作出决断。
笔者愿意在结尾时对评价马基雅维利使用肯定的言辞,这无疑会为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思想史上的高大形象再增添一笔。可以肯定,所有评价马基雅维利的人无论彼此之间意见多么分歧,都会赞同巴特非尔德在评述施特劳斯的这部著作时说的一句话:
很清楚,无论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开创性意义或者本身的意义多大,它都为历史增添了分量,因为它激发了别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