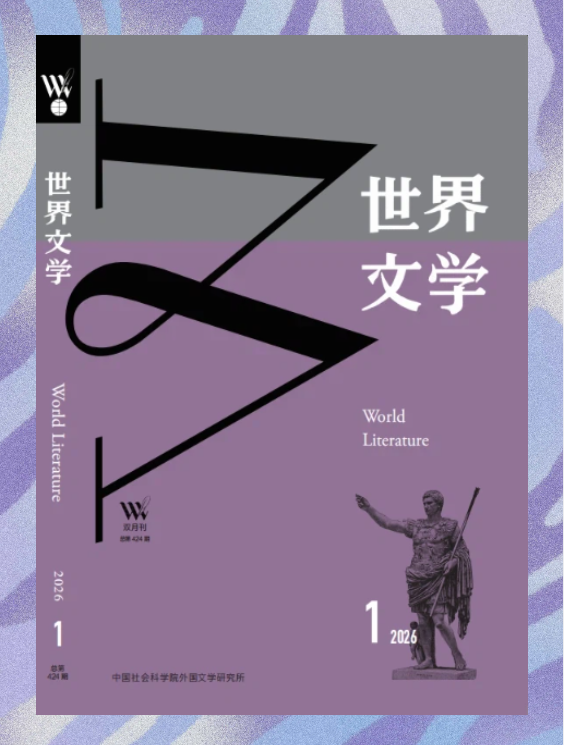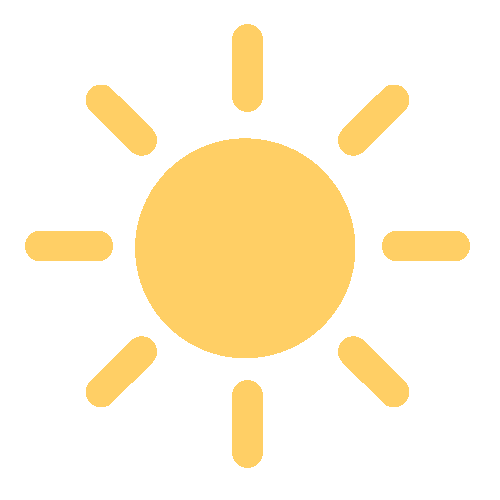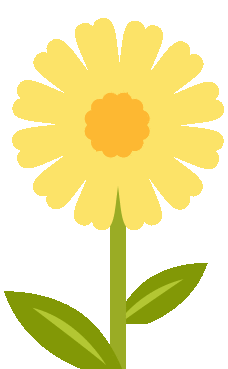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赫•哈比拉【尼日利亚】:来到拉各斯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我转过身,打量自己所在的位置。我站在铁路网中间;右手边是熙熙攘攘的亚巴市场,铁轨就从市场前面经过。这就是拉各斯。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欣喜若狂、不知所措,只觉得又累又饿,还有点担心。

赫隆·哈比拉作 刘海英译
如果你生活在尼日利亚北部,前往拉各斯【拉各斯是尼日利亚西南角的港口城市。如作者下文所说,他居住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贡贝市。从贡贝前往拉各斯是斜跨整个国家的长途旅行】就是一项史诗级壮举,甚至足以称得上一场成人礼。十四岁时,我觉得朋友里头就只有我不曾到过拉各斯。他们常常带回关于这座大城市的奇妙故事:数不尽的桥梁,不可思议的高楼,迷宫般的道路——道路交织缠绕,消失在彼此之间,就像是等待司机解开的谜题。我最好的朋友去过一趟拉各斯,回来后走路就开始大摇大摆,斜着右肩,这姿势一直保持到现在。他带着一种曾经笑对危难的过来人的神气,谈到自己碰到拉各斯危险游民“地区男孩”时的惊心遭遇。他说,“地区男孩”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命令你交出钱包,那架势倒像是他们赶时间而被你耽误了似的。他说到街头斗殴——倒卖巴士票的黄牛互相殴打,有时居然在大街上撕破对方的衣服。真是可怕的地方。这倒让我们更想去亲眼看看,亲身体验一下。小偷会在就擒的现场被公开施以火刑:橡胶轮胎挂在他们的脖子上,还有一点儿助火的煤油、一根火柴,人群在欢呼,催着赶紧开场。那个地方的野蛮超出了我这个小镇居民的想象。还有那些女人,啊,拉各斯的女人,说到这儿,我的朋友不再多言,看样子,他不仅见过那些女人,还跟她们打过交道。我的朋友带回许多东西,其中有一样是约鲁巴语的绰号:阿赖耶·巴巴,意思是“世界之王”。
那一年,我为瓦解来自母亲的阻力,对她展开了攻势。如果母亲点头,父亲就会同意——事情总是这样。有一天,她终于答应了。我要去拉各斯了。那是一九八三年,正值暑假期间——就是我们所说的“长假”。
前往拉各斯有多种出行方式。如果你像我一样住在贡贝,那就得先坐汽车到乔斯或者到卡杜纳【贡贝是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城市,1996年成为新成立的贡贝州的首府。乔斯是尼日利亚中央区域高原州的首府。卡杜纳是尼日利亚中北部卡杜纳州的首府】,从那里你再乘坐“豪华”巴士——其实压根儿谈不上“豪华”——这样,你就踏上了一生中最鲁莽、最危险的旅程。有传言说,司机们靠服兴奋剂来保持头脑清醒——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在夜间出行。道路又黑又窄,坑坑洼洼,不用说,没有什么时速限制。至于抵达日期,那是说不准的。估摸通常需要两到三天,但实际上,这趟行程是急不来的。因为巴士可能会中途抛锚,停在某个可怕的树林中,距离最近的城镇或村庄还很远,而司机则以寻找修车工为借口溜之大吉,不见踪影,留下倒霉的售票员来对付怒气冲冲的乘客。据说,在巴士修好之前,乘客们要等上好几天,像难民一样露宿道旁。较有经验的乘客都熟悉这种路数,干脆就抓过自己的旅行袋,拦下任何一辆他们能够拦住的过路车,请求司机把他们带往最近的城镇,然后再搭上另一辆巴士前往目的地。即便巴士没有抛锚,也还有武装劫匪需要对付——匪徒在马路中间堆起巨石,潜伏在黑暗中,等着轿车或巴士撞上石头,之后就能从从容容地抢劫受伤或发蒙的乘客。
也许正因为如此,母亲才决定让我乘火车,不让我坐汽车。我准备去看望我的姐姐露丝。回想往事,令我惊讶的是,母亲竟然允许十四岁的我独自乘火车去拉各斯。如今我看着自己十四岁的儿子,心想,我绝不可能让他独自进行一场那样的旅行。但是,母亲辩解道,那时的世界,也就是尼日利亚,远比现在安全得多。一九八三年,整个国家就像沉睡已久的巨人,开始慢慢地苏醒过来。虽然凶杀案和公路抢劫案确实发生过,但十分罕见——你或你的邻居不会遇到这样的事,它们只存在于令你惊骇的新闻报道之中。那些日子里,武装劫匪在拉各斯的海滩和其他城市的足球场被公开枪决——这种场面对跃跃欲试的匪徒来说确实具有威慑作用。
而且,我虽然年纪轻轻,但旅行经验相当丰富——尽管我还未曾去过像拉各斯那么远的地方。许多妈妈喜欢假期里送孩子去探亲,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也许她那时正想通过我来实现内心深处的旅行愿望——如今她早已为人妻为人母,永远无法达成这样的心愿了。每次我回到家,她都喜欢听我讲述假期见闻,什么细节都不想错过,包括她的兄弟姐妹过得如何,他们的孩子表现得怎么样。十二岁之前,我就已去过扎里亚、包奇【扎里亚是尼日利亚卡杜纳州的城市,包奇是包奇州的首府】、乔斯和卡杜纳。我对旅行上了瘾,一到假期,就收拾好背包,准备再次启程,去见识新的地方;旅行就像拼凑未知世界的地图——每次我回来,一块新的拼图就会落到应有的位置。这个幅员辽阔、多元化的国家就这样慢慢地展现在我稚嫩的想象之中。原本我只是在历史和地理书中读到过这些想象中的地方,如今,它们却变成了真实的所在:我可以凭借亲身经历所赋予的权威来谈论乔斯高原的温和天气——这与尼日利亚其他地方都不相同;我亲眼见过、亲手摸过扎里亚和包奇的著名城墙,也曾亲身走过卡杜纳的街道。我如同被关在封闭房间里的人,此时找到了窗户,正在把它慢慢地打开:一点点展露在眼前的是外界难以言喻的美景。


我从包奇火车站出发前往拉各斯。以西结叔叔开着崭新的大众汽车送我到包奇;他总是这样匆忙,把我留在巨大候车楼的门口,便挥手告别了。此刻,我独自一人站在长长的混凝土月台上,开往拉各斯的火车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到站。我的身边放着圆筒状行李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我到了车站,当真要开始旅行了,内心的兴奋不由变成了恐惧。一大原因是我以前从未坐过火车。
我和家人一起去过贡贝火车站两次,为我的哥哥送行——他去拉各斯看望我的姐姐。火车站是个神奇的地方,巨穴般的候车大厅里挤满了乘客及其家人,他们身后拖着行李,排着长队购买车票。他们一会儿看看门上的大钟,一会儿看看那个似乎相距遥远的唯一售票窗口,脸上写满了焦虑和兴奋。大厅外面,唯一的站台上堆着小山高的箱子、旅行皮包和帆布背包,监视行李的主人此时已经买到票了,目光正盯着狭长的铁轨——轨道在泛光灯下闪着幽光,逐渐消失在漆黑潮湿的夜色里。终于,驶向车站的火车远远地发出刺耳的鸣笛声,伴随着金属车轮在轨道上撞出的叮当声。我们可以看到火车的灯光照在月台灯光的外围,等待解除警报的信号。当长长的火车机车和车厢最终驶入车站时,眼前的景象——闪闪发光的金属车身,戴着鸭舌帽的司机,透过窗户向外张望并挥手的乘客——在候车乘客中间引起一阵骚动,就像一阵风掠过草野一样;火车气闸喷出的气浪把纸屑和灰尘送至夜空。旅客们涌向正在打开的车厢门,一拥而上,逼退了准备下车的乘客。这好比是一场疯狂的进食:男男女女如食人鱼一般对准猎物狠狠咬去。一名男子将一个袋子从一扇敞开的车窗扔了进去,紧跟着钻了过去。一个气喘吁吁的胖男人抱起一个惊恐万分的孩子,越过堵在门口的乘客头顶,将他抛到接应者手中,然后也跟着挤了进去,身后竟还拽着一个小孩。一个女人后半身卡在狭窄的车窗处,不断踢脚扭身,直到一只手猛推她的臀部,她才掉入车厢里,后头的人便跟着她,拼命伸展、扭曲着身体,以适应车窗铁栏之间的距离。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所有人都上了车,站台变得出奇地安静、冷清,只剩下一小群送行的家庭成员,正在向他们的儿子、女儿、叔叔、阿姨和朋友挥手告别——他们即将前往洛科贾、卡杜纳、埃努古、伊巴丹、哈科特港【洛科贾、埃努古、伊巴丹、哈科特港分别是尼日利亚科吉州、埃努古州、奥约州、河流州的首府】和拉各斯。
包奇车站的安静令我大为惊讶。在我到达后的两三个小时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乘客出现在月台上;他们三五成群地站着,神色淡然地注视着火车即将到来的方向。一个大块头女人睡在面对铁轨的长椅上,双腿摊开在自己面前。下午六点钟左右,火车终于进站,停留不到三十分钟就开走了。我诧异地看到车厢里挤满了人,不知为什么,我以为车厢会像站台一样空呢。所有席位似乎都有人占着。一些席位分上下铺——铁皮长凳焊接在地板上,表面铺着泡沫塑料垫。我提着行李包站立在那里,火车加速时就抓着栏杆。没想到车厢里竟然这么昏暗。一团团黑影紧挨着坐在一起,孩子们正在不安地哭泣;有些人把碗放在大腿上,伸手从碗里抓东西吃。车厢里散发着食物和身体的味道,这一切的底调是尿味,正从车厢两端敞开的厕所里飘荡过来。没有空调,唯一的清新空气来自车厢侧壁上那些间隔分布的窄长窗户。慢慢地,我的眼睛适应了阴暗的环境,我注意到有一个年轻姑娘坐在自己对面;她指了指身旁的一小块儿地方。我坐下来,微笑着对她表示感谢。
后来我们攀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露丝。
“哦,我的姐姐也叫露丝。我正要去看望她。”我说。
“去哪里?”
“拉各斯。”
“我也要去拉各斯。”
她和我差不多大,也许大一岁。她讲着一口流利的豪萨语,带一点儿约鲁巴口音。她是约拉联邦政府女子学院【约拉联邦政府女子学院创建于1979年,位于尼日利亚阿达马瓦州的约拉城】的学生,正准备回家度假。我猜,她一定多次乘坐过这趟火车——有个高个子女人突然蹲在车厢中间,开始往塑料碗里哗哗地小便,她却很淡定地别过脸去。而我却没法这么做。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直到那个女人完事后,平静地把碗里的东西泼出窗外。我回过头,发现露丝正在看我,她被我的表情逗乐了。她告诫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去厕所。
“为什么?”
“厕所不干净。等我们到洛科贾时再去。还有几个钟头就到了。”


五个多小时后,我们才抵达洛科贾。火车在午夜后驶入车站。车厢里昏暗而安静,外头的车站却亮如白昼:庞大的车站主楼里灯火通明,楼前的一根柱子上挂着扬声器,播放着西非轻快的歌曲,孩子们在灯光下相互追逐。洛科贾是尼日利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来自东南部和西南部的铁路穿过杰巴的尼日尔大桥【杰巴是位于尼日利亚西部夸拉州的城市,杰巴的尼日尔大桥建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汇合,形成一个动静脉交叠般复杂的交通网络。在殖民时期以及火车尚未停运的年代,这里是大多数货运的集散中心——来自北方的花生、牛羊和谷物,以及来自南方的棕榈油、山药和木薯先通过铁路运到这里,再通过公路运往尼日利亚的偏远地区。火车昼夜不停地进出车站,小贩们伺机等在站台上和铁轨旁,他们把货物放在托盘和桌板上或者放在大碗和盆子里,把脑袋挤进黑暗的车厢,胆大者甚至跳入车厢,向昏昏欲睡和疲惫不堪的乘客们大声叫卖手里的物品。
露丝站起来,指着她的包说:“我很快就回来。”
我站在车厢门口,看着她从上下火车的人群中挤出去,消失在夜色中。大约三十分钟后,她才回来,我当时正变得焦躁不安,不知道她是否在往回走。她看起来十分清爽,好像刚刚洗过澡;身上换了一件新衬衫,旧衬衫叠好了放在手中的塑料袋里。她从约拉出发,沿途还有多次临时停车,我估算着,她在火车上一定已经待了二十四个小时。现在该我下车,轮到她照看行李了。
我买了一瓶可乐和一条面包,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死死盯着火车,生怕被它落下。吃完后,我四处找厕所,找不到,就决定到灌木丛中去。火车就像巨型虫子似的趴在黑夜里,有些看起来黑乎乎的,好像是被废弃的样子,有些里面有灯光在闪动,并且有乘客在上下车。老式蒸汽机车与柴油机车并列而立。一些出故障的发动机正在接受维修。印度籍和本地工程师带着工具箱有条不紊地四处察看,用手电筒和电灯探照发动机内部,拿金属工具叩击着金属部件。光亮之外,我看到人们若无其事地蹲在火车不远处便溺,有的蹲在铁轨上,有的在车厢后面,还有的在大树底下。有男人,有女人,也有孩子。现在我能闻到臭味了。我一面低头小心地看路,免得踩到别人的排泄物,一面加入他们的行列。


火车从洛科贾向南变轨;铁轨朝另一个方向可以延伸到卡诺【尼日利亚北部卡诺州首府】,距离拉各斯七百英里远。其余的行程只给我留下模糊的印象;黑夜变成白天,白天又变成黑夜;火车又一次在某个村庄停靠时,便有灯光照入车厢,小贩们走进来,用托盘装着炸豆饼、烤花生、蒸豆布丁、香蕉和芒果,用奇怪的语言叫卖。在纷至沓来、如万花筒般的图像和事件中,只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火车在杰巴横穿尼日尔河,离拉各斯大约还有三百零六英里。我们都冲到窗户前,看着下面长长的黑暗河道。尼日尔河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令我无比兴奋:跨越尼日尔河意味着踏入北方人常说的“南方”。实际上,我来到尼日利亚南部,就好像踏入另一片国土,因为就连泥土散发出来的气息都与我家乡那种有时干燥、有时芳香的热带草原气息迥然不同。从杰巴开始,树木越来越高,树林越来越密,空气的湿度越来越重,腐烂植物的气味也越来越浓。我意识到这个国家何其广阔、何其多样,自己来到了离家乡何其遥远的地方。
露丝疲惫地朝我一笑。我们已经挨着坐了两个夜晚——火车常常毫无理由、毫无征兆地停下来,然后小贩就魔幻般地从黑暗中涌现,工程师用工具敲打火车的金属引擎;有的时候,火车会静静地停留几个小时,乘客可以下车去伸展四肢,也有的时候,火车只停下几分钟,就又开动了。自从上车以后,我只能断断续续地打个盹儿;感觉关节疼痛,双脚似乎肿了起来。我看着地板和扶手上的污垢越来越厚。又有乘客爬了上来,所有空地都塞满了行李;每个人的脸庞都无比倦怠,满是污垢。我们忍受着别人身上的难闻气味,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也满身臭气。露丝告诉我,沿着过道往前走,走过很多节车厢之后,就是头等车厢;她的语气充满了遐想。那里有床,有淋浴,有空调,餐厅很干净,供应可口的食物和饮料。三等车厢的餐饮区已经变成了睡眠区——早就遭到了餐饮商的遗弃——乘客只能在站台购买小贩手里的食物。
“伊巴丹到了。”露丝大声说道。她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地坐着,不睡觉的时候就眺望窗外。但此刻她神采飞扬,站起来朝车站看了又看。“明早前我们就能到达拉各斯。”伊巴丹距离拉各斯只有一百二十六英里,但火车在伊巴丹一直停到第二天早上,可能正在接受进一步检修。有人说,这是因为谁都不想在晚上进入拉各斯。夜晚太危险了,据说会有暴徒行凶抢劫,他们用刀尖指着你,抢走你的行李袋。露丝出去了,回来时拿着一瓶可乐,并把可乐递给了我。我摇摇头,她却坚持把可乐塞到我手里。
“你最期待在拉各斯看到什么?”她问道。
我毫不犹豫地说道:“大海。”
我从未见过大海。我无法想象一片水域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向上升起,与地平线上的天空相接。临近清晨,在机车的烟雾里,伴着响亮的汽笛声,火车缓缓驶出车站。露丝拿出一把发梳,梳理她那一排排玉米垄式的小辫儿,还系上一条彩色头巾。她用瓶子里的水浸湿一块手帕,轻轻地擦拭脸和颈部。梳洗完,她看起来清新、漂亮,我更加意识到自己有多邋遢。三天没有换过一件外衣,一条内裤。我感觉自己嘴巴很臭,甚至不敢开口讲话。快了,我告诉自己,很快就到了。露丝已经教过我如何去亚巴的马英军营。火车抵达亚巴时,我就可以跳下车,没必要一直坐到终点站——伊多火车总站。
“火车减速时你就跳下去。”
看到我有点迟疑,她笑着说:“这很容易。你的行李又不多。”
确实很容易。看到别人从我旁边擦身而过,跳下火车,我顿时壮大了胆子。火车到达亚巴市场旁边的十字路口。它完全停了下来,等待十字路口的大门打开。我抓过行李包,挥手告别露丝,在车轮开始向前滚动的刹那跳了下去。我站在铁轨旁的碎石路上,朝开动的火车挥手。露丝把头伸出车窗外,招手回应我,那条红黄相间的头巾在风中飘动着。
我转过身,打量自己所在的位置。我站在铁路网中间;右手边是熙熙攘攘的亚巴市场,铁轨就从市场前面经过。这就是拉各斯。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欣喜若狂、不知所措,只觉得又累又饿,还有点担心。我知道,等我休息好以后,兴奋的感觉就会回来了。我深吸一口气,想试试在这里能否嗅到大海的气息。我打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把我送到马英军营,在亚巴理工学院的门口把我放下来。

赫隆·哈比拉(1967—),尼日利亚当代重要小说家、诗人和评论者,非洲后殖民文学中“新声音”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生涯起步于新闻业,曾长期从事编辑和记者工作,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关注社会现实的底色。代表作有《等待天使》《测量时间》《水上油》。作品获得多种奖项,包括2001年的凯恩文学奖。《来到拉各斯》(Coming to Lagos)选自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2021年出版的散文集《关于我们国家的那些事儿——著名尼日利亚作家谈他们所熟知的家园、身份和文化》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6年第1期,策划及责任编辑:叶丽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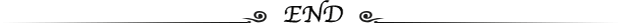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