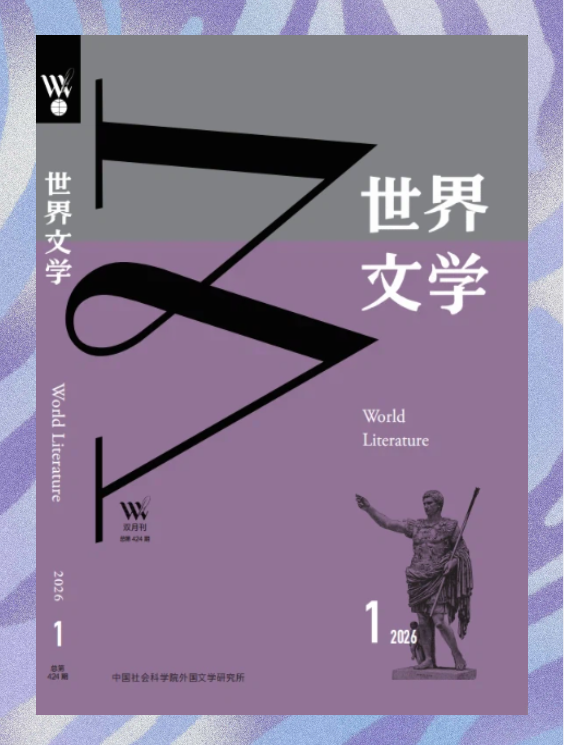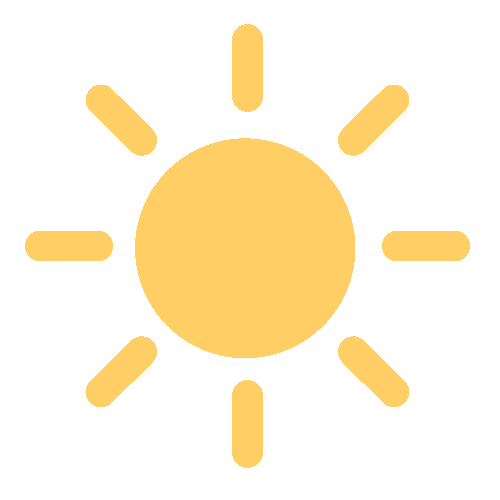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肯•布谷尔【塞内加尔】:言语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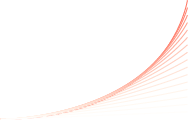
五十年过去,一种心照不宣的缄默,掐灭了所有抱怨的苗头。于是,舌头缩回上颚,嘴唇被活生生缝上,如同一座座熄灭的火山。一些人因无力远行留了下来;另一些人,则由家人——儿子、丈夫——代替自己离开。

言语之主
肯·布谷尔作 陈贝译
母亲是在一个降水丰沛的雨季过后买下那片土地的。那是一个让整个花生盆地【位于塞内加尔中西部地区,以种植花生闻名】和周边的许多农民都心生欢喜的雨季。母亲并不种地,她做布料生意,是个印染匠,染出漂亮的蜡染布和靛蓝布,雨季时赊账卖给农民。待到一年一度的花生收购季,那些挥汗劳作了一整个雨季的人们一拿到钱——簇新的钞票在手中沙沙作响——便会自己登门还账,或是托人送来。遇上个把迟迟不还的,母亲便让我去催账——我负责替她记账。就这样,在一个风调雨顺的年头之后,母亲决定买下那片地,就在一片浓密的芒果林旁边,在通往姆布尔辛的路上。那片地很大,足有千余平米。买来后,母亲就把它租给了种木薯的农户。她买地是为了投资,但心中一直渴望拥有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尽管从未说出口过。她当时还住在自己母亲的房子里。那房子并非祖传,而是外祖母当年用自己的血汗钱买下一大块地后盖起来的,直到今天还很坚固。母亲买的那片地以土质肥沃闻名,种下的木薯长得快,块茎结实,味道甘甜,深受人们喜爱。然而,地前屋后、田间垄上,总是传着一些流言。说什么了?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但那个传言说:母亲地里那棵猴面包树的树干里封存着言语之主的灵魂。正因如此,那片地向来无人居住,母亲也始终未能在那里建成什么,哪怕只是间茅屋,或是座带廊台的三间小房。听那些比我年长的人说,在塞内加尔的某些地方,尤其是在锡内【位于今塞内加尔萨卢姆河三角洲的北岸地区】一带,有一种巨大的猴面包树,它中空的树干能够安放言语之主的遗体。那些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背倚大树竖直放置,一具挨着一具。岁月流转,几十年过去,干尸仍旧挺立。言语之主不似那些取代了言语的人,他们从不睡下,从不躺平,从不爬行,从不舔舐他人的靴履。言语之主始终站立,随时准备高举世人日益渴求的言语。它就在那儿,在母亲地里那棵猴面包树的树干里,完好如初。母亲曾与我一同生活过几年,却从未谈起过那片土地,那片属于她的土地。小时候,我常和小伙伴一起,跑到母亲的土地旁,去捡拾芒果树下的落果。邻居们用带刺的灌木把果树团团围挡,可那些高大的芒果树却向我们发出邀请。然而,尖利的荆棘挡在那里,压制了我们想要施展各种绝招钻过去的热忱。重要的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拨开一根根枝条,穿过带刺的灌木丛。尖刺划破了我们的手臂与指尖,却没有人愿意就此作罢。夜晚,一颗颗芒果从枝头掉落到阴凉的土地上,就这样水灵灵地呈现在眼前和嘴边,只消望上一眼,我们便立刻行动起来,哪怕有路人大声斥责,哪怕另一头传来邻居的叫骂——他们挥舞着拳头,骂我们是偷芒果的贼。我们回嘴道:才不是呢,我们只是捡起了掉落的果子。这些芒果树,又没有长在谁家的地里,它们长在路边,自是属于所有人。然而,近旁的几户人家却将芒果树视为私产,为了编扎围篱,他们先是砍光了自家枣树的枝条,又不辞辛苦地跑去附近的灌木丛里搜寻带刺的枝杈。尖利的刺钩划破了他们的手掌和手臂,他们浑然不觉,因为心中燃烧着阻止孩子们偷走落果的执念。孩子们不抱怨荆棘,他们更年轻,也更灵活,胸中也燃烧着兴奋的热忱,最终总能轻轻松松钻过刺篱。不得不说,路边那些高大的芒果树,落下的果实也非同寻常:果肉香甜,丰沛的汁水常常顺着孩子们草草擦洗的脸颊淌下。天一亮,孩子们便从床上一跃而起,在父母——尤其是在母亲——的命令下,拿起院子里扔着的萨塔拉【原文为塞内加尔土著语言沃洛夫语,指传统的水罐或盛水器具】,往手心倒上一捧水,抹一把睡眼惺忪的脸庞。在昨夜的梦里,那些熟透的芒果在沁凉的夜色中翩然落下,色泽充盈了整个梦境。那个世界的清


晨,到处都弥漫着猴面包树清冽而略带沉郁的花香,母亲土地上的那棵猴面包树——我们在家从不提及的那棵树——也开出了美丽的花朵。花影远远就能望见,可从母亲的屋子里,却看不到分毫。记忆中,我们始终闭口不提那片土地,即便提及,也是一带而过。“下个雨季会有人用这块地”,总是这样寥寥几句,让我至今都怀疑,母亲是否真的提起过它。关于那片土地的故事,我全是从流言中听来的,而那时的我并不在意这些故事。母亲从未和我说过什么。虽然我帮她记账,可地价多少,我一无所知。传言中,那是笔不小的数目,但她未曾说过一字一句。另有一棵猴面包树,生长在道路的交汇处,就在萨巴拉家门前,不属于任何人。村里的几条要道在那里交汇。一条是从通向巴奥尔【位于塞内加尔中部】和卡约尔【位于塞内加尔河与佛得角之间】边境的大道上分出的岔路,去往更偏远的人家。另一条从集市而来。集市是维系生计的命脉,是交易往来的枢纽,是采买生活必需品的地方。那里有商住一体的楼房【指底层商铺与上层住宅合一的建筑】,还有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的牲畜圈地——他们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便在此地经营。因此,这条路很重要。还有一条路,从母亲的那片地延伸而来,但被坎特家侵占到路面的房屋挡住了一点。于是,从清晨到日暮,萨巴拉家门前的那棵猴面包树下总有人影往来交错。附近的人家纷纷拿出草席,搬出小木凳。路人停下脚步,甚至席地坐下,顺手拔掉身边的草芽——尽管有行人与牲畜终日踏过,这浅褐色土地上仍有坚韧的草芽冒出地面。过了这个岔路口,右转可以斜穿过母亲的土地;左转则能沿着墓园,去往牧场那边。即便在萨巴拉家门前的那棵猴面包树下,在那岔路口流传的诸多谣言里,母亲的那片地也极少提及,更不用说地里的猴面包树了。它玄奥而神圣,强大而神秘,是言语的守护者,是真理的象征。而今,真理如同木棉树的叶子,随风远扬,碎散飘零,残挂在枝头;而今,一种心照不宣的缄默弥漫开来。母亲土地上的猴面包树,树干中封存着言语。关于母亲土地上的那棵猴面包树里封存着言语的故事,我也是不久前才偶然得知的——某个族人无意间引发的一个偶然事件。此人瞒着兄弟姐妹,打算把土地卖给一家电信公司,这家公司当时正在全国拓展业务,计划在这个偏远村庄架一座信号发射塔。大家都说,村子受到了危机的影响。可事实上,早在那场用作借口的危机出现之前,村子自火车停运那一刻起就奄奄一息了。它失去了灵魂——那个曾经作为交通枢纽的灵魂:锡内、萨卢姆、卡约尔和巴奥尔等多个地区都在此地交汇。而火车,是它的肺脏,它的生命所在。当年,正是这一通向东方的战略位置,以及周边的花生盆地,才吸引了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来到这偏远内陆经营花生贸易,售卖工业品、农具与生活必需品。火车停运了,这个地方也随之衰落。周边的村庄,甚至更远的地方亦然。如今,放眼望去,整个国家都被火车停运波及。火车曾承载着生命、交流、交融、情感、历史与血脉,还承载了无数回忆!而今,没有火车了。大家一句话都没说,很沮丧,却没有反抗。年轻人启程奔向未知的远方;有些人举家迁往别处,前往公路沿线的新兴聚居地。公路蜿蜒曲折,遍布全国,路面布满坑洼与巨大的裂缝,小巴、客车、拼车式出租车、马匹和马车在上面左摇右晃,颠来倒去。道路的中央,横陈着公牛、母牛、狗和飞鸟的尸体——被那些喷吐浓烟、哐当作响、坟墓般的车辆撞倒,碾压,夺去了性命。这些车也撞死过人。只有在外闯出了一番名堂的离乡者才会在多年后重返故土。一些人买下了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留下的房屋——他们已随着国家历史的变迁离开了。这个国家自诩独立了,并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五十年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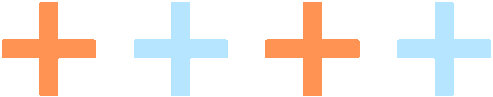


一种心照不宣的缄默,掐灭了所有抱怨的苗头。于是,舌头【在法语中,“langue”一词既指舌头,也指话语,此处为双关用法】缩回上颚,嘴唇被活生生缝上,如同一座座熄灭的火山。一些人因无力远行留了下来;另一些人,则由家人——儿子、丈夫——代替自己离开。留下来的人每天要在岔路口聚上好几次,就在萨巴拉家门前的猴面包树下。大家默契地把这里当成聚会的首选之地,借此排遣命运带来的钝痛。怯懦或是背叛将他们征服,击倒,吓垮了。而母亲的那片土地,始终在那里,把言语封存在自己的脏腑中。它目睹了太多的事件,见证过那些现已消失的七月十四日【塞内加尔曾是法国殖民地,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庆典,也见证了一九六○年四月【1960年4月4日,塞内加尔正式宣布独立】的那场独立宣告。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纷纷离开,迁往工业中心和首都。经年干旱,人畜凋零。铁路衰落,火车停运。大规模的流亡。风卷尘沙,恰似那些未能兑现的诺言。民主,哦吼!【沃洛夫语里的常用感叹词】母亲的那片土地上,差点就装了信号发射塔。那个打算卖地的族人,本以为势在必得,却被一个“潜伏者”【此处原文为sous-marin,该词在法语中既指潜水艇,也指秘密获取机密信息的人】搅了局。“潜伏者”是个受到危机影响的村民,料准公司一定会开出诱人的价格买地,便利用了流言阻挠。那家公司靠着把越来越多的手机卖到人们耳边的成功经营,聚敛了不少钱财。可人们又生出其他烦忧,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大家不敢说真话,也不敢对自己坦诚,而是依附于那些陈词滥调,将之当作避难所。他们扼杀了自己的话语,使之沦为简单的拟声词,变成生活的碎片与残渣,陷入一片地狱般的嘈杂之中。人人都想拥有一部手机,也都如愿以偿。没有人愿意再过没有手机的生活——司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小贩、乞丐、摩托车手,总之,所有人。于是,那个同样急于出售自己土地的“潜伏者”告诉那家公司,他们看中的姆布尔辛路上的那块地有问题。他借用流言的说法,说那块地没人能住。因为地里的猴面包树中藏有一个秘密:一个足以让所有计划落空,甚至会给定居此地的人带来杀身之祸的秘密。于是,公司放弃了母亲的土地。因为,如果真在那里架上信号发射塔,谁知道会发生什么?猴面包树势必遭到无情砍伐,那言语将何去何从?猴面包树又会怎样?那些砍树的人又会遭遇什么?必须从外乡找个人来砍这棵猴面包树。这个村子里,没人会碰它。谁敢呢?那被封存的言语怎么办?“必须释放它。我们需要听见,需要倾听言语。那被扼杀的言语,必须从猴面包树中释放出来,再次履行它的使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几个胆大的人在岔路口自言自语道。当可能将言语释放的消息传出后,那里顿时挤满了人。那个传言证实革命正在进行。一个处于缄默中的民族——那心照不宣的缄默、懦夫的缄默、被操纵者的缄默,迷失者的缄默——总算要终结这种状态了。这个民族曾躲在奇闻和流言里寻求慰藉,为那心照不宣的缄默寻找理由。在萨巴拉家门前的猴面包树下,大家说已经受够了各色流言。或许,等那个传言说出大家真正渴望听到的话后,便会永远噤声。人群沸腾了。他们雀跃,握手,欢呼,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喝止:“的确,正是那个传言自身印证了这些流言蜚语。然而,要将言语从猴面包树的树干中释放出来,并非易事。必须请教那些知晓门道的人,循着章法来办。言语已然被封存太久: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打从一艘船在西海岸靠岸那天起就被封存了。如今,年轻人纷纷往外跑,为的是不让村庄彻底隐没。老一辈人大多已离去,带着释然的叹息,也带着对未来的忧虑,交还了灵魂。现在该怎么办?圣人也已离去,临终前劝诫大家要保持耐心,明辨方向。可眼下,村子里还有谁能主持这仪式?必须要举行仪式。”在这必要性之上,又添上了一丝绝望——悄然滋生于聚集在这个重要路口的人们心头。他们双手掩


住嘴巴,回到各自家中。早在我母亲买下那片土地之前,他们紧闭的嘴巴便已噤声,而那片土地自始至终在那里。母亲为何会买下那片立着一棵孤独的猴面包树的土地?她是否知道,那棵猴面包树里封存着一个秘密?在众多屋宅之间,她为何偏偏选中那片唯有一棵光秃秃的猴面包树伫立在入口处的土地?那片地的后方,有几户人家。右侧只有几棵高大的芒果树,树下竖着带刺的围篱。左侧是一条沙路,因为紧挨墓园而鲜少有人踏足。人们终归忌惮死亡。近在咫尺的墓园提醒着他们死亡的存在。而墓园旁的那棵猴面包树,以及关于它的那些变化无常的流言,更让人心神不宁。母亲为何会买下那片紧邻墓园的土地?那天早晨,住在同村的姐姐说,当初那个搅黄了项目的“潜伏者”曾诋毁过母亲的土地。那片地分明很好,土壤肥沃、地势也佳(尽管我不太明白,它夹在难以接近的、高大的芒果树和墓园之间,究竟好在哪里?或许是因为它朝向太阳吧!)。姐姐还说,需要为猴面包树举行的那个仪式,其实简单得很。消息经流言散播,人们再次聚集在萨巴拉家门前那棵猴面包树下。流言说:那个女人的长女通晓仪式。消息不胫而走,愈演愈烈。人群默契而激动地向姐姐家涌去。姐姐泰然坐在庭院中央的椅子上,嘴里叼着根牙签,好像正等着他们的到来。那么,该怎么释放言语?姐姐目视前方,答道:“要砍倒猴面包树,得先买来新鲜的红肉。”众人屏住了呼吸。“我会把红肉放在树下。”众人松了口气。“等到那肉彻底腐烂,化为灰烬的时候,就可以砍树了——如果非砍不可的话。”
“可我们并不想砍掉那棵猴面包树。”
“我们只是想释放言语。”
“难道不砍树,就无法释放言语吗?”
人们回到路口,彼此交换着眼神。
那棵猴面包树不能砍。
不能砍树,不能砍一棵猴面包树。
一棵猴面包树会自己倒下。
时代已然改变。如今,猴面包树在心照不宣的缄默中被砍倒。是的,但那些被砍倒的猴面包树,树干里没有封存言语之主。它们封存的,不过是隐约的怨恨。为了这个事业——一个正义的事业——难道不该砍掉那棵猴面包树吗?如今最紧要的,是释放言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然,就只能为自己缝制紧身衣,遏制已经出现的神经官能症——既要避免陷入无处不在的操控,也要防止坠入那已然开始编织罗网的洗脑灌输。大家约定明日再见。我们总说“以后”,反复思量后再做决定,可到头来,一切都不过化成喉底心间的几声嘟囔而已。
非要等到为时已晚,才肯行动吗?
“我们现在就要言语。”有人高声喊道。其他人惊慌失措,纷纷侧目。
“看看你们如今的模样!你们要求收回的言语从未离开过。人家答应归还,你们却开始发抖、犹豫不前!我明天就去找她女儿,她可以完成那个仪式。”
第二天凌晨三点左右,姐姐突然感到不适。她口吐白沫,死在了椅子上。流言像瀑布般传开,说这是个凶兆。
就这样,言语依旧封存在母亲土地上的猴面包树里。
“释放言语并非易事,早就有人这样说过,但言语会自行解脱,无需砍倒那棵猴面包树。”流言大胆地低语道。
不能砍倒一棵封存言语的猴面包树。
不能砍树,不能砍一棵猴面包树。
一棵猴面包树会自己倒下。
言语即将爆发,势不可挡。因为我们——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曾懦弱地目睹了它的窒息和沉默。没有什么能够抑制言语。即便在缄默之中,言语仍在。举行仪式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那棵猴面包树。
流言最后一次传播开来。
母亲的土地依旧在那里。入口处,那棵猴面包树依旧挺立。一棵结出果实却无人采摘的猴面包树。但它的四周,没有了带刺的围篱。
END
作者简介
肯·布谷尔(1947—),塞内加尔法语作家。原名玛里埃图·姆巴耶·比莱·奥马,青年时曾赴比利时留学,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工作,现居贝宁。1982年,她以在比利时留学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首部小说《疯狂的猴面包树》,迄今已出版《灰烬与余火》《里万或沙之径》《往返》等长篇小说11部,荣获黑非洲文学大奖、法兰西学士院法语文学大奖等重要奖项。布谷尔的作品多以探讨后殖民时期非洲社会的复杂性为主题,已译为多种语言。《言语之主》是布谷尔创作的一部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整个故事以土地传说为隐喻,揭示后殖民时代塞内加尔社会的精神困境。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6年第1期,策划及责任编辑:赵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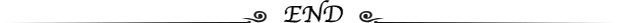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