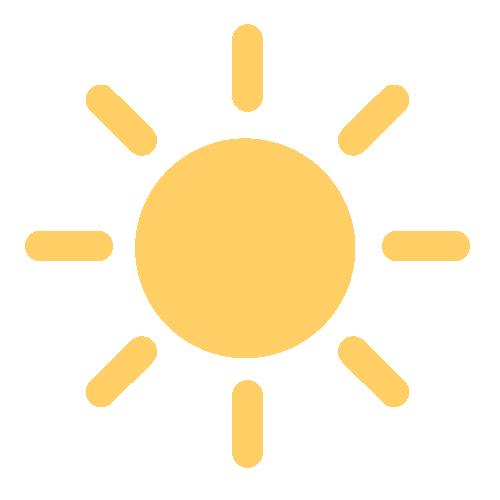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丹•利帕托夫【俄罗斯】:青年人的科学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加莫夫想着他刚才的话,他没有听见他说的那些关于学术胜利、科学发现、光明未来,以及物理学是年轻人的科学、青年人的科学之类的话语。“为青年人的科学,为青年人的科学干杯……”所有人立刻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举起了酒杯,人们拍着手,碰杯的声音不绝于耳,相互转述着刚刚听到的祝酒词。人们喝干了杯中酒,刀叉开始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
丹尼斯·利帕托夫作 侯丹译
未婚妻等了很久他也没有回来,就不再等他了。这也没什么可惊讶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总共只写了四封信,只在很少的几个节日抽出时间到摩尔曼斯克打过几次电话。当他从别人那里,从第三方口中得知他的未婚妻已经结婚的消息时,已经是两个月之后了。所有人都害怕让他知道这件事,向他隐瞒着这个消息,就像隐瞒一个直系亲属的死讯那样。他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感到惊讶,甚至都没有问一句她嫁给了谁。他只是叹了口气,耸了耸肩膀。还能怎样,他说,她是个女人,和所有女人都一个样。很多人都认定他以十分冷漠的态度接受了这个消息,也就是说,他并不爱她。所以,人们(尤其是女人们)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们开始把他看作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事实上,他第二天就去上班了(尽管按照当地的风俗他完全可以因为悲伤休息两天,而且完全不会因此受到惩罚。既不会被记录为旷工,也不会因此被扣掉奖金)。他去上班了,无论在吸烟室还是在餐厅吃饭时,他没都和任何人提起所发生的事情。在餐厅里他偷偷地往糖水煮的酸果蔓中掺入了一点儿酒精。当有人小心翼翼地向他表示同情,说你的奥莉娅是个母狗的时候,他只是叹一口气、耸耸肩膀。他说:能有什么办法呢,她只是个女人,和所有女人一样渴望爱和抚慰,不是遥不可及的爱,而是实实在在的肉体上的爱,这样才能有家庭和孩子,如果因为这一点而怪罪她就如同怪罪盐是咸的一样。他甚至没有开始酗酒。他继续工作,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在屏幕前坐到很晚,反复查看仪表上的读数,试图执行自己设计的某个试验程序(第十条延迟线给出的结果总是不一样,信号不断被刷新,每次都不一样)。每逢休息日,他就抱着一线希望仔细翻检自己研究过的资料,希望能够发现一些被遗忘的手稿,或是一些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资料。渐渐地,他写论文的材料就搜集够了,这是些真实的、质量很高的材料,除了在这里,在实验场里,任何别的地方都无法得到这样的材料。总之,他未来的工作变得完全明朗起来。
他委屈得几乎要哭出来了。再过一个月他就能回去了,不会更久,不会了,而她却不肯再等。甚至她都没有亲自给他发一封电报。最可笑的就是他知道这件事的方式。切聂齐耶夫有一位堂兄,上大学时他也顺便认识了切聂齐耶夫的这位堂兄。切聂齐耶夫来实验场之前,他的堂兄和他一年最多也只见一次面,这次却无缘无故地寄来了一封信。当然,信是寄给切聂齐耶夫的。这位堂兄在信中说完最新的首都八卦之后,顺便写上了这么一句,他说,请转告应该知道这件事的人,奥莉娅结婚了。真是应该谢谢她,居然以这样的方式让他得知这个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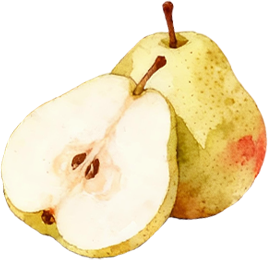


现在他甚至不知道要怎样出现在莫斯科,要在那儿做些什么。而出发的日子正在坚定不移地逐渐靠近,还剩下一个星期,一共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整个部门的同事都来为他饯行:他们一起聚餐,喝酒,说着祝酒词,祝愿他一切顺利。他的学术导师伏谢沃洛德·安德烈伊奇已经微有醉意,他在大家欢乐的喧哗中对他低声说道:“您是个聪明的、有才华的小伙子,我对您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请允许我再次向您重复一遍我的忠告:换个姓氏吧。带着现在的姓氏您会遇到不少困难。哪怕用您母亲的姓氏也行。这么说吧,要知道加莫夫这个姓氏在学术界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在这个姓氏背后蕴含的东西太多了。您以这样的姓氏进入科学界,就像您以普希金的姓氏发表诗歌一样,即使作者真是姓这个姓氏,即使这些诗歌真的很有才华,也还是不会成功。人们会笑话他,他既不会被理解,也不会被接受。第二个问题是……”他的低语声几乎无法听清,干枯的双唇在不断地颤动,双眼意味深长却又十分平静地看着他,“您自己也明白,加莫夫【乔治·加莫夫,即格奥尔基·安东诺维奇·加莫夫(1904—1968),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后来移居美国】是个不能提及的人物,他从祖国逃跑了,或者像他们说的那样,是背叛,总之他的名字不可能再被提起……”他不再说话,走到了一旁,很快又恢复刚才那副醉醺醺的心不在焉的样子。人们立刻聚拢到他的身边,“伏谢沃洛德·安德烈伊奇,伏谢沃洛德·安德烈伊奇,举杯说几句吧,请您举杯说几句吧!”人们给他倒了一杯伏特加,用叉子扎上一些下酒菜递给他,有蘑菇、鱼、香肠(或者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把沙拉向他那边推了推……“安静,安静,要祝酒了,伏谢沃洛德·安德烈伊奇要提酒了……”他有些费劲儿地站了起来。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加莫夫想着他刚才的话,他没有听见他说的那些关于学术胜利、科学发现、光明未来,以及物理学是年轻人的科学、青年人的科学之类的话语。“为青年人的科学,为青年人的科学干杯……”所有人立刻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举起了酒杯,人们拍着手,碰杯的声音不绝于耳,相互转述着刚刚听到的祝酒词。人们喝干了杯中酒,刀叉开始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
伏谢沃洛德·安德烈伊奇坐了下来,目光忧郁地盯着自己的学生加莫夫,这是他的希望,他很清楚加莫夫不会听他的话,决不会改变姓氏……


加莫夫并不了解莫斯科。对他来说城市完全是另一码事:那是别人的地方,不是他的容身之地。他只想把自己锁在自己的小公寓里,关掉收音机和电视,把窗户用窗帘遮上,再捂住耳朵,这样就听不到闹纠纷的邻居们的抱怨声;电话线拔不拔下来都无所谓,因为没有人会给他打电话。咖啡、香烟、红酒……(似乎是卡戈尔酒),这是人们为他送行时让他带上路的,是送给他的礼物,他们还嘱咐他要在答辩之后拆开这些礼物,他们让他为那些还留在这里——实验场的人干杯。对他而言实验场已经不是这里,而是那里了。伏谢沃洛德·安德烈伊奇就是这么说的。他现在正喝着送给他的酒,瓶子里只剩下底部的一点点酒了。有几次他试着给过去的未婚妻打电话,但是话筒里传来的却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他胆怯地挂断了电话,然后长时间地听着窗外单调的、永无休止的汽车喇叭声。他的生活同样单调而枯燥,而且毫无出路、毫无意义,从这个层面来看用“无尽无休”这个形容词来评价他的生活也完全恰当。绝望的处境让他想起总督说的那句话:“毒药,给我毒药。”【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的著名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句子】有一次,仅仅只有一次,是她拿起了话筒,她的声音也让他感到陌生、不亲近,而且令人捉摸不透。他想要说点儿什么,他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用和过去一样的语气说了起来,但是她的回答很简略,他听见她说他们双方都有了另外的生活,什么都不可能改变了,而且也没必要改变。然后她挂断了电话。都结束了。
他很少上街。他出去只是为了买一些必需品。而现在即使缺少很多东西他也能凑合。最后一次上街是什么时候他已经记不得了。所以,他从大门里出来走了几步之后,突然惊讶地发现,原来又是冬天了。大楼又变成了灰蒙蒙的颜色,天空又变得模糊昏暗,脏兮兮的积雪又出现在了城市里,人行道上的树木又是光秃秃的模样,像患了病的可怜巴巴的乞丐一样,不过,我国并没有这样的乞丐。长了很多疤节的弯弯曲曲的黑色枝条让人感到不舒服。天气潮湿而善变,行人身上掉了毛的领子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死猫挂在衣服上;而鞋子,即便是新鞋也立刻变得肮脏而破旧,好像已经穿了十年之久。
他走到了商店。不知何故商店已经关门。他转过身,慢慢往家走去,一路上尽可能地躲开身边那些行色匆匆、面带忧郁的行人不友善地射向他的目光。突然人流中有人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回头。他在想,这不是在叫他,莫斯科有很多叫亚历山大的人。这时他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姓氏,身后还传来一阵急促的、就像害怕迟到一样的脚步声,脚步声逐渐靠近,变成了沉重的喘息声(唉,喘粗气,该戒烟了),这声音从他左肩的方向传了过来。加莫夫转过身来,他看见了一张典型的哈扎尔人的面孔。“唉,这就喘上了,该戒烟了。”陌生人说道,脸上挂着一丝歉疚的却又十分愉快的微笑,他看着加莫夫的眼睛说道,“总算找到你了。好了,走吧。”他步履坚定地向加莫夫家的大门口走去,加莫夫既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没能插进来一句话。


这个人看加莫夫的样子就像是看着一个老熟人,但是加莫夫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是谁。他搜寻着记忆,想要冲破眼前的黑暗。这个人脸上的轮廓让他觉得似曾相识,但还是不能确定他是谁。客人犹豫地站在那里。他看着加莫夫,就像人们对某个人久闻其名并且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完全走了样的想法)想象其模样(想象得跟真人完全不一样),而后终于见到了真人那样。他(客人)站在那里,站在大街上,首先伸出手去,抓住了加莫夫那只已经被遗忘的、毫无生气地垂在身边的手臂,加莫夫随即感觉到了陌生人手上的潮湿,握手的感觉就像完全把他罩住,再也不让他跑掉一样,他还闻到一丝甜甜的烟草味道。进屋之后,来客在圈椅里坐下,故作惊讶地问道:“怎么,难道不认识我了?切聂齐耶夫。”加莫夫立刻又看了看他,那样子就像踩到了一只刚才没有发现的已经发胀的死老鼠。“切聂齐耶夫。”客人又重复了一遍,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哦,对了,当然是他,好像有一个吊在线上的小钢球在他的脑袋里摇晃起来,他想起来了,切聂齐耶夫,就是那个写信说奥莉娅结婚了的人,是瓦夏的堂兄。很多记忆立刻各就各位了。他还有一些已经模糊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拍的是他们在大学时代的一些联欢会,在这些晚会上他们曾经短暂地碰过面,那些照片还拍了他们在宿舍里纵情狂欢和晚上出去做客的情景。瓦夏不大喜欢自己的堂兄,很多人都认为是瓦夏嫉妒自己的堂兄,但是瓦夏却反驳说,他的堂兄没什么可令人嫉妒的,他是个骗子、马屁精、冒名顶替者!为什么说是冒名顶替者?这时切聂齐耶夫正坐在那里四下张望,翘着二郎腿,一边弹着舌头一边打量着房间:壁纸有点脏了,有些地方已经掉了下来,露出下面非常朴素的蓝色墙壁,而且墙壁滑腻腻的,就像浴室里的墙壁一样;家具很简陋——一个已经掉漆的衣柜,一个塌陷的沙发,还有一把瘸腿的椅子。堆满书的写字台就像一个独立出去的共和国,高傲地、孤零零地立在另一边,它无法说出因为没有得到预期的宠爱以及被主人弃之不用而感到的伤心和委屈。地板上也堆着书。不知为何,地板上还放着一个小碟子,里面堆着小山一样的烟灰和烟头。切聂齐耶夫坐在圈椅里,他没有发觉他的脚碰到了小碟子而且还把它踢翻了。烟灰飘散在空气中,然后又慢慢地撒落在旁边堆放的书籍上面。“怎么这样,这算过的什么日子,”切聂齐耶夫晃着腿说,“哎呀,兄弟,你这是把自己给耽误了。这样可不行。”加莫夫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坐在地毯上还没完全清醒过来,他拿出一根香烟,抽了起来。他机械地将已经空了一半的揉皱的烟盒递给了切聂齐耶夫。切聂齐耶夫拒绝了,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普力马牌香烟。“这样可不行。”他一边寻找放在圈椅旁的公文包一边郑重地说道。
他不是无缘无故到这里来的,而是事出有因。但是,客人并没有急着说明自己到访的缘由,而是声音轻缓——就好像一边下山一边说话一样——空洞无味地聊了很长时间他们都认识的一些人的情况,加莫夫对这些人几乎都快忘了(“波尔,你能想到吗,他成了精神病院的护理员,安德烈耶夫和州委员的女儿结了婚,让科学见鬼去吧,沙什金夫妻俩离婚了”)。他还说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说很多人都很同情他——加莫夫。“顺便问一下,”客人自己打断了一下,“我弟弟在那边怎么样啊?没打电话吗?没写信吗?那可真奇怪,我还以为你们是朋友呢。好吧,不说这个了。”


他一刻不停地说着这些废话,不给主人留下哪怕一秒钟的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好把客人看个清楚。切聂齐耶夫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些东西:看我找到了什么,都是吃的——面包、干酪、香肠(已经切成了整齐的小圆片,它们似乎已经在包里等得不耐烦了)、干咸鱼脊肉,还有一瓶格鲁吉亚产的红葡萄酒。切聂齐耶夫很有气势地拔掉瓶塞,红色的天鹅绒一般的酒液满满地倒进了普通的多棱玻璃杯中。酒很不错。吃喝过后,他们看待彼此的眼神简单多了,不再那么缺乏信任、小心翼翼,人们通常都是这么看别人,尤其是长期没有来往之后再见面更是这样。切聂齐耶夫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而加莫夫则相反,仍然很拘谨,只是勉强用简短的话语回答一些问题。
“就是说,瓦夏没有给你写信,你什么也不知道?”切聂齐耶夫问道,他把自己的云斯顿牌香烟放在了桌子上,点着一根抽了起来。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圈椅里,抽着烟,看着加莫夫,“什么消息都没有吗?”
加莫夫摇摇头,也点了一支烟,在空气中挥舞着还在燃烧的火柴。
火柴熄灭后的烟雾像一条细蛇一样蜿蜒着向上盘旋,直冲到了他的眼睛里。窗外天色昏暗起来,汽车打开了车灯缓慢地行驶着,似乎它们已经因为白天的奔忙而累坏了。瓦夏的确没有写信,就好像断绝了来往一样,而且也没有打过电话。
“你明白吗,你没有获得成功让伏谢沃洛德·安德烈伊奇多么难过。你对他而言,怎么形容好呢……是他的希望,是他最后的爱情,就像少年普希金对茹科夫斯基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很多人都嫉妒你能得到这样的庇护……”切聂齐耶夫沉默下来,等着看他的话会产生怎样效果……“但是,他没有等到啊。”
一路上他都带着一丝厌恶的情绪尽力不去想这件事,想起这件事就和马上去见牙医的感觉一样。他想象着怎样通知加莫夫这个消息,他总是希望加莫夫已经从别的渠道知道了这件事,这样他就不用告诉他了……但是这个隐居者又能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呢?切聂齐耶夫皱着眉,撇着嘴,像吃了酸东西一样,这是因为他想到他不得不对一个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而且他也不感兴趣的人的死亡表示同情,而且恐怕他还难免要想出一些话来安慰别人、鼓励别人——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厌烦。“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在心里为自己辩解着,但还是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羞愧,因为这一点他对自己更加恼火。他对加莫夫说道:“人都是要死的,我的一个叔叔就在从前的某个时候死去了,就是瓦夏的父亲。”但是他不需要因为这件事来想出一些话语表示同情并且做出一脸苦相了:加莫夫甚至连头都没有转过来。他继续抽着烟,眼睛看着自己的正前方,双眼因为烟雾的刺激眯缝着。烟一直抽到了烟蒂,直到红宝石一般的火星烧到了手指他才回过神来,他用力按着烟蒂,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它按灭。从他的嘴里喷出了最后一缕灰蓝色的烟雾,随后一个简单的句子也像烟雾一样从他嘴里喷了出来:“什么时候?”仅此而已。


切聂齐耶夫非常失望,尽管他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不用做那些他不想做的事情了……准确的日期他记不得了。他对日期和所有不是很重要的数字都记得不牢。
“大概是一个月前下葬的。我以为,瓦夏已经告诉你了。”
“一个字也没说……”
“他就直接葬在那里,实验场里,甚至都没有送到摩尔曼斯克。这是他自己的愿望。人一死就全完了,就再也没这个人了,就像从来没有过一样,他的全部领地就只有两米宽三米长而已,而他本打算要作为一个胜利者、成功者继续生活下去的,他还想来找你……而你呢?”切聂齐耶夫突然停下来,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似乎在思忖要不要说出来。不能心肠太软,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叹了口气,说道:“你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加莫夫皱了皱眉,说道,那只是别人的说法,只有致力于某件事的时候才能谈到失败,而他就像是把自己囚禁起来一样,哪儿也不去,面对的只有墙壁、墙壁、墙壁!如果说有过失败,那就是说他有能力去工作。否则伏谢沃洛德就会把他赶走,而雇用一个更有才能的人。但是在这个领域需要的不是去工作,而是去战斗,而他却不具有这样的力量。你看,我现在喝着酒,而他连酒都喝不到了,就这么死了。也许,我也很快就要死了。不过对他来说早就无所谓了。
切聂齐耶夫点了点头,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加莫夫,似乎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他用亲昵的、故意拉长的语调问:“你是怎么回事呢,萨沙,你不听他的吗?要知道他可是个精于世故的人,他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得罪的。”
加莫夫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浑身发抖,勉强克制着自己,双手紧紧地攥着拳头,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他大叫着让切聂齐耶夫滚蛋、滚蛋、滚蛋,所有见鬼骂娘的粗话都说了出来,他让切聂齐耶夫不要过问他的事,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要求过什么,从来没有……
“行了,别发火了,”切聂齐耶夫安慰他,“现在已经太迟了,你已经不可能再向别人证明自己了,什么也不会改变了。我们还是干一杯,纪念一下那个老酒鬼伏谢沃洛德。”
切聂齐耶夫再次倒了满满两杯酒。加莫夫喝酒的时候有一半都洒了出来,因为他的双手不停地颤抖,喉咙里发出呜呜咽咽的哭声,他的胸口因为难以承受的悲伤和沉重的孤独感所带来的痛苦已经撕裂开来。他是那么孤单,就像实验场的那个坟墓一样。


切聂齐耶夫要走了,他还是没有说出来访的目的。加莫夫忙乱起来,提出要去送送他。虽然切聂齐耶夫不让他送,但是,他现在不能够、完全不能够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公寓里。无可逃避的痛苦从公寓的所有缝隙、所有角落里探出头来,四处张望,甚至从剥落的壁纸下面、瘸腿椅子底下,以及零乱地摆着残羹冷炙的餐桌上钻了出来。总之,房间里它的身影无处不在。它直视着他。痛苦发出单调的鸣响,就像牙疼一样,似乎永远不会过去。它冷酷无情地提醒着加莫夫,生活之花尚未开放就凋零了,未来只有没有尽头的空虚岁月,或者根本就是一无所有;要是他在那个时候,在那个遥远的七月,在那条浑浊的小河里呛死就好了,那条小河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倒下来的树干,那是他第一次到乡下过假期——对了,要谢谢那个叔叔救了他(他叫什么名字……马特维,米赫伊……已经记不得了)。生活已经结束了——这个想法一点点地清晰起来,但是加莫夫还不想承认这一点,对生活他只是短暂地瞥了一眼就立刻转过头去了,虽然这个事实已经不言自明,他仍旧装作自己一无所知的样子。他很认真地倾听切聂齐耶夫说话,回答问题,进行争论,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虽然他一个字也没听懂。突然一个念头在他脑袋里炸开了,要知道伏谢沃洛德已经死了,怎么会这样……怎么就死了……就这么死了,死了。“人们还叫他去杜布纳,叫他去萨罗夫,叫他去泽列诺戈尔斯克,现在哪儿也不叫他去了,谁也不需要他了……姓什么又有什么关系,而奥莉娅,那个母狗,对,她就是条母狗。算了,我已经不爱她了,我现在当一阵子装卸工,当一阵子更夫勉强度日,就是这样。这烟不错,谢谢,我自己来,火柴放哪儿了……”然后他们又喝起了酒,一直喝呀喝,喝得脑袋嗡嗡作响,他已经忘了自己的痛苦,忘了那个愚蠢的想法,但是那个想法和他的痛苦并没有忘记他,它们像两个可怜的沾亲带故的老太婆一样相互紧挨着待在角落里大睁着眼睛看着他,就像是看着她们总也看不够的亲孙子一样。后来切聂齐耶夫突然站起身来,他打算走了:我该走了,兄弟,该走了。你怎么能就这样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呢?和这些东西待在一起?站在街上他们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他还是要一个人往家走,切聂齐耶夫消失不见的时刻就要到来,要把他一个人永远地留下来,这似乎是他生活中最可怕的时刻。恐惧让他不再说话(因为在说话的时候,时间向那个可怕的时刻流逝得更快),他还愚蠢地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公交车已经没有了,那样切聂齐耶夫就毫无办法,只能回来和他一起在他的房子里过夜。事实上,周围的确一片漆黑,也许,已经很晚了。潮湿而温暖的风吹在脸上感觉就像是三月的天气,而他们正处于莫斯科郊外十一月的夜晚之中,脚下是湿滑的水洼、令人作呕的积水,还有正在融化的冰块。黑暗中偶尔能看见汽车两只发亮的眼睛,听见汽车发动机发出的响亮而疲惫的轰鸣声。切聂齐耶夫在钻进出租车之前对他说,明天或者后天他还会再来,嘱咐他不要任性、不要气馁。他握了握他的手,就消失了。好吧,就这样吧,希望你一切顺利……而生活已经毁掉了。


他往家走去。可恶的十一月的晚风像散发着臭气的破布一样直扑到他的脸上。那些所谓的正派人全都瞧不起他,而只有这个切聂齐耶夫还算得上够朋友。瓦夏一封信也没写,扎赫列宾也是一样,都来莫斯科两个星期了还没有露面。
忽然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刺痛了加莫夫的心,他犹豫不决地在敞开的电梯门前停下了脚步,似乎他突然想起了什么。电梯门吱吱呀呀地关上了。加莫夫走到小平台上,那里挂着住户们的信箱。手冻僵了,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才把钥匙插进锁孔里。信箱打开了。里面有一封信。他拆开信,立刻就认出了瓦夏·切聂齐耶夫的笔迹。“萨沙,伏谢沃洛德·安德烈伊奇去世了……”
…………
丹尼斯·利帕托夫(Денис Липатов,1978—),俄罗斯诗人、小说家,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市。2001年毕业于下诺夫哥罗德国立技术大学工程物理化学系。在研究机构从事化学研究工作。擅长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创作。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3年第2期,责任编辑:孔霞蔚。上文截取了小说前两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可购入纸刊继续阅读。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