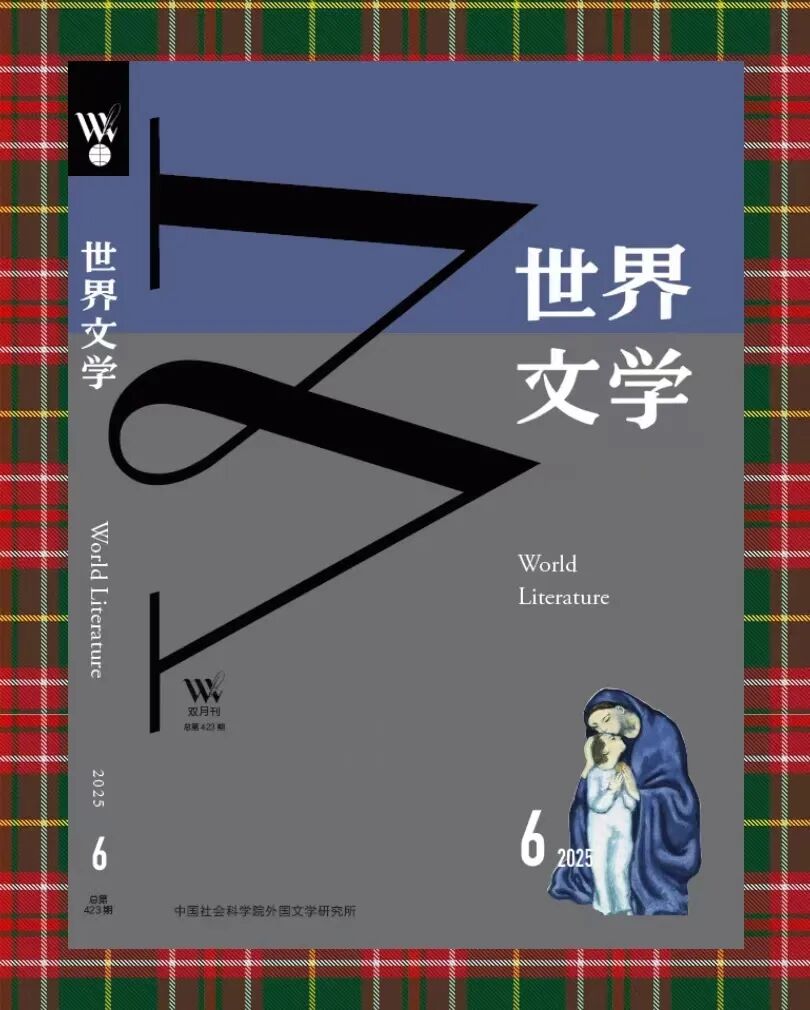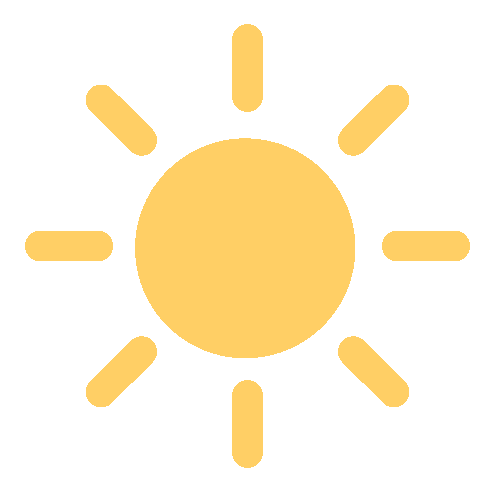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布•埃文森【美国】:书本终究还是获得了生命,而且带着我们一起重获生机……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我们是有形的实体造物,以特定的方式阅读——这种方式彰显了我们作为实体造物的阅读感受,反复委婉地提醒我们在让书本获得生命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由此来看,书本立于阅读的中途,总在维持我们和阅读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安全距离。
布莱恩·埃文森作 崔梦田译
大卫·B【大卫·B为法国作家、漫画家皮埃尔-弗朗索瓦·博沙尔(1959—)的笔名】《夜间离奇事件》第二卷有一场旧书店枪战。原是十分常见的交火,反派之一突然发出尖叫,他低头看去,发现一本书正死死夹住自己的腿,仿佛一对钳嘴。没过一会儿,又一本书紧紧捂住另一位反派的脸,让他差点窒息而死。“这些书,”恶徒们受到惊吓,大声嚷道,“正在向我们发动进攻啊!”
大卫·B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物问书店老板,他这些书到底在干什么,老板答道:“这些不是我的书,咬人的是书中的文字。”
书籍是奇特的存在,因为某种意义上,它们的物质属性并不重要:咬人的是书中的文字,和人们手中捧阅的书本身毫无瓜葛。至少,从理论上说,文字确实能咬人——不管是电子书还是纸质书,不管是大声念出来还是默默阅读。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一旦如此断言,便会不由自主想到诸多例外:一些书,一经高声朗读渲染,含义便会受到限制;一些书,一旦以某种形制呈现,效果便会增强或减弱。
书籍存在于不可思议的空隙,介乎实体与非实体之间;在这个空隙里,一方面(如果“方面”【“方面”的原文为hand。作者有意让读者在读到“一方面”“另一方面”时产生与“手”有关的联想】这个字眼合适的话),我们会觉得书的实体性并不是那么重要,另一方面,书的物质属性又与阅读经验密不可分。阅读经验之所以独特,正是由于捧在我们手中的书册的种种细节。一方面,同一本书的电子版、精装本、平装本全都“一样”,就像世界上所有椅子大概都会具备柏拉图所谓的“椅子性”,指向那把理念之椅、实质之椅一样。但另一方面,一旦我们确认自己所坐的椅子具备了“椅子性”,这把椅子的独特性和舒适度就会变得格外重要。
去年儿子出生后,我发现给他喂奶瓶时,要想一只手抱他,一只手拿书,实在不太容易,但还是可以勉强在智能手机上看看书。手机屏一页显示大约十行,四十个词左右,读完一页,我会伸出拇指滑动屏幕,翻到下一页。我把儿子抱在臂弯里,一手拿奶瓶,一手捧手机。不用变换姿势,就能放下手机、开机或关机。这样确实很方便。从很多方面来说,用手机看书,对于当时的我,不仅是最舒服的阅读方式,也是那种特定情况下唯一的选择。
不过,就算明白这一点,我依然心有所念。我最想念的是翻动书页那极其轻微的躯体动作。我想念能向前翻阅,查看章节于何处结束。想念能将书本倾侧,对比已读书页与未读书页孰厚孰薄。想念书的重量,所谓书的“厚重”。想念以前卧床时把书本摊于胸前,在阅读中渐渐睡去。此外,用手机读了几本书后,我开始想念触觉的转换:那种从一种封面和重量的书切换到另一种的体验。当时内心有个想法——某种程度上至今未变——用手机看书和读实体书的确有相似之处,但不尽相同,就像听有声书既是阅读又不尽然一样。
我当时确实算是在“阅读”——能和他人谈论这些书,而且谈得相当深入。我获取了全部内容(或者说几乎全部内容,因为有时形制转换确实会影响内容),甚至获取了所有形式——与阅读纸质版的所得并无分别。但我没有获得某些特殊体验——对我来说,它们才是阅读纸版书的独有感受。我并没有翻动书页,只是滑了一下屏幕。没有夹入书签,而是触碰智能手机屏幕的一角,标上虚拟书签。也没有站起来拿铅笔,标记想回头查阅的文字,只是用拇指摁着屏幕,移动指头,直至文字高亮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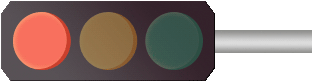


书籍的物质属性将阅读转变为个体化的过程。说起来,这种物质属性与书的内容甚或形式几乎毫无关系,而是主要关乎我们与文字之间的介质——我们的眼睛扫过文字的同时,内心将文字串联在一起,由此形成阅读经验。这种物质属性乃是过量或者剩余的象征,而非不可或缺。与此同时,它又能抚慰心灵,镇静神经,可以形成惯性,甚至令人上瘾,程度不亚于吸烟这类经常重复的习惯。我们明白,完全可以换种方式吸食尼古丁,甚至可以换用更好的办法(贴片、液体烟、电子烟),但令我们恋恋不舍的,是某种关乎习惯的东西,与我们已习得的唇部、手部动作有关。这说明从深层次上看,阅读并非只是获取构成叙事的形式和内容;它其实是一种重复性的慰藉动作,与一部特定书籍的特殊细节发生关联,于是,习惯与细微、隐约的独特体验在此合而为一。
我们回想曾经读过的书,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书,所记起的不仅是文字,不仅是故事,不仅是形式和内容,还有阅读情境——对我们来说,阅读情境仿佛已经成为书本的一部分。我记得读罗伯-格里耶【阿兰·罗伯-格里耶(1922—2008),法国作家,导演】的《橡皮》时,正独自在犹他州的盐滩中间野营:书中简洁的客观描写似乎与我所处的朴素环境交相呼应。我不会忘记看这本书时面前篝火的气味,之后好几年,那缕烟火气息仍然盘桓于书页之间。我还记得在威斯康星棕鹿公共图书馆阅读《尤利西斯》的情景——那时我是摩门教牧师,本应挨家挨户上门探访——许多细节我还有印象,比如当时伏案读这本书用的桌子,胳膊肘撑在桌子上的感觉。我还记得读彼德·史超伯【彼·史超伯(1943—2022),美国恐怖小说家,诗人】《夜屋》的环境——印第安纳州没有路灯、寂然无声的市郊社区——这对我阅读的影响至今难忘。我依然记得小时候裹着毯子读《二十一只气球》【美国作家威廉·佩內·杜·博伊斯(1916—1993)出版于1947年的小说】的经历。我想不起来到底在父母家的什么地方读了这本书,但每次看到这本书的封面,那种被包紧、裹住的感觉仍然会浮现出来。
这些记忆和前面提到的书籍并无本质联系,而且全是无法向他人诉说的体验。但对我来说,正是这些记忆让那些书籍变得非同一般,赋予相关的阅读经历某种实体性和独特性。
当然,抱着孩子、捧着手机读书,多少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倒不是说这种阅读经历缺少实体性,而是说它的实体性有所不同;由于我从一本书切换到另一本书时并未更换阅读设备,抱着孩子、捧着手机读书的经历反倒更具实体性,尤其与自己和具体书籍的关系相比,这种经历更是如此。至于那些电子书,全都混在一起了。除非在读不同书时更换手机壳,不然我的手机摸来摸去都是一个感觉。
我拥有很多本从同一家二手书店淘来的图书。我假设这些书籍曾属于同一主人,但其实,它们很可能出自几个背景相似之人的收藏。不过,在我的脑海里,他们都是同一个人:此人的阅读品味值得我信赖,烟瘾也很大,他(在我的想象中,是男性)缓慢又仔细地通读自己的藏书,阅读时总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位置距书页几厘米远。我翻开其中一本阅读时,仍能闻到上面的烟味,气味已不怎么新鲜,却依然浓重,而且每页都能闻到。假如我以前是个烟鬼,也许就会产生“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是20世纪文学中最著名的感官记忆象征,出自《追寻逝去的时光》】那样的体验,但我从不吸烟,浮现在记忆中的,其实是自己翻阅过的其他带烟味的书籍——它们构成了一份秘密藏书目录,部部精彩,为我而备,而那位主人甚至对这事儿毫不知情,当然,他也并非为了我才这样做。我这番特殊的阅读体验——与气味息息相关——在紧紧跟随他人的阅读习惯中产生,并在那些书籍之间形成短暂而微弱的联系。而且,由于我乐于拥有这位想象读者的阅读品味,我一翻开书,闻到香烟味,承诺便随之而来:这会是本好书。
换句话说,我阅读一些二手书的满足感部分源于气味,我从中可以构建有关旧主人的叙事或故事,继而构想这样的画面:某人双手捧书,正在缓慢又仔细地阅读,一只手发黄的指尖夹着一支烟,他觉得眼前的书有趣极了,甚至忘记把烟举到唇边。


从几美元买来的一堆书中,我似乎塑造出一个和蔼可亲的虚构形象——这个人正在以吞云吐雾的方式把自己送进坟墓;而且,我的阅读过程中始终萦绕着这一源自想象的人物。
但在书本世界里,那些由书而造的人物很少这样和善无害。弗里茨·莱贝尔【弗·莱贝尔(1910—1992),美国作家,主要创作奇幻、科幻、恐怖小说】的《黑暗圣母》中,主角弗朗茨是位作家:他酗酒如命,沉迷于神秘学,睡在一张堆满书和杂志的床上,久而久之,这些书刊呈现出一个人形轮廓。于是,他将这个书堆视为“学者的情人”。最后他开始对书堆说话,仿佛对方是真实存在的女人;在作品将近结尾处,“学者的情人”获得了生命:“她身材瘦削,肩膀宽阔……显然完全由切碎、压紧的纸拼合而成。”然后,她发起了进攻。“那张干枯、粗糙、坚硬的脸紧贴着他的脸,堵住他的嘴,挤压他的鼻孔;大鼻子扎进他的脖子。他感到难以承受、无法估计的重量压在了自己身上。”
迈克尔·西斯科【迈·西斯科(1970—),美国怪奇小说家,教师】的首部小说《神学院学生》中,开场便是小说同名主人公遭闪电击中。他丧生后,他们
“将他的内脏——还热乎着,冒着气儿——丢到地板上,取出成堆的书和马尼拉纸夹,撕下书页,翻出纸张,上面全都写满了字,他们将这些纸填进他的体内,压到他的肋骨后头,一股脑塞入他的腹部。他们选择哪些书页,撕下哪些书籍,并不要紧,关键只在于用文字填满他,再使他复原,命令他执行任务”。
过了一会儿,一场夸张的洗礼仪式过后,他重新活了过来,成了包着人皮的“字人”。
哪怕阅读经历告一段落,在我们的想象世界里,书籍仍会呈现自己的生命——持续演变、发展,慢慢形成某种持久不衰的生命体。记得二十岁出头时,我曾向朋友描述贝克特的《莫洛伊》吸引自己之处,结果他告诉我,书中实际上并没有我说的那些内容。回去重读才发现,我注意到的其实是某种向量或方向性——预示或暗示着尚未充分展开的东西。这倒不是说我误读了《莫洛伊》,而是说即便把书合上了,我仍然没有停止阅读:我在以神恍甚至神秘的方式继续读下去,范围已远远超越全书的尾页。
前两次读《莫洛伊》,我用的是格罗夫出版社的大众平装本,这个版本包含全套贝克特三部曲【这里所说的“三部曲”包括《莫洛伊》《马龙之死》《难以命名者》】,页面发黄,装订边局促,卖相不好。这版译自贝克特的法文原版,译者是帕特里克·鲍尔斯【帕·鲍尔斯(1927—1995),南非译者,作家】和贝克特本人。第三次读《莫洛伊》,我用了法文原版,由午夜出版社发行。《莫洛伊》英译本最奇特之处就在于它极其严格、极其固执地保留了法文版的句法和词序,在尽可能这么做的情况下确保文字表达看起来像英文。因此,我认为这本书的英法文版相差不大,不及我平常见到的译本和原著之间的差异。
但我当时深有体会、如今仍历历在目的,是版式的差异:午夜出版社那版装订边开阔,墨迹精准,字体更大,这些都有助于改善文本的观感。这种感受大概就像追完数期简装漫画小册后,再读结集出版的图像小说:不仅二者外在形制迥异,就连作品本身似乎也发生了变化。
此后,我还读了贝克特全集收入的《莫洛伊》英文版,体验又有差别:大众平装版的图书让读者置身某种状态,而精装全集则让读者置身另一种境遇。虽然故事相同,但不同版本邀请我进入其中的方式却不一样,支持我完成阅读的路径也大不相同。如果说我在读另一本书,并不尽然,但若说我重读了同一本书,也不准确。这些不同版式多有重合,却不全然相同,每个版本都让我带走一份独特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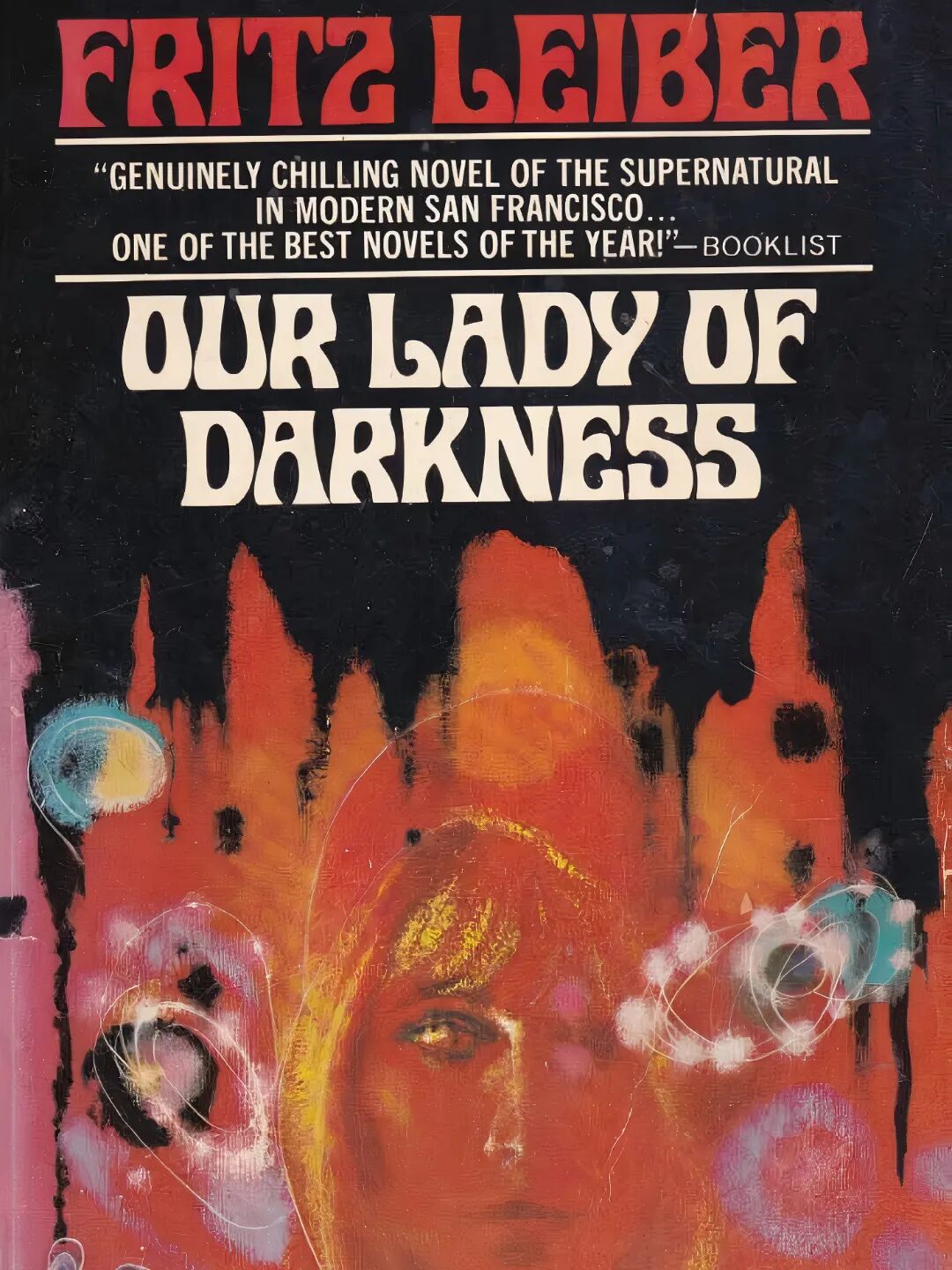

左为《黑暗圣母》书影,右为《莫洛伊》书影
如果开始阅读时用一种版式,之后换成另一版式,也会有类似体验,例如,将大众平装本换成精心设计的初版精装本,或者把纸质书换为电子版,再换回来。这种转换带来的迷失感,竟然如此强烈,着实令人讶异。字词明明毫无差别,阅读感受却完全改变了。
读实体书时尤其明显,我们会接收到某种“遗留物”——有的一目了然,有的却莫名其妙。阅读的门道多半在于学会忽略这样的“遗留物”,不过分留意字体大小、泛黄的书页或者印刷尺寸。从一个方面看(当然会有例外,例如威廉·霍·加斯【威廉·霍·加斯(1924—2017),美国小说家,批评家】的《威利·马斯特斯的孤独妻子》【《威利·马斯特斯的孤独妻子》是威廉·霍·加斯发表于1968年的中篇小说。小说文本混用不同字体、颜色、排版模式,插入照片、素描、乐谱等视觉元素。)】所谓阅读,便是看穿这些细节,假装我们眼前的窗户并未改变它后面的风景。
但即便我们基本忽略“遗留物”,它却依然发挥着影响,这就好比我们读书时选择坐的椅子、光照质量等都会和一本具体的书产生关联。
就二手书而言,这种“遗留物”往往指向另一个人。前主人的名字也许就签于封面内侧。有几页的书角可能留有折痕。有些文字大概会出现勾画或标记痕迹。没准儿还有边注,甚至夹了书签,上面草草记着几个页码。阅读二手书的过程中,我们一边集中大部分注意力留心故事情节,一边沿着另一个人的路线前行,有时紧步相随,有时偏离方向——个中感受可能是人生一大乐事,也可能是一大憾事。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参与到对他人阅读往事的想象之中。
用手机和电子阅读器看书,也会碰到边注——用电子设备做笔记、标书签、划重点段落等相对容易。但这种参与方式有别于二手书带来的体验,往往并非孤立行为,也不是读者之间的匿名传递。例如,在Kindle上,我注意到你只会在两种情况下看到别人的边注。一种是我“借给”你一本我买的电子书;这种情况下,你无需想象前一位读者,因为你很清楚是谁把这本书借给了自己。另一种情况与陌生人有关:你用Kindle读电子书,偶尔会遇到标了下划线的文字,旁边附有说明——“其他二十七位读者标记了这段文字”。你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不明白他们为何标注这段文字,只晓得有这么二十七个人。这会让你觉得也许应该重视这段话。这里,边注不再是与他人的阅读互动,倒更像是一种需要服从的压力。
十五年前,我买过若热·亚马多【若·亚马多(1912—2001),巴西现代派作家】的《味似丁香、色如肉桂的加布里埃拉》,买的是二手书,拿回家后,发现一封信被当作书签,夹于书页间,从未拆封过。信现在仍躺在那本书里,不过,书买回来几年后,我拆开那封信读了。信上写了什么并不重要,或者说,至少在这一情境下,对我们不重要。这只是一封普通书信,和众多平淡无奇的信件无甚差异,不过是以克制的方式表达爱意,请求对方回信。这封信与众不同之处是,信封上的邮戳时间和这本书英文版的出版年份一样:一九六二年——那年我还没出生,自那以后,很显然,它一直夹在这本书里。我对信本身兴趣不大,令我兴味盎然的问题是:它为什么最后会被放在这本书里?怎么放进去的?我对书的主人也很好奇:他是把信搁那儿,忘了拆呢,还是有意选择不拆?或是无法拆信,因为收信人已经去世?
我一直无法迫使自己读完这本二手版的亚马多小说,尽管有几次曾在旅途中随身携带,想要读下去;我料想,如果真要读,得另买一本。有时,“遗留物”过于沉重,我们甚至还没真正翻开书页,浏览文字,便已感受到这份重量。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亚·巴里科(1958—),意大利作家,导演】的《格温先生》【《格温先生》现行中译本的书名为《一个人消失在世上》】写到一位有意不再出版图书的作家。他决定当“书写员”,随着时间流逝,他逐渐明白“书写员”的深意——这意味着他要给他人“作画”。
此间深意很难向他人解释。他租了个场地,找来一些灯泡(已定好时间,会在大体确定的时长过后熄灭),之后他的实验对象到现场展示自己的裸体,这个过程持续三十来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事——在房间里走动、静坐、睡觉等——他在一旁默默观察,有时会做些笔记。所有灯泡熄灭后,他会完成一份文字画像,准确刻画这些对象的独特性。他只保留两个副本。一个副本留给供其描述的模特们,只给他或她自己观看——他们已经提前签下声明,保证“严格保密,否则会受重金惩罚”。另一个副本他放进抽屉,留给自己。
这些“画像”并非人物素描,至少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那种素描。据第一位“作画”对象吕蓓卡所说,这个人写的是“一个故事、一个场景,仿佛是一本书中的片段”。故事并非“画像”;它暗示了其他人物的存在。对此,吕蓓卡是这么回应的:“贾斯珀·格温教会我,我们不是人物,我们是故事……我们是整个故事,不只是人物。我们是他散步的树林,欺骗他的坏人,他周围的混乱场面,所有路过的人,事物的颜色,声音。”
这个例子要说明的,不是书本如何获得生命,而是如何深入而仔细地观察人——这种观察多少揭示了如何将人转化成文字,而文字如何进而成为镜子,呈现人的样子。进一步说,成为我们自身镜子的,并不是故事中的人物,而是整个故事。
我们是有形的实体造物,以特定的方式阅读——这种方式彰显了我们作为实体造物的阅读感受,反复委婉地提醒我们在让书本获得生命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由此来看,书本立于阅读的中途,总在维持我们和阅读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安全距离。【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阅读过程中,人类总不自觉地将自我与文本镜像(即前文所说的故事)重叠或混淆;而书本的作用恰恰在于以其物质实体将读者与作品世界隔开,维持二者间的审美距离】
然而,书本终究还是获得了生命,而且带着我们一起重获生机。

布莱恩·埃文森 (Brian Evenson, 1966— ), 美国当代知名作家, 主要从事恐怖小说、 科幻文学以及实验性文本创作。出生于爱达荷州, 成长于摩门教家庭。博士毕业于华盛顿大学, 在杨百翰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布朗大学等学府任教过。作品以冷峻的极简风格著称, 善于调用心理惊悚元素, 表现存在主义困境。著有《瘫倒的马》《末日》《地狱里燃烧的玻璃地板》《世界解体之歌》等数十部作品或文集, 获得欧·亨利奖、雪莉·杰克逊奖、世界奇幻奖等奖项。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6期,策划及责任编辑:叶丽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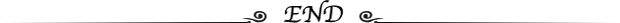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