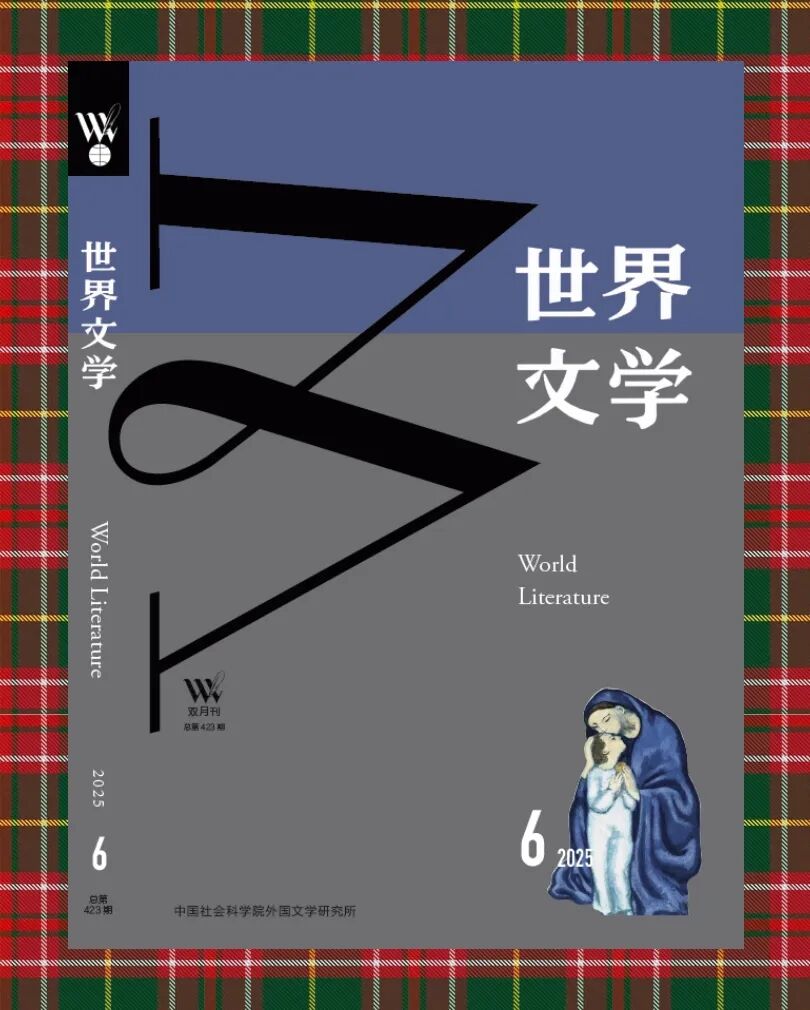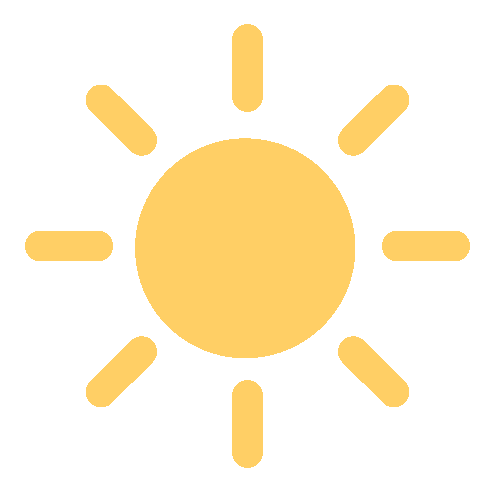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雅•博内【法国】:藏书癖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藏书家和他成千上万本的书之间形成了奇怪的关系,就如同园丁和入侵的攀缘植物之间的关系一样:植物自行生长,肉眼看不出其生长过程,但几周后就会有明显的进展;如果不砍断它,人就只能引导植物朝他所希望的方向生长。如此一来,无限扩张的图书馆就成了有自主意识的生命体——“一个人打造的图书馆是有生命的。它绝非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彼此孤立的书籍的总和”(《纸房子》)。

雅克·博内作 陈雨薇译
“那些读不完的书和走不遍的图书馆与我何干?它们的主人终其一生,恐怕连书上的标签都没读过。”
——塞内卡
小说中充斥着图书馆的身影。有时,图书馆甚至成为故事的决定性元素(比如《玫瑰之名》【意大利符号学家、作家翁贝托·埃科(1932—2016)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中世纪意大利修道院的故事。图书馆是整部小说的重要场景之一】中本笃会修道院的图书馆,德泽森特【法国作家若利斯-卡尔·于斯曼(1848—1907)的小说《逆天》中的主人公。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德泽森特在乡下过上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并建造了一座图书馆】的图书馆,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作品《迷惘》【英籍犹太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汉学家彼得·基恩——由于厌恶人们的虚荣心,摒弃公职,终日与书本为伴】中汉学家彼得·基恩的图书馆,又或是尼莫船长【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中的角色】的一万两千册“权威”藏书),但据我所知,只有一部小说里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有藏书癖: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卡·玛·多明格斯(1955—),阿根廷作家】的《纸房子》。小说的叙述者苦于书籍泛滥的威胁(“书籍在房子里扩张,无声无息,无辜无害。我对此束手无策”),一直追寻藏书家卡洛斯·布劳尔的踪迹,而后者早已在跟藏书的战斗中败下阵来(“两万册图书不可能一下子就整理好。必须严守秩序,我是说,对秩序抱有一种超人般的敬意”)。由于丢失了那个对管理藏书而言不可或缺的卡片箱,布劳尔的精神状态面临崩溃:没有目录,他的图书馆就无法使用。于是,布劳尔用自己的书在人迹罕至的海滩上修建了一座房子(纸房子),但为了归还别人的那本康拉德的《阴影线》,最终又毁掉了这座房子。但人究竟是如何积累起成千上万册书,给自己带来这么多麻烦的呢?对此的解释五花八门——而且并不相互冲突——具体视我们所讨论的藏书者类型而定,因为“藏书癖”这个统称涵盖了多种截然不同的现实情况。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两大类:收藏家和书迷。
收藏家又细分为行家和“囤书者”。行家往往关注某一个作者(特里斯坦·伯纳德【特·伯纳德(1866—1947),法国剧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和律师】于一九二四年出售了他费心收集的《保尔与维吉妮》的一百七十三个版本);聚焦一个时代或一种流派(皮埃尔·让·雷米【皮·让·雷米(1937—2010),法国外交家、官员、作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钟情于十八世纪的色情作品);专注一个主题或一种装帧,等等。此外,还有更奇特的收藏癖好,比如一位收藏家只收集作者姓氏以字母B开头的书籍,或者只收集与自己同名——都叫儒勒——的作者的作品。

杜米埃【奥诺雷·杜米埃(1808—1879),法国画家、讽刺漫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题为“兴奋的旧书商”(1844)的石版画完美地展现了藏书爱好者对稀有书籍的痴迷。画中,一个人正翻阅着一本小册子,激动地对另一位同好说:“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开心了……我刚刚花了五十埃居买到了一本一七八〇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贺拉斯的作品……这个版本非常珍贵,每一页都错误百出!”
收藏家很容易变得爱囤积,只需将一个收藏兴趣叠加到另一个之上,再继续叠加就可以了。但很多时候,一旦目标实现,某种特定类型的收藏家就会失去兴趣。收藏完成了,又该何去何从?没有可发掘的东西了,兴趣便消失了。收藏家先是欣赏一段时间自己的藏品(透过藏品,他看到的是自己坚持不懈并且最终能达到目标的形象),接着便会将之搁置一旁,或者处理掉,转身投入下一次收藏。重要的是追逐的过程。我们不禁想起《马耳他之鹰》【1941年拍摄的美国动作片,剧情围绕雕像“马耳他之鹰”的悬案展开】的片尾:古特曼【电影《马耳他之鹰》中的人物,是一位寻宝者】先生意识到自己好不容易弄到手的东西是赝品时——“假货!这是个冒牌货!”【本段里的仿宋体文字原文皆为英语】——想到自己又可以返回伊斯坦布尔去寻找真品(“好吧,先生,您有什么高见,我们是站在这里落泪,互相埋怨,还是出发去伊斯坦布尔?”),脸上顿时洋溢出了喜悦之情。追逐可以继续了。如果萨姆·斯佩德【电影《马耳他之鹰》中的人物,是一位私家侦探】找到的猎鹰是真品——马耳他骑士团一五三九年献给查理五世的那只纯金猎鹰——古特曼的人生就会失去意义,又得重新去找一个目标。这次的失败反倒让他省了力气,只需继续找下去就好。
“囤书者”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完全无法控制藏书的数量,并且已经放弃了阅读堆积成山的书籍。加兰塔里斯【克里斯蒂安·加兰塔里斯(1932—),法国古董书收藏家、古文物研究者】引用了理查德·希伯爵士【理·希伯爵士(1774—1833),英国藏书家】的例子:爵士拥有三十万册藏书,分布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五个不同的图书馆,每座图书馆占据了五处房产(“书籍无处不在,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森林——有小径、林荫路、小树林、小路,书本从书架上溢出,堆满了桌子、家具、地板……走路时一不小心就会碰到”)。至于安托万·玛丽·亨利·布拉德【安·玛·亨·布拉德(1754—1825),法国公证人、藏书家、翻译家、政治家】——拿破仑时期的公证人兼巴黎第八区区长——他藏书的初心是为了拯救那些在革命中因没收和挪用而流入市场的书籍,最终却买了九到十栋楼房来存放自己的六十万册书。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三二年间,他的儿子们组织了这些藏书的拍卖,据说书店和旧书摊人满为患,二手书价格暴跌,持续了好几年。



另一大类藏书家是那些狂热的读者。不是说前一大类不读书,只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在别的方面,也并不是说这一大类最终不会囤书,只不过囤书是他们痴迷阅读的后果,而非最初的目的。一开始,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对阅读充满了渴望,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会囤一堆可以在图书馆查到、借阅或转卖的书籍。而收藏家型的读者却想要保留这些物品,以便随意支配。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小说中的叙述者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读者不仅痴迷于阅读的过程,还迷恋书籍本身:
我经常自问,为什么要留下那些只会在遥远的未来对我有用的书,那些偏离了我日常阅读路径的书——那些书我只读过一次,并且不会很快就重读,也许永远不会。但是,我该如何舍下《野性的呼唤》这样的书呢?它是我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怎么能丢开让我的青春期浸泡在眼泪里的《希腊人左巴》【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1883—1957)于1946年出版的小说】呢?还有《二十五小时》【罗马尼亚作家维吉尔·格奥尔吉乌(1916—1992)于1949年出版的小说】以及许多别的作品。它们在高高的书架上搁置了多年,仍然完好无损,在我们对它们的神圣忠诚中保持着沉默。(《纸房子》)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阿·曼古埃尔(1948—),阿根廷裔加拿大作家、翻译家、编辑】也有类似的感慨:
当我把熟悉的书一本本摞起来时……每次都会自问为什么要保留这么多明知再也不会读的书。我自答道,每次处理掉一本书,几天后就会发觉它是我正在找的书。我告诉自己,没有(或者很少,几乎没有)哪本书不能让我从中发现令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阅读地图:一部人类阅读的历史》【曼古埃尔于1996年发表的作品】)


在此,曼古埃尔与老普林尼的观点不谋而合:“一个有学问的人即便是面对一本糟糕的书,也很难会认为它一无是处。”在无法割舍一本书的两个原因——阅读情结的驱使,或是未来对它产生兴趣的可能——之中,潜藏着某种焦虑。书籍是情感的物质化体现,或者说是未来可能拥有这一情感的机会,而放弃一本书会带来严重的缺失。当收藏家困在尚未拥有某本书的忧念中时,狂热的读者在担心失去他们读过的、有一天可能会重读的书。这些书承载着他们过去的踪迹,寄托着他们对于未来的希望,但这种令人不安的阅读狂热从何而来?最初的场景——想必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溜走了——大概发生在学习阅读的神奇时刻,以及解码文字内容、产生一种超越无限之感的瞬间。我童年时把出现在身边的东西读了个遍:所有的书,还有海报、告示、广告、报纸的碎片——甚至在吃饭时阅读各种盒子背面或瓶子标签上的说明,直到可以对“英国宫廷独家供应商”以及各种美食展览或比赛的获奖者如数家珍的程度。一种无法遏制的好奇心激励着我去追问单词和句子背后隐藏着什么,去探究我所要面对的未知事实,一如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中所说:“我希望你不仅对你所读的东西感到惊叹,还要对它是可读的这一奇迹感到惊叹。”狂热的读者不仅焦虑,还充满好奇。人类的好奇心——自基督降临后就被某些教父批判得一无是处,甚至在福音书出现后被明令禁止——难道不是我们行为的决定性动因之一吗?不是人类获取知识、探索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吗?不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吗?好奇心是没有边界的,永无止境。它从自身汲取能量,永远不会满足于当下的发现;它永远在前进,直至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息。(我曾在某处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期间,一个死刑犯在去往断头台的刑车里看书,上断头台之前,他给自己正在读的那一页做了标记。)或者像维克多·雨果在戏剧《玛丽翁·德罗尔姆》【维克多·雨果于1828年创作的五幕剧,讲述了生活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的著名交际花玛丽翁·德罗尔姆的故事】中所写的那样——“国王:你为何而活?/安吉利:我因好奇而活”。阅读延展了我们有限的现实,让我们能够置身于那些遥远的年代,感受不同时代的风俗、心灵、思想以及人类的动机,等等。当一个可以逃离有限环境的机会摆在眼前时,我们又怎能止步不前呢?自由在触手可及的前方,要做的就是阅读,阅读,再阅读,期待能够摆脱命运的掌控。只需将这种无限的好奇心与一定的系统思维结合起来,促使自己读完一位作家的所有作品以及所有关于他的作品,接着开始读另一位作家的作品,针对某一主题的作品,还有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文学作品;慢慢地,我们就将读过的书保留了下来,再加上新出版的相关书籍,就这样,成了一个藏书读者。
藏书家和他成千上万本的书之间形成了奇怪的关系,就如同园丁和入侵的攀缘植物之间的关系一样:植物自行生长,肉眼看不出其生长过程,但几周后就会有明显的进展;如果不砍断它,人就只能引导植物朝他所希望的方向生长。如此一来,无限扩张的图书馆就成了有自主意识的生命体——“一个人打造的图书馆是有生命的。它绝非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彼此孤立的书籍的总和”(《纸房子》)。我们为图书馆选择了主题和发展轴,却只能眼看着它占据房间的每一面墙壁,爬上天花板,并逐一吞并其他房间,把一切妨碍它的东西都挤出去。它会把墙上的画和妨碍查阅书籍的物品都清理掉,带着笨重但又不可或缺的同伙——板凳和梯子——四处移动,要求人对它进行持续的重新整理:因为它的发展不是线性的,故而需要新的分配。同时,图书馆无疑是其主人的反映和化身。对于那些能够巧妙解读它的人而言,书架的格局体现了图书管理者的深刻本质。此外,任何稍有规模的图书馆都各不相同,都有其独特的个性。

雅克·博内(Jacques Bonnet,1949— ),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译者、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编辑。迄今已出版《洛伦佐·洛托》《以友谊之名》等10部小说和随笔集、20本译著,主编了《为了一个时代的丛刊》等多部文丛,还为法国《世界报》《快报》等报刊撰写了大量文学艺术主题的专栏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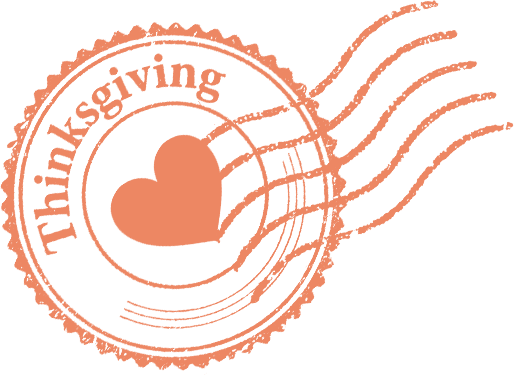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第6期,策划及责任编辑:赵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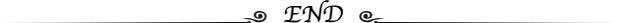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