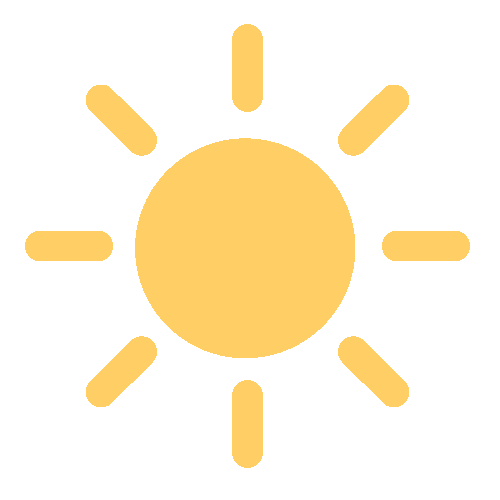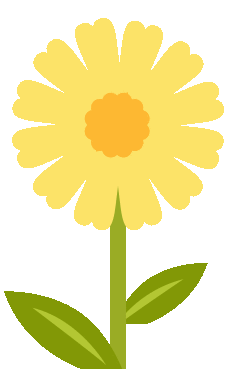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于泽熙:词典之外的人性回音——读《不存在的词典(三篇)》有感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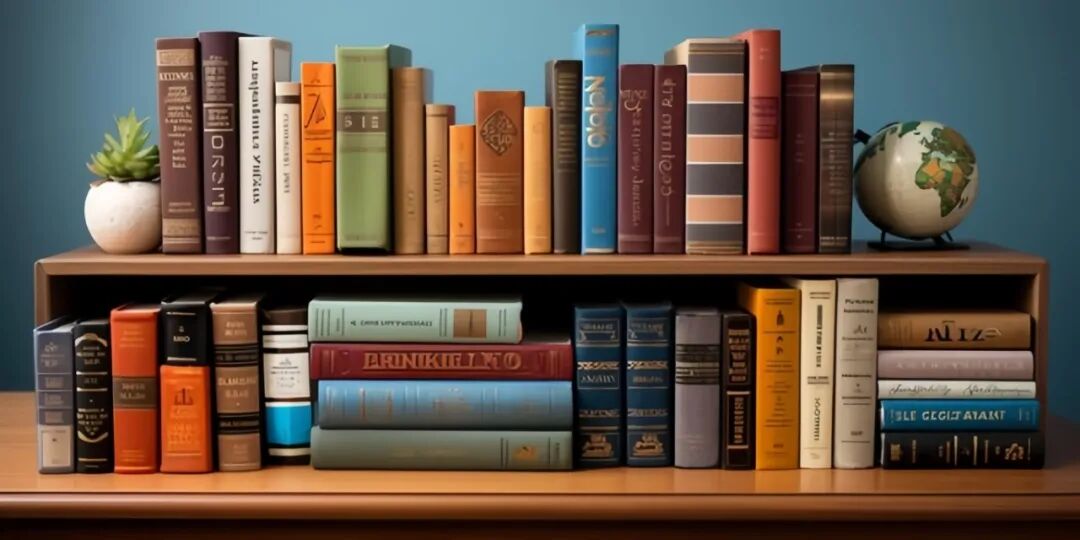
这些“不存在”的词语,扎根于真实人性的土壤——提醒我们语言有边界,但人心共鸣无界。只要愿用心倾听、共情,便能跨越词典的局限,听见彼此心中最真实的声音,理解这复杂多元的大千世界,以及生活其中的每个鲜活生命。那些被现有词汇忽视的人性微光,终会在故事的传递中,汇聚成照亮彼此的温暖光芒。

词典之外的人性回音
——读《不存在的词典(三篇)》有感
于泽熙
掠过意大利作家斯特凡诺・马西尼的《不存在的词典(三篇)》的文字(发表在《世界文学》2025年第3期上),我不禁想起那些“不知该怎么形容”的时刻:比如面对未知时的纠结、对抗偏见时的孤勇和拥抱情感时的悸动。而马西尼以真实历史为基,用二十一个“不存在”的词语作钥,打开了被现有词典语言封藏的情感。每一个虚构出的词语背后,都藏着现有词汇难以描摹的人性细节与社会棱面,让“无法言说”的感受有了被看见、被共情的可能。


“安诺奈心理”(Annonismo)与“恋地情结”(Attacismo)这两个词语,如双面镜般,照出了人类在面对自由与归属的选择时永恒的矛盾心理。孟格菲兄弟耗尽半生破解飞行秘密,可当载着梦想的热气球即将升空时,他们却退缩了,送羊、公鸡与鸭子先行探寻天路去了。这份“渴望飞翔却惧怕失重”的犹豫,并不是怯懦,而是本能的自我审视——既向往挣脱束缚探索广阔的世界,又贪恋地面的安稳。人类始终在“突破”与“固守”间摇摆,这种矛盾仿佛早已刻入人性底色。
美国水手查理・科沃特的经历让这份矛盾与孤独更显沉重。不到十七岁的他,体型粗壮如象,却有着不符合年龄的迷茫,脸上总笼罩着某种飘忽感,像是与世界隔了层屏障。他在拳击场上展露天赋,场外却如“不雅的侏儒”,不分季节地穿着同一件羊毛夹克外出,如“行尸走肉”般游荡。一九三二年五月,科尔尼营地上空的阿克伦号飞艇改写了他的人生。这艘“飞天航母”需百名水手协作系泊,却遇阵风将一切打乱。飞艇失控攀升,查理竟因牢牢抓住绳索而被带至两千英尺的高空——人类从未涉足的冰冷区域。



高空中,风拍打着身体,他的尖叫无人听闻;地面上,人群散去,无人发现他的缺席。这种“被遗忘的孤独”,远非“寂寞”所能概括,是个体被无视的割裂感,是在痛苦中挣扎却无人察觉的失重感。现有词汇无法捕捉这种复杂的情感,而马西尼却创造出“恋地情结”一词,让这份委屈与孤独有了具象的载体。查理回到地面后所得的“恋地者”绰号,成为对人类孤独的注解——我们终其一生寻求归属,当世界将我们遗忘时,对“脚下土地”的渴望才愈发迫切。
“多蒂主义”(Dottismo)一词如同玫瑰的刺,刺破性别偏见的阴霾,照亮女性在困境中倔强又美丽的生长。多萝西・帕克(又名“多蒂”)终其一生都在对抗命运的残酷与社会偏见。犹太家庭出身的她,被继母送入天主教学校,在信仰的冲突中成长;生父与继母壮年离世,叔叔在泰坦尼克号上丧生,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可她将苦难藏在幽默和犀利的言辞之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纽约以“毒舌作家”闻名。她敢于调侃主流、戳破性别的不公。当记者问她“是否幸福”时,她的回答是“女人的幸福总比男人低一级”,这份回答里藏着对现实的无奈与不向偏见低头的锋芒,这便是“多蒂主义”的鲜活注脚。
多蒂精神在海莉特・德安格维尔与阿弗西娜・慕里尼的故事中得到呼应。一八三八年夏,四十四岁的海莉特要攀登勃朗峰,以女性的行动对抗社会质疑。镇长以“尊严”为由要求她穿裙装登山;村民对她充满质疑,连牧师也拒绝为其祈福。但她决意“证明夏娃的后代同样有能力登上峰顶”——裙子被灌木丛缠住,便用力将之扯脱,顺带将质疑扔在身后。



九十年后,意大利女孩阿弗西娜为了实现自己参加自行车比赛的梦想,与传统习俗进行了坚决的抗争。父亲反对她沉迷于“不务正业”的运动,她便剪去长发,去掉名字结尾的元音来假扮男性报名比赛、以做弥撒为借口溜出家门,悄悄换骑行装束备赛。比赛后,即便脸颊因受伤而滴血,捧回奖品——一箱樱桃——时,眼里仍闪着光芒。可是,她们的胜利始终被偏见的阴影笼罩:海莉特登顶归来,迎得的是“女人登顶让攀登失色”的嘲讽;阿弗西娜因女性身份暴露,被取消环意大利自行车赛的参赛资格,理由是女性运动员的出现“让运动蒙羞”。
现有词汇里的“勇敢”“坚强”等词语都太过单薄,载不动她们对抗偏见时的痛苦与执着。“多蒂主义”的出现,让女性以幽默化解苦难、以坚韧打破束缚的精神有了专属注脚,更揭露了被忽视的一个社会棱面: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女性每一次的突破都需付出远超常人的代价,那些“出格”的抗争,不过是对平等与尊重的朴素追求。
“罗莎贝拉般的”(Rosabelliano)一词里藏着爱情里最动人的矛盾与释然,勾勒出陪伴与离别在人的美好心性中的深层呼应。贝丝・拉内尔从十三岁起就被衰老恐惧困住,第一根黑发飘落时,便感悟“春天终将结束”,美貌会如花瓣般凋零。她甚至厌恶母亲的脸,怕母亲的衰老终会在自己脸上重现。这种焦虑如牢笼,让她在梦中窒息,从梦中惊醒,甚至在演唱《罗莎贝拉》时突然失声。
魏斯兄弟的出现,让她的“牢笼”里透进了光。起初贝丝对这两位魔术师并无好感,担心他们的表演会影响自己的收入。可当她看见埃里希・魏斯(后称胡迪尼)从锁链与密封水箱中脱身时,彻底被震撼了——这个能破除一切束缚的男人,或许真的能帮她对抗衰老恐惧。她被埃里希的技艺与直面困境的勇气吸引,而埃里希同样注意到了这个内心藏着阴郁的女孩,两人的爱情由此萌芽。
一八九四年,贝丝与埃里希结婚,成了埃里希舞台上最信任的助手,为他“上锁、闩上板条箱、密封装满水的水箱”,每一步都是两人之间绝对的默契。可死亡终是逃不开的牢笼,一九二六年十月,埃里希因腹部中拳离世。临终前,他与贝丝约定在每年的祭日举办降神会,以她心爱的歌曲《罗莎贝拉》的开头做暗语,想从死神手中逃回到她身边。
此后十年间,贝丝遵约燃烛唤夫,却从未得到回应。一九三六年十月,衰老的她望着烛火忽感释然——即便伟大如胡迪尼也逃不开死神,“来生”只是对永恒的幻想。她并未落泪,因为懂得埃里希坚定地选择与她共度有限时光的珍贵,这一切早已超越了对“永恒”的追求。那句简单的“晚安,埃里希”背后隐藏着最深的爱意与释然:爱情从不是永不分离的承诺,而是在有限时光里全然的相伴,是离别后仍能携回忆坦然前行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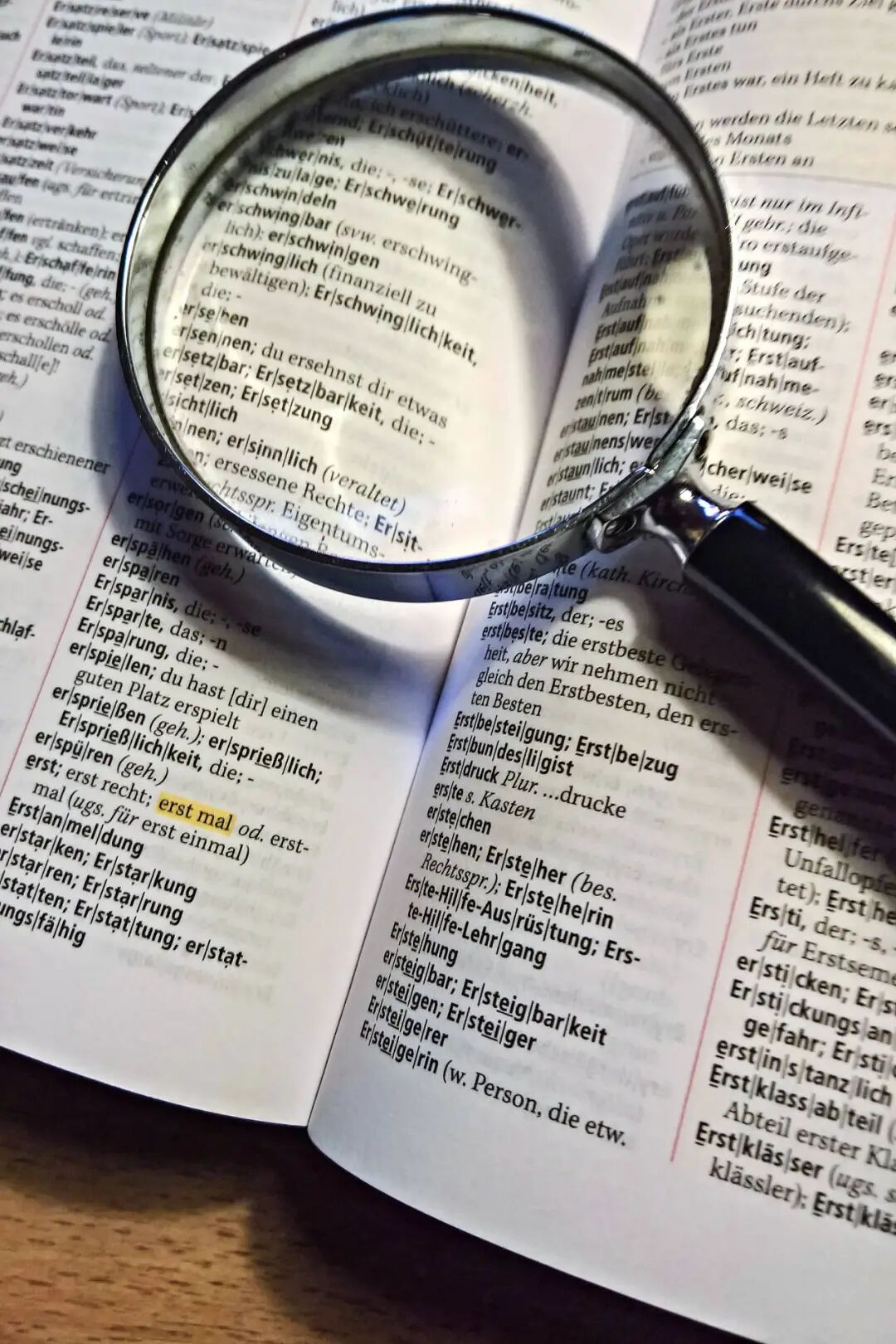


现有词汇里的“深情”“忠贞”难以描摹这份复杂情感——“明知会离别却仍要全力去爱,虽然有遗憾却因陪伴而圆满”,而“罗莎贝拉般的”一词将依赖、信任、遗憾与释然悉数容纳,让爱情脱离甜言蜜语的简单堆砌,有了更厚重真实的温度。
三个词条读下来,马西尼创作的这些“不存在”的词语的意图渐明。语言是认知世界、交流情感的工具,可当现有词汇无法精准描述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便隔了层薄雾。孟格菲的犹豫或被归为“怯懦”,海莉特与阿弗西娜的抗争或被视作“固执”,贝丝的等待或被看成“偏执”,无人读懂这背后瘾藏的审慎、艰难与坚守。
这些虚构词语如同拨雾的清风,打破了语言的牢笼。它们并非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而是对“无法言说”的情感的尊重,是对人心最温柔的回应。这些“不存在”的词语,扎根于真实人性的土壤——提醒我们语言有边界,但人心共鸣无界。只要愿用心倾听、共情,便能跨越词典的局限,听见彼此心中最真实的声音,理解这复杂多元的大千世界,以及生活其中的每个鲜活生命。那些被现有词汇忽视的人性微光,终会在故事的传递中,汇聚成照亮彼此的温暖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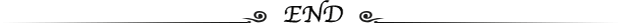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