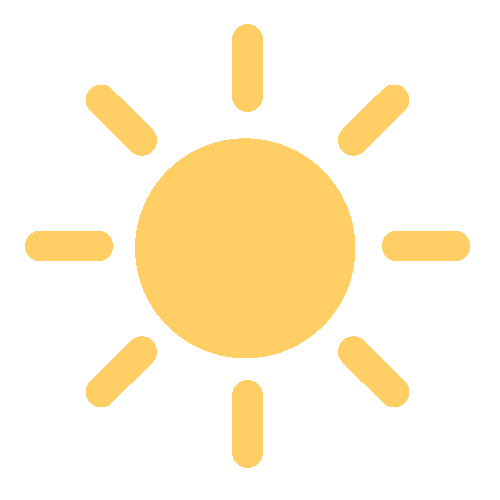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斯•弗•瓦西连科【俄罗斯】:约尔卡,或一位帅飞行员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当她给他解开皮夹克扣子,摘掉飞行头盔后,她吃惊地呀了一声。他长得的确很帅,这个飞行员满头金头,高高的额头,嘴角轮廓刚毅,真像一个男子汉。他是一位白马王子,长得无可挑剔。

斯韦特兰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瓦西连科作 任光宣译
十二月末,突然春意融融了。先是下了雨,随后天空就像是塌陷的屋顶,倾盆大雨从天降下来。可天上的朵朵云彩中间,却闪出来一轮暖洋洋的太阳。她和儿子去到原野上,那里长着朵朵雪莲,还有许多春蘑菇、羊肚蘑也在十二月生了出来。他俩甚至还采了一点蘑菇,可后来就随路扔掉了:要是冬天的蘑菇有毒呢?阿赫图巴河面已经封冻,凝固在一旁,她和儿子从冰面上走了个来回,想试试冰冻得怎么样。既然冰面还结实,那就还是冬天。在这条河的结冰部分前后,河水自如地流淌,水是黑的,颜色像是深秋的河水,真不知怎么在河的中间——冻结出一条宽宽的冰道。


但春天还像是春天的样子,这是元旦前的一段时间,醋栗和樱桃树已开始抽芽,仿佛是某种奇迹发生的先兆,孩子们在这时候去“军官之家”参加新年枞树晚会。
元旦前夕,天气突如其来冷得要命,可万里无云,繁星满天——星星有大点的、有清新的、有冰冷的,一颗一颗像是结成的冰块,闪烁在漆黑的夜空。儿子十岁,站在他们那间芬兰式小房子门坎上,他身旁是一棵枝头挂着冰霜、吱吱作响的苹果树,儿子就像是一位少年神【此处指古希腊神话的阿波罗神】抬头望着闪烁的星空,同时说:“天上也住着人,向他们挥挥手吧!”她站在那里,举起一只带着毛手套的手向着天上的星星挥动。
迎接元旦佳节的有他们三个人:她自己,儿子,还有她的已瘫痪卧床的老妈妈。喝完香槟酒,母亲和儿子就睡觉去了,可她决定出去溜达溜达。她喝得稍微有点多,傻呵呵地去开门,折腾了好半天门钩才把门打开了……她从结着薄霜的台阶跑下去,穿过花园里结上薄冰的小径,一脚踹开了篱笆门,沿着人行道直接向大道跑去。之后,她又沿着冰霜覆盖的大道往下跑,一直跑向一片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把他们住的那个保密的军事小镇同一个村庄和余下的外部世界隔离开了。她一动不动地站在悬崖边,简直愣住了。他们家住的那个军事小镇就建在这个悬崖上,而悬崖下面的深谷里是那个村庄,她此时就处在悬崖和深谷中间。不知是什么人为了穿行的方便在带刺的铁丝网上搞出来一个洞,她从那个洞把头探了出去,蹲在那里动都不敢动,因为喉咙上的血管怦怦直跳,被一个带锈的铁刺顶着,随时都可能扎进去。
她放眼望下去,下面就是那座村庄。村庄从这头到那头罩在一片灯火之中,仿佛是星空翻倒在地上。况且,整个村庄都在歌唱,好像歌唱的不是村庄,而是灯火,歌声从村子这头飘到那头,刚从村子这边响起,就在村子那头结束。歌者的声音尖亮,富有穿透力,就像是严寒冬日里从灶火的烟筒里冒出的滚滚浓烟,轻摇直上,一直升向天空。歌声缭绕在天地之间,久久消散不去。
我的天啊,这是令人感到多么幸福的时刻啊,她想道,可是一层铁丝网就把她与这种幸福隔开了。
她时时能感到一些与人们隔绝、离开世人圈子的时刻,她的这种感受最近一段时间尤为强烈。她的眼睛近视,动作笨拙,为人腼腆,不善辞令,不会唱歌跳舞,不善于衣着打扮,不会开玩笑,办事总办不到点子上。可是她会张大嘴露出皓齿,傻乎乎地幸福微笑(人们称她的微笑为加加林【尤里·加加林(1934—1968),苏联宇航员。1961年4月12日,他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航天飞行。他曾留给世人一张他张开嘴大笑的照片】式的),她还会竭尽全力默默地爱着自己儿子、自己母亲和自己为数不多的男女朋友、热爱自己家的那片草原和草原上方的星空,除此之外,她身上确实是一无所有了。
从不久前开始,她开始盼望着奇迹的发生。
她十七岁那年,生下了自己的儿子,那个男人叫什么她都不知道。中学毕业后,她去士兵浴室附设的洗衣房当洗衣工,她母亲也在那里工作。她在几个大桶里给士兵洗他们从军营运来的军上衣、裤子、床单、被子。这活很累,三班倒,可不少女友还羡慕她,因为在小镇上再没什么事可干。那里有时候一年征两次兵,她和母亲就算是走运了。汽车拉来的新入伍者身上还是穿着牛仔裤、时髦衬衫、高领毛衣、西服和夹克衫这些“百姓服”。他们在浴室里洗过澡后,立刻就换上军装,那些“百姓服”就送到洗衣房了。她和母亲把送来的衣服洗干净后,在当地市场上把它们当作“二手货”卖掉,卖得的钱虽不多,但还算有点油水吧。也就是在这个洗衣房,当水锅煮着士兵内衣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屋里到处雾气弥漫的时候,她怀上了自己的儿子。那个小兵把自己的内衣从军营运到了洗衣房,把她拖到一个小储藏室,用毛巾塞住她嘴,就在一捆捆士兵的脏衣服包上把她强奸,之后就溜之大吉了。她明白自己怀孕时已经晚了,肚里的孩子不能做掉了。
她看重自己的儿子,希望他有美好的前程:想着他先中学毕业,后入军校,再成为军官回到故乡小镇。况且,她的儿子萨沙的确让她有这种希望,因为他学习很棒,长得一表人才,是个聪明善良的小帅哥儿。可是不久前,他回家后痛哭流涕地问她:“妈妈,大街上的小男孩子们说,我的父亲是个当兵的,还说我生在栅栏下。这是真的吗?”听了这句话后,她吓得倒吸了口凉气,她明白,那个有关身世的肮脏的秘密,立刻就会把她儿子抛下深渊,抛回他来到人世的那块地方,儿子从那里大概就再也挣脱不出来,就会死于流言蜚语的。因此,她把嘴边的一句话顺口说了出来。
“你父亲——是飞行员!你记住,他正在执行国家的重要公务。”
儿子似乎相信了这句话。可她睡在儿子身边哭了整整一夜。从那个时刻起,她就执着地盼望着奇迹发生。她所期盼的奇迹其实很简单,就是盼望着她儿子萨沙有一个父亲出现。
她双手小心翼翼地扒开铁丝网,慢慢地往上爬。但是,她刚刚爬到坡顶,又重新滚了下去。这次往下滚的时候,她的两脚没有触到那条薄冰覆盖的道路,就像一只失去翅膀的小鸟,一颗不长眼的圆球,不可遏制地向着深渊滑下去。她使劲弓着身子,吓得要死,呼天喊地叫着。这时,有个人跟在她身后从陡坡上跑下来。
就在她滚到悬崖边的时候,有个身穿棉坎肩的男人把她抓住了。他一把抓住她,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她的双唇贴在他的胸口,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他赤身穿着棉坎肩。她感觉到他那跃动着生命欢乐的、健壮而年轻的男性躯体,他那强健的肌肉和光滑的皮肤,还有他那直接撞击着她嘴唇的怦怦心跳声。
“约尔卡,是你吗?”
她抬起眼睛看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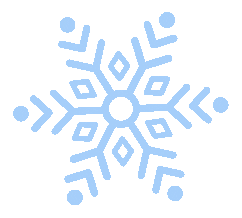

他叫斯拉夫卡,年轻的大尉军官!她跟他有过一段罗曼史,那是好久前的事了,还在夏天的时候,当时他还是个中尉。他教她跳舞,学的是探戈,深更半夜,在大街上,有一台录音机伴奏。他问了一句:“我俩来蹦达几圈?”随后就带着她跳起来。她半天学不会,她踩住他的皮鞋绊倒了,他把她扶起来,在柏油路上转起圈来,她晕得仿佛星星从夜空上掉下来。时值八月。转了几圈后,他拖着她走到果园里,那里有一张床,上面挂着白纱蚊帐。夜晚,蚊帐被风卷起,他俩赤身裸体地拥抱在一起,躺在星空苍穹下,整个世界上似乎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俩啃着苹果,一个苹果两个人吃,用三公升的罐头瓶(是母亲不注意留在果园的)喝家酿樱桃甜酒,还放声大笑,像是两个疯子。那床白色蚊帐就像幽灵一样在果园里飘舞。
就在那个时刻,他给她想出来“约尔卡”【在俄语中,约尔卡本意为小枞树】这个名字。他说他爱她,答应了娶她。
一个月后,一个女邻居跑来对她说,斯拉夫卡与尼侬同居,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他已经把自己的东西转移到她那里了。尼侬在野战医院当护士,是约尔卡最好的女友。打这之后,约尔卡再也不相信任何人对她的爱情了。她明白了谁都不需要她这个有拖累——年幼的儿子和病歪歪的母亲——的女人。
“放开我,斯拉瓦【斯拉夫卡的本名】……”她试图挣脱开他的双手,“你的尼侬在哪里?”
他松开了对她的拥抱,摇了一下头。
“瞧,在那里,就在上边站着,”他心猿意马,毫无希望地说,声音完全像女人,一副向约尔卡诉苦的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简直成了我们家的酒鬼……”
尼侬酗酒毫无节制,这件事整个镇上的人都知道。在那家野战医院,尼侬曾经享有最佳外科护士的美名,她都升到护理员一级了。
“朋友们!”尼侬全身摇摇晃晃,手里还挥动什么东西,从高处喊道,“你俩怎么卡在那儿了?”
他们慢慢地折了回去。尼侬一只手拿着酒瓶,站在一株挂着冰霜的赤杨树下——赤杨树枝在她的头顶上吱吱直响。斯拉瓦满脸像是上了一层霜,因为脸气得煞白。
“你从哪儿搞到的?”
“来了一个军官。我猜到了。我有权利,”尼侬神秘兮兮地说。斯拉瓦从她手中夺过了酒瓶,在柏油路上砰地一声摔得粉碎。
“傻瓜!”尼侬说,“犯抽风病了!”
“滚蛋吧,你!……”斯拉瓦转身走开了。
“你要去哪儿?”尼侬在他身后喊道,同时心不在焉地问约尔卡,“他去哪儿了?”她俩跟着他走了。在半路上遇见了嘉尔卡,这是一位年轻活泼的合同兵【合同兵是指按照合同在部队服役的士兵,与义务兵有所不同】,单身女子。她往前跑着,以躲避一个军官的纠缠。
“那我和你到底什么时候再见面?”那个军官丧气地问。
“嘿,刚分手就立刻问什么时候再见面!”嘉尔卡回答。
嘉尔卡跑到了两位女友跟前,说:
“这个人是在迪斯科舞会上缠上我的……我当时想给自己找个男人过夜。我想那么做,可做不到!”嘉尔卡说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实验场里从准尉到将军,所有军人都与她有染,她谈到自己的艳遇总是十分坦率,像士兵汇报一样:与谁睡了,什么时候,睡了几次。
“既然想与他共度良宵,那你干吗把他撵走了?”约尔卡感到奇怪地问道。
“我也不是逢人就睡的,”嘉尔卡同样惊讶地答道。
他们三人——约尔卡、嘉尔卡和尼侬——闷闷不乐地往回走。几条大街上空无一人。
在经历了一场冬季暴雨和严寒之后,小镇仿佛凝固了,变成了冰城:道路、房屋和树木都被冰霜盖住了,一切好像变成玻璃状的物体,让人感觉不真实。
“我们只要度过了元旦第一个夜晚,那么一年就会过去的,”嘉尔卡说。
“夜晚已经来了,”尼侬说。
“看来,这一年不会好,”约尔卡说。
可是突然间……
他的确是突然间出现的。哪儿也不曾有过他,她们从来也没有见过他。是不是还要钻进地缝里去看看?不过,倒是有个人曾经在半道上挡过她们的路,她们试图绕过那个人,可那个人不让她们过去,于是她们气愤地同时抬起三个脑袋,就像一个长着三个头的蛇,只是在那时候她们才看清了他,一位长得很帅的飞行员……他站在她们面前,穿着一件夏装夹克,头戴夏季飞行头盔。他身材魁梧,相貌英俊,但醉醺醺的。
“姑娘们,”他说,“我这是在哪里?”
“在月球上,”嘉尔卡说。
“真美啊!”飞行员环顾了一下四周说道。
他一边欣赏一边用目光神往地扫了一遍月光下她们的小镇美景,她们也跟着他仔细地观看起来:四周一片静悄悄的,显得庄严肃穆。
之后,她们三人的目光又重新盯到那位似乎从天而降的帅飞行员身上。
“这是哪个城市,”飞行员问。
“怎么,小伙子,你头朝下从飞机上弹射出来了?”尼侬问。
“我把飞机停在一个广场上了,”飞行员摇摇头说,“机上的燃料用完了。”
“您从哪儿飞来的?”约尔卡彬彬有礼地问。
“从N城来的。”
“对了,”尼侬说,“到这里要飞三小时。”
“是四十分钟,”飞行员反驳说,“我驾驶的是歼击机。”
嘉尔卡拽了一下约尔卡的袖口。
“这位不是有精神病,就是躁狂者。少跟他废话,我们走人吧,”嘉尔卡在约尔卡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之后她就走了。约尔卡和尼侬也默默地跟着她快步离开了。



“姑娘们,你们去哪儿?”飞行员喊了她们一声,“可别丢下我啊!”
“我们可没有时间管你,”三位姑娘犹豫不决地站在自己芬兰式房子的篱笆门旁,好随时准备跑开,而嘉尔卡高声地说:
“父母会骂我们的,况且我们跟你这个醉鬼能干什么?”
嘉尔卡说话的时候,飞行员又慢慢地走到她们跟前,一下子把她们紧紧地搂到一起。
“我没有喝醉,”他身子晃晃悠悠地说,“我是在执行任务。我要找新年枞树……”
“瞧这个家伙怪里怪气的……我们跑吧!”尼侬尖叫了一声。她们挣脱开后就赶快向四处跑去,藏在自家房子的门后。
飞行员孤零零地站在一片陌生的、冰霜覆盖的房子中间,他喊着她们:
“在那里,在月球上!来人啊,我要冻僵了!”
嘉尔卡第一个忍不住了,她走出来说:
“我们去板棚吧,在那里过一夜,你不会冻僵的,有煤很暖和。”
她把飞行员放倒在一堆无烟煤上,随后她自己躺在他身边。
“来吧!”她说。
“干什么?”他不明白地问。
“难道你不懂吗?”嘉尔卡说完后就扑在他身上。“你是我的心肝……”
飞行员尽量躲闪着。
完事之后,嘉尔卡一本正经地说:
“现在你走吧。不然父亲看到要大发雷霆……”
飞行员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看了一眼天上的月亮。
“喂,男子汉,”尼侬走到篱笆门跟前,叫了他一声。
“什么事?”飞行员兴冲冲地问。
“你有什么可喝的东西吗?”
飞行员拿出来一个军用水壶。
“这是什么?是酒精吗?”尼侬高兴得说话都快换不过气来了,“快给倒上!”
他俩用壶盖喝酒,没有任何下酒菜。
“尼侬,你在哪里?”从门后传来了斯拉瓦睡意惺忪的声音。
“你快点走开……”尼侬对飞行员说,“我丈夫醒来了。”
约尔卡耐着性子站在凉台门旁边,仔细地听着。她看见飞行员先是去了嘉尔卡那里,后来又找了尼侬。当外面再没有什么动静了,她把门微微打开,看到飞行员坐在路灯下结冰的石阶上沉思。
“喂!”约尔卡叫了他一声。
飞行员没有回应。约尔卡怯生生地走到他跟前。
原来飞行员坐在那里睡着了。
她试着把他叫醒:
“您起来吧,您要冻僵了……”她反复地劝他起身。



飞行员只是打着呼噜,同时把她推开了。后来,他扑通一声倒在冰冷的路上,四仰八叉的,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就像一个被杀死的人。
“天啊,”约尔卡央求起来了,“他这样真的要冻死的。”
她用双臂把他搂住,拖着他在冰路上走。他的身子很沉,像全身灌了铅似的。要知道,曾经有过他们这些身体像铸了铅一样沉重、被铅弹击伤的男人被人从战场上抬下来的时候,她想着,抬他们下战场的是一些像她这样身体脆弱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就在她拖着他的时候,他对她嘟哝了几句,他说他与几位飞行员战友喝酒了,新年要到了,可是没有新年枞树,四周是一片荒原,他答应去搞新年枞树,于是就驾机飞出来了。她把他放在沙发上,他又睡着了。当她给他解开皮夹克扣子,摘掉飞行头盔后,她吃惊地呀了一声。他长得的确很帅,这个飞行员满头金头,高高的额头,嘴角轮廓刚毅,真像一个男子汉。他是一位白马王子,长得无可挑剔。
她久久地看着他。那时,她突然想到了她们见到他的一幕。她明白奇迹发生了,确切地说,奇迹正发生在此刻。她站起身来,走进另外一个房间,把儿子叫醒。
“我们家来客人了,”她神秘兮兮地对儿子说,并且让他穿好衣服。她神情严厉而庄重地把儿子领到飞行员躺在沙发上的那个房间,他正在沉睡。
“好儿子,”她说,“你瞧,谁来我们家了?”
儿子先是看了飞行员一眼,随后又看看妈妈,最后才用时断时续的声音问道:
“这是我的爸爸?”
她默默地点点头。奇迹发生了。明天整个大街小巷的人们都会议论萨沙的飞行员父亲归来这件事,他是在元旦晚上驾着歼击机来看自己儿子的。


快到黎明的时候,全家人都沉浸在梦乡,这时她再次试图把那位飞行员叫醒,可飞行员还是沉睡不醒。第二天早晨他醒来后一定会问,他这是在哪儿,他们是什么人,那么他就会让奇迹化为乌有。于是,她当下就想好了该怎么办。她拿起电话打给军队警备司令部,说:
“我抓住一个犯罪分子。请过来一趟。他劫持了一架飞机。”
让部队来人把睡梦中的飞行员抓获带走,随后他们会搞清事情真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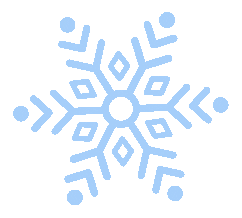

斯韦特兰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瓦西连科(Светлана Василенко)1956年生于距伏尔加格勒一百公里的一个军事小镇卡普斯金·雅尔。她1983年毕业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在文学院学习期间,她发表的短篇小说《在高鼻羚羊群后面》被评论界视为年度最佳小说。1988年,瓦西连科与拉里莎·瓦涅耶娃共同创办了《新亚马孙女人》女性作家小组,先后出版了几部女性小说和诗歌集,诸如《不记恶的女人》(1990)、《新亚马孙女人》和《喷沫的香槟》等等。
瓦西连科的主要作品有《如雷贯耳的名字》(1991)、《短篇小说集》(1997)、《战后》(1998)和《愚蠢的故事》(2005)等。她的小说已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深受俄罗斯国内外读者的喜爱并引起文学评论家们的注意和争论。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7年第3期,责任编辑: 孔霞蔚、李政文。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