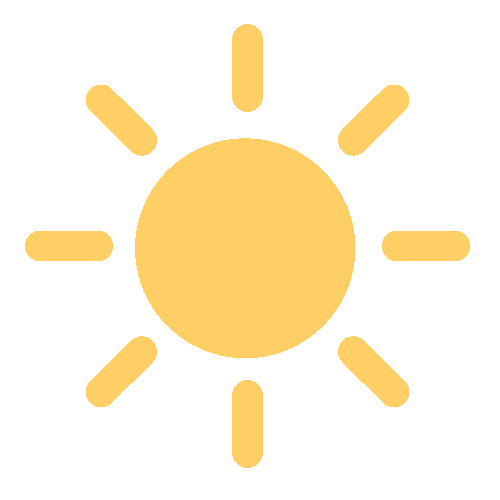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克•阿莫兹【法国】:一次神意裁判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这事是我干的,即使不是我亲手装的子弹,即使不是我的手扣了扳机。我得到了我隐隐约约渴望的东西:外面世界蜂拥来到——调查人员、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我们这个家庭小监狱。我隐隐约约最想得到的东西:消灭一个比我更有天赋的对手。剪除也许会成为艺术家的弟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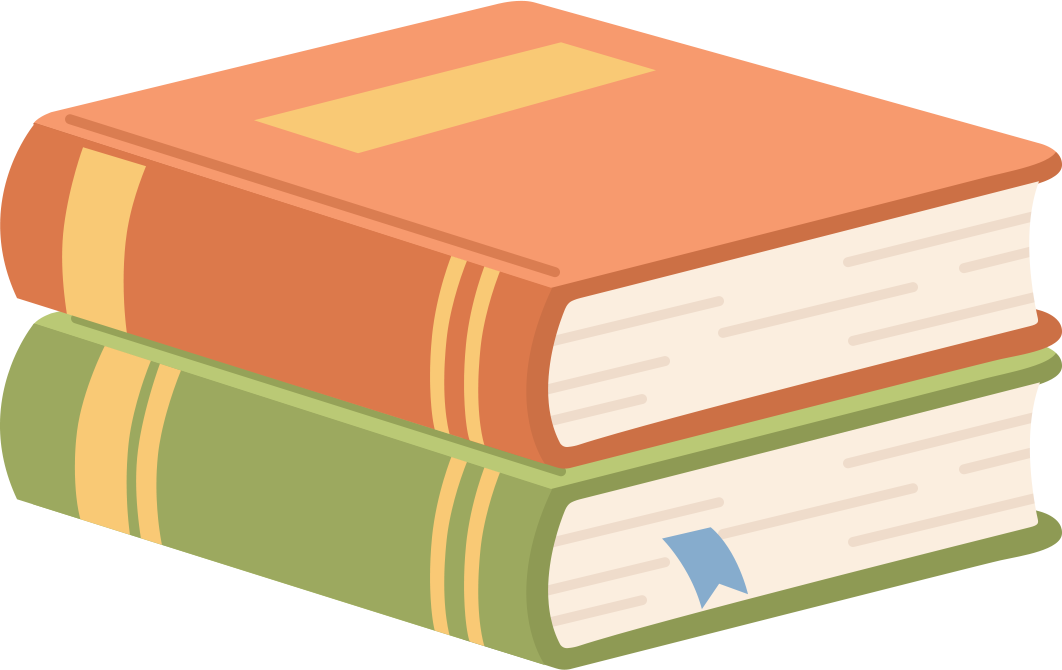
克萝德·阿莫兹作 徐家顺译
献给天文学大师
克里斯蒂安·古亚尔
顺致我的友谊
“整个的灵魂暴露给夏至的火把,
我敢正视你,惊人的一片光华
放出的公正,不怕你无情的利箭!”
保尔·瓦莱里《海滨墓园》
【这里借用卞之琳先生的译文,特此说明】

火车东站。玻璃天棚上方是浅灰色的天空,酷似暗淡的目光,人们绝不会以为是在八月份:在秋日凄凉、潮湿的空气中,人们禁不住浑身哆嗦。可是在站台上,人群异常拥挤,反倒觉不出寒冷。莫里斯不禁想起上前线的情景,激昂或顺从的士兵在原地踏步,人群推推搡搡,叫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喇叭筒里的命令及相反的命令声。一个农村小伙子,还没有睡醒,置身于稠密的人群之中,竭力寻找他的几个兄弟:他们像他一样应召入伍。他想在列车将他的兄弟们运往各自不同的战斗岗位之前,向他们道别;他伸长了瘦长的脖子,军大衣限制了他的行动;几个月后,人们将把他裹在这军大衣里埋葬他。莫里斯清楚地想象出这士兵目瞪口呆的样子,他觉得他和这士兵是一个人,虽然他们之间相距八十五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很长时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然而,站台上人头攒动,仿佛首都再次遭受大逃亡的威胁。人们只要能挤上车厢,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他们手脚并用,推搡弱者、胆怯者、过于斯文的人,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人们见到他们总是毕恭毕敬地退让,人们让道的话,别人就会毫不后悔地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只要有可能,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谁力大气粗,谁蛮横不讲理,谁会动嘴皮子,谁粗野,谁就是赢家,占座位是天经地义的事。
莫里斯和这些征服者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一个瘦弱的人,面色苍白,步履蹒跚,弯腰驼背,老态龙钟,尽管他只有三十岁。他之所以能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进来,那是因为他提前买了票、订了座位;试图引导人群从栅栏后面通过的工作人员见他拿出车票,连忙让他通过。他很快就登上挤满人群的列车,坐在一个过分激动的男孩旁边,这孩子不停地把防护眼镜罩在脸上。粉红色纸板镜框镶嵌着一片透光膜,形状像铝箔。这膜片略微像医生们为米歇尔制作的不透明的玻璃。它们也能反光:莫里斯每次转身面对着他弟弟时,都看见自己的面影在对方眼睛处浮动,总是很吃惊。
“把这东西给我!”孩子的妈妈在走道另一头叫嚷。“你会把它撕坏的!那就甭看太阳了。你知道,电视里是怎么说的么:你会变成瞎子的。”
“反正不会出太阳,”父亲喃喃地抱怨说。“什么也看不到。这坏天气……”
“天气预报说,中午有短暂的晴朗,”对面的一个女孩子插嘴说。“天气变化多端。某些运气好的人似乎可以利用雨后的晴空,而在几公里以外的另一些人,则头上乌云密布。一切都得看运气。”
“既然如此,”那人抱怨说,“我就放心了。运气,我从来都没有过。今天也没理由例外呀。”
年轻姑娘蜷缩在她情人怀里,一个脸色红润、金色胡须的小伙子。这节车厢的旅客都是恋人及全家出游的;莫里斯是少见的独行者。迪亚娜曾要求他陪她去拉芒什海峡,据说,那儿是观看日食的绝好地点——如果天公作美不下雨的话。他的拒绝伤了她的自尊,再次说他没心肝,阴险,不可捉摸,不懂爱情……最后她和一个“女朋友”离开了,也许是男朋友,一个潜在的情人。莫里斯朝相反方向走了:他朝东走,去兰斯,他们两人之间地理位置上的距离和误解的深度相似。这误解他要负完全责任,他意识到了。他不想让迪亚娜发现他与十九年前秋天发生的事件相关的任何事情:她会蔑视他,瞧不起他,或者更糟,会可怜他。如果她不知道一切,今天他更不能留她在自己身边:她无忧无虑的性格会消除他的勇气。


莫里斯将手放在自己的眼皮上;他从指缝里看一闪而过的景色。发白的天空上,涂上了一抹浅色的条痕——青色,灰色,棕色。他的这个想法来自于一幅画,表现出滞重的天空:不停地逝去的线条,将目光引向苍白的天际,然而那却是一种闭塞的感觉……
莫里斯摇头。他还是个孩子时,梦想成为画家:他用私自拿来的不多的报纸,孜孜不倦地拓树木、花草、房屋。拓下的图画很规矩,缺少激情,没有创意。很明显,小弟米歇尔是个天才。从小时候起,他就将纸、茎、水果挤压在纸板上,他用这种简陋的材料创造出奇形怪状又极其和谐的作品。他像有幻觉的人那样顽强地工作,努力地伸舌头。对马克的嘲笑视而不见,马克比米歇尔大一岁。而大哥莫里斯,则年长两岁,他掩饰不住他的妒忌,梦想离开,梦想自由,却一直得不到。
莫里斯,马克,米歇尔……三兄弟……他们的父母亲名叫马蒂约及莫妮克,他们的绰号是三M:在他们心中,同一个开头字母有相同的价值,如同一个秘密口令,一个团体的标志。因为马蒂约确实想在上阿尔代什的农庄建立一个团体,他试图在这里艰难地回归于土地。他借口躲避“制度”,让家人生活在以他为一家之长的圈子里;管束他的家人,不让他们与外界联系。
没有电视,不许去电影院看电影;他们从来没有假期,不与任何人来往。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从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思潮中记住了适用于他的东西,从他的信条中删去了欢迎、团结一致、集体生活这些字眼……三个男孩是作为野蛮人被抚养成人的,像是与野兽为伍,半裸身子,污秽,粗野,凡是难为情的动作,任何亲密的表示会被视为资产阶级虚伪的迹象受到批评。禁止关门,尤其是洗手间或水房,马蒂约挑衅地在这些房间周围转悠:“你为什么插上门闩?你害臊么?为什么动物不藏起来呢!”
事无巨细,一切均在他的掌控中。身体或良心都不允许有隐蔽的角落。三个男孩都到入学年龄了。马蒂约声称要亲自教育他们,让他们一周一周地旷课,女老师慑于他挑衅的语言——他甚至会毫不迟疑地举起猎枪,有机会时,她装作相信他们患咽炎、感冒及其他疾病——此外,当这三兄弟缺课时,课堂里井然有序……马蒂约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学校是监狱、兵营、生产奴隶的地方。莫里斯很久以后才明白,实际上,他父亲冠冕堂皇的言论掩盖了他自私的专横、暴虐:父亲不愿意看见家庭与外界发生联系,他担心会因此失去他的权威。
“兰斯到了!”
火车还没有完全停稳,旅客们都站起来了,准备向外冲。好斗成性,这种战争氛围……莫里斯一直从容镇定,那孩子的父亲学他的样子,重复那些悲观的论调:
“我真不该糟蹋这一天假期。天上的云一时半会儿不会散去:看起来好像要下雨。当人倒霉时……”
站台上的人群比巴黎东站的人群还要多,阶梯上及地下通道中挤满了人,雷穆瓦一家显然不大习惯;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办事员及胸前挂着市政服务者小牌的年轻人试图用强有力的手势疏导人流。
大部分旅客朝大教堂走去,按预定计划,教堂前面有一个露天音乐会:日食结束时,杰茜·诺曼【杰·诺曼(1945— ),美国女歌唱家,出演过歌剧《阿依达》中的女主角】将唱一曲来迎接光明回到大地。莫里斯一点儿不想加入到人群中去;他在地图上发现,埃纳运河对岸有一个公园。那里也许找不到孤寂,但至少可以找到些许平静。他大步流星地朝那个方向走,一边看沿途张贴的大量招贴画,林荫大道两旁的这些招贴画炫耀着城区的魅力。他觉得,著名的微笑天使【微笑天使是兰斯大教堂最著名的一座雕塑】的小嘴上有一丝讽刺的意味,承载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你和我,我们约会的日子到了,时间临近了!”
十二时二十五分将有日全食。“正义的正午,”迪亚娜喜欢重复说,一边引用一首谈到太阳及坟墓的诗。今天正午的正义女神正在临近。
兰斯……去年,莫里斯和迪亚娜一起游历过这座城市。她是历史学家;她帮助他补足知识方面的缺陷。她对他讲述奢靡的圣事仪式;她还提到兴旺发达的巨商富贾——呢绒商、酒商——他们的影响遍及城乡。今天莫里斯又想起这些话,他眼前浮现出一个富庶城市的形象,以及相应的秩序、工作、虔诚、公平。辛劳必受奖,过时必受罚。一个谴责他的城市。
迪亚娜拖他去了教堂旁边的塔乌宫。“你不能错过这座宫殿,咳!这儿有宝贝,美妙的挂毯……”他很不乐意地跟着她走:他父亲剥夺了他应当受到的教育,使他有了根深蒂固的偏见,照他看,博物馆都是可鄙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自命不凡的炫耀。但是,在这庄严建筑的二楼,他受到了震动。在他面前,一尊女雕像,两个胳膊只剩下残肢,被岁月侵蚀,被污染腐蚀——然而,这悲惨的景象掩盖不住它的美,它高傲的姿态,它细致的腰身,它腹部的曲线,它忧郁地撇嘴。石头眼睛蒙上了一条带子。
“犹太教,”迪亚娜没注意到他同伴很激动,眼睛盯着导游手册解释说,“基督教徒喜欢将面对得胜教会的犹太教表现为屈辱的神态。你看,它戴的冠冕滑落到一边:它被打败了,它承认失败了。”
犹太教的苦难引不起莫里斯的兴趣。浮现在他眼前的是米歇尔。是米歇尔的不幸。也是他全家的不幸。他们家人人都有错。尤其是他有错。他抓住迪亚娜的胳膊,不顾她的反对,将她拉到外边:“你怎么了?你疯了么?”他必须尽快逃跑。
很久以来,他一直在逃避。从将近十九年前十月的一个星期六起,他就在不停地躲藏。那天像今天一样,天空堆满了乌云,有时候乌云被撕开,射出暴风雨前的一缕阳光。起先,他躲避到谎言之中。当调查人员宣布他是唯一一个不应受责备的人时,他没有纠正他们。谎言,沉默,思想上逃避。后来,几年以后,真正的逃学,苦役。去收容所,街头巷尾,人行道,瞎对付,后来逐渐安定下来,直到与迪亚娜邂逅为止,她给他找到一份照相馆的工作,她帮他重新建立起一切,却并不知道……
天色开始暗下来;城市的路灯刚刚亮起来。莫里斯凭着地图找到横跨运河的一座桥,然后找到一条小河。他很快找到公园的入口,他决定在公园里看日食。他不是唯一有这主意的人。有一队激动的人群在小径上走来走去。很多人在草地上席地而坐:他们随处架立起一些支架,用来固定望远镜、摄影机、照相机,镜头上都装有可观的遮光罩。观看日食的人带来一篮子一篮子的肉食:他们在草地上铺开毯子和桌布。人们打开橘子汽水或可口可乐。有些人已经在喝酒,高谈阔论,抚掌大笑。
愉快的节日气氛……月亮恐怕已经开始在吞噬太阳的边缘:当云撕开一条缝时,哪怕是一丝小缝,所有的人都抬起头,用防护镜遮住眼睛。但是,没有人看出什么名堂:失望的抱怨往往多于惊奇的叫声。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光线明显地越来越弱。现在还能看清东西,但是天色越来越暗淡了:真像是一个冬日的黄昏。穿着夏装的莫里斯瑟缩发抖。他没想到要多穿点衣服。报纸倒是预告了,日食之际会突然降温。但是他一旦上路之后,自然就不太操心舒适不舒适的事情了。
公园中央有一个水塘,水塘周边有一些老树。他离开小径,朝那个方向走去。潮湿的草地打湿了他的裤脚——已经下露水了。
他走到岸边,面对水塘坐下,背靠在柳树干上。树叶在晚风中飕飕作响——正午的日食好像傍晚……随着天色暗下来,看日食的人越来越激动,一个女孩子大声抱怨说冷;一个小伙子提议给她暖和:“你知道怎么暖和吗,宝贝?”放荡的笑声。另一个人说:“你要我的打火机吗?”“不用!你就是我的火焰!”
有一家人坐在几米远的水边。莫里斯透过树枝空隙观察这一家人,他的心情很复杂,仿佛是一个有窥视癖的人,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在室外透过窗帘偷看明亮的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年龄大约在十五岁左右,穿一条镶边饰的裙子,忸怩作态,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眼神很淘气,他们的父亲明显地以这些孩子为骄傲,每次他的目光落在孩子们身上时,便掩饰不住自负的微笑,母亲安详,温柔。毫无疑问,一个幸福的家庭。很明显,他们之间十分默契。他们相互叫小名,相互抚摸,低声地笑,只有他们才能懂得笑什么。莫里斯看见他们兴高采烈,觉得心里难受,他自己的童年之后这么多年,仿佛这些美少年偷了他——以及马克和米歇尔——什么东西似的……那一期间,在他们兄弟之间没有温情,和邻居之间的感情联系更加缺乏;只有敌对,由于父亲的执拗及他们兄弟幽闭在孤寂之中,这种敌对状况加剧到无法缓解的地步。野兽为了争夺狭小的地盘进行殊死的搏斗。马克的武器是挑衅和暴力,莫里斯的武器是阴谋诡计、谎言。米歇尔虽然年纪小,却是最强有力的:他具有——想必是从马蒂约那里遗传的——坚定的决心,如同那些确切知道自己的价值、对如何行动心里有数的人那样。至于莫妮克,这男性家庭里唯一的女人,她不算数,一个胆小、平凡的人,“绝对未成熟,消极被动,”当马蒂约控制的密不透风的家庭秘密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调查人员这样说。
由于我的过失……多亏我……解放采取了摧毁性爆炸的形式。我能有别的办法吗?我周围及我身上有那么多仇恨。
幸福家庭的母亲用塑料平底大口杯给家人分发热气腾腾的饮料。热巧克力的香味飘到莫里斯跟前。他突然觉得饥肠辘辘。他身子下面的湿草地弄湿了他的长裤,湿布贴在他的皮肤上。他真想得到一杯提神的热饮料,尤其是一份亲情。
现在,黑暗降临得越来越快了。树林中,鸟儿惊恐不安,叽叽喳喳地叫,就像入夜时分它们习惯的那样。一只鸫唱起了小夜曲,这时候,这歌声使人肝肠寸断,俨然向光明永诀。即使是身穿镶边饰裙子的、活泼的金发女孩,手指头抓住她那杯巧克力,身子也在发抖:
“我害怕,爸爸,我真的有些害怕……”
她是在半开玩笑。她母亲给她肩膀上加了一条披肩。
“你会着凉的,宝贝。”
突然,水溅起来的声音使大伙儿吃了一惊。鱼儿成群地浮到水面;现在天几乎完全黑了,有些鱼儿甚至跳出水面。一只夜鸟飞过,飞得很低,它的翅膀在莫里斯跟前扇动,他感觉到翅膀就在离他脸几米的地方沉重地扇动。


马蒂约恨猫头鹰:他说要像从前一样,把它活活钉死在谷仓的门上。这是莫里斯的一件恐怖的杰作,一天他逮住一只猫头鹰:他想象它临终挣扎了几个小时,翅膀撕裂,爪子不停地抓木头。至于乌鸦及小嘴乌鸦,它们是人们憎恨的目标:仿佛它们落到土地上,是来向他挑衅的。
在这种情况下,莫里斯在那个十月的星期六,如同过去的星期六一样,带着他的步枪走了。他带回来五只乌鸦,莫妮克做了一顿啃不动的炖肉——按马蒂约的说法是美味佳肴:免费的营养,还有什么比吞食敌人更有滋味呢?
马蒂约回到家里时,莫里斯在车库里。一定是他把血淋淋的乌鸦运到厨房里的,因为他禁不住厌恶地打哆嗦,他的刚强应当受到刻薄的嘲笑。他在父亲的讽刺面前低下脑袋时发现,父亲在气愤中,把枪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后,忘记了完成例行的举动:拉开滑槽,推出子弹,检查子弹匣里是不是空的……
“啊!”
仿佛心窝挨了一下,突然的早搏使身子抽动起来,无法恢复正常的呼吸。色调层次变化,黑暗缓慢地渗透,倏地终止:一瞬间,世界突然跌入黑暗之中,如同吹灭了火焰,余下的光线不到一秒钟就被吞噬掉了。人群发出呻吟声,本能的、集体的呻吟。
然后是寂静。这儿,那儿,神经质的笑声,猫头鹰的叫声,鱼儿的水中跳跃的声音,青蛙的叫声,这些声音打破了这寂静。一个女孩用不大自信的声音说:
“如果天气晴朗的话,人们会看见星星,像在半夜一样……”
“我看见一颗星星,在那儿,你看,在两片乌云之间……仿佛是织女星……金星……这星星多么明亮……”
莫里斯白白地寻找星星。漆黑一片,十分压抑。尽管人们知道,光明终将回到人间,人们还是驱赶不掉世界末日的印象……一种莫名的恐惧与激动沁入心中,使人难以忍受。
将近十九年前,在爆炸之前的几天里面,他有同样的感觉。莫里斯不停地想那支子弹上膛的枪,在车库里;他反复说他父亲很快又要去打猎,他这次回来后,就会把子弹退出来……这段时间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马克常玩弄这支枪。他用这支枪威胁米歇尔,远远超出玩笑的范围,对他来说,超出了发泄心中愤怒的方式。马克喜欢爬上那棵老梨树,从上面向米歇尔瞄准,当米歇尔在草地上走过来时:
“你要是再向前走一步,我就叫你的脑袋开花!”
“我就要走!”米歇尔笑着说。一段时间以来,他不再装出害怕的样子。
通常,空房间的砰砰声……通常……
这事是我干的,即使不是我亲手装的子弹,即使不是我的手扣了扳机。我得到了我隐隐约约渴望的东西:外面世界蜂拥来到——调查人员、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我们这个家庭小监狱。我隐隐约约最想得到的东西:消灭一个比我更有天赋的对手。剪除也许会成为艺术家的弟弟。
媒体预报说,日全食历时两分十五秒。这太短了,然而,这时间会延长……如果媒体预报错了呢?如果……
突然,就像光线被突然吞噬掉一样,光线又回来了,虽然很微弱、虚弱,但是,毫无疑问,光线确实在眼前,黑夜让位了,银色反射光沉浸着草坪及湖泊……光线回来了……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强大的幸福,本能的,看生孩子时会体验到的那种幸福……一种复苏的、坚定的信念:人们以为死去的东西复活过来,有了第二次机遇,一切可以重新开始。
莫里斯周围的人群自发地鼓起掌来。人们相互拥抱;香槟酒塞子嘭地开启了。金发女孩搂住她的父母亲,疯狂地亲他们的脸。在城市里,运河那一边,大教堂灯火通明:音乐开始演奏,回声一直传到这儿,女歌唱家热情的嗓音似乎与歌唱黎明的乌鸫的颤音相呼应。莫里斯用手摸脸颊,泪痕满面。他使劲擦脸。不要被舒适的环境软化了,正在出现的色彩,多么赏心悦目……


这会儿,太阳几乎完全被阴影遮挡不再刺眼时,应该行动。他想起今天早晨在广播里听见医生的忠告:
“用适合的眼镜保护您的眼睛。尤其不要直接用光学仪器看太阳。视网膜灼伤不会有疼痛感,您的神经系统不会通知您如何预防灼伤导致的不可逆转的损伤。”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他从口袋里取出带在身上的望远镜,坚决地罩在眼睛上,对准苍白的天际,朝阳将从这里喷薄而出。云层仿佛变得稀薄了,有的地方撕裂开来,远远看见一片片淡蓝色的云。现在是由变幻的天空做出决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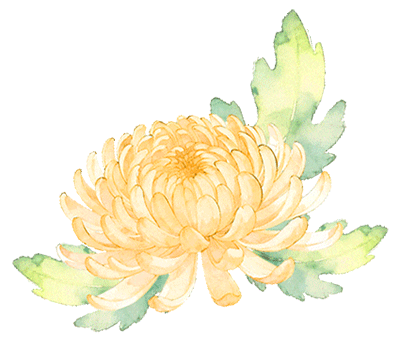
克萝德·阿莫兹(Claude Amoz)是当代法国女作家。她已经发表的长篇小说有《墓穴》(1997,获得墨血奖)、《乌合之众》(1998)、《旧罪》(1999)和《过火林》(2002)等。阿莫兹的短篇小说多散见于一些杂志和合集。这里介绍的三篇小说选自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苦根》(Racines amères,2002,奈斯蒂弗根出版社,“短篇小说丛书”之一)。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7年第2期,责任编辑:余中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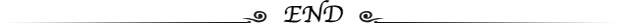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