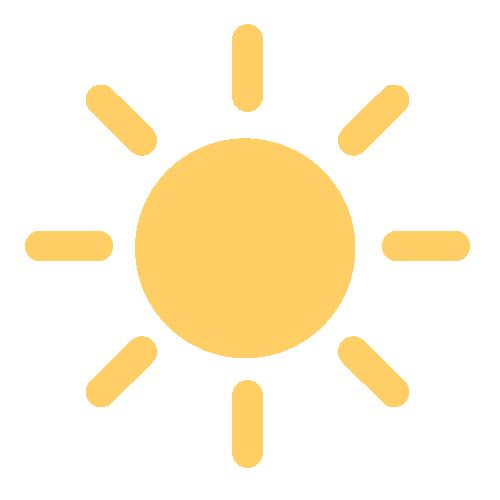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陈士宇:镜中泡沫——读尼克•华金《五月节前夜》有感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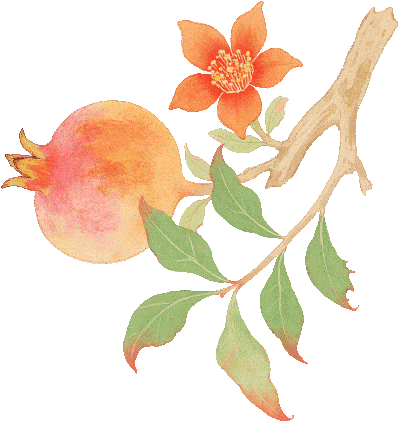
这面镜子,最终照见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也并非想象中的美好爱情,而是少男少女对美好爱情的想象与回归婚姻生活的日常琐碎之间的碰撞以及美好泡沫的幻灭。巴多伊与阿格达,这对在年轻时都对美好爱情憧憬万分的男女,最终在日常的婚姻生活中都活成了对方和自己当初最厌恶的模样。
镜中泡沫:
读尼克·华金《五月节前夜》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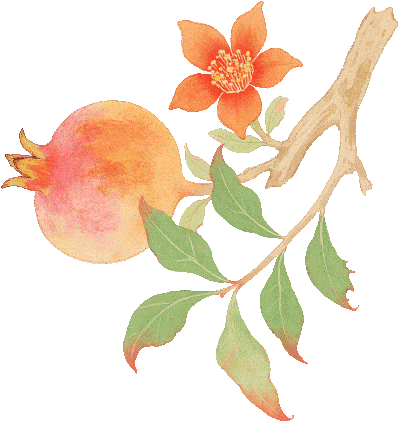
陈士宇
尼克·华金的《五月节前夜》的核心意象是一面贯穿全文的古镜,它不仅仅是宅邸的一件装饰品,更是穿越时光的载体。在1847年喧闹的舞会后、1890年死寂的宅邸中反复开启。整篇故事由阿格达对1847年舞会的回忆展开。年轻叛逆的阿格达不顾老阿纳斯塔西娅的劝诫,在神秘午夜手持火烛走向镜前,渴望像传说中一样透过镜子预见未来的真命天子时,爱情和婚姻便悄然展开了两者的对垒。镜子中出现的正是代表着美好爱情的纨绔子弟巴多伊·蒙提亚。这场充满戏剧性的初遇在他轻佻的言语和阿格达的抵抗中拉开序幕。巴多伊的轻佻调笑如火星溅入干草,瞬间点燃了阿格达野性未驯的反抗。她的激烈撕咬,是防御,亦是某种不自知的吸引与挑衅。在巴多伊的凝视下,阿格达的一切特质都被情欲的目光所捕获与放大:她生气时“肤色多美”,烛光在裸露肩头勾勒出“纤柔的绒毛”,脖颈扭动时那份“傲慢劲儿”,直至丝滑长袍下隐约起伏的“紧实的双乳”——这一切原始的生命力,使她在巴多伊眼中瞬间幻化为不可抗拒的“尤物”。但在阿格达的视角里,巴多伊是个从欧洲浪荡回来的纨绔子弟,阿格达只想逃离并咬了巴多伊一口。
我们可以看到,当叙事视角转回向现实世界时,认清了美好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差距的年迈阿格达是这样对女儿说的:“我看见了魔鬼。”并以此劝诫女儿:“这就是为什么好女孩不要轻易地照镜子,除非有妈妈的许可。宝贝,你必须戒掉这个坏习惯,不要路过一面镜子就孤芳自赏,否则有一天你会看见一些吓人的东西。”透过阿格达的话语,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熟悉的味道:这不正是老阿纳斯塔西娅对年轻叛逆的阿格达的劝告吗?旧事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传播,一遍又一遍的劝告在不断提醒着年轻人提防婚姻的陷阱,正视想象中的美好爱情与现实婚姻生活的差别。
叙事时间跳转至1890年迟暮的宅邸:同一面镜子前,垂垂老矣的堂·巴多伊向他的孙子——一个掉进了美好传说的陷阱进而渴望爱情的可怜少年——讲述镜中“女巫”的恐怖传说。那是一个魅惑人、折磨人、吃人心喝人血的可怖女巫。这个女巫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妻子阿格达,更是婚姻生活的一种具象化。这个可怕女巫的形象就是巴多伊内心的创伤和恐惧的投影,但当孙子提及外婆阿格达同样在这面镜中见到了“魔鬼”并可能因此早逝时,老人瞬间被记忆的洪流吞没,陷进了回忆之中。镜中那个在烛火下明艳照人的少女阿格达,与现实中最终成为“一个形容枯槁、呼哧呼哧的肺痨病人,用刻毒的语言骂个没完”的妻子形象形成残酷对比。此处强烈的对比难道不正是美好爱情与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吗?爱情的泡沫经不起敲打,轻轻一碰便碎成婚姻的一地鸡毛。女巫不是女巫,不过是爱情破碎后面对婚姻的不甘和恐惧;魔鬼不是魔鬼,是婚姻生活戳破爱情泡沫的空虚。女巫和魔鬼的对比,阿格达和巴多伊的改变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曾被阿格达指认为魔鬼的巴多伊在经历了婚姻的考验后,不也在年迈时将妻子比作吞噬人心的女巫吗?
菲律宾作家尼克·华金用手术刀般的笔触精准切中了现实生活中美好爱情与婚姻的矛盾。老阿纳斯塔西娅和老阿格达所代表的,正是经历了现实婚姻后想用自身经历劝诫年轻人的婚姻忠告,而年轻的阿格达和她的后代就是那尚未经历婚姻的蛊惑爱语。过来人企图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警示年轻人正视爱情与婚姻的差别,但年轻人却依然沉溺于美好爱情的泡沫中。


这面镜子,最终照见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也并非想象中的美好爱情,而是少男少女对美好爱情的想象与回归婚姻生活的日常琐碎之间的碰撞以及美好泡沫的幻灭。巴多伊与阿格达,这对在年轻时都对美好爱情憧憬万分的男女,最终在日常的婚姻生活中都活成了对方和自己当初最厌恶的模样。当巡夜兵“巡——夜——兵!现在是十——二——点!”的呼喊穿越时空同时在1847年和1890年响彻天地时,老人耳边与记忆中的青春喧嚣重叠,泪水夺眶而出——这泪水不仅为逝去的爱情与生命而流,更是为一代人在爱情与婚姻血淋淋的对比中无处安放的自我而恸哭。
在文章中随处可见的对比正是尼克·华金对爱情和婚姻的巧妙解构,我们不禁反问:我们所渴望的究竟是什么,在饱受婚姻折磨后我们失去的仅仅只是爱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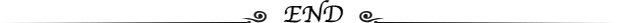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