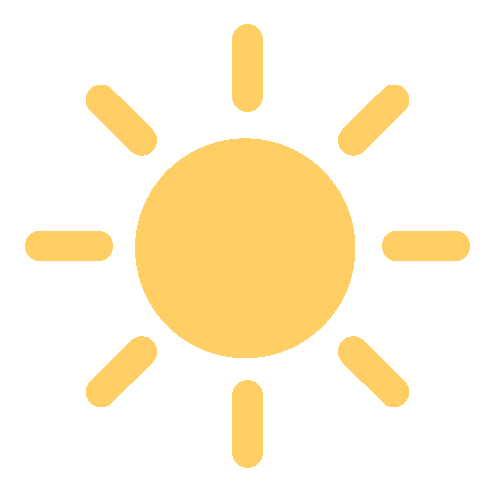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多•诺盖【法国】:失败人生经营指南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总之,真正失败的生活,无论如何都不应包含复仇或骄傲的蛀虫——或者任何一种让失败的人生变成命运的价值。它不应该得到辩护或救赎;它必须保持暗淡无光、平平无奇、无可救药。如果它能给人满足,那也只能是一种微不足道、难以察觉、毫无反响的满足,只能随失败者一同进入坟墓。



多米尼克·诺盖作 孟瑶译
显然,评判人生的难度在于标准繁多。哪怕在同一个评价体系内,结论也可以大相径庭。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观点,下一代或者说每一代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如果要在虚构作品中找个例子,那就找唐·乔万尼【唐·乔万尼是由莫扎特谱曲、达·蓬特编剧的两幕意大利语歌剧《唐·乔万尼》的主人公】吧?这家伙结局很惨,人们说他是性无能,可能有早泄的毛病。但他勾引了两千零二十四个小妞(六百三十个意大利的,一百个法国的,西班牙的“已经一千零三个了”【原文为意大利语,出自《唐·乔万尼》第1幕第5场】),这可不容易!还有拉瓦亚克【让-弗朗索瓦·拉瓦亚克(1577—1610),刺杀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凶手】——那个刺杀好王亨利的凶手,他的人生够失败了吧?确实,一六一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格列夫广场惨死。开胃小酒——人们把他刺杀国王的手臂放进硫磺火焰中,又用钳子拔掉他的双乳;开胃小菜——人们把热蜡淋到他的伤口上,又在手臂和腿部浇上大量熔铅和热油;主菜是大名鼎鼎的四马分尸,分步骤进行。首先,将四匹马分别拴在他的四肢上,再鞭打这些马,马跑得太慢,好心的老百姓便拽着绳子加把劲;稍事休息后,人们拷问受刑者,逼他供出同伙的名字,他什么都没说;于是继续分尸,由于四肢迟迟不肯脱离躯干,人们不得不用棍棒刀剑助力;最后,作为奶酪和甜品,大家把他的四肢取下来,分别运到巴黎不同的街区,声势浩大地焚烧。这一顿饭口味很重,但也正因如此才能流传至今。让-弗朗索瓦·拉瓦亚克不仅成功完成了任务,帮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还有一些法国贵族)搞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还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这是他从前做贴身男仆和学校老师时不可能获得的。
还有拿破仑,他的人生真的失败吗?也许如此,他没能实现与亚历山大比肩的梦想,没能踏足亚洲,也没能攻占美洲。他经历过失败,体会过绝望。他在一七九九年曾写道:“荣耀乏味无比。我才二十九岁,就已经走到尽头……我为什么不去死?”十六年后,他留下了一个衰弱困顿的国家。而他在圣赫勒拿岛的结局,无论有没有蟑螂【语出法国雕塑家让-路易·富尔(1931—2022)的雕塑作品《圣赫勒拿岛,1818年2月5日星期四:拿破仑在观察蟑螂》。——原注】,有没有英国砒霜,都不是一件乐事。尽管如此,夏多布里昂虽非他的好友,却说他是“行动的诗人,战争的天才,不知疲倦、精明老练的管理者和勤奋理智的立法者”,他“站在全新世界的入口,如同世俗或神圣故事里描绘的原初社会的巨人,在大洪水后出现”【语出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墓中回忆录》】。真了不起!


很难过上真正失败的生活——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外人而言,总能找到理由认为生活有成功的地方。总有一些“毕竟”“总之”“确实,但另一方面”让天平偏向正面的评价。屡屡失败?确实,但人是多么正直!一生斤斤计较、招人憎恶、作恶多端?不错,但能免遭遗忘。让人不能彻底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这样那样令人作呕的积极价值(美德、善良、幸运、智慧),总有可能从内部支撑起表面破败的生活;另一方面,正如斯塔尔夫人的名言所说,荣誉是“幸福光鲜的丧服”,能抚慰最大的困厄,点亮最惨淡的人生。我们可以称前者为贞节寡妇综合征,后者为黑若斯达特斯【黑若斯达特斯(?—公元前356年)是一个古希腊青年,为了让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于公元前356年7月21日纵火烧毁了位于土耳其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他放火烧毁了阿耳忒弥斯神庙)综合征:默默承受女士和善做营销先生。更不用说那些先后或者同时结合两者的人们,他们获得了双重补偿,处境便更加不妙——真正失败的人生不应该有任何补偿,没有任何救命稻草。
当然,这并不等同于一种彻底无望的生活。因为——我们正准备下个定义——失败的生活首先是一种不幸的生活,这是自然,但不能过于不幸。可以适度不幸,只要持续不断就行。我们可以借用音乐术语,称之为通奏低音般的不幸。也就是说,在生命的音乐中,这种烦人的背景音嗡嗡作响,萦绕心头,破坏兴致。就像杜·德芳夫人【指杜·德芳侯爵夫人(1696—1780),法国著名沙龙女主人,艺术赞助人,也是著名的书信作家】描述的烦闷——像一只绦虫,啃噬本能使我们幸福的一切事物。总之,就像我们的意大利朋友说的“蛋疼”【原文为意大利语un rompimento di coglioni,字面意义为打碎睾丸,表示让人厌烦】,一堆烦心事,烦恼无休无止,虽然足以让人内心煎熬、胃部溃疡,但不能过于频繁或强烈。否则我们就要换套说辞,从平庸的失败叙事转入更高层次的殉道或是悲剧。
如此一来,就前功尽弃了。这是因为如果你拥有悲剧英雄的命运,你的人生便会引人注目,而引人注目与失败的人生不可兼得。一旦如此,你会暗暗滋生骄傲,甚至快感,也会招致外人的嫉妒,这些都是寻常成功人生的标配。因此,只失败还不够,还不能过分张扬!
想来确实如此——过多的不幸便扼杀了不幸。悲剧英雄最终会笑对命运接连的打击(我们也会跟着他笑),殉道者则沉醉于自己分泌的内啡肽,从痛苦中获得快感。而失败与欢笑和享乐并不合拍。真正的失败者会陷于沮丧和晦暗之中,毫无慰藉与乐趣可言。他和堂吉诃德一样,是一位苦相骑士。
不过,塞万提斯的“英雄/主人公”【法语中héros既指英雄,也指虚构作品的主人公,此处为一语双关】至少从不幸的遭遇中为自己,也为全人类汲取了教训,甚至获得了好处。如此说来,他不是真正的失败者,没有理解失败的基本规则——不能只是不幸,这种不幸还必须毫无意义。因为有些苦难富于教益——或是暂时的苦难,能带来极大的幸福和成功;或是永久的苦难,却通过幽默或文采的炼金术,生发出一部好小说、一首诗、一曲悲伤的歌;甚至是一个简单滑稽的故事,能在宴会的尾声或咖啡厅的桌前活跃气氛。总之,大众的智慧总能对这类遭遇作出评点:坏事不一定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失败的人生可以承受一些微不足道、转瞬即逝的小幸福,总好过那些可恶的大痛苦。
总之,真正失败的生活,无论如何都不应包含复仇或骄傲的蛀虫——或者任何一种让失败的人生变成命运的价值。它不应该得到辩护或救赎;它必须保持暗淡无光、平平无奇、无可救药。如果它能给人满足,那也只能是一种微不足道、难以察觉、毫无反响的满足,只能随失败者一同进入坟墓。
当然,这是最难办的!因为——读者,我们再说一遍——留下痕迹的愿望堪称人类最大的怪癖。它近乎以主体的方式根植于最孱弱的身体和最平庸的心灵,是我们追求失败人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为了幸福生活”而“低调行事”的人已经不多,若这样做是为了不幸福的生活,更是少之又少!我当然是在谈论那些有选择的人。因为这世上到处都是没有机会选择的受苦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加以考虑。在这不计其数的受苦人当中,一些人长期挨饿,流离失所,在无休止的内战中挣扎,却得不到媒体的关注。还有夭折的孩子、智力障碍者、各种各样的残疾人和昏迷不醒的人。面对这样的生活,我们甚至不能谈论失败。要想失败,首先需要有一个没达到的目标,而且至少能意识到自己的失败。然而,这些悲惨的生命没有目标,也无知无觉。他们只能盲目地漂泊,生活水平低于我们所说的SMR(最低失败标准)。让他们继续惨淡的人生吧,我们只谈论那些勉强在标准之上的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无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至死都不放弃追求荣耀的幻梦。
其中一人,从十六岁起开始收集酒瓶底或猫王的荧光画像,想要郑重地传给曾孙们(这并不妨碍曾孙们把他当作特大号傻瓜)。另一个人用小刀在一棵梧桐树上(这棵树幸运地逃过“愤怒车手”【“愤怒车手”指法国愤怒车手联合会成员。2001年,一名摩托车手撞到路旁的梧桐树后死亡,愤怒的摩托车手们用电锯砍伐上百棵梧桐树以示复仇】的砍伐)刻下自己的名字,他的儿子没这么粗野,却更有雄心:在巴黎地铁的车窗上乱涂乱画,仿佛得了帕金森病的先天愚病人。第三个人花费大量时间踏遍法国的偏远角落查阅档案,试图证明自己是亨利三世某个宠儿的侄孙的家庭教师的堂兄的私生子,他的本名应是科尓维·德·普吕士·德·默恩-马东·德·薄那和【此处应为文字游戏。其中,“科尓维·德·普吕士”的原文Corvay de Plusche的发音接近Corvée de pluches,意为“削土豆皮的脏活儿”;“默恩-马东·德·薄那和”的原文为MeungMathunde Bonneure,其发音近似于Mon matin de bonheur,意为“我的幸福早晨”】。
这个女人将所有的周末、节假日和调休假都用于打字,像疯子一样敲击着电脑键盘,长篇大论地写下弃妇或吸食海洛因成瘾的前嬉皮士的悲叹,然后四处奔走,把五百三十六页手稿寄给二十个出版社,甚至亲自送到出版社前台。那个男人用蹩脚的诗歌和烂俗的音乐创作出颇具“异域风情”的爪哇舞曲,又用簧风琴给自己伴奏,录制成磁带,虔诚地递交给SACEM【法国“音乐作者、作曲者、出版者协会”的缩写】。
尽管如此,人们早已得到警告要远离荣誉!正如夏多布里昂子爵曾在如今伊夫林省【法国法兰西岛大区所辖省份】的思考:“朗布依埃【法国法兰西岛大区伊夫林省省会】,这不光彩的隐退之地,最伟大的家族和人物都在此地消逝;在这不幸的所在,弗朗索瓦一世告别了人世;亨利三世从街垒中逃出后,曾全副武装在此地过夜;路易十六也在这里留下了他的踪影!如果他们只是朗布依埃的牧人,该会多么幸福!”【语出夏多布里昂的散文《墓中回忆录》】
确实如此,名声只会招致麻烦。维克多·雨果写道:“荣耀就像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的床;外表光鲜华美,内里却爬满臭虫。”【语出维克多·雨果的诗歌《辱骂者》】此外,名声往往待人不公,且毫无意义。待人不公:黑若斯达特斯在公元前三五六年烧毁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靠着愚蠢历史学家(塞奥彭普斯【塞奥彭普斯(公元前380年—公元前31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辞学家】和斯特拉波【斯特拉波(公元前63年—公元24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宣传,他竟比建造神庙的人更出名!毫无意义:正如雇佣兵队长贝维拉夸【或指乔瓦尼·巴蒂斯塔·贝维拉夸,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名雇佣兵队长】的坟墓上所刻,荣耀从来都是一种二次死亡【原文为拉丁文】,也就是完全遗忘之前的片刻缓刑。一切终会消逝,大陆会漂移,山峰会遭侵蚀,大地会震动,河流会冲出河床,亚历山大图书馆会着火,画作会剥落,雕像会磨损,胶片会变色,录像会失真,报纸会停刊,法国文化电台的领导会调动!
但还有建筑不可撼动。不可撼动?得了吧!人们常说世上有七大建筑奇迹。其实不过是些沙上城堡!塞弥拉弥斯的空中花园和巴比伦的城墙早在若干世纪前就已消失不见,萨达姆·侯赛因在八十年代主持的重建工作也收效甚微(我亲眼所见),还面临下一颗美国炸弹的威胁。菲迪亚斯【菲迪亚斯(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30年),古希腊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雕刻的奥林匹亚宙斯巨像终被烧毁。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也是如此,我们已熟知其遭遇。它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得以重建,但也同样遭到了摧毁(尽管部分残余用于建造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或被英国人带回了大英博物馆)。最后是地震摧毁了哈利卡纳苏斯的陵墓【指位于古希腊城邦哈利卡纳苏斯(今土耳其博德鲁姆)的陵墓,墓主是波斯帝国在当地的总督摩索拉斯夫妇,始建于公元前三百五十年左右】、罗得斯岛巨像【指遗址位于希腊罗得港入口处的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始建于公元282年】和亚历山大灯塔【亚历山大灯塔遗址位于埃及亚历山大港外的法洛斯岛,始建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总之,七大“奇迹”中的六个已经消失,只有金字塔群依然存留。它们历经四十二个世纪,一直注视着我们(但不论是我们还是它们,都已变了模样!)。
要想找到一个争议更少的成功案例,我们需要到远东地区。中国的长城由成千上万的不幸之人建造,又在公元前三世纪,由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修缮完成。在某段时期,它的长度甚至达到一万公里。据说(可惜我不能亲眼看见),长城也是唯一可从月球看见的人类建筑。
然而,即使是得到允许,我们如今又能在哪里建造这样的城墙?现在是拆墙的时代,不是建墙的时代!那该怎么办?如何留下持久的痕迹?难道要学贺拉斯,像他一样去孵六音步诗吗?也就是说,用文字构筑“比黄铜更持久,比壮观的金字塔更高”【出自贺拉斯《纪念碑》一诗。原文为拉丁文】的纪念碑吗?唉!这纪念碑很美,可惜我们已经不学拉丁语了!这些诗歌本应阻止诗人“完全死去”,可是到明天,甚至在今天,还有谁能记住?当然,我们还可以翻译。一些妙语、格言和机锋,得以跨越语言,口口相传,从纸莎草到羊皮纸,从纸质书到录音带,如同轻盈的灵魂之鸟,比最坚不可摧的塔楼更有机会流传千古,哦,双子塔!然而,这些表达虽然“年深日久”并被吸纳进“民族智慧”,如橡胶般柔韧持久,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作者的信息。是谁首先参透“滚石不生苔”或“星期五笑的人星期日会哭”的?有谁对这些作者的长相、职业,哪怕是名字有一丁点的了解?亲爱的夏尔·德内【路易·夏尔·奥古斯丁·乔治·德内(1913—2001),法国著名歌手、歌曲作者、抒情诗人】,你说得对,“诗人们死后很久,他们的歌依然在街头传唱”【语出夏尔·德内《诗人的灵魂》一诗】,但没人知道作者!最精妙的格言、最伟大的发明皆是如此。
当然,如果仔细检索,我们也能找到甜菜收割机、双梁天平或硝化甘油的发明者(巴雅克、罗贝瓦尔、索布雷罗)。多亏了四个大胡子【“四个大胡子”是一组法国当代歌手组合的名字,曾唱过一首名为《晾衣夹》的歌。歌中以戏仿的方式讲述所谓晾衣夹发明者的人生】,我们也知道了晾衣夹的发明者是热雷米-维克多·奥普德贝克。
尽管如此,还有很多重要的发明找不到发明者。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将是另一番模样,我们也不会如此自豪地位列其中。对于这些发明,我们仍是一头雾水:当然可以通读史前考古学家之父布歇·德·彼尔特与福楼拜的朋友路易·布耶的作品——后者曾用亚历山大诗体书写重大发明的历史——也可以遍览勒鲁瓦-古汉【安德烈·勒鲁瓦-古汉(1918—1986),法国史前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也是技术人类学的先驱】和老普林尼的作品,但有谁知道是哪位天才发明了轮子、黄油可颂或者裤子的前浪?
既然这样,何必要撸起袖子或提起裙子,日夜劳作三四十年甚至更久?一个人只有很小的概率能在地球上留下微乎其微的痕迹,就连地球也不会永远存在。



因此,别再白费力气,执着于留下痕迹,要坚决摒弃这些诱惑。不必重提《传道书》中的表述【指“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1:2)】——尽管一些虔诚的当代作家仍在重复这些陈词滥调,上文已不无动情地指出这些诱惑都是虚空,足以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接受失败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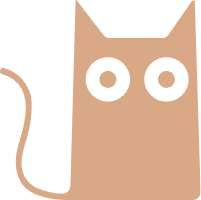
多米尼克·诺盖(Dominique Noguez,1942—2019),法国作家、评论家、哲学教授和电影编导,一生发表了大量广受赞誉的小说、随笔、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著有长篇小说《世界的最后几日》(1990)、《头巾百合》(获1995年罗歇·尼米埃文学奖)、《黑色爱情》(获1997年女性文学奖)等。其随笔作品以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感见长,出版于1999年的随笔集《圣诞礼物》曾获年度黑色幽默文学大奖。
《失败人生经营指南》是诺盖在法国Payot & Rivages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随笔集。书名可直译为“失败人生经营十一课”,围绕“如何彻底搞砸自己的生活”展开了方方面面的探讨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5期,策划及责任编辑:赵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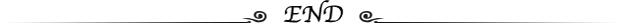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