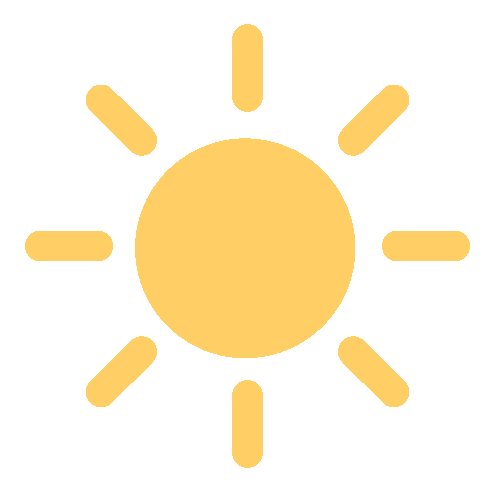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马•奥西波夫【俄罗斯】:莫斯科—彼得罗扎沃茨克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让一个人免于和周围的人与事纠缠,保持距离——这难道不是进步的使命所在么?而且别人的悲欢苦乐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您说,一个人怎么就不能独处?哪怕是独自出门呢?
留心,约伯,听我说,保持沉默。
——《约伯记》(33∶31)
让一个人免于和周围的人与事纠缠,保持距离——这难道不是进步的使命所在么?而且别人的悲欢苦乐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您说,一个人怎么就不能独处?哪怕是独自出门呢?
有人问了:谁去彼得罗扎沃茨克?学术会议,有国际友人参加。要求得是博士,得有人去。我们知道这些会议是怎么回事:三两个侨民——他们总是参会。喝点小酒,把宾馆一住,做场讲座,出席大型酒会——然后就回家了。讲座之后还会有人提问,而你身后是几个健壮的汉子,他们脸膛通红,指着手表——到点了。这些汉子是本地的教授,外省那些人现在都是教授,就像在美国南方——但凡一个白种男人,都是法官或者上校。
那么,谁要去彼得罗扎沃茨克呢?我主动请缨:想去看看拉多加湖,还有别的一些地方。“不是拉多加湖,是奥涅加湖。”“有什么区别?您去过彼得罗扎沃茨克?”“我也没去过。”
*
火车站是个挺可怕的地方,我打扮成真正的旅行者的样子,这可以保护我。我貌似淡然地走向车厢,好让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我经常光顾火车站,抢劫我没有意义。
从莫斯科开往彼得罗扎沃茨克的火车,顺便说一句,路上要走十四个半小时。火车上的旅伴几乎总是麻烦制造者:喝啤酒,扔烟头,灌“巴格拉季昂”和“库图佐夫”牌白兰地,高谈阔论,还有就是寻衅滋事。
火车开动了。目前还好,只有我一个人。
“查票了,请把车票准备好。”
“姑娘【这里指的是女列车员】,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我呢,您看……嗯,就是说,我想一个人待着。”
她打量了我一番:“那就看您要干吗了。”
我能干吗呢?!
“我就看看书。”
“要是看书,那就五百卢布。”
这时突然上来两个人,差点儿误了火车。他俩都在下铺,坐着呼哧呼哧直喘气。唉,活该你倒霉!出行不利。真烦人。你们坐吧,我不打扰了。我爬到上铺,背过身去。他俩在下边忙乎。
第一个人看上去普普通通,没啥文化。头、手和鞋子都显得又大又笨拙,嘴巴微微张开——一副蠢相。满头大汗的蠢货。他掏出手机玩起了游戏。“叮铃叮铃”的铃声意味着赢了,如果输了,就发出“哔哔哔”的声音。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摆弄拉链——也是一种噪音,还时不时地吸吸鼻子。但人好像还不糊涂。
第二个人在我下铺,没好气地说道:“把外套脱了,废物。”这人是个暴脾气。“别出怪声。”
真难受。车轮在“咣当咣当”地响。下面的手机“叮铃叮铃”响个不停。这还怎么看书?难道一路上都得这样吗?
我来到走廊上。隔壁包厢的人在聊天:“俄罗斯属于那种椭圆形国家,”一个年轻男人声音悦耳地说道,“与美国或德国那样的圆形国家不同。顺便提一下,我在这两个国家都住过很长时间。”一个女孩高兴地惊呼一声。“俄罗斯,”那个男声继续说道,“就像一只蝌蚪。在俄罗斯,人们坐车只能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人口相对集中的‘蝌蚪躯干’除外——那里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步行就可以。”
这是我左边包厢里的情形。右边的包厢里,人们在喝酒,几个男人用手撕扯鸡肉、掰西红柿,碰杯,放声大笑。


我回到自己的包厢。天啊,时间过得太慢了,火车这才驶离莫斯科。
又过了半个小时,又过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特维尔了。那个蠢货还在“叮铃叮铃”地玩手机。另一个人来了精神。
“关掉声音。”
“托——托利【托利和托利亚都是阿纳托里的昵称】,这……”
如此说来,他叫托利亚。个子高高的,大概有一米九,手指又长又白,指甲是圆的。脸长得没什么特点。嘴唇很薄。面色似乎有点苍白。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是不太喜欢托利亚。他身上没有气势,仅此而已。Anaesthesia dolorosa——痛性感觉缺失【医学术语。一种罕见的神经症状,患者身体某部位失去了正常的感觉,但会感受到剧烈的疼痛】。你用手去摸,却分辨不出自己触碰到的物体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我是不是太挑剔了?人家可是头脑清醒,彬彬有礼,尽量不打扰别人啊。
“报纸,买报纸了,新出的报纸。”
谢谢【此处原文为法语词的俄语音译】。我们知道你们的这些报纸总爱登些什么:女网球运动员当着男记者的面脱衣服,电视主持人的家庭悲剧,亿万富翁的女儿被绑架;保持腹部平坦的秘密;犯罪新闻;某人英年早逝。呸!不过,托利亚还是买了一份报纸,“哗哗哗”地从后往前翻。过了一会儿,他对那个蠢货说:“走。”
我只独自待了一小会儿。出门在外,还能怎样呢。
在大家放松身心准备睡觉之前,又发生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
第一件事,是隔壁包厢——就是有人喝酒的那个包厢——的一个酒鬼误闯了进来。他手里拿着相机,醉醺醺地打开门,准备拍照。托利亚一下子冲到他跟前,然后马上转过身去,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啊哈,原来是克格勃,契卡。现在清楚了。
醉汉把我拉到他跟前——当时我正准备去刷牙——让我给他和他的朋友们拍张合照。“咔嚓”一声。好了吗?不,还没好呢。我还得听他讲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几乎趴到我身上了:酒味儿、汗味儿、烟草味儿——喏,你就闻吧。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就像在美国那样。
当年他妈妈给了一百卢布让他买相机,可是后来钱没了——她又收了回去。而他从小就喜欢摄影。是这样啊,啊?!我深表同情,然后准备走开。
“站住!”他要给我朗诵一首诗,超级棒的诗。
“对不起,”我说,“我肚子疼。马上就回来。”好不容易挣脱出来。
“在……冻土带,铁路沿线!”【《在冻土带,铁路沿线》是俄罗斯著名诗人、创作歌手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1938—1980)的诗歌作品】他吼道,一边吼一边张开双臂做拥抱状——冲着所有闪避不及的人。
事实证明,我那两位邻座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你想想,克格勃啊。一句话不说,身上也没有怪味,而且还注意保持距离——也像我一样,讨厌和别人凑得太近。
第二件事,是离得最近的厕所不能使用了:马桶里被人塞满了报纸。那些浸湿的彩色图片——是干吗用的呢?
第三件事,是泡茶的水只是温热而已,可能还没烧开。
“苏——苏——苏沃克【原文为совок,本意为收垃圾的小簸箕或撮子,苏联解体后被用作苏联、苏联人或与苏联有关的一切的代称,也用来指代虽不属于苏联时期但带有苏联特点的人或现象】。”托利亚说道。
不,他不是克格勃。
车厢里熄灯了,试着睡觉吧。是什么把他俩联系在一起的呢?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既不是亲戚,也不是同事。也许是同性恋?谁知道呢。不过这关我什么事?也许就是同性恋。这种事在普通人中间要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常见。
耳边依旧响着“叮叮咣咣”的声音。心疼自己。我睡着了。


*
我睡着了,而且睡得意想不到地香甜、长久。醒来的时候,迎接我的是清晨的阳光、窗外的白雪和刺骨的严寒——这一点是根据枞树的状态做出的判断。
我没去注意那两个旅伴,独自走出了包间。火车停了。“斯内奇”——应该是我没看清站牌上的字。停车期间使用厕所……还是等等吧。唉,再过两小时就到期待已久的彼得罗扎沃茨克了,就有宾馆、热水和美味佳肴了。现在我的心情好多了。真是的,我怎么这么娇气!
我的邻座已经收拾停当:托利亚显然根本就没有躺下睡觉。他坐在窗边,激动地转着脑袋瓜:“怎,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车啊?”
“好像到斯内奇了,”我说,“斯内奇站。”
“什么?谢雷,我们这是在哪儿?”
“停车半小时。是斯维尔【指的是斯维尔河,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东北部最大的河流】。”谢雷此刻给人的印象好了很多。他没有在玩小孩爱玩的游戏,也没有瞎说。
谢雷离开了,火车开动了。我草草洗了把脸,喝了点热茶,心情也好些了。我想做日常在做的事情了:吃早饭,开开玩笑,八卦一下莫斯科的教授们,向年轻的女博士献献殷勤。我们不会晚点吧?走了一圈,打听了一下。好像不会。
哎呀,我的邻座怎么了?现在,在大白天,托利亚一个人待着,显得特别可怜。
“阿纳托里,您不舒服吗?”
“什么?”他扭头看着我。
天啊,他全身都在发抖!这种情况我见过好多次了:病人在住院后过完第一天之前,常常会开始发抖,驱赶邪祟,甚至还会跳窗户——酒精中毒症!就这么简单。原来托利亚是个酒鬼。
“姑娘!姑娘!”我喊道,“这位乘客酒精中毒了,您明白吗?酒精依赖。有药箱吗?”“没有药箱。”真是苏沃克!糟糕!得赶紧去找列车长!可是去哪儿找他呢?“给他点葡萄酒吧,我来付钱,否则他会把你们这儿全砸了!”
“您别急,这位乘客!”列车员说,“他的朋友在哪儿?”
“他在那个斯卫理还是斯威利——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下车了。”
“他怎么能在那儿下车?他的票是到彼得罗扎沃茨克的!”列车员大声喊叫着,“他用报纸把厕所弄得一团糟!他拿走了整沓报纸!难道卫生纸不够用吗?”
这关厕所什么事?乘客不舒服,需要她帮忙,而不是歇斯底里地发脾气。他在那边恐怕正在用头撞墙了。完了,来不及了,他病情发作了。
“我们这就来处理您包厢的问题,先生!我们会把他赶下车的!”列车员跑开了。见鬼,我也不敢进包厢了,而是站在门口等着。
比亚日·谢尔加站。警察来了。是的,这个人能处理好问题。我,一个医学副博士,都处理不了,他能处理好。捷尔任斯基同志对真理有着敏锐的直觉。【出自高尔基的回忆文章《弗·伊·列宁》。小说中的这句话与高尔基原话略有出入】
“来,证件准备好。”
他只扫了一眼我的证件。不过托利亚这边却出事了,非常可怕:他一下子蹿到小桌上,抬脚用靴子踹窗户。第一脚没踹碎,但后来还是踹碎了:玻璃片,冷风,鲜血。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警察用橡胶警棍击打托利亚的双腿,托利亚于是伸手抓住上面的架子吊在那里,后来扑通一声摔到地上。我没看到他们是怎么把他拖出去的,因为列车员把我带到了隔壁包厢,那个令人愉快的小伙子和那个女孩身边。
托利亚在我们车窗下被殴打了不止一分钟:跑过来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小伙子(穿得过于单薄了),还有一些警察。他们用黑色的警棍和拳头打他。我们这儿就是这样治疗酒精中毒症的——直说吧,这可不是什么罕见病。还需要详细描述吗?他们有个术语,叫“强行拘留”。有那么一刻,我好像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尽管隔着双层玻璃很难听到声音。
他们一边打人,一边念叨着什么,甚至还问了些什么。谢雷也被他们不知从哪儿拖了过来,也在挨揍。他很快就摔倒了,护住脑袋,缩成一团,他们对他倒是没使那么大劲。打累了,这些维护秩序的人。
*
我们隔着窗户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后来火车开动了。
“可怕,太可怕了!”女孩哭了。我们干吗要让她看呢?“真恐怖!我不想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不想!”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种情况,”年轻男子说,“但是何必为这种事唉声叹气、长吁短叹呢,没有意义。”
我没有马上意识到是自己闯了祸。当你犯了致命的医疗错误之后,总有一段时间,你会傻呆呆地看着病人、仪器屏幕和自己的同事,大脑里一片空白。
“这打人的和被打的,他们可真是绝配,”年轻男子继续说道,“要是伯克利的教授让人这么打了,他一定会不堪受辱,上吊自杀。可是这两人就能爬起来,抖抖身上的土——不要紧,耽误不了办喜事【俄语谚语,原文为до свадьбы заживет,即没什么,不要紧,不值得为一点不顺心的事或病痛而烦恼的意思】。”
“那换了是您呢?”我问道,“您会怎么办?”
“我吗?”他微微一笑,“我就跑了。”
依我看,我们仨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那挨打之前为什么不跑呢?”女孩插话道,“正常人不该在这里生活。”
我的新同伴又笑了:“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我可爱的女伴,我该怎样忍受这次旅行。这列火车上连双人包间都没有。”
我环顾四周:奇怪,这个包厢看上去跟我那间一样,可是这里却透着整洁和安宁。那个年轻人身上散发着好闻的男士香水味。是的,他也是去参加学术会议的。他以前是医生,现在的身份是出版商,出版一本杂志(就像普希金一样),是某个协会的会长,还有很多其他头衔。小桌上放着半瓶“拿破仑”牌白兰地。还有那个女孩,也确实可爱。
“您应该喝一小杯。”他随身带着小酒杯,用玉石做的,不知道是缟玛瑙还是碧玉。玉石酒杯。嗯,白兰地也是上好的。
年轻人解释了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走的原因:是因为文化。
“比如,对我的美国朋友来说,triple A 指的是美国汽车协会。可是在我们这里,三个 A 会让人联想到什么呢?”他停顿了一下,“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他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们,又补充道:“还有商业。”他就是这么说的——商业。
在你一手酿成两个人的不幸之后,喝点白兰地暖暖身子也挺好!
“您绝对正确,”年轻人继续说,“这不是我们的国家,这是他们的国家。”“难道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您要知道,我们并没有雇佣这些人来保护自己。一种消极的淘汰法则在这里起作用。结果就是:在现行体制的框架内不可能有仁慈的警察!体制会把他们排除在外。那还能干什么?改变体制。再有就是内部流放。实在不行,”他悲痛地摊开双手,“那就降低对生活的要求【这里原文用的是英文的俄文拼写】。”
我捕捉到了女孩的目光。嗯,是的。降低对生活的要求。
有人用力敲门:“十五分钟后到终点站。”我得回自己包厢去取行李了,邻座要帮我,我道了谢。


*
包厢里一片狼藉,我有一个重大发现:我知道托利亚和谢雷是做什么的了。在板铺下面,挨着我的小皮箱放着两个巨大的蛇皮口袋,拿着这种袋子到处走的只有一类人——倒爷。这样我那两位旅伴之间奇特的友谊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两个大不相同的人都当了倒爷——而且他们遭受野蛮殴打的原因也变得一清二楚。
“跟竞争对手算总账,”年轻人同意我的看法,“警察设的一计。”
“既然是设计好的,干吗那么卖力?”
“为了寻开心呗。我不是跟您说了么,警察不是人。”
倒爷。我的聊天对象就这一领域的人类活动有话要说。
“您看到没有,他们在履行重要的社会职能。”他用那动听的声音说道,“我们所有人,整个社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都想要同一种东西——昂贵的衣服、劳力士手表,可是有些人买不起瑞士产的劳力士。”他摆了摆左手:“而您的那两位倒爷——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给那些人提供了中国或别的国家造的‘劳力士’,不过这好歹也是手表啊,能显示时间,而且看上去还挺好。”
蛇皮口袋好沉!现在该把它们弄到哪儿去?交给列车员?不,这个坏蛋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任何东西!年轻人耸耸肩,我把袋子拖到走廊里:“您能帮我弄走吗?”
“要不这样?”他想了想,“把您的皮箱给我。否则我拖着这两个可怕的袋子看着像什么话?”
那好吧,谢谢。我想讨好他,于是说道:“您的女伴真可爱!”
“您得了吧!”他答道,“皮肤不好,长得也不好。只能打七点五分。”
不知为什么,我确认道:“满分是十分吗?”
“不,满分是七点五分!”他笑着说,“而且她稀里糊涂的【这里原文为英文】。——您明白吧——满脑子浆糊。”
他和她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这让我很满意。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竟然会为此感到激动。但是我和他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度过这段时间,这着实让人非常难过。
列车员冷漠地打开车门放我们来到站台上。有人来接那位姑娘了,我们和她告别,然后等待搬运工。随后,我们紧跟在那人后面走着,看到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参会者”,看来这次会议确实很重要。
年轻人坐进出租车之后,说道:“您呐,别想着您那两个让人揍得半死的家伙了!”随即这位出版商嘿嘿一笑,因为他头脑中冒出一个笑话:“揍得半死——听起来有点像ISBN【这句话包含着一个谐音梗:“揍得半死的”原文избиенных与ISBN(国际标准书号)的俄语发音颇为相似】。”
“但要知道正是我给他们惹了麻烦!这么说不准确——是灾难!”
“哈,”他摆摆手说,“知识分子的负罪感。现在全国各地的警察都在打击倒爷。该习惯了:生活本来就是不公正的。您就别去想这件事了。”
“不行,”我自语道,“他是个俗人。可我不能不管这件事。”
入住酒店之后,我要来电话簿,到处打电话。内务部、俄铁股份公司、联邦安全局——一大堆缩略语。奇怪的是,很容易就打对地方了。“过来吧,上校会接待您。”于是,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已经乘坐出租车奔向一座黑乎乎的、毫无特色的楼房。我带着蛇皮口袋。上校正在等我。


*
上校的门上黄底黑字写着“沙茨”,下面是“谢苗·伊萨科维奇”【施廖马·伊茨科维奇(1936— ),本名谢苗·伊萨科维奇,俄罗斯远东地区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和社会活动家,对药物成瘾及酒精依赖问题颇有研究。从上下文看,上校与这位医生同名。下文中的“真大胆”指的是他把医生的别名也写在了门上】,再往下,括号里写着“施廖马·伊茨科维奇”。从没见过这种写法。真大胆。
办公室的主人谢苗·伊萨科维奇刚睡醒,还迷迷糊糊的。他穿着背心和运动裤坐在沙发上,旁边没放枕头和被子,什么都没有。谢苗·伊萨科维奇一只脚已经伸进靴子里了,另一只还没有。这是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身材矮小,秃头,也没留胡子,但是耳朵和鼻子里——都是不该长毛发的部位——却长出很多毛。他的双手、肩膀和胸脯都覆盖着黑灰色的汗毛。我想:“长得真像以扫【《圣经》中的人物,传说为以撒和利百加的长子,雅各的哥哥】。”
该怎么称呼这位上校呢?施廖马这个名字既适合他,又很让我喜欢,但是大概只有自己人才能这样称呼他吧?
“我是沙茨上校。”他一边说,一边一瘸一拐地走向办公桌——还是没能把另一只脚伸进靴子里。
明白了,上校同志。
他肚子很大,手臂粗得和举重运动员的一样。鼻子大大的,肉乎乎的,毛孔粗大。脸颊上也坑坑洼洼的。眼睛不太好形容:我几乎没看他的眼睛。上校走到桌边,把制服外套穿到背心外面,然后坐了下来。
我有所准备,介绍说我是一名医生,来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医生,”他说,“公职人员。”沉默。“坐吧。”
我坐到对面的小椅子上。房间里只有一张大大的抛光桌子,一个沙发,几把椅子。看得出来,这里最近刚装修过。
“哈迪斯【希腊神话中的冥王,宙斯和波塞冬的兄弟】?”
我点点头。真是可笑:公职人员哈迪斯。他不也是如此么。或者,我们还是谈正事吧?我开始讲述:和我同行的那两个倒爷,客气点说吧,遭遇了非人的对待,有人借上校的同行之手找他俩算总账。希望上校能够不偏不倚地秉公处理此事。至少应该物归原主。
上校时而点头,时而轻轻摇头。
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简短地应答,基本上一直在骂人。我不喜欢脏话和粗鲁行为,但这些东西在这里却很应景。
墙壁上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画像。只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上面插着一些小旗子。野心勃勃。搞不懂墙上插小旗的逻辑。
“好的,快点结束那边的事情吧。”他放下话筒,转而对我说道,“我们以前有个党小组长,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德米特里奇是德米特里耶维奇的简称】,是个好人,每天早晨都要喝一瓶白兰地,八点整的时候就已经醉醺醺的了。”
我干吗要知道这个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得了吧。
“……所以他偷藏了那么多白兰地,足够每天早上来一瓶。你明白了吗?”
我姑且听着。
“……可是就在这个地方,”他冲着电话点头示意,“一个国家机关的领导被查抄了一千三百万美元——全是现金。他单位同事都半年没领到工资了。你告诉我,这个怪人要一千三百万美元干什么?”



确实令人震惊。但是这跟那两个不走运的倒爷有什么关系?
“倒爷?也可以这样说。你看。”
上校拿出一份报纸,就是火车上有人要卖给我的那一份。
“通缉双重谋杀案嫌犯,”我读道,“彼得罗扎沃茨克人……”还有一张托利亚的照片,留着小胡子。照片上的他在酒桌旁边,面带微笑。遇害者是一名男子和一个十来岁的少女。他们让托利亚到自己家里去住。
真是荒谬:那个男人带着小女儿生活,把房子卖了,想搬到小一点的房子里去,托利亚喊来了同伙……对,我明白了,那人叫谢雷,谢尔盖。
“不,不是谢尔盖,”上校说,“谢雷——出自他的姓氏。出于调查需要,不方便公开嫌犯的姓名。”
我艰难地折起报纸,把它还给上校。我的手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
“对不起,上校同志,”我终于说道,“但这是一份黄色小报,而且任何报纸都不能作为证据。请原谅,这没有说服力。”
“怎么,你是陪审团吗?还得让你信服?”
他说话的语气让我明白,报纸上写的是真事。
上校拿出几张照片,说:“你说你是医生?喏,你看。”
我们学过法医学,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开始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而且没能掩饰住自己的不适。
“给,喝点水。”他给我倒了点水。
托利亚和谢雷是怎样杀死那两人的,我就不讲了。有些事情是任何人都没必要知道的。
我对上校解释说,我没睡好,空腹喝了白兰地,嗯,总之……
“可以理解【此处原文为德语词的俄语音译】。”他回答道。
“这些照片是干吗用的?”
作证用的。让嫌犯在本地的客户开口说话。
他们根据从公寓里拨出的电话查出了凶手。所有的号码在自动电话局都有登记,我以前不知道。凶手中的一人或两人都往彼得罗扎沃茨克打过电话,作案之前打过,而且,重要的是,作案之后也打了。漫游资费很贵,他们想省钱。
他们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那套房子里跟尸体一起过了夜,这让我极度震惊。患者死亡之时,你会想敞开窗户,尽快离开病房,而这两个人……是的,在现场待了一夜,甚至可能是两夜。
“我的天啊!”我吓呆了,含糊不清地说,“我居然跟两个杀人犯一起过了夜!而且还睡得挺安稳!什么也没感觉到。我的天啊!”
上校对这番话没有任何感想。
“别去想他们的事了,”他说,“杀人犯也是一般人。”
又来电话了,他又是听得多,回应得少。我又能缓口气了,很高兴能舒缓一下情绪。他放下话筒。
“这里面是什么?你看过了吗?”他问的是蛇皮口袋。
没看,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看。他拿起口袋,轻松地放到桌子上。力气真大。
“手别碰啊。否则还得提取指纹。”
电子产品。游戏机——这肯定是谢雷的。上校打开一个琴盒。
“这是什么?”
“长笛。”
小女孩会吹长笛?——见鬼,我又开始难受了。
“未必,所有这些东西有可能来自不同地方。”
衣服。连私人衣物也不放过!不,这是用来蒙圣像的。
“圣像,”上校说,“你信上帝?”不等我回答,他又说:“现在所有人都信教。我们这里甚至连犹太佬也戴十字架。”
我本能地抬手摸了摸脖子:项链是不是露出来了?希望上校没注意到。我突然不想惹他不高兴。
书。不是书,是集邮册。
“你懂邮票吗?”
不,我哪懂啊?我只知道有的邮票价格昂贵。
上校把东西放回口袋里:“这些东西都值钱。”
“我好奇的是,那两个凶手,脖子上戴着十字架吗?”
“有什么可好奇的。我跟你说——他们也是一般人。”
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对人如此不了解?为什么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我又喝了口水——已经有点适应这里了。
上校开始收拾那些口袋。
“坐下。你做得都对。协助了我们调查。不然我们还得去市里抓你。”
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巧合。原来,在同一列火车上还有一位从莫斯科来的侦查员——他是来抓捕他们的。我想起那个穿运动服的人。只是巧合而已。他们也有可能根本找不到嫌犯。破案几率微乎其微。
“微乎其微?谁跟你说的?哪个怪人说的?”
上校微微一笑,温和地说:“什列马兹。”
我掌握的词汇里没有这个词。这是什么意思?
“什列马兹,”上校高兴地重复了一遍,“就是吃奶的孩子。”
我这次来彼得罗扎沃茨克,难道就为了让人说我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令人难过。
“在美国,”我说道,“就不是非要用警棍打人不可。有固定的程序。我说这些可不是在袒护凶手。”
“在美国,”他回应道,“我告诉你是什么样。”
于是,上校给我讲了他父亲的故事。
*
老沙茨,一个受过割礼的犹太人,战争初期应征上了前线,但是没能参加战斗:一九四一年八月,他们整个部队被包围后就投降了。沙茨弄到了一名阵亡乌克兰红军战士的证件,因此没有被立即枪毙,也没有落入集中营,而是先到了一个劳动营,后来又转到另一个。最后,他到了鲁尔区【德国重要的工业区。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下游支流鲁尔河与利珀河之间】的一座煤矿。
“你知道德语‘沙茨’是什么意思吗?”
宝藏、财富、财宝。上校点点头说,他父亲能勉强说点德语——战前大家都学德语。就这样,他来到矿山后唯一的愿望就是——活下去。毕竟,你想想看,战争何时结束、以何种方式结束,家里人情况怎样——这些全都是未知数。劳动营不是灭绝营,但是那些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关在这里的人,侥幸生还的只有十分之一。
去当翻译吗?不,这种事绝无可能。首先,要像所有人一样,才能不被人注意到;其次,营地里的正常人全都秉持苏联那套思维。只有败类才会在没有受到更多胁迫的情况下跟德国人打交道。沙茨的做法不同:他不止完成一个人的工作量,而是干双份的活儿。为此他能得到一些奖励:面包啦,烟草啦。他戒了烟——可以说,吸烟原本是他唯一的乐趣,但他还是戒了,为了有更多的食物,为了好好干活,完成指标。他用烟草跟同伴换食物,所以总能吃饱。有时他第一个从矿井里出来,就从看守那儿偷点东西——土豆,鸡蛋,面包。只偷吃的。被抓到就要挨打,打得很凶,每次打二十棍。德国人讲规矩。整个后背都被棍子打得乌青。他们打他,但没打死。
“最后也没发现您父亲是犹太人?”
“甄别活动期间没发现。在浴室里大家帮他遮掩,他对自己人编了个理由。”
“包茎。”
“对对。后来被发现了。还是我们自己人泄露出去的。”
沙茨的犹太人身份暴露后,他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成了“有用的犹太人”——那时德国人用这个专门的词汇来形容这种情况。他不得不完成三个人的劳动量,还要忍受德国人和自己人的折磨。不过,营地里真正的虐待狂并不多。看守也都是普通人。
“一般人。”我意有所指。
“对,一般人。”上校没有察觉其中的讽刺意味。
虐待狂不多,不比现在多,但其中有一个女人——劳动营管理主任的妻子。父亲说,她是个漂亮女人。她喜欢穿着鞋子踢人的裆部,强迫囚犯当着她的面脱裤子。总之就是寻开心。玩过头了。
美国人解放了他们。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包围了劳动营,等着看守投降,然后被囚犯打死。他们可以等一天,两天。保持距离。这是美国人惯用的手段。德国人想成为他们的俘虏,但是他们要德国俘虏有什么用呢?
“他把她怎样了?”我问。
“强暴了。明白了吗?他最先强暴了她。”
“那后来呢?后来她怎样了?被人杀了?”
“嗯,可能吧,”他耸了耸肩,“所有德国人都被打死了,未必有人幸免。”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请问,您父亲怎么看待【这里的“看待”一词,原文用的是动词过去时】德国人?”
“正常啊。为什么‘看待’这个词要用过去时呢?我父亲还活着。他只是恨德国人不给他发补贴。他在德国人的文件中从来没有作为沙茨出现过。”
他父亲还活着。那他现在做什么呢?“什么也不做,有什么可做的呢?喜欢逛市场。经常回忆那个德国女人。以前我母亲还在的时候,他闭口不谈,可是现在,聊那个女人比聊自己老婆还要频繁。”
办公室里几乎没有光线。我突然想迎合一下上校,哪怕只是看着他的眼睛,但他背对窗户坐着,我看不到他的眼睛。我尝试说点什么:关于情绪失控,关于老年人的性欲。医生的职业属性似乎赋予我一种权利,让我可以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
“在整个战争期间,”上校说,“我父亲没有杀过一个人。要是你的美国人当时能以应有的人道方式释放他,如今他就不会想起那个德国女人。”
上校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渐渐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我是不是该走了?
我最后问道:“那你们地图上的小旗子代表什么呢?”
他突然大笑起来,昏暗中能看见他的牙齿:“什么也不代表。小旗子就是小旗子。仅此而已。”
那好吧,我要走了。
“你不戴帽子就出门啊?”上校问道,“有帽子吧?”
“有,甚至有两顶:一顶鸭舌帽和一顶暖和的针织帽。”
“把针织帽戴上。”


*
彼得罗扎沃茨克:黑暗,寒冷,到处是冰,街灯昏暗,什么都看不清楚。
晚上,在国际会议的大会上,我遇到了那个声音悦耳的年轻人,就是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他跟我分享了他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说它“也像其他地方一样糟糕”。他还表示,回到莫斯科后想继续和我交往。一起吃顿饭怎么样?说好了,我请客。他顺便问了我一句:“打听到之前那两个让人揍得半死的人的情况了吗?”好样的,可找到话题了。
“没有,”我回答道,“没有。”
END
马克西姆·奥西波夫(1963— ),俄罗斯著名作家。毕业于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拥有临床医学副博士学位,曾经是一位有所成就的医生。现居德国。创作生涯始于2007年,擅长写作中短篇小说,迄今为止出版了六部作品集和一部合集,在俄罗斯国内外获得诸多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作品已被译为英、法、日等二十多种语言出版。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5期,责任编辑:孔霞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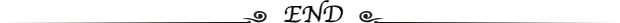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