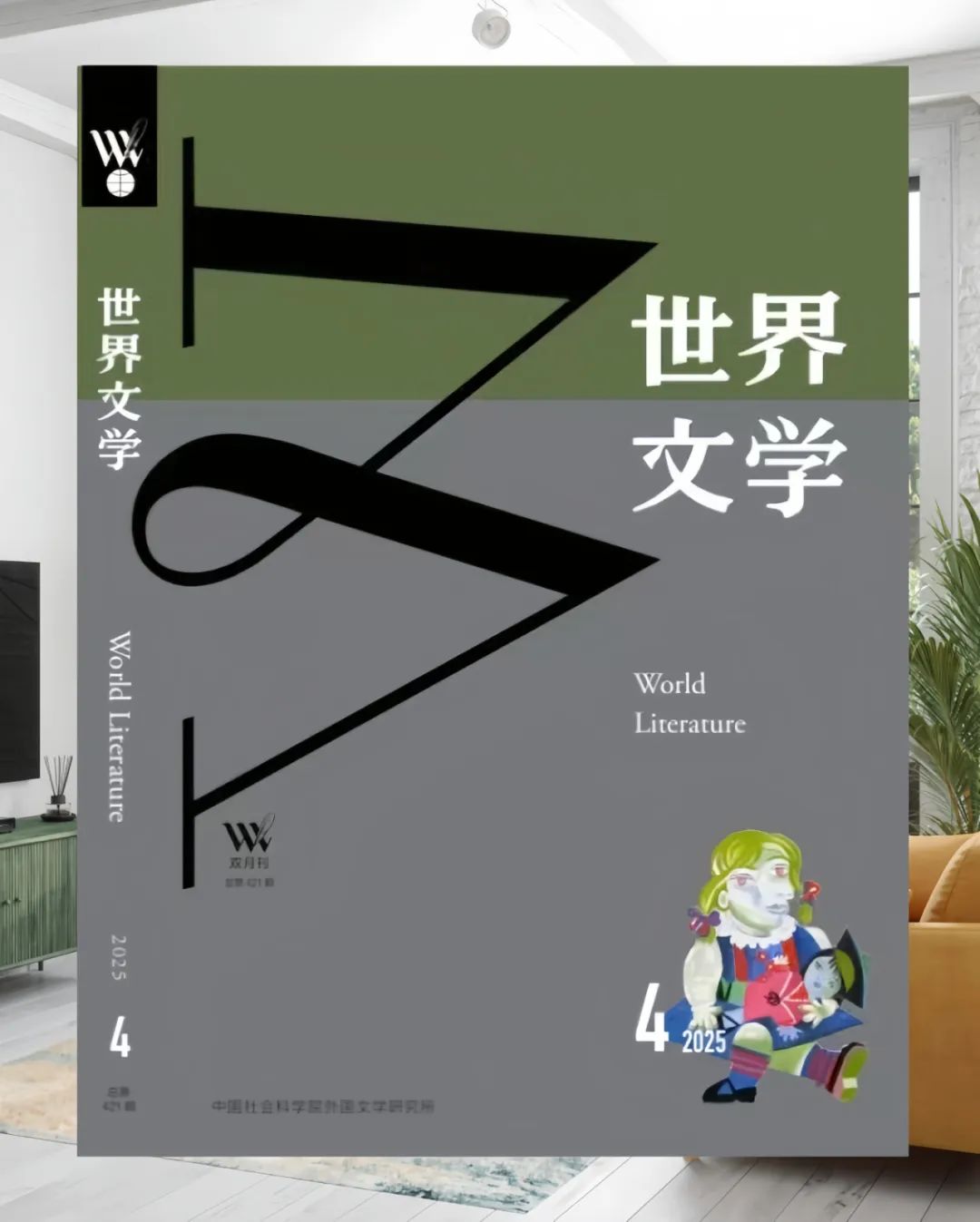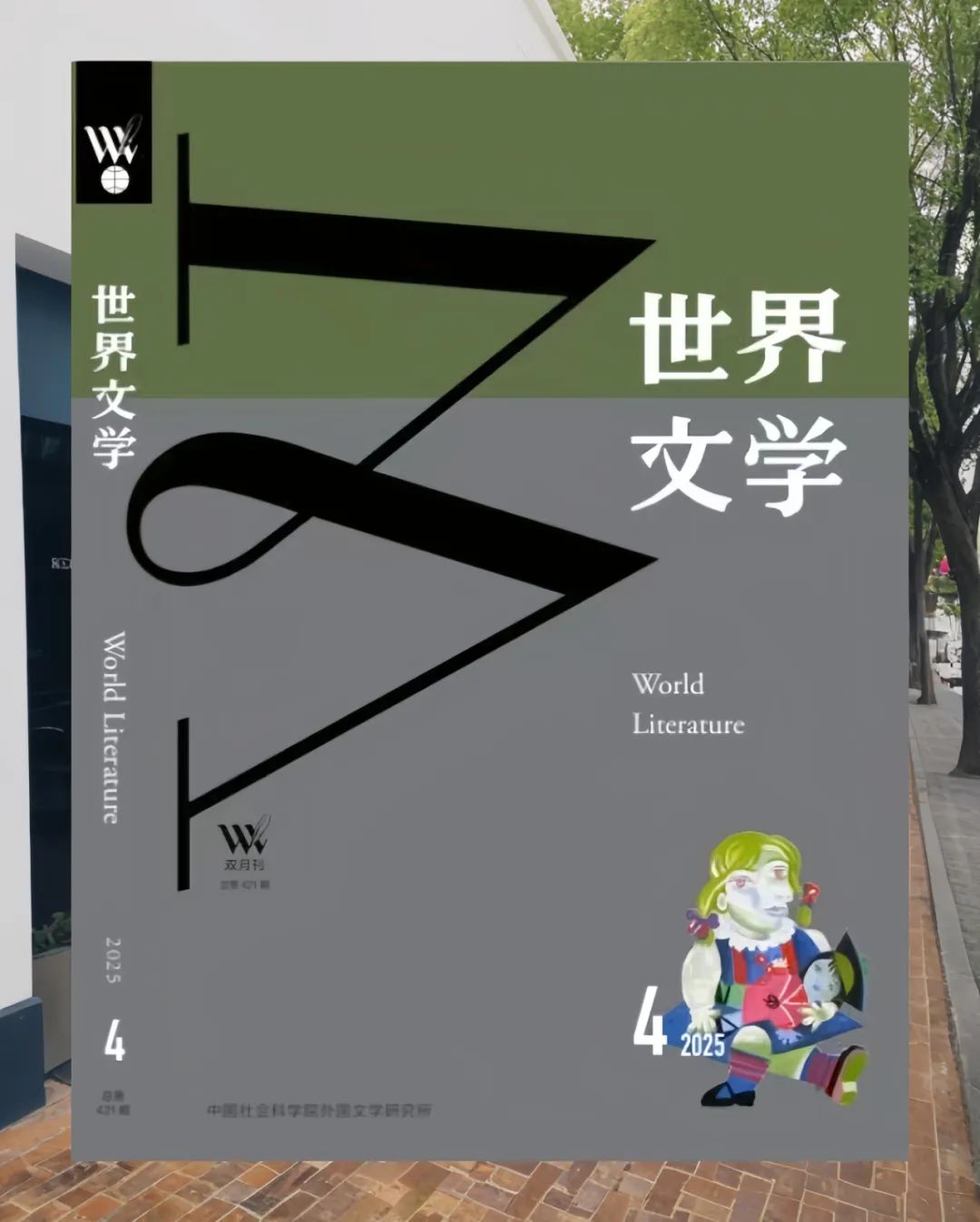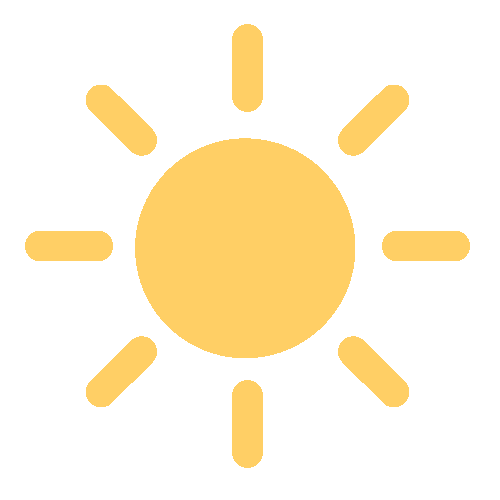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北原:读《在我家墙里》和《贝伊奥卢市政废物管理交响乐团》——对被时代抛弃之物的隐忧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两部作品都着力描写了现代社会中的空间。在《在我家墙里》中,墙壁既是囚禁杜蒂耶尔的物理空间,也是一种个人隐私的边界。对杜蒂耶尔来说,当墙壁不再能保护隐私时,他的存在本身也失去了意义。而在《贝伊奥卢市政废物管理交响乐团》中,垃圾桶、阁楼和最终的监狱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垃圾桶容纳了与时代龃龉的人或物,阁楼是多样化文化的庇护所,监狱则象征着整个社会被禁锢的状态。这些空间的象征意涵共同反映了作家对时代的反思。


北原
翻开《世界文学》2025年第2期,比利时作家贝尔纳·基里尼的《在我家墙里》与土耳其裔美国作家柯南·奥尔罕的《贝伊奥卢市政废物管理交响乐团》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两篇小说虽然诞生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之中,但都以非凡的想象力构建起超现实的世界,将奇幻与现实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令我感触颇深。


基里尼的《在我家墙里》以轻松荒诞的笔调续写了法国作家马塞尔·埃梅的经典作品《穿墙记》。小说的主人公“我”偶然发现自己家围墙里竟然“住”着埃梅笔下的传奇人物杜蒂耶尔——一个因意外永远困在墙壁中的穿墙人。故事由此展开,讲述了“我”和杜蒂耶尔的侄孙对杜蒂耶尔的营救行动。侄孙计划用自制的化学药剂将杜蒂耶尔从石墙中解放出来,这一设定让故事的发展愈发离奇,其中描绘的科学细节更让这篇小说充满奇幻色彩。而当杜蒂耶尔真的从墙中“复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巴黎时,小说真正的主题开始显现:现代社会中隐私的消失以及无孔不入的媒体,让杜蒂耶尔曾经引以为傲的穿墙异能变得毫无用武之地。他感到与新时代格格不入,最终选择重新将自己封印在先贤祠的石柱中,以此表达对这个“无墙可穿”的世界的失望与抗拒。基里尼的这则故事戏谑地剖析了现代社会如何侵蚀个人隐私的神秘感,进而导致个体的焦虑。《在我家墙里》的语言风格诙谐幽默,但在轻松的趣味背后,作品从杜蒂耶尔的视角出发,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与《在我家墙里》中主动穿入墙壁的杜蒂耶尔不同,奥尔罕的《贝伊奥卢市政废物管理交响乐团》则将目光聚焦于被社会与时代抛弃的人或物。故事以一位女性垃圾工“我”的视角展开,从“我”在伊斯坦布尔贝伊奥卢区收垃圾的日常工作写起,逐渐展开对那些被抛弃的人与物的描绘。故事从“我”在一位作曲家的垃圾桶里先后发现了被丢弃的乐谱、各种各样的乐器开始。“我”最初仅仅是将这些东西捡回收藏,但随着作曲家本人也被丢进了垃圾桶,事情开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我”在接下来几周陆续从垃圾中找到越来越多的乐手和乐器,这些乐手在“我”家狭小的阁楼里共同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废物管理交响乐团”,换言之,乐团也是这些人逃离成为“垃圾”的命运的避难所。或许可以说,这个“乐团”恰恰代表了在日益单一化的社会中那些不容于主流、被视为“垃圾”的文化、艺术和思想。小说对现实政治进行了鲜明的指涉:在书籍被禁、艺术家被迫害、树木被铐走等一系列荒诞事件后,文化多样性和个体自由也逐渐消失了。在这一意义上,阁楼里的乐团恰恰象征着“我”和乐团成员们对现实做出的一种文化上的抵抗。最终,连主人公自己也因一管“非土耳其红”的颜料而被捕入狱,监狱内部的景象更是将社会的荒诞推向极致:牢房里关押着各种各样的人,包含老人、青年、孩子在内,甚至警卫自己也成了囚徒。这显然暗示,整个社会都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囚笼。


在将两篇小说对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篇小说中其实存在着不少共通之处。首先,两者都运用了奇幻或超现实的元素来构建故事的核心矛盾。基里尼的“墙中人”和奥尔罕的“垃圾中的交响乐团”都是对现实逻辑与秩序的颠覆。然而,基里尼的奇幻更偏向于哲学上的思辨,探讨的是个体在信息逐渐透明的现代社会中的困境;而奥尔罕的奇幻则更具有现实政治的影射性,直接批判了压抑、威权的社会环境对文化的摧残。其次,两部作品都着力描写了现代社会中的空间。在《在我家墙里》中,墙壁既是囚禁杜蒂耶尔的物理空间,也是一种个人隐私的边界。对杜蒂耶尔来说,当墙壁不再能保护隐私时,他的存在本身也失去了意义。而在《贝伊奥卢市政废物管理交响乐团》中,垃圾桶、阁楼和最终的监狱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垃圾桶容纳了与时代龃龉的人或物,阁楼是多样化文化的庇护所,监狱则象征着整个社会被禁锢的状态。这些空间的象征意涵共同反映了作家对时代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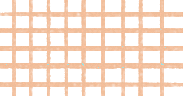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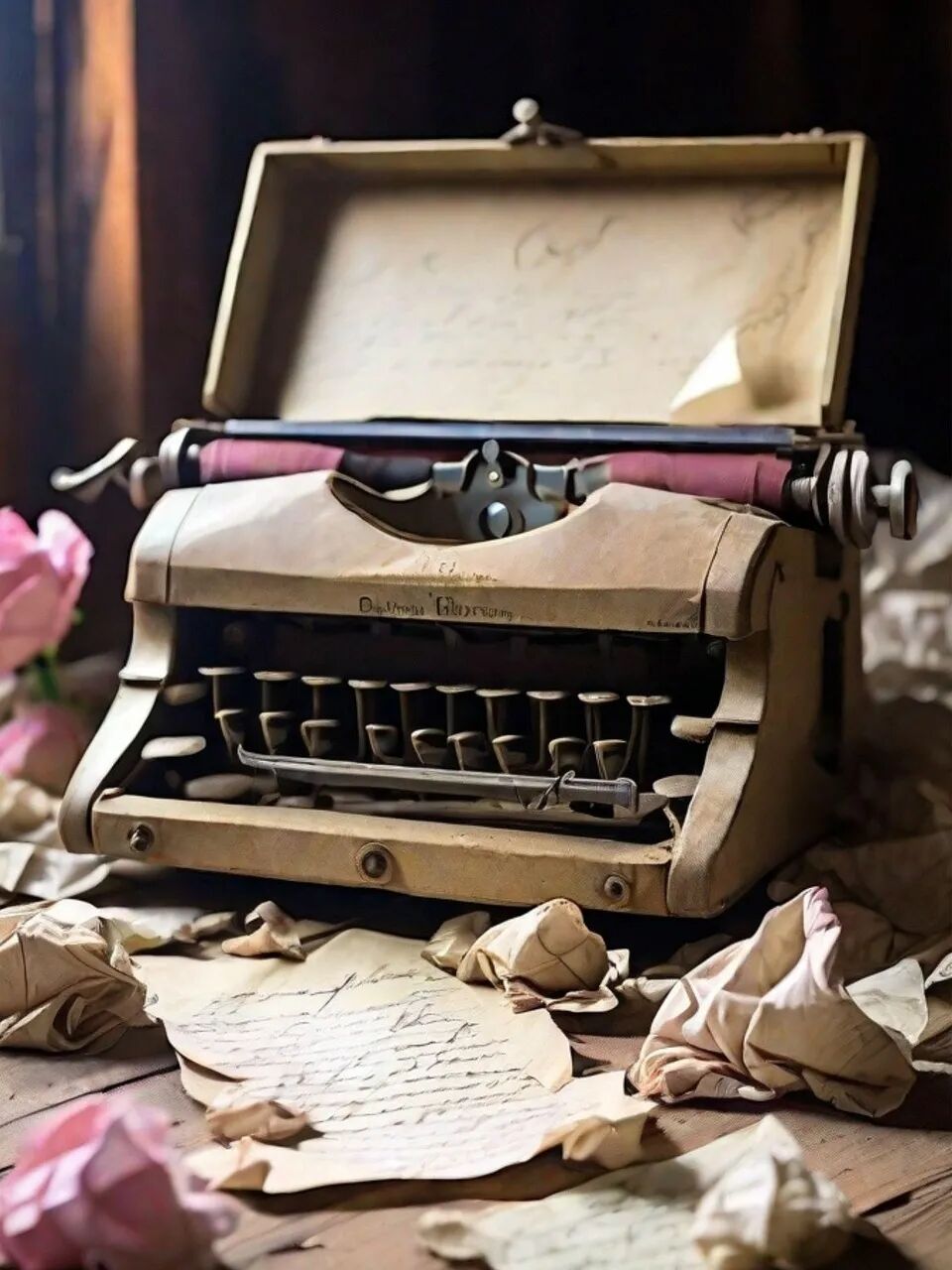
《在我家墙里》的杜蒂耶尔最后选择了自我放逐;《贝伊奥卢市政废物管理交响乐团》的主人公自己身陷囹圄,“乐团”的未来尚未可知。在某种程度上,诞生于过去的一些价值观念与文化信念已经被时代抛弃,而小说人物重拾这些被抛弃之物的尝试最终也是徒劳无功。尽管这两篇小说的切入点和表现方式各异,但它们都运用超现实的想象,成功地呈现出对被时代抛弃之物——无论是杜蒂耶尔本人还是“我”和“乐团”成员——的隐忧,从而进一步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文化以及个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刻的追问。它们提醒我们去关注那些被遮蔽、被遗弃、被边缘化的事物与声音,去反思在看似进步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可能正在失去的珍贵价值。阅读这两篇作品让我们不仅能领略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奇幻文学的魅力,更能从中汲取审视现实、守护精神家园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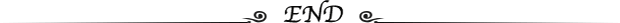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