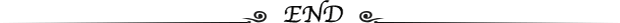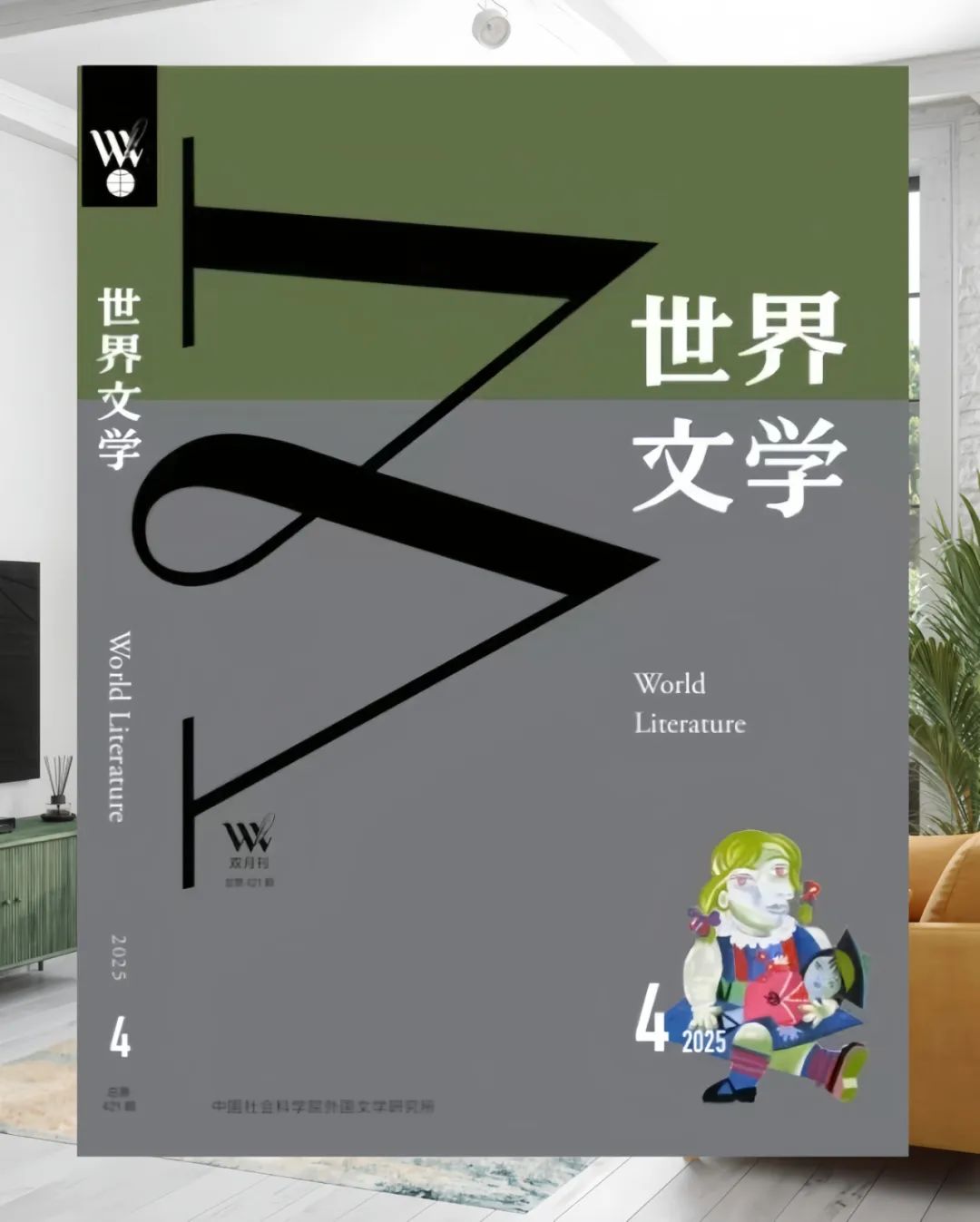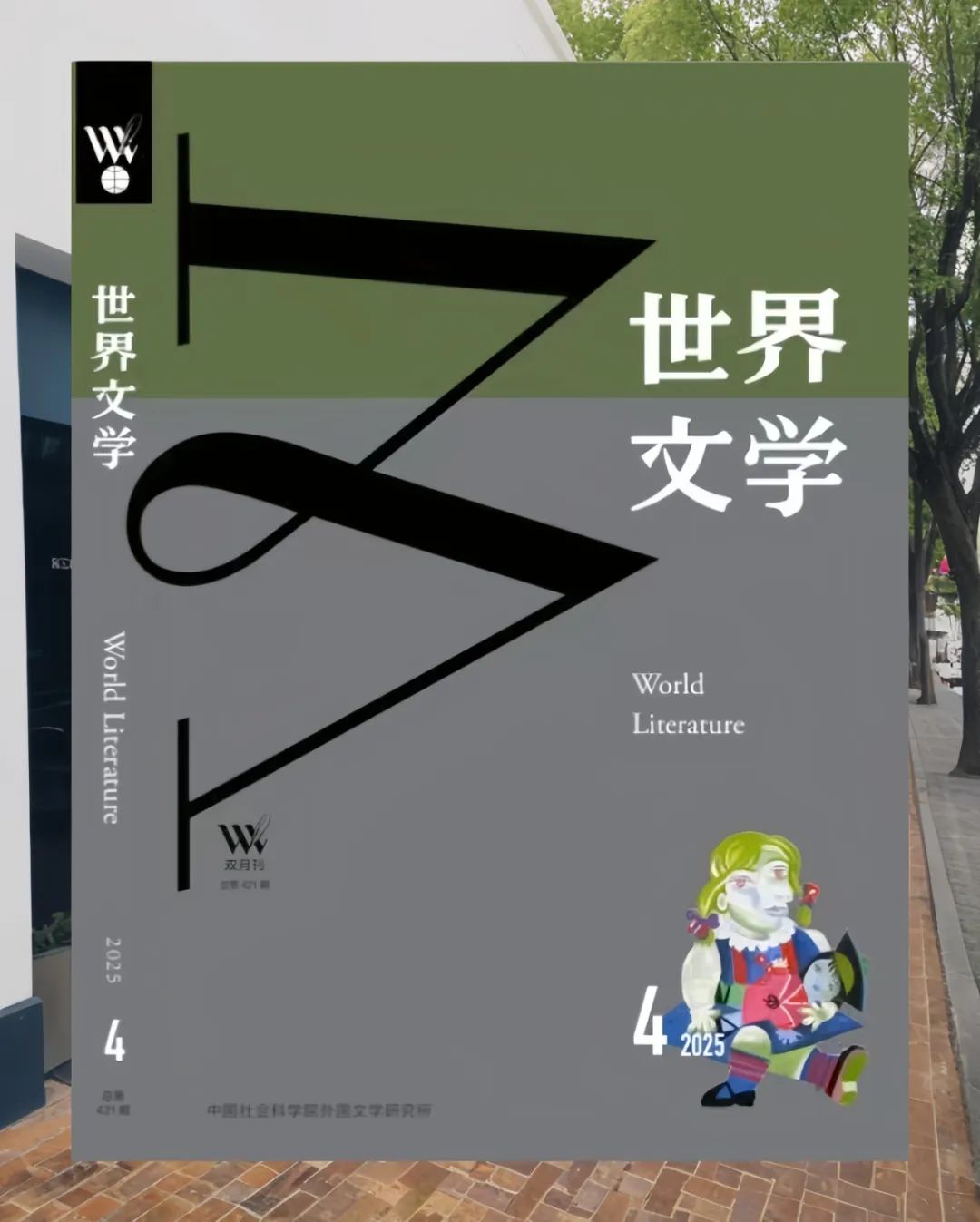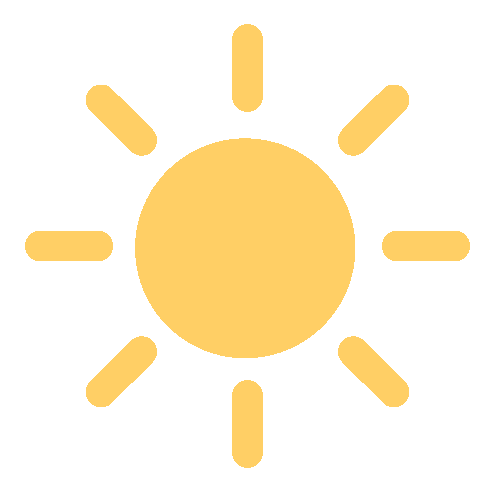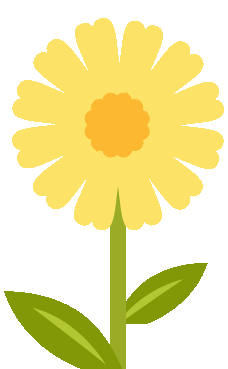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马钰玲:疯狂的女性,未尽的殖民——读《你的使命,玛尔尼》有感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一方面,她坚信这声音是来自上帝的馈赠……对声音的盲从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玛尔尼在巴黎感到的孤单。而另一方面,声音的存在又一次昭示了玛尔尼内心孤独的事实。每当她感受到与周围的隔阂时,声音就如影随形地出现,让玛尔尼可以暂时逃避到非理性的象牙塔里。而当理智归来时,玛尔尼仍然能清晰地意识到: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听到这个声音的人,自己苦苦找寻的生存意义根本不被外界知晓。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在瓜德罗普,她都感到一种莫大的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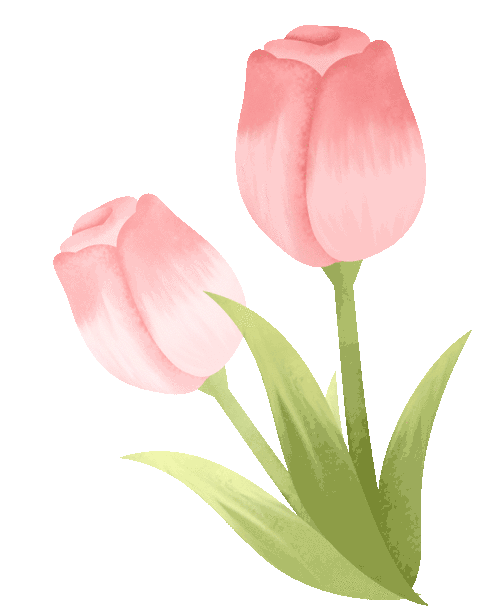
马钰玲
“疯狂”在加勒比文学中通常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形式出现,用来谴责殖民历史、奴隶制、流离失所等遗留问题对加勒比地区造成的精神创伤。而在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之外,黑人女性还面临着父权制霸权的威胁,承受着双重的身份焦虑。因此,她们也往往成为文学作品中“疯狂”的代表。
吉赛乐·皮诺是法属加勒比文学的杰出作家,其作品深受爱德华·格利桑“克里奥尔化”理论的影响。皮诺从非裔女性作家的视角出发,参照自身在巴黎和瓜德罗普两地的生活经历与精神科护士的职业经验,用细腻的笔触书写了当代移民,尤其是女性移民的生活和心理处境,而疯狂与精神疾病更是其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你的使命,玛尔尼》描写了来自瓜德罗普的黑人女学生玛尔尼在巴黎逐步走向疯癫的过程,将疯狂、种族与女性身份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小说采用了非线性叙事,以主人公玛尔尼脑海中突然出现的声音为线索展开叙述、串联前后。声音作为玛尔尼疯癫的主要标志,是她异化状态的内在表现。当我们将声音作为完全的第三方与玛尔尼分隔开来时,它无疑是在与玛尔尼争夺自我意识的主导权;而当声音被纳入玛尔尼“疯狂”的语境之中,她的“幻听”则以更为复杂的状态呈现——既象征着玛尔尼对外界霸权的妥协,又代表了她的抵抗。
在主人公玛尔尼正式出场之前,我们就已经“听见”了这些声音:
嗡嗡……
上天入地……
上帝的使命……
嗡嗡……
渎神的红斑疹……
这些声音带着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意味,突兀地剥夺了玛尔尼作为主角的主体地位,并用神圣的字眼与不同的字体彰显着自身强烈的存在感。
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声音,玛尔尼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她坚信这声音是来自上帝的馈赠,陪伴着她,赋予她神圣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声音的盲从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玛尔尼在巴黎感到的孤单。而另一方面,声音的存在又一次昭示了玛尔尼内心孤独的事实。每当她感受到与周围的隔阂时,声音就如影随形地出现,让玛尔尼可以暂时逃避到非理性的象牙塔里。而当理智归来时,玛尔尼仍然能清晰地意识到: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听到这个声音的人,自己苦苦找寻的生存意义根本不被外界知晓。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在瓜德罗普,她都感到一种莫大的孤独。
巴黎的大都市气息让玛尔尼难以适应。依她来看,城市噪音、摩托车轰鸣声、混乱的科技信号、天线和卫星干扰这些东西,都是“人类为了自己的不幸而发明的”。而在面包店因种族而受到的异样眼光,加深了她对周遭一切的抵抗情绪。于是声音又在这时出现:
上帝的毒药!
吃了会死的面粉!
恶魔与诱惑!
玛尔尼遵从脑海中的声音,将法棍扔进了垃圾桶。这看似是声音抹除了玛尔尼的个人意识,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忠实拥趸。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控制恰恰赋予了玛尔尼一种能动性,让她反抗自己不喜欢的事物。


扔掉法棍的动作不仅代表着玛尔尼对店员等人的种族歧视的抵抗,也代表着对法国都市生活的拒绝。小说中列举了一长串来自家乡安的列斯群岛的美食,这些都是在巴黎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此时,食物成为了玛尔尼在巴黎划定自身空间、确立身份的标志,是她与故乡的精神连接所在。尽管瓜德罗普人在表面上获得了法国公民的身份,但身边的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他们仍然是不受欢迎的。玛尔尼试图通过拒绝饮食来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找回自身与家乡的联系。因此,在阁楼里给母亲写信时,她脑海里的声音也偃旗息鼓。
但瓜德罗普同样不是玛尔尼的归处。通过小说中的暗示,我们可以猜测,玛尔尼在狂欢节之夜跟随“漂亮女孩”团体行动,对性有了最初的渴望与了解——这也让她第一次直面了自己的“饥饿”(各种意义上的),尽管这与母亲的期望背道而驰。那天是玛尔尼第一次听见那些声音,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厌食症状。这种症状在精神病学上可以解释为对怀孕的恐惧;也有人认为,拒绝进食是试图在生活失控时通过控制体重缓解对生活不确定性的焦虑;或者是社会文化对身材的病态渲染加剧了女性对身材的过度关注,等等。这些或许都是导致玛尔尼厌食的因素。
卡罗琳·克纳普在《欲望:女人为什么想要》中写道:“女人与饥饿和满足的关系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她的自我意识以及她在广阔世界中的位置。一个女人允许自己饥饿(各种意义上的饥饿)到什么程度?如何填饱自己?她真正感到自己有多自由,或者说有多压抑?……这是关于自我与文化之间的碰撞,女性的欲望在一个奇怪的世界中被释放——这个世界对女性的权力仍然深感矛盾,并在同等程度上激起女性的欲望和羞耻感……”


厌食仅仅只是一种表象,而玛尔尼不得不对自我欲望进行压抑,才是她一步步走向疯狂的根本原因。在父亲缺席的背景下,母亲对玛尔尼有着极强的掌控欲望:她认定玛尔尼是上帝的礼物,注定要成为一名医生。于是,在瓜德罗普,玛尔尼为了满足母亲的期待不得不削足适履;在法国,黑色的皮肤仿佛是她的原罪,令她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无所适从,而姨妈的冷漠更是加剧了玛尔尼的疏离感。
小说中这样描写玛尔尼第二次听到声音的情形:
在巴黎,她已经待了六个月,没有朋友,也没有爱人。在医学院的长椅上,她如此孤独;在这片大陆上,她如此孤独。在这里,只有一个不找她麻烦但和她保持距离的丹尼丝姨妈。
……
玛尔尼这时已独居六个月。没有朋友也没有爱人,就这样独自待在法国,独自待在贾维尔地铁站。远在异国他乡,唯一可以和她有关系的人就是离她很远的姨妈,后者却把毕生的怨恨和痛苦都带到了这里。
“没有朋友”“没有爱人”“孤独”是反复出现的词眼——即使如此,她仍然独自在法国待了三年,没有回瓜德罗普。母亲沉重的爱与期待将她绑在了一个不接受自己的城市,没有一个地方是她的归处。因此,玛尔尼只能抓住自己唯一拥有的东西,“坚信心中的声音以一种超自然的甚至是福音的方式滋养着她”,正如母亲笃信玛尔尼受天使庇佑的命运一般。可越来越粗暴的声音却反映出玛尔尼越来越压抑的内心。此时,自我毁灭就成为了她灵魂的出口。
声音洞悉了她心底的愤怒与脆弱,两次催促玛尔尼放火:
放火!让一切烟消云散!
渎神……
不知耻的女人……
你的母亲就是个恶魔……
你是罪恶之女……
你是撒旦之女……
你必须以死来拯救世界……
放火吧!
放火吧!
放火吧!
你的使命,玛尔尼……
声音的语气从愤怒的指责转向坚定的定罪,也代表了玛尔尼的内心转向。她对外界压力的抵抗宣告失败,于是选择了放火。同母亲一样,她承认了自己种族与生俱来的罪恶,并在与外界的交互中不断强化这种隔阂。因此,她感到必须用火焰来洗涤自己的灵魂,从而获得救赎——这是她在日益加深的身份焦虑下为自己选定的结局。此时,玛尔尼的命运正式落成,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神婆的预言。
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与疯狂》中写道:“在一个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社会中,身为黑人和女性所遭遇的问题是令人震惊的,生活中充斥着暴力、自我毁灭和无端恐惧……”《你的使命,玛尔尼》深刻揭示了殖民历史、种族歧视和父权制对黑人女性的多重压迫。尽管玛尔尼在火灾中幸存,余生却都需要在护士的监督下服药,让脑海里的声音安静下来。显然,声音没有消失,玛尔尼对身份认知和生存策略的求索仍未停止。
作者有意将玛尔尼的疯狂展现为一种普遍的孤立和疏离状态,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加勒比地区,这打破了一直以来将加勒比地区作为“疯狂”代名词的传统,指向了更为广阔的视角。玛尔尼的疯癫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缩影。她的故事提醒我们,殖民主义的阴影远未消散,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仍在继续。我们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和理解,打破这些无形的枷锁,帮助那些在边缘挣扎的灵魂找到真正的归属和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