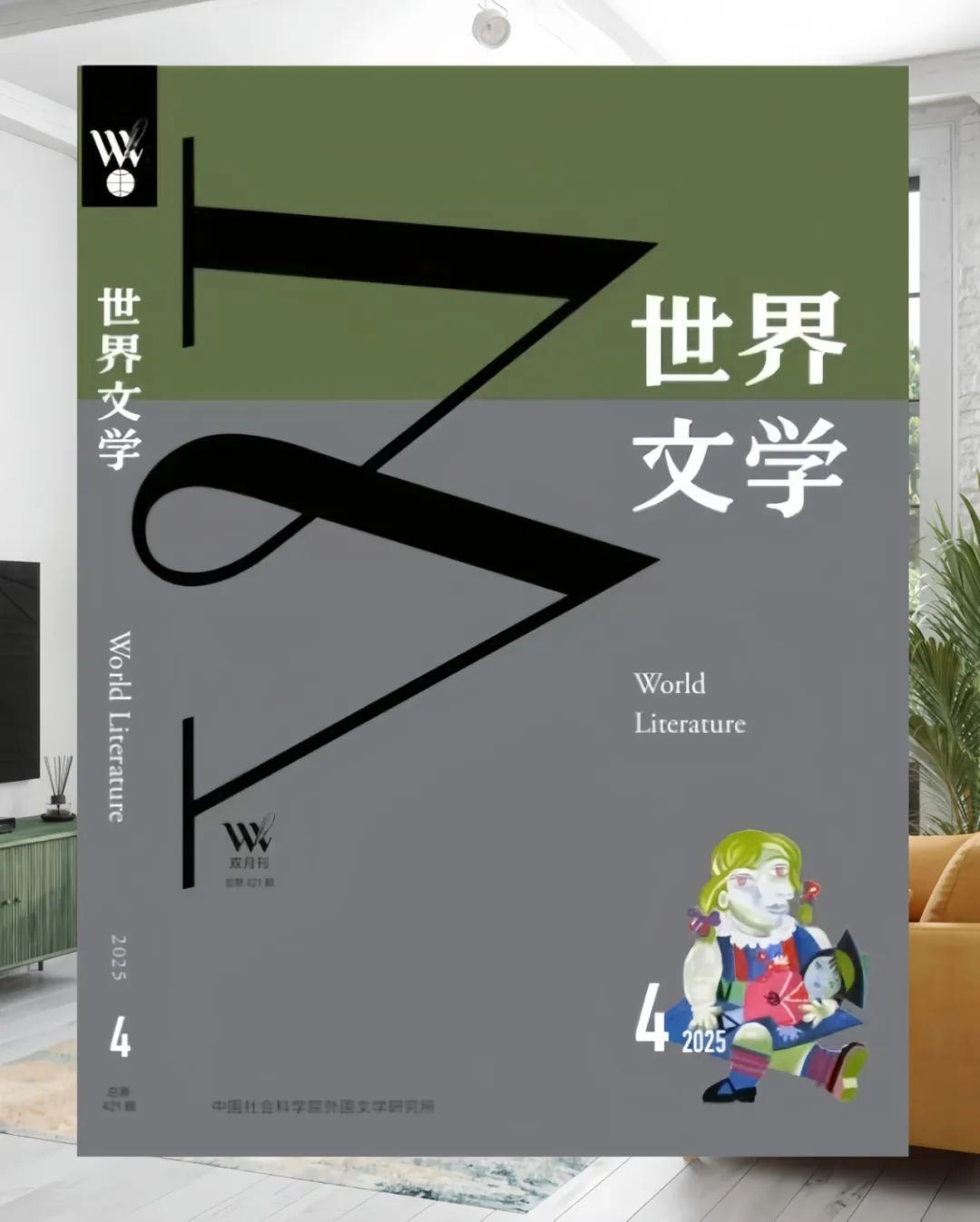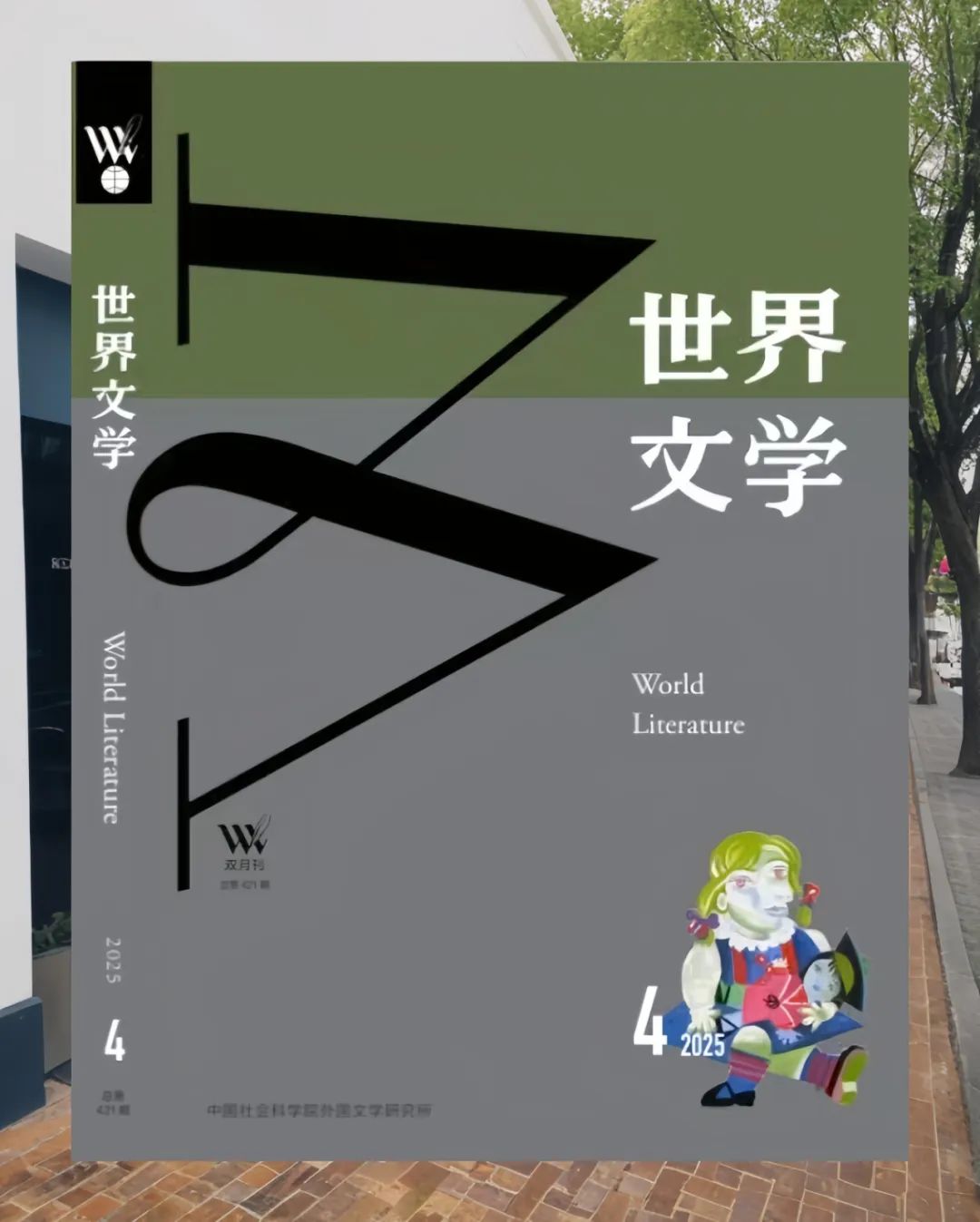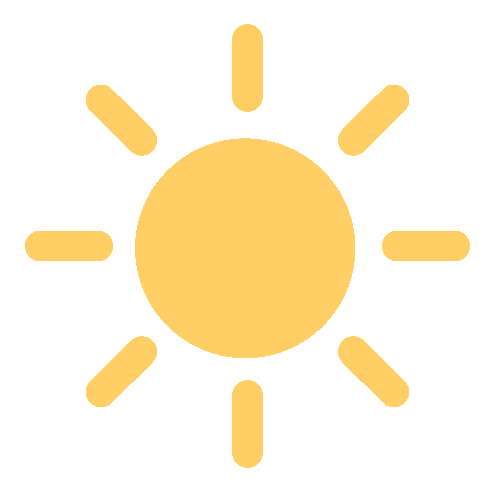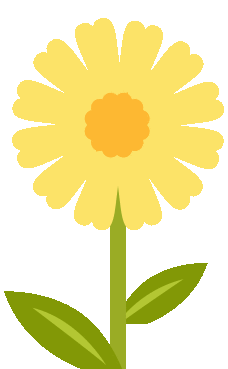散文品读 | 罗•穆齐尔【奥地利】:诗人之认识随札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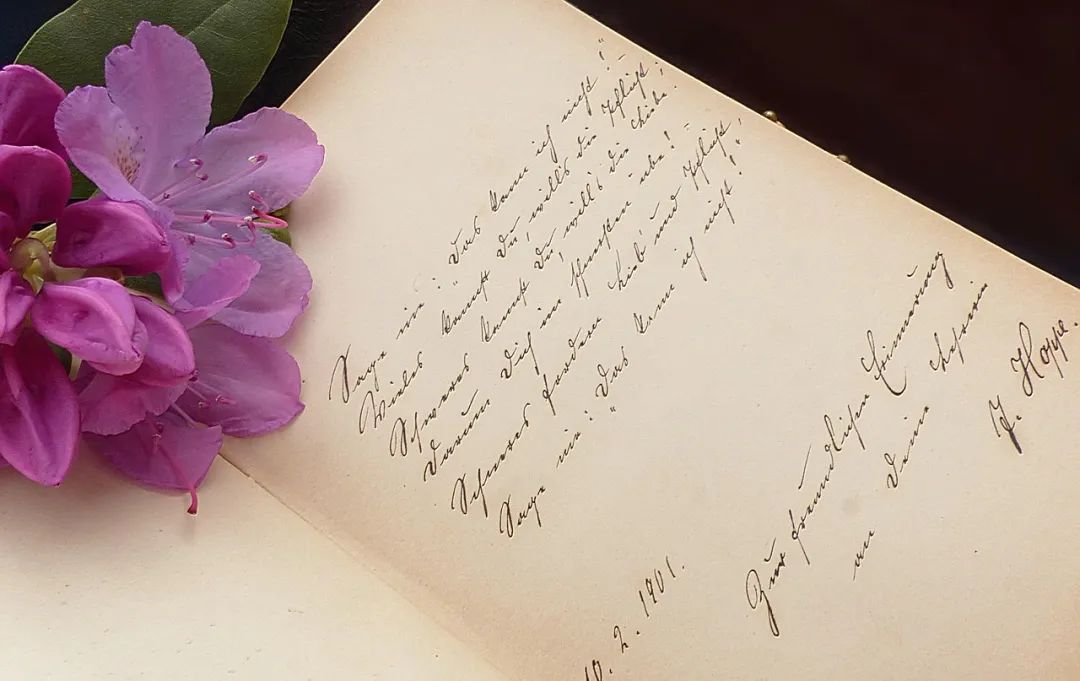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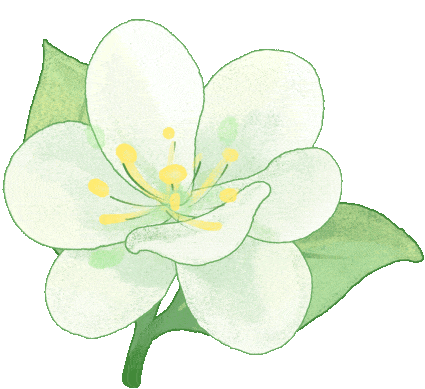
正如自保罗教派时期和俾斯麦时期以来受损的教授的声望一度在公众生活中提高了上去,而诗人的声望却低落了下来;在教授知性达到了世界存在以来最高的实际影响的今天,诗人却沦落到写作匠这样一个通用的名字,这一名下被理解的人,是没有被查明的缺陷妨碍了他成为一名派得上用场的记者。不应该低估这一现象的社会学方面的重要性,而且有理由对它作些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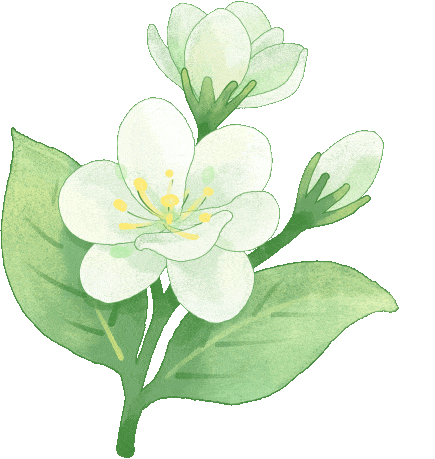
罗伯特·穆齐尔作 吴晓樵译
正如自保罗教派时期和俾斯麦时期以来受损的教授的声望一度在公众生活中提高了上去,而诗人的声望却低落了下来;在教授知性达到了世界存在以来最高的实际影响的今天,诗人却沦落到写作匠这样一个通用的名字,这一名下被理解的人,是没有被查明的缺陷妨碍了他成为一名派得上用场的记者。不应该低估这一现象的社会学方面的重要性,而且有理由对它作些思考。这一思考局限在对智性的考察,而且规模很小,就如同一篇认识理论考试的论文,这一思考把诗人仅仅看作一个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和在特定的领域中的认识者。这就是所想达到的限制,当然其合理性惟有通过结果来检测了。不过要事先声明的是,这里所讲到的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的类型,不仅是指写作的人;而且还包括许多害怕这一活动的人,他们对这一类型的作用部分构成反作用的一面。
人们也许能够把诗人描述为这样的人,即最强烈地意识到自我在世界上和在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无救的孤独者。人们决不能对一个被人描述为敏感的人作出评断。他们的性情更多的是对无足轻重的理由、而不是对那些关键的理由作出反应。他厌恶性格,怀着那种孩子在中年早逝的大人面前所拥有的可怕的优越感。他甚至在友谊和爱情中感觉到厌恶的气息,这一气息使每一个生物与其他的生物疏离,构成了个体的那种痛苦虚无的秘密。他甚至可能憎恨自己的理想,因为在他面前这些理想不是目的,而只是他的理想主义的腐化的产品。这些只是单个的例子和特例。与所有这些相适应的、或进而言之构成其原因的,是一种特定的认识姿态和认识经验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客观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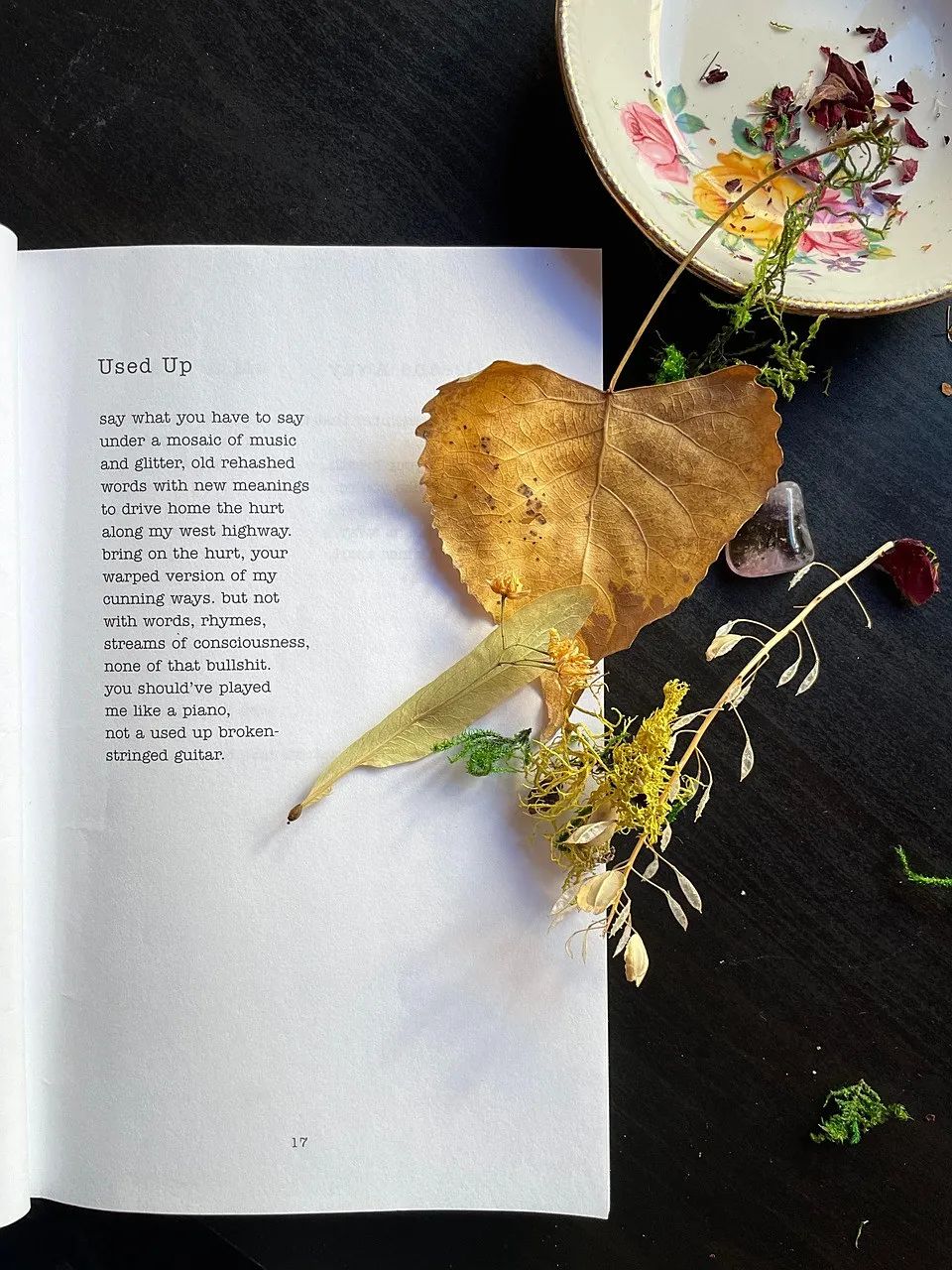
如果人们从诗人的对立面出发,就会最佳地理解诗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对立面是有着固定的点a的人,在ratioiid【拉丁文,意为“理性、合理”】领域中的理性的人。请大家原谅我遣词的怪癖以及它所根源的历史上的混淆,因为不是自然以理性为指归,而是理性以自然为指归。但是我找不到任何词语,它不仅曾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方法,而且还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成功;不仅仅表达出事实的被征服,而且还表达了事实的可征服性。这种自然在特定的情境下表现出的受之有愧的善意,当然随即在所有情境下都要求人的一种无计可施。这个ratioiid领域包括——初略界定——所有科学上可以系统化的、可以归纳为规律和规则的东西,因此它首先指的是物理的自然;但是只在少数几个成功的特例下包括道德的自然。其特征表现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单调乏味,表现为大量的重复,表现为事实之间的一种相对的独立,以致事实通常都可以被嵌入早已形成的规律、规则、概念之林,而无论它们被发现的顺序先后。但是它最主要的特征还是,事实在这个领域中可以被清晰地描述和传达。数字、亮度、色彩、重量、速度,这些是观念,但是它们的主观成分并不减轻它们客观的、可以普遍适用的意义。(相反,从一个非ratioiid领域的事实,例如从“他曾要它”这个简单陈述的内容中,如果没有没完没了的补充,人们决不能得出充分明确的印象。)人们可以说,在这个ratioiid领域中满布的是坚固之物的概念和未曾被考虑的误差的概念;充满的是作为某种实际上来自根基的虚构【原文为拉丁文】的坚固之物的概念。就是在这里,在最底层,地基也在摇晃,从逻辑上讲,数学的最深刻的基础也是不稳固的,物理的规则也只是近似而已,而天体也无非是在一个根本没有元点的坐标系统中运动。但是人们希望——不是没有原因——还能将一切理顺,而且在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就说过:“给我一个固定的支点,我可以把整个世界撬起”,它今天仍是我们执著于希望的行为表现。
从这种行为中,产生了人类精神上的团结一致,而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是以往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种教会的影响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也就丝毫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也试图在道德——最广泛意义的——关系上遵循同样的行动,尽管这在那里变得一天比一天困难。今天,连道德领域也在按照打桩的原则行事,把概念这一僵硬的沉箱——在它们之间张着一面由规律、规则和公式组成的网——垂放到这个很不确定的空间。性格、正义、规范、友善、绝对命令、所有方面的牢固即是这样一些桩,之所以在其僵化上维系,是为了能在它们上面固定这张成百上千的、每天都要求做出的道德的单个决断的大网。今天仍在起着影响的伦理——根据其方法——是一种静止的伦理,以坚固作为其基本概念。但是既然人们从自然走向精神的路途同时也是从一个僵硬的矿物标本室跨进一座充满无限生机的暖房,那么伦理的应用就要求一种很滑稽的限制的技巧和撤消的技巧,仅其复杂程度就足以让我们的道德露出没落之态。大家试想想“你不该杀生”这条戒律演化的过程这个普通的例子,它从谋杀发展到殴杀,发展到杀死负心人,发展到决斗、枪杀直至战争,如果人们为此找一个统一的理性公式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它就像一个筛子,在使用它的时候,网眼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它的牢固的编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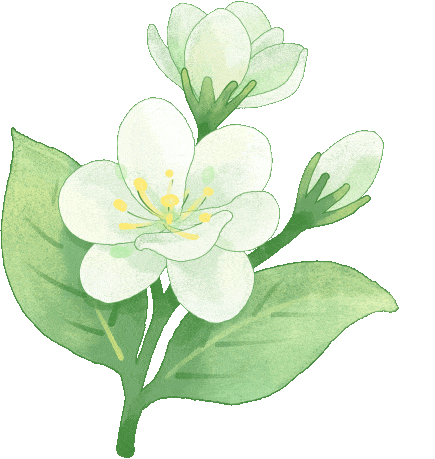
因为在这里人们久已踏入非ratioiid领域,对我们来说现在道德只是该领域的一个主要的例子,正如自然科学一度是另一个领域的主要的例子一样。如果说在过去,ratioiid领域是“有着例外的规则”主宰的领域,那么现在的非ratioiid领域则是“例外在主宰着规则”的领域。也许这只是一种层次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又是如此地极端对立,以致它要求认识者立场的完全的倒转。事实在这个领域并不臣
我不能肯定,切割得这么复杂,是不是有些迂腐之嫌,也许这只是老生常谈,在这里没有被讲到的,尽管它也是同样的重要,我只好请大家原谅:尤其是同所谓的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分野,这并不简单,但是却证实了上面所说的。但这些研究是被评价为迂腐还是被评价为不可或缺,最终只能根据赋予一项证据的重要性来评断:这项证据是,是世界的结构而不是人的天赋的结构把诗人的任务指派给他:他担负着使命!
人们经常把这样的任务指派给诗人,要他做时代的歌手、美化者并且把它——按照它所是的情况——带进语词的过度浮华的空间;人们要求他为“好”人树立凯旋柱和把理想神圣化;人们要求他有“感情”(也就是说当然只是特定的感情),要求他对批判的知性说不,因为批判的知性缩小了世界,它从世界那里拿走了形式,正如一座坍塌的房子的残垣要比先前的房子小一样。最后人们还(如在印象主义的实践中,它和昔日的新唯心主义有着共同的命运)要求诗人把事物的无限性同事物关系的无限性相混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完全错误的形而上学的激情:所有这些都是对“静止”之物的调和,它们的要求是同道德领域的力量相悖的,是违背物质的。人们会指责说,这里所说的一切反映的只是一个纯粹智性主义的观点。那好,有些创作,它们与这里作为主要任务所考察的很少有关联,但同样是撼动人心的艺术品;它们有它们的美丽的血肉,而且这种荷马式的血肉的光辉穿越数千年一直照彻到我们。从根本上讲,这只是来自一些恒定地保留下来的或再次回归的精神的立场。但是此间业已完成的人类的运动,来自于变体。而且剩下的惟有这样一个问题:诗人应该是他时代的孩子还是应该成为不同时代的创造者?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著名小说家。1880年11月6日,出生于奥地利南部克拉根福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1903年入读柏林大学,先后攻读哲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190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一时期深受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尼采的“强力意志说”、克尔恺郭尔的存在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等学说的影响。穆齐尔1902年即开始着手然终其一生仍未告完成的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1—2卷,1930—1933),为他死后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今天,这部宏大的未竟之作(德文版厚达两千多页)已被人们公推为20世纪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3期,责任编辑:水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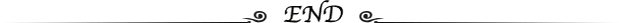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