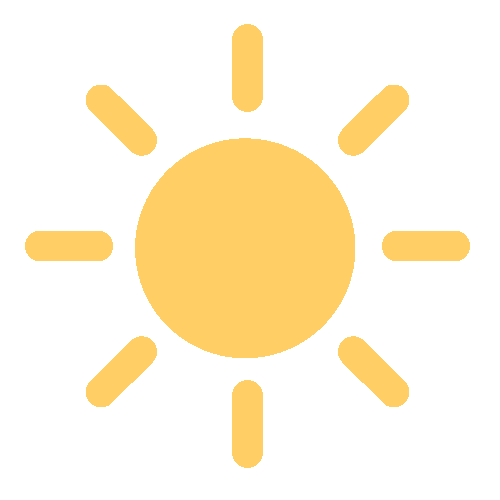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玛•库伊乌姆齐【希腊】:沼泽里有一些卑鄙的东西……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沼泽里有一些卑鄙的东西。除了罪恶、仇恨和错误,那里自带杀戮的天性,并不需要来一场战争就可以痛饮鲜血。它不区分敌人和朋友,像一场邪恶的瘟疫、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一张没有个性和性别的脸上。沼泽伸出双手,从这张脸上挖出双眼,剥掉皮肤,抽空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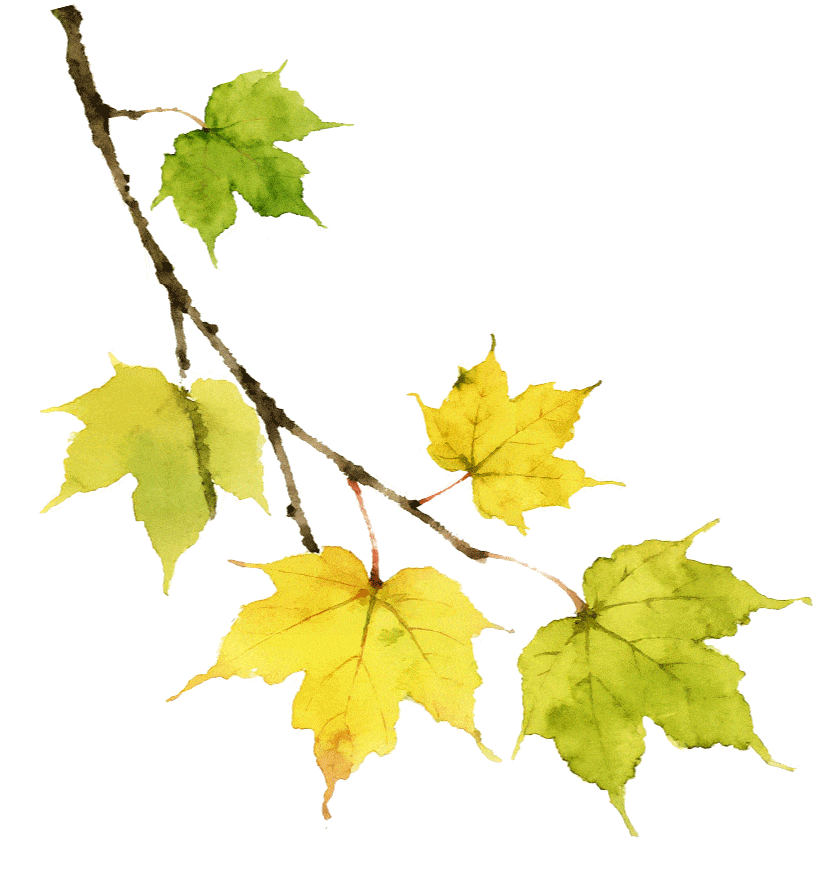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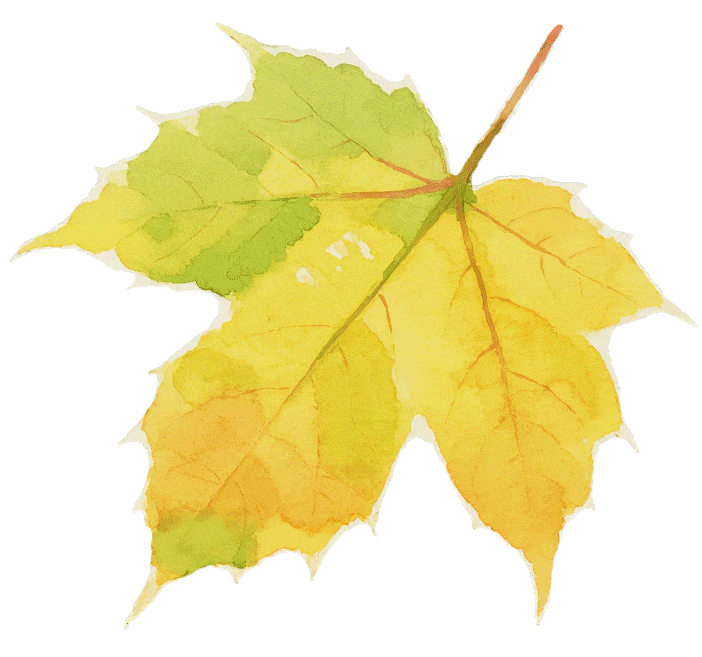
玛丽亚·库伊乌姆齐作 李维译
那时我还是一名助理医生,刚刚在瓦里亚村安顿下来。很早以前,这里曾是一片沼泽,可怕的沼泽,会吞噬人和动物。那时人烟稀少,房子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又过了许多年,沼泽干涸了,上面盖满了房屋。但据说,某些日子里,它会再度活跃起来,使整个村庄在一片黑色粉末般的迷雾中窒息。你能闻到死水的气味,村民们也变得疑神疑鬼、暴躁易怒,这种情况一般会持续几天。
一天,医生感到非常疲乏,便派我去探访他的一位病人——老卡夫里洛斯。
“今天你会看到沼泽之王,”他对我说,“卡夫里洛斯。他已经从王座上下来了,不过还继续在家里发号施令。所有留下来的人——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都得听他的指挥……注意,不要掉以轻心,沼泽可还是活着的。那里面会伸出手和脚来,过往的一切随时会把你抓走。不要让迷雾的浪漫蒙蔽了自己。那是莎乐美的面纱,她可是想要你的人头。内战【指发生于1946年至1949年间的希腊内战】期间,很多人消失在了那里。他们原本想去藏身,却被泥沼吞没。当时那儿只有一两栋房子。第一栋是卡夫里洛斯修建的,他很清楚沼泽是怎么把人拖进去淹死的。即便是现在,沼泽已经干涸,却还能吐出人骨。每当它醒来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就会记起之前的杀戮和那些死去的人,在迷雾中把尸身推向岸边。别笑,我的朋友。鲜血有自己的法则。你无法控制。那时,人们的头颅里蹦出了一些会说话的东西,理智给荒谬让了路。听听你的腕表发出的滴答声,时间在拉着你走,就像在拉一头拴着的野兽。
“沼泽里有一些卑鄙的东西。除了罪恶、仇恨和错误,那里自带杀戮的天性,并不需要来一场战争就可以痛饮鲜血。它不区分敌人和朋友,像一场邪恶的瘟疫、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一张没有个性和性别的脸上。沼泽伸出双手,从这张脸上挖出双眼,剥掉皮肤,抽空声音。你可以确定,这个卑鄙的东西在和你讲话。你可以感觉到它是在冲着你说话。泥沼把你身上的人性剥离,再把它变成某种非人性的存在。原本纯白的东西突然拥有了黑色的面孔。一条黑色的舌头舔着尖声祷告时露出的白色牙齿。这黑黑的舌头尝遍了一切,又厌恶地吐了出来。没有一丝光亮,某种不正常的、邪恶的东西在这片泥沼里晃动着,那是你的大脑。”
医生叹了口气。“去吧,”他说,“卡夫里洛斯在等你。天黑前赶过去,等回来的时候,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我困了,都是沼泽惹的祸,湿气快把我的腿都弄断了。到那儿之后,你就给卡夫里洛斯吃上镇静剂,不然他会用故事把你的耳朵炸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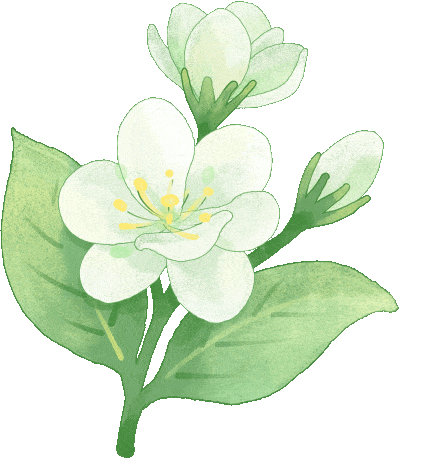
我拿上医疗包出了门。黄昏就要降临。树枝也无法托住迷雾。似乎有一只滤网正在将这里过滤。房屋、树木和人声都在消失,但同时又向我靠近。墙壁抓挠着我的后背,树枝挂住了我的头发。我退缩了,害怕冲撞到看不见的存在。某种东西和大雾碰撞的声音隐约传来。我像个半瞎子,靠着看不见的房子里发出的亮光摸索着往前走。嘴里像进了灰尘一样难受,手脚无比沉重,双眼刺痛。困倦不仅没有让我麻木,反而让我焦躁不安,跪倒在地。一道模糊的屏障高耸在我和世界之间,让我只能看清半步之内的景象。我陷入了恐慌,觉得自己可能再也找不到路了,将永远成为这里的俘虏。沼泽里的毒气——即便只是回想起来——会让我的身体陷入一种焦躁和神经质的敏感状态。在毒气的影响下,我感觉泥沼似乎正向外吐着回声,那是来自它自身力量的回声,我的双脚随之陷入淤泥中好几厘米。仿佛有一些手,一边把我的双脚往下拉,一边又把它们推回表面。
很快,我意识到自己在原地打转,完全迷路了。我几乎要放弃,任由自己困在迷雾里,下沉,被吞没,变成一具空壳……这时,传来一个声音——“到这边来,医生”——一只老妇人的手把老卡夫里洛斯家的大门指给了我。
房屋很阴暗,好像没有人住,但老妇人让我去敲门,说里面有人。
我推开摇摇欲坠的院门,脚下一滑,倒在一棵梨树的树枝上,像是有人用身体托住了我。我毛骨悚然,伸出脚,试探着寻找干燥的地面,但踩到的地方都很湿滑。我觉得沼泽已经吐出一些淤泥堆到岸边,形成了一个个小岛,而我会被拖进岛下泥坑的深处。
敲门之前,我在石头门廊的台阶上坐下来喘了口气。在迷雾深沉的幕帘中,月亮仿佛蒙上了一层黑色的面纱,布满灰尘的光线从面纱的孔洞里透了出来。
我懒懒地待在那里,仿佛眼前还有用不完的时间。不知过了多久,好像有人走过来坐到了我身边。一只手放在我的后背上。
我茫然地站起来,敲了几次门,没人回应。我屏住呼吸,侧耳细听。房屋里传来各种声响:有人在挪动家具,还有人在床上翻来覆去,轻声地喘气。我吓坏了,正要离开时,门吱呀一声开了,出来了一位个子很高的老妇人,手里擎着一盏老式的油灯。她高大的身材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
“请进,医生。”她一边说,一边退到旁边,几乎是推着我往里走。我必须仰头才能看到她那张严肃的脸。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高傲和嘲讽。
我犹豫了一下,跟着她走进客厅,在一张快散了架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或者说陷了进去。老妇人擎着灯消失在一扇门后,把我留在黑暗里。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低语声、脚步声、拖动物品的声音,仿佛有人在小声争吵。突然,有个东西从天而降,落在了我身边。原来是只体型巨大的猫,双眼像审讯灯一样忽闪着。
我的心怦怦直跳,干咳几声以表明自己的存在。响动停止了,整个房间又陷入了墓地般的安静之中。
就在我决定离开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仿佛有台拖拉机驶了过来。转眼间,老妇人推着辆轮椅出现在我面前。轮椅上坐着一个极其肥胖的男人:卡夫里洛斯。
他将手举过头顶比划了一下,老妇人便退了下去,把他留在客厅中间。卡夫里洛斯转着轮椅巨大的轮子,在一张小桌旁停了下来,离我几步之遥。
“你身边有盏小灯,”他说,“把它点上,我受不了太强的光线,这个灯光足够你写处方了。”



他块头很大,大腿极粗,短睡裤下露出两只肿胀的脚,上面满是糖尿病造成的伤口。一只脚的趾头已经切除了,剩下那只脚的脚趾也是黢黑的。他的上身像女人一样窄,双肩塌陷,满是褶皱的脖子上端坐着一个硕大的光头。表情生硬的脸上,两只眼睛像两片干枯的烟叶,在黑暗里闪着光。那目光似乎能进到你的脑子里,读取你的心思,甚至会把它拽出来,翻来覆去地把玩,怀疑地审视,最后满不在乎地扔掉。
他的儿子出现在他身后,也是个大块头,肚子挺得很高,两只眼睛在肌肉松弛的脸上半闭着。灯光穿透了他稀疏的发丝。
我朝他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打开医疗包。
老妇人几乎是立刻走了过来——巨大的身影映在褪色的墙壁上,屋里越发显得阴暗了——手里端着一大壶热茶和点心。她示意卡夫里洛斯不要碰这些东西,老头却没有理会,往嘴里塞了两小块库鲁里点心【一种希腊传统甜点】。老妇人只给我一个人斟满了茶,也没有再拿别的东西过来。她把父子俩的药盒放到桌子上,就消失在客厅深处的一个角落里,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玩起了扑克接龙。在这么暗的地方怎么能看得见呢?我不禁感到疑惑。她仿佛听到了我思考的声音。
“这是我常走的路,”她说,“我知道路线。这条路上没有警察,也没有士兵。干什么都可以。”
“没有规则吗?”我问。
“这就是游戏的关键。你要能够凌驾于规则之上。只有凌驾规则,你才能学到东西。就是这样。不然,卡夫里洛斯现在就会跟他儿子一样,成为一只安静的绵羊,任何人都可以榨取它的乳汁。这就好比你不可能既不失去贞洁,又能生孩子。只有摧残、侵犯才会带来延续。”
“你说得太多了,老太婆,闭嘴吧。”卡夫里洛斯的声音传了过来,“光是你那张脸就够让我烦的了。”老妇人扬起宽大的手掌,对着他张开五指【希腊文化中表示侮辱、诅咒的手势】,说道:“我能说什么?我看到的不光是你的脸,那些东西可比你的脸糟糕多了。”
“这个吉普赛女人该管好自己的舌头了!因为帮我换过内衣,就觉得可以骑在我头上了。笑一下,让大家看看你还有几颗牙,老太婆,看我不把你剩下的牙全给掰下来!因为上过三年初中,她就自以为比我更了解世界。滚去读你的所罗门智慧书吧,闭嘴。要不是因为困在这个笼子里,我倒要看看你还敢不敢对我抬高嗓门,就算是抬起眼来看我,量你也不敢。”
“对,没错,”她说,“轮椅也没法把你这狗东西变得再坏些了。”
“这母狗一块糖也不给我吃,她以为可以把我藏在她的小裙子下面,可我还有小绵羊——我的儿子——他可以分分钟拿来任何我想要的东西。”
女人厌恶地看着他:“连我的手都知道你有多混蛋,胖头佬,就你自己不知道。”
男人伸出手,抓住小猫的脖子朝她扔去。女人俯下身,小猫轻轻落在她的扑克牌上。


我弯腰查看他肿胀的双脚,检查了上面的脓疱,问他有没有经常贴膏药,然后迅速结束了检查,因为病人的身体散发出一种氨气和酒精混合在一起的恶臭。我有一种荒唐的感觉,那就是他会抬起病腿,一脚踹到我脸上。因为他已经把我的大脑扔在地上,看穿了我的心思。我觉得糖分正在蚕食他的身体,很快,他就会失去双脚,成为一根圆木,最终这根木头也会被彻底吃掉。疾病也是一种沼泽,正在缓慢地吞噬他。
我又坐下来,检查了药品,然后打开处方本。老人命令儿子站直了,后者照做了。
“天气变得很糟了,医生,不是吗?那些年沼泽还活跃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上哪儿知道去?”他说,并不在乎我是否回答。
他恶狠狠地看向自己的儿子。
“你也听着,蠢货,学着点儿,要知道自己的家史。我猜你还记得那场屠杀,对吧?”
儿子开始抽泣。
我看着他们,并不觉得好奇,几乎可以说是无动于衷,似乎与他们有千里之遥。
“好吧,在一个这样的夜晚,医生,”轮椅上的男人把身子探向我,小声说,“在一个和今晚完全一样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来了四兄弟要把我干掉。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沼泽没有把他们吞掉。当时我正在马厩,有匹小马刚出生,但是情况不大好,一直在喘息,眼看要断气了。”
他又一次转向儿子。
“他们踹开门,进到屋里。你妈妈正在厨房做饭,上上下下地忙碌着。不知道她错把那些人当成了谁,因为她说:如果你们想吃点儿东西,我这里有做好的肉,还可以喝甜葡萄酒。你还记得那些人说了什么吗?我们是要吃人肉、喝人血的。他们是四个人,拿着手枪指着你、你妈妈和你死去的妹妹。最后进来的那个人听到了马的嘶鸣,来到马厩。我当时正躲在马背后。突然,身边一只母鸡咯咯叫起来,我立刻把它掐死了。那人看到小马奄奄一息,就弯下身去抚摸它。我冲上去,拿刀捅了他的后脖颈,又夺走他的手枪,跑回屋里,眨眼间又杀死一个家伙。剩下的那两个跑过来追我,我就把他们引向沼泽,沼泽像一张巨大的嘴,一口把他们吞了进去。我认识他们——是从上法内罗梅尼【希腊雅典地区的一个地名】来的四兄弟——他们原本兄弟七人,我和侄子布拉一个半月前干掉了三个。这些人长得实在是太丑了,光凭这一点就配得上吃枪子儿。
“你妈妈喉咙受了伤,从此就不能说话了,你妹妹死了,你的脸色变得像石灰一样惨白,吓坏了。你妈妈的血像喷泉一般涌了出来,我用她的头巾捂住伤口,她把手指压在上面,像在堵一个瓶口。她浑身抽搐,扑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却哭不出声来。
“我回到马厩牵马,想去找医生,却发现小马驹活了过来,它舔了那个死人的血。我浑身的血都在沸腾,脱下死人的血衣,给小马盖上,它不能受凉。我把这些死人——除了你妹妹——全都扔进了沼泽里,几分钟之内,死人全给吞没了。蚊子像饿疯了一样咬我……你知道他们对我们做了些什么吗?你记得吗?”
他的儿子发出一声怪叫,像树叶一样颤抖起来。眼睛直直地看向前方,他跪倒在地板上,开始祷告。
“你瞧,”老卡夫里洛斯说,“他现在正看着那四个男人放下手枪,来抬他妹妹的尸体。他情绪上来的时候告诉过我。看,这个蠢货正在为她们祈祷呢……谁能告诉我,我怎么会生下这么个没用的东西……”


灯光仿佛刺痛了我的眼睛。
老妇人走了过来。“别吓孩子了,”她对老人说,然后又转头对我说道,“糖分让他满嘴胡言,行了,你该看的也看了,现在他该睡觉了。太晚了,给他开上胰岛素和镇静剂,把处方放到桌子上,关上门赶紧走吧,雾已经没那么浓了,还能找到路。”说着,她开始推动轮椅。
那儿子此时已经不见了,仿佛有人在画布上给他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现在又擦掉了。
卡夫里洛斯推开妇人:“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挥了,去死吧,让开……”
她又对他做了一个诅咒的手势,摇着头离开了。
“唉,医生,那时候我的手没有耐心,出手比动脑子快。我没必要那么做,没必要用绳子套着他的脖子,在泥沼里来回磕他的脑袋。可是他的死不能让我解气,我要让他受罪。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我的手比脑子先明白这一点……
“有人给我写了几封信。他们家族里的一个人。就算我认字,我也不会去读。他们能说什么我喜欢听的呢?还有,我的女儿呢……他们能说她什么?她死了,又复活了,每天在这些屋子里走来走去。现在怎么办?我说,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不可能重来了。每当我躺在床上时,就感到床是冰凉的;每当我侧过身时,就能感觉到她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我能闻到她头发里泥土的味道。可是,我已经亲手做了一副棺材把她放进去了啊。十字架传递着她的信息,她在这房子里走来走去,想要什么?有时候,她从相片里走出来,坐在门廊那里,就那么看着。她想看什么?看到我还不够吗?她还想看些什么?
“即使后来事态平息了,我也不想离开这里。我把沼泽抽干了,免得里面的尸骨喋喋不休;还在这里盖起了房子。为自己盖的,我曾经这么以为。可是你也看到了,其实我是为所有死去的人盖了个家。那些尸体蜷缩着挤在一起,睡在我院子里的树上。到了晚上,他们的叹息声像割下的稻草一样扑簌簌掉下来。路中间会突然长出一只手、一根手指头,可没有人能看得到,没人会把它们捡起来。因为我们只有什么都看不见才能生活下去。
“我的妻子去世前又开口说话了。她之前一直是用另一种语言在说话,就像是玻璃瓶碎片发出的声音。后来,她把一根手指放到喉咙上,我就能听清她的话了。她一直说,要让她穿着那条花裙子下葬,要让她在黑暗中身上也有鲜花;不要给她穿鞋,她要光着脚,在‘下面的世界’里轻巧地走路。你必须穿上你的黑色西装,绝不能穿着睡衣过来,必须藏起你满是伤痕的脚,她这样命令我。她不希望别人看到我们当时真实的样子。
“她下葬那天一直在下雨。我希望她不会怨恨我没去参加葬礼。田野当时已是一片金黄,那么热烈,我看了一整天。我想看地面上的东西,不想看地下的。女儿站在我身旁。这是正常的,她说。
“有时候,我的妻子会坐在小台阶上吃葡萄。这是我自己拿的葡萄,她说,不是你拿给我的。你不想承认我已经死了。她伸开双手把头发抓起来,那些头发缠在她的指尖上。你看,她说,头发都明白,我已经死了。
“好多年前,这里来过一个大学生。我来研究沼泽,他说。快走吧,我对他说,沼泽不适合你。它不懂什么意识形态,它会把你拉下去,连同你的那些自以为是。可是这里已经没有沼泽了,他说。你这么认为?那你看看我,看看沼泽正在对我做些什么。它在吃掉我的身体,至于你,它会吃掉你的脑子,无论你多没脑子。谁会吃掉我的脑子?他问。那些死去的人,我回答道。他嘲讽地笑了,嘴里还叼着根稻草。他不知道,这根稻草是内脏生出的芽,是心脏长出的苗。我对他说,沼泽不适合你。这里一直都住着别人,你的家不是你现在待着的这个地方。你的家应该是你的父辈安息的地方。将来,那里的十字架上也会写上你的名字。否则,你将永远是一个异乡人。那些后来的人在这里种树,开垦农田,种植小麦,和沼泽里的死人发生冲突。这里是死人的家,后来的人却赶走了他们。到处都是尸骨。那些后来者甚至不知道死者的名字,但是沼泽知道。每当沼泽想起这些人时,就会把他们翻上来,把你们吓跑。死去的人不需要做买卖,不需要兜售门票来供你参观。沼泽里到处都是隐形的无名十字架。它不需要弯下腰来看这些十字架,它全都认识。


“大学生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和衬衣。我对他说:‘埋你的时候肯定不会让你穿着这身衣服。我想穿着睡衣下葬,如果到时候我还有腿能套进裤子里的话。’那个大学生以为我对他的了解不及他对我的了解。他根本没用脑子想过,他知道的都是别人告诉他的,而我知道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
卡夫里洛斯在轮椅上睡着了。老妇人走了过来,扔给我一条毯子。“躺下睡吧,”她说,“变天了,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你走不了了。”她推着卡夫里洛斯的轮椅走开了。在消失之前,她还嘟囔着:“世界已经存在了这么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可你我不行。人就是过客,不过是让世界运转的玩具罢了。一场梦而已……快睡吧。”
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屋里门窗的合页吱呀作响,仿佛在因疼痛而呻吟。到处弥漫着潮湿粘腻的热气。沼泽似乎渗进了房屋,正在慢慢吞噬这里。
我无法控制困倦感,无力地靠在沙发上,任由睡意令人窒息的手指摆布。小猫挠着我的脚,蜷缩在我身边。轮椅的声音渐行渐远。我感到这个世界自身,还有人们,正在远去,就像一个逝去的画面。有人让这个画面在某个瞬间显现,但不会让其复现。卡夫里洛斯和我都是照片,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拍摄了下来,而黑暗——并非光亮——又将它烧毁。
玛丽亚·库伊乌姆齐(1945— ),希腊当代著名作家。已出版《狂野的天鹅绒》《你的房间为何这样冷》《永远》《一触即发》等短篇小说集,《如果天不亮》《高烧的夜晚》等长篇小说,多次获得文学大奖。库伊乌姆齐的作品多以穷人、弱者等边缘群体为主人公,着重探讨人性在贫穷、战争、情欲纠葛等困境中的底线。
《沼泽》选自库伊乌姆齐荣获希腊国家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小说集《一触即发》(卡斯塔尼奥提斯出版社,2016),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库伊乌姆齐幼年时亲身经历了二战和希腊内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对战争的反思是她作品的一大主题。在《沼泽》中,作者采用象征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反思:沼泽既是真实存在的地理环境,又象征着战争的余孽、人性的黑暗以及命运的无常。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4期,策划与责任编辑:赵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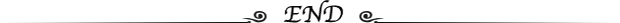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