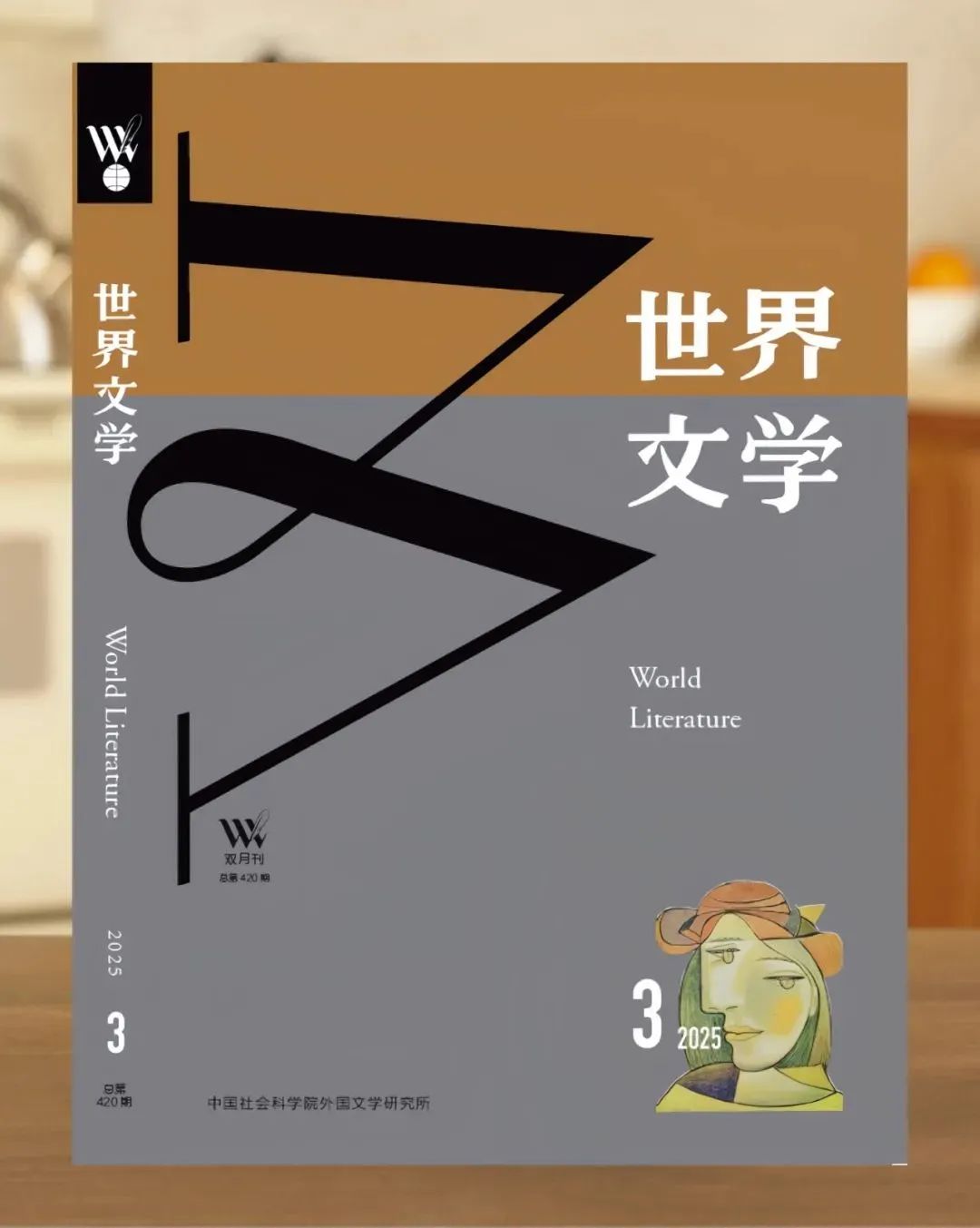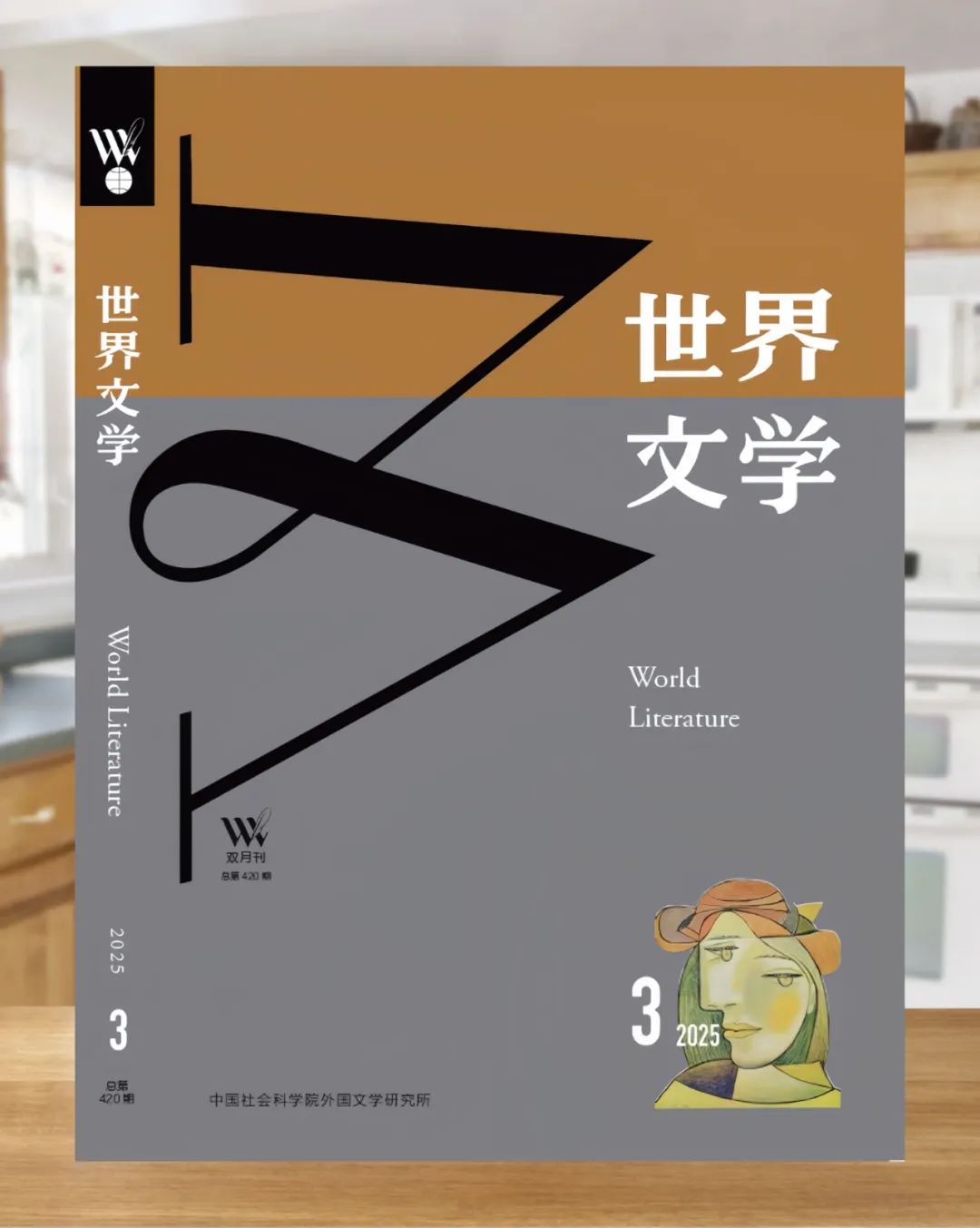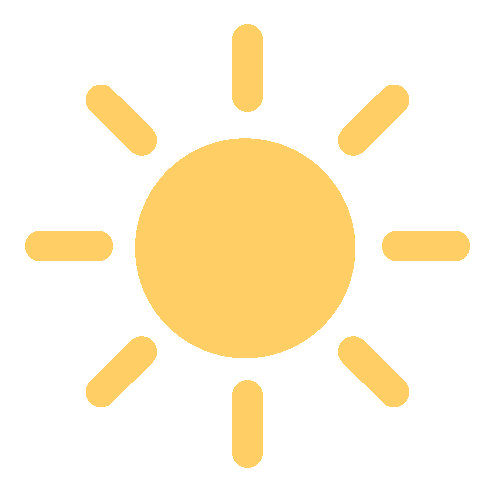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璧人:优雅、从容而强悍——读韩江随感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少年来了》写的是痛,《永不告别》写的是爱,这爱是在痛中表现的,面对同样的邪恶、残忍,由痛艰难地走向爱……《少年来了》直接写痛、写历史,《永不告别》间接地写,通过他人回忆、历史资料的逐步披露,写下一代人的、亲属的痛。这些碎片拼凑的历史仍然沉重、震撼,倍经摧残的爱也更显坚韧。或许这是作者在这部书中没有直接写历史的原因,因为她想写的是穿过痛史的爱。


璧人
去年诺奖颁布后,我开始找来韩江老师的作品阅读,先读了电子版的《素食者》《白》,感觉很不错,于是又买来《少年来了》《永不告别》读,很受震撼,最后读的是短篇集《植物妻子》。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阅读,我想说:形象纤柔的韩江老师贡献了力度强悍的伟大作品。
我习惯每读完一本书后写点随感,以下是我读韩江老师作品的随感,与同好者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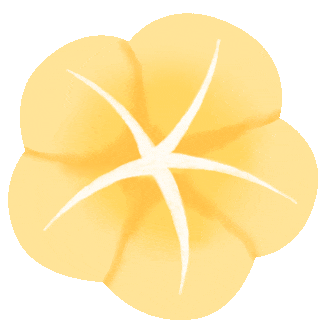
刚开始阅读时,这部作品让我很容易地想到了村上春树:恬淡的文风,平和的节奏,带着点忧伤。但是我马上发现,这些只是前奏,只是表面——即刻,文字变得犀利,叙述转入深沉,而这正是村上春树所欠缺的,他始终浮在表面,始终轻飘飘的。
然后我联想到卡夫卡,英惠、仁惠姊妹及仁惠丈夫的内心都在变形。最犀利、最直接的当然是英惠,仁惠和丈夫因为英惠的刺激诱发出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区别在于,仁惠丈夫醒悟在先,借机释放了,仁惠最后理解了英惠,也发现了自己内心的阴暗面,但最终如何面对和处理自己和英惠,仍是个谜。卡夫卡开创的文学世界到今天依然生机勃勃,从中发掘出的资源源源不绝地滋养着今天的文学世界。
英惠的内心是如何形成的,作品并未进行充分展现,只是给出只言片语的信息碎片作为暗示,比如父权的野蛮、家庭的冷漠、女性社会地位的弱势,但这些并不能理解为全部原因。作者也没有给出英惠决定素食的原因——这不重要——,而她对于英惠坚持素食的决心却刻画得细腻、惊心动魄,似乎这才是叙述的重点:个体对自身选择的生存状态的坚持和为此甘愿做出巨大牺牲的勇气,应该才是这部作品的指向。
英惠的梦、仁惠丈夫的艺术追求,是生命深处的电光一闪,点醒了生命;接着,现实却无法承载被点醒的生命,无法把控这电光一闪造成的撞击,导致了命定的悲剧。你可以发现,可以追求,但也必须承受,结果往往是激烈的,也是璀璨的。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性、惊悚等俗套的元素熔炼出了诗意,三个部分三种气质,并统一于一种格调,整部作品堪称一首长诗,沉淀进人心深处。
与多数诺奖作品相比,这部作品或许还不够凝重,但韩江的获奖却在宣示一种融合了新世代特质的全新文学形态的成功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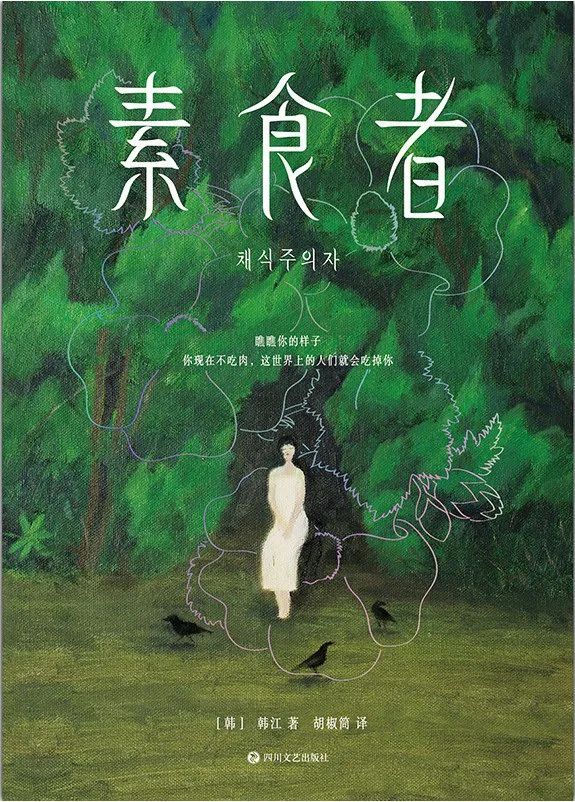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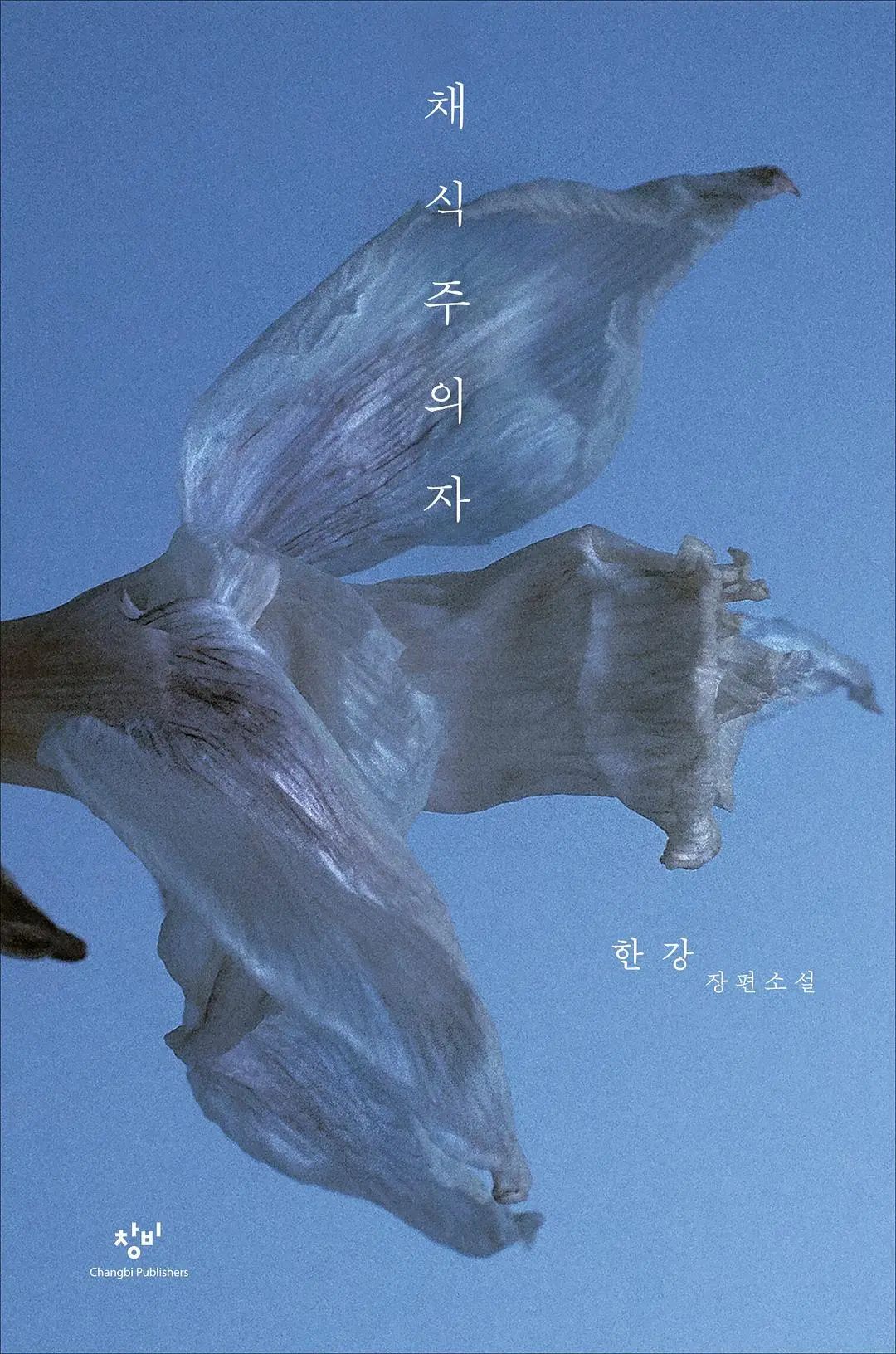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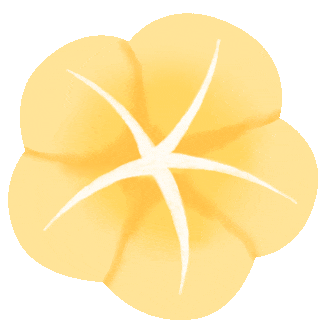
大体上看,这部作品具备了简单的情节、人物塑造、时间线的联络、想象的虚构,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小说,但就其总体内容和行文风格来看,不如说是一本散文集、箴言集、随感集,只是借用了小说的结构方法。《白》语言优美,意象动人,有些思考也颇有深度,值得阅读。这种写法对于小说和散文创作都有启发,可以视作跨文体的创作。
结合《素食者》,可以看出韩江老师是一位有奇思妙想的作者。这种奇思妙想不是轻飘飘的,而是一种杰出创作力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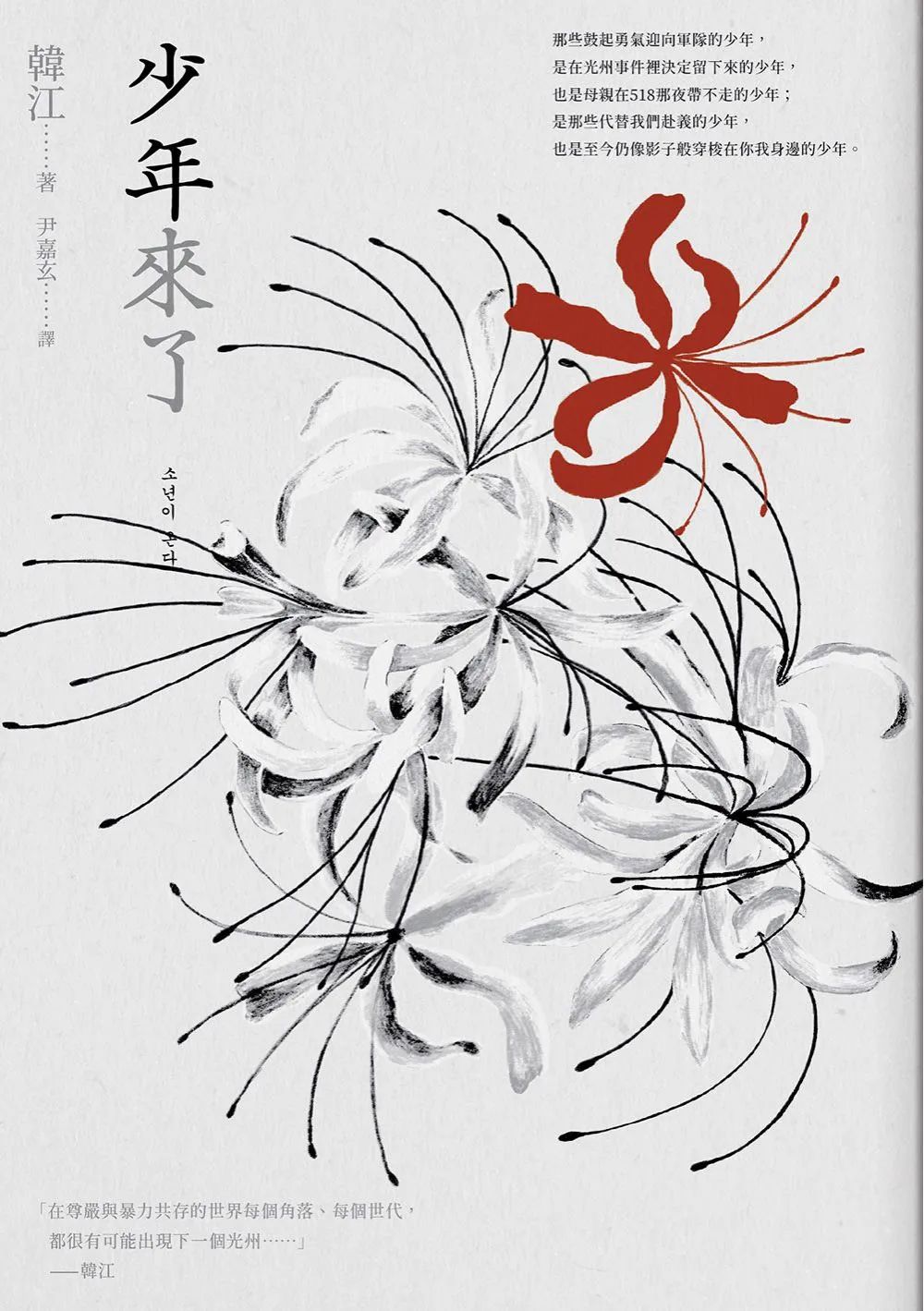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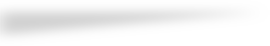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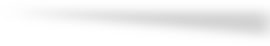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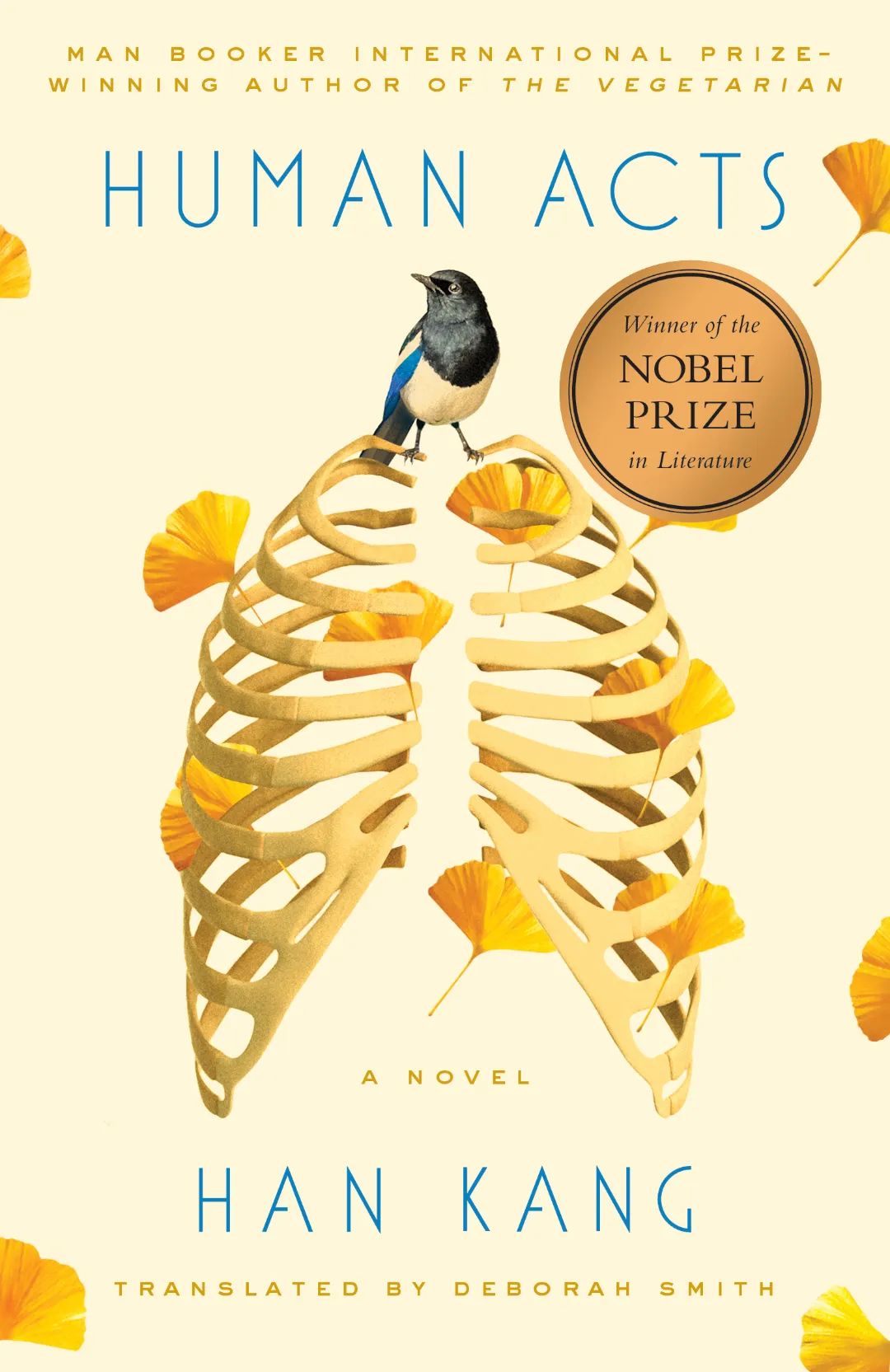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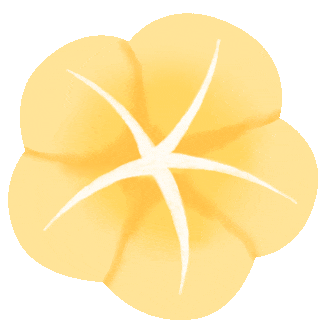
读《素食者》时,我感受到作者的犀利、冷静,读《白》时,可以隐隐窥见作者对时代、历史的思考,而在《少年来了》中,这些内容都清晰地浮出水面,得到集中体现。
这是一部少有的直面死亡的作品,第一、二部分对死亡细致、正面的描述令人窒息,这种冷静、勇猛的笔触是少见的,尤其是出现在一位看上去如此纤弱的作家笔下,令人震惊。有了第一、二部分对死亡的沉重呈现,后面几部分对人物心灵创伤的表现才顺其自然。历史并未过去,而是深深地刻在每个人心间。
作品采用第一、三视角交叉的叙述,那个以“你”称呼所有人物的“我”最后表明身份是作者自己。这种叙述打破了作者与作品人物之间的界限,作者进入作品,与人物融入一个时空,不同于常见的多角度叙述,很妙。
故事以一九八〇年韩国光州运动为背景,当下很少有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写作。作者对人性的展现和逼问及其对邪恶的痛斥极有力量。她所采取的手法是瞄准个人,展开细腻、深入的内心描写,不仅独特,还令历史不再冰冷,鲜活如在眼前。这似乎借鉴了个人口述史的写法,选准代表性个体,进行深入的表述,完成历史的形象化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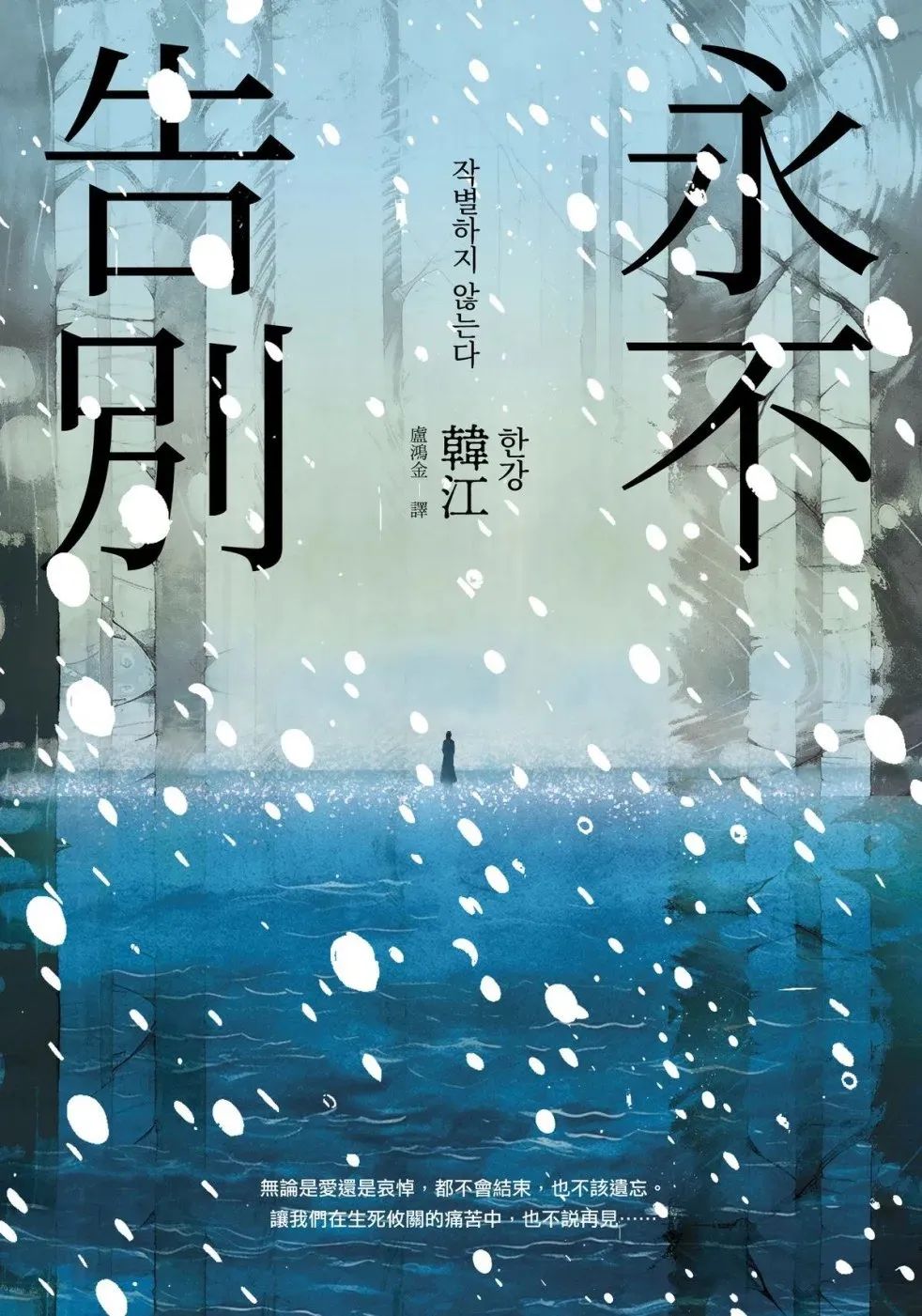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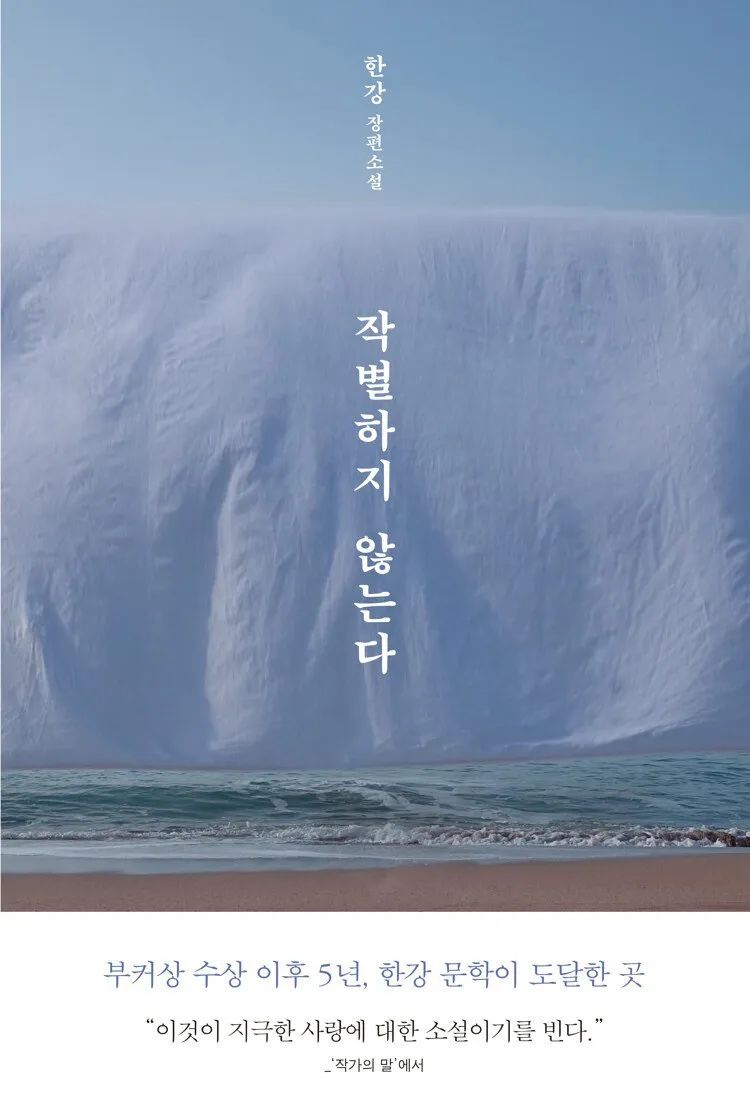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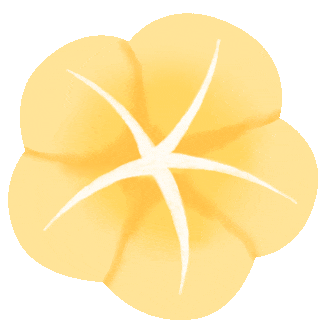
《少年来了》写一九八〇年光州民主运动,《永不告别》写上世纪四十年代济州岛集体屠杀,这种深刻的大历史题材书写真是不多见了,我想再一次向这位纤柔的作家致敬。作品开头部分庆荷的叙述基本可以视作韩江的自白,她深陷在《少年来了》创作带来的心灵震撼中,将前一段痛史写作引发的情绪带入了又一段痛史故事之中,完成了历史与历史的沟通,也增加了作品的厚度。
《少年来了》写的是痛,《永不告别》写的是爱,这爱是在痛中表现的,面对同样的邪恶、残忍,由痛艰难地走向爱。作者说这部小说拯救了她,可能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作者还说,这是一部关于极致之爱的小说,其极致或许就来自于极度的痛对爱的淬炼。
《少年来了》直接写痛、写历史,《永不告别》间接地写,通过他人回忆、历史资料的逐步披露,写下一代人的、亲属的痛。这些碎片拼凑的历史仍然沉重、震撼,倍经摧残的爱也更显坚韧。或许这是作者在这部书中没有直接写历史的原因,因为她想写的是穿过痛史的爱。
雪和冷贯穿本书主要故事的始终,定位了作品主体的美学格调和气质。最后的那截脆弱、温暖的蜡烛极具象征性,那是爱,是沟通生与死、历史与现实的关键。
由庆荷的难耐的热开始,转入她和仁善的雪和冷的世界,是从一场煎熬进入另一场煎熬的譬喻。庆荷或许可以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因为仁善的痛分担了她的痛。这于她个体是幸运的,于人类整体却是悲哀的。一滴痛苦的水在痛苦的海洋中得以生存。
最后,庆荷与仁善是生是死,作品并没有给出答案。或许,她们已经跨越生死,成了生死界外的叙述者、阐释者。这样的处理有些玄,也有些妙。
面对这样的沉痛,韩江的叙述也是优雅、舒缓、从容的,她对情绪与节奏的杰出把控令人吃惊。
不同角度叙述的穿插或许显得有些混乱,但整部作品光芒四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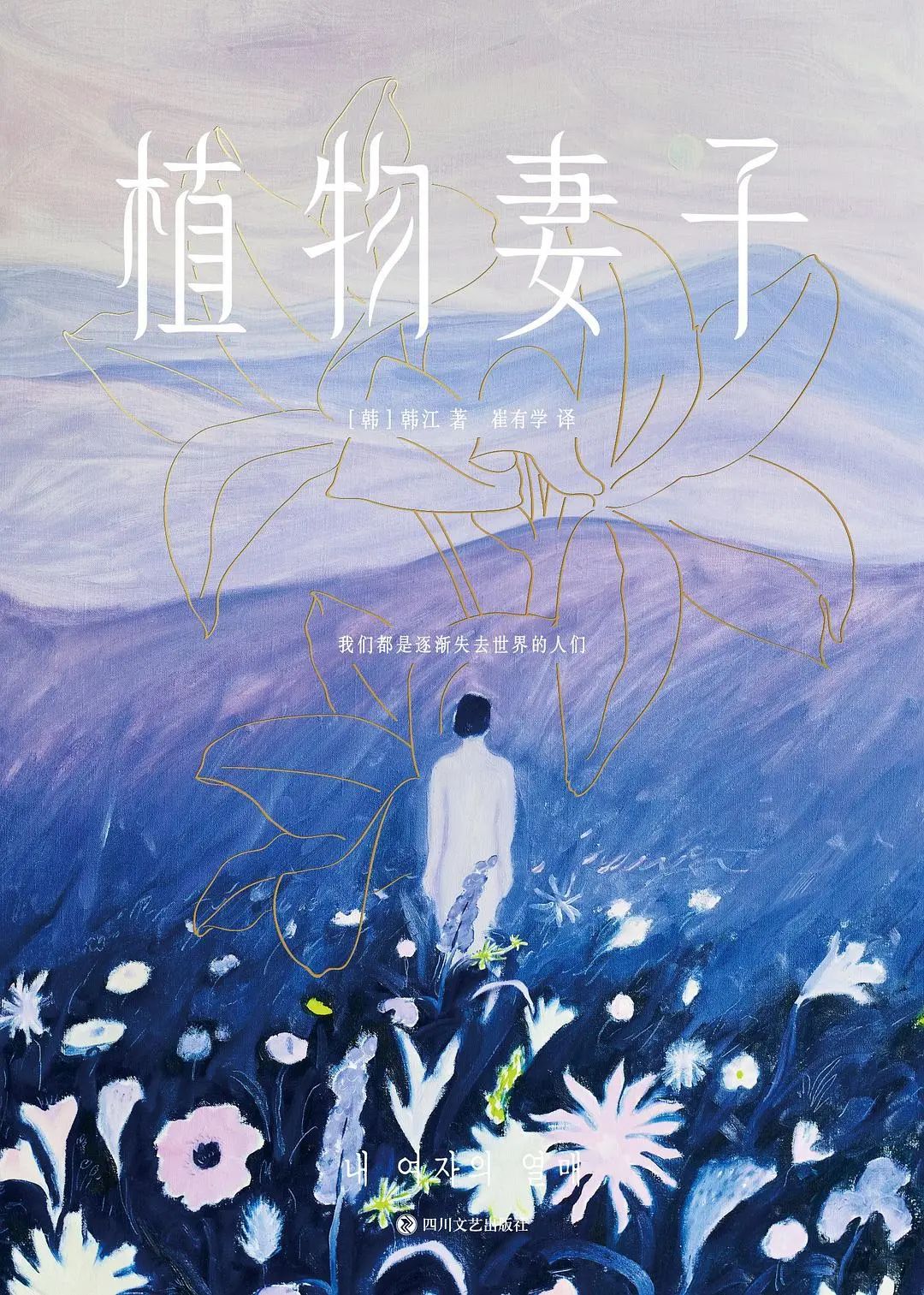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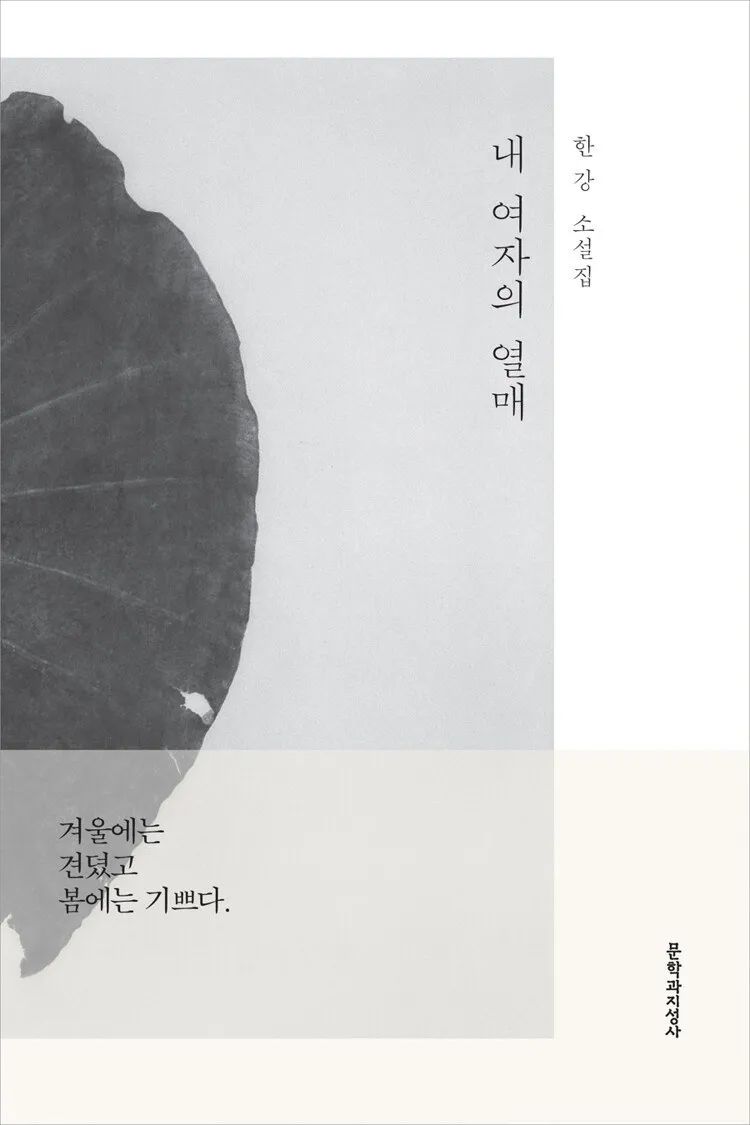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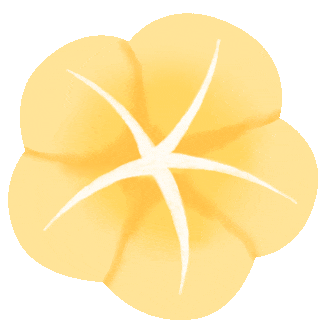
韩江的人物总是孤独、压抑、沉默寡言的,她的作品总是冷隽的,叙述舒缓,语言富有诗意,画面感很强,情绪不泛滥,压抑着。这在作家中是一种少见的、可贵的品质,有很多作家不懂得控制自己的表达欲。
韩江笔下人物的言行有一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排除了外在干扰,从而使得对人物内心的挖掘以及人物自身的思索和感受能够专注而深入。这是一种高明的处理方式。写作者似乎真的没必要把人物完全暴露、缠绕于所谓的现实中,因为事实上不管怎么写,写出来的现实总是不完全、不真实的,甚至是虚假的。那么不如直面独特的人物及相应的主题,塑造一个有针对性的、不隐晦其设计感的现实,给“ta”一个“ta的世界”。当然,这个“ta”和“ta的世界”必须有实在的基础,经得起逻辑、情感、思想的推敲。这很考验作者,否则就会造出一个“怪异”的东西。这让人想起“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环境”这类概念,以及贯彻此类概念的“典型作品”。但事实上这跟“ta”和“ta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典型”对应了一种呼应,本质上是大众化的提纯,但“ta”和“ta的世界”不要求呼应,是独特的、个人化的,希望得到认识和体悟。虽然这个“ta”和“ta的世界”可能具有代表性,但是这种代表性是不自觉的,只是将其代表的群体自然地“显性”出来而已,不同于“典型”所代表群体的高姿态和高纯度。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区别。
包括几部长篇小说在内,韩江的故事都比较简单,但人物的内心都是深邃、复杂的,这种强烈的对比产生出鲜明、凌厉的艺术效果。这也是很现实的:表面上每个人都过着一样的生活,太阳底下无新事,而事实上千人千面,人心隔肚皮。似乎简单、单一的现实抹平、掩盖、伪饰了人心的差别,正是这种忽略和强制抹平的态度造成并持续加剧了人的孤独及因此而生的痛苦。故事似乎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永远无法抹平的人心丘壑,而作家的笔是要刺破现实的表皮、伸到下面去的。这是另一种冰山理论。
这几部作品的人物都是卑微的,每个人、每一种卑微都有切实的痛感,都是伟大的,哪怕是傍晚时分的流浪狗、流动商贩、跑腿的劳工、透明般存在的比丘尼。
《植物妻子》被认为是《素食者》的前身,前者的女主人公是被爱着的,后者的女主人公是被嫌弃的,不过结局又是一样的。相同的结局让周围人对她们的态度差异变得不再重要。什么是重要的呢?是作为女性本身的弱势地位和无法挣脱现实困境的无奈。设定不同的人物境遇或许体现出韩江对女性的思考。
韩江的写作着眼点很高,这让她看得更深,写得更有力量。这也是杰出作家与平庸作家的本质区别,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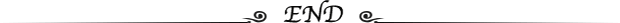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