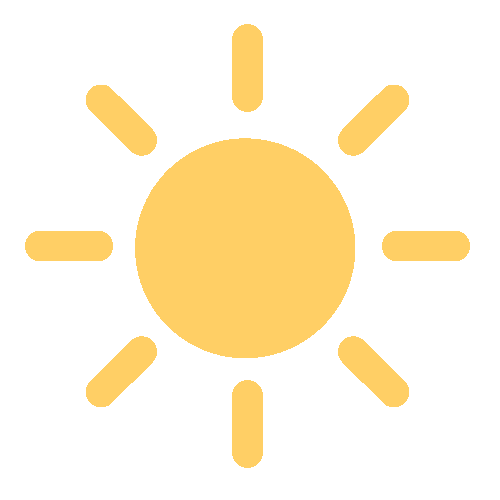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尼•华金【菲律宾】:五月节前夜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他猛地推开窗户,向外看去——发臭的街道中世纪的影子;几盏街灯闪烁着,最后一辆马车正当啷当啷地驶过鹅卵石路;几不可见的黑色的宅子仿佛在向马车轻声说:“嘘,嘘!”

尼克·华金作 郑友洋译
舞会应该在十点钟结束,这是老人们定下的规矩;可现在已快到午夜了,四轮马车才赶到门口列队接人;仆役跑前跑后,手举火把为离开的客人照明;要留宿的姑娘们即刻被赶到楼上的卧室去了,而聚拢过来向她们道晚安的小伙子们,假模假样地叹息几声,发几句牢骚,对她们上楼而去以示抱怨;他们嘴里说着自己有多伤心,但转眼就扭头走开,去干完剩下的潘趣酒和白兰地;他们早已喝醉了,满怀炽烈的情绪——欢笑、傲慢与放肆——因为他们是刚从欧洲回来的公子哥;舞会是为他们举办的,他们跳了华尔兹、波尔卡,自吹自擂,趾高气扬,彻夜地调情,到现在仍毫无睡意;在这个湿润的热带夜晚?不,天呐,不!在这神秘的五月节前夜,不能就这样睡过去!入夜尚早,夜色撩人,要是不出门做点什么,简直有病!有人嚷着去邻居家唱小夜曲【即菲律宾传统的求爱习俗Harana,由男子在夜间到女子的窗下唱歌求爱。其中,吉他是最常用的乐器,而固定曲目则体现了西班牙音乐、前殖民地时期本土音乐和他加禄语诗歌的融合。该习俗的重要特点是在夜间进行,求爱的男子通常有亲人、朋友作伴,是一项社交活动。它始于中世纪欧洲,经由西班牙和墨西哥对菲律宾产生了影响,在西班牙殖民初期开始流行】,有人嚷着去巴石河【巴石河,将马尼拉从南至北一分为二的重要河流,连通了马尼拉湾和菲律宾第一大湖贝湖】游泳,还有人嚷着去捉萤火虫;接着一阵穿外套和披肩、取帽子和手杖的喧哗声响起,他们跌跌撞撞地往外头走去;发臭的街道有中世纪的影子,他们步入其中;几盏街灯闪烁着,最后一辆马车正当啷当啷地驶过鹅卵石路,几不可见的黑色宅子仿佛在向马车轻声说:“嘘,嘘!”覆有瓦片的屋顶隐现,在昏沉、荒凉的天空下犹如阴险的棋盘;天空中有一弯邪恶的新月潜行于一角,还有杀气腾腾的风在飞旋,呼啸作响,那风时而闻起来是是大海的味道,时而是夏日果园的味道,不断地将童年时期那种让人按捺不住的番石榴熟透的气味吹向正喧闹不已、成群结队走在街上的小伙子们;在楼上卧室更衣的姑娘们尖叫着涌向窗口,挤在窗边吃吃傻笑,但很快就开始含情脉脉地叹息起来——对着那些正在楼下大喊大叫的坏家伙,对着他们华美的衣着、得意而闪烁的眼睛以及在月光下那么黑、那么醒目的优雅小胡子——陶醉在爱意中的姑娘们开始互相叫嚷起来,男生活得真自在啊,做女生可真无聊,这个世界真烦人真烦人,直到老阿纳斯塔西娅揪着她们的耳朵和辫子,把她们赶上床才作罢;此刻,从街上传来了巡夜人的靴子踩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咔嗒声,灯笼碰到他膝盖发出的当当声,以及他那低沉顿挫、划破夜色的大嗓门:“巡——夜——兵!现在是十——二——点!”


又到五月了,老阿纳斯塔西娅说。五月的第一天,女巫们在夜里都出来了,她说,因为这是一个占卜之夜、情人之夜,倘若是有心人,往镜子里仔细看,就会看见那个真命之人的脸。阿纳斯塔西娅一边说话,一边瘸着腿拾掇堆成团的裙撑,叠好披肩,把轻便舞鞋归拢到角落处。姑娘们爬上四张帷柱床,那些床巨大无比,反倒让房间显得太小了。她们开始恐惧地尖叫,挤作一团,恳求老太太不要吓唬她们。
“够了,够了,阿纳斯塔西娅!我们要睡觉了!”
“你倒是去吓唬那些男生啊,老巫婆!”
“她不是巫婆,而是先知。她可是在平安夜出生的!”
“圣阿纳斯塔西娅——贞女和殉道者。”
“啊?不可能!她降服过七任老公!阿纳斯塔西娅,你还是贞女吗?”
“我不是贞女。就因为你们这些姑娘,我都殉道七次了!”
“让她预言,让她预言!老吉卜赛人,我会嫁给谁?来嘛,告诉我。”
“要是不害怕的话,你可以去看看镜子。”
“我不怕,我就去!”年轻的阿格达表妹大叫着,从床上跳了起来。
“姑娘们,姑娘们——咱们太吵了!我妈会听见的,不得捏死我们。阿格达,躺下!还有你,阿纳斯塔西娅,我要你闭嘴,走开!”
“我的大小姐,您母亲吩咐我在这里过夜!”
“我才不睡呢!”叛逆的阿格达跳到地上,喊道,“老太婆,你站住。告诉我要怎么做。”
“告诉她!告诉她!”其他人附和道。
老太婆放下她手中收好的衣服,走近那个女孩,眼睛一直盯着她。“你得拿上一支蜡烛,”她吩咐道,“走进一个漆黑的、里头有一面镜子的房间,你必须是独自一人在那儿。然后向镜子走去,闭上双眼,念这些话:
镜子啊,镜子,
让我看看
我会成为
谁的女人。
要是一切顺利,在你左肩上方,就会出现你要嫁的那个人的脸。”
一阵沉默后,阿格达问道:“要是一切不顺利会怎样?”
“唉,那就愿主对你发慈悲吧!”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会看到——魔鬼!”
女孩们尖叫起来,互相攥紧了手,身子颤抖着。
“一派胡言!”阿格达喊道,“现在是一八四七年,已经不存在什么魔鬼了!”但是,她的脸色却变得苍白。“不过我能去哪儿呢?对了,我知道了!到大厅去,那里有面大镜子,而且现在也没有人。”


“不,阿格达,不要!这是大罪!你会看到魔鬼的!”
“我不在乎!我不怕!我就要去!”
“哎,你个坏女孩!太疯了!”
“你要是不回到床上,阿格达,我就叫我妈妈来。”
“要是你叫她来,我就告诉她,去年三月份去修会学校找你的那个人是谁。来吧,老太婆——把蜡烛给我。我走了。”
“姑娘们——快阻止她!抓住她!把门堵住!”
可阿格达已经溜出去了;她光着脚小心翼翼地穿过走廊,乌黑的头发从肩膀垂下,然后飞身下楼,秀发在风中飘扬;她一只手拿着噼噼啪啪燃烧的蜡烛,另一只手将白色的睡裙从脚踝处拉起。
在通向大厅的门道处,她气喘吁吁地停下,心脏快受不了了。她试着去想象这间屋子的另一番模样:满是灯火,欢笑,旋转的舞伴,欢快、急切的小提琴音乐。噢,可现在这是一间暗室,一处诡异的大洞穴——窗户已经紧闭,家具都整齐地沿着墙壁码放着。她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走了进去。
她面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面镜子;这是一面巨大的仿古式镜子,金色边框上刻有花、叶和神秘的旋曲饰纹;她看见镜中的自己胆怯地靠近:一个小小的白色鬼影在黑暗中出现,但显得不太情愿,模样也不完整,因为她的眼睛和头发太黑了,那张脸接近镜子时,看起来就像一张向前飘浮的面具——一张明亮的面具,上面开着两个大洞,在白云般的长睡裙吹送下,正向前飘动;等她站到镜子前面,把蜡烛举到下巴齐平处,那死气沉沉的面具就绽放成她那张鲜活的脸。
阿格达闭上双眼,轻声地念咒语。念完后,她陷入一阵恐惧,感到无法动弹,睁不开眼。她觉得自己着魔了,会永远站在那里。但她听见身后响起了脚步声,还有强忍着的笑声,于是马上睁开了眼睛。


“你看见什么了,妈妈?那是什么?”
但阿格达夫人已经忘了坐在腿上的小女孩:她的目光透过依偎在自己胸前的这个卷发小脑袋,注视着挂在房间里的大镜子中的自己。还是那个房间,还是那面镜子,但如今她从中看到的是一张苍老的面孔:灰白头发下,一张冷酷、怨愤、苦大仇深的脸。伤心啊,那张脸已经变了,伤心啊,那白面具一样的脸已经面目全非——以前那张鲜活而年轻、宛如清雅面具的脸,许多年前那个狂放的五月节前夜出现在这面镜子前的脸……
“到底是什么,妈妈?噢,接着说呀!你看见什么了?”
阿格达夫人低头看着女儿,眼里充满泪水,但脸色并没有变得温和。“我看见了魔鬼!”她愤恨地说道。
孩子的脸吓得煞白:“是魔鬼吗,妈妈?啊……啊!”
“没错,我的宝贝。我睁开眼,看见镜子里我的左肩上方有东西冲着我笑,那是魔鬼的脸。”
“噢,我可怜的小妈咪!你吓坏了吧?”
“你想象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好女孩不要轻易地照镜子,除非有妈妈的许可。宝贝,你必须戒掉这个坏习惯,不要路过一面镜子就停下来孤芳自赏,否则有一天你会看见一些吓人的东西。”
“可是,妈妈,魔鬼长啥样呢?”
“唔,让我想想……他一头卷发,脸颊上有一道疤——”
“像是爸爸的那道疤?”
“嗯,是的。但魔鬼脸上的是罪恶之疤,而你爸爸的是一道荣誉之疤。他大概是这么说的。”
“接着说魔鬼。”
“唔,他留了小胡子。”
“就像爸爸那样?”
“不是。你爸爸的胡子有点脏,是灰白色的,还有难闻的烟味,而魔鬼的胡子非常黑,还很优雅——噢,太优雅了!”
“他长角吗?有尾巴吗?”
母亲撇了撇嘴:“有的,他长了!不过,哎呀,当时我并没有看到。我光看到他华丽的衣裳、闪亮的眼睛、他的卷发和小胡子。”
“他跟你说话了吗,妈妈?”
“说了……说了,他跟我说话了。”阿格达夫人说着,低下白发苍苍的头,哭了起来。


“美人,你如此光彩照人,何须蜡烛?”他向镜中的她微笑着说,又后退几步,轻佻地向她深鞠了一躬。她转过身,对他怒目而视,而他却大笑起来。
“我认得你!”他大叫道,“你是阿格达。我离开时,你还是个婴儿,现在我回来了,你已出落成一个大美人。刚才,我同你跳了一曲华尔兹,但你不肯再跟我跳波尔卡。”
“让我过去。”她很激烈地嘟哝着,因为他挡着自己的路了。
“可是美人,我想和你跳波尔卡。”他说。
他们就这样站在镜子前,漆黑的房间里,唯一的声响就是他们的喘息声;烛光在两人之间摇曳,把他们的影子抛到墙上。年轻的巴多伊·蒙提亚烂醉地溜回家,本想上床安静地昏睡过去。他突然发现自己酒醒了,十分冷静,非常清醒,有把握去做任何事。他双眼放光,脸上的疤泛着猩红色。
“让我过去!”她又叫嚷起来,语带愤怒,但他紧紧抓住她的手腕。
“不,”他笑了,“我们得先把舞跳了。”
“见鬼去吧!”
“我亲爱的,你脾气还挺大!”
“我不是你亲爱的!”
“那又是谁的呢?是我认识的人吗?是我曾经严重冒犯过的人?否则,你为何对待我和我的朋友,都像死敌?”
“那又怎样?”她质问道。她把手腕挣脱出来,对着他牙齿一呲:“呵,我太讨厌你们了,一群自负的小年轻!去了一趟欧洲,回来就成了高雅的大人。我们这些卑微的女生太乏味,不配取悦你们。我们没有巴黎人的风度,我们没有塞维利亚人的激情,我们没什么滋味,没滋味,没滋味!哎呀,我讨厌死你们了,烦死你们了,一帮瞎讲究的小年轻!”
“得啦,得啦——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情况?”
“我听到的呀,你们自个儿在那儿聊天时我听到的,我鄙视你们这群人!”
“可是这位小姐,很明显,你并不鄙视你自己。你甚至半夜来照镜子,欣赏自己的美貌!”
她青了脸。那一刻,他有种邪恶的满足感。
“先生,我不是在欣赏自己!”
“那么,你是在赏月?”
“噢!”她倒抽了口气,突然哭了。蜡烛从手中掉落,她用手捂住脸,楚楚可怜地抽泣着。蜡烛灭了,两人站在黑暗中,年轻的巴多伊感到很内疚。
“嗨,别哭呀,小宝贝!原谅我!请你别哭了!是我太混蛋!我喝醉了,小宝贝,我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摸索着,摸到了她的手,把它轻轻放到自己的嘴唇上。白睡裙里,她的身体在颤抖。
“让我走。”她呜咽道,一边无力地拽扯着。
“不。你要先说原谅我。阿格达,说你原谅我。”
她没有说话,而是将他的手拽到自己嘴边,咬了一口——狠狠地咬住他的指关节,他痛苦地叫出声,并用另一只手猛力回击,但只打中了空气,因为她已经不见了,逃跑了。听着她上楼时裙子的声响,他狂怒地吮吸着自己流血的手指。
恶毒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急速转动:他要去告诉妈妈,让她把这个野蛮的丫头从家里赶出去——或者,他可以亲自去女孩的房间,拖她下床,啪啪啪抽打她那张愚蠢的脸!但同时他又想起,明天一早,所有人要一起去安蒂波洛【安蒂波洛,菲律宾黎刹省的首府城市,位于马尼拉以东。安蒂波洛以“菲律宾朝圣之都”著称,这里的大教堂供奉着安蒂波洛圣母像。安蒂波洛圣母即“我们的平安圣母”。1626年,该圣母像由时任菲律宾总督的胡安·尼诺·德·塔博拉从墨西哥带到菲律宾。他将这趟在太平洋上的安全航行归功于圣母像的保佑,这尊圣像由此得名。在每年基督教圣周期间的濯足节和4月30日晚上,大批信众会从黎刹省内或马尼拉等邻近地区出发,徒步前往安蒂波洛朝圣,于耶稣受难日和5月1日到达。小说所写的五月节就是指5月1日这个朝圣日。事实上,由于五月份是天主教中的圣母月,因此整个五月都是安蒂波洛的朝圣季。在五月节当日举行的安蒂波洛圣母像的游行拉开了这个朝圣季的序幕】,于是开始盘算怎样设法让她和自己坐同一艘船。
呵,这个小荡妇,他要报复,要让她付出代价!他舔着流血的关节,贪婪地寻思着:她得为此受到折磨。可是,该死啊!她那双眼睛!她生气时肤色多美啊!他想起她裸露的肩膀:在烛光下呈金黄色,像覆着纤柔的绒毛。他看到了她扭动脖颈时的傲慢劲儿,她紧实的双乳稳稳地耸立在丝滑的长袍下。这婊子养的,她太迷人了!她怎么能说自己没激情没风度呢?还没滋味?她的滋味少说得有二十斤重!就像俗话所说:
洗礼上的圣油
里头可不缺盐!
他在漆黑的房间里大声唱起歌来,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疯狂地爱上了她。他很痛苦,想再见到她——立刻就见!——想触摸她的手和秀发,想听到她严厉的声音。他跑到窗边,一把推开窗子,夜色之美猛然回击了他。这是五月,是夏天,而他正值青春——青春!——还疯狂地陷入了爱情。快乐在他身体里涌动,泪水夺眶而出。
可他并没有原谅她——不会原谅!他还是要她付出代价,还是要报复。他一边动起恶毒的念头,一边亲吻受伤的手指。但是这个夜晚太美妙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夜!”漆黑的房间里,他站在窗前,无比惊叹地说出心中所思。他双眼含泪,头发在风中飘动,流血的指关节紧紧抵在嘴上。


哎呀,可是呢,人心是会淡忘的,人难免会分心。五月的时光已经过去;夏天结束了;暴风雨袭向成熟后枯萎的果树林;心灵也衰老了;时日与岁月不断堆积,直到记忆变得拥挤不堪、杂乱无章:尘埃在此聚集,蛛网大肆蔓延;墙壁发黑,逐渐腐朽、破败;记忆堙灭……有一次,堂·巴多伊·蒙提亚于五月节的午夜散步回家,此时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甚至也不在意自己是否记得;他还能在意的,就是拄着手杖,探着回家的路,穿过街道;他的眼睛已经模糊了,腿脚走路不稳——他老了,已年逾六旬,是一个驼背的瘦老头,头发和胡子都白了,此时刚从一场谋反者的秘密集会上归家;从正门拾级而上、步入漆黑沉寂的宅子时,他脑海中仍然回响着那些演讲,一颗爱国的心仍然振奋不已;他对这个五月的夜晚全然没有感知,直至他穿过走廊,正巧瞥了一眼大厅,他停了下来,颤抖着,一身冰凉——他在那面镜子里看见了一张脸——一张被烛光照亮的、幽灵一样的脸,双眼紧闭,嘴唇翕动;他突然觉得自己曾在这里见过这张脸,尽管过了整整一分钟,逝去的记忆才开始涌现,如潮涨而来,淹没了眼前的真实时刻,迅速冲走了堆积已久的时日与岁月,让他突然重返青春:他又是一个快乐的公子哥了,新近从欧洲回来;他跳了一整夜的舞,喝得烂醉;他在通向大厅的入口停下,黑暗中他看见一张脸;他叫出了声……站在镜子前的男孩(一个穿着睡袍的男孩)害怕地跳了起来,差点摔掉手中的蜡烛,但他环顾四周,看到是老人以后,就松了口气,笑着跑了过来。
“噢,外公啊,你可吓死我了!”
堂·巴多伊脸色十分苍白。“原来是你,你个小坏蛋!喂,怎么回事儿啊?这么晚了,你在这下面搞什么鬼?”
“没什么,外公。我刚才只是……我只是……”
“好你个‘只老爷’。很高兴认识你,‘只老爷’!不过,要是我用拐杖敲阁下的脑瓜,把拐杖都敲断,你就不会老在那‘只只只’了!”
“外公,我就是在犯傻。他们跟我说,我能看见我老婆。”
“老婆?什么老婆?”
“就是我老婆呀。学校里的男生说,今晚我能在镜子里看见她,只要我念:
镜子啊,镜子,
让我看看
我会成为
谁的爱人。”
堂·巴多伊悲伤地大笑起来。他揪起男孩的头发,一路把他拖进房间,然后坐在椅子上,把男孩拉到两膝之间:“好了,你把蜡烛放在地上,孩子,我们聊聊这事。这么说你想讨老婆了?你想提前看到她?但你知道吗?这都是害人的把戏,那些玩这种把戏的调皮孩子可能会看见恐怖的东西。”
“好吧,他们的确警告过我,说我可能会看到女巫。”
“没错!非常吓人的女巫,可能会把你吓死。她会魅惑你,折磨你,吃你的心,喝你的血!”
“哦,得了吧,外公。现在是一八九○年。没有女巫了。”
“噢,不,我的小伏尔泰!我要是说自己就亲眼见过女巫呢?”
“你见过?在哪儿?”
“就在这屋子里,就在那面镜子里。”老人说,他那开玩笑的口吻变得凶狠起来。
“什么时候呀,外公?”
“不算太久远。那时,我只比现在的你大一点。噢,我当时是个自恋的家伙,晚上很难受,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死了就好,但经过门厅时,还是忍不住停下来往镜子里看自己快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探着头,却在镜子里看到……”
“女巫?”
“没错!”
“那她魅惑你了吗?”
“她魅惑我,折磨我。她吃我的心,喝我的血。”老人愤恨地说。
“噢,我可怜的外公!为什么你从未跟我提起?她很可怕吗?”
“可怕吗?天啊,不可怕——她很漂亮!她是我见过最美的尤物!她的眼睛有点像你,头发如黑瀑一般,裸露的肩膀闪着金色的光泽。天呐,她好迷人!但是我应该想到,即便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应该想到,她是个邪恶的、要命的尤物!”
一阵沉默过后,男孩低声说道:“外公,这面镜子真恐怖。”
“为什么这么说?”
“唔,你在那里头看见女巫了。有一回妈妈跟我说,外婆以前也告诉她说自己在这面镜子里看见了魔鬼。外婆是因为这事儿吓死的吗?”

堂·巴多伊心里一惊。有那么片刻,他忘了她已经去世、已经死了——可怜的阿格达;忘了他们俩最终得以修好,她疲惫的身体得以长眠;她衰弱的残躯终于摆脱了尘世间那些残酷的恶作剧——五月之夜的陷阱、夏日的圈套、银色月光织就的可怕的罗网。最后,她瘦得只剩下白发和骨头:一个形容枯槁、呼哧呼哧的肺痨病人,用刻毒的语言骂个没完;眼睛像烧红的煤块;面如灰烬……现在,一切都没了!除了墓地里的一块石碑,除了石碑上的一个名字。没了,什么都没了!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狂放的五月节午夜,镜子里那个如此明艳动人的少女已经荡然无存了。
想起她抽泣的可怜样儿;想起她咬了他的手逃走后,他在漆黑的屋子里大声唱歌的样子,以及他在坠入爱河时那一瞬间的心惊肉跳;悲伤撕扯着他的喉咙和眼睛,让他在孩子面前感到惭愧;他推开孩子,站起身,踉跄地走到窗户边;他猛地推开窗户,向外看去——发臭的街道中世纪的影子;几盏街灯闪烁着,最后一辆马车正当啷当啷地驶过鹅卵石路;几不可见的黑色的宅子仿佛在向马车轻声说:“嘘,嘘!”覆有瓦片的屋顶隐现,在昏沉、荒凉的天空下犹如阴险的棋盘;天空中有一弯邪恶的新月潜行于一角,还有杀气腾腾的风在飞旋,呼啸作响;那风时而闻起来是大海的味道,时而是夏日果园的味道,不断地将令人无法承受的、装有久远爱情的五月回忆吹向窗边一个哭得身子发抖的老人;佝偻的老人在窗边哭得十分伤心,泪水从脸颊流淌下来,头发在风中飘动,一只手紧紧抵在嘴上;此刻,从街上传来了巡夜人的靴子踩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咔嗒声,灯笼碰到他膝盖发出的当当声,以及他那低沉顿挫、划破夜色的大嗓门:“巡——夜——兵!现在是十——二——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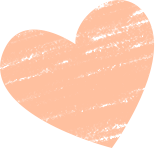
尼克·华金(Nick Joaquin,1917—2004),菲律宾作家、记者、翻译家和编剧,菲律宾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菲律宾国家艺术家勋章获得者。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两个肚脐眼的女人》(1961)和《洞穴和阴影》(1983),短篇小说集《热带哥特风》(1972)和《华金风格:摩登派神话》(1983)等,以及诗歌集《散文和诗歌》(1952)和《诗歌选集》(1987)。
华金的作品有浓重的怀旧感,经常写教堂的礼仪活动、民间传说,充满了神秘因素和恐怖色彩。华金正是通过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交融来延存传统精神和正统的天主教信仰,以最终达到清除现代社会弊病的目的。
《五月节前夜》(May Day Eve)选自2017年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两个肚脐眼的女人及热带哥特风故事集》(The Woman Who Had Two Navels and Tales of the Tropic Goth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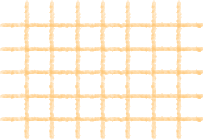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3期,策划与责任编辑:杨卫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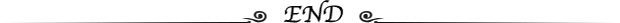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