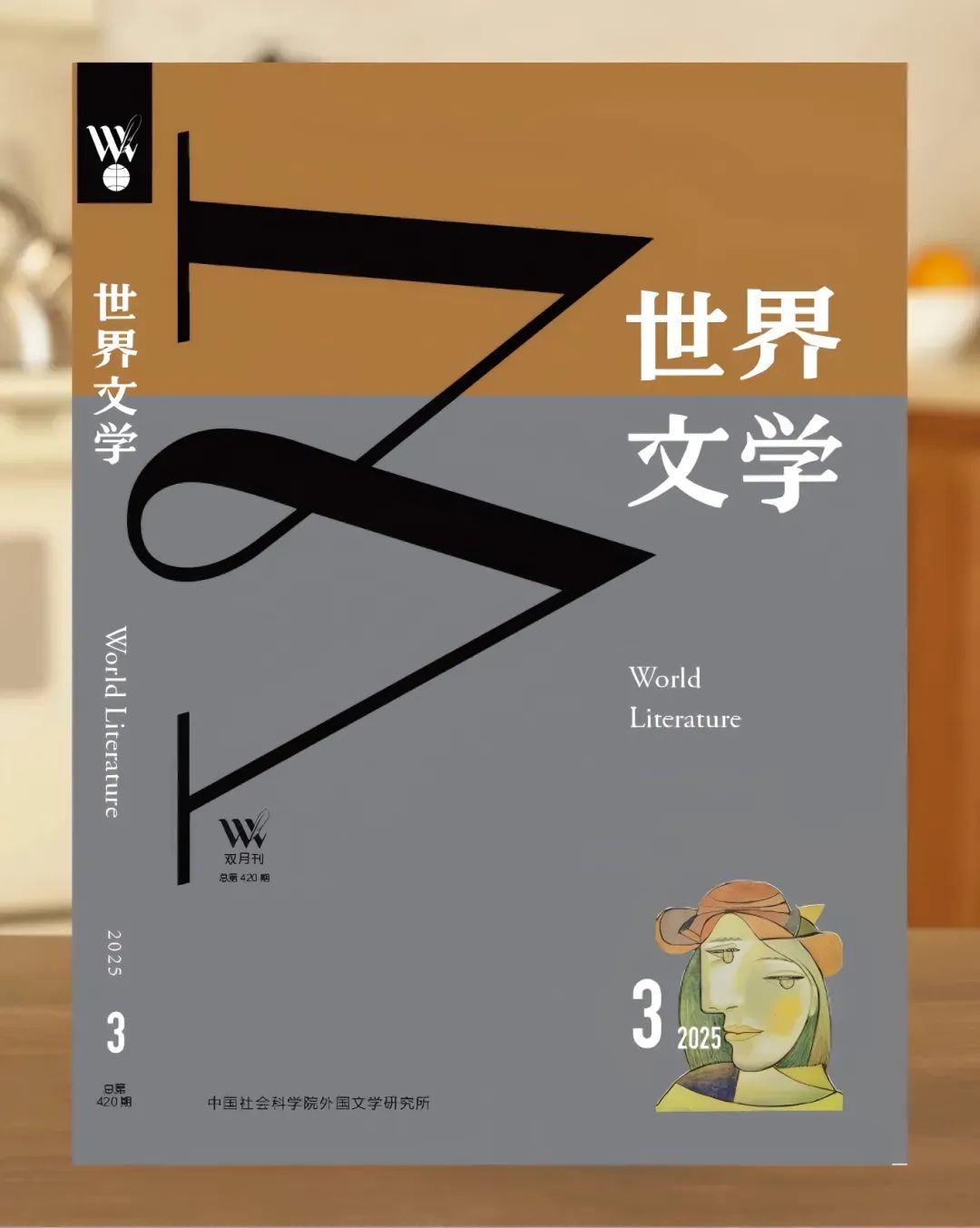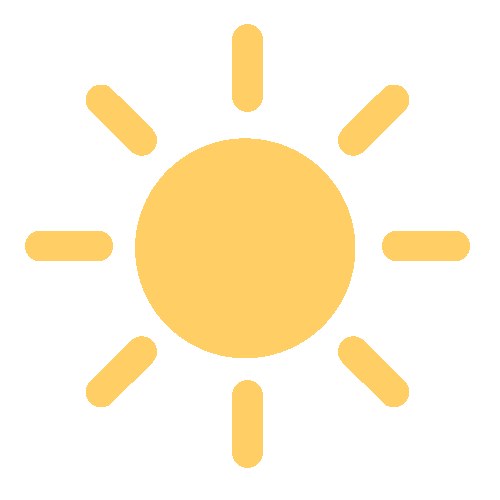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亚•切伊【美国】:写作生涯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我名叫亚历山大·切伊,英语专业四年级本科生。我选修过菲莉丝·罗斯的《小说I》和基特·里德的《小说高级课程》两门课。去年夏天,还在本宁顿学院的作家工作坊跟随玛丽·罗宾逊和托比·奥尔森学习过。下面几个故事,选自我正在撰写的创意写作论文,指导老师为比尔·斯托教授。但申请您这门课的真正原因却是:我每每告知别人自己在卫斯理上学时,他们都会问有没有跟您学过,我希望能有更好的回答,而不是说没有。
亚历山大·切伊作 李晖译
亲爱的安妮·迪拉德:
我名叫亚历山大·切伊,英语专业四年级本科生。我选修过菲莉丝·罗斯的《小说I》和基特·里德的《小说高级课程》两门课。去年夏天,还在本宁顿学院的作家工作坊跟随玛丽·罗宾逊和托比·奥尔森学习过。下面几个故事,选自我正在撰写的创意写作论文,指导老师为比尔·斯托教授。但申请您这门课的真正原因却是:我每每告知别人自己在卫斯理上学时,他们都会问有没有跟您学过,我希望能有更好的回答,而不是说没有。
感谢您拨冗垂阅,
亚历山大·切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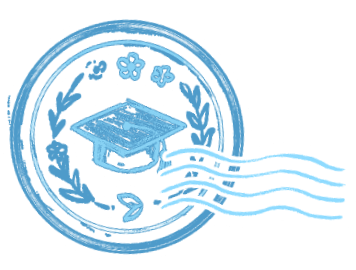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我准备选修安妮·迪拉德在卫斯理大学的非虚构文学课,这是我连同申请表一起寄出的信。当时正是我英语专业四年级最后一学期——我先前无法通过工作室【艺术专业工作室艺术是美国艺术教育中的一种教学模式。学生在艺术工作室内跟随导师学习艺术所需的技艺,毕业后可以拿到工作室艺术文科硕士学位】考试,已经按照学校默认的条件转为英语专业。
一边等待回复,一边心里想着肯定遭拒的时候,我去购物广场买圣诞礼物。走过的一家家书店里,到处摆着安妮·迪拉德作品——《汀克溪畔的朝圣者》《美国童年》《坚固圣质》——的盒装本,还有《一九八八年美国最佳随笔集》,没错,是安妮·迪拉德编的。我绕着这些书转悠,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书就是她本人而非她的作品。最后,我空着手离开了。
我没买,是因为如果她拒了我,守着这堆书会让我无法忍受。
等选了这门课,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如果真买了她的书,也是比较草率的。她告诉我们,跟她学习期间不要读她的作品。
会对你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她说。你们会想着取悦我,只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师。我不想让你们千方百计模仿我。我不想让你们写得像我。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然后又说,我想让你们写得像你们自己。
在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有些人的脸上露出了负罪感。我也有负罪感。我并不了解她的作品,只知道她由此而成名。我倒希望自己有那个意识想去违背她。我觉得自己肤浅,但还是来了,因为父亲以前总说,不管你想干什么,都要找这方面水平最高的人,看他们愿不愿教你。
我已经把卫斯理大学的其他所有人都考虑过一遍。她是最后留在我拟定名单上的那一位。


*
我至今仍能听见她在耳边说:把你所有的死亡、事故和疾病都放到最前排,放在开头。可能的地方。“可能的地方”是她经常用来应答的措辞。我们始终要记住,出于写作的需要,有可能不遵循各种规则或指示。
放在这段故事开头的事故是这样的:二年级那年春天,我在艺术系主任的绘画课上睡着了,醒来后发觉自己的肩膀正被她紧抓着。她是一位盛气凌人的优雅女性,短短的黑色鬈发,仪态庄重而温和,以描绘云彩闻名。
切伊先生,她说着把我拽了起来。我认为你应该回家去干这件事。
我觉得自己的脸颊和下面的垫纸都洇湿了。我迅速收拾好画材,然后离开了。
在此之前,她喜欢过我的作品,常在班里表扬我。在此之后,我干什么都不对。评分的时候,她开始把返给我的作业标记为“未提交”,似乎把赞美过我作业的记忆都一笔抹消了。我把这批作业放进她信箱,上面明明白白有她的评语,希望能够借此自证清白,但不管用:她评的“B-”导致我课程分数低于专业学生所需的平均水准。我给扫地出门了。
三年级开始前的那个夏天,我一直在琢磨自己到底该干什么。彼时的情形使我成了严格的素食者,每天骑行二十英里,在我家经营的海鲜餐馆里,给我妈当前台夜班经理,结果体重从一百六十五磅掉到了一百四十五磅。我成了棕色线描画里的人物形象,边吃草莓冰棒,边给游客结算龙虾和炸薯条账单。再后来,等到八月最后几天,隔壁镇上的一位校友打电话到我家。
你有打字机吗?他问。
有啊,我说。
我能借用一下吗?他问。我这篇故事要打印出来申请菲莉丝·罗斯的课。今天下午我能过来取吗?
行,我说。
挂掉电话之后,在他来之前的四个小时里,我用那台打字机写了一个至今还能回想起来的故事。我记得这个故事,多少是因为它产生的过程——就我现在所知,鲜少有故事能做到那样:下笔快,信心足。当时,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之前的文学成绩了。中学时候,我拿过杰拉尔丁·洛·道奇基金会的诗歌奖。我有一部剧作荣膺缅因州天才班项目——波特兰舞台剧团的演员为此还举办过一场朗读会。不过,这些都像是意外,像是隔壁某人的生活。出于某种原因,这头一个短篇,实现了我心中的那种想法:我能够用原来做不到的一种方式来写作。
我用自己的一些生活碎片来创作,将这些碎片重整成另一种东西,就像绘画课上的练习,将描画三件静物的习作组合成一幅虚构的生动画面。那篇故事讲的是整个夏天都在骑自行车的一位少年(我)。他让汽车给撞了,陷入昏迷状态,其间不断梦见自己经历的这场事故,直至醒来(我爸爸遇到过这种事,不过,我在那堂毁灭性的艺术课上也遇到了同样情形)。小伙子苏醒之后,有位神职人员来看望他,想要确认他有没有丧失信仰(我和我的牧师在我父亲死后这样做过)。

作家洛丽·摩尔【洛·摩尔(1957—),美国女作家,代表作有《就像生活》《美国鸟人》等】曾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创意写作三十年。将那一天的体验称为“面具的慰藉”:你打造出自己人生中并不存在的某个地方,为了你人生里容不下的那份生活,为了你记忆中的那些流放者。可是,我当初并不明白这一点。
那个时候,我只知道自己也终于能对自己刮目相看了。无论写故事究竟是怎样一种行为,我都想重新来一遍。
朋友来了。我盖好打字机盒交给他。我没有告诉他自己刚才干过什么。不知为何,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自己正在干的这件事。等他离开后,我转身去了邮局,心里有一丝负罪感,似乎在干什么不法勾当,然后寄出了那个短篇。
我在录取名单里看到了你的名字,几周过后回到卫斯理,我朋友说,声音里似乎带着点受伤的感觉。恭喜你。
等再看名单,才发现他没在上面。感觉像是在给他打字机之前,我从里面取走了某样要紧的东西,所以就想道歉。
我不认为被录取是因为自己写了什么。
我在那个班里继续上课并拿到了A,这让我无法理解,甚至听到同班同学宣称他拿到B的时候,也仍然无法理解。我不理解是因为似乎感觉不到自己在做什么。我确实申请并且加入了下学期基特·里德的小说高级课程班——每两周写二十页的小说——还继续从她那里拿到下一个神秘莫测的A系列分数。接下来我申请并加入了贝宁顿学院的写作研讨班。我在那里跟随玛丽·罗宾逊和托比·奥尔森学习,还遇见了简·斯迈利在克诺夫出版社的编辑鲍碧·布里斯托尔。她答应审读我的一则短篇,后来返还文稿时留言说:假如我能把它变成一部中篇小说,她就会买下来。
我对中篇小说毫无概念,也不知道怎么写,读她留言时的激动变成了困惑,然后是伤心。
令人羡慕的大事?在我身上接连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换作另一位学生,他可能会请玛丽·罗宾逊或基特·里德帮他弄明白什么是中篇小说,这样他就能够写出来,那么到二十一岁就已经有作品出版了。然而我不是那种人。我以为自己能够选择命运。我希望简·斯迈利的编辑告诉我:去当一名视觉艺术家,忘掉写作这件事吧,孩子。我这种人不懂得怎样认识自己当前的道路,脚下的这条道路。
这就是,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老师的原因。


我对她最清晰的记忆,是在春天,她向我走来,微笑着,唇膏整齐的边沿环绕着她的笑。我从来没问她为什么笑——我只知道,我站在要上课的教学楼前抽烟,她冲着我笑了。她是安妮·迪拉德,我是她写作班上的学生,一个二十一岁的“陈词滥调”——黑色衣衫,故意蓬乱不整的头发,抽着烟,随身听里播放着阴郁而通俗的乐曲。我现在十分确信,她肯定觉得我很滑稽。她走路来上课,因为她跟丈夫和女儿住在一栋漂亮房子里,离我们教学楼只有几个楼区的距离。每次我从校园经过那里,都会念及她的存在,仿佛空气里有一丝悸动。若干年后,她不在那里住了,我回来教书后,才体会到这种缺失。
背后的深绿色树影清晰地衬托出她的轮廓。她身穿浅色衣服,戴珍珠项链和耳环。个头高挑,体格健壮,精力很是充沛。皮肤紧绷发亮。她冲我伸出一只手。
切伊,她说,那东西给我来一口。
她用姓氏称呼我们所有人。
她让烟雾缭绕了片刻,然后猛然吁出一口气。谢谢,她说,把烟递回来,再次微笑着走进楼里。
万宝路的金色滤嘴冠以唇膏的印痕。
我马上就知道了,这意味着离上课只有五分钟了。把烟头捻灭时,我想到那些会收藏滤嘴的人。至少有一个人会。我满腔道德正义感地将烟头踢进下水道。
第一次上课,她佩戴着珍珠首饰,衬衣的拉袢领从套头毛衣领口里探了出来,但她那模样好像在说:假如不老实,会给你一拳。迈着女牛仔的步伐,她走进教室,从提包里抽出一本写满笔记的标准拍纸簿,一个装满咖啡的保温杯,一袋独立包装的布拉赫牌黄油奶糖,随后坐了下来。她轻轻拧开保温杯,把咖啡倒进充当容器的杯盖,小口啜饮着,笑容满面地环视了整个屋子一圈。
嗨,她说,好像是用笑容发出的声音。你们有一百三十人申请了这门课,我就选了你们当中的十三个。
一群影影绰绰、面目不清的被拒者迅速聚拢在我们周围。一种险些错过的恐慌感袭来,随即又消失。
不许旁听,她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行。我可不管是谁。
这门课自带一种节奏——取决于她为了让新婚丈夫高兴而戒烟的状态。我们是异地恋,在一次我们边抽烟边长聊的课间休息时,她对我说。我们开会时认识的。直到同居,他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烟鬼。她说起这件事就笑,就像看待恶作剧一样。
一开始上课,她就会从包里取出细长的咖啡保温杯,还有那袋独立包装的布拉赫牌黄油奶糖——带白色夹芯的那种。她放下写满笔记的标准拍纸簿,倒杯咖啡,一边喝一边剥开糖果吃。一小堆塑料包装纸在她左手边的桌面上渐渐堆起。她来回快速地翻动拍纸簿,旁边糖纸跟着微微抖动。她讲述写作时会抛出格言警句,常常就此展开,讲解一番,但有时只是罗列格言警句:绝不要使用“灵魂”这个词,假如有可能的话;永远不要引述你能够简单概括的对话;避免描写人群场面,尤其是聚会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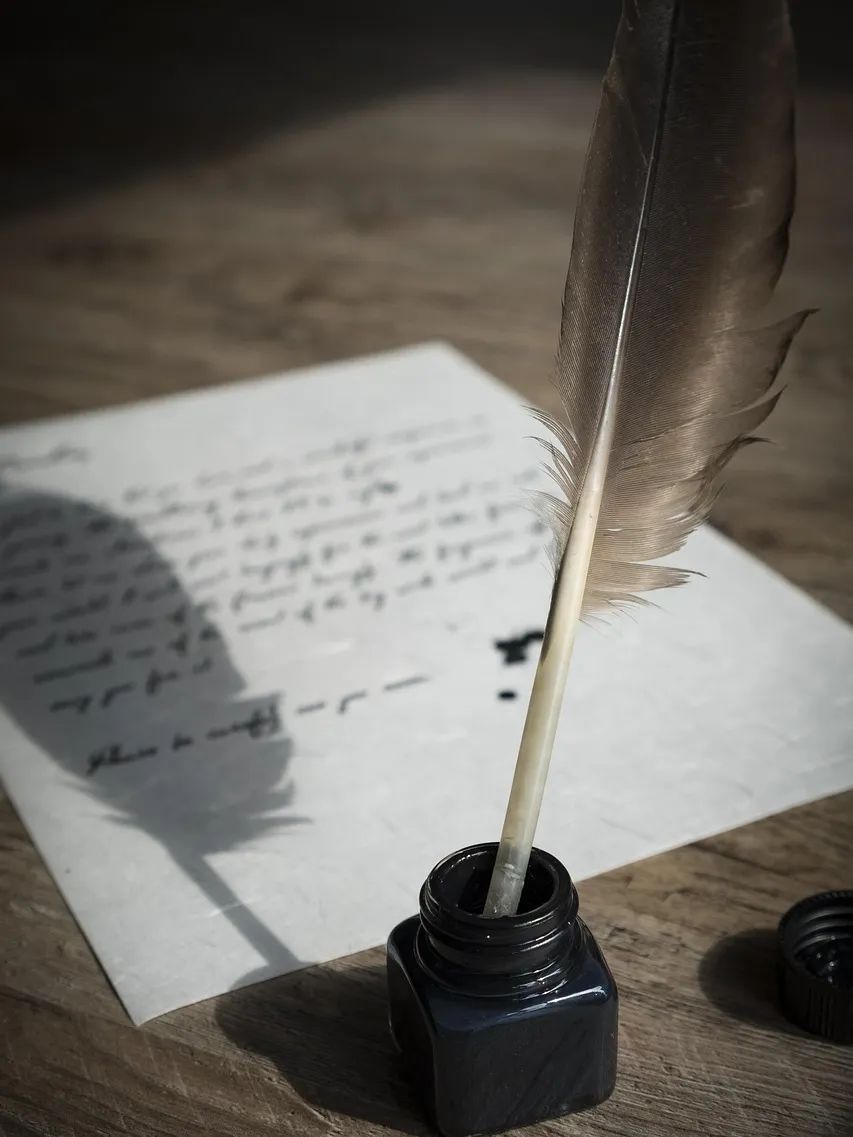
她刚开始讲话时,甚至会带着一丝困倦,但很快就变得语速匆忙。不是慌乱,而是那种歌剧式的节奏。随后她可能稍事停顿,在短暂静默中检查自己的拍纸簿,等我们做完笔记,写字的声音沉寂下来,她再朝着另一个方向进发。
我们每周必须就当周布置的任务提交一份作业,要求七页纸和三倍间距。
三倍间距?第一节课上我们就问过,真是难以置信,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要求过我们。
我需要你们在句子中间留出地方给我随手写批注,她说。
教室里的沉默是我们脑海里琢磨这句话的声音。应该也没那么多话可说吧?
但她已经站起来走到黑板旁边,写下了一系列的编辑符号目录:Stet是拉丁文,意思是“保留不删”……如果我在什么东西上面划道横线,再添一个向上翘的小辫子,意思就是“拿掉它”。
确实有那么多话可说。我们每逢周二交作业,周四课上再领回来,三倍间距的空隙外加边角位置全都写满了她的铅笔批注。有时候你写的句子令人称奇,她的批注告诉我,有时候令人称奇的是你居然还会写句子。她划出两条箭头,指向那个令人称奇的句子和那个令人失望的句子。从她手里取回文稿,就像是进入夜店舞池后才在黑光灯下发现,你最喜欢的那件黑色衬衣沾满了头发和灰尘——它们一直粘在那里,只是之前你看不到而已,现在却看见了。
在她的课上,我才明白虽然这辈子都在说英语,其实对它了解甚少。英语源自低地德语——一种有利于分门别类的语言——它曾经用希腊语、拉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词汇填饱肚皮,如今正逐步从亚洲各地语言那里摄取食物。拉丁派生词是多音节词,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却简洁短促,可能最多只有两个音节。优秀作家同时采用这两种词汇来变换语句的节奏。
从我的文章里,她非常迅速地辨认出她称为“怪诞语法结构”的东西。根据安妮在我文稿上的划圈内容来看,显然我出问题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来自缅因州。从我妈妈家族这一边,我不仅获得了讲述细节的天赋——你舅舅查尔斯实在太抠门了,他甭管多饿,也不会给自己一次买两个汉堡——我还获得了一种混杂着被动语态的表达习惯,它是那一隅世界的常见用法——我给您写信,是想问您有没有被这件事引发兴趣——这种说话方式,钝化了所有的攻击性,钝化了所有直截了当的问询,当然也钝化了所有描述的效果。这是当年苏格兰定居者在英国统治者胁迫下迁居缅因州而形成的退变句法,是他们在离开故土、留驻异乡期间使用间接引语的产物。雪上加霜的,还有那个盘踞在我无意识里的陈词滥调博物馆。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前苏格兰殖民地的孩子,通过观看吉恩·凯利吉·凯利(1912—1996),爱尔兰裔美国男演员,好莱坞歌舞片巨星,主演过《雨中曲》《锦城春色》等电影。的电影而自学英语。
被动语态尤其能够制造写作危机。“被”这个字只告诉你有某样东西存在。但这样还不够。关于这一点,我几乎一字不差地记得安妮的赋格式讲课内容:
你们希望文笔生动。我们怎样做到文笔生动?动词,首先。精确的动词。页面上的整个行动,一切发生的事情,都借助于动词而发生。被动语态需要以动名词的形式让事情发生。但是同一页出现太多动名词却会让人耳鸣:running(奔跑)、sitting(坐)、speaking(说话)、laughing(笑),一大堆的inginginginginging。不行。别这样做。动词告诉读者某件事是发生一次还是持续发生,什么还在继续运动,什么已经休止。动名词却在偷懒,你不用做出判断。结果很快,所有事情都在同一时间发生,着急忙慌,一片混乱。别这么做。还有,选择糟糕的动词就意味着要使用副词。多数情况下,你们不需要副词。他是在飞快地奔跑,还是在冲刺?他是在慢慢地走,还是在蹒跚或闲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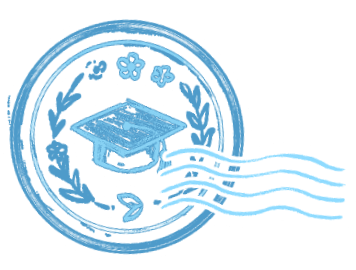
此时此刻的混乱属于她的拍纸簿和糖纸,桌上的风暴正通过糖和咖啡因的助燃而趋于“渐强”。我记得这种情况下会出现片刻停顿,她抬眼望向教室中间位置,再回去看她的拍纸簿,嘴里念叨着:我意思是,你们的文章内部究竟在发生什么?
假如说虚构类小说提供了面具的慰藉,那么根据安妮的看法,非虚构作品则提供了面具之下的感受力——无可取代,具有潜在的巨大价值。文学随笔,就像她看到的那样,则是一种道德演练,涉及怎样与未知之物直接交涉,管它是异邦文明还是你内心,至关重要的还是你自己。
你是你的唯一,她说。你独一无二的视角,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当前时刻,无论关注突尼斯还是你窗外的树木,都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别担心有没有创意,她不屑一顾地说。没错,所有东西都有人写过,但是别忘了,你想写的东西,在你写下来以前,是不可能有谁写的。否则它早就存在了。你来写,它才有可能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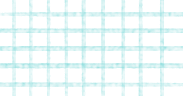


叙事写作是按照某种秩序来安排细节,以便在读者的内心再现作者的经历或体验,她如此宣称。这似乎显而易见,却非同凡响——从来没有人向我们说得如此直白浅显。她经常提到“做活儿”。假如你活儿做好了,读者会感受到你的感受。你不用告诉读者怎样感受。没有人喜欢听别人说应该怎样感受某种东西。你要是不相信,那就随便。你不妨告诉某个人怎样感受试一试。
我们要避免情绪化语言。如果你这么做,句子会变得灰不溜秋,她说。别告诉读者某个人高兴还是悲伤。你这么干,读者什么也看不到。她并不是生气,安妮说。她是把他的衣服扔出窗外。要具体。
删了再删,这个移到这里,那段放在开头,这个归到第六页,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懂得,一部文稿的前三页通常就是清清嗓子准备说话,大多数情况下,作品真正开始的地方是在第四页前后。假如本该放在开篇的内容没有放在那个位置,有时甚至会到结尾部分才出现;结果,你花费了这许多时间,全都是为了抵达你文章的起点;假如你将文稿前几页和最后几页内容进行调换,可能比保留原先顺序的效果更好。
有一天下午,按照她的吩咐,我们带来了纸、剪刀和胶带,还有一篇散文的若干修改稿——我们已经费劲修改过好几个版本了。
现在,把最像样的句子剪下来,她说,再把它们贴到白纸上。贴好以后,在它们四周写东西,她说。把缺少的东西填进去,让它达到你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写作水准。
我眼看着一个个无关紧要的句子分崩离析。
你们可能觉得自己身为作者的声音会自然浮现,完全独立自主,不用任何帮助,真这样想就错了。我从稿纸上看到的,其实是陷入困境、紧张、懒散的声音。在我的作业中,甚至是失忆脱节的。必须要删到自在了才行。
听完这一段关于动词的讲解,我们数了数纸上的动词,把它们圈起来,在每一页的边沿记下数目,再算出平均值。你们能不能增加每一页使用的动词数量?她问道。我从塞缪尔·约翰逊那里学到了这种练习方式,她说,约翰逊相信每一页文字都要生动活泼,所以经常数自己用了多少动词。好吧,再看一看。你们的动词有没有用对?它是不是表达那个确切事物的确切动词?记住,副词是你用错动词的表征。动词掌控了一件事情在读者脑海里发生的时间点。仔细想想——跟那件事相关的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你是不是这样描述它的?
我若有所思地望着我那页纸上的圆圈,以及圆圈内外的错误选择。
你们可以编造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她说。放在边角位置。你们不能编造那些至关重要的细节。


我清楚记得这个至关重要的细节:那年仲春的某个周四上午,我在上课前走到学生活动中心,从校内邮件里取走了我的手稿。就是这篇文章让我在写作时达到了至今无法企及的投入与热忱。我觉得我终于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了——怎样通过选择,逐行逐句,让作品变好或变差。经过一年多的失落,这种新鲜的感觉就好像你的脚板在幽暗的水里触碰到水底。就是这里,你心想。我可以在这里蹬一脚。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那份手稿,行间空隙布满了纹身般的字句,比往常还要密集。我仔细读了所有的话,一页页翻到背面接起来看,直到发现了附在最后面的这句话:我整宿没睡,在琢磨这篇东西。
我写的东西让她整宿没睡,这件事就足够重要,足可以引发我的关注。好吧,记得当时我自言自语道,假如你写的东西能让她整宿不睡,大概你是有能力干这一行了。
我一直讨厌有才华的说法。没办法推崇;在我的经验里,也没有其他人推崇。在学校里被别人说有才华,只会让我沦为受挖苦的对象。我想做事情。做事情,能让我引以为荣。安妮的想法也一样。
只有才华是不够的,她告诉过我们。写作就是做事情。任何人都能做这件事,任何人都能学会这件事。它不是火箭科技;它是心思习惯和做事习惯。起初我周围有些人的才华比我高很多,她说,现在他们要么死了,要么坐牢,要么不写作了。我跟他们的差别就是我还在写作。
才华可能什么也给不了你。不做事情,才华就只是才华而已——有希望,无成果。我想知道一个从故事开篇就遇到事故的人怎样变成作家,我从她那里知道了诀窍。
跟安妮的学习结束后,我想成为她那样的人。
我想让哈泼·柯林斯出版我的套装书,我想有一位英俊的教授丈夫和一个女儿,我想有一套学校提供的房子,我想每年教一门课,其他时间全都用来写作。我甚至想拥有那辆破旧的绅宝车和科德角的几处房产。从我当年产生这种想法的场景来看——站在她位于校园的家里,在学期末的一场户外烧烤聚会上——这似乎是一位作家最可能拥有的生活。我上四年级了,知道毕业意味着我对生活与现实的感觉会整体湮灭。就是在这里,我用手端着一个吃完汉堡后满是污渍的纸托盘(需要声明的是,此时我已经放弃了严格素食)——就是在这里,目标忽然清晰起来。
假如我尽到了自己的职分,她在最后一堂课上说,接下来的十年,你们就不会满意自己写下的任何东西。并不是因为你们写得不好,而是因为我提高了你们给自己设立的标准。不要互相比较。你们要比较的人是柯莱特【西多妮·柯莱特(1873—1954),法国女作家,代表作品有《吉吉》《谢里宝贝》等】,或者是亨利·詹姆斯,或伊迪丝·沃顿。拿自己跟经典比较。向那里开枪。



她停了下来,再一次进入赋格状态。然后她笑了。我们都知道她说得对。
走到书店里将来会摆放你本人著作的位置,她说,直接走过去找到你在书架上的位置。每次伸出指头,在那里放一放再离开。
在课上,这种想法听起来很荒唐。但课程结束后的某个时间点,我还真这样做了。我走到书架旁边。夏邦【迈克尔·夏邦(1963—)),当代美国作家,代表作有2000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契弗。我把手指放在他俩中间,挤出一道空隙。很快,每次进书店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做。
若干年后,我告诉自己的学生也这样做。正如梭罗——安妮极度钦佩的人——曾经写过的话:“从长远来看,我们永远只会击中自己瞄准的目标。”她把我们指向了那个地方。

亚历山大·切伊(Alexander Chee,1967— ),美国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出生于罗德岛,韩美混血,童年在韩国和关岛等地生活。大学期间开始学习写作,参加过卫斯理大学和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班,著名散文作家安妮·迪拉德曾经当过他的指导老师。切伊迄今只写过两部长篇小说和一本散文集,但他富有隐喻的文风在同行中颇得好评。他本人长期担任《新共和》杂志的文学编辑,同时在大学里教授创意写作。
作为美国创意写作体系的过来人,切伊对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在今天传统表达方式逐渐没落的背景下,“怎么写”是作家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面对虚构的文本世界,虚构的文本世界和现实之间会有什么样新的关联,应该是作家们未来需要思考的地方。所选两篇译文皆关涉创作。《写作生涯》(The Writing Life)则从作者申请安妮·迪拉德的写作班开始,用丰富的细节回忆了这位大作家的课堂讲授,其中不乏对于写作这门古老手艺的个人理解。译文选自切伊2018年的散文集《怎样写一本自传性小说》(How to Write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Essays,玛瑞纳图书出版公司)。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3期,责任编辑:胡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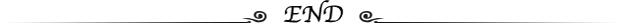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