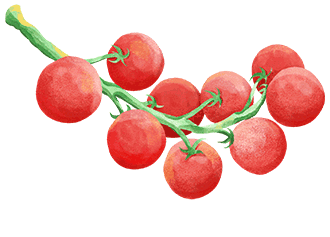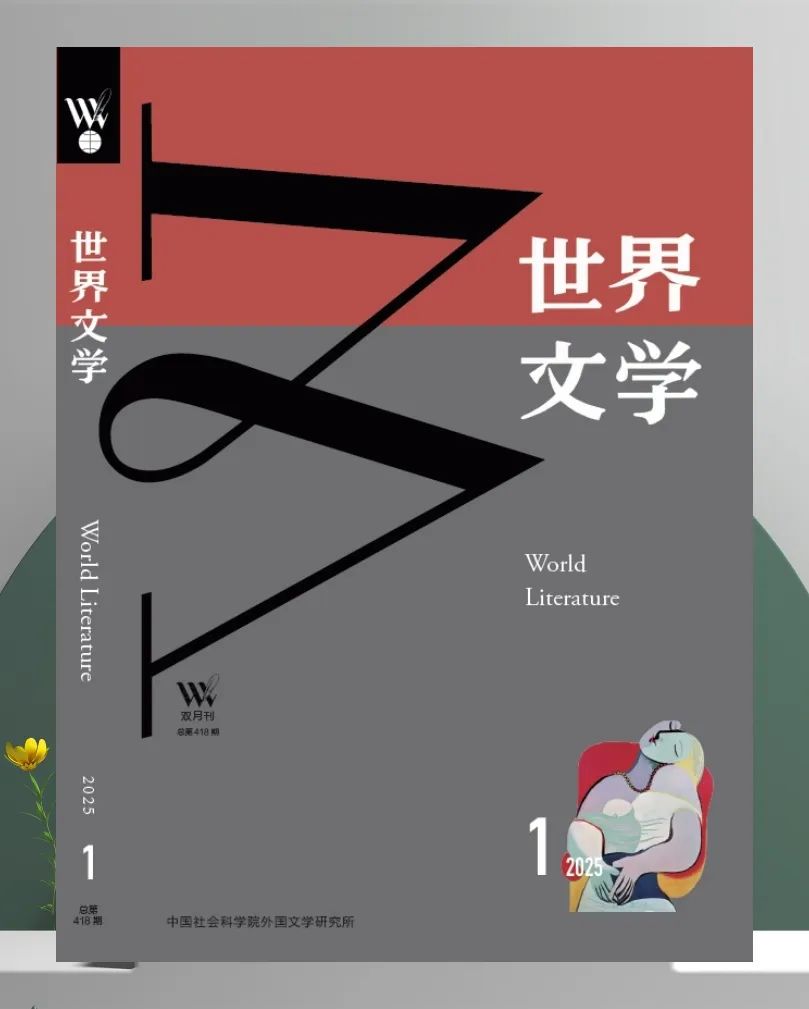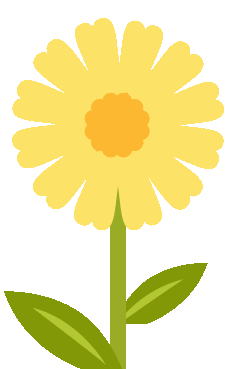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朱雨:名为家的鬼魂——读《闭门的家》有感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哥特式的情节连接了小说的两条线索:刷墙的仪式既完成了主人公、父母与“家”的合体,又实现了主人公对“家”的致敬与告别。“鬼魂只是一种化身”,对主人公而言,过去的鬼魂是沉默的化身,盘踞在失声的灰色世界里;现在的鬼魂则是“家”的化身,他学会了为记忆命名,也学会了回望曾经的“家”。
朱雨
近年来,社会学名词“原生家庭”在社交媒体上流行,并且常以负面涵义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试图从中找出当下困境的根源。“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无形且深沉的,就像游荡在人心中的鬼魂;或者引用西班牙作家赫玛·涅托在小说《闭门的家》(载于《世界文学》2024年第6期)中的话,“家”会把自己的根“一直扎到黑暗的地底”。这篇小说的情节不算复杂,但叙述充满跳跃性:主人公的童年与成年经历交替浮现,“家”在一幕幕闪回中保持沉默,最终与主人公达成和解。然而,这种“和解”不是一种简单的妥协:主人公离开了“家”,收获了全新的人生,并且在以自己的理解完成对父母和“家”的纪念仪式后,才可以“无所畏惧地回望他的根系”。

对主人公来说,“家”的沉默如同无休止的暴风雨,他在沉默的深渊中逐渐窒息。他从未怀疑过“爱”在家中存在的事实,但长期沉默导致的低气压阻碍了“爱”的正常表达,这也是他最终选择离开的原因之一。平静的水面下暗藏激流,激流不断擦身而过,却难以碰撞出浪花;母亲的去世又带走了家中“仅有的活力和语言”,失语的父子只能偶尔在分歧中暂时打破沉默。主人公会在童年时暗暗妒羡同龄的孩子,他在家中扮演着服从者的角色,遵守“沉默”这一律令,但外面的世界总是撩拨着他内心的火焰,借哑巴男孩之手抛来红色水球,炸裂在他心灵的百叶窗上。这些刺激呼唤着他,引导他日后卸下重负,走向另一种生活。他需要的是一个诞出人声的子宫。
“万物得到命名之后才真正存在”,“命名”是一种声音、一种语言,而人的情感不能离开这种“语言”。主人公与父母没有语言上的隔阂,却不能交换彼此的心意,只能让情感如顽石般浸泡在沉默中;他与哑巴男孩语言不通、无法直接交流,但信报间里的亲吻和圣乔治节的彩纸玫瑰可以化开顽石,少年的心绪在悸动中得到释放。语言可以是无声的,可以是慌里慌张的,但是如果没有语言,人就会永远困在灰色的屏障之中,触碰不到外界的色彩。主人公收到了男孩羞涩的“语言”,虽然这只是一次角落里的邂逅;当他在未来的某一天想起打破沉默的水球,想起信报间加速的心跳,他一定知道那才是最初的语言。语言激发情感,情感带来勇气,勇气支撑着他选择自己的路,实现年少时的心愿。他用“逃生”形容这条道路,尽管记忆的藤蔓总会在不经意间攀上路面。


如果小说的一条线索是主人公的离家和成长,那么另一条线索就是他与父亲、与“家”的和解。一场意外爆炸带走了母亲的生命,却没有在“沉默”的律令上炸开任何缝隙。父子二人默契地保持着爆炸前的生活状态,直到前来购房的旅游公司搅动水面,暴露出藏在水底的巨石。这一次,主人公在沉默中退出了对峙——他已经背负巨石长达二十年,不能让未来的人生继续在水下窒息。“在他眼里,生活总是在别处”,他厌倦低气压的家庭——这个被他视为“牢房”的地方,需要走向彩色的世界。他会怜悯独居的父亲,但是在父亲面前,他只能是当年那个静悄悄的孩子,刹住一切流到嘴边的温情话语。推动他真正走上和解之路的是父亲中风后的卧床,就像许多“原生家庭”的既定走向一样。长时间的陪伴给了他看清父亲与“家”的机会,也给了他几个月的思考时间,让他能够从容地规划父亲身后的纪念仪式。


他慢慢明白,在父亲的沉默之下也有火焰:父亲会在结束一天的劳作后和母亲相拥在一起,会在脑功能退化时念叨去世已久的母亲;父亲在房子里看着自己的家庭诞生、壮大,认为他可以与这个“家”对话;他无法接受房子被收购的结果,即使死也要死在家里而不是医院。父亲变成了一个影子,固执地游荡在同样垂垂老矣的家中。公寓里游人如织,闭合的家门终有打开的一天,但在那天到来之前,主人公决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扮演最后的抵抗者。“那段日子,他和父亲说的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沉默没有离开这个家,不过情感能跨越沉默的鸿沟。
在小说临近结尾的部分,作者揭示了开篇处“鬼魂”的真相:主人公将父母的骨灰倒进涂料桶,均匀涂抹在房间泛黄的墙壁上。他亲吻墙壁,与阴阳相隔的家人对话,而租住的游客对管道异动和地板脆响感到恐惧,纷纷留下差评。哥特式的情节连接了小说的两条线索:刷墙的仪式既完成了主人公、父母与“家”的合体,又实现了主人公对“家”的致敬与告别。“鬼魂只是一种化身”,对主人公而言,过去的鬼魂是沉默的化身,盘踞在失声的灰色世界里;现在的鬼魂则是“家”的化身,他学会了为记忆命名,也学会了回望曾经的“家”。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出走少年回归家庭的传统故事,“和解”更不意味着向过去低头。在这场纪念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充满爱意的谢幕——主人公向父母坦白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很幸福,虽然他不会忘记童年时父亲的警告,但爱的种子总会顶开沉默的巨石,“家”也总是愿意成为孩子新的起点。或许鬼魂可以是“家”的存在形式之一,长期的心口闭合导致家庭成员只能以跨越两界的方式交流,但至少“原生家庭”的裂痕消弭在墙壁涂料之下,逝者已经安息,生者也获得了慰藉。夜幕降临,主人公躺在父亲去世的房间里,他的呼吸与“家”同频。他将静静等待记忆的藤蔓,等待那个名为家的鬼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