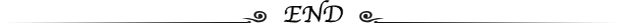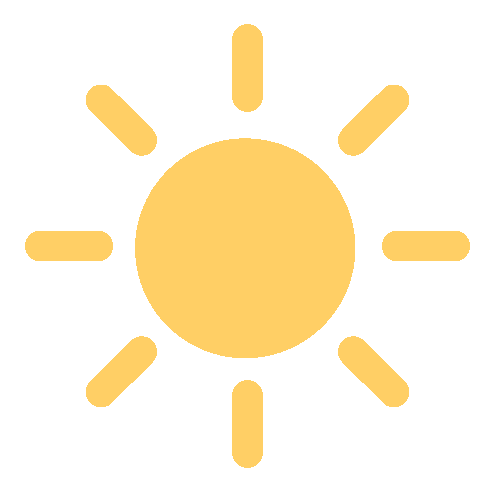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弗•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三次相见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忙乱世界的又一个奴才,
透过万物身披的粗糙外貌,
我看到了不朽的紫气东来,
我感受到神的光芒照耀。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作 刘文飞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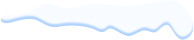
我在提前庆贺战胜了死神,
我用爱松绑了时间的链条,
永恒女友,我不呼唤你的名称,
但你能够感觉这颤抖的歌谣……
我不相信充满欺骗的世界,
透过万物身披的粗糙外貌,
我感觉到不朽的紫气东来,
我意识到神的光芒照耀……
你是否三次呼应我热切的目光,
哦不,这肯定并非我的梦幻!
你是预兆、是救助或是奖赏,
你的形象在回应灵魂的召唤。

第一次,哦,很久以前的往事!
转眼已有三十六载的时光,
孩子的心灵伴着梦的忧思,
突然之间体验到了爱的渴望。
我当时九岁……她也同样年纪。
费特笔下的“莫斯科的五月天”。*
我表达了爱。沉默。哦,上帝,
有个情敌。啊!他会发出挑衅。
决斗,决斗!耶稣升天节的弥撒。
灵魂在痛苦激情的沸水中翻滚。
我们在拖延……借口吃喝拉撒,
嗓音拉长,衰落,最终消隐。
祭坛敞开……可牧师和执事在哪里?
可哪里有俯首祈祷的人群?
激情的水流干涸,了无痕迹。
蔚蓝环绕,蔚蓝在我的心灵。
你周身焕发着金色的蔚蓝,
你手持一枝异域的花朵,
你站在那里,笑容灿烂,
向我点头,然后消失在雾中。
童稚的爱情已让我感觉陌生,
我的灵魂已无视吃喝拉撒……
德国奶妈伤心地一再重申:
“瓦洛佳,唉!他是真傻!”
*俄罗斯抒情诗人阿法纳西·费特(1820—1892)于1857年创作诗歌《莫斯科宜人的五月天》,其中有几句诗描述了恋爱中人甜蜜的忧伤。


岁月流逝。我首次出境,
是带有硕士头衔的副教授。
柏林,科隆,汉诺威,
相继在我的眼中一闪而过。
不是西班牙,不是世界中心巴黎,
不是东方绚丽的耀眼光芒,
大英博物馆才是梦想之地,
它从未欺骗过我的梦想。
我怎能忘记这幸福的半年?
不是转瞬即逝的美的精灵,
不是生活、激情和自然,
是你俘获了我全部的灵魂。
就让无数的人在那边忙碌,
伴随喷火机器发出的轰鸣,
就让没有灵魂的巨人等候,
神圣的静谧,我独自一人。
当然,万事都要仔细斟酌!
我独自一人,却并不厌世;
人们往往也会陷入孤独,
我如今该把哪一位提起?
可惜我无法将他们的姓名
纳入我的诗作,传闻很耳熟……
我会说,有两三位英国奇人,
还有两三位莫斯科来的副教授。
不过阅览室里只有我一人;
有秘密的力量在为我选书,
上帝知道,信不信由您,
好让我阅读关于她的全部。
当内心涌起罪恶的念头,
让我拿起不相干的书本,
这样的事情经常会有,
我只好羞愧地走向家门。
然后有一天,已经快到秋天,
我对她说:“哦,神性的花朵,
我能感觉到,你就在身边,
为何在我成年后你不再显容?”
当我想到这个崇高的词汇,
金色的蔚蓝突然充盈四周,
在我的眼前再次闪耀光辉,
她的面容,只有她的面容。
那一瞬间成为长久的幸运,
心灵又对尘世的事熟视无睹,
如果能遇见“真实的”传闻,
话语就会变得含混而又糊涂。


我对她说:“看见你的面容,
但我还想看到你的全部。
你曾对孩童的我慷慨迁就,
你也不能拒绝已长大的我!”
“去埃及!”内心响起一个声音。
火车带我向巴黎,向南方。
感性甚至没与理性抗争:
理性沉默不语,像白痴一样。
里昂、都灵、皮亚琴察和安科纳,
巴里、布林迪西和费尔莫,
我乘坐一艘不列颠轮船,
置身波浪起伏的蓝色怀抱。
开罗的阿巴特旅店让我落脚,
可惜这家旅店如今已关停!
它舒适又朴素,世上最好……
住有俄国人,甚至莫斯科人。
十号房间的将军让众人捧腹,
他记得高加索的古老风俗……
提起他的姓名也并非罪过,
我不念旧恶,他去世已久。
他就是著名的法德捷耶夫,
一位舞文弄墨的退役军人。
他是花花公子,呼朋唤友,
他身上藏有黑暗的潜能。
一日两餐,我俩坐在一起;
他谈兴很浓,神情愉悦,
他擅长讲述滑溜溜的段子,
还要尽可能加进一点哲学。
我一直在期待被允诺的相见,
有一天,在静谧的夜晚,
像是一阵微风的清凉呼吸:
“我在荒漠,请你来见我。”
我没有补给,也没有钱财,
步行前往鬼才知晓的地方
(我的衣袋早已空空如也,
我已在旅店度过数天时光,
从伦敦前往撒哈拉也不免票),
像涅克拉索夫笔下的弗拉斯*,
我在晴朗的一天走向荒漠
(我找到了韵脚,谢天谢地)。
你大约在笑,在荒漠深处,
我身披大衣,头戴高礼帽,
健壮的贝都因人视我为恶魔*,
我引起惊慌,差点被杀掉,
两个部落的酋长举行会议,
一阵阿拉伯语的喧闹之后,
他们做出决定,事不宜迟,
像个奴隶我被捆住双手,
和蔼地押我走过一段路程,
他们给我松绑,转身就走。
你我一同微笑:就像诸神和人
微笑面对已经过去的灾祸。
与此同时,静夜降临大地,
它笼罩一切,直截了当。
我在四周只能听见静谧,
看见黑暗,透过繁星的微光。
边看边听,我在大地躺卧……
突然听到放肆嚎叫的胡狼;
胡狼大约在幻想中撕咬我,
我甚至没有向它举起棍棒。
胡狼算得了什么!寒意逼人……
一准是零度,白昼却是酷暑……
群星闪烁着无情的清冷;
星光和严寒都是睡眠的敌手。
我久久地躺卧,睡意难耐,
微风拂过:“睡吧,我可怜的朋友!”
我睡了;当我敏感地醒来——
玫瑰花香充盈着大地和天空。
你身披天上辉煌的紫衣,
你眼里满含蔚蓝色的光,
你在端详我,你酷似
创世之日的第一道光芒。
过去和现在,永远的未来,
这静静的目光拥抱着万物……
我的身下是蓝色的河流和大海,
还有遥远的森林,雪山的顶部。
我看到了一切,一切的一切,
只有这女性之美的形象……
你有限的形象能容纳无限,
你占据着我的目光和心房。
哦光明的你!你没有骗我:
我在荒漠目睹了你的全部……
那些玫瑰在我的心灵不会枯萎,
无论生活的界限出现在何处。
稍等一下!幻象转眼隐消,
一轮圆圆的太阳升上天穹。
荒漠寂静。灵魂在祷告,
报喜的钟声长鸣在心中。
神清气爽!但我两天没吃喝,
我的仰望也变得模糊不清。
人们说,饥饿会来给你上课,
唉!当你尝试去拥有灵魂。
我沿着落日向尼罗河走去,
在傍晚时分回到了开罗。
心灵留存粉色微笑的痕迹,
两只靴子上却有许多窟窿。
外人看来这一切十分愚蠢
(我道出事实,隐藏了幻象)。
将军他喝着汤,默不做声,
然后他看着我,神态端庄:
“当然,大脑有犯傻的权利,
但是最好不要把它滥用:
人类的愚蠢可不是大师,
疯狂的类型也各有不同。
“因为您遭到了他人的欺负,
一个疯子,或是一个傻子,
关于这一次丢人的事故,
您今后再也别对他人谈起。”
他谈了很久,兴高采烈,
我的面前已无天蓝色的雾,
生活的海洋被神秘的美打败,
它在缓缓地向着远方移步。

忙乱世界的又一个奴才,
透过万物身披的粗糙外貌,
我看到了不朽的紫气东来,
我感受到神的光芒照耀。
我用预感庆贺战胜了死神,
我用爱松绑了时间的链条,
永恒女友,我不呼唤你的名称,
但是请你宽恕我虚弱的歌谣!
1898年
*俄罗斯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弗拉斯》一诗写于1855年,诗中的弗拉斯是一位俄国农民。
*这行诗中提到的贝都因人,指的是在西亚和北非的沙漠与荒原地带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1853—1900),俄罗斯19世纪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诗人,在俄国文化史上享有较高地位。《三次相见》(Три свидания)是索洛维约夫的文学代表作。这首带有浓郁自传色彩的长诗融哲学、神学思考与文学想象于一体。作者写了自己与智慧女神索菲娅的三次相遇(即他的三个幻想),将他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具象化。
评论文章《〈三次相见〉:索洛维约夫哲学的诗歌呈现》除了对长诗进行详细解读外,还对其相关背景信息及其在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思想乃至俄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做了全面、透彻的解析,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和把握《三次相见》的内涵。
《三次相见》选译自苏联作家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索洛维约夫著作《诗作和谐谑剧作选》(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шуточные пьесы)。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4年第6期,责任编辑:孔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