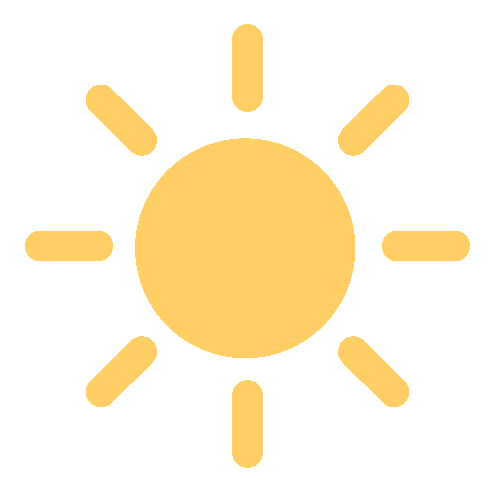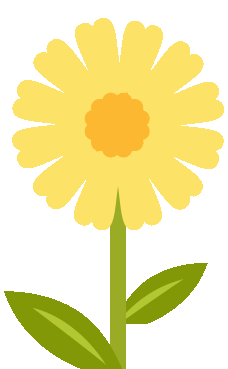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丨安•玛•舒亚【阿根廷】:钓鱼往事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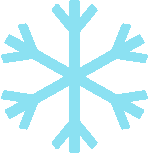

安娜·玛丽亚·舒亚作 赵彦译
小时候,每到夏天,我和爸爸都会去钓鱼。我们的鱼盒是木制的,外面刷了一层绿漆,里面藏有各种型号的鱼钩:小的用来钓银鱼,大的用来钓鲨鱼。鱼线上的铅坠也有各种功能和型号。铅坠通常呈金字塔状,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们在码头或“波多黎各深坑”钓鱼时,因为岩石太多,铅坠总是会一不留神就被勾住。所谓“我们”,实际上只是我父亲一人在钓鱼,而且米拉海也没多少鱼可钓。我有一根小鱼竿,但从不带它,我喜欢的不是钓鱼,而是待在爸爸身边。码头上的人都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其他在那里钓鱼的人,比如弗拉科,满头金发,眉毛墨黑。还有一位老先生叫伊巴拉,比我爸爸年纪还大。我为自己丰富的垂钓知识得意,一有机会就炫耀起来。比如,我知道石斑鱼虽然个头小,但拖拽力很大,有时鱼竿弯折的幅度会让人误以为钓上了大鱼。有时候,某个垂钓的人因为浮子在抖动而费好大力气往上拖鱼线,整条鱼竿拉成弓状,绷得发抖,我就会走过去提醒他:“只一条星鲨罢了。”我知道如何辨别星鲨,那是一种小鲨鱼,身上有黑斑,我们叫它“小花马”。如果钓到星鲨,人们会把钩子从鱼身上取下来,把鱼扔回水里。有时候,我们也能钓到一两条鳐鱼。爸爸告诉我,对付鳐鱼得松开鱼线上的星形卸力【卸力是挂在鱼竿线轴上起制动作用的零件,用来在钓到大鱼时控制鱼轮被大鱼强拉出线的力度,消耗大鱼的力气】,把线放长一点,否则它们就会扯断鱼线。有一次,爸爸单枪匹马去钓鱼,回来后说自己那天运气糟透了,刚松开星形卸力,就有个东西(我们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冷不丁咬住钩子,迅速地把鱼钩拖走,尼龙线在那一瞬间的摩擦灼伤了他的拇指。我清楚地记得爸爸拇指上那道伤痕留下的白线。
可是,我爸爸死了,能相信吗?
最开始是爸爸摔倒后的当天晚上,他感觉到脊柱靠近腰部的地方抽了一下,前所未有的疼痛袭来。第二天早上,爸爸卧室的地板上铺了一张床单,我不明所以。“你爸爸整晚都睡在地板上,”妈妈告诉我,“他在床上连翻身都翻不了。”到了晚上,爸爸回来的时候,只是觉得有点累,疼得不那么厉害了。“从地上起来真是酷刑。”爸爸让我放心,下午他去看过医生了,诊断结果是椎间盘突出。“吃点止痛药吧。”
绿盒子里还会有鲭鱼,我们用它来做鱼饵。有时候爸爸会把切块的活儿交给我,但上饵的环节永远是他亲自来做,因为他怕鱼钩刮伤我的手(爸爸总是怕我受伤。他还发明过一个可以套在刀刃上面的铁丝护罩,让我学习削橙子的时候不会切到自己)。鲭鱼的腥味很重,妈妈看到我们在家里鼓捣鱼盒就会发火,平时我们只好将它收在汽车的后备箱内。尤为特殊的场合,爸爸会买上一些鱿鱼放在冰箱里:对我们来说,鱿鱼是顶级鱼饵。码头上风总是很大,我经常穿妈妈织的一件芥末黄色的肥大套头毛衣,假装自己是一只箩筐:蹲下身子,把这件对我来说太大的套头毛衣往下拉,直到完全罩住腿,勾住靴子边。还有一个避风的方法,是躲到码头那边一间小房子的外墙根下面。风向要是变了,我就换一面墙。
渔民收网后,我自得其乐地玩起占卜游戏,猜他们捕到多少条黑眼鱼,大部分时候都是一条也没有。我学过怎么拿稳黑眼鱼——它们会在我的手上留下亮晶晶的鳞片——再扔进渔民事先准备好的铁皮筒里。抄网时,渔民会把一团黏状的鱼饵扔进水里吸引黑眼鱼,我很喜欢那种鱼饵的气味。不过,码头上能钓上来的只有星鲨。
在“波多黎各深坑”那边,大家会更走运。我们得从悬崖上一道天然形成的小天梯爬下去,对我来说,这看上去有点危险,不过也别有趣味。通常爸爸会先下去,然后照看着我爬下来。所谓“深坑”,其实是一个又窄又长的小滩涂。爸爸会在沙滩上甩甩鱼竿,用这种方式测试铅坠到底能抛多远。他用步子来丈量距离:每一步算一米。我总是希望鱼竿抛得越远越好,但其实从来不曾超过七十米。爸爸的足迹我记忆犹新:沿着海滩绵延差不多七十米。
可是,我爸爸死了,能相信吗?
很快,爸爸开始感觉右腿抽痛。最初是脚踝处,随后是小腿。脊柱已经不疼了。当时,他上班的那家工厂出了些财务状况,爸爸不得不每天在市中心走很多路,从一家银行到下一家银行。“别折腾了,和别人一样去看个医生吧。”连素来对医生没好感的母亲都这样劝他,“对病情一无所知只会让病更严重。”这是真的,父亲已经跛得很厉害了。三王节的周末,他疼得坐也不是卧也不是。那天,妈妈去马德普拉塔看望我的外祖父母了,我觉得自己必须负起责任,让爸爸尽可能舒适一点。抽痛已经爬升到大腿了,爸爸只能半卧在客厅的沙发上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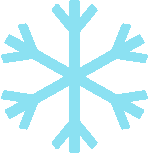

我们钓鱼的真正好去处其实是爸爸称为“臭水坑”的地方,离家很远,我们并不常去。那一带是马德普拉塔河排放污水的地方,鱼类加工厂会往里面扔掷加工后的废料。要去“臭水坑”,必须起个大早。去的前一天,妈妈会给我们准备好三明治和饮料。我们垂钓的地点在悬崖上。地上铺满了鱼骨头和各种垃圾,亮晶晶的绿头苍蝇嗡嗡地围着垃圾堆飞了一圈又一圈,不紧不慢。该死的,爸爸骂骂咧咧,他烦透它们了。“臭水坑”能钓上鲶鱼,就是那种胖胖的、长着胡须、腥味扑鼻的鲶鱼。一钓上来,爸爸就会赶紧剪掉它们的胡须,因为鲶鱼的胡须很扎人。到了晚上,妈妈会一边喋喋不休地数落我们,一边把鲶鱼做成酱。
我们钓鱼时几乎一声不吭。必须保持安静,以免把鱼吓跑。爸爸握紧鱼竿,食指和拇指捏住尼龙线,感觉鱼有否咬钩。每次他让我握一会儿鱼竿,我总感觉有鱼上钩,让他赶紧起竿。有两个问题经常让人头痛:鱼钩和鱼线轮。鱼钩要是缠住了,爸爸就会拽紧尼龙线将鱼竿平放在地上,尽可能揪住鱼线,再一下子松开。要是不解开打结的地方,鱼线就会扯断。无论是鱼钩还是鱼线轮,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让人抓狂。尤其是鱼线轮最为棘手,有时还会跟鱼线一起出状况,一旦缠上了,我们就只能先都收起来,回家后再耐心地慢慢拆解。鱼线轮不好使的话,我们整整一个星期都会颗粒无收。
我最喜欢的环节是剖鱼。爸爸会用他藏在绿盒子里的小刀片给鱼开膛剖肚,割鲶鱼的胡须和鳐鱼的尾巴也是用它。他会先取出内脏,然后割开肠子,看看它们最近都吃了什么。我总是想象里面可能会出现种种奇迹,比如一只魔戒,或者玻璃碎片。我从来不会失望。查看内脏时,爸爸会耐心地给我讲解鱼都吃了什么。有时,我们会在鱼肚子里发现蜗牛或小螃蟹之类的小家伙。有一次,我们钓到一条黑色海鲈鱼,肚子里鼓鼓的全是鱼籽。那条海鲈鱼大得出奇,爸爸拍了一张照片,拍照时它的嘴巴还挂在鱼钩上呢。我还保留着那张照片。
可是,我爸爸死了,能相信吗?
为了决定父亲是否动手术,妈妈提前从马德普拉塔赶回来。先是创伤科医生,再是神经科医生,他们都告诉我,爸爸“要是不动手术,腿就废了”。妈妈和爸爸不想做手术,但医生告诉爸爸:“坐骨神经压迫,你想一辈子拖着一条没用的废腿吗?”他们知道爸爸肯定不愿意。“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告诉他,“必须马上动手术。”医生们想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
在米拉海上我们有过两次“滑铁卢”。一次是鱼汛来的那天,下着大雨,我们正在家里修补鱼线。我喜欢把玩鱼钩上那些小尼龙绳结。突然,门铃响了,是弗拉科。“码头那边来了一大群鱼。”说完就跑走了。


码头上芦苇丛生,人头攒动。海浪涨得很高。爸爸怕我被鱼竿的铅坠打到头,不让我离开他左右。我们没带鱼竿。码头上平时的常客都在,还多了很多人。鱼的确很多,史无前例。一大群无须鳕鱼后面跟着一群鱼。伊巴拉钓到了五十一条半无须鳕鱼,说“半条”是因为另外半条在钓出水面前已被鱼吃掉了。鱼牙齿很锋利,长着一副凶相;相反,无须鳕鱼性情比较温和。鱼群的大部队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不值得再回家去拿鱼竿。
另一次是在“环宇深坑”举办的捕鲨大奖赛。“环宇深坑”位于米拉海入口处,是一个大海滩。爸爸那次也没带鱼竿,他拿着摄像机拍下了在那里钓鱼的人。从录像带里可以看到,我当时已经不是小朋友了,穿着蓝色套头毛衣,衣服大得很,松松垮垮的,但也遮不住我身体正在发生的变化。我还扎了一根马尾辫,显得奇丑无比。渔民们捕获了大批鲨鱼,几乎都是怀孕待产的雌鲨鱼。有一个镜头拍到某个满头栗色头发的健壮男孩正在踩一条鼓起肚子的鲨鱼,出来了六七条还在扑腾的小鲨鱼。爸爸没出现在任何一个镜头里,但我们都知道他在那里,在镜头的另一边。
可是,我爸爸死了,能相信吗?
爸爸去世前一天,在疗养院里,他让我们给他拍点东西。当时手术做完已经三天了。爸爸喜欢用镜头记录重要事件:翻车车祸现场、工厂的突击检查、我出水痘……可我不怎么想拍他。他仰面躺着,无法动弹,手臂上扎着针,针头连着小塑料管,小塑料管接上一个盛满液体的输液袋,固定在高大的立式支架上。爸爸感觉好点了,还让我给他拿杏仁糖。
鱼钩并不总是勾在鱼的嘴里。有时,鱼会把整个鱼钩吞下去,这时候,取鱼钩不啻于一场屠杀,简直是生剖。有时候,鱼钩会勾在鱼鳍或者鱼身上。碰上后两种情况,爸爸会说这条鱼是我们“偷来的”。我们去“臭水坑”的时候,总是带着我们称为“大盗”的四棱形大鱼钩(它像四个巨大的钩子粘在一起)。“大盗”用来在不扯断鱼线的情况下钓起那些大块头鱼。一旦看起来有大家伙上钓了,爸爸就会收拢鱼线,让我准备好“大盗”在一旁待命。海鲈鱼钓出水面时会发出奇怪的、持续不断的哼鸣,像打鼾一样。所以有个绰号叫“打鼾者”。鲨鱼在空气中的耐力最为持久。鳐鱼生命力顽强,爸爸用小刀斩断它们的尾巴时,它们会血流如注。
我从未问过爸爸,为什么鱼离开水就会死?我觉得鱼没有鼻子,自然是不能呼吸。爸爸喜欢在钓鱼的时候为我解答各种疑惑,而我总是想方设法问出一些古怪刁钻的难题让他为我解答。
可是,我爸爸死了,能相信吗?
“我喘不过气了。”妈妈哭着告诉我爸爸曾这样向她叫苦。只要一抬起头,她就能看到他那双绝望狂乱的眼睛。但是,氧气什么忙也帮不上,按压心脏也无济于事。科拉明药【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物】也没用。他没有呼吸了。“我们尽力了。”妈妈向我哭道,“肺部栓塞要了他的命。”
小时候,每到夏天,我和爸爸都会去钓鱼。
可是,我爸爸死了,能相信吗?他被钓起来了。

安娜·玛丽亚·舒亚(1951—),阿根廷当代重要作家,诗人,编剧,有西语文学界“微型小说女王”之称。出版有7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8部微型小说集和一部诗集,作品被翻译成15种语言。曾获阿根廷国家艺术基金奖、伊比利亚美洲胡安·何塞·阿雷奥拉文学奖等。《钓鱼往事》(Los
días de
pesca)选自舒亚1981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Corregidor出版社),是她在短篇小说领域的成名作,已由作家授权本刊发表。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4年第6期,责任编辑:汪天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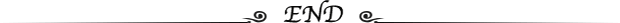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