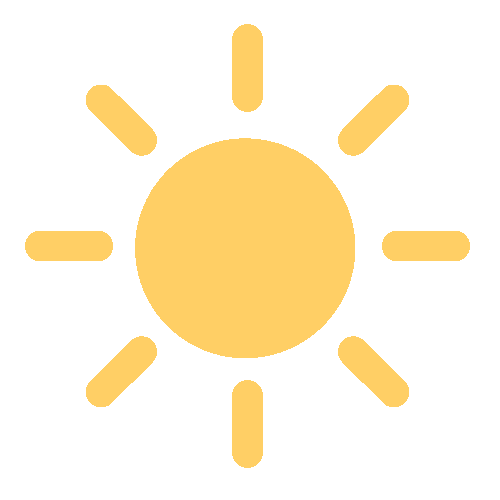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颜宽【中国】:“谁偷走了我的外套”——评曼德尔施塔姆小说《埃及邮票》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颜宽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罗斯文学中‘人’的观念研究”(22AWW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埃及邮票》创作于一九二七年。在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史上,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虚构小说。除去作家诸多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文学评论,曼德尔施塔姆一生创作过四部重要的非韵文作品,分别是《时代的喧嚣》(1925)、《埃及邮票》《第四散文》(1929—1930)及《亚美尼亚旅行记》(1933)。这四部作品中,第一部是自传性散文,第三部是讽刺性速写,第四部是游记,唯独《埃及邮票》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小说。这部作品自诞生起就受到俄国文学批评界的极大关注,若干年间,对它的诟病远多于赞美。其原因,首先在于它的艰深晦涩令文坛人士大为头痛,几乎所有评论者都曾抱怨这部小说不易理解。其次,是作家在小说中插入了叙述者“我”对主人公的大量评论及相关的联想与回忆,而这部分看似可以与情节线索相剥离的内容,几乎占据了小说一半的篇幅,如此一来,作品看起来更像一份带有修订意见的草稿。就连以讲究形式技巧著称的理论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都抱怨小说写得过于散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们越来越发现《埃及邮票》具有深刻的内涵,其结构形式也随着现代性精神的普及而得到广泛认可。俄罗斯文学研究界甚至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埃学”考据研究,并取得了日渐丰硕的成果。小说对俄罗斯经典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其独有的叙事结构对人物塑造及情节推进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引人注目。



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不难发现,《埃及邮票》延续了“小人物”这一俄国文学传统人物主题。小说主人公帕尔诺克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十九世纪彼得堡的小人物们。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叶甫盖尼、果戈理《外套》中的巴什马奇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中的杰武什金,皆是帕尔诺克的穷亲戚。但是,上述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所面对的压迫属于强者对弱者的迫害,这种压迫均来自社会上层,即统治阶级及其所附属的官僚体系。但是在《埃及邮票》中,这样的上层结构并不存在,克伦斯基政府没有丝毫威力,犹如寡淡的“柠檬水”,又“似鲈鱼般消失、沉睡”。帕尔诺克所受到的压迫恰恰来自和他同一阶层的其他平民,比如裁缝梅尔维斯、洗衣女工和鞋匠。在这里,传统小人物主题中“强者迫害弱者”被替换成了“弱者迫害更弱者”。如果说十九世纪文学中小人物的悲剧源自社会体制的缺陷、统治阶级的残忍与不公,那么在《埃及邮票》中,帕尔诺克的悲剧则是社会体制崩溃及时代大断裂导致文化、法制、道德完全失去约束造成的,其后果便是社会开始奉行最原始的丛林法则,弱者利用一切机会将更弱者挤至社会边缘,毁灭其人格价值。帕尔诺克的不幸便由此而来。
小说一开始,梅尔维斯决定对帕尔诺克实施“正义”的惩罚——在夜晚偷走了后者的礼服。【曼德尔施塔姆在文本中隐去了事情的前因后果。通过对比小说草稿,可以得知,梅尔维斯是因为帕尔诺克拖欠五卢布的工费而决定偷回礼服】而那件礼服对于帕尔诺克来说,可不仅仅是一件外衣,还是社会身份的象征。在小说草稿中,帕尔诺克正是穿着这件礼服去讲授人智学、出席午餐会、和女人约会的。但是如今,失去了这件衣服,也就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叙述者以插叙的方式感叹道:“哎,梅尔维斯,梅尔维斯,你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要抢走帕尔诺克尘世的躯壳,为什么要拆散他和他可爱的女伴?”
失去“尘世的躯壳”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死亡。而那件失去的衬衫也具有类似的象征意味。洗衣女工拒绝将原本属于帕尔诺克的衬衫还给他。“她正躺在搁板上,已经熨烫平整,吞下了不少大头针,胸部的凸纹布亮光闪闪,熟樱桃色的细条纹遍布全身。”吞下大头针象征着受刑,熟樱桃色的细条纹象征着浑身上下鲜血流淌,这是主人公的又一次象征性死亡。
对同类的迫害以及对个性的践踏在小说第四节(即民众对小偷处以私刑的场面)达到了高潮。私刑是在没有得到法律程序认可的情况下,以寻求社会公正为借口,以集体参与的形式对他人造成身体与精神伤害的暴行。实施私刑的过程既不存在双方公平辩论的可能,也不考虑量刑轻重,而是伪装成公权力的集体暴力对个性的压制。因此,在曼德尔施塔姆笔下,私刑的受害者是没有面孔的,取而代之的是他的衣物、后脑勺及耳朵。曼德尔施塔姆用借代手法暗示了受害者人格的丧失。不过,施暴者自身同样在施暴过程中失去了人格,成为集体的附庸。曼德尔施塔姆将人比作昆虫,以这种方式来表现集体无个性,比如,他写到,“这个奇怪蜂群的蜂后”,“人群挤在一起,像蟑螂一样”,“来路不明的人形蝗虫数之不尽,黑压压地挤满了丰坦卡河岸”。所有人都承受着集体的压力,“恐惧将人们像木桶上的一块块板条那样紧紧地箍在一起”。在这种压力下,人的个性被践踏,良知也随之泯灭。即使像帕尔诺克这样的少数人仍在极力抗争,终究还是难逃被时代碾压的命运。曼德尔施塔姆在小说第五节讲述了帕尔诺克最后一线希望的破灭。


帕尔诺克与心爱的姑娘约定在亚历山大剧院前会面,他为此准备好了礼服,买好了戏票,但克里日扎诺夫斯基大尉却掳走了他的心上人:帕尔诺克在剧院前苦苦等待时,克里日扎诺夫斯基大尉正带着那位姑娘在涅瓦大街上欢快地奔驰。帕尔诺克最后的希望也被残忍地剥夺了。值得注意的是,抢走礼服、衬衣及姑娘的原本是革命前人人喊打的宪兵大尉,但二月革命的风暴让一切都倒了个儿,克里日扎诺夫斯基成为时代的宠儿,作为时代的化身,夺走了帕尔诺克的一切。
除故事情节外,小说的名称“埃及邮票”也喻示着帕尔诺克的个性遭到践踏的事实。“埃及邮票”本是帕尔诺克的绰号。在曼德尔施塔姆以往作品中,“埃及”一般意味着稳定、实在与家园感。譬如,他在文章《论词的天性》(О
природе
слова)中做了如是比喻:“希腊精神是埃及逝者的灵船,它载着一个人继续漫游尘世的所有必需品,甚至也包括香水瓶、小镜子和梳子。”不过,在《埃及邮票》中,这个词组被赋予了另一种涵义。根据研究者罗涅恩的提示,在埃及曾经有过一套成熟的邮票回收利用技术。早先二道贩子们时常通过擦掉邮票上的邮戳来重复使用邮票。为了遏止这一投机行为,埃及邮政在二十世纪初推出了一种用特殊工艺制作的邮票。票面上的图案由特殊油彩制成,二道贩子们试图擦掉邮戳时,也会将票面图案一同擦除,这样一来,整张邮票就会变成白纸,从而失去价值由此,埃及邮票便获得了“易被抹消”的内涵。曼德尔施塔姆将这一内涵与“埃及”所具有的“稳定”“家园感”联系起来,延伸出了秩序崩溃、精神丧失等意义。在他的笔下,帕尔诺克犹如一张轻易就会被擦去图案、在后埃及时代变得多余而无用的埃及邮票。
帕尔诺克的故事是一则关于个性被践踏的寓言。帕尔诺克是动荡年代脆弱群体中的普通一员。在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个群体无法适应时代的生存法则,只能成为其他适应性强的个体的垫脚石。恰恰是这一点赋予俄国经典文学人物类型“小人物”以新的内涵:这里的“小人物”之“小”,不再是下层阶级相对于上层阶级的“弱小”,而是个人面对历史、面对时代巨变时所显现出的“渺小”。不过帕尔诺克并非《埃及邮票》中唯一的小人物,小说的叙述者“我”也背负着同样的命运。



“我”尝试向读者讲述帕尔诺克的故事,却讲得破碎凌乱,反而被大量看似不相关的插叙占了上风。俄罗斯作家霍达谢维奇与别尔别洛娃就曾抱怨小说的这一布局十分荒谬,对频繁出现的插叙感到愤怒和不解。他俩在一篇共同署名的文章中写道:“小说写得隐晦模糊,像是在呓语,有时甚至是胡闹,让人觉得完全站不住脚。你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它的意思:这是在说谁?为什么要这样做或那样做?这到底说的是谁?这个段落里指的又是哪个人?还有,这些如此精致的抒情插叙究竟意义何在?”但是事实上,小说作者正是借助这些插叙,才使叙述者的形象变得真实、饱满起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与帕尔诺克有着内在一致性:他们同是时代之惊涛骇浪中的小人物。
插叙的主要内容是“我”对童年及彼得堡的回忆。仔细比较每一段回忆文字,不难发现,文化符号与死亡象征物总是穿插出现。具体来说,这样的文化符号主要包括那些凸显异国风情的家具、钢琴、文化沙龙、音乐会、芭蕾舞、教堂、马林斯基剧院、艾尔米塔什及皇村;而作为死亡象征物的,则是火灾、白喉、猩红热、寒冬、反常的炎热、葬礼等。
以小说中出现的第一段回忆为例。“我”回忆起梦境与老屋里的旧家具。梦境中出现了“中国人”及“美式布谷鸟决斗”,而老旧家具中有“维也纳式圆椅”和“荷兰式蓝花盘碟”,“我”把老屋形容为“物的埃及”,指出它渴望“瓦尔哈拉——科科列夫仓库”。在这里,大量地名用作定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象征着旧时代遍布各地的文化宝藏,即曼德尔施塔姆所眷念的世界文化。然而,这些带有地名的旧物件的结局,却皆是“死亡”:“决斗双方开枪射穿了玻璃餐橱、墨水瓶和家传的油画”,“时间的离心力将我们那些维也纳式圆椅及荷兰式蓝花盘碟甩向四面八方,一件不留”。其他物品,如摇摇欲坠的老屋、被搬走的钢琴和被法院充公的镜子,在语义上也明示了“死亡”之相。
“文化—死亡”这种微型结构还出现在“我”对意大利女歌唱家的两段回忆中。根据学者列克曼诺夫的注释,小说中提到的那位女歌唱家指的是十九世纪中期意大利著名女高音安吉奥利娜·博西奥。她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及欧洲各地巡演,一八五九年病逝于彼得堡。在《埃及邮票》中,这位女歌手自然也是世界文化的象征。但是在第一节中,对女歌手的回忆以她在彼得堡的葬礼结束:“后来,近卫骑兵从四面八方赶到奎朗教堂参加安魂弥散。金色的兀鹰纷纷啄食这位信奉天主教的女歌唱家。”在第七节,对博西奥的回忆以她的濒死场面结束:在她生命垂危之际,身边的人们被涅瓦大街上的消防车所吸引,转移了注意力,她只得独自一人轻轻哼唱初次登台时演唱的曲目:“她稍稍欠起身子,哼唱出接下来的旋律……再见了,茶花女、罗西娜、采琳娜。”
类似的精巧设计几乎出现在每一段回忆中。曼德尔施塔姆采用了白银时代颇为流行的“装饰体”手法,即作者在同一文本的不同语境中重复个别意象、结构、词语等等,强调被重复单元的语义内涵,突出其在整个文本结构当中的中心地位。这种写作手法好比交响乐的构曲原理,重复的部分好比主旋律。这是一种以形式而非逻辑线索来构成意义的书写方式,即“内容层面的因果联系完全失效或者退居次要地位,不再担当主角。主旋律叙述成为作品的主导结构,要求读者以阅读抒情文本的方式从整体层面考察作品”。在《埃及邮票》中,文化与死亡就是这样两段交错的主旋律,它们借助不同的隐喻在每段回忆的相同位置重复,以强化二者共同的内涵——往昔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叙述者的每一段回忆都可以看作关于“文化分崩离析”的寓言。这一寓言在文本中重复出现,构成了回旋的主题——旧时代的远去。
另一方面,随着叙述者在回忆中愈加强烈地表现出对过去的留恋,他对当今时代的惧怕也愈是弥漫在字里行间。透过叙述者对帕尔诺克故事的品评,我们不难发现他内心的恐慌。叙述者竭力想要拉开自己与帕尔诺克的距离,惶恐地写下“老天啊!可别让我像帕尔诺克一样!赐予我力量,让我和他有所不同”;他承认自己也像帕尔诺克一样受尽了侮辱与嘲笑;他把一九一七年的事件形容为“时代的体温蹿升至三十七度三”;他评价二月革命后的生活“既让人觉得恐惧,又让人觉得美好”。最后这句评价看似矛盾,但如果结合小说草稿中作者对时代的描绘来看,叙述者所说的恐惧是其自身作为弱者的心态,而感觉美好则是强者的心态。叙述者受到时代的挤压,背负着“小人物”的命运,是帕尔诺克的同貌人。但是与帕尔诺克不同,“我”并不是静态形象——“我”的心态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曼德尔施塔姆通过文本独特的叙述结构表现了这一点。
《埃及邮票》的叙述结构是小人物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叙述者与被叙述者身份相似,这有时会赋予叙述行为额外的意义。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穷人》中的主人公在翻看果戈理的《外套》时,因读到对自身处境的艺术写照而惊慌失措:“何必要写这种事?写它干什么?难道读者之中有人看了这个会给我做件外套吗?……结果你的公私生活统统被写到书里去,印出来,让大家传阅,挖苦,纷纷议论!”这种恐惧源于自身处境的暴露,而个体在面对这一危机时的第一反应,大多是出于否认目的的逃避。而这也正是《埃及邮票》中叙述者的做法。

起初,“我”极力否认自己与帕尔诺克相似。在“我”对他的评价中,冷漠与嘲讽的态度占据上风:“但是要知道世上真有这么一类人,他们从没得过比风寒更重的疾病,总是扣挂在现代生活的边缘……这类人从不觉得自己已经成年,都三十岁了还时常抱怨他人,咎责他人……我真想把他们集中起来,迁移到谢斯特罗列茨卡,可惜再找不到比这更远的地方了。”对刺激源的贬低是压制恐惧的常见反应。同理,小说前四节中大量有关世界文化的回忆也是为了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减缓刺激。这种笔法就好比胆小的观众在观赏恐怖片时会不由自主地遮住双眼,同时又在回忆那些安抚情绪的画面。叙述者在讲述使自己恐惧的情节时,也会通过插叙来淡化情绪。
然而,否认并不能消除问题。随着叙述的展开,“我”与帕尔诺克形象的重叠度越来越高,“我”在心态上发生了相应变化,不禁开始从回忆里挖掘类似的小人物的经历。“我”对帕尔诺克的评价也由嘲讽转为同情:“彼得堡,你要为你可怜的孩子负责!”与帕尔诺克共情意味着“我”对自身小人物处境的接受,这是叙述者心理蜕变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从病理学的角度分析,“我”的这一行为类似于满灌疗法(flooding
therapy),即让患者逐步暴露于令其害怕的刺激源之下,从而加深患者对恐惧的接纳,最终获得与恐惧共处的能力。在《埃及邮票》中,得益于对恐惧的正视,“我”逐步认可了自己与帕尔诺克的相似,并且将叙述重心从帕尔诺克的故事转移到了自身经历,暴露出自己深层次的忧虑。这一转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中的情节恰恰相反。《白夜》的主人公因惧怕讲述自己的难堪经历而采用第三人称转述(“还是让我用第三人称讲吧,娜斯琴卡,因为用第一人称讲太难为情了。”显然,讲述者是在利用第三人称的距离感来减轻回忆的刺激。而在《埃及邮票》中,当叙述者能够直面恐惧时,叙述便从第三人称自觉过渡到了第一人称。从第五节起,小说的实质内容就从帕尔诺克的故事变为“我”的故事。



叙述者在讲述帕尔诺克故事的过程中发现了真正的自我并实现了思想上的飞跃。那么,这位帕尔诺克,是纯粹虚构的人物吗?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不少研究者指出,他是曼德尔施塔姆以其友人为原型塑造的。这位友人,就是以“帕尔诺克”为笔名的瓦·雅·帕尔纳赫(В.Я.Парнах)。帕尔纳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文学团体“诗人车间”的成员,是诗人、翻译家、舞蹈家,发表过少量诗作,组织了苏联的第一支爵士乐团。在《埃及邮票》发表后,帕尔纳赫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在借帕尔诺克的形象诋毁自己,于是很快与曼德尔施塔姆断绝了关系。至于曼德尔施塔姆为什么要以帕尔纳赫作为自己作品主人公的原型,至今没有定论。但是有一种相对可信的说法,认为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选中帕尔纳赫,是因为他俩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出生于一八九一年,自小喜欢波德莱尔与魏尔伦,都是犹太裔诗人,都曾就读于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都在法国留过学并造访过索邦大学,后来又都加入了阿克梅派的“诗人车间”。或许,曼德尔施塔姆下意识地将帕尔纳赫看作自己的同貌人,而正是这一点促使他以帕尔纳赫为原型创作了帕尔诺克这个人物形象,他俩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投射在了《埃及邮票》中叙述者“我”与帕尔诺克的关系上。
至于叙述者“我”,他在小说中的困境确实反映了曼德尔施塔姆本人的困境。作家曾不止一次自比为被时代碾压的小人物。在他一九二三年的诗作《找到马蹄铁的人》中,“我”就以一枚被时代碾压的硬币自喻:“世纪尝试咬碎它们,在上面留下自己的牙印/时间切割我,就像切割一枚硬币/而我已无法勉力自持。”而在曼德尔施塔姆写于一九三一年的作品《拉马克》中,同样身为小人物的抒情主人公自比自然界中的低等生物:
在拉马克的活动楼梯上
我将占据最下一阶。
下行穿过环节与蔓足动物,
窸窣地游走于蜥蜴与蛇群,
沿着富有弹性的跳板,沿着曲折处,
坍缩,消失,就像普罗透斯。

被墨涅拉奥斯掐住的普罗透斯无论如何变形,都无法挣脱前者的双手,而曼德尔施塔姆无论如何逃避,也无法避免被挤压至社会边缘的命运。但是就像《埃及邮票》叙述者所经历的心理蜕变,死亡的恐惧并没有吓退曼德尔施塔姆,反而令他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重任。二十世纪初俄国历史巨变带给作家的巨大冲击不亚于死亡,它就像一场成人礼,让作家意识到知识分子在历史面前的责任。他决心为弱者书写历史,因为“仿佛盐粒铺满砌成的道路/良知在我眼前闪耀白光”,他发誓绝不背弃谋求正义的第四阶层。即便在一九三○年身陷囹圄之时,他仍旧不忘捕捉时代的噪声。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是一个人,一切都完了。不过,断裂也是财富。一定要记录下来。不要洒了。我觉得,你的热尼亚似乎还能坚持住。”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让伤痕以其原有的样貌醒目地留存在历史当中。不承认伤痕的存在,就无法避免同样的悲剧在未来再次发生。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暴露伤痕,让后人谨记、理解和评判。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还原被压抑的时代伤痛的过程中,曼德尔施塔姆像《埃及邮票》中的叙述者一样实现了与命运的和解,面对历史交出了问心无愧的答卷。也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的群体中促成对创伤性经历的分享,并建立一种避免重蹈覆辙的共识,推动后来者去制定新的社会正义标准。暴力或许会偷走良心的外套,但人道的温暖终究会捂热寒风中的正义。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4年第6期,责任编辑:孔霞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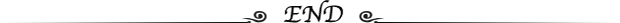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