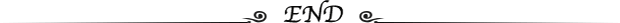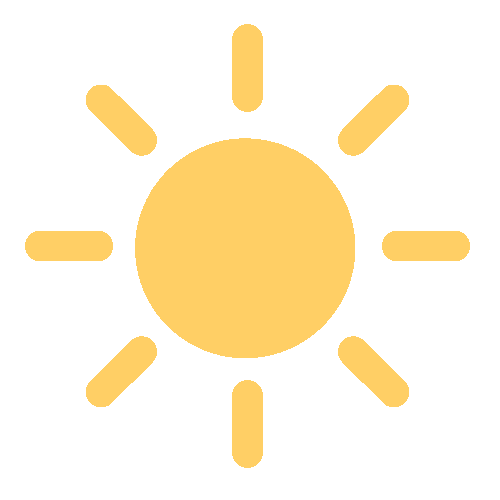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赫•涅托【西班牙】:闭门的家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突然看见撕裂我们的光。凝望那束击溃我们的光,从此刻直到生命尽头。像是猛然在早餐桌上看见从未出现过的食物,散发着余温,纯真,骇人,然后确认一切曾经熟悉的东西再也不会回来了。
赫玛·涅托作 彭梓洲译
沉默占据一个家,就很难再让它离开了;
越是重要的事情,就越不想让别人发现它(……)
我们看不见鬼魂,是因为鬼魂在我们体内。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阿利克西,或徒劳的搏斗》

“雨下得可真大。”
其实,不管下不下雨,要做的事情都一样简单:决定一下大人要不要开车送他上学就行了。不需要深思熟虑,做出决定就好。他把雨衣套在校服外面穿好,和妈妈一起站在大门口,望着外面的滂沱大雨。等爸爸把车开来,他就小跑过去,这样不会把身上弄得太湿。他在后排坐下,大雨一点一点溶解外面的城市。放学回到家,再把头斜靠在窗边,看着夜幕一点一点笼罩外面的城市。“雨下得可真大”——听到这句话,他才意识到雨下得真的很大,毕竟,自世界诞生之初,万物得到命名之后才真正存在。
家里的阳台还是老样子,站在街上一眼就能看见。他家在一栋刚翻新过的老楼的四层,位于一个临海街区,层高挑得很高,外墙雅致,门厅宽敞,地板上铺了大理石砖,还有外国游客追捧的那种镶嵌式艺术。百叶窗用深色木头打就,铁制栏杆弯曲成漂亮的花草形状。这栋楼现在是一家旅游公司名下的房产,专为旅客提供短租服务。在公司的威逼利诱下,原先的邻居早已全部搬走,一个都没留下。
他站在人行道上,抬起头,用手在眼睛上搭了凉棚,透过树枝眺望着阳台。依然是那个阳台,外沿有石雕装饰。他感到肩头的重量又回来了,像一团雾气捉摸不定,又像一只推开回忆的手。世上所有的家都把根扎得很深很深,一直扎到黑暗的地底。虽然这些根系无人能见,却撑起了一切。就算房子一直空着,他也知道,自己的家从来不是无人居住的。
每次回到这座城市,哪怕只住一宿,他都会把这里租下来。倘若有人捷足先登,他就推迟或提前自己的计划,好在房子空出来的时候住进去。网上的差评让许多游客放弃续租这间房子:大家都说,屋里管道的异响比楼里其他任何一间房都更严重;室内常有来向不明的气流,阵阵微弱的哀求声和墙板的嘎吱声此起彼伏,简直令人无法安眠。种种原因使得许多方才安顿下来的租客决定立马搬去别处。迄今为止,最为骇人听闻的评论来自一位俄罗斯租客。天刚亮,她就尖叫着冲出房门,大喊:“墙里有死人!”而他只想在这个房子里过夜。对所谓的鬼魂,他的理解与众不同。他觉得鬼魂只是一种化身,现形出恐惧,愧疚,未曾说出口的话,欠而未偿的债,或是某段爱情故事。
他心里最大的鬼魂是自己的家。


那天下午,海风带着近乎不真实的力量吹进阳台,捎来五月的气息,期末考试将至,然后便是探索荒蛮之国的承诺。那些地方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在那个年纪,所有的孩子都以为自己总有一天会亲自踏上探索世界的旅途。那天,他像每个晴朗的午后一样坐在客厅外的阳台边上,高处的窗户是敞开的,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紧接着,一道红色闪电迎头劈下来。整个过程不到一秒。一个水球擦着他的头顶飞过,在百叶窗上炸裂开来。他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能在看到那颗飞弹逼近时举起双手保护自己。即便是此刻,身旁的墙面往下滴着水,身上的衬衫也全部湿透了,他依旧呆若木鸡,不敢探出头去看看究竟是哪个家伙干的好事。不过,他也不用这样做,父亲已经从客厅的暗处跑出来,气喘吁吁,嘴里说着脏字,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阳台边,整个身子倚在栏杆上,朝外面那个不动声色望着自己的人大骂起来:“臭哑巴!我认得你,我见过你,走着瞧吧,等我去跟你爸告状的时候你就有好果子吃了,臭不要脸的!”
刚才的事把他吓得不轻,仿佛擦过自己的脸炸开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颗从胸膛里掏出的新鲜心脏。但接下来,父亲悻悻地对他抛下一句话,吓了他一跳:“你要是敢跟那家伙玩到一块儿去,你也走着瞧!”
随后,父亲嘟囔着回到屋里,口中还喋喋不休地咀嚼着方才的愤怒。
他下决心探出身去看看。透过树枝的缝隙,他认出了那个兀自站在街边的男孩,那个扔水球的人。
显然,这就是肇事者,不可能是别人。面对男孩满含深意的绵长目光,自己始终不知该如何回应。对方家住一楼,年纪比自己大一些,满头金发,像抽条的麦穗,眼睛大大的。男孩不会说话,只能比手语,像个警觉的望员,平时总爱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朝路人做鬼脸。那个下午,男孩就那么杵在街上,朝自己露出稀稀落落的门牙,像是要跟他决斗,眼里闪过狡黠的光,仿佛在为刚才的准头沾沾自喜。男孩等待着,这种等待也是一种沉默,火花四溅、刻意为之的沉默。而自己无法做出任何回应,只能耷拉着胳膊,垂下眼帘。两人之间语言不通,又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交流的词语,该如何交流?交流些什么?他看不懂手语,潜意识里的狂风暴雨已经将自己判为输家。晚餐时间,一家人吃饭时例行的沉默里,没有人抬起头,而那暴风雨的雷声继续轰鸣。沉默仍旧啃咬着他,沉默那不安分的嘴吞噬了家具和门锁,却没能将自己内心深处的呐喊一并吞下。大火迫在眉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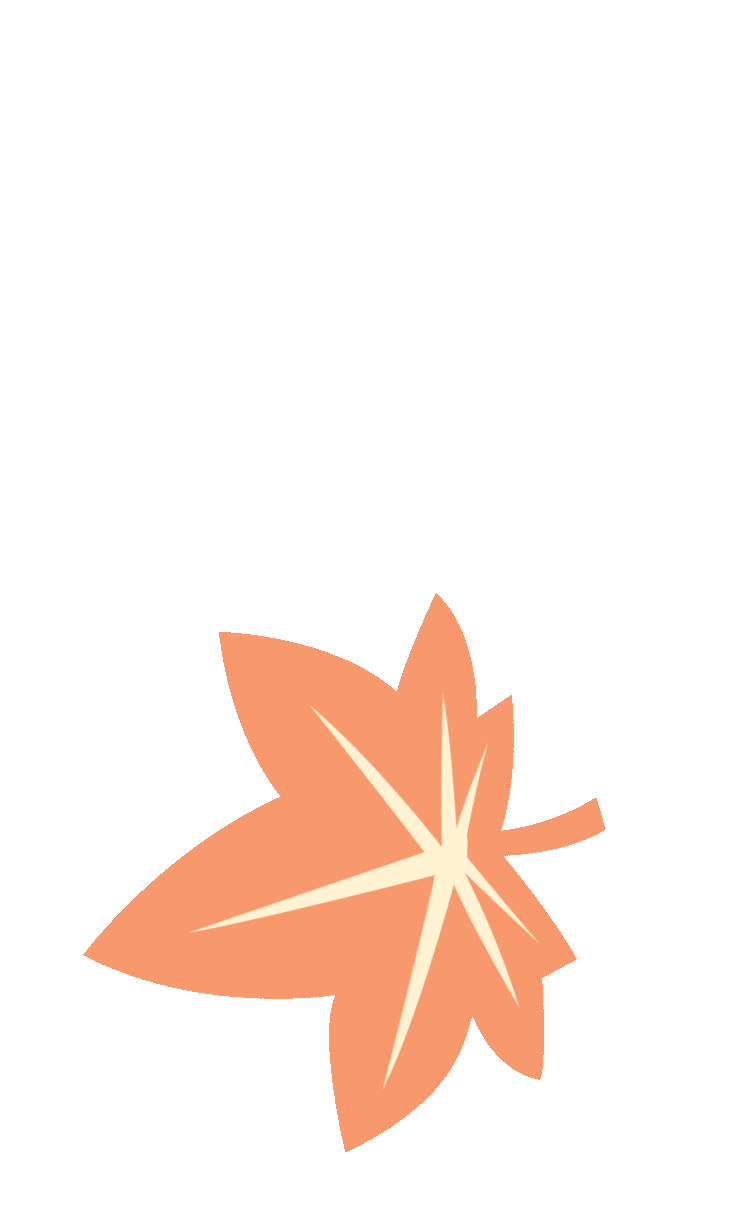

他慢慢地爬着楼梯。狭窄的中庭正在安装电梯,而这成了父亲不愿出门的又一个理由。历时四十五分钟,工人们终于把电梯修到了四楼。
门开了,大战一触即发。手指紧贴墙壁,空气变得凝重,家门摇摇欲坠。父亲看上去苍老了许多,像是被吓得不轻,眼神涣散,前言不接后语,仿佛在质问自己的手是否会成为永久锁闭那扇门的钥匙——门永远是那扇门,总有人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你别走,你妈妈去哪了?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还没到家?”或许,那种情况下,父亲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毁灭一切,要么被一切毁灭。而在死神的安排下,率先发生的似乎是后者。他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脆弱孩子,而父亲的性格也是如此。母亲离世后,父亲完全崩溃了,悲痛欲绝,显得格外孤独渺小,相形之下,他们的家变得更大了。父亲说他觉得家里的墙都在把自己往外推,要让他缩到走廊里。父亲走路时,头会不小心撞上客厅里的吊灯,有一次撞得太狠,甚至磕出了血。这种时候,父亲就会开始谩骂,说连家具都想让他滚得远远的。那段日子,父亲日复一日地重复一套规定动作,回答同样的问题,忍受屋外的噪音:一会儿,房产经理登门拜访;一会儿,游客挤满整栋建筑;一会儿,行李箱的轮子开始在走廊喧闹;一会儿,人们在楼梯间大声聊天;一会儿,忍无可忍的邻居开始怨声载道;一会儿,记者带着摄像机在门口大行其道。一部分年迈的邻居已经离世,另一些人则搬去了别的地方。有些人搬去和儿女同住,另一些住进了养老院。父亲只想死在家里。在自己家里善终是他一直以来的执念。日子一天天过下去,这个家垂垂老矣,父亲变成一个影子,披着悲伤的幕布四处游荡。父子二人早就不同住了,他偶尔回来看望父亲。他们之间依旧默契地保持那十年如一日的沉默和紧张,但父亲的境遇着实让他心生怜悯。他想,如果父亲不得不用生命的最后几年拒绝求购房屋的陌生人,这世界对父亲未免太过苛刻了。他想要表达一下关心,却做不到,舌头底下那颗儿时的种子早已深深扎根,生生刹住任何温情的话语。心里的野马意欲狂奔,拳头却握紧缰绳,死死勒在马儿胸口,逼得他不得不原地踏步。只要父亲还在世,他就永远是那个小孩,跟着父母学会了如何在沉默中潜泳。对他而言,家是记事簿,是牢房,记录着每一朵从沉默里开出的花,墙上刻满了他掰着手指数过的日子。家是废车处理厂,是堡垒,是避难所,是渐行渐远渐陌生的土地。但是,家也是他的摇篮,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过去和现在,是他无法彻底抹去的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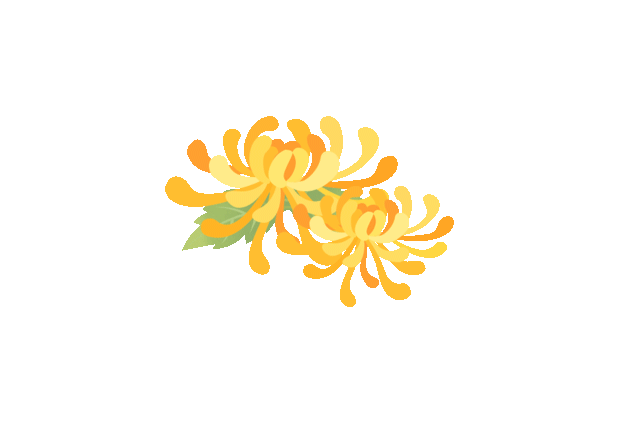
远方,远方,回忆之远,心中所有未解之结的生发地。少年时代,他在阴暗的家庭氛围里长大,低气压填满肺腑,任何形式的新鲜事物都进不去。他一丝不苟、温温吞吞地扮演服从者的角色,任凭时间的烟云将自己裹挟,日日呼吸充斥着固体颗粒的空气。同龄的孩子心里难免有各式各样的焦虑,他表面上不屑一顾,却暗暗妒羡。内心深处,他同样感到顽石般的焦虑,无从解释,也从未在他人身上见过。他无法对这与众不同的焦虑视而不见,它们与暴风雪扬起的烟尘并无二致,混沌不明。他恨极了从沉默深处长出的树状珊瑚,它们深深扎进自己的五脏六腑,高声挑衅着:“敢不敢把我们全拔出来丢出去?”——就像那个男孩丢出的红色水球,完美、精准地炸裂。沉默面前,他是一个胆小鬼;母亲面前,他又怎敢让对方望子成龙的幻想落空?未经命名的东西其实还不存在。因此,又一阵大雨开始落下时,他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雨是不是真的下得很大。或许,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一切保持原样。或许某一天,顽石会悄无声息地崩解,而他冷漠如旁观者的姿态能帮自己免于新的焦虑。
住在一楼的金发男孩把他拉到昏暗的信报间,在那里,他第一次懂得,原来湿润的亲吻也能融化心底的顽石。这个邻居家的男孩从小就是哑巴,面对自己嘲弄或好奇的目光,像电流贯穿的蝴蝶一样扇动双手。而同样“不会说话”的自己,在彼此加速的脉搏和纠缠的舌头里沉沦,那一瞬间习得了沉默中言说的能力。于是,他发现原来除了喉咙艰难发出的声音,还存在另一种语言。男孩突然慌里慌张地结束这个吻,在他的困惑中拿出一朵圣乔治节【圣乔治节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传统节日,据传与解救公主于恶龙的利爪之中的勇士乔治有关。每年的4月23日,加泰罗尼亚人都会庆祝这个节日】的彩纸玫瑰,轻轻放在他手心。这让他心跳加速,自那以后,当时心中翻涌的羞涩再难忘怀。时至今日,只要屏气凝神,他仍然能听到昏暗角落里的心跳。阳光触不到的信报间,包容了所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沉默的声波在那里盘旋,停留。时光流转,万事堆叠,当时的心跳始终鲜活如初。那是诞出人声的子宫,是世界生发的原点。
他始终不懂得如何解读对方的戏码。当时的年纪,每个人都不得不去回答“我们是谁”和“我们将要变成谁”这样的问题,男孩的举动显得那样动魄惊心。整个白天,他变成了猎手,捕捉着男孩双手中翻飞的蝴蝶。每时每刻,他都想看见对方,抚摸对方,他想重温那次邂逅。一听见阳台外面的自行车铃,他就期待着能在一楼门厅或大楼门口见到对方,小跑着下楼时,肌肉因迫切而绷紧。有时,他看见窗外树枝随风摇曳,以为是那个男孩,却只是刚学会飞的小鸟引发的骚动。他再也没见过那个男孩。对方随父母搬去了别的城市,他们甚至没来得及说声再见。他把那朵纸玫瑰珍藏在床头柜抽屉里。过了几周,盛夏时节,母亲去世了。夏天总是引人怀旧,阵阵热浪向百叶窗袭来,如同最初的欲望一般热切,打得他措手不及。阳光留下橘色的印痕,他一言不发,凝视着那些小小的光斑,心中没有任何期待,没有任何线索。胸口的石头一块块堆积成山……
“爸爸……”
他无数次想要跟父亲说些什么,或许正是想到了有一天他们会为此刻的沉默而懊悔。可是,话要说出口的刹那,总有一道屏障挡在前面,他生撕硬咬,却从来未能够冲得破。父亲看着他,或许心里也有同样的恐惧。客厅里,只有父子二人,两个绝对孤独的身影。玻璃柜里,盛有母亲骨灰的盒子在沉默中凝望着他们。
“没事。”


突然看见撕裂我们的光。凝望那束击溃我们的光,从此刻直到生命尽头。像是猛然在早餐桌上看见从未出现过的食物,散发着余温,纯真,骇人,然后确认一切曾经熟悉的东西再也不会回来了。
母亲去世后,家中仅有的活力和语言也随她而去。他站在客厅和玄关之间的阴影里,万念俱灰。母亲死后,连续好几天,他眼里只能看见爆炸中心的那个点。当时,母亲的身体就跌落在那里,冲击波的圆心。这场爆炸在家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挂画和电灯逐一掉落,玻璃全部炸裂。地板翻出内脏,家具碎成烟尘,墙上的窟窿里胡乱塞着瓦砾。只有沉默岿然不动,无人栖居的宇宙里空洞的永夜。沉默岿然不动。爆炸过后的沉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浓稠,更振聋发聩。父子二人也仿佛被炸飞到空中,落地后拾起自己残存的躯体,继续活下去。正是在那段时间,大批游客涌入这栋楼,在毗邻的房子里住上几天又离开。父子二人从未见经历过这等喧嚣吵闹,上门开价的中介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父亲回绝了一切访客,像一个在接连不断的冰雹里寻找容身之处的人。买下这个房子的时候,父亲还是个小伙子,在这里看着自己的家庭诞生、壮大,因而拒绝离开这个家,哪怕只是听说可能要出售,都会怒火中烧。父亲无法忍受陌生人占据自己曾经的居所。儿子偶尔会斗胆在聊天中提起这个话题,父亲则会为了与儿子对峙,打破自己的沉默。
“爸爸,他们给的钱很多……”
“门儿都没有!听到了吗?门儿都没有!陌生人来我家?来我们的家?他们屁都不懂!这可是你妈妈住过的地方,我们全家一起住过的地方!”父亲瘦弱的身体竟能在瞬间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声音越来越高涨,痉挛似的暴烈喘息着,“这个家,每个角落,发生过的每件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个家在跟我说话啊……”父亲抚摸着摆放骨灰盒的玻璃柜,态度似乎柔和下来。然而再度转向儿子的时候,眼神冷如寒冰:“你和他们是一路人!秃鹫!吃里扒外!”
父亲站起身来,脑袋又撞到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吊灯。那盏灯像一个不再挣扎的吊死鬼。
“爸爸,别闹了!”
父亲望着儿子,眼里半是蔑视,半是惋惜,随后继续沉湎于往昔回忆,想要以此掩饰失望,眼睛里透着厌倦,因为没能死在应当死的时候而倦怠不堪。
“你会遭报应的!等着吃苦头吧!”
而他也不再回应了,像一个悄悄打开牢门找寻同伴的囚犯,沉默地离开了家。年仅二十岁的他,最不想要的就是驮着巨石继续苦苦攀爬人生的金字塔。他想要一个从头开始的契机,抛却枷锁,卸下担子。他想把舌头底下长出的杂草连根拔起,杂草却如脚镣,紧紧把他钳住。那颗种子日日为唾液所浇灌,野蛮生长,结出果实。每个深夜,他吃下这果实,找寻着未曾得名之物,咬下去的时候甚至不认识它,却发誓下次再不吃了。如果父子二人的关系更加紧张,如果无法说服父亲接受那笔钱,搬进更好、更清静的房子,他发愿会自行离开这个家——这里,除了沉重的沉默,别无他物——找新朋友合租,谋个工作,开始另一种生活,让父亲变成电话另一端的人。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过几天吧,爸爸。”
他无意主动想起父亲,对方的形象却浮现在脑海里,难以克制。他想到父亲日复一日愈发颓靡地苟活,不知道是该在夜晚来临前留守家中等待日光褪去,还是该在天黑前出门,直到深夜再回到黑暗、寂静的家。
实际上,父亲选择哪种方案并不重要。无论如何,悲伤都会笼罩那个家,如同暗夜降临。



抗拒与逃避很容易携起手来共同作用。负罪感像一架精良的迫击炮。他反感回家,越来越不愿意去看望父亲,同时又觉得这样做似乎太过残忍自私。父亲一生都与家人同住,如今,鳏居的孤独和独子的逃离像是给他的舌头松了绑,他开始在儿子回家的时候不停回忆自己和妻子的恋爱往事,或者尝试向儿子解释这个家对于夫妻二人的重要意义:那时,他们年轻,充满希望,刚刚踏上生命之路,沿途挥洒着对未来的期许,像耀眼的光束穿透窗户,尚未遭到时间背叛。父亲反复说,当时夫妻二人都觉得崭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承诺突然兑现,他们发现了全新的海域。儿子却低下头,假装看了看手表,不是难过,也未见得有多厌倦(难过和厌倦只针对这个家),唯有一种生理性的抵触,外加不解。在儿子看来,父亲视若珍宝的家不过是墙壁、地板和天花板而已,这些东西对自己没有任何意义,也给不了他什么。父亲全部的回忆都浓缩在这个家里,儿子却只觉得,与其把这些回忆拥在怀中形影不离,不如让它们留在原处,安妥地长眠,最终缩小成一团线头,遗忘于沉默,永不复苏。这个家已经容纳不下儿子了。每次回来履行看望父亲的义务,他都尽可能缩短时间,看见父亲身体尚可,就放心地离开去往别处。在他眼里,生活总是在别处。
那个下午,他掏出钥匙打开门,喊了父亲一声却没人回应。走廊里反常的沉重气氛让人紧张,仿佛一切都结束了。越往屋里走,他的神经越发紧绷:还是没有听到任何动静。走到客厅的时候,他明白了,此刻的负罪感将伴随自己余生。父亲倒在地上,像是完成了生命仪式的全部步骤,抵达不可避免的终点。那个瞬间闪电一般击中了他。时间的终结从这一刻开始。他必须接过这片荒漠,这片虚无,以此为起点重新出发。


他在父亲的病床边坐下,看着对方干瘦的手疼得发抖,全世界的疲倦仿佛都汇集在这只手上。日复一日,他在煞白的病房里看着父亲的手,离开了那个闭门的家,或许父子二人都感受到无拘无束。他开始陪伴父亲,共享对方的沉默。中风后的父亲无法动弹,也说不好话,只能用短句和含混不清的发音表达自己唯一的念头:想要儿子带自己回家。他安抚着父亲,知道自己左右不了去意已决的父亲,结局已定,他能做的,只是让结局来得慢一些,等对方的精力恢复一点。父亲已经糊涂了,偶尔片刻的清醒,也只会在儿子给自己调整枕头位置或递上水杯时轻轻摆手,继续坚持要回家,要死在家里。他再有一万个不愿意,也无法对父亲的恳求充耳不闻。父亲回家的意愿如此强烈,几乎耗尽了最后一丝生气。有时他甚至觉得,如果不遂了父亲的心愿,对方的病情就会飞速恶化。有一天,父亲的语气已经从命令变成哀求,他踌躇不决,父亲的坚定动摇了他饱经磨难的疲倦内心。他望向父亲的眼睛,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的父亲。就这样,他为父亲办理了自愿出院手续,护工把父亲抬上担架,又花了快一个小时才顺利穿过狭窄的楼梯送进家门。而他的目光不经意间掠过当年的信报间,有一瞬间,沉湎于另一世的回忆之中。
那段日子,他和父亲说的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甚至偶尔能闲聊上几句,这样的转变让他惊讶。父子二人回忆着过去,第一次共同谈论起他们都无比熟悉的事情,也第一次心照不宣地理解了,有些事情虽然永远不说出口,却将永远留存在记忆里。父亲变成了一个面对世界无比惊奇的婴儿。不出几周,病情每况愈下,脑功能的退化比医生预想的更快。可是,谁又能武断地说像父亲这样成天等待妻子回家的男人毫无用处呢?现在,父亲的喜忧完全取决于那扇总关闭的门是否还可能打开。“儿子,你妈妈去哪了?为什么她还不回家?”或许,父亲心里的根深深扎在地里,尝试逃离终归是徒劳。或许,他就应该放任父亲想说什么说什么,就算觉得这些话无关紧要。共同的丧失是连结父子二人的根系,追光生长的花朵在他们的言谈间盛开。
他踏上缓慢的和解之路:与父亲,与这个家。背景里的杂音父子二人早已置若罔闻:关门声,拖行李箱的声音,大门口无时无刻的嘈杂人声,门铃声……不动产公司开出的价钱一次比一次高,到最后,拒绝这笔钱开始显得有些不合理了。继续坚守下去给他带来什么?他该如何照料父亲的身体?这样的生活还能持续多久?他看了看椅子上的父亲,对方一如往常,在等母亲回家。父亲问儿子几点了,因为脑袋里的时钟说妻子该到家了。他握着父亲的手,感受着自己手上的重量。他想叫一声“爸爸”。父亲的手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但是已经听不懂他说的话了。可是,哪怕不跟父亲说话,逃避风暴也是一种背叛。这个想法让他十分不安。失智与沉默慢慢淹没了父亲的意识。要怎么办?要在何时让步?“爸爸,你在家里呢,我陪着你呢。”他开始憎恶游客,也讨厌那些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不动产经理——那些人递来名片,假惺惺地劝他接受公司开出的条件,把老人送进疗养院或私人诊所,劝他“在那里令尊能得到更好的照料”。他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或许,父子二人会成为最后的抵抗者,他知道父亲永远不会放弃这个家。
走进房门,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吻墙壁。墙上的灰色涂料保存得很好,没有褪色。他轻轻敲了几下墙壁,儿时他就是这样和妈妈隔着房间交流的。他感觉自己回家了,这个家也认出了自己:墙体内传来一阵轻微的震颤,只有用指尖才能感受到,像是抚摸到总是等在这里的父亲老去的面庞。
他已经不在这座城市生活了。现在,他实现了年少时的心愿,果真到别处去生活了,这确实是他唯一知道的逃生路线。他和另一个人一起搬去了远离大海的内陆城市,打开窗户的时候不再有风拂过。他已经与过去和解,学会了为每段记忆命名,不再惧怕突如其来的回忆将自己绊住。回忆的藤蔓在他的心里攀缘,而他已经明白,尝试拨开,藤蔓只会越缠越紧,直到让人窒息。于是,每次回家乡出差,他都会去住自己曾经的家,按日付房租,伴着管道里的异动和地板的脆响入睡。这场景,以前谁能预想到呢?鬼魂总是这样出乎意料地回转现身,亡灵与生者总有奇异的和解之路。
父亲去世后,他把自己想了几个月的事付诸实践,将父亲的骨灰摆在玻璃橱柜里,挨着母亲的骨灰盒,让夫妻二人单独说了几天话。随后,他开始准备了,把茶几和书桌上散落的房产经纪人名片找出来,开始一点点清空家具。房间逐渐回归空无一物的原始状态,他终于看清了沉默的模样:它站在家中的角角落落,像一个从未离开的住客,越长越高。他把衣服和回忆一起叠好,收走自己的物品,丢弃杂物。他打了几通电话;买来珍珠灰色的涂料、滚筒和刷子;跪在地上,在房间空荡的回音里,用报纸铺满每一寸地板。他坚定地打开那两个小小的盒子,把父母的骨灰倒进涂料桶里,搅拌均匀。他沉默地做着一切,专心致志,不受任何外物干扰,直到完成整个仪式。对他而言,这是情理之中最为极致的致敬与告别。还有一件事要做:最重要的环节。
他的舌头上还负载着多年来未能说出的那句话,必须措词小心,像鸟妈妈一口一口给雏鸟喂虫子或谷粒;看似微不足道,却像鞋里的小石子,暗中决定了每一步。他把一颗微小的种子吐进涂料桶——像一个农夫从果实中挑出种子,播撒在田间,再看着它茁壮成长——这是他充满爱意的谢幕。对于过去已经发生和原本可能发生的那些事,他既无怨言,也无悔恨。他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将自己必须割舍的一个部分永远留在这个家里,去别处盛放,享受生活和爱情。终于,他说出了那句话,舌头自由了。
“妈妈,爸爸,我和一个男人结婚了。我很幸福。”
泛黄的墙壁现在涂上了珍珠灰,完全覆盖了他心中的种子生长过的那片土地。他知道,从今往后,自己终于可以无所畏惧地回望他的根系了。
刷完整个家的墙壁,他在售房协议上签了字,离开了家。
此去经年,屋里的家具换过几轮,装饰风格和从前大相径庭,格局也有所调整,不变的是他亲手选择的灰色涂料。他抚摸着墙壁,感受着最后一抹余晖中墙体的脉搏。他们就活在里面,在这个家里。
夜幕渐临,有什么东西从墙上走下来,比睡意更深沉,更引人入胜。终于,他平静下来,在父亲去世的房间躺下,感觉到整个家朝自己弯下了腰,像在欢迎一个初次来到这里的新生婴儿。他一点儿也不担心其他住客害怕的地方。他把后背紧贴着墙壁,让这个家拥住自己,让自己的呼吸与它同频。墙内的絮语哄他入睡,庇护着他。周围,窗外,余下的暗影缓缓垂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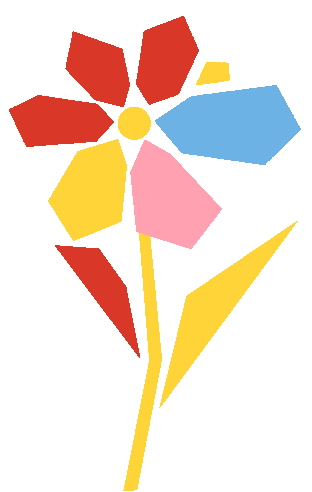
赫玛·涅托(Gema Nieto,1981—)是西班牙当代女作家、编辑,出生于马德里,已出版两部长篇小说,在各类文学期刊上发表多则短篇小说。《闭门的家》(Casa Cerrada)选自2019年出版的《冲击奥兹国:新时代酷儿短篇小说选》(Asalto a Oz Antología de relatos de la nueva narrativa queer,Dos Bigotes出版社),已获作家授权。小说标题中的casa一词在西班牙语中既指抽象意义上的“家”,也指其具象载体“房子”。对主人公而言,家(房子)是庇护,是栖居之所,也是牢笼,是不能说的秘密。闭门的状态隐喻了家庭成员之间情感沟通无能的困境,或许唯有爱能逾越这道沉默的鸿沟。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4年第6期,策划及责任编辑:汪天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