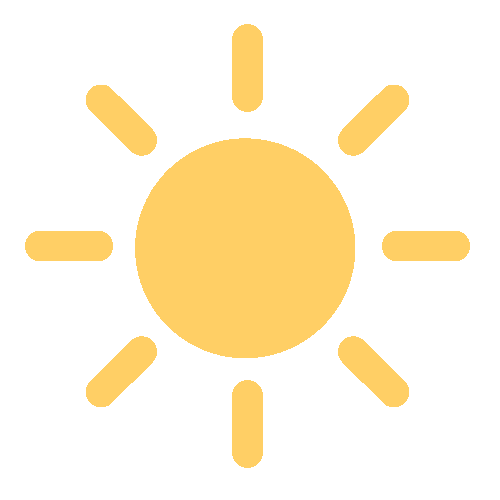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克•卡斯蒂永【法国】:黄色的百叶窗和绿意盎然的牧场总让她想起过去的幸福时光……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他的前妻(外三篇)
克莱尔·卡斯蒂永作 张可音译
他的前妻要带孩子们度假四周。他在西班牙海边为她租了一栋别墅,面积大到能邀请他们所有的旧友一起来住。之后她还要单独度假两周,期间我们来管孩子。她的前夫怕她看不到孩子们时会难过。他的前妻非常爱孩子,如果我们想把他们接来过圣诞节,她会威胁说要自杀。为了填补孩子们的缺席,他为她精心打造了梦幻般的行程:西南部的美食之旅以及三星级酒店的海水浴。她要求酒店等级再多一星。他觉得自己偷走了孩子,为了减少负罪感,总是先把前妻安排妥当。去年,他送她去了布拉格玩,但她回来时很生气,因为没能在房间里泡上澡。他想过段时间就给她在海边买所小房子,这样,星级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的前妻不喜欢自己那套小破房了——当年他们一起挑选的,离婚时留给了她。黄色的百叶窗和绿意盎然的牧场总让她想起过去的幸福时光。
他已经养成为了抚慰她的单身状态而宠溺她的习惯。他养着她,宁愿给她钱也不想逼她在这个年纪再去工作,尤其是怕她能找到的岗位可能配不上她的学历。他想假如有一天自己手头紧张了,我要是能去帮衬她最好不过。
他买了一套家庭影院,让她孤独的周末更丰富多彩。他把趁工作便利得到的影碟先送给她看。她一直没还我们,而是丢给孩子们了,他们把光盘折断,做成锋利的武器。她的前夫每周二晚上领走孩子时,会给她安排一个话剧之夜。为了不让她落单,他还给她的一个穷朋友付了一半的票钱。他每周三晚上把孩子们送回去时,会在她家吃晚饭,他们要时不时让孩子们知道爸爸妈妈不是敌人,这点很重要。此外,我从孩子们那里得知,在问好时,她的前夫亲的是她的嘴,可能是害怕从嘴变成脸蛋会惹怒她。离婚后,他尽量不让她为无足轻重的小事哭鼻子。他回家时身上会有抓痕,他说是猫干的,我信了。
他前妻的存在比过去更让人难以忍受。他们还在一起时,我是个快乐的小三,虽然这身份让人沮丧,但我内心深处十分满足。如今,当我看着她的前夫请求老天保佑,保佑他给前妻的惊喜不会让她不快时,我感到不解,从前那个和我在一起不到两个月就决定离婚的勇敢斗士现在去哪儿了呢。
最近,我有了一个报名参加健身俱乐部的主意。每天下班后,一起通过运动发泄一下感觉很爽。他们分开之前,她的前夫很喜欢锻炼。他抱怨她萎靡慵懒的毛病,说和我在一起,他至少不会躺平。我们经常去森林里跑步。有时,我们会借条船一直划到湖心岛,倚着树拉伸,感觉自己好像飘了起来,树叶都会从头发里长出来。运动让我们浑身轻盈。她的前夫绝不会错过任何一次慢跑训练。健身俱乐部?好啊!他立刻给前妻在体育中心报了名。她或许能在那儿找个男伴!
“是给我们报,不是给她报!”我向他解释道。
“我们?”他说,“你觉得我像是打算健身的人吗?”
他的前妻只要开启一项新的活动,就会劲头十足。一周一次的健身操课对她来说不够,她想要一张无限次卡。可一旦什么都有了,她又什么都不想做了。她不再去上课,开始长胖。她威胁说要恢复抽烟来减肥。他向她保证,等自己一有钱,就给她做腹部抽脂,激励她调整饮食。有些夜晚,当我想吻他时,当我试图在他前妻两次发疯似的来电——来电的原因是大儿子背不下来不规则动词变位,小女儿的臼齿松动了——之间重新营造一点私密的氛围时,他对我说:一想到有一天烟会侵噬她的肺,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的前妻做了隆鼻手术后,我们搬到了一个更小的公寓,孩子们来时我们得睡到客厅去。在他们面前,我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我说服自己只要多一点微笑和温柔,总有一天,孩子们会叫我名字的。他们一直对我没有任何称呼,但她的前夫说这样更好,他的前妻听到我的名字就痛苦,他们叫得越少,她就越想不起来。他们不直接跟我说话,让他们的爸爸当传话筒:让女佣给我们读个故事,叫丫头给我们做个蛋糕。有时,他们说完会挨揍。毕竟这样很过分。但之后,她的前夫又后悔虐待了他们,不停地道歉,如此激烈的痛悔之情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件坏事的帮凶。于是,我给他们做了苹果馅饼和草莓奶油布丁。他们不说谢谢,说:我们不喜欢你做的点心。
他的前妻把孩子们假期的最后两周留给了我们,彼时已经有季末之感了。我们带他们去露营。月底了,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去住酒店。这次露营差点毁了我们的夫妻关系。她的前夫有洁癖,厌恶这样的度假方式。还和她在一起时,他会悄悄带着我出去,我们去过一些很美的地方。那些回忆让现在的我想去当时没能涉足的地方。但他说,不去更能保护我们如今光天化日之下的爱情。
在营地,我们的炉边夜谈(在能够成功点燃一半柴火的前提下)无非是他如何为单身前妻焦虑,为孩子们就要长成青少年而松口气,并由此得出结论:坚决不再要孩子。
但是,每次他谈到买车时我都坚决赞同,还暗示一定要后排有四个座位的。我想象着我的两个娃坐在她的那两个中间,听多了我的孩子们叫妈妈,她的那两个或许也能对我说点好听的话。这样我们多多少少能成为一家人。
新车的事,她的前夫考虑了。他倾向于送辆车给前妻,然后让她不时借给我们用。他相信她会同意的。特别是等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她人很好,你知道的,他对我说。而且,她还有车位。我们现在还没孩子,有什么开车的必要呢?汽油那么贵。而且,他的前妻说——她曾经是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油价只会越来越高。

嫉妒
他总是笑,笑得有点太多了,好像脸上的皱纹里都能藏下另一个女人的齿痕。他晚上很晚回家,经常出差,周末还要开车出去做推销。他跟两个双胞胎儿子说,乖乖跟妈妈待在家里,儿子们听着,从十七岁的身高高度俯视着他。有天晚上,他犯了个错误,为了避开客厅里的我,他进到他们的房间里打电话。他以为孩子们不在家,其实他们只是很早就睡了。这种情况偶尔会出现,他们很能睡,但他们的父亲对此一无所知,毕竟他每天回家都很晚。两个双胞胎儿子已经初入梦乡,却听见爸爸鬼鬼祟祟地溜进来,在电话里小声说一些非常露骨的话。他们之后转述给我听了。孩子们听见爸爸解开裤子,立刻打开灯大叫:哦爸爸,别这样!
我跑进去,看他僵在那儿,一动不动,电话掉在了地毯上,双手高举,好像被人拿枪威胁着,可笑的阴茎绵软无力地垂在那儿。他向我发誓不是冲着孩子们来的。他重复好几遍自己是搞混了他们的房门和厕所的门,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向你们发誓!我向你们发誓!孩子们想替父亲开脱。他不是想乱伦,而且,两个儿子说,所有男人都会时不时给一个令人作呕的语音信箱致电,他们会从中得到慰藉。孩子们让我与时俱进,不要为一个很经典的喜剧场景上吊自杀。
起初,我看他总是神神秘秘的,还以为他在悄悄筹划我的五十岁生日会。他带着手机、笔记本和电脑出去散步,有时还拿上所有这些东西,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打电话。我刻意不去听,生怕听到了说话的内容。我甚至会调大音响的音量,把他的声音盖住。我不想提前知道一个惊喜活动的具体安排。
很快,我就大体知道了电话另一头那个女人的形象。显然,那不是色情语音信箱,而是一个情人。或许是特意想向我挑明真相,她在他们做爱时拨通我的电话。我本想抱着鸵鸟心态逃避这件事,毕竟木已成舟。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丈夫,我觉得他会站在我这边。但我不想当受害者。我甚至想经常听他们的做爱直播,好让自己在心里跟他做个了断。她搞到我的电话号码,悄悄背着他拨通,也可能是把他的眼睛蒙上了,好自由地拨号。他们享受着云雨之欢,当我丈夫喊她的名字时,我太过痛苦,挂断了电话。他对她说一些从未和我说过的话。过程中,有犬吠的声音闯进来。莉丝应该有一条狗。她常常故意把狗屎粘在我们车后座的地毯上。肯定是的,她有条狗。我丈夫不会那么叫唤!而且她留长发,我确信。见鬼!我是怎么知道的?她把扎发髻的簪子插在车座的头枕上,我一坐下,就会被戳到。还有她的香水,一丝甜腻的味道让我丈夫容光焕发,眼里尽是柔波,和十年前他看佩特拉时类似。她的年龄?可能和我差不多,这一点有些伤人。一个熟人先说她看起来年轻得多,又赶快改口:她笑的时候,只有在她笑的时候。她笑的时候看起来很年轻。但她经常笑。另一个朋友说,他只是逃离你们之间的问题去换换心情罢了,他会回到你身边的!你也出去找别人!
我们之间什么问题也没有!
他带她到我们共同的朋友家里吃饭。他这次带去一个,下次又换了一个。两个都不是我。我是恨意、冰冷和悲伤的代名词。
我想大叫,但是一叫喊就会掉头发。我不想哭,因为他的甜言蜜语让人害怕,他安慰人的能力更糟,我怕他会用她的名字叫我。莉丝故意在车门里放了一封他写给她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总结出大致内容:莉丝·当德兰——他贪婪而小心翼翼地渴望着的女人。他从哪里学来的这套话?她就住在我家附近。遇见她后,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要和我谈谈。这封信是八个月前写的,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然而,他什么都没说。我想他或许想继续这样下去,我尽可能让自己忘掉这封信,但脸色还是经常很难看。强留住一个想离开的男人,这么做不太明智。显然,周末他总待在家里会引发他和莉丝之间的争吵,他不在身边令她伤心懊恼,他自己也闷闷不乐。我后来随便找了个借口出去,他就去看她了,回来后仿佛得到了治愈:平静,面带微笑。估计他答应很快就跟我摊牌,她才高兴地放他走,对事情的进展感到满意。在家里,他看起来很幸福,并没有表现出马上要离开的样子。周末,他很享受我端上热乎乎的饭菜,两人边吃边看战争片。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感到年轻和轻松。他也喜欢周四晚上:自从我们结婚,周四就是我们二人世界的专属时刻。看电影,打扑克,或者去酒吧。他喜欢去他哥哥或者堂兄家度假。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我猜他有时会琢磨怎么把另一个女人也带过去。
或许他想等到双胞胎长大离家后再跟我摊牌。我可以跟孩子们谈,要求他们留在家里。他们会理解我的,但我不能那么做。哀求他留下来?绝不!如果是我外面有了人要离开,他求我才值得。我也不会跟他提莉丝,我只会说分手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决定。我会迅速离开,避免看见他眼睛里的如释重负,以及紧随其后的担忧。是的。因为我走后,他的好日子只会延续三天。他会告诉她说,他终于迈出了那一步,挺起了胸膛,但她会纠缠着要和他生小孩,强迫他戴隐形眼镜、停止穿三角裤衩、散步、跳舞,每当这样的时刻来临时,他就会想到我,我会成为他失去的女人,他今后永远梦寐以求的女人。
现在是凌晨两点,我刚刚迈进生命的五十岁,他还没回来。

让步
罗多尔夫随时有可能离开我。当年,他是选择了我——但那时参加滑冰比赛的一共有十八人。贝蒂滑得最好!他在表示我不是最漂亮的那个之前先铺垫了一下。他说,论脸,他喜欢瓷娃娃一般的狄安娜;论身材,安德蕾娅更胜一筹,但她的脸蛋儿不讨人喜欢,自来卷给人一种营养不良的感觉。上周她已入土为安,在棺材里裹着上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长毛大衣,像一把扫帚。罗多尔夫是我的人生挚爱,如果他离开我,我就绝食,在十天内死去。
我爱他,尊重他的喜好,但我也知道这些喜好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前段时间,我终于问明白了他不喜欢我的地方。他的回答是:你的香水。真让人生气,我已经喷了十七年慕尼丽丝香水。我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难闻的?六十多年前吧,他说。然后,我想知道:相反地,我身上什么地方讨他喜欢。通过排除法,他最终选择了我的耳朵。于是,我就用塑料皮筋把头发扎起来,但他把皮筋拽了下来。他不喜欢鼠尾辫。可要想扎成马尾辫,他还需要耐心等待。我的发型师很笃定:我这个年龄已经留不了那么长的头发了。但我还是想再试试看。但她说的也对,中短发洗起来更方便。
“但这是你的头发,贝蒂!你要坚持自己的选择。”罗多尔夫对我说。
我永远不会向他承认我听从了发型师的意见。他可能会鄙视我。
一起出门时,我走在身边给他带来了压迫感。我让开一些,给他更多呼吸的空间。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两个人插到我们当中。和罗多尔夫这样的男人在一起,要懂得让步。尽管很嫉妒,我还是让他决定邀请谁加入我们的游戏桌:他提议阿尔芭、莫琳、艾米莉、康斯坦丝、法黛特和莫里塞特。我看着她们拿纸牌的手,暗想,她们的手指比我的好看。
我总在让步,罗多尔夫逐渐掌控了一切,我们的住处、朋友、休闲活动和家具都由他来选定。回想往昔,我从欣赏他的爱好到一步步失去了自己的爱好。我任由他追逐艳遇,但是我的陪伴对他来说也很重要,他经常回来请求我做出让步,和他一起出去吃动物肠子,或者去看斗牛。久而久之,看斗牛从让步变成了习惯。我退一步睁开眼睛,我的眼睛再让一步翻着大白眼看。我退一步竖起耳朵,我的耳朵又让一步自己关上了。我不再听得见公牛的喘息,也听不到他们的铁蹄声,我几乎听不到人浪的欢呼,甚至会想那是不是汽笛声。
昨天,我又一次做出了让步。罗多尔夫想和我一起看电影,在床上而不是在沙发上。紧接着,他说我应该理解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仍有欲望,哪怕是对他的老女人。我同意他以鸡奸的方式进入我,尽管这是我们的神圣之书圣经所禁止的。结果现在,我遭大罪了!但是我得让步,特别是在狄安娜刚搬进我们养老院这个节骨眼儿上。她丈夫死了,她现在就住楼上,如果我不在罗多尔夫上我的时候叫出声,她一定会来把他抢走,她做梦都在想这个,肯定的!她还生着一张孩童般的脸。我这一生都在提防她,从来不转告罗多尔夫她的邀请。整整七十三年我都在提防她,这该死的瓷娃娃狄安娜。最近这段时间,她把头发编成一个辫子,还在上面系了条老旧的蓝丝带。“这是土耳其蓝,”她说,“孩子,你到饰品店里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我又做出了让步,拉直嗓门连声叫好。萨冯女士——我同层的邻居——不愿意和我说话了。她说我堕落了,但我退一步把这当成恭维话。至少,狄安娜会以为我们的生活无比美满。
我八十八岁了,开始冒着下地狱的风险接受非天主教徒的生活方式。我不再睡觉,不再吃饭,护士长女士以为我有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我认为自己可能有些“土耳其蓝”式的忧郁。这辈子,我因为让步而没能成为母亲,担心罗多尔夫会不喜欢我扮演那个角色。我嫉妒狄安娜的小肚子。此刻,我开始了自己的精神性妊娠。
指责
“我要吃蜜桃味冰淇淋和圣多诺黑【一种经典法式甜品,由鲜奶油、卡仕达酱和焦糖泡芙球等组合而成】蛋糕,列日巧克力杯和瓦什汗奶酪。我要毫不犹豫地享乐。”
当我问妻子,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两小时会干什么时,她如此回答。紧接着,她借机说出挂在嘴边的指责:无聊。世界末日?这对我没太大影响。你一回家,世界末日就到了。不是你借给我点助眠药,就能让我少伤点神的,而且我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会对这种书感兴趣。无聊透顶。
我总感觉很孤独,她接着说,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你人虽然在,但和你不在也没什么两样。如果没有晚餐时不看电视的仪式——我坚持用这一仪式来拯救我们的夫妻关系——可能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在过日子。哦!我已经习惯了,不抱怨了。但是世界末日不末日的,无关紧要。
一旦我想和妻子聊聊天,她马上就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政治?都是相互残杀!体育?一群蠢蛋!电影?看看都是什么玩意儿!外国菜难以下咽。执政的女人都是婊子。非洲的饥荒?骗谁呢。如果和她说起我工作中的烦恼,她就这么回应:你是回家了还是在办公室呢?如果心还在办公室,就赶快回去吧!
一个话题还没开始,她就给堵死了。
唯一能聊的话题——以不打断她的话为前提——是去渍妙招。用冰块除掉残留的口香糖,用橡皮擦掉麂皮绒上的墨水,用汽水去除红酒污渍。她从来都问不倒,这一话题可以无限延伸。绝对不能提我们那三个忘恩负义的孩子。我们有三个正常的小孩,他们都很善良,都在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我不会指责他们很少来看我们,因为我理解。然而真实情况是:我们生了一群白眼狼,她朋友的孩子要成功得多。
当这些她称为“自私鬼”的孩子来看我们时,她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因为忍受不了我们之间那些令她插不进嘴的谈话。孩子们聊天时,她把我看成自己人,问我他们在聊什么鬼。等我一加入他们,她就溜回自己的角落里。客厅里气氛凝重。我们开始反省自己是哪里做错了。最勇敢的一个孩子跟上去,想拉她回来,却被斥责为什么不让她自己待着。他硬把她拽了过来。妻子的眼圈红了,看着自己做的蛋糕,泪水在眼底打转,但刚才明明大家都吃了。我们只要没把她做的菜吃完,就是在朝她吐痰。
孩子们走了,她又把自己关在屋里,因为我的过错。我猜她是在想:如果是和别的男人一起做的蛋糕,孩子们会吃得更多。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自豪,把它当奖章一样挂在胸前——我是个英雄,从来没有背叛过妻子。
不过,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了(虽然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在妻子大吃大喝时,我会选择去泡澡。我把头埋在水下,让水灌满双肺。我先经历世界末日,独自来到天堂,一边享受着伊甸园的快乐,一边等着妻子来与我会合。她来后,一定会哭着抱怨园子里的花和果实,因为果实会让她想起孩子们,而花朵,会让她想起我们的婚姻或者坟墓。



END
作者简介
Castillon,1975—),法国作家、演员,已出版《阁楼》《跟您说说她》《他们》等长篇小说12部,《气泡》《昆虫》等短篇小说集8部,3次获颁文学奖,2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昆虫》一书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couplets)是由贝尔纳·格拉塞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一部短篇集,共收入女作家36篇小小说,大多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感受,揭示了亲密关系中种种矛盾复杂的情感。我们从中选出了《他的前妻》《嫉妒》《让步》《指责》等8篇介绍给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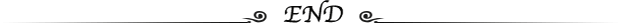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