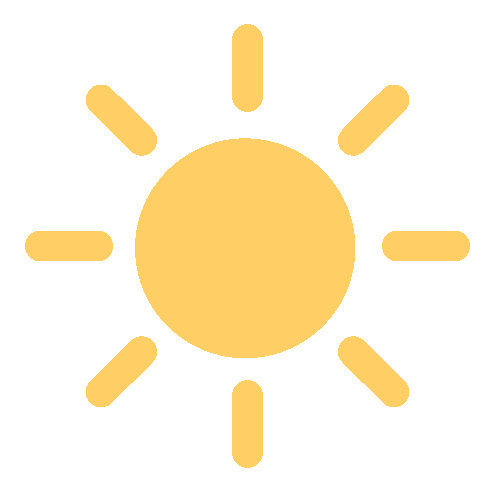散文品读 | 瓦•惠特曼【美国】:哦溪流,以你的语言,继续絮语下去……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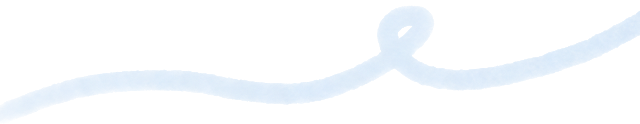
瓦尔特·惠特曼作 马永波译
于是,继续闲逛,来到柳树下的清泉旁——水声柔和,如丁冬作响的杯子,注入一条相当大的溪流,宽如我的脖颈,纯净而清澈,在它的缺口处,溪岸拱起,如一条硕大蓬乱的棕色眼眉,或者是嘴唇状的屋顶——永不止息地潺潺着,潺潺着——似有深意,说着什么(要是你能破译,该多好)——它总是在那里汩汩而流,一年四季毫不停歇,永远消耗不尽的是薄荷的海洋,夏天的黑莓——光与影的选择——刚好是我七月洗澡、做日光浴的好地方,炎热的午后,当我坐在那里,吸引我的主要还是那无可比拟的柔和的汩汩声。这一切是怎么生长进我的内部的,日复一日,一切都和谐一致——那野性的、刚可分辨的芳香,斑驳的叶影,以及这个地方所产生的所有自然疗法的、基本道德的影响。
哦溪流,以你的语言,继续絮语下去!我也将表达在我的岁月和进展中所收集的东西,本土的,地下的,过去的——还有现在的你。把你的道路旋转、延伸——无论如何,我都会和你,待上一会儿。当我如此频繁地与你相盘桓,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你知道,你与我毫无关系(可是为什么这么肯定?谁能说明?)——但是我将向你学习,沉思着你——接受、复制、印刷那来自你的信息。
那么离开吧,去放松下来,松开神圣的弓弦,如此的紧绷,如此的长久。离开,离开窗帘,地毯,沙发,书本——离开“社会”——离开城市的房屋、街道、现代的改进和奢侈——离开,去到那原始的蜿蜒的、前面提到过的林中溪流,它那未经修剪的灌木和覆盖着草皮的岸畔——离开束缚之物,紧巴巴的靴子,纽扣,和全副铁铸的文明化的生活——离开周围的人工商店、机器、工作室、办公室、客厅——离开裁缝和时髦的服装——也许,暂且离开任何的服装,夏季的炎热在推进,在那些有水、有阴影的孤独之中。离开,你的灵魂,(让我把你单独选出,亲爱的读者,无拘无束地交谈,随意散漫,充满信任),至少一天一夜,返回我们所有人赤裸的生命之源——返回伟大、寂静、野性、接纳一切的母亲!哎呀!我们中有多少人是如此迟钝——有多少人漫游得太远,以至返回几乎已不可能。
而我的这些便条,是随来随记的,散乱无章,没有特意的选择。它们在日期上几乎没有连续性。时间跨度约有五六年之久。每一条都是用铅笔随便记录的,在户外,在当时当地。也许,印刷工会因此感到某种困扰,因为他们复制的大部分内容来自那些匆忙写下的最初的日记。
你可曾碰巧听见鸟群午夜的飞行,穿过头上的空气和黑暗,不可胜数的军队,改变着它们初夏或夏末的栖息地?那是不该忘记的事情。昨晚一个朋友十二点之后给我打电话,让我注意巨大鸟群向北迁徙的非比寻常的喧闹(今年这已经是很晚了)。在寂静、阴影和此刻美妙的气味中(那只属于夜晚的自然的芳香),我认为那是珍贵的音乐。你可以听见有特点的运动——一两次“巨翅的急促拍击”,但更经常的是一种柔和的沙沙声,久久延续着——有时非常近——伴随着持续的呼唤和吱喳,一些歌调。这声音从十二点持续到三点之后。有片刻,鸟的种类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来;我可以辨认出长刺歌雀、唐纳雀、威尔逊鸫、白冠麻雀,偶尔从高空传来凤头麦鸡的鸣叫。


五月——蜂拥的、歌唱的、交配的鸟儿的月份——大黄蜂的月份——开花的紫丁香的月份,也是我出生的月份。我匆忙写完这一段,就在日落之后来到外面,来到溪边。光线、香味、旋律——蓝鸟、草鸟和知更鸟,在各个方向——喧闹、回荡、自然的音乐会。那些低音,是附近一只啄木鸟在叩响它的树木,远处是雄鸡的响亮尖锐之声。然后是新鲜泥土的气味——色彩,远景中微妙的枯黄色和薄薄的蓝色。草的明亮的绿色因为最近两天的温润潮湿而略有加深。多美啊!太阳安静地攀上广阔清澈的天空,开始它白昼的旅程。多美啊!温暖的光线沐浴着一切,亲吻一般汹涌而来,我的脸颊几乎感到了灼热。
自从塘蛙开始聒噪,山茱萸绽放最初的白色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金色的蒲公英在无尽的挥霍中,点缀大地的各个角落。白色的樱桃花和梨花——野生的紫罗兰,以它们蓝色的眼睛仰望着,向我的双脚致敬,我徜徉在树林边缘——露出玫瑰红蓓蕾的苹果树——麦田清澈的祖母绿——裸麦的暗绿色——温暖的弹性渗透在空气中——矮杉树慷慨地装饰着棕色的小果——夏天完全苏醒了——黑鸟在集会,吵吵嚷嚷的一群聚集在某棵树上,当我坐在附近,它们使时辰和地点变得喧闹。
后来。——自然列队前进,像军队一样,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一切都为我做了许多,并且依然做着。但是最近两天陪伴我的是野蜂,大黄蜂,或者像孩子们所称呼的,“嗡嗡嗡”。当我散步,或者一瘸一拐地,从农舍走向溪边,我横越前面提到过的小路,路的两旁是旧铁轨形成的篱笆,带有许多的裂口、尖片、中断、孔洞等等,那些低吟的、毛茸茸的昆虫就选择这样的地方栖息。在这些铁轨的上下左右和中间,它们拥挤在一起,数量巨大,无法胜数,在空中冲刺和飞行。当我缓慢地一路行去,经常有一片黄蜂组成的移动的云彩伴随着我。在我清晨、日午或黄昏的漫游中,它们扮演着主角,往往以我从未想到的方式主宰着风景——它们充满了长长的小路,不是成百,而是上千。数量巨大、活泼而迅捷,时而美妙地冲刺,时而响亮地膨胀开来,始终在嗡鸣着,不时地被什么东西改变着,几乎像一声尖叫,它们前后疾飞,快速地闪动,彼此追逐,尽管它们是小家伙,却给我传递了一种新鲜而生动的力量感、美、活力和动感。它们是到了交配的季节了吗?这么巨大的数量、速度、渴望、展示,到底是什么含义?当我散步,我以为跟随我的是一个特殊的蜂群,但是略加观察,我发现那仅仅是一系列蜂群在快速地变换,一个接着一个。
写这则日记时,我是坐在一棵大的野樱桃树下的——暖热的白昼因时而飘过的云彩和清新的风而变得温和,那风既不太强也不太弱——我长久地、长久地坐在这里,包裹在这些蜜蜂单调而低沉的音乐中,它们成百上千只地掠过,平衡着,在我周围前后疾飞——大家伙穿着淡黄的夹克,闪耀鼓胀的硕大身躯,粗短的脑袋和薄纱般的翅膀——哼唱着它们永远丰富柔和的歌曲。(难道其中不存在作曲的暗示,这些嗡鸣不就该是那音乐的背景吗?某种黄蜂的交响乐?)这一切多么予人滋养,以我最需要的方式,把我催眠;户外,裸麦田,苹果园。最近两天的太阳、微风、温度和一切都毫无瑕疵;永远不会再有这样完美的两天了,我好好地享受了一番。我的健康有了一点儿好转,我的精神安宁平和。(不过,我一生中最悲哀的丧失和忧愁的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
又匆忙写一段,有一个完美的日子:中午之前,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包裹在大黄蜂的嗡鸣和鸟的音乐中。苹果树上和附近的一棵杉树上,有三四只褐背画眉鸟,每一只都在唱着它最好的歌,以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最好的方式唱着华彩段落。两个小时我放任自己,倾听着它们,懒散地沉浸在这场景中。我注意到,在一年中,几乎每种鸟都有一个特殊的时辰——有时仅仅是几天——那时它唱得最棒;现在就是这些褐背画眉鸟的时辰。同时,在小路上下,是冲刺着、嗡嗡着的大黄蜂。当我回家时,又有一大群黄蜂充当了我的随从,和以前一样随着我移动。
两三个星期后,当我写下这些,我正坐在一棵郁金香树下的溪流边,树有七十英尺高,浓密、清新、青翠,正当青春旺盛——美丽的东西——每根树枝、每片叶子都完美无瑕。从树顶到树根,都有大群的野蜂拥挤着在花朵里寻找甜蜜的汁液,它们响亮而稳定的嗡鸣形成了一片低音,为整个世界,为我的心情和时辰。关于此,我将以亨利·比尔斯注小书中的诗歌做结。
当我躺在远处的深草中
一只醉醺醺的黄蜂经过
被甜蜜的棕榈汁弄得神志恍惚。
它身体周围金色的腰带
几乎勒不住它鼓溜溜的肚子
被忍冬的果冻胀得满满。
玫瑰酒和甜豌豆的酒
用神圣的歌曲充满它的灵魂;
整个温暖的夜晚它都沉醉不已,
它毛茸茸的大腿沾湿了夜露。
它的游戏中充满了古怪
当世界穿过睡眠和阴影。
它常常用焦渴的唇
啜饮花杯里甜蜜的琼浆,
在光滑的花瓣上它会打滑,
或是在纠结的雄蕊上旅行,
还一头扎进滚动的花粉里,
沾了满身金黄爬了出来;
要不然,它沉重的脚会绊在
蓓蕾上,跌落在草丛中;
躺在那里,用低沉柔和的男低音
嘟囔着——这酒后爱伤感的可怜的蜂!


六月十日。现在是下午五点半,我在溪边写字,没有什么能胜过我周围宁静的光彩和清新。正午的时候下过一场大阵雨,伴有短暂的雷鸣和闪电;雨后,头上,那罕见得无法形容的天空(在本质上,不是细节或形式上)的清澈的蓝,翻卷的银色——毛边的云彩,纯净眩目的太阳。衬着天空,树上已经满是温柔的叶簇——液体的、尖利的、拖得长长的鸟的音符——烘托着一只好抱怨的北美猫鸟焦躁的咪咪声,还有两只翠鸟愉快的尖声啁啾。有半个小时我一直观察这两只翠鸟,它们和往常一样,依照惯例在溪流上空和溪中嬉戏;显然,那是一种最为活泼的欢闹。它们彼此追逐,盘旋着飞行,不时欢快地浸入水中,泼溅起如宝石般喷射的水花——然后猛地飞升而起,翅膀倾斜着,优美地飞行,有时飞得如此靠近我,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暗灰色的羽毛和奶白的脖颈。
日落的芳香——鹌鹑的歌声——隐居的画眉
六月十九日,下午四点到六点半。独自坐在溪边——孤独,但是景色足够明亮,足够生动——太阳闪耀着,相当清爽的风吹着(昨夜下了大阵雨),草和树显示出它们最美的模样,各种不同的绿色形成的阴暗、阴影、半阴影、水面斑驳的闪光,从隐蔽之处,传来附近一只鹌鹑六孔竖笛的音符,池塘里刚好可以听见的雨蛙的定音声——乌鸦在远处呱呱地叫着——一群小猪拱着我所坐橡树附近的柔软土地——有的靠近来嗅嗅我,然后匆匆溜走,咕哝着。还能听见那鹌鹑清晰的叫声——我写字时,叶影在纸上颤抖——天空高远,飘浮着白云,太阳西斜——许多沙燕来来去去,迅疾地飞行,它们的洞穴开在附近的泥灰土岸上——杉树和橡树的臭气,这么容易觉察,当黄昏靠近——芳香,色彩,附近成熟麦田的青铜色和金色——红花草田,蜜一般的气息——丰满的玉米,带着长长的沙沙响的叶子——大片大片茂盛的马铃薯,微暗的绿,到处点缀着白花——我头上古老、多瘤、庄严的橡树——混合着鹌鹑的双音节歌曲,穿过附近松林的飒飒风声。
当我起身准备返回,一阵美妙的收场白一样的歌声让我久久徘徊,(是隐居的画眉吗?)歌声来自沼泽那边灌木丛生的隐秘之地,懒散而忧虑,一遍遍重复着。和最后的夕辉中成打成打雀跃不已、飞着同心圆的燕子相比,这声音就像高空中车轮的闪耀。
白炽化的高热,但在这纯净的空气中变得完全可以忍受——白色和粉色的池花,带着巨大的心形叶片;小河透明的水面,堤岸上浓密的灌木,如画的山毛榉、阴影和草皮,一只鸟从隐蔽处发出尖利的叫声,打破了温暖、懒洋洋、几乎是奢侈的寂静;偶尔,有一只黄蜂、大胡蜂、蜜蜂或熊蜂飞来(它们在我手边和脸上盘旋,但没有惹恼我,我也没有惹恼它们,它们似乎检查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就离开了)——头上广袤的天空如此清澈,营营飞舞的小虫在那里缓慢旋转,画着庄严的螺旋和圆圈;就在池塘表面,两只深蓝灰色的大蜻蜓,舞着带花边的翅膀,盘旋着、冲刺着,偶尔非常静止地平衡着身体,翅膀却始终在颤抖着(它们不是在炫耀,让我高兴吧?)——池塘里生有剑形的菖蒲,水蛇——偶尔一只轻快的黑鸟,肩膀上带有小红点,倾斜着一掠而过,这时,某只塘鸭的嘎嘎声带来了孤独、温暖、光与影——(蟋蟀和蝈蝈在中午的炎热中默不作声,但我听见了最初的蝉鸣)——然后在一段距离之外,在小河对面,马踏着快速的步伐,拖曳着一台收割机穿过黑麦田,发出喀嚓声和呼呼的转动声——(我刚刚看见的那只黄色或浅棕色的鸟,如小母鸡大小,短颈长腿,扑啦啦笨拙地飞过麦田,投入林间,那是什么鸟呢?)——细微然而容易觉察的、辛辣的红花草的芳香,占据了上风;而对于我的视线和灵魂而言,超越一切、环绕一切的,是自由的天空,透明的蓝色——在西方天空中盘旋的,航海者称之为“青花鱼群”的大朵灰白色羊毛似的云彩——天空中银色的旋涡像摇动的发绺,蔓延着,扩散着——无声无形的巨大幻影——但那也许是最真实的现实和万物的缔造者——谁知道呢?
八月二十二日。蝗虫细弱单调的声音,或者螽斯的声音——我在夜里听见后者,而前者白天夜里都能听见。我认为早晨和傍晚鸟儿的颤音令人愉快;但是我发现,我也能同样快乐地倾听这些陌生的昆虫声。在两百英尺远的一棵树那边,当我写作时,我现在听见一只蝗虫近午时的声音——一阵长长的呼呼声,继续,十分响亮的声音,以独特的螺旋或者摇摆的圆圈渐渐升高,其力度和速度增加到一定程度,然后是一阵振翼声,悄悄地微弱下去。每一次用力都持续一两分钟。蝗虫的歌与风景非常相配——喷涌出来,富有含义,充满阳刚之气,就像上好的陈酒,并不甜蜜,却远比甜蜜要好。
但是螽斯——我要如何描述它刺激人的声音?有一只就在我敞开的卧室窗外的柳树上歌唱,有二十码远;两周以来每个清澈的夜晚,这歌声都抚慰我入眠。有天傍晚我骑马穿过一片树林,走了一百杆远,听见无数的螽斯——有片刻我感觉非常奇妙;但是我更喜欢我那个树上的邻居。让我再说说蝗虫的歌声,即使有些重复;一阵长长的、彩色的、颤抖的渐强音,像铜盘在不断旋转,发射出一波一波的音符,开始时是温和的敲打或拍子,速度和音调迅速增强,达到巨大的能量和意义,然后迅速而优雅地低落下去,停息。不是鸣鸟的曲调——远远不是;这普通的乐师可能没有考虑曲调,但对于更敏锐的耳朵,那肯定是有着它自己的和谐的;单调——在那嘈杂的嗡嗡声中却有着怎样的摇摆啊,一圈一圈,铙钹一样——或者像铜套环的旋转。

十月二十日。晴朗、凉爽的一天,干燥而多风的空气,充满了氧气。脱出那包裹我、让我心气平和的理智、寂静、美丽的奇迹——树木、水流、青草、阳光和初霜——今天我看得最多的是天空。它有着那种细致、透明的蓝色,秋天独有的色彩,仅有的或大或小的云彩都是白色的,在广阔的天穹上或静止,或做着精神的运动。早些日子(比如说七号到十一号)它一直保持着纯净但生动的蓝色。但是当中午靠近,色彩变淡,有两三个小时完全是灰色——然后有片刻变得更灰暗,直到日落——我透过长满大树的山丘缝隙观察着,令人目眩——火焰的投掷,和淡黄色、肝脏色和红色的绚丽展示,还有水面上巨大闪耀的银色斜光——透明的影子、箭矢、火花,以及超越了所有绘画的生动色彩。
这个秋天,我不知道是如何就拥有了一些美妙满足的时刻,对我来说,这似乎最应该归之于天空,我时时在想,我一生中当然每天都看见天空,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看它——难道我不应该说那是完美的幸福时刻吗?我曾经读到过,拜伦就在死前告诉一个朋友,他一生中只有过幸福的三小时。还有有关国王的铃的古老德国传说,说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当我出去,来到林边,那美丽的日落透过树林,我想起拜伦的话和铃的故事,我头脑中出现的念头是我正在拥有一个幸福的时刻。(尽管也许我没有记下我最好的时光;当它们降临时,我无法用写日记来打破它们的魅力。我仅仅是放纵我的心情,让它漂浮,用它安静的狂喜载着我漂浮。)
无论如何,何为幸福?此刻就是幸福的时刻吗,或者是类似的时刻?——如此无法感知——仅仅是呼吸,一种短暂的色泽?我不能肯定——所以,就让我假定自己是无辜的吧。你,清澈透明的,在你那蔚蓝的深处,是否为我这样的人预备了药物?(哦,我生理上的衰朽和精神上的麻烦已经持续了三年)现在,你没有细心地神奇地穿过无形的空气把它滴到我身上吗?
十月二十八日夜。天空异常透明——星星出来了,数不胜数——银河的大路,及其分叉,仅仅在非常晴朗的夜晚才能看见——木星,在西方出现,看上去就像一朵偶然的盛大的水花,有一颗小星为伴。
穿着白色的外套,
这贵族缓慢地走进空空的圆形竞技场,
手上抱着一个小孩,
像无云夜空上有木星相伴的月亮。
——印度古诗
十一月初。我们已经描述过的小路那端,通向一片多草的高坡上的田野,有二十亩,微微向南倾斜。我习惯在这里散步,观赏天空的景色和效果,在清晨和日落。今天,就在这片田野上,整个上午,我的灵魂都被头上清澈的蓝色拱门所镇静,扩展到难以描述的程度,没有云彩,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仅仅是天空和阳光。它们给人安慰的伙伴,秋叶,凉爽干燥的空气,微弱的芳香——乌鸦在远处呱呱地叫着——两只大雕在远处的高空优美缓慢地盘旋——偶尔有风的呢喃,有时非常温柔,然后又威胁地穿过树林——只见一群农夫在田野里装玉米秸,耐心的马在等待。
如此色彩与光线的游戏,不同的季节,每天不同的时辰——遥远地平线的线条,那里,色泽微弱的风景边缘消失在天空之中。当我沿着小路慢慢地一瘸一拐走向一天的终结,一轮无可比拟的落日,一枝一枝,发射着熔化的蓝宝石和金子,穿过长着长叶子的玉米的队列,在我和西方之间。另一天。郁金香和橡树丰富的暗绿色,沼泽柳树的灰色,悬铃木和黑胡桃的沉闷色调,杉树(雨后)的祖母绿和山毛榉的淡黄色。


十一月十四日。当我坐在溪边,散步后休息一下,来自太阳的一阵温暖的柔情沐浴着我。没有声音,只有一阵乌鸦的鸣叫,没有动静,只有它们黑色的影子从头上飞过,反射在下面池塘的镜子中。的确,今天风景的主要特征就是这些乌鸦,它们不停地鸣叫,远远近近,它们数量巨大,连续地从一地移向另一地,不时地以其不可胜数的数量几乎把天空遮暗。当我坐了片刻,在溪畔写下这个便条时,我看见远远的下面,它们黑色的、清晰的影子,飞越水的明镜,或单独,或成双,或连续的一长串。昨晚整夜我都听见附近树林中它们的巨大鸟巢中发出的喧闹。
二月十日。今天,一只鸟发出最初的吱喳,几乎是在歌唱。然后我注意到,阳光中,一对蜜蜂在敞开的窗边迅疾飞行。
二月十一日。在夕光柔和的玫瑰红和发灰的金色之中,这个美丽的傍晚,我听见正在苏醒的春天最初的嗡鸣和准备——非常微弱——是在土里、根须里,还是昆虫开始动弹,我不知道——但是那是可以听见的,当我靠着一根围栏(我在我乡村寓所的楼下待了一会儿),我远眺西方的地平线。我转向东方,当阴影加深,天狼星出现了,壮丽眩目。巨大的猎户星座,还有偏东北方向一点儿的大北斗七星,竖立着。
二月二十日。池塘边孤独而宜人的日落时分,用一棵手腕粗细的坚硬橡树锻炼我的手臂、胸肌、整个身体,树有十二英尺高——我又拔又推,激起了甜蜜的风。和树较量了一会儿之后,我能感觉到它年轻的树液和效力从大地里涌起,刺痛着,从头到脚穿过了我的全身,像补酒一样。然后为了再锻炼锻炼,换换花样,我开始练习发声;大声地慷慨激昂地朗诵一些片段,伤感、悲哀、愤怒,等等,取自常用的诗歌和戏剧——或者是鼓起肺叶,唱出我在南方听到黑人唱过的一些野调和叠句,或者是我在军队里听过的爱国歌曲。我激起了回声,我告诉你!当黄昏落下,在这些情感迸发的间歇中,一头猫头鹰在溪对面什么地方发出声响——突,哦,哦,哦,哦——柔和而略带沉思意味(我想象还含有一点讽刺),重复了四五遍。这声音既是对黑人歌曲的喝彩,也可能是对悲哀、愤怒、陈腐诗人风格的讽刺性评价。
在完全的静谧和孤独中,远离此地,置身森林之中,独自一人,或者像我所发现的,置身于荒凉的草原,或者群山的寂静中,你从来不能完全抛开环顾四周的本能(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信任地告诉我他们也这样),你想发现是否有什么人出现,从土里冒出来,或者从树后和岩石后,这是怎么回事?那是从野生动物继承下来的、徘徊不去的原始的警惕性,还是从人类野蛮远祖遗传而来?它根本不是紧张或恐惧。似乎有什么陌生的东西可能潜伏在那些灌木丛中,或是僻静的地方。不,可以非常肯定,一定存在着——某种有生命的看不见的存在。



二月二十二日。昨晚和今天都是雨蒙蒙的,云很重,直到下午三点左右,风突然转向,云彩像窗帘迅速地撤去,现出清澈的天空,和一架我所见过的最美、最壮观、最神奇的彩虹,完完整整,非常生动,两端落在大地之上,展开明亮而广阔的薄雾,紫罗兰色、黄色、枯绿色,在头上的各个方向,阳光从中透过——难以描绘的色彩和光,如此绚丽,如此柔和,此番景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仍在持续,整整一小时,它落在大地上的两端才完全消失。后面的天空完全铺展在半透明的蓝色中,上面有许多小块的白云和边线。日落填充着、主宰着审美和灵魂的感觉,豪华,温存,充溢。我在池塘边写完这则笔记,光线刚好能够让我透过黄昏的阴影,看见水的明镜中那西方的倒影,树的倒影。我不时听见一条梭子鱼扑哧一声跃出水面,在水上激起涟漪。
大门敞开
四月六日。真的可以觉察到春天了,或者是春天的迹象。我坐在明亮的阳光中,在溪边,溪水刚刚被风吹出涟漪。一切都是孤独的,早晨清新,随意。陪伴我的是两只翠鸟,它们航行、盘旋、冲刺、浸着水,有时任性地分开,然后又飞到一起。我听到它们的喉咙在不断地嘁嘁喳喳;有好一会儿,周围只有那种独特的声响。随着中午的靠近,其他鸟儿也兴奋起来。知更鸟尖利的音符,两部分组成的一个乐段,一种清晰悦耳的汩汩声,应和着其他我不能确定方位的鸟儿。池塘边,不耐烦的雨蛙不时地以低沉的呼噜声加入进来,是的,我刚好听见。温暖而强烈的风,咝咝的呢喃不时穿过树林。然后一片可怜的小小的死叶,长久地被冰冻住,从空中某处旋转而下,在空间和阳光中,狂野自由地喧闹着,然后猛冲向水面,水把它紧紧拥抱,不久就沉了下去,看不见了。灌木和树林仍是光秃的,但是山毛榉还挂着皱巴巴的黄叶,是上个季节的叶子大量留下了,杉树和松树往往还是绿的,杂草也显出即将丰满的证明。在美妙清澈的蓝色天穹上,光在游戏,来来去去,大片的白云在游弋,那么的安静。
五月二十一日。回到坎登。又开始了一个透明异常、星光璀璨的蓝黑色的夜,仿佛要显示,无论白昼有多么盛大和自负,总有些什么东西留下,留在夜晚里,比白昼长久。最罕见的、最美丽的、拖延很久的清澈的阴暗,从日落一直到晚上九点。我来到特拉华,反复穿越。金星像闪耀的银子喷涌在西方。新月又大又薄的苍白月芽,半小时高,倦怠地沉落在一片云彩的纹章斜条下面,然后又冒出来。大角星在头上右方。一阵微弱芳香的海的气息从南方飘来。黄昏,温和的凉爽,带有景色的所有特征,难以描述地令人安慰,予人滋补——这样的时辰总让人想起灵魂,无以言表。(哦,如果没有夜晚和星星,哪来精神的食粮?)广阔无垠的空气,天空朦胧的蓝色,似乎已足够神奇。
夜晚一边前进,一边更换着它的精神和衣装,变得更宽敞更威严。我几乎意识到一种确定的存在,附近无声的自然。巨大的水蛇星座伸展开它盘绕的身躯,几乎占了大半个天空。天鹅座展开翅膀,飞下银河。北方的皇冠,天鹰座、天琴座,全都就位。从整个天穹上放射出光点,与我默契一致,穿过清澈的暗蓝。所有平常的运动感,所有动物,似乎都被抛弃了,似乎都成了虚构;一种奇怪的力量,如同安静休息的埃及众神,取得了所有权,尽管依然难以觉察。更早的时候,我见过许多蝙蝠,在明亮的夕辉中平衡着,在这里和远处的河面上,它们黑色的形体急速移动着;但此刻它们都不见了。黄昏星和月亮已经消失。活力和安宁沉静地躺下,在流动的无所不在的阴影中。
八月二十六日。白昼一直很明亮,我的精神也是一样,一个突强音符。然后夜晚降临,显得异样,带有难以表达的沉思意味,还有它独有的温柔和适度的壮丽。金星徘徊在西方,带着迄今为止这个夏天还没有显示过的奢侈的绚烂。火星早早升起,愠怒的红月亮,两天之前就已经盈满了;木星在夜的子午线上,而长长的蜷曲倾斜的天蝎座,完完全全伸展在南方。火星现在步入了天穹的最高点;整个一个月我晚饭后出门去看它;有时午夜起床,再去看看它无以伦比的光亮。(我最近看见一个天文学家利用华盛顿的新望远镜搞清楚了,火星一定有一个卫星,或许是两个)苍白而遥远,但在天空中很近,土星位于它的前方。
硕大、安静的毛蕊花,随着夏天的推进,丝绒一般光滑柔软,带点浅绿的枯黄色,在田野里到处生长——是大地上最早的丛生植物,它们宽阔的叶子低垂,每棵有八片、十片或二十片叶子——在小路尽头,在二十亩休耕地上繁茂生长,尤其是在篱笆的两侧——起初靠近地面,但不久便迅速生长起来——叶子和我的手掌一样宽,更低处的叶子有手掌两倍长——在早晨中如此清新,沾满露水——茎杆现在有四五英尺,甚至七八英尺高了。我发现,农夫认为毛蕊花是卑微的没有价值的杂草,但是我却逐渐喜欢上了它。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训诫,包含有其余一切事物的暗示——最近我有时认为,这些坚硬的黄色杂草中集中了为我所准备的一切。当我清晨来到小路上,我在它们柔软的羊毛般的花、茎和阔叶前停步,它们闪耀着数不清的宝石。到现在,它们已经开了三个夏天了,它们和我一起静静地返回;在这样漫长的间歇,我在它们中间或站或坐,沉思着如此多的时辰和部分康复的情绪,沉思着我疯狂的或病态的精神,在这里尽其所能地靠近安宁。
一八七七年九月五日。上午十一点,我写下这些,在岸边一棵茂密橡树的遮蔽下,我在那里躲避一场突来的阵雨。整个早晨都细雨蒙蒙,但一小时前雨势缓和下来。我来这里是为了我前面提到过的我所喜欢的日常简单的锻炼——拉拉那棵年轻山核桃的树苗——摇晃和弯曲它坚硬又柔软的垂直树干——希望偶然能让我的老肌腱从其获得一些有弹性的纤维和清澈的树液。我站在草地上,做这些程度适当的健身的拔树运动,做做停停,将近一小时,吸入大量清新空气。在溪流边漫步,我有三四个喜欢的天然休息场所——除了我随身拖着的一把椅子,偶尔审慎地用一用之外。在其他我所选择的便利之处,除了刚刚提到的山核桃树,结实而柔软的山毛榉树枝或冬青树枝,只要是方便够到的地方,都是我锻炼手臂、胸肌、躯干肌肉的自然器械。我很快就能感觉到树液和力量上升,渗透我全身,就像遇热的水银一样。在阳光和阴影中,我小心地抓住树枝或较为纤细的树,和它们的纯洁、健壮进行较量——并且知道功效由此从它们身上传递给我。(或许是我们交换——对此,或许树木比我所想到的更有意识。)
但现在愉快地被禁锢在这里,在这棵大橡树下——雨在滴落,天空覆盖着铅云——什么都没有,只有池塘在一侧,另一侧是一片延伸的草地,点缀着奶白的野萝卜花——远处木头垛边有人挥动斧子发出的声音——在这沉闷的景色中(大多数伙计会这么说),为什么我独自一人如此幸福(几乎是幸福的)?为什么任何打扰,即便是我喜欢的人的打扰,也会败坏这种魅力?可我是孤独的吗?无疑,一个时刻降临了——也许它已经来到我面前——那时,一个人,通过他整个的存在和那明显的情感的部分,感觉到主观的他和客观的自然之间的一致性,谢林和费希特如此喜爱的一致性,正变得紧迫。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经常在这里认识到一种存在——在清晰的情绪里我肯定它的存在,化学、推理、审美都不能做出最基本的解释。过去的整整两个夏天,它一直在强化和滋养着我病弱的身体和灵魂,以前从来没有过。感谢这无形的医生,感谢你无声的良药,你的日与夜,你的水流和你的空气,堤岸,青草,树木,甚至杂草!


当我被雨隔在我的大橡树的荫蔽所下(完全干燥而舒适,尽管雨滴在到处格格乱响),我用铅笔把此刻的情绪记录在一首五行诗中,我现在给你看:
与自然悠闲地相处,
接受一切,自由自在,
净化提纯着眼前的时辰,
无论它是什么,无论你在哪里,
而过去,仅仅是遗忘。
你能领会吗,亲爱的读者?你有多喜欢?
五月六日,下午五点。这是光与影自动组成奇特效果的时刻,这效果足以让画家精神错乱——熔银的长长辐条水平穿过树林(现在树林正是最明亮最嫩绿的时节),每片叶子和每根有无穷叶簇的枝条都成了一个燃亮的奇迹,然后,这些光束都平卧在新鲜而成熟的无边无际的青草上,以任何其他时刻都完全陌生的方式,不仅给草地整体赋予了壮丽,也赋予每片草叶以壮丽。在一些特定的地点,我可以观赏到这些完美的效果。水面上泛起一道宽宽的水花,伴随着许多闪闪发光的涟漪,衬托着后面迅速加深的暗绿色朦胧透明的阴影,沿着岸边间歇地闪烁。这一切,当太阳沉落下去,伴随着抛掷在树木和草地上的巨大的水平火焰,形成越来越独特的效果,越来越壮丽,非人世所有,丰富而令人目眩。
七月三日至五日。晴朗,炎热,喜人的天气——一个美丽的夏天——生长出来的红花草和杂草现在基本被割掉了。熟悉的怡人芳香充满了谷仓和小路。当你沿途散步,你看见灰白色的田野微微染上了黄色,谷捆松弛地堆放着,缓慢移动的货车经过,农夫在田里和结实的男孩们在拣谷子,把它们装上车。玉米就要开始抽穗了。整个中南部各州,布满为大地这个伟大骑士准备的矛形战斗阵列,它们数不胜数,长长的、光亮的、暗绿色的羽饰弯曲着,飘荡着。我听见我的老相识,鹌鹑“汤姆”那快乐的音符;但是想听到三声夜鹰的歌唱却已经太迟了(尽管前天晚上我听见一只孤独逗留者的鸣叫)。我观察一只红头美洲鹫大范围地庄严飞行,它有时升高,有时低到能看见它身体上的线条,甚至它展开的羽根,鲜明地映衬着天空。最近一两次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鹰,在掌灯时分低低地飞行。


六月十五日。今天我注意到一只新的大鸟,身量几乎有一只成年母鸡那么大——一只傲慢、白身黑翼的鹰——我从它的喙和整体外观猜测是一只鹰——只有鹰才有那么清晰、响亮、十分有乐感的叫声,像铃声一样,以一定的间隔,它的鸣声一再地重复,从一棵死树高耸的树顶,悬垂在水面之上。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我在对面的岸上观察它。然后它俯冲下来,十分潇洒地掠向溪水,擦着水面——缓慢地上升,一个壮观的景象,然后翅膀宽宽地展开,稳定地飘飞,根本没有拍动翅膀,在池塘上面上上下下两三次,在我附近飞着圈子,可以清晰地看见它,好像是专门让我欣赏一般。有一次它非常靠近地从我头顶上飞过,我清楚地看见了它的弯嘴和严厉不安的眼睛。
单单在鸟鸣中就有多少音乐啊,无疑,它们是野性的、简单的、粗野的,却是如此甜蜜。它占了鸟类发音的五分之四。鸟的音乐种类多端,风格万变。现在,最近这半个小时,我一直坐在这里,某个有羽毛的伙计在灌木丛中一直在一遍遍重复着我称之为颤动的鸣叫。现在,一只知更鸟大小的鸟刚刚露面,全身都是桑葚红,在灌木中轻快地飞着——头、翅膀、身体是深红色的,不是特别鲜艳——就我所听到的,它的鸣叫不是歌。四点:我周围有一场真正的音乐会在进行——一打种类不同的鸟正在同心协力。偶尔会有阵雨落下,植物就全都显示出雨水生动的影响。当我记完这则笔记,坐在池塘边的一根原木上,远处传来更密集的啁啾和鸣啭,一个有羽毛的隐士在附近树林里有趣地唱着——音符不是太多,但却充满了音乐,几乎会引起人的共鸣——这歌声持续了很久,很久。
Whitman,1819—1892)生于美国长岛一个海滨小村庄,由于生活穷困,只读了五年小学。他当过信差,学过排字,后来当过乡村教师和编辑。这段生活经历使他广泛地接触人民,接触大自然,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大自然的挚爱与赞美、将自我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思想,贯穿了惠特曼的所有写作,在1882年出版的自传式笔记《典型的日子》(Specimen
Days)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8年第6期,责任编辑: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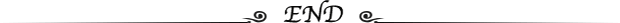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