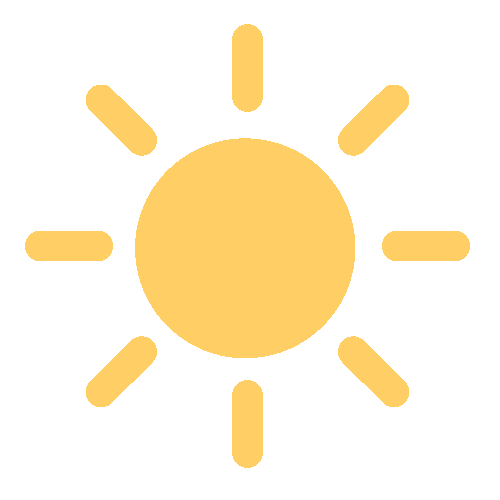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马•德•阿西斯【巴西】:衰人可真多啊!但愿我最后的心愿能够完成……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马查多·德·阿西斯作 闵雪飞译
自寻短见之人都有一个极好的习惯,先得把活不下去的原因和境遇讲出来,之后再结束生命。也有些人一言不发地死掉,不过却极少出于骄傲。大多不是因为没有时间,便是因为不会写字。这的确是个好习惯:第一,这很讲礼貌,人间不像舞会,不等最后一舞跳完,就能悄悄溜走;第二,遗言会在报纸上刊登、传播,这样,死者还能多活一到两天,有时甚至长达一个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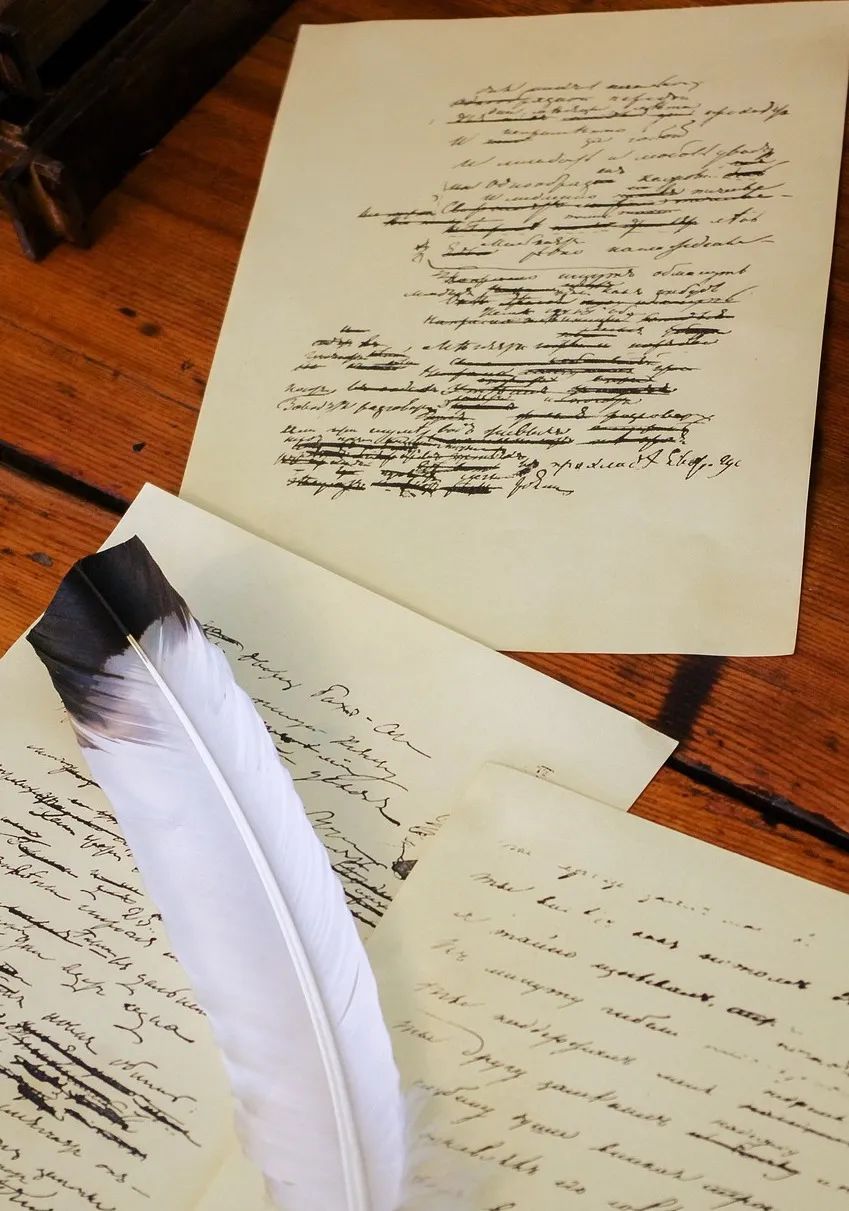
不过,尽管这是个好习惯,我却宁愿一言不发地离开。因为,我这一辈子都很衰,我害怕最终的遗言会妨害我的永生。然而,不久前发生了一件小事,令我改变了计划,我离开时不但留下了文字,而且还留下两份。第一份是我的遗嘱,我刚写完,封了口,就放在桌子上,挨着上膛的手枪。第二份就是我的这篇小传。注意,我写第二份,是为了给第一份做出说明,如果没有任何解释,它看起来就太荒诞不经、不可理喻了。在遗嘱中,我做出安排,变卖我不多的书籍、旧衣服,还有卡图比的那间租给一个木匠的陋屋,用这笔钱买新鞋新靴子,再以我指定的方式来分配,我承认这很不寻常。倘若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馈赠,就会令遗嘱面临失效的危险。馈赠的理由萌生于刚发生的事件中,而那正与我的一生息息相关。
我叫马蒂亚斯·德奥达托·德卡斯特罗-梅洛,父亲是军士长萨尔瓦多·德奥达托·德卡斯特罗-梅洛,母亲是堂娜·玛丽亚·达索莱达德·佩雷拉,他们都过世了。一八二○年三月三日,我出生在马托格罗索的科伦巴,所以,今天,一八七一年三月三日,我五十一岁了。
我再说一遍,我是个大衰人,比所有人都衰。有那么一个谚语,我可以说是把字面意思全做到了。那是在科伦巴,我当时七八岁,一次午睡时间,在一间空铺瓦【空铺瓦,热带国家特有的铺瓦方式,瓦片之间不用水泥接合,以保持通风良好】做顶的屋子里,我在吊床上悠荡着。或是因为吊床的钩子松了,或是因为我这边太使劲了,吊床突然从墙上脱落,把我甩到了地上。我是仰着摔的,虽说是面朝上,却摔坏了鼻子,因为有块瓦片早就松了,正想逮着个机会砸下来,趁着这番震动掉了下来。伤势倒不严重,好得也快,惹得父亲大肆嘲笑了我一番。下午,咏祷司铎【咏祷司铎,天主教会的一种荣誉神职,又称“法政牧师”】布里托找我们一起喝瓜拉纳茶【瓜拉纳是原产于巴西的一种植物,种子富含天然咖啡因,含量是世界已知植物中最高的,瓜拉纳茶被誉为巴西的国民饮料】时听说了这件事,便援引了那句谚语,面朝上,摔破鼻,这么荒诞的事儿,我是第一个真把它干出来的人。任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不过是个开头,未来还有很多事发生。
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讲述童年与青年的其他不幸上。我想在正午时分死去,而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而且,伺候我的男孩被我打发出去了,他可能会提前回来,打断我的死亡计划。倘若我有时间,会细说一下痛苦往事,有一次我被打了,因为被人认错了。是我一个朋友的敌人干的,情敌,当然是失意的那个。听说那个人如此不讲道义,我的朋友和他的爱人都为我挨打而愤愤不平,但私下里却为打错人而庆幸不已。我也不想说我遭遇过的病苦。就跳到我那位一生都很贫穷的父亲吧,他死的时候穷困潦倒,而我母亲没比他多活到两个月。布里托司铎当时刚当选议员,提出带我去里约热内卢,让我成为神父。我们一起去了,结果刚到那儿五天他就去世了。一衰起来就没完没了。
我才十六岁,孤零零的,没有朋友,也没有钱。皇家圣堂的一个教士出主意,让我进去当教堂司事,但是,尽管我在马托格罗索帮过很多次忙,我也会点拉丁文,但是因为没有空缺,我没被录用。另有一些人劝我学习法律,坦白说,我果断地接受了建议。开始时我还能得到点儿帮助,后来就断了,只能靠自己奋斗,最终我获得了学士学位。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一生衰命中的例外,因为正是法学文凭把我引向了更严重的不幸。但是,无论我从事什么职业,命运都一定会摧折我,所以,无论什么特殊影响,我都不会怪罪法律学位。获得学位时,我很开心,这是真的。我还年轻,对一切都会变好深信不疑,以为这张羊皮纸会变成钻石钥匙,可以打开所有的幸运之门。



然而,起初,我兜里可不只有这张学士文凭。不是的,先生,它旁边还有一些信件,十来封,那是一场爱恋的结果,一八四二年圣周期间,在里约热内卢,我爱上了一个寡妇,她比我大七八岁,但人很热情、欢快,而且有钱。她同一个瞎眼的兄弟一起住在伯爵大街。恕我不能透露其他信息。这场恋爱在我的朋友中人尽皆知,有两个人甚至读过情书,是我给他们看的,借口夸赞这位寡妇文笔优美,其实是想让人们看看她对我说的那些绵绵情话。大家都觉得我们结婚这事板上钉钉,再靠谱不过了。寡妇只是等着我完成学业。在我毕业时,其中一个朋友为我庆贺,以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来凸显他坚定的信念:
“你的婚姻可是天意啊!”
他笑着问我,为了这句“天意”,我能不能给他弄到五万雷斯【雷斯,巴西旧时货币单位,从殖民时期一直使用到1942年10月5日。这种货币通常以1000元纸币流通,久而久之,人们开始普遍使用“米尔雷斯”,意为“1000雷斯”,作为单一货币单位。本文为了避免混淆,通过换算仅使用“雷斯”这一单位】,他有急用。我身上没有五万雷斯,但是这句“天意”在我的心田中甜蜜地回响着,我整日奔走,给他搞到了钱。我激动极了,亲自送了过去,他满怀感激地接过了钱。六个月后,他迎娶了那位寡妇。
我不想尽吐我当时的痛苦,我只想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把这两个人都用枪毙了,其实在脑子里我已经这样干了,甚至看到他们垂死挣扎、气息奄奄地求我原谅。复仇发生在想象里,现实中我什么都没做。他们结婚了,去了蒂茹卡的山顶,看着那轮蜜月升起。我把那寡妇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其中一封这样说:“上帝一直在听我说话,知道我的爱是永恒的,我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昏昏沉沉中,我自言自语,亵渎神灵:上帝嫉妒成性,不想身边有别的永恒,因此揭破了这个寡妇。除了天主,再不能有其他的主,因此,戳穿了我的朋友。这样,我才能解释为什么我失去了爱人与五万雷斯。
我离开了首都【指巴西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到乡下当律师,不过时间不长。衰神一路跟着我,我骑驴,他在鞍子上,我下来,他也跟着下来。我发现凡事他都要插一脚,搞得我没有案子接,有案子也挣不着多少钱,或者根本挣不着钱,能挣到钱的,也都无一例外地全输掉了。且不说案子胜了的委托人一般会比输掉的更感恩戴德,我接连失败,委托人都对我避之不及。一段时间后,一年半左右吧,我返回首都,与一位老同学贡萨雷斯一起做事。




这个贡萨雷斯不是干司法的料,能力不足以应付法律问题。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废物。如果我们把智识生活比作一幢富丽的房子,那么在沙龙里,贡萨雷斯连十分钟都聊不下去,他会溜出去,下到储藏室里,找佣人们闲扯。但是,这个缺陷得到了弥补,因为他在某些方面很是精明,对于不十分复杂难缠的事情,他很快就能理解,他表达很从容,还有,他时时刻刻开开心心,对于我这个被命运鞭打的可怜蛋来说,这点可不寻常。起初没什么案子,为了消磨时间,我们谈天说地,东拉西扯,高谈阔论,他总能占上风,无论是聊政治,还是聊女人——对女人这个话题,他尤为感兴趣。
但是案子渐渐多了起来。其中一桩牵涉财产抵押问题。那是海关雇员特米斯托科莱斯·德萨·伯特略的房子,他再无其他财产,想把这处房产保住。我负责这个官司。特米斯托科莱斯对我很满意。两个星期后,我告诉他我还未婚,他笑了,说不想和单身汉打交道。他和我讲了别的事,邀请我周日一起吃晚饭。我去了,结果爱上了他的女儿,鲁菲娜,十九岁的少女,很漂亮,尽管有点不够大方,颇为死板。也许就是这样教养的,我想。几个月后,我们结了婚。我当然不会邀请衰神,然而,在教堂中,整齐的唇髯与光洁的颊须之间,我似乎看到我残忍的对手狰狞的脸庞与睥睨的眼神。正因如此,婚礼上,就在我说出那句神圣而终极的誓言时,我颤抖了,迟疑了,最终,我怀着恐惧,跟着神父结结巴巴念完了。
我结婚了。鲁菲娜确实不是那种闪闪发光、优雅动人的女人,比如说,她显然当不了沙龙女主人。然而,她宜家宜室,我也不指望其他。生活得平平淡淡就够了,只要她能满足这点,那就一切都好。然而,婚姻生活的苦处正在于此。请允许我用颜色来比喻,鲁菲娜的灵魂不是麦克白夫人的黑,也不似克娄巴特拉那般红,既非朱丽叶的蓝,也不像贝阿特丽彩那样白,她灰暗褪色,一如芸芸众生。她善良,因为她冷漠;她忠贞,但不是出于美德;她友好,然而既无温情又无爱意。天使可以迎她进天堂,魔鬼可以引她入地狱,两种情况她全不挣扎,前者不会为她增光添彩,后者亦不会令她名誉扫地。这是梦游者的被动消极。她没有虚荣心。她父亲安排了这桩婚事,为的是有一个律师女婿,而她不为这个。她接受我,就像接受神父、律师、将军、公务员、军官,并非因为着急嫁人,而是服从家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像别人一样。别人都有丈夫,她就也想有个丈夫。我的本性对此深恶痛绝,然而我结婚了。


幸运的是——啊!在一个衰人的终章里,这一声“幸运”确实反常,但是请继续读下去,你们会发现这声“幸运”是写作风格,并非生活本身,只是一种行文过渡的方式而已。我要说的不会改变已经说过的内容。我要说的是,鲁菲娜的宜家宜室令她拥有很多优点。她很朴素,不爱舞会,不爱散步,也不爱在窗前眺望。她独来独往。她不用为家里劳心劳力,也没有必要。我去工作,供给她一切,穿衣打扮都从“法国女人”那里定做,当时用这种说法代指找裁缝。发号施令的间隙里,鲁菲娜接连几个小时坐着,懒懒地豢养着灵魂,消磨着时间,那是一尾九头蛇,永远都不会死。然而,我再说一遍,尽管有这些缺陷,她依然是个好主妇。从我来说,我就好比是青蛙,想要一个国王,然而朱庇特送了我一根木头【指《伊索寓言》中青蛙求王的故事:青蛙请求众神之王朱庇特给它们派一个国王,朱庇特往水里扔了一根树干。青蛙不满意,觉得这个国王太迟钝了,要求朱庇特换一个更好的国王。朱庇特很不高兴,于是派了一条蛇下去,青蛙围了过来,而蛇吃掉了青蛙】,我不能再要求什么,不然会招来一条毒蛇,把我吃掉。木头万岁!我对自己说。要不是为了呈现我命途那不变的逻辑,我根本不爱讲这些事。
又得说一次“幸运的是”,不过这次不仅仅是行文过渡。一年半过去了,地平线上现出一线希望,如果从这则消息给我带来的震撼来看,那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希望。期待已久的终于到来了。我期待什么?一个孩子。我的生活立即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向我微笑,一如订婚那日。我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购置了一个奢华的摇篮,花了我很多钱,是用乌木和象牙做的,美轮美奂。之后,我一点点地购置小孩衣物,为他缝制最为精细的麻纱,最为温暖的法兰绒,一顶漂亮的蕾丝帽,我给他买了一辆小车,盼望着,盼望着,准备在他面前跳舞,就像大卫在约柜前面跳舞【《圣经》记载大卫运送约柜到耶路撒冷时为表崇敬和喜悦,在约柜前跳舞】……哎!衰神!约柜空着进入了耶路撒冷,孩子出生就死了。
安慰我走出不幸的正是贡萨雷斯,他本该成为孩子的教父,是我们的朋友、食客与信任的人。他有耐心等待,他告诉我:我会成为下一个孩子的教父。他以朋友的体贴安慰我,和我说别的事。时间会平定一切。后来,贡萨雷斯本人警告我,如果那孩子注定要成为衰人,就像我说的那样,还不如生下来就死了。
“你觉得他不是吗?”我反驳道。
贡萨雷斯笑了,他不相信我的衰理论。实际上,他没空相信任何东西,时间太少,都不够他快活的。毕竟,他开始转做律师,不是打官司,就是在写诉状,要不就是去参加听证会,一切都是生活逼的,他说。然而他总是很开心。我妻子觉得他很有意思,听他说话、讲笑话,总被逗得哈哈大笑,虽然笑话有些过火。我起初还会私下里说说他,后来我就习惯了。况且,他是朋友,还是个欢快的朋友,谁又不能原谅他的轻浮呢?我得承认,他自己克制住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竟然发现他正经了不少。你恋爱了吗?有一天我问他,他的脸一下子白了,回答说是的,然后他笑了,虽然有些勉强,接着说婚是一定要结的。我,在餐桌上,谈到了这个话题。
“鲁菲娜,你知道贡萨雷斯要结婚了吗?”
“他揶揄我呢。”贡萨雷斯激动地打断了我。
我暗骂了一声“轻率”,再也没提这个话题,他也没有。五个月之后……这个过渡很快,但是实在没办法延长。五个月之后,鲁菲娜生病了,病得很重,连八天都没捱过。她高烧不退,死掉了。


真奇怪:她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分歧造成了关系的疏离,主要靠需求和习惯来维持。死亡却以其巨大的灵魂之力改变了一切。鲁菲娜出现在我面前,仿佛从黎巴嫩下来的妻子【出自《旧约·雅歌》,新郎的歌词这样唱道:“我的新妇,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水乳交融代替了分歧。我抓住那个充满我心灵的形象,用它将生命填满,而在过去,生命只占据了极少的空间与时间。这是对凶星的挑战。这是在不可摧毁的磐石之上立起一幢命运之厦。请你们理解我,依靠外力的东西自然转瞬即逝:瓦片随着吊床的晃动而掉落,圣衣拒绝加于教堂司事之身,寡妇的誓约与朋友的“天意”一起飘走,案子踉踉跄跄地到来,泥牛入海一般离开。终于,孩子出生便夭亡。但是一个死去女人的形象是不朽的。有了她,我可以挑战邪恶命运的睥睨眼神。幸福紧紧握在我的手上,在空中扇动着兀鹰一般的巨大翅膀,而同时,衰神,恰如一只猫头鹰,拍打着它的翅膀,沉入黑暗与寂静。
然而,有一天,我刚发过高烧,突然想起要清点一下逝者的遗物。我从一个小盒子开始,自从她五个月前去世后,这个盒子就没有打开过。我发现了很多零零碎碎:针、线、饰带、顶针、剪刀,圣居普良祷词,衣服清单,其他小玩意儿,还有一沓信,用蓝丝带捆着。我解开丝带,打开了信:是贡萨雷斯写的……快十二点了!我得赶快写完,男仆随时会回来,所以,再见!你们无法想象这种情况下时间过得有多快。一分一秒飞驰而过,仿佛帝国兴替。最重要的是,此情此景中,纸张随着时间消逝。
我不想细数那些开不出的彩票,做不成的生意,半途而废的关系,我更不想纠结于命运其他的捉弄。我累了,也倦了,我明白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幸福。不仅于此,我相信幸福不存在于尘世,所以,从昨天我就做好了准备,要纵身一跃,进入永恒。今天,我吃过早饭,点起一根雪茄,探出了窗台。十分钟之后,我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经过,他总是盯着脚看。看一眼我就知道,这人遭遇过巨大的不幸,但是他边笑边走,凝视着自己的脚,确切地说,他在看自己的鞋。这双鞋很新,油光锃亮,剪裁得体,估计缝制也很精细。他抬眼看向窗户与人,但又一次向鞋子看去,仿佛由一种发自内心并高于意志的吸引力驱策。他开心地走着,脸上浮现出至喜的表情。显然,他很幸福,也许他并没有吃午饭,也许他口袋里连一分钱都没有。但是他很幸福,他在凝视他的皮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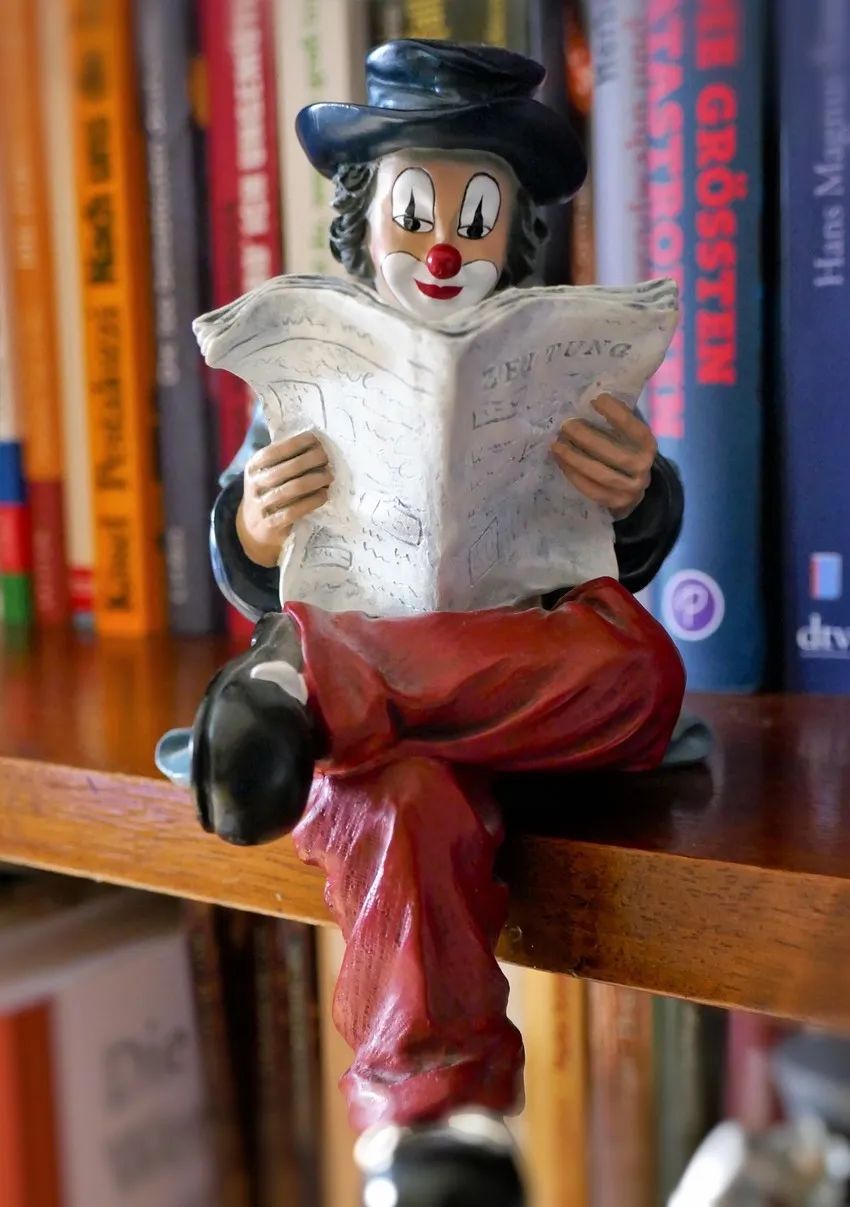
难道幸福就是一双皮靴?这个男人,生命如此多舛,终于发现命运的一丝笑意。一切都不值得。这个世纪的全部忧虑,任何社会或精神问题,新世代的欢乐,旧世代的悲伤,苦难或阶级战争,艺术和政治的危机,对他而言,都不如一双靴子。他凝视着它,呼吸着它,与它一起闪闪发光,他用它踩在属于他的星球的大地之上。因此,他昂首挺胸,步履坚定,神情如神一般平静……是的,幸福是一双靴子。
这就是我对遗嘱的解释。浅薄的人会觉得我疯了,寻短见的人神志不清,才拟了这条遗嘱。但我是在跟聪明人与命不好的人说话。我也不接纳反对意见,说什么与其送人不如自己穿了。不,这是唯一方案。我把靴子分发下去,会造就一大堆幸运儿。唉!衰人可真多啊!但愿我最后的心愿能够完成。晚安!记得穿鞋!



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1839—1908)出生于里约热内卢,是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曾任巴西文学院首任院长。他被誉为“巴西现代文学之父”,一生创作颇丰,出版有十部长篇小说,二百余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诗歌和戏剧作品,备受斯蒂芬·茨威格、苏珊·桑塔格、艾伦·金斯堡、菲利普·罗斯、卡洛斯·富恩特斯等重要作家的推崇。
马查多年少时便展露出惊人的文学天赋,16岁发表处女作长诗《她》,此后长期为多家报社撰稿。187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复活》,这是他浪漫主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1880年,马查多出版了《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这部作品标志着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此后,马查多的作品日臻成熟,创作焦点也从爱情转向人性与社会。如他本人所言,“我对自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人”。在亲历了巴西社会的动荡变革(包括1888年废除奴隶制和1889年共和国建立)之后,马查多的作品开始以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为主要背景,不仅从宏观层面展现了阶级矛盾、父权体系和奴隶制造成的社会撕裂、种族对立等问题,更通过对具体人物和细节的刻画,展现出当时巴西社会的普遍状态和面貌。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5期,责任编辑:汪天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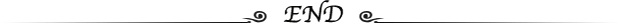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