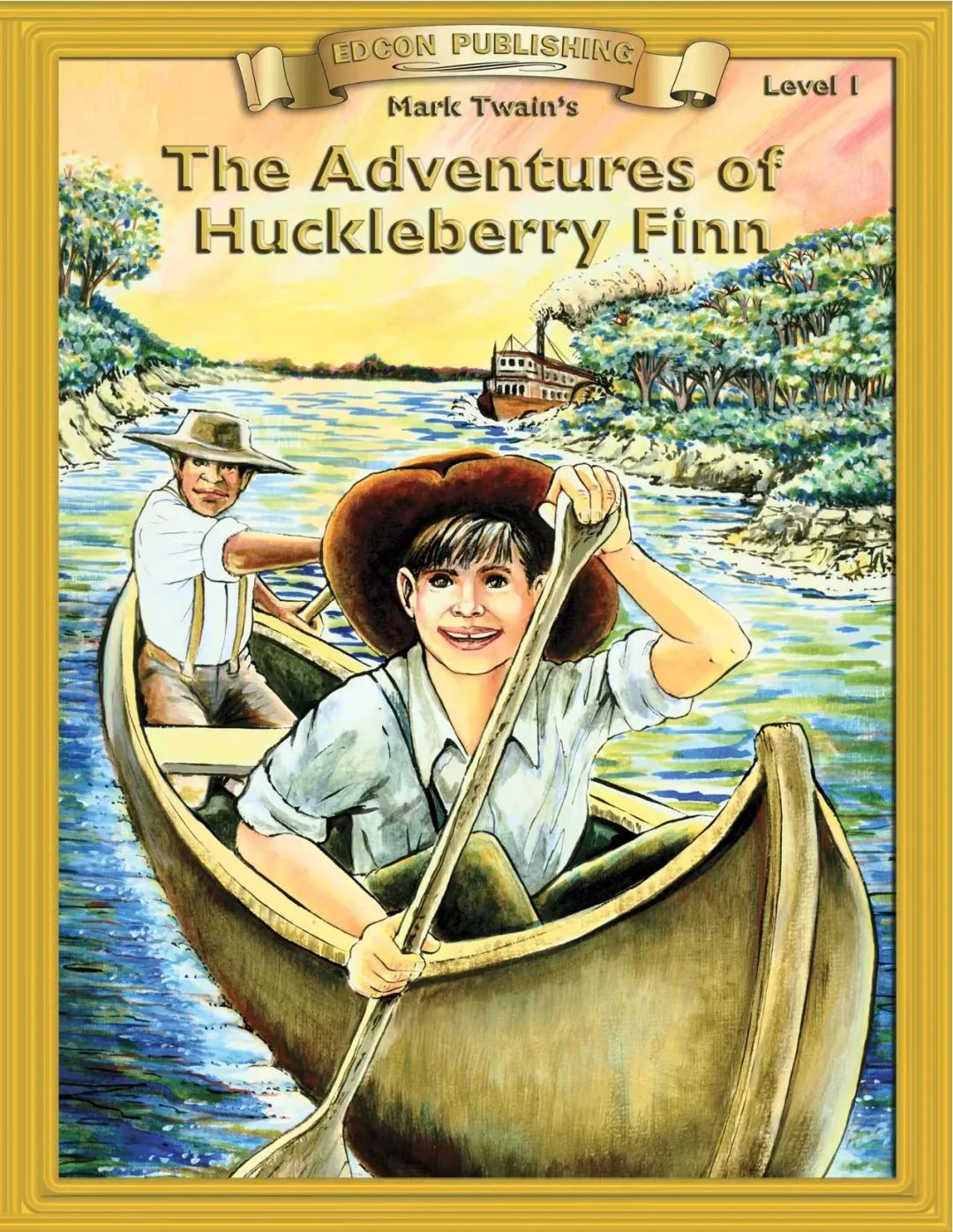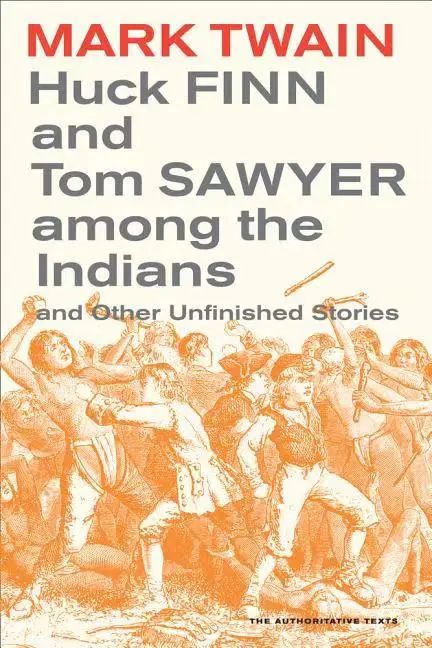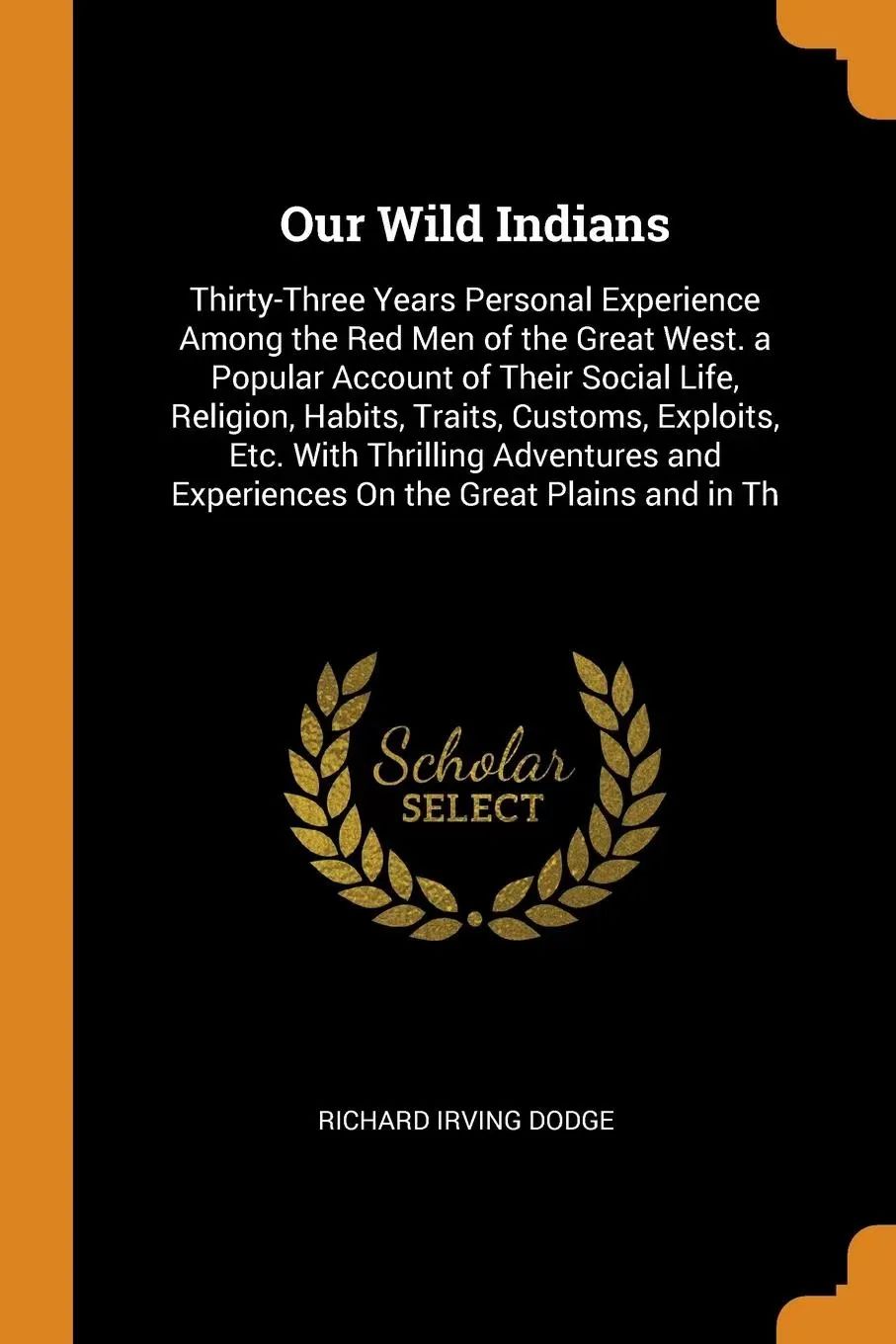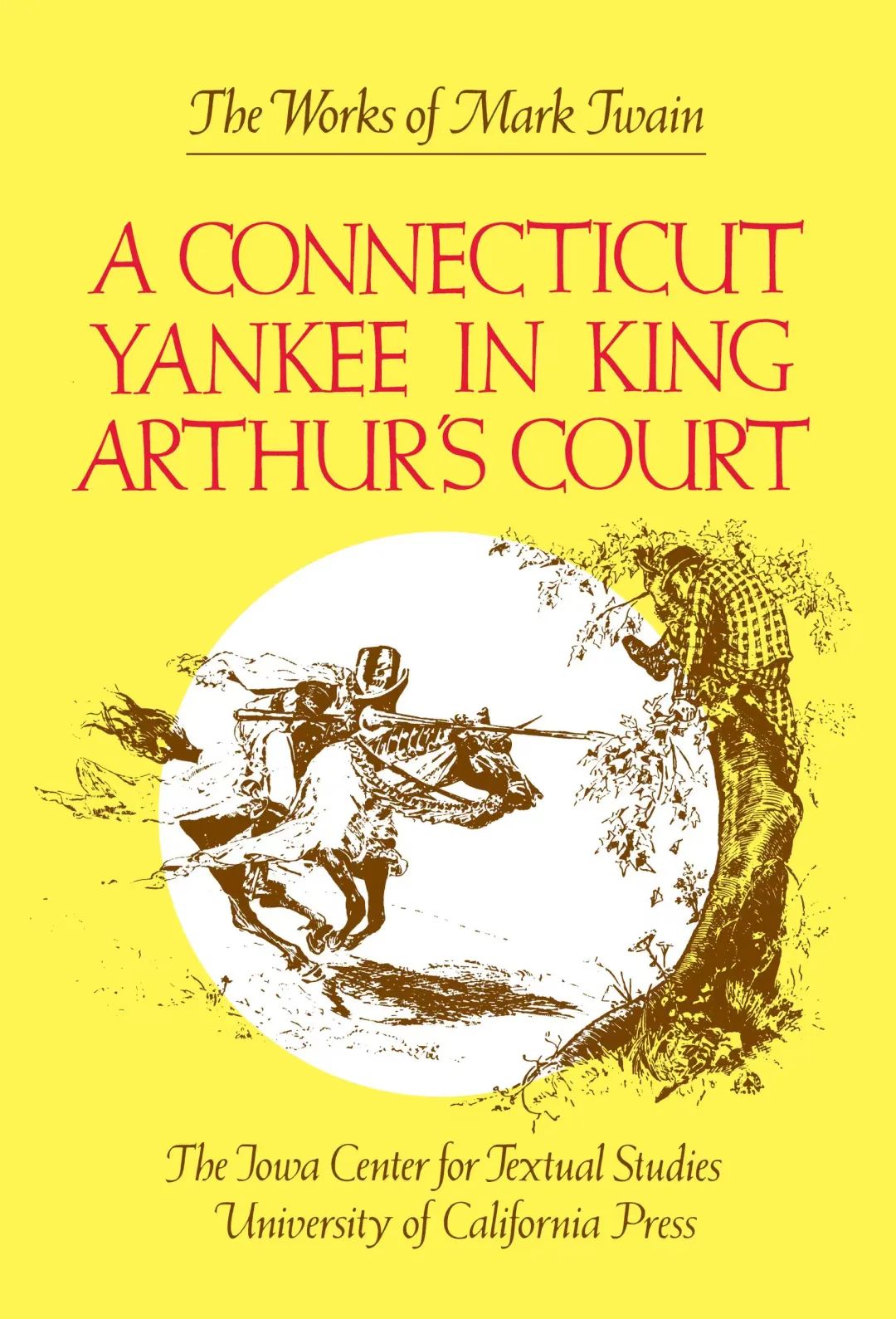孙胜忠丨论马克·吐温《来到印第安人中的哈克·费恩与汤姆·索亚》夭折之谜

孙胜忠,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近年来的研究领域为美国西部史和西部小说。近期发表的论文有《霍桑的〈红字〉:传奇面纱后的历史小说》(载《外国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等。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美国西部小说的历史书写研究”(23FWWB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 马克·吐温于1884年夏完成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接着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创作其续篇《来到印第安人中的哈克·费恩与汤姆·索亚》,但在写到第九章时,却突然“莫名地”戛然而止。吐温为什么没有完成这部续作,学界众说纷纭。本文围绕小说中那把“藏进衬里的匕首”,从吐温创作的技术层面和小说的生产语境两方面入手,尤其关注当时政治、历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和吐温对印第安人立场的改变,探究这部小说夭折的深层原因。透过吐温的印第安人书写,可窥见他对印第安人复杂而微妙的态度转变:从鄙视真实的印第安人到反对“书中的印第安人”,再到为他们辩护,而这部未竟之作正处于他从反印第安人到为他们发声的转折点。吐温放弃创作或许是他遇到了技术难题,但究其根本是他对反印第安人立场的回避。
关键词 马克·吐温 《来到印第安人中的哈克·费恩与汤姆·索亚》 终止创作之谜 印第安人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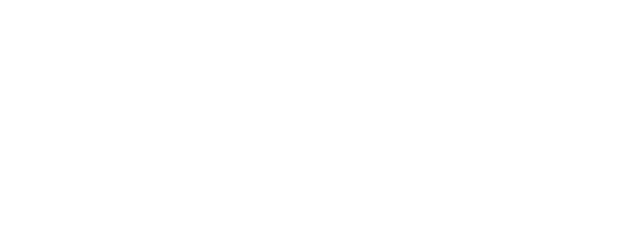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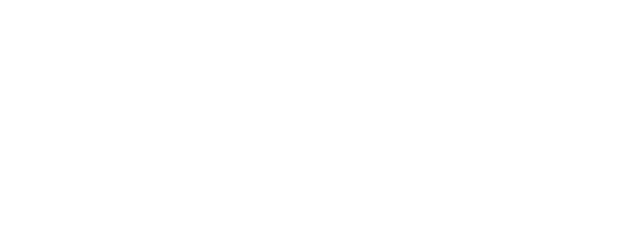
马克·吐温于1884年夏天完成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紧接着便满怀信心地着手创作这部小说的续篇——《来到印第安人中的哈克·费恩与汤姆·索亚》(Huck Finn and Tom Sawyer among the Indians,以下简称《来到印第安人中》)。在阅读了大量有关西部冒险的文献后,吐温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一口气完成了将近240页的手稿,总计约22,000字。然而,他没有继续完成这部续作。这份未完成稿于1968年面世,学界主要从作家创作的灵感、风格、情节设计和象征处理等技术层面分析了这部未竟之作的夭折原因。早在20世纪初,吐温的第一位传记作者潘恩(Albert Bigelow Paine)就提出了灵感枯竭论:“在第九章结束的时候,哈克和汤姆已经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似乎无法脱身,而情节被悬置起来有待进一步的灵感,但显然这个灵感再也没有到来。”直至20世纪末,有的学者仍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吐温写到第九章的时候,“油箱”似乎流干了,所以他突然“神秘地”停止了这一西部小说的创作,其手稿直到他去世将近60年后才得以作为“珍品”出版。还有学者则试图从吐温的创作风格上找原因。例如,吐温研究专家布莱尔认为,“一向在其作品中拘谨”的“幽默作家”吐温“不得不处理佩吉·米尔斯被钉在地上,然后[可能]遭到强暴的可怕迹象”,所以,他“很可能得出结论——完成这个故事是不可能的”。更多学者聚焦于小说创作的技术操作。有的认为吐温的情节设计出了问题,与他的创作初衷相悖,致使他无法继续写下去:“也许他本打算让佩吉获救,未受到印第安人的伤害,但觉得他已经如此确信无疑地把她写进了困境,以致对证据的任何其他解释都不可信,也不值得费力了。”还有的认为:“马克·吐温显然打算让匕首在他错综复杂的情节中再次出现。事实上,难以处理一个不仅与暴力而且与性暴力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的象征,可能给吐温放弃这个故事增加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图片源自Yandex
就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对于吐温为何没有完成《来到印第安人中》,国内学者尚无相关讨论,国外学者也只是在有关吐温的研究中稍有涉及,并未细究,更没有专门研究。本文认为小说生产语境的变化和吐温对待印第安人立场的改变才是破解《来到印第安人中》夭折之谜的关键。下文从吐温创作《来到印第安人中》的初衷出发,参考他在写作中采用的素材——道奇对印第安人的个人观察、记述,重新审视小说中的核心象征,即那把匕首,逐层论述这部小说夭折的技术原因;同时,文章还将分析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的变化给吐温带来的压力,探讨吐温终止创作的外部原因。本文认为,吐温没有完成这部小说的原因有二:一、他在创作过程中意识到小说的情节走向与“童年三部曲”的创作初衷相悖,性描写和过度依赖“二手资料”与他的创作理念冲突;二、他正处于由反印第安人——尤其是反“书中的印第安人”——向同情乃至维护印第安人转变的节点上,可以说,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反种族主义的社会氛围迫使吐温不得不竭力避免引起反印第安人乃至种族主义的嫌疑。


一、 构想中的“童年三部曲”
与难以言喻的“天真丧失”
吐温显然是把《来到印第安人中》作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续篇来写的:两部小说在情节上首尾相连,而且二者开篇的风格和语气如出一辙,叙述者也都是哈克。更有意思的是,叙述者一开始都会提到前一部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开头引入《汤姆·索亚历险记》:“你要是没有看过《汤姆·索亚历险记》那本书,就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过,那也不要紧。那本书是马克·吐温先生做的,他说的基本上是真事。也有些事是他胡扯的,不过基本上他说的还是真事。可那也没关系。”与此类似,《来到印第安人中》是以介绍前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开始的:
我之前写的另一本书,叫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许你还记得。但如果你不记得,那也没什么影响,因为它与这本书没啥关系。它的结尾是这样的。我和汤姆·索亚,还有原来属于沃森老小姐的黑鬼吉姆,都到阿肯色去了,住在汤姆的姨妈萨利和姨父塞拉斯家。吉姆不再是奴隶了,而是自由的;因为——不过这就不要在意啦:他是怎么获得自由的,是谁干的,还有,这么干有多费劲,多危险,这些都在那本书里讲过了。
这两个语气和风格一致的开头显然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在这里,吐温采用了在他其他故事中已确立的哈克的声音,让他继续扮演叙述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哈克的声音具有“独特的特性”——“天真、务实、活泼”,发挥着烘托主题的重要作用,作者让哈克的声音与“社会冷峻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其观察必然会凸显社会矛盾”。
《来到印第安人中的哈克·费恩与汤姆·索亚》
图片源自Yandex
从总体设计来看,《来到印第安人中》不仅要作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续篇,而且还要与《汤姆·索亚历险记》一起构成“童年三部曲”:
从故事的开始到突然结束,马克·吐温显然打算把“来到印第安人中的哈克·费恩与汤姆·索亚”实质性地当作《哈克贝利·费恩》的续篇,就像这部杰作是《汤姆·索亚》的续篇一样。这三本书可以被看作马克·吐温的童年三部曲——以童年天真丧失告终的三部曲。这部印第安人小说的残篇从前两部男孩小说中拓展了许多主题,但它也揭示了田园诗般的童年在本质上是短暂的;哈克不可能回到木筏上——留在那里就是要拒绝长大。
童真的丧失和长大成人意味着对现实的觉醒,从“天真”走向“经验”。就《来到印第安人中》而言,主人公原本是通过重新认识印第安人来实现“觉醒”的。因为这部小说虽然在情节上与前一部小说的结尾相衔接,但很快便更换了场景,由密西西比河一带转向西部;批判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从揭露河岸上腐败的成人世界,转向描写主人公对“书中印第安人”的幻灭感。紧接着《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结尾,《来到印第安人中》里的哈克、汤姆和吉姆来到密苏里西部的一个种植园,可是,很快他们就对那个小小的种植园感到厌烦,因为“汤姆受一个念头毒害不浅,他要到印第安人中待一段时间,去看看那会怎么样”。
汤姆深受其害的“念头”就是库珀小说中的印第安人形象。受其影响,汤姆对印第安人竭尽赞美之词,称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尚的人”,他们诚实、慷慨、智慧、勇敢善战,因此,他认为,“与印第安人在一起,生活就是一场马戏”,对印第安人“怎么赞美都不为过”。途中遇到五个印第安人时,他还认为“没有这么高贵的白人”,哈克、吉姆和其他人也都“喜欢他们”。吐温试图通过这一冒险经历描写两个男孩由幻想走向幻灭的过程。按照这个构思,小说讲述了一场悄然而至的悲剧:在汤姆一行对印第安人充满美好想象和信任之际,印第安人杀害了与他们结伴而行的佩吉的父母和三个兄弟,残忍地剥了他们的头皮,并掳走了吉姆、佩吉及其妹妹。针对印第安人的暴行,哈克问了一个令汤姆无比尴尬的问题:“汤姆,你是从哪儿了解印第安人的——他们多么高贵,诸如此类的事情?”汤姆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他犹豫片刻后回答道,“库珀的小说”。吐温曾撰文严厉批评库珀对印第安人的浪漫化书写,此处,他笔下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印第安人——背信弃义、懦弱,热衷于偷窃、绑架和集体谋杀。遭遇此劫的汤姆和哈克“再也不想见到印第安人了”,要“远离”他们。
为了推动情节发展,吐温在小说中埋下一个伏笔——佩吉的恋人布雷斯·约翰逊交给她一把匕首作为“礼物和纪念品”,告诉她一旦落入野蛮人之手,她应该毫不犹豫地自杀。后来哈克得知了布雷斯把匕首送给佩吉的真实原因——他希望佩吉在被印第安人捕获后自杀,以避免被强暴,从而守护自己的贞洁。因此,哈克将他在印第安人营地发现的那把佩吉的匕首藏在自己夹克的衬里中间,作为他终身的“纪念品”。正是这一情节设置让吐温既难以回头又逡巡难进,因为他无法让哈克直面男女两性的问题,只好让哈克将匕首藏进衬里。
如前所述,吐温的童年三部曲是为“童年天真的丧失”而写的,但在这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哈克和汤姆天真的丧失,或者说在什么情境下他们失落了天真?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目睹了血腥的暴力吗?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在前两部小说中早就见识过谋杀和相互残杀的暴行。一种猜测是少年主人公可能因见证性暴力而失去天真。但这一设计与吐温早先构想的让哈克一行对“书中印第安人”幻灭的主题相悖,也不符合他一贯在性话题上谨慎的创作风格。
关于吐温为何放弃《来到印第安人中》,不仅学界有各种猜测,而且市面上还出现了至少两种这部小说的续写本。续写本,尤其是哈默完整的续写,从反面为本文的上述分析提供了支撑:吐温无法让少年哈克见证性暴力,刻意收起那把旨在揭露印第安人卑鄙、残忍的匕首。哈默的续写本暗示了吐温的难言之处,又极力回避吐温欲言又止的内容,并设法对他留下的疑团作了另类化解。但要想深入了解吐温把匕首藏进衬里的苦衷,我们还必须紧扣文本和小说的素材,尤其是要回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历史现场。


二、“二手资料”与少年视角的冲突:
吐温遭遇的技术性难题
关于《来到印第安人中》的“流产”原因,吐温本人从未解释过。如前所述,潘恩认为在残篇结尾处,哈克和汤姆陷入了无法脱身的困境。其实,与其说这个困境是吐温笔下人物的,还不如说是他自己的。吐温这部小说的创作在人物刻画、事件的叙述等细节上大量借用了当时出版的有关西部和印第安人的资料,尤其将道奇的《大西部平原及其居民》(The Plains of the Great West and Their Inhabitants, Be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Plains, Games, Indians, &c. of the Great North American Desert,1877)和《我们野蛮的印第安人》(Our Wild Indians: Thirty-three Years’ Personal Experience among the Red Men of the Great West,1883)当作权威资料。根据道奇对印第安人俘虏白人女子情形的描述,像佩吉那种情况,他们绑架她之后一定会折磨和强暴她。吐温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他借用的西部资料太多,“由此造成的独创性丧失对他来说代价太大”。
《我们野蛮的印第安人》
图片源自Yandex
更何况,《来到印第安人中》的素材主要来自书本,而不是吐温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这便颇具讽刺意味了,因为吐温在这部小说中攻击的对象恰恰是“书中的印第安人”(book Injuns),而他小说里所谓的本土美国人实际上也是如此:他塑造的本土人物更多来源于“书中的印第安人”,而不是“他真正遇到的人”。他把道奇描述的印第安人形象当成了他的“第一手资料”,把他自己对印第安人的粗浅认识权当可靠的判断依据。据此,有学者将吐温对印第安人态度的变化,或曰“摇摆不定”,归咎于“他漫无目的的阅读和他有限的经历”:
他早期对浪漫主义文学的阅读误导了他,使他认为,印第安人是盎格鲁社会理想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反映;他在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的经历提高了他对印第安人困境的认识,但也将他的反应转化为种族刻板印象——尤其表现在他的滑稽作品中。的确,对印第安人以及对浪漫化描写印第安人之人的滑稽模仿,在吐温的创作中成了常用的文学手法。但在批判性地评价浪漫主义作家时,吐温把印第安人作为暴力的隐喻和不文明的象征。他后来的阅读提供了互相矛盾的观点,鼓励将文明和灭绝作为解决一些人所谓“印第安人问题”的方案。
确实,吐温对现实生活中印第安人的了解极其有限,他真正见识过的只是内华达肖肖尼(Shoshoni)部落残留下的那些穷困潦倒的印第安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此基础上经常对其他作家笔下的印第安人冷嘲热讽。其全部观点可以归纳为“美国文学艺术家一定从未见过一只独木舟,也未涉足过林地,就对皮裹腿及诸如此类做了如此荒唐的夸张描写”。可以说,他自己也未见过多少印第安人就开始在其早期作品中对他们进行“夸张描写”,只不过他采用的是嘲讽而不是赞美的语气。
这种对二手资料的依赖或许连吐温自己都感到恼火,因为受制于此,他不能按照自己的风格来书写平原。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整个情节线索有瑕疵”,光指出传说中浪漫的印第安人与现实中的印第安人之间的反差,这个“单薄的基础”还不足以支撑整部小说。在残篇的三分之一处,汤姆对印第安人的幻想就随着佩吉家五人遭到屠杀而破灭了,他心目中原来的“高尚的”印第安人已成了“比魔鬼更卑鄙、更铁石心肠”的人。连哈克都“注意到”,“汤姆眼下正把印第安人置于魔鬼之下。你看,他这时候差不多已经想通了,书中的印第安人与真正的印第安人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小说就要“围绕着疑似强奸”收集证据,吐温担心这会“对他的声誉造成持久伤害”,因为在追寻印第安人的途中,哈克在一个印第安苏人营地发现了一块佩吉带血的衣服碎片,断定她非死即伤,于是把布片藏起来以免布雷斯窥探到他们一直隐瞒的真相。但布雷斯还是发现了一个白人女子的鞋印,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四根钉在地上的木桩”。
由于吐温的《来到印第安人中》过分依赖他所收集的有关印第安人的材料,致使他无法令人信服地从哈克这样的少年的视角进行性描写——毕竟,像哈克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单纯男孩是无法理解小说中暗示的那种残忍而变态的性暴力的。尽管哈克在前两部小说中已目睹过谋杀、盗墓、欺诈,但性犯罪他是第一次遇到,他甚至都不曾有过恋爱的经历,对性一无所知。在童年三部曲的前两部,吐温始终将哈克描写为一个天真的少年,试图通过他纯洁的眼睛来审视成人世界的缺陷和罪恶;在这部小说中,哈克第一次遭遇性问题,像其他成长中的男孩一样,性是他进入成人世界必须面对的问题,要了解成人世界,他必须了解性。但在处理哈克对性的认知,描写他如何由“天真”走向“经验”时,吐温受制于他所掌握的材料,设置的情节过于血腥,结果他不得不让一个天真如哈克的少年通过发现集体强暴来了解性,这是一个尴尬困境。再说,无论是哈克还是佩吉,一开始都不明白布雷斯为什么要送给她一把匕首。佩吉只是把匕首当作布雷斯送给她的“礼物和纪念品”,哈克也不明白那把匕首的真正意义,而布雷斯不知道佩吉已失去了匕首,所以令他略感欣慰的是,佩吉有把匕首可以自杀。但布雷斯在那个遗弃的印第安人营地发现有四根钉进地里的木桩,而哈克也发现了那个女孩带血的衣服碎片。这明显是佩吉遭到强暴的迹象,此时,哈克与汤姆已预感到佩吉可怕的命运,只是需要确证。哈克一再追问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我走上前问布雷斯,他是否真的希望佩吉已死;如果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这样希望。他向我解释了这件事,然后事情就全清楚了。”哈克此时才得知,布雷斯宁愿佩吉死,也不愿她遭到印第安人强暴,在布雷斯看来,这是比死还糟糕的命运。因此,哈克与汤姆此后就极力掩饰佩吉还活着的可能。
如果吐温继续写下去,就必须回应他前面埋下的伏笔,那把匕首必然会再次出现,他就“不得不处理佩吉·米尔斯被木桩束缚在地上遭到强暴的可怕迹象”。吐温感到自己无法应对这个难题:“显然,马克·吐温觉得很难想象,哈克目睹了原始的性拉肢刑具,发现了佩吉带血的衣服碎片,还能继续以天真的眼光看待世界。……让哈克和汤姆追上印第安人,发现17岁的佩吉没有死,而是失去了贞洁,这显然是无法忍受的局面。”于是,吐温陷入了困境,他原先设计的叙述者根本无法讲述他毫无经验甚至无法想象的事件,因为按照现有的情节线索,接下来他要揭示印第安人的罪恶,而这要通过描写集体性暴力来实现,这显然越界了,既超出了哈克“天真的”视野范围,也不符合吐温在性描写方面一贯拘谨的创作风格。
上述推断可以在吐温八年后出版的《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The Californian’s Tale”,1893)中得到佐证。与《来到印第安人中》类似,这个短篇小说讲述的也是白人女子被印第安人掳走后命运未卜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汤姆深情地给陌生的访客讲述了他19岁的新婚妻子打理家庭的点点滴滴。其实早在19年前,他的新娘就死了,“或许比死更惨”,因为她在出嫁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六傍晚从娘家返回的路上,被印第安人“俘获去了,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她的消息”,结果,汤姆“就这样疯了”。吐温在这个故事中并未提及屠杀或强暴,但“比死更惨”显然暗示汤姆的妻子与佩吉的命运一样,很可能遭到了印第安人的强暴。这便是吐温欲言又止之处,因为这个未决的问题极容易引起怜悯和恐惧。吐温之所以只是暗示,而不言明,说明他依然不愿或不敢触碰印第安人卑鄙残暴这个敏感的话题,宁愿继续把它藏进自己的“衬里”。
吐温阅读过许多有关印第安人的材料,并“大量运用了文学资源”,以致在创作中利用这些资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程序”。尽管他声称对西部有话语权,但实际体验很少,这成了他小说中对印第安人细节描写方面的“严重劣势”。这也许让他意识到过分依赖别人书中有关西部的描述存在严重缺陷。一来无法驾驭这些材料,二来这些材料提供的信息与他选择的少年视角严重不符,这些都可能是他终止创作的原因。


三、“藏进衬里的匕首”:
吐温对反印第安人立场的回避
《来到印第安人中》的夭折不仅仅是因为它与童年三部曲的构想发生偏离,以及二手资料与童年视角的冲突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吐温对小说走向及其后效的担忧,他担心这将被读者视为他又一部反印第安人的小说,而这种担忧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社会压力。
《亚瑟王朝廷上的美国佬》
图片源自Yandex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主要倚重道奇的个人观察,而就现有的残篇来看,吐温同道奇一样,对印第安人持极其严厉的批判态度,而且按照现有的线索,最后的结局只能是道奇所描写的集体强暴。忌惮反印第安人立场才是吐温终止创作的根本原因,“因为他对陷入这种严厉的基调不满”,虽然他此前攻击过印第安人,甚至在《亚瑟王朝廷上的美国佬》(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1889)中还嘲弄过土著印第安人,但他后来“从未直接聚焦过美国印第安人迸发出的邪恶”。但那把匕首出现在屠杀现场,说明佩吉没有把它带在身上,自此之后,它就成了故事情节的中心线索。如果吐温继续写下去,那么,他就势必要按照道奇的记述,进一步揭开佩吉遭到强暴这个谜底。这一方面会使小说走向道奇设定的情景,落入西部一角小说(the Dime novel)的窠臼,另一方面也会引起读者的不良反应,因为当时大众已开始质疑对印第安人的刻板描写。于是,吐温让哈克将那把匕首藏进衬里之后,就此终止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前文提到有学者认为难以处理小说中匕首这个象征是吐温放弃创作“令人信服的理由”。其实,对于小说大师吐温来说,处理一个象征未必艰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让大众接受他所描绘的印第安人,因为已设定的情节无法回避呈现残忍、卑鄙的印第安人形象。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回避反印第安人的立场才是吐温不得不放弃这部小说的真正原因。
毋庸讳言,吐温多年持反印第安人的立场,至少他给读者留下的是这种印象,但他最终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乃至公开为他们伸张正义。大约从1868到1895年,吐温在这20余年期间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他由攻击真实的印第安人转化为诋毁库珀小说中的印第安人,直至最后转向对殖民者的无情批判,尤其是20世纪伊始创作的作品。究其深层原因,还是社会氛围发生了改变,当时在检讨西部历史时,批评的锋芒已从本土印第安人转向了殖民者白人。“从广义上讲,这是从狭隘的种族刻板印象向文化相对主义的转变。……只有当吐温开始严肃对待印第安人时,这种态度才有所改变。”有学者认为“他的反印第安人作品反映的是19世纪后半叶他的广大读者的态度”。更有人认为,“他早期的作品鼓励了这个国家对印第安人的蔑视,但可能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印第安人苦难命运的真相”。实际情况是,吐温十分在意读者的反应,他早年作品表现出的对印第安人的反感态度的确深受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他甚至大量借用了道奇有关印第安人的说法。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也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因为印第安人在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已经开始松动,大众不再想当然地认同他们是嗜血成性的野蛮人。这种观念的变化对吐温产生了影响,出于对读者反应的考虑,他只好让《来到印第安人中》胎死腹中。
尽管有人说,“艺术和政治必须在两个不相关的渠道流动”,但作为艺术家的吐温,“他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也很浓厚”。这种“兴趣”对吐温的创作产生了两种影响:一方面,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是他小说创作的动力源泉之一;另一方面,他十分在意小说出版后读者的反应。这两种影响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创作和出版中已显露出来。1884年出版的这部小说很明显关注当时的一个社会热点——南方问题。这个问题极具争议性,吐温“担心失去敏感的买家”,即读者,因此,他在书的扉页中就以惯常的幽默口吻发表了“不承担责任的声明”(disclaimer):“试图在这篇故事中寻找动机者将被起诉;试图从中寻找寓意者将被放逐;试图从中寻找阴谋者将被枪毙。”这一策略似乎给他提供了在艺术与政治这两个渠道流动的自由,是否奏效暂且不论,但这显然表明,他十分关心小说出版后读者的反应。对南方问题敏感性的担忧也传导到正在创作的《来到印第安人中》,这次他要带着读者熟悉的哈克和汤姆到印第安人中去,这势必又涉及另一个争议性话题——印第安人问题。
有学者指出,关于印第安人,吐温在他那个“群体”中有“无法公开表达”的“深层矛盾心理”,因为当时他周围的许多人,包括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都支持“康涅狄格印第安人协会”(Connecticut Indian Association,1881—1888)。这个慈善组织创立的目的就是探讨“为美国印第安人工作以及与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有证据表明,在创作《来到印第安人中》期间,吐温全家都感受到了这种“社会压力”。
吐温感受到的压力也与政治气候密切相关。在政治和法律上,当时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旨在促进土著美国人土地所有权的《道斯法案》(The Dawes Act),这表明美国政府已意识到印第安人问题,开始考虑他们的地位和权利,因此,吐温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也伴随着他们在白人社会中形象的变化而悄然改变:
公众对1887年的《道斯法案》的良知正在增强,该法案将开始实施把印第安人转变为公民的政策,而不是用武力“安抚”他们,许多迹象表明,吐温正试图理解他们和黑人的观点。他对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当选感到欢欣鼓舞,其中包括对把赞成政党分肥制的人排除在保留地之外的展望;1886年,他给总统发了一封愤怒的短信,内容是关于新墨西哥一个小镇悬赏阿帕奇人头皮的报道。
政府已将印第安人视为公民的立场促使吐温本人重新理解和重新认识印第安人,这可能是他放弃《来到印第安人中》写作的深层原因,因为这部小说按照原来的设计不可避免地要将印第安人视为另类,展示他们的残暴和嗜血。残篇止笔于哈克一行追寻绑架者印第安人,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就是佩吉的命运,揭示她遭到印第安人强暴的“真相”,这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不合。
此外,在19世纪80年代,西部一角小说中宣扬的暴力和对耸人听闻事件的描写遭到大众,尤其是为人父母的读者的抵制,因为民众认为一角小说会诱导少年犯罪。到80年代中期,
如此多的美国人要么亲身体验过西部,要么通过大量生产的叙事作品吸收了西部主题,以至于在不落入高度规定、公式化的文学表达模式的情况下,写出任何有关该地区的东西,都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到了19世纪80年代,西部“母题”(motif)已经变得如此定型化,以致在诸如野牛比尔的蛮荒西部表演这种情节滑稽剧和成百上千快速写成的西部一角小说中,它都开始自我戏仿了,一角小说中,情节、主题和陈腐的人物导致了形式和功能的反常。在一角小说市场中,原创性越来越成为一种对事实的歪曲和对轰动效应的追求。
而吐温在1884年夏天着手创作的《来到印第安人中》原本就过分倚重过时的西部资料,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接近一角小说的暴力模式,无论是在情节设置上,还是在题材上,这部小说都带有一角小说的印迹。如果说小说的前两章还在延续前面两部小说的风格,让天真的哈克和汤姆带着浪漫的幻想前往西部寻找库珀式的印第安人,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吐温笔锋一转,直指暴力现场——印第安人杀害了佩吉一家五口人,并将其两个女儿和吉姆掠走。至此,作为“高贵野蛮人”的印第安人形象在哈克和汤姆的心中荡然无存。这种快节奏的情节呈现酷似一角小说,而且在追寻绑架者的过程中,条条线索——带血的衣服碎片、佩吉的脚印和地上的四根木桩等等——均指向性暴力。凶杀、剥头皮、折磨和变态性侵犯等情节都落入了一角小说的俗套,并且这些都将展现在少年的哈克和汤姆眼前,甚至有可能唤起他们潜在的暴力和变态倾向,而这正是当时公众所担心的,因此,吐温无法回避公众的关切。就在吐温创作《来到印第安人中》的1884年,《文学新闻》(Literary News: A Monthly Journal of Current Literature)上还发表了一篇有关一角小说负面影响的文章,该文描写了一帮模仿一角小说的少年抢劫犯,那些男孩的父母都“十分受人尊敬”,但他们的“良好影响”都被男孩们读的小说“抵消了”,文章发出的警示是,“教师和牧师的工作被一角小说化为乌有”。这种警示是当时文化和文学氛围变化的体现,必然会对吐温的创作产生影响,迫使他放下手中这支有可能“抵消”社会对儿童正面教育的笔。
不可否认,吐温之所以要在《来到印第安人中》兑现他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结尾处的承诺,让他笔下的人物“到印第安人保留地去”,是因为他看中了西部小说这个在当时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富矿带”(bonanza),但很明显,“吐温对这部著作的抱负超越了金钱利益”。一贯对创作苛求的吐温无法容忍自己的小说沦为一角小说。而且,他的这部小说主要是为了颠覆库珀小说中的印第安人形象,把他们拉下“高贵野蛮人”的神坛,显示其嗜血和歹毒的本性。但如果吐温按照已有的西部资料完成这部小说,那他就会犯自己指责库珀所犯的“文学之过”——“没有创新”,同库珀的《杀鹿人》一样,“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艺术品”。这也可能是吐温放弃《来到印第安人中》的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是他要回避反印第安人的立场。20世纪初,吐温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更加慎重而理性,他在1901年写给索尼克森(Albert Sonnichsen)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全世界人的心都差不多,不管他们的肤色是什么。”可见,他已不再将印第安人视为另类。


费德勒和博纳姆,图片源自Yandex
有学者认为,令吐温进退两难的“显著”原因是:“作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及其最勤勉的人道主义者之一,吐温乐于,甚至急于要谴责对遭受苦难的少数族裔的压迫。此论值得商榷。多数学者认为吐温仇恨印第安人,例如,美国文学批评家费德勒(Leslie A. Fiedler)称吐温“绝对是个仇恨印第安人的人”;雷沃德(Carter Revard)也认为吐温的作品总是带有“对印第安人固执的鄙视和歹毒的仇视”,他“恨印第安人,在依然十分流行的书中非常恶毒地表达这种仇恨——而在美国文学和文化机构中尚无人仔细地考察过这种仇恨及其激烈的种族主义表达”,以致博纳姆(Philip Burnham)称吐温“不是一般仇恨印第安人的人”。揭露对印第安人不公的是吐温的后期作品,如《伊斯兰教的托钵僧和出言不逊的外来者》(“The Dervish and the Offensive Stranger”,1902年创作,1923年出版)就“试图理解和挑战否定印第安人权利的既定西部体制”,明确为印第安人声张主权。但这部为印第安人发声的作品创作于吐温终止《来到印第安人中》18年之后,而且他生前并未发表这个作品。其实,在印第安人问题上,吐温一直处于一种“道德困境”,如前所述,他的创作尤其倚重道奇的作品,但后者特别关注白人“文明”与印第安人“野蛮”之间的对立,这使他进退两难的窘境更加突出。随着对印第安人以及美国政府对印第安政策真相的进一步了解,吐温逐渐改变了立场,只是为了避免引发对自己不利的反应,他在当时才没有公开表达。
在主流社会开始整体反思印第安人问题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下,吐温担心按照既有情节创作的小说表达的是与社会思潮背离的反印第安人立场。这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无奈地选择了将针对印第安人的那把匕首“藏进衬里”。进一步看,这与吐温自身对待印第安人的立场有关,而他由攻击印第安人走向为他们辩护的一个转折点就集中体现在他的未竟之作《来到印第安人中》的命运上。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4年第5期“作品及作家研究”专栏,责任编辑龚璇。前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s://www.nssd.cn/)可免费下载全文。
责编:艾萌 校对:袁瓦夏 张文颐
排版:雨璇 终审:文安
相关链接
往期回顾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 点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