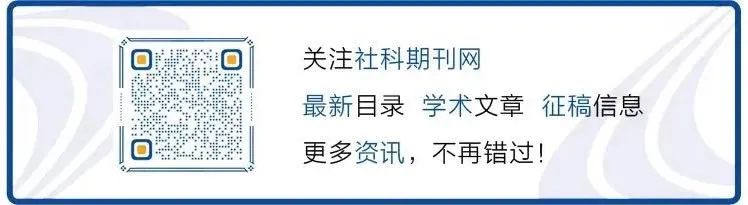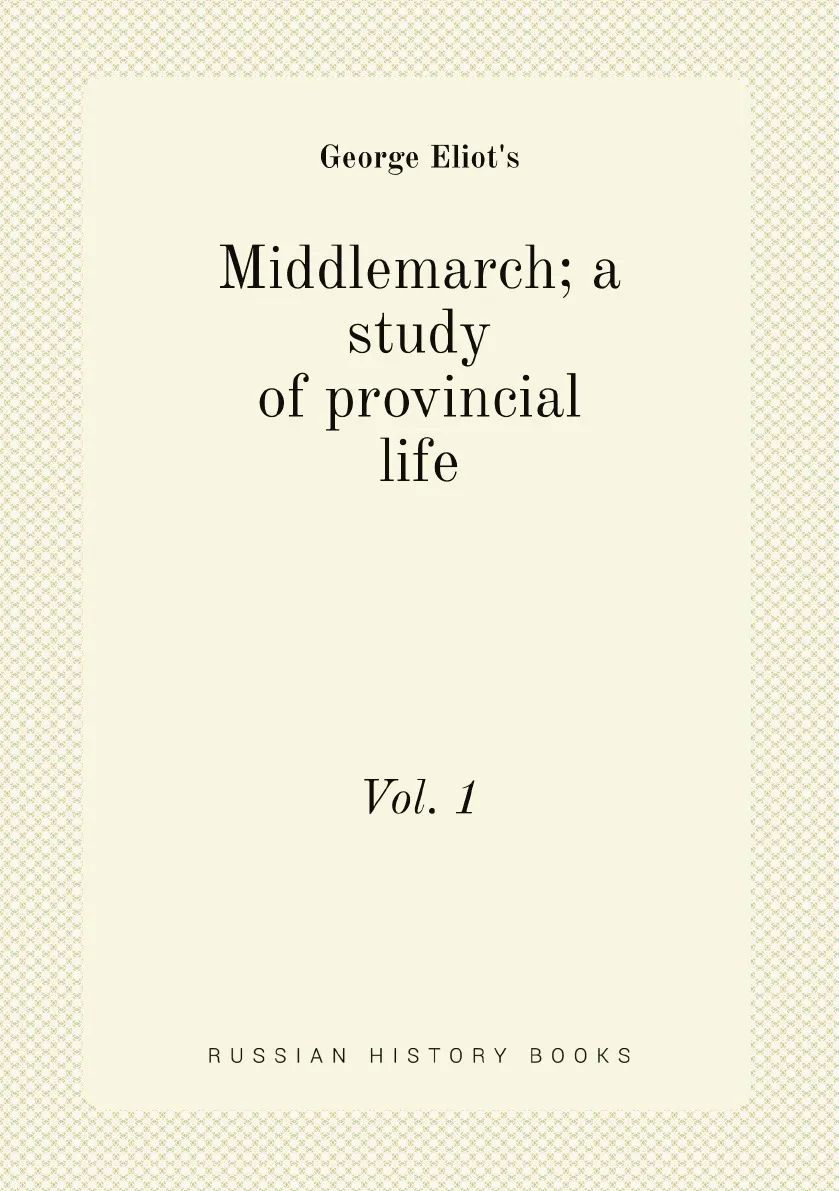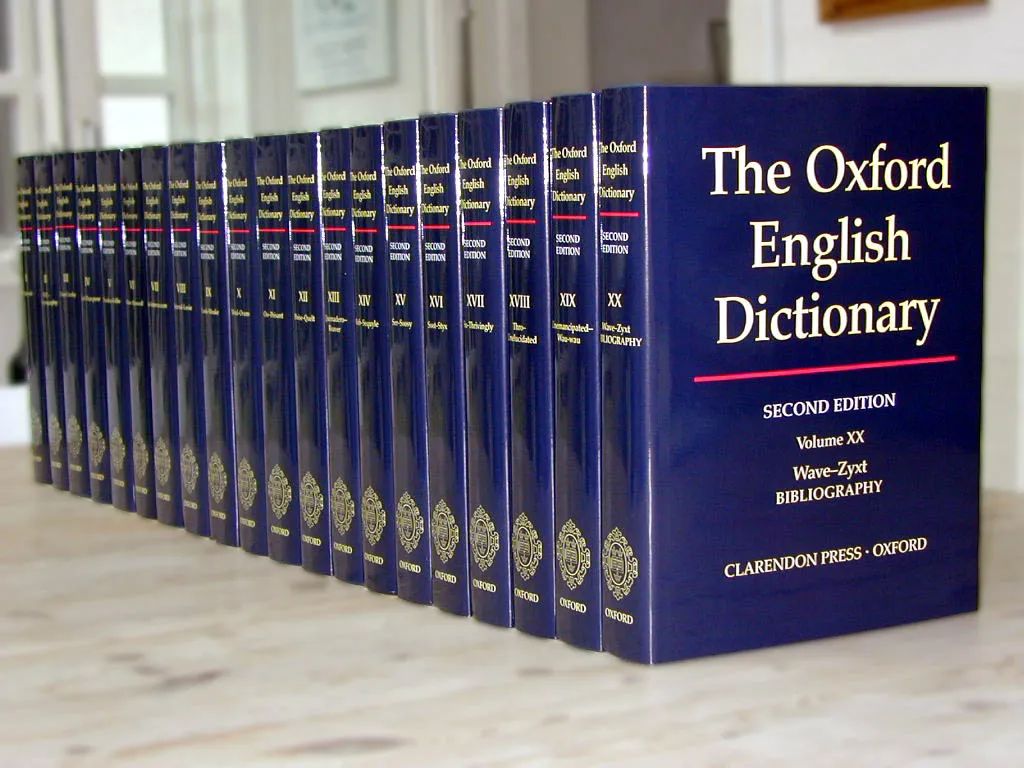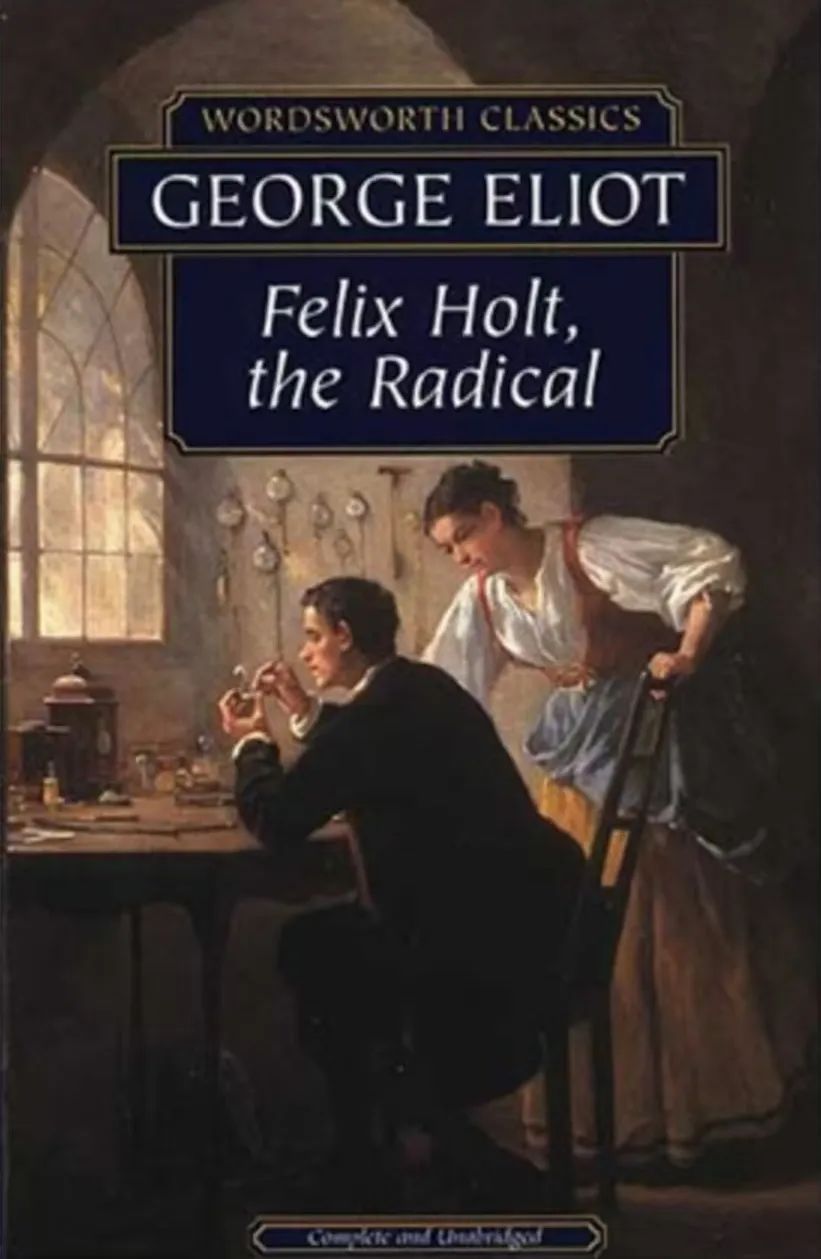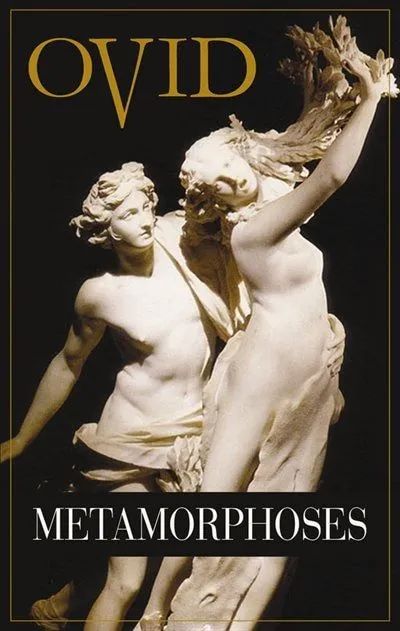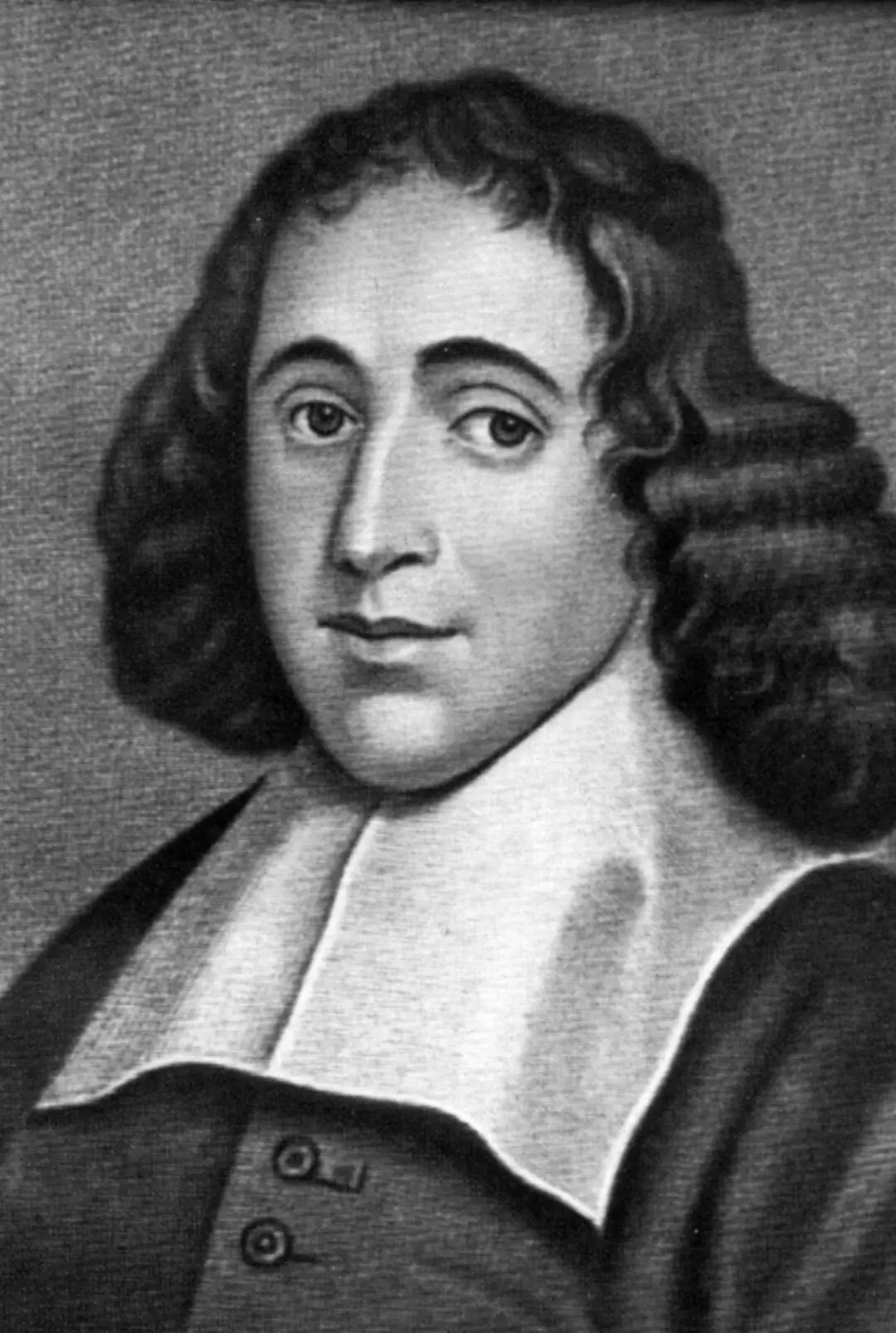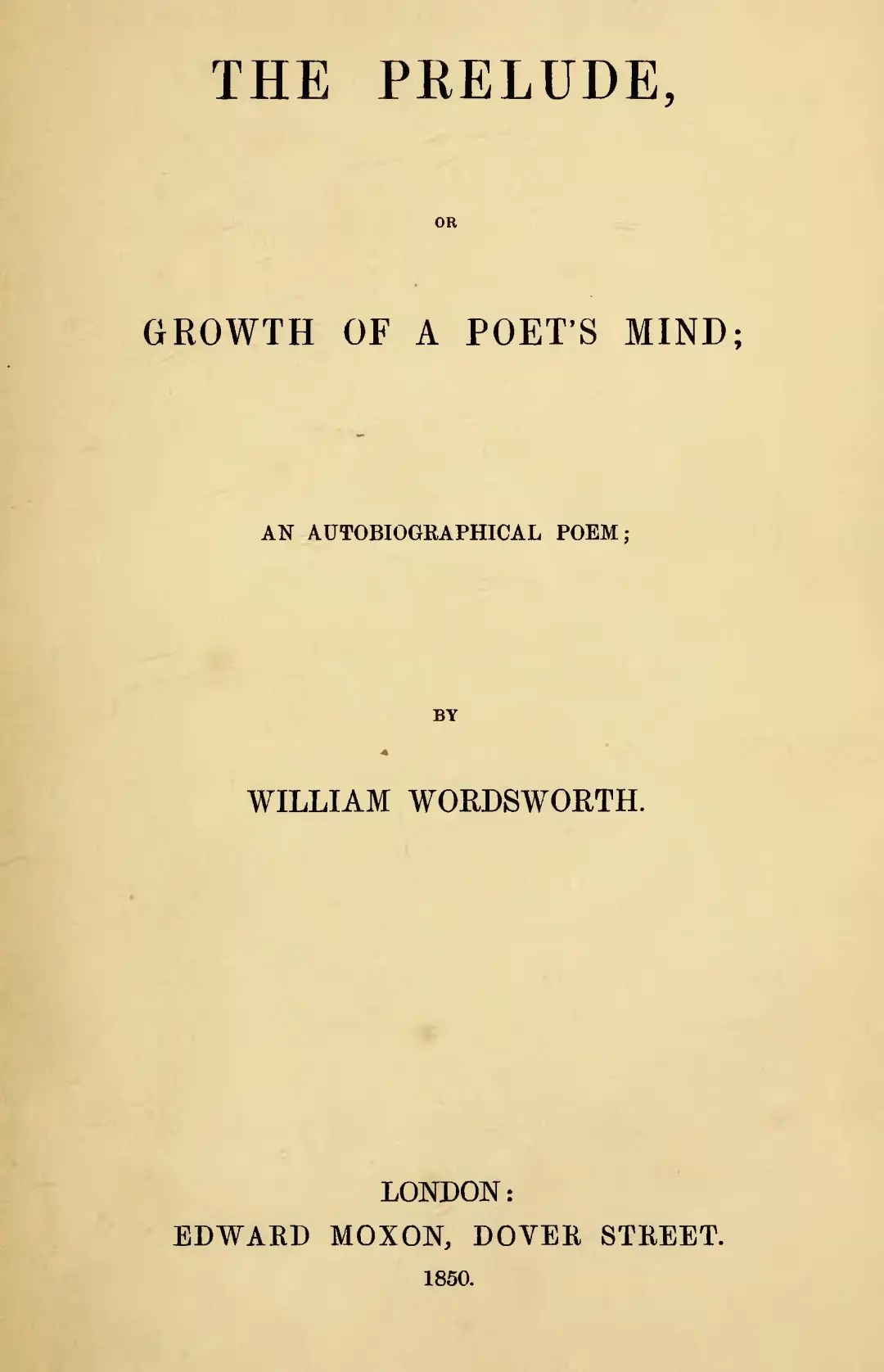王婉莹丨“赫拉克勒斯的选择”:论《米德尔马契》中的美德与幸福
内容提要 在小说《米德尔马契》中,乔治·爱略特以诗性语言介入美德与幸福的关系这一经久不衰的哲学争论,通过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诠释了古典幸福观和现代幸福观之间的分歧。通过改写“赫拉克勒斯的选择”,爱略特反思现代幸福的伦理缺失,重塑美德与幸福的纽带,揭示了以“活得好”和“做得好”为核心内涵的美好生活,藉此介入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幸福话语建构。
关键词 《米德尔马契》“赫拉克勒斯的选择” 美德 幸福

引 言

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被誉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哲思的小说家。在19世纪英国,人们趋之若鹜地追求“最大的内心满足”,如何在教条和权威衰落时挽救美德(virtue)和幸福(happiness)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问题。与此同时,《尼各马可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的作者亚里士多德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古希腊哲学家。正如托马斯·阿诺德所言,亚里士多德与其说是古代作家,不如说是维多利亚文人。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率先提出幸福(eudaimonia)即至善,直至18世纪以前,幸福作为个体的至善及“一切道德和政治的行为指南”几乎是社会共识。然而,英语中的“幸福”(happiness)概念在18世纪经历了“地震般的变迁”(a seismic shift)到世纪末几乎沦为一种“纯粹的感觉”,丧失了其伦理与政治内涵。自19世纪初以来,happiness一词常常用来表示“愉悦的感觉”(feelings of pleasure),总之,“幸福与美德之间的既定联系被切断了”。正是基于上述背景,爱略特敏锐地觉察到维多利亚人在想象幸福与美德的关系方面存在问题,于是尝试通过阅读亚里士多德以寻找“至善”(the chief good)并追求它,其小说便是对这场围绕幸福的古今之旅最好的记录。
乔治·爱略特和《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
图片源自Yandex
爱略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Middlemarch:A Study of Provincial Life,1871—1872)在探讨幸福与美德的关系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相关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要数意大利学者瓦莱丽·温赖特的研究。温赖特认为,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探讨了道德卓越与幸福(eudaimonia)的关系,追问如何才能过上“既活得好又做得好”的生活,即令人愉快且充满意义的生活。需要说明的是,温赖特使用的eudaimonia一词在小说中从未出现,但与之相关的happiness/happy合计出现了150次,其频率之高反映了19世纪英国社会对幸福的普遍焦虑。然而,温赖特对以下问题却语焉不详:古典幸福(eudaimonia)与现代幸福(happiness)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它们各自与美德的关系又如何?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如何呈现这两种幸福观,并表达了怎样的伦理诉求?
作为一个幸福原则,“赫拉克勒斯的选择”(The Choice of Hercules)不失为回答上述问题的切入点。“赫拉克勒斯的选择”是爱略特小说创作的重要母题,作家以此表现她对幸福与美德的深入思考。大卫·希格登指出,爱略特深受《赫拉克勒斯的选择》之启发,在小说中塑造“美德”(Virtue)女神与“愉悦”(Pleasure)女神两类女性形象。实际上,通过改写“赫拉克勒斯的选择”,爱略特不仅与古典以及同时代的幸福思想传统实现了互动,还表达了她对美德与幸福之关系的深刻理解,并运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加以生动呈现。下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美德与幸福何以分离?爱略特如何以小说形式改写“赫拉克勒斯的选择”?又如何化用“赫拉克勒斯的选择”来表达重建幸福与美德之纽带的愿景?

一、 美德与幸福的分离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ED),幸福主义(eudaimonism)是一种“以产生幸福的行为倾向为道德义务基础的伦理体系”。但从18世纪晚期开始,幸福主义的伦理维度逐渐被遮蔽,它作为“默认的伦理思维方式的地位”主要受到了两个竞争对手的挑战:康德理论和功利主义。这两种传统在维多利亚时代尤为盛行,加速了幸福与美德的分离:一方面,两者都将幸福界定为“愉悦”(pleasure)或“欲望的满足”(the fulfillment of desires),因此误解了幸福主义。另一方面,幸福与美德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在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马克思那里,美德与幸福“紧密纠缠”,而在像康德这样的现代道德家眼中,两者几近势不两立。事实上,上述种种问题均可以归结为以下这一点:古典幸福(eudaimonia)和现代幸福(happiness)已然成为迥乎不同的概念,甚至被称作“两种幸福概念”。如果说古典幸福将美德(virtue)视为关键,那么现代幸福便以愉悦(pleasure)为核心。也就是说,古典幸福与现代幸福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与美德的关系:前者与美德密不可分,后者则基本与美德无涉。
《牛津英语词典》,图片源自Yandex
前文提及,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善视作幸福(eudaimonia),并将幸福等同于至善。他提出,幸福的要点在于“合乎美德(德性)的实现活动”,而这种活动必定自身就令人愉悦;也就是说,幸福意味着既要“活得好”又要“做得好”,才能有利于城邦共同体的幸福。从词源上看,eudaimonia一词源自古希腊语,由两个词根“eu”(好的)与“daimon”(神衹或神灵)组成,意思是“当一个人自爱并受神宠爱时所拥有的良好生活状态与良好行为状态”。需要说明的是,美德并非仅仅是古典幸福的一个侧面,而是占据了一定的支配性地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实现真正的幸福,人需要努力养成内在于灵魂的“卓越品质”,也就是“美德”(或“德性”),例如勇敢、节制、慷慨、正义、智慧等,并在生活中积极地付诸实践。换言之,古典幸福取决于美德,而美德的养成要求人们乐于做符合美德的事。
古希腊哲学中的幸福(eudaimonia)概念是现代英语中幸福(happiness)概念的缘起。美国历史学家麦马翁提出,现代的幸福(happiness)概念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犹太—基督教思想的产物。亚当·波特凯同样指出,happiness植根于古希腊伦理学。尽管该词偶尔出现在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中,但直到18世纪,它作为eudaimonia的英译才广泛流行起来。根据《牛津英语词典》,happiness主要包括三层内涵:1.生活或特定事件中的幸运、成功与繁荣;2.愉快的精神状态,指称获得成功或某种“善”而产生的状态;3.适宜性,通常与得体的言行相关。编者特意指出,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便指第二层内涵,表示一种主观愉悦感,这也是现代幸福最普遍的定义。现代幸福观诞生于17至18世纪期间的启蒙运动,后者的标志性胜利就是对“世俗幸福”(earthly happiness)的确认。作为启蒙现代性的核心命题,幸福观念经历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随着启蒙思想家对体系化思想的过度依赖,现代幸福观逐渐演变为一种个人主观模式,导致责任从幸福观念中分离,其伦理维度日渐瓦解。
天长日久,古代“好生活”理论被一分为二,一半是“道德善”,另一半是“主观幸福感”。换言之,美德与幸福渐行渐远,这在约翰·洛克和康德的哲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譬如,洛克相信,现代幸福不再是单一的至善(summum bonum),而是寄托于多种不同的事物之上,并提出“完满的幸福就是我们所能享受的最大快乐(the utmost pleasure)”。在洛克看来,人人都渴望幸福,而幸福则在于满足欲望。康德则将“幸福”(Glückseligkeit)界定为“对个人需求和倾向的全面满足”,即“现在和每一个未来状态中的最大幸福”。用美国学者朱莉娅·安纳斯(Julia Annas)的话来说,康德笔下的幸福几乎是“享乐主义”的代名词。康德宣称“道德威严与享受生活无关”,并呼吁“将所有幸福原则从道德准则的考虑中排除”,进一步将幸福与美德相分离。
爱略特敏感地意识到现代幸福与美德之间的分歧,她对亚里士多德所描绘的“好生活”理念充满向往。前文提及,1852年7月21日,爱略特在写给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的信中宣称自己正在追求亚里士多德笔下的“至善”。她多次在信件及小说中盛赞亚里士多德为“最伟大的古人”“最睿智的智者”以及“伟大的权威”等。在题为《希腊哲学、洛克与孔德》(“Greek Philosophy & Locke & Comte”)的笔记簿中,爱略特大量摘录与亚里士多德相关的内容,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亚历山大·格兰特(Alexander Grant)所著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Aristotle,1857—1866)等。值得一提的是,格兰特在其著作中不仅将亚里士多德笔下的eudaimonia译为happiness,还花了两三页篇幅解读普罗狄科斯(Prodicus of Ceos)的故事《赫拉克勒斯的选择》。此外,从1868年1月到1871年12月的作家阅读清单来看,爱略特在创作小说《米德尔马契》期间,有计划地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等作品。在《米德尔马契》中,爱略特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赞许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进一步揭示了该小说与古典哲学之间的互文关系。
亚里士多德,图片源自Yandex
有鉴于此,有理由认为,在《米德尔马契》中,爱略特不仅以诗性语言介入“美德与幸福的关系”这一经久不衰的哲学争论,还充分吸收以美德为核心的古典幸福和注重主观感受的现代幸福思想,将它们编入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之中。要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从爱略特对《赫拉克勒斯的选择》的改写说起,这则古希腊寓言故事几乎把幸福与美德置于对立的两端。

二、 爱略特对“赫拉克勒斯的
选择”的改写

爱略特曾多次阅读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um Socratis Dictorum),后者最早记载了普罗狄科斯的《赫拉克勒斯的选择》。根据色诺芬的记录,青年赫拉克勒斯正处在思考人生选择的阶段,迎面走来“美德”(Areté/Virtue)和“邪恶”(Kakia/Vice)两个女人,后者被她的朋友们唤作“幸福”(Eudaimonia/Happiness)。美丽迷人的“邪恶”许诺赫拉克勒斯每一种感官满足,永远告别战争、痛苦与烦恼。衣着朴素的“美德”则呼吁他认真劳作、直面逆境,以追求高尚的幸福。“邪恶”提供一条“最快乐最容易的道路”,“美德”则代表一条艰难又漫长的道路。西塞罗曾在《论义务》中重述这一故事,将赫拉克勒斯面临的两条人生道路概括为快乐之路与美德之路。
《赫拉克勒斯的选择》主要传达了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幸福与美德以两个女人或两条道路的隐喻构成了某种对照甚至对立。例如,康德指出,这则“美丽的寓言”将赫拉克勒斯置于“美德”与“感官愉悦”的冲突中,从二元论的视角呼吁人们成为追求美德的理性存在。另一方面,邪恶和美德分别象征着轻松的感官快乐与艰难的精神愉悦。根据格雷对希腊文版《回忆苏格拉底》的研究,色诺芬让“邪恶”和“美德”各自宣称她们的道路能通往“幸福”(eudaimonia)的同时,不加区分地使用了“快乐”的同义词,强调这两个女人将为赫拉克勒斯带来不同种类的快乐:前者提供“感官快乐”(sensual pleasures),后者则倡导“精神愉悦”(spiritual delights)。简言之,赫拉克勒斯的选择亦可以被视作关于“两种快乐/幸福”的抉择。还需指出的是,《赫拉克勒斯的选择》在后世被反复诠释与改编,以戏剧、绘画、诗歌、音乐等多种形式呈现,成为西方文学和艺术中的一个经典母题。这则故事在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广泛流行,并渗透到维多利亚小说的创作之中。
《激进党人菲利克斯·霍尔特》
图片源自Yandex
爱略特在多部小说中改写“赫拉克勒斯的选择”,强调美德与幸福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1860)里,麦琪认识到“无法替自己或别人选择幸福(happiness)”,只能面对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尽情享受欢愉,另一条则是为了忠于崇高的动机而牺牲眼前享乐。同样地,在《激进党人菲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 The Radical,1866)中,埃丝特意识到自己处于两条道路的岔路口:一条是由哈罗德引导的走向堕落生活的轻松道路,另一条是由菲利克斯指引的通往“伟大的善”(greatly good)的艰难道路。在《米德尔马契》中,“赫拉克勒斯的选择”这一母题得到了最生动的呈现。第18章中,爱略特假借牧师费厄布拉泽之口直接提及“赫拉克勒斯的选择”:
“我知道,世界对我来说是太强大了。但我本来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我也永远不会成为德高望重的圣贤。赫拉克勒斯的选择是一则很好的寓言,但普罗狄科斯把这位英雄的行为说得轻而易举,好像只要下定决心就成了。另一个故事讲到他开始手握纺纱杆(hold the distaff),最后穿上了涅索斯的衬衣(Nessus shirt)。据我看,正直的决心可以使一个人走上正路,但必须其他的人都决心帮助他。”
当费厄布拉泽提及“赫拉克勒斯的选择”时,他的谈话对象正是27岁的利德盖特。爱略特在该章题词里写道:“人间最崇高的愿望(the loftiest hopes)与私心杂念(meaner hopes)在抓阄儿”,暗示利德盖特当时面临的重要抉择,即该选泰克还是费厄布拉泽为医院的牧师。爱略特细腻入微地刻画了利德盖特的内心挣扎——“不论走哪条路都觉得不是滋味”:赞成布尔斯特罗德所支持的泰克“无异是为自己选择一条方便的道路”,有利于自己参加组阁,但投票给正直能干的费厄布拉泽才符合他内心真实的呼唤。囿于狭隘庸俗的环境,利德盖特无奈选择了前者,为他接下来更为重要的选择——婚姻选择埋下了伏笔,后者与幸福紧密相关。
与赫拉克勒斯一样,利德盖特在人生的岔路口遇到了两位互为对照的女性,即多萝西娅与罗莎蒙德。多萝西娅盘着朴素的发辫,身着淡雅的服饰,却透露出古典高贵的气质,而罗莎蒙德拥有华丽的发型,身穿带绣花大领圈的时尚外衣,完美地诠释了时髦女郎的形象。当多萝西娅出现在时髦女郎中间,仿佛当今流行的报刊文章引用了一句《圣经》的名言或“老一辈诗人的警句”。除了在外表和气质上展现古典与现代之别,多萝西娅和罗莎蒙德眼中的幸福观也大相径庭。多萝西娅喜欢透过“窗户”远眺,超越个人的喜怒哀乐,希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满足他人的需要、促进他人的幸福。罗莎蒙德却经常独自对着“镜子”自我陶醉,将幸福局限于满足个人私欲,即“得到一切最好的享受”。在一定程度上,多萝西娅与罗莎蒙德的幸福观分别象征着强调美德的古典幸福与注重享乐的现代幸福。
爱略特将“幸福即享乐”的现代幸福观巧妙地编织进了利德盖特和罗莎蒙德的婚恋情节中。她有意强调,多萝西娅的求知欲令利德盖特感到不耐烦,显然不符合利德盖特的“口味”。相反,利德盖特却情不自禁地被罗莎蒙德吸引。后者被描绘成“美的化身”,仿佛“一支美妙的乐曲”“真正的旋律”或“一条千娇百媚的美人鱼”,拥有“甜蜜的笑声”与“美丽、蔚蓝的眼睛”等令人愉悦的特质,成为他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典范。利德盖特形容内心“梦寐以求的幸福”(ideal happiness)如同一座迷人的“乐园”(paradise)或“甜蜜的温柔乡”,那里充满了不劳而获的享受。由此看来,罗莎蒙德在利德盖特心中唤起的幸福想象不仅与古希腊神话中愉悦女神向赫拉克勒斯所允诺的感官快乐一脉相承,还彰显了自启蒙时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幸福话语。正如弗洛姆指出的那样,现代人眼中的世界犹如一个巨大的“苹果”、“酒瓶”或“乳房”,只是为了填饱他们的肚子而存在。在爱略特的笔下,以利德盖特和罗莎蒙德为代表的现代人习惯于将世界视作哺育“至高无上的自我”的“乳房”或“充满尘世享受的花园”,这体现了启蒙运动以来“重感受轻责任”的主观幸福论。
《变形记》,图片源自Yandex
需要留意的是,费厄布拉泽提到了两个版本的赫拉克勒斯:英雄赫拉克勒斯和手握纺锤的赫拉克勒斯(distaff Hercules)。除了重释赫拉克勒斯的选择,爱略特还将故事“涅索斯的衬衣”编织进小说情节中,后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作家奥维德《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的《赫拉克勒斯之死》。在奥维德的笔下,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得伊阿尼拉(Deianeira)为了让丈夫回心转意,将染着涅索斯鲜血的衬衣送给他,结果害其身亡。利德盖特曾立志五年内不结婚,向往通过“既高尚又困难的过程”为米德尔马契“做一些小小的好事”,并为世界“从事一项伟大的研究”。但面对罗莎蒙德的诱惑,利德盖特日益沉迷于眼前的短暂快乐,于是违背初衷、仓促地步入了婚姻。在债台高筑的婚姻生活中,利德盖特才逐渐认清罗莎蒙德自私冷漠的真面目,后者时而是他身旁“一股浑浊的泥水”,时而是一株以吸取他人脑髓为生的“罗勒草”。他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但迫于现实为名利行医,供给罗莎蒙德奢侈的生活,最后因疾病早逝。由此看来,利德盖特的不幸婚姻与“涅索斯的衬衣”故事形成了呼应:利德盖特是意志薄弱版的赫拉克勒斯,选择轻松而非艰难的道路,穿上妻子提供的“有毒衬衣”不幸早逝。和奥维德一样,爱略特拒绝对传奇英雄的单一描述,选择同等关注赫拉克勒斯的两副面孔,批判伦理缺失的现代幸福观。

三、“做得好”的幸福

爱略特曾在1879年10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赫拉克勒斯的选择”这一短语,似乎暗示“要不要接受约翰·克罗斯(John Walter Cross)的求婚”正是她当时面临的“赫拉克勒斯的选择”。而在《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的第二次婚姻选择,即“多萝西娅要不要改嫁威尔”,也是小说中最浓墨重彩的“赫拉克勒斯的选择”。
多萝西娅的选择一直以来备受争议,但很少有学者深入讨论这一选择背后的幸福主题。温赖特曾指出,爱略特提倡一种既“活得好”又“做得好”的生活,但她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及多萝西娅与威尔的结合,含蓄地表示两人的结合是一种“充满激情和进取心的婚姻联盟”。多萝西娅的婚姻选择蕴含着爱略特对幸福与美德之关系的深刻反思。具体而言,多萝西娅改嫁威尔的文化意义在于重塑美德与幸福之间的纽带,折射出爱略特对幸福的伦理维度的重视。
首先,多萝西娅和威尔的幸福观均伴随着一份责任感,两人的结合表明爱略特提倡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伊格尔顿曾说,如果将《米德尔马契》看作成长小说,那么威尔的成长在于能够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威尔出场时是一位视人生如假期的享乐主义者。多萝西娅屡次关心威尔的工作选择,希望后者通过认真工作培养责任感。对多萝西娅来说,婚姻并非“个人的安乐问题”,而是一种肩负“更高责任的状态”(a state of higher duties),意味着“新责任的开始”。多萝西娅把婚姻比作走向有益且必要的“工作”的阶梯,她的幸福取决于能否帮助另一半成就事业:“要是我不能在工作(work)上帮助他,我就没有幸福可言。”在小说结尾,威尔成为一名议会成员和社会活动家,以全力以赴的心态对待工作。婚后的多萝西娅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努力发现并承担身边的责任。作为议员的妻子,多萝西娅还有机会协助撰写威尔的议会演讲,从而间接地参与政治,两人的结合隶属“职业婚姻”(vocational marriage)的范畴。
在维多利亚社会,幸福论述经常与“有用的工作”(useful work)相结合,这与卡莱尔所提倡的“工作福音”(Gospel of Work)不无相关。在卡莱尔笔下,赫拉克勒斯摇身一变成为工作福音的化身:“认识你能做的工作,并像赫拉克勒斯一样认真去做”,“工作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安宁”。受卡莱尔影响,当时一本名为《登上巅峰的房间,或如何获得成功、幸福、名望和财富》(Room at the Top. Or, How to Reach Success, Happiness, Fame and Fortune)的自助手册同样将工作福音与幸福伦理相融合:“男人和女人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在有用的工作之外寻找幸福。从未有人在这样的追求中找到过幸福,只要世界存在便永远也找不到。”可以说,多萝西娅改嫁威尔,就像卡莱尔笔下的赫拉克勒斯选择拥抱工作福音,两人将共同投身于伟大事业,努力寻求个人幸福与更大责任之间的动态平衡。
其次,多萝西娅和威尔的幸福观均强调对道德善的热爱,进一步体现了爱略特倡导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例如,小说第39章的题词引用了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作《承诺》(“The Undertaking”,1633):“如果你像我做过的一样,/看到美德(vertue)扮成一位女子,/敢于爱它,而且直认不讳,/不管它究竟是他还是她。”在这一章中,多萝西娅和威尔分享了彼此的信念。多萝西娅坚信“真正的善”能“扩大光明的范围,缩小与黑暗斗争的规模”,威尔也表达了对于“一切善和美的事物”的热爱。基于对“善”的共同爱好,多萝西娅立即表示他们的信念如出一辙。结合第39章的题词与内容,我们不难联想到《赫拉克勒斯的选择》,后者首次将美德拟人化为女性形象。爱略特介入性别政治议题,暗指这位由美德化身的女子既可能是多萝西娅,又可能是威尔。威尔平日里喜欢在贫困人群中闲逛,他送给诺布尔小姐的礼物正是多萝西娅发现自己对他的爱情的起因。此外,威尔拒绝了布尔斯特罗德提议的资助,并打算建议他将这笔钱捐赠给慈善事业,这一举动让多萝西娅整张脸都在“发亮”(brightening),说明威尔的善行得到了她的赞许和肯定。可见,多萝西娅和威尔对彼此的爱情包含并强化了对善的热爱,与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在《伦理学》(Ethics)中的主张相呼应:“一个人为他自己而追求的善或他所爱的善,如果他看见别人也同样追求它,则他对它的爱,将更为持久。”
斯宾诺莎,图片源自Yandex
小说第77章记录了威尔的危机时刻,此时他同样面临着“选罗莎蒙德还是多萝西娅”的赫拉克勒斯式选择。在创作笔记中,爱略特用“多萝西娅,罗莎蒙德与威尔”三个名字概括这一章的内容,有意突出威尔在美德与愉悦之间的拉扯。在该章中,多萝西娅不经意间瞥见以下一幕:罗莎蒙德坐在威尔身旁,“她脸对着他,眼泪汪汪的……而威尔向她俯出身子,握住了她举起的双手,正用轻轻的嗓音热烈地述说着什么”。此刻,威尔背对着多萝西娅,身体向罗莎蒙德倾斜,他的姿势让人想起18世纪英国画家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以“赫拉克勒斯的选择”为主题的画作《悲喜剧之间的加里克》(David Garrick between Tragedy and Comedy,1761)。雷诺兹让加里克的眼神望向表情严肃、衣着端庄,代表“美德”的“悲剧”,身体则被拉向低头含笑、袒胸露臂,代表“愉悦”的“喜剧”,充分暴露加里克的道德瑕疵和内心冲突。在《米德尔马契》中,当罗莎蒙德抛来幸福的橄榄枝时,威尔的内心同样经历了一番撕扯与挣扎,随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正走在危险的边缘,几乎快要投入罗莎蒙德的怀抱。
而正是对善的热爱使威尔顺利度过考验,他的幸福观和多萝西娅一样都包含对他人幸福的关心。当威尔为自己失去多萝西娅的信任而失落时,他仍然主动拜访罗莎蒙德与利德盖特一家,试图增进他们的幸福。他的行动恰恰是多萝西娅所提倡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最主要的幸福,那么别人的幸福还在,那也是值得争取的。”多萝西娅还多次呼吁要“让穷人的生活焕然一新”,“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美好”,表达了对增进共同体幸福的诉求。比起强调个体感受的现代幸福,两人的幸福观显然更接近于古典幸福(eudaimonia),因为后者包含对共同体幸福的关心,也就是说,“对他人的关怀”早已内在于对自身幸福的关切中。我们知道,“行善”是亚里士多德眼中构成普通人福祉的关键要素。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德性是那些不仅按一定方式行动,而且按一定方式感觉(feel)的性情。合乎德性地行动并非像康德后来所认为的那样,是去违背爱好(inclination)地行动;而是根据由德性的培养所形成的爱好去行动”。威尔和多萝西娅时常反思并拷问什么是“真正的善”,并以此不偏不倚地指导自己的行动。可以说,两人的婚姻不啻为善的结合,促进了“世上善的增长”,充分彰显爱略特对幸福之伦理性的呼唤。

四、“活得好”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不仅是万物中最美好、最高尚的,还是最令人愉悦的。“愉悦”是一种“灵魂状态”,每个人的所爱即愉悦,“德行对于爱美德的人就是一种愉悦”;这样一来,那些“做得好”的人的生命本身便带着“愉悦”。同样地,爱略特笔下的多萝西娅和威尔不但积极行善,而且洋溢着生命自身的喜悦与繁荣,两人的婚姻因此折射出爱略特对作为“活得好”的幸福的拥抱。
众所周知,卡苏朋缺乏“坚强的体魄”与“热烈的心灵”,难以体验高度的“喜悦”,这是导致多萝西娅第一次婚姻不幸的关键。多萝西娅和卡苏朋之间的许多琐事使得“喜悦的种子”(seeds of joy)无法生根发芽,两人的婚姻变成“一片荒芜的园地”。相比之下,威尔的笑容仿佛一道“内心的光芒”,透过他明亮的肤色和眼神向外辐射,它在多萝西娅的脸上唤起了愉悦的笑意。正是威尔的出现,让多萝西娅一改从前压抑爱好和轻视快乐的态度,转而热爱世界、享受生活。在第22章中,多萝西娅和威尔进行了第一次促膝长谈。多萝西娅指责艺术游离于大多数人的生活之外,无法真正地改善世界,使得她不能很好地享受艺术。威尔随即反驳“这是同情的狂热症”(fanaticism of sympathy),并对多萝西娅劝诫道:“最可取的虔诚还是在你能享受的时候,享受一切。这样,你就是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拯救世界,把它看作一个愉快的星球(an agreeable planet)。享受应该光芒四射(enjoyment radiates)。想关心整个世界,那是徒劳的。对它的关心只能表现在你对艺术,或者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兴趣上。”
《序曲》,图片源自Yandex
此处,威尔为艺术和快乐辩护,指出多萝西娅的“同情狂热症”不利于实现“更广泛的个人繁荣”,呼应了古典幸福主义(eudaimonism),后者在爱略特的伦理思想中占据比康德的义务论更为重要的位置。考虑到威尔本身颇具浪漫主义诗人气质,他呼吁多萝西娅“享受”生活,不难让我们联想到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常常歌颂的“存在的喜悦”(the joy of being)。根据波特凯的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在华兹华斯身上发现的喜悦主要关乎存在本身:“呼吸、循环血液、感知、感受愉悦、维持生命”,比如华兹华斯在《序曲》(The Prelud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 An Autobiographical Poem,1850)里感叹“我欣喜地呼吸着”,又如他在《写于早春的诗行》(“Lines Writtenin Early Spring”,1798)中写道,“我深信每朵花都享受它呼吸的空气”。以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例,他在《自传》(Autobiography,1873)中袒露自己从华兹华斯的诗歌中收获了源源不断的“内心喜悦”(inward joy)及“和万物一体同仁的愉悦”。爱略特不仅是华兹华斯的忠实读者,还是“浪漫主义的或华兹华斯式的作家”。就像华兹华斯的诗歌教会穆勒重新学会将愉悦的心境与万物相连,威尔鼓励多萝西娅以愉快的眼光看待世界,在自然风景和艺术作品等美好事物中享受喜悦。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joy源自拉丁语gaudia/gaudium,经由法语joie演变,主要用来形容“一种源自幸福感或满足感的强烈愉悦情感”,表示“喜悦的来源或对象”,抑或代表愉悦的、“幸福”(happiness/felicity)的状态,尤其是天堂的至福。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的《英语词典》在解释joy一词时已经调用了happiness这个概念,可见这两个词的亲近关系,但两者又不尽相同。作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核心字眼,“喜悦”(joy)从内心满溢而出,又像雨水从天而降,它既是一种主观隐秘的个人力量和财富,又主张超越自我关切和私人忧虑,寻求与更大世界的普遍喜乐相融合。在第62章里,爱略特运用一连串joy形容多萝西娅确认自己和威尔相爱的心境:“最先是喜悦”,“喜悦还是喜悦”,“喜悦并未由于无可挽回的分离而减少,也许还变得更完满了”。就这样怀着喜悦的心情,多萝西娅坐上了马车:
车夫习惯于驾着灰色马飞跑,因为每逢卡苏朋先生离开了他的书桌,便对什么都不感兴趣(unenjoying),对什么都不耐烦,每次旅行都想尽快到达终点;现在多萝西娅便沿着大路在飞驰。坐在车上是愉快(pleasant)的,夜里下过雨,路上没有飞扬的尘土,蔚蓝的天空一望无际,只有一处有着大朵大朵的乌云积攒在一起。大地(the earth)像笼罩在蓝天下的一片乐园(a happy place)……
这里,卡苏朋和多萝西娅对于马车旅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只在乎目的地,无异于约翰逊口中的“从一个事物迅速驰向另外一个事物”,而后者却自发地享受大自然,和“蔚蓝的天空”、“乐园”般的大地共享生命的愉悦与繁荣。多萝西娅用形容词“幸福的”(happy)来描绘“大地”,恰好应和了前文威尔所倡导的世界好比一颗“愉快的星球”。从多萝西娅坐马车时的所观所感不难看出,爱略特把喜悦刻画为理解自然的产物,呼应了华兹华斯在《丁登寺》(“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1798)里描述的自然界中的“一种存在”,它孕育着“高尚思想的喜悦”,栖居于“落日的余晖”和“蔚蓝的天空”等万物中。波特凯指出,华兹华斯对“喜悦”的歌颂流淌着斯宾诺莎的影响,后者强调理解上帝或自然的智性喜悦,主张幸福或德性以保存自我存在为基础:“一个人愈努力并且愈能够寻求他自己的利益或保持他自己的存在,则他便愈具有德性……自我满足(self-contentment)实在是我们所能希望的最高的对象。”爱略特细腻地描述多萝西娅通过观察自然感受存在的喜悦,同样折射出华兹华斯、斯宾诺莎等人的影响。
柯勒律治,图片源自Yandex
除此以外,爱略特将喜悦与音乐相连,赋予喜悦以审美内涵。譬如,对威尔而言,倾听多萝西娅说话好比聆听她的“心与灵魂”演奏的音乐,犹如“风弦琴”(the Aeolian harp)一般赐予他“独特的愉悦”(unique delight)。巧合的是,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曾发表《风弦琴》(“The Eolian Harp”,1795)一诗,在诗中把风弦琴比作被清风爱抚的娇羞少女,形容琴声所到之处皆是“欢愉”(joyance)。柯勒律治还在《沮丧颂》(“Dejection:An Ode”,1802)中把喜悦比作“圣洁的女神”(virtuous lady),为灵魂带来“高昂的乐曲”,传来阵阵“甜蜜的声音”。柯勒律治通过诗歌书写“审美喜悦”(aesthetic joy)的价值,相信关乎音乐或艺术的喜悦能以一种最有益的方式使人超越自我。爱略特以小说语言诠释喜悦的审美性,强调威尔总是能为多萝西娅的心灵带来喜悦的音乐,给予她无惧流言蜚语的力量,体现了柯勒律治的影响。可以说,威尔不仅为多萝西娅的生活注入了喜悦,还帮助她领悟到喜悦的审美价值,引导她走向富有艺术气息的生活,折射出爱略特对“活得好”的幸福理念的认可与宣扬。一言以蔽之,多萝西娅选择改嫁威尔不仅仅是拥抱美德的伦理选择,更是拥抱生命繁荣的幸福选择,两人的结合可以看作是爱略特化用古典幸福主义思想谱写的一曲赞歌。

结 语

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深入探讨美德与幸福的关系,诠释了古典幸福观和现代幸福观之间的分歧。通过改写“赫拉克勒斯的选择”,爱略特反思现代幸福的伦理缺失,重塑美德与幸福之间的纽带,揭示了以“活得好”和“做得好”为核心内涵的美好生活。爱略特对幸福的深度思考和穆勒不谋而合,后者深谙“赫拉克勒斯的选择”的教训,将热爱美德视作公众幸福的首要条件,努力调和“快乐生活”(pleasurable life)和“道德生活”(moral life)的关系,鼓励人们像“高尚但道德脆弱的”赫拉克勒斯一样勇敢追求反映这种双向关系的生活。和穆勒一样,爱略特寻求快乐生活与道德生活的有机融合,她的小说印证了波特凯的观点:19世纪美德和幸福之间的关联性依然清晰可见。
在维多利亚时代,卡莱尔、阿诺德(Matthew Arnold)、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罗斯金(John Ruskin)和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文化批评家们纷纷强调“生活质量”在于“精神与物质的互补和平衡,更在于心灵的尊严和高贵”。通过小说创作,爱略特介入维多利亚社会的“幸福话语”建构,亦即参与文化批评语境的建构,这正是小说的深度之所在。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曾这样评价简·奥斯汀(Jane Austen):正是因为奥斯汀将“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主题”统一在一种确定的社会语境之中,才使得她成为美德传统的“伟大而富有想象力”的声音。现在看来,用这句话形容爱略特也不为过。
相关链接
往期回顾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 点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