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苏萝

圣埃克苏佩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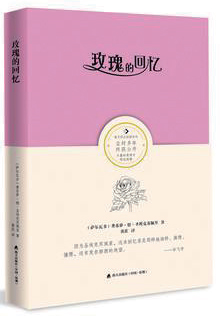
一直很喜欢法国飞行员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因为他的文字有一种既崇高又稚气的美,像高山上的空气,很干净、很纯粹。2000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收到了法文版的《玫瑰的回忆》。书看得很快,我很投入,仿佛“玫瑰的故事”打湿了自己曾经的岁月,心房里涨满了许多莫名的哀伤。忽然有一种念头,觉得这本书就是我的,我一定就是它的中文译者。我曾经也翻译过不少东西,但很奇怪,第一次有这样一种感受:希望这些文字能从我的心里、我的手上流淌出来,像音乐,像一首不压韵的诗。
出版社买到版权后,它果真是我的了。我一路跑着,顾不上看两边的风景,龚苏萝和圣埃克苏佩里的故事就这样占据了我的头脑,不管我愿不愿意,书中的一些文字就在嘴边,仿佛一不小心就要溜出来。这就是征服,被这本书完全征服。我不由自主地想哭,想在别人的故事里忘了自己,天地间似乎就只剩下那朵单薄的玫瑰,那么美丽,那么孱弱。
作为圣埃克苏佩里的妻子,龚苏萝身上维系了太多的传奇和令人费解的谜。1927年,这个来自中美洲萨尔瓦多、像“小火山”一样倔强的女子应阿根廷官方邀请,越洋来参加第一个丈夫戈麦兹·卡利洛的葬礼。在朋友的介绍下,龚苏萝结识了当时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负责南美洲邮航的圣埃克苏佩里。像大男孩一样的飞行员对这位优雅、美丽、执拗的“岛上小鸟”一见倾心。龚苏萝也被圣埃克苏佩里在飞行间隙写的文字深深打动。
于是交汇时互放的光芒把两颗像星星一样的心灵维系在一起,天上的童话吸引着他们,龚苏萝有孩子般的单纯和执著,圣埃克苏佩里有孩子般的天真和任性。两个人的世界一开始就是潮湿的,圣埃克苏佩里哭着说:“您不吻我,是因为我长得丑”;龚苏萝怀里揣着天上的大鸟写给她的情书,哭着在教堂向上帝寻求感情的答案;在市政厅结婚登记处,圣埃克苏佩里又哭了,“我不能在远离家人的地方结婚”……感情一直是咸的,因为有太多的泪水。1931年,两人终于走上了结婚的礼堂,但幸福似乎总是和他们失之毫厘,仿佛两人从来就没有为这个婚礼真正准备好一样。
回到巴黎,圣埃克苏佩里成名了,《夜航》荣膺费米娜奖,接踵而至的是荣誉、鲜花和不胜其烦的应酬,但光荣只属于丈夫一人。妻子被冷落、被排挤,她躲在自己的角落织补破碎的心灵,灰姑娘嫁给了王子,但没有像童话中写的那样成为公主、回到城堡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女崇拜者温柔的包围中,有的是做妻子的龚苏萝寂寞的失眠和苦涩的泪水。不是彼此不爱,只是相爱的方式不对;不是彼此对对方不好,只是有外界太多的喧嚣介入到二人的世界。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圣埃克苏佩里一直就没有真正长大。他不会设计生活,没有丝毫的经济头脑;他出尔反尔,今天让妻子找了公寓、交了定金,明天就可以毁约,事前不和妻子打一声招呼,自己一个人飞到地角天边。不知道为妻子设身处地,于是无知的错误里有一份残忍,但龚苏萝承受了,绝望中总是希望着、等待着,等待夜航的结束,等待情感的黎明。
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他不想失去的东西就绝不放手。他自己拈花惹草,却多次阻止龚苏萝嫁给别人。1944年,圣埃克苏佩里在二战一次侦察任务中飞机坠入大海,和小王子一样,永远地消失在地平线上。留下那朵他生命中最爱的玫瑰,如他在《小王子》中所说:“我太年轻了,不知道如何去爱她。”
生活在传奇里,他们的故事有很多超出常人想象的点滴。为什么爱得这么深,这么痛,这么彻底,又这么伤心?从拉丁美洲到法国,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西班牙到非洲,穿越时空的爱恋,聚散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只有爱没有理由。托尼奥说“来,龚苏萝,我需要你”,于是她来了,不远千里,像一个宽容的母亲永远无法放弃自己的孩子;托尼奥说“走,这里没有你的位置”,于是她蜷在心灵黑暗的角落哭泣。丈夫死后,在流落美国的孤独中,龚苏萝用她松散、倾斜的字体,写下她和作家-飞行员的生活。后来,她将手写稿用打字机打印在薄薄的纸上,笨拙地将它们用黑色的硬纸板装订起来。她记录的只是她和爱人的生活,不想评价是非对错,那是她作为“玫瑰”的回忆。
文稿在她死后留下的行李箱里一搁就是25年,她一直深爱着丈夫,以属于她的方式,怀念过去的幸福和辛酸,用沧桑过后的宁静和笑容。龚苏萝就是那朵有四根刺的玫瑰,她以为自己很坚强,能照顾自己,可以用她的刺从容应对人生,但刺刺痛更多的是她自己稚嫩的心灵,因为骄傲。如今,一切都平息了,在回忆里,她收敛了刺,用质朴的笔触写下她和圣·艾克斯的故事。别人的评说,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就这样,《玫瑰的回忆》在圣埃克苏佩里百年诞辰的时候得以重见天日。它是一份从另一个角度见证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记忆,给我们开启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飞行员作家夫妻生活的内情,让我们接触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圣埃克苏佩里:不仅有他天才迷人的一面,也让读者看到翅膀合上后,天上巨人懦弱、不成熟甚至冷酷的一面——“人”的一面。